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南向政策」-這一個政治以及國家策略的想像,對於我們建築人來說,到底暗示的是甚麼呢?西方殖民觀點下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雖早已在時光中被逐步抹去,但如今南亞再度被凝視的價值,則由資源的提供者成了市場開發的潛力者。但是南亞真的這麼「不堪」嗎?她只是一塊提供補足世界市長擴張達到瓶頸的處女地,只因為她的人口眾多,以及多數區域地緣政治逐步走向市場經濟的原因嗎?在台灣政治術語中的「南向政策」其根本用字「向」果真提倡的概念還正是一種積極的經濟侵入,這個「向」絕對不是一種凝望下的學習,一種被動、輕柔的觀摩想像。
最近許多東南亞的建築觀察團帶回的確是令然讚嘆;越南的武重義竹構造真的令人驚艷、馬來西亞林錫山的熱帶建築風情令人神往、楊經文的生態建築推演想像的創意啟發…還有在泰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等國家首都中出現的超級現代大師作品。然而我想像的相互學習的「南向」並不在只是「哇!」的感受,而在於提供我們建築師們面對自我創作過程中,給予對話他者的機會。而東南亞南向的對話儼然已成為重新思考地域性另一個開啟的窗口,其原因有二:(1)由批判性地域主義開啟的地域觀,過去常理論化的對於在地材料的一味熱情,隨著時代的變化也面臨何謂在地材料以及老式工藝技術喪失後,在地材料已急需新的詮釋機會;而東南亞年輕建築的實驗性提供了不僵化下的地域觀點頗令人值得玩味。(2)許多在地年輕建築師們在一股頗具時間感中體會身體、建築和自然間的互動;他們的建築提供一種不可言喻的地點氛圍。對於台灣逐步都市化而都市和鄉間兩極中的分野狀態中,台灣建築師們似乎習慣了將自然當成造景的工具,而非生活伴隨的一部分。對於更加具自然性的許多東南亞建築師作品中,我們看到一股有趣清新的地點文化想像。
我選擇了馬來西亞建築師團體窩工房(TETAWOWE)以及WHBC的各三個作品,和台灣的寬和、和光接物以及深宇建築師事務所的幾件新案作對話。台灣的幾個案子基本上都位於郊區,可看到的是這幾年逐步成功的幾種設計實踐:多元的材料組合、細膩的細部、木頭建構或內裝的建構、物理環境以及自然植栽的使用、以及在地紋理的連接等。而馬來西亞案則看到混凝土的強大表現性、熱帶性的物理環境性、金屬的大量使用、植栽的使用等等特性。我想任何一位觀察者不須過多被指引,但卻都能看出相似以及極為不同的空間質感;這一部分引介的「對話」應頗能有激發相互間的凝望。
就在去年的2月27日,著名的建築師修澤蘭病逝於大陸。11月教育部為中山樓建成五十周年頒發感謝狀給傅積寬先生(修澤蘭丈夫)。也約莫在同時網路上傳來姜樂靜建築師對於修女士已經過世一事感到不可置信,因為包含公會、建築相關雜誌、以及主流媒體似乎都未曾報導。對於這一位傳奇人物的過去,而我們的無感確實不可思議。但礙於學界對於修澤蘭研究的確很有限,《TA》唯一能做的是在這「健忘成性」時代下的修補一點我們受損的記憶。由殷寶寧及徐明松老師等人提供的幾許觀察論述,配合由殷老師協助下所編輯出來的一份「修澤蘭經典20」圖文版。 我個人是期待有人能拿這一份資料去走讀僅剩下的十八座經典,看看在那遙遠年代中台灣最強女建築師到底做了甚麼有趣的事。但或許誠如另一位建築大老所言,修澤蘭真正絕佳的原創作品不多(十五件吧!),但觀察她所建成的「世界」也算是觀察我們自己血脈中的一條紋理-深刻且動人。
總編輯褚瑞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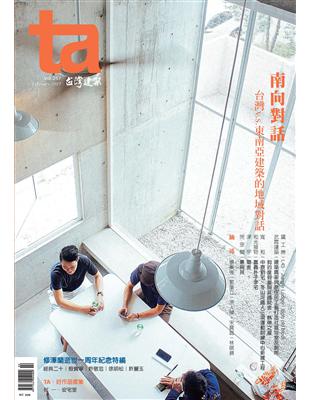

 收藏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