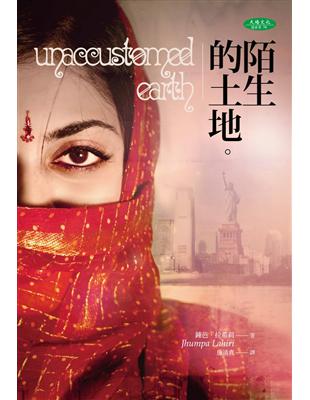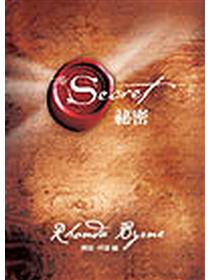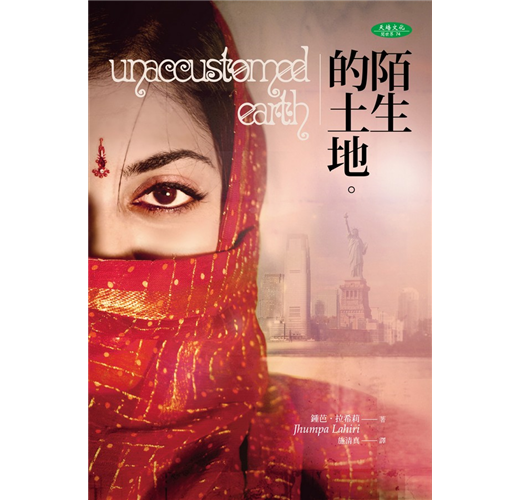只是好意
是素妲哈讓拉霍爾頭一次接觸到酒。她在賓州大學讀書的某個週末,就讀於高三的拉霍爾來訪,他從啤酒桶中喝下生平第一口酒,隔天早上在學校餐廳喝下生平第一杯咖啡,他斷言兩種飲料都令人作嘔,還說他比較喜歡杜松子酒,而非啤酒,然後倒了十幾包糖到咖啡裡。隔年夏天、她回家時,他打算趁他們爸媽到康乃狄克州過夜的時候開派對,請她幫他買幾箱半打裝的啤酒。他已經突然長高到一百八十公分,不再戴著牙齒矯正器,嘴巴周圍長出了鬍渣,兩頰偶爾冒出暗色的青春痘,他已是她徒有其名的「小弟」。她去一趟附近的酒類販賣店,幫拉霍爾把啤酒分別藏放在他和她的房裡,這樣他們爸媽才不會發現。
爸媽睡了之後,她帶了幾瓶啤酒到拉霍爾房裡,他偷偷溜下樓,取來一杯冰塊幫溫溫的百威啤酒降溫。他們分喝了滿滿一杯啤酒,然後又喝了一杯,邊喝邊聽拉霍爾唱盤上播放的「滾石」和「門戶」合唱團唱片,兩人站在開著的窗戶旁偷偷抽菸,透過紗窗吐出白煙。素妲哈好像又回到高中時代,做著一些她沒膽量、也沒有那種小聰明想得出來的事情。她感覺跟她小弟形成了一種新的默契,那種感覺就像是經過多年只把他當個小孩後,她和弟弟終於成了朋友。
素妲哈上了大學才敢違逆爸媽。在那之前,她照著他們的期望而活,她勤奮向學,僅跟班上其他乖女孩交朋友,只求確保將來有一天能夠得到自由。來到賓州、脫離爸媽監控後,她認真讀書,主修經濟和數學,但週末的時候,她放鬆自己,參加派對,跟男孩子上床。她開始喝酒,而這正是她爸媽不會做的事。他們對於含酒精的飲料非常謹慎,幾乎像是滴酒不沾的清教徒,他們也看不順眼那些喜歡在社交場合啜飲威士忌的孟加拉朋友們,也就是指孟加拉男士們。大一的時候,有些晚上她喝得爛醉,醉到在街上大吐特吐、弄髒了人行道、跟朋友們跌跌撞撞走回宿舍。但她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裡,素妲哈不喜歡失控的感覺,基本而言,能力與幹練才是她的人格特質。
拉霍爾高中畢業後,他們爸媽認為這下已經成功在美國養大了兩個小孩,欣喜地大肆慶祝。拉霍爾將到康乃爾大學讀書,素妲哈仍在賓大,準備攻讀國際關係的碩士學位,他們爸媽辦了個派對,邀請了近兩百名賓客,而且買了一部車給拉霍爾,理由是他在綺色佳(Ithaca,譯註:康乃爾大學所在地)需要用車。他們吹噓兒子進了康乃爾大學,康乃爾顯然比賓州大學更讓他們印象深刻。「我們的任務完成了。」派對結束時,她爸爸一邊感嘆、一邊把拉霍爾和素妲哈拉到身邊照相。多年以來,他們始終被拿來跟其他孟加拉小孩相比,爸媽時常告訴他們誰拿了科學展覽的金牌、哪所大學提供全額獎學金,素妲哈的爸爸有時從報上剪下天才青少年的報導,諸如二十歲念完博士的男孩、以及十二歲就進入史丹福大學的女孩,並把剪報貼在冰箱上。素妲哈十四歲時,她爸爸寫信給哈佛醫學院要了一份申請表格,而且把表格放在她桌上。
素妲哈立下了榜樣,讓爸媽知道孩子離家上大學沒什麼好擔心的。拉霍爾也應付自若,不像素妲哈上大學前的那個暑假一樣焦慮。他對於即將面臨的改變幾乎無動於衷,那種態度讓她想起他向來比她聰明。素妲哈以前竭盡全力名列優等學生之列,確保自己成為畢業生致辭代表,但拉霍爾從來毫不費勁,除非有興趣,否則他從來不翻開書,而且早慧到了跳過三年級的地步。
夏末時,素妲哈回家幫他打包,但到家之後,她發現自己沒事可做。他已經塞滿皮箱、把唱片裝進一些牛奶箱裡、從收放餐巾桌布的櫥櫃裡拿了毛巾和床單、將電源線繞著打字機收好,他跟她說她不必大老遠去一趟綺色佳,但她堅持坐上他的新車,跟他一起開車過去,他們爸媽尾隨其後。康大校園位居山坡坡頂,農場、湖泊和瀑布環繞四周,景觀跟賓大完全不同,她幫忙卸下行李,跟著其他大一新生的家人一起搬著箱子穿過方庭。說再見的時候,他們的媽媽哭了,素妲哈想到把不滿十八歲的小弟拋棄在這個偏遠、宏偉的地方,也不禁輕輕拭淚,但拉霍爾沒有表現出被拋棄、或是獲得自由的模樣,他接下大家告別時、爸爸點數交給他的錢,素妲哈和爸媽還沒有駛離校園,他已經轉身走向宿舍。
她再次見到他的時候是聖誕節。晚餐時,他對於所修的課、教授、或是新交的朋友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他的頭髮已經長到蓋住脖子,隨便塞到耳後,他穿著一件格子法蘭絨襯衫,手腕戴著一條多結的繩編手環,他不像素妲哈一樣,一坐上媽媽的餐桌就大吃特吃,他似乎感到無聊。當素妲哈和媽媽用她和拉霍爾小時候製作的吊飾裝飾聖誕樹時,他只在一旁觀看,而沒有動手幫忙。素妲哈記得自己聖誕節假期的時候似乎總是患了感冒,考試的壓力一解脫,她整個人馬上癱了下來,她以為拉霍爾說不定也一樣,但那晚稍後,他看著她在樓上房裡包禮物,精神似乎不錯。「嗨,妳把那東西藏在哪裡?」他問。
「藏什麼東西?」
「別跟我說妳空手回家。」
「喔!」這下她明白他的意思,「我沒想到這一點,我以為既然你已經上大學……」這是實話,這回她沒想到塞半打啤酒到包包裡。她現在比較喜歡葡萄酒,她在賓州跟朋友出去吃晚飯時小酌一杯,但回到衛藍德的家中時,她可不期望有酒可喝。
「我年紀還是不夠大,在這裡什麼都不能買。」他環顧四周,好像房裡說不定藏了他在找的東西似的,逕自過去看看她的衣櫃、五斗櫃抽屜、以及堆滿包裝紙的床上,床上有個百貨公司的盒子,盒裡擺著一件她幫媽媽買的睡衣。
「去一趟酒類販賣店吧?」他邊說邊在床上坐下,弄皺了一些她已經捲開的包裝紙。他的手撥弄禮物的標籤和膠帶,一樣樣拿起禮物,然後再一樣樣放下。
「現在?」她問。
「不然妳晚上有其他事情嗎?」
「嗯、沒有,但如果我們忽然出去的話,媽爸會覺得奇怪。」
他擺出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姊,拜託喔,妳快二十四歲了,妳真的在乎他們怎麼想嗎?」
「我剛剛正要換上睡衣。」
他拿起剪刀,凝視著慢慢開合的刀刃,好像頭一次發現剪刀的功用般。「妳什麼時候變得這麼無趣?」
她知道他在開玩笑,但這番評論依然讓她難過。「明天吧,我保證。」
他站起來,又變得跟晚餐時一樣疏離,她感到自己心意動搖。「好吧,我想店還開著。」她看著手錶說。就這樣,她跟爸媽謊稱必須趕緊去一趟購物中心,然後跟著拉霍爾一起出門。拉霍爾說他開車載她過去。
「妳最正點。」他們朝向鎮上前進時,他跟她說。他搖下他那邊的車窗,讓車內充滿冰冷的空氣,然後從大衣口袋裡摸出一包香菸,他用儀表板上的打火機點燃香菸,問她要不要也來一支,但她邊搖搖頭邊調高暖氣。她告訴他,她已經申請明年去倫敦政經學院攻讀第二個碩士學位。
「妳要去倫敦一整年?」
「你可以來找我。」
「妳為什麼需要另一個碩士學位?」他聽來有點難過,也不太贊同。她預期爸媽會有這種反應,爸媽當初不准她到牛津讀大三,他們說她太年輕,不能一個人住在國外,但現在他們卻很高興素妲哈要去倫敦,他們剛結婚的時候住在倫敦,素妲哈也在倫敦出生,他們甚至打算去看素妲哈,順便看看幾個老朋友。
她解釋倫敦政經學院的發展經濟學非常知名、她將來想幫「非政府組織」工作等等,但拉霍爾似乎沒聽進去。她生他的氣,其實也氣自己同意這麼晚跟他一起出來。「你要半打啤酒?」他們開到酒類販賣店時,她問道。
「一打更好。」
以前她想都不想就付帳,但現在她注意到他沒有伸手到口袋裡拿錢。
「還要一瓶伏特加。」他加了一句。
「伏特加?」
他從香菸包裡抽出另一支菸。「這個假期很長。」
等到他們回家時,爸媽已經上床睡覺,但素妲哈堅持像以前一樣把東西藏起來。她想拉霍爾在家的這幾個星期,媽媽說不定會找個理由進去他房間打掃、或是收放洗好的衣服,所以她把酒擺在她房裡。衣櫃後面藏了幾罐,書櫃後面的縫隙藏了幾罐,另外再拿一件毛衣把洛伏特加包起來,藏在五斗櫃抽屜裡。她告訴拉霍爾這樣比較保險,他卻似乎不在乎。他拿了幾罐晚上喝,離開前輕輕吻她臉頰一下,當她說她太累、不跟他一起喝的時候,他也沒有堅持相邀。
他出生的時候素妲哈六歲,而素妲哈這輩子最初記得最清楚的事,就是媽媽生產的那個晚上。她記得當時在爸媽一個孟加拉朋友家中參加派對,爸爸必須直接送媽媽去醫院,沒空回家拿素妲哈幫忙整理的小皮箱,皮箱裡裝著媽媽在醫院用得上的牙刷、面霜和睡袍。因此她被留在爸媽朋友家過夜。雖然素妲哈知道有個小寶寶即將誕生,小寶寶有時好像要踢破媽媽肚皮的時候,她也伸手摸摸、感覺到小寶寶的存在,但看到媽媽額頭頂著牆壁呻吟,她依然非常害怕媽媽快死了。「走開!」素妲哈試著輕拍媽媽的手,媽媽卻大聲斥喝,那種聲調令人心痛。「我不要妳看到我這種樣子。」她爸媽離開後,派對繼續進行,大人們吃晚餐時,素妲哈照常跟其他小孩在地下室的洗衣機和乾衣機之間玩耍,派對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沒有小孩,素妲哈睡在客房的一張小床上,房裡除了一個燙衣板、和只能清洗用具的櫃子外,沒有任何家具。隔天早上,她沒有家樂氏香甜玉米麥片可吃,而只有吐司和果醬,她跟大人們吃了一頓令人失望、萬分拘束的早餐,就在這時,電話響了,傳來她弟弟已經出生的消息。
她一直希望有個妹妹,但依然很高興自己不再是唯一的小孩,也很高興有了另外一個人幫忙填補她在爸媽家感受到的空蕩與空虛。爸媽擁有的少數幾樣東西總是擺在原位,最新兩期的時代雜誌總是放置在咖啡桌上同一個地方。素妲哈比較喜歡她美國朋友們的家,這些朋友的家裡堆滿了東西,水槽沾上一層厚厚的牙膏,軟軟的床也沒有鋪好。拉霍爾出生後,家裡終於出現同樣的髒亂與擁擠:衣櫃上堆滿嬰兒油和尿布,爐子上擠放著鍋子和煮燙的奶瓶,每個房間充滿嬰兒強烈的奶味。她記得自己好興奮,她把她房間裡的東西移到一邊,挪出空間放拉霍爾的搖籃車、換尿布的桌子和小蜜蜂玩偶,最後總會派上用場的嬰兒床裡堆滿了玩具和其他禮物。她最喜歡一隻白色的兔寶寶,你若轉動兔寶寶脖子上的鑰匙,它就會唱歌。她不介意媽媽半夜進來房裡坐在搖椅上、輕唱孟加拉童謠哄拉霍爾睡覺,素妲哈聽著那首小男孩的腳被魚刺刺到的童謠,聽著聽著也再度沉沉入睡。他們在藥妝店買了出生卡,卡片是素妲哈選的,她還幫忙把卡片裝進信封、跟爸爸一起用溼海綿沾溼郵票。他們照了好多照片││拉霍爾在搖籃車裡睡覺,拉霍爾在塑膠盆中洗澡││她自行把照片放進一本特別的相簿裡,相簿的封面是藍色牛仔布,因為拉霍爾是個男孩。
在素妲哈還是小寶寶時沒有留下同樣紀錄。她出生後,她爸媽在倫敦的巴林區租了兩個房間,房東是一位名叫帕爾先生的孟加拉人,素妲哈幾張僅存的小寶寶照片就是房東先生拍的。照片中的她穿著一件白色的蕾絲邊洋裝,洋裝本來是件受洗服,但她媽媽覺得很漂亮,所以買了下來。她爸媽本來跟一位英國老太太租房子,但房東太太不准家裡有小孩,幸好帕爾先生在她媽媽懷孕的時候接納了她爸媽。爸媽告訴她,在六○年代,倫敦一半的出租房屋都「只限白人」,他們是印度人,再加上她媽媽懷了身孕,情況糟到她爸爸考慮把她媽媽送回印度生產,直到他們遇見帕爾先生,問題才迎刃而解。對素妲哈而言,這個故事像是希臘神話、或是聖經故事,充滿了祝福和預兆,讓她的家人們成了奇怪而凶險海域中的倖存者。
四年後,她爸爸從獾式企業調到雷神公司,全家搬到麻州。他們沒有帶走任何曾在倫敦生活的紀念品,除了她媽媽每天早上喝茶配麥維他小餅乾、以及一輩子堅信英國胸罩的品質、經常請在英國的朋友代為選購之外,看不出他們曾經住在倫敦。素妲哈的玩具沒有一件跟著來到大西洋彼岸,小寶寶童裝、床具和任何型式的紀念物品也全都留在英國。上幼稚園的時候,老師請素妲哈向全班展現她從小到大的紀念物品,其他同學帶來毛毯、磨破了的鞋子以及變黑的湯匙,她卻只有一個信封,信封裡裝了幾張帕爾先生拍的照片,她站在教室面前展示照片時,同學們都覺得沒意思。
拉霍爾出生後,這些全都無所謂。以前沒有人重視素妲哈,但她下定決心讓小弟像個美國小孩,留下種種成長印記。她幫他尋找種種適宜的玩具,從二手市集覓得動物農莊、玩具卡車、發出動物聲音的有聲玩具、以及其他在朋友們的遊戲房裡看到的玩具。她請爸媽幫小弟購買以前一年級老師念給她聽的故事書,比方說《彼得兔》和《青蛙與蟾蜍》。「買書給一個不會閱讀的小孩幹什麼?」她爸媽問。這個問題問得有道理,所以她從學校圖書館借來故事書,自己讀給拉霍爾聽。她請爸媽在草坪裝上自動灑水系統,好讓拉霍爾夏天在水柱間跑來跑去,她也說服了爸爸在後院設置鞦韆。萬聖節時,她費心把他裝扮成一隻大象、或是一個冰箱,她自己卻穿戴隨便買來的簡陋圍裙和單薄面具。有時她比拉霍爾更在乎他自己的成長過程││雖然到了那時她已經太大、不適合坐鞦韆,但放學之後在後院盪鞦韆的卻是她,花好幾小時用積木堆出城鎮的也是她,爾後拉霍爾小手隨便一揮,整座城鎮就毀了。
雖然她喜歡他、寵愛他,但在一些小地方,她也開始嫉妒他。她嫉妒他四肢修長,她自己卻從初經來潮之後就有點圓胖;她嫉妒人們可以叫他「拉夫」,在人群中,他可以安然介紹自己,不必受到詢問;她嫉妒他長相俊美,即使當他年紀還小,大家就清楚看出他將來會是個英俊的男子。他的臉完全違反了家族遺傳,素妲哈的下巴跟她爸爸一樣圓滾,髮線跟她媽媽一樣低垂,一看就知道是她爸媽的孩子,但拉霍爾長得只有一點像爸媽,他的基因顯然來自其他更久遠、被人遺忘的祖先,他的膚色較深,顯然是深棕色,五官輪廓鮮明,不像她和她爸媽一樣含混不清。他夏天可以穿短褲,也可以在學校參加運動競賽,而她媽媽卻認為女孩子做這些活動不恰當。素妲哈認為拉霍爾是男孩子,再加上他是老二,更何況到了那時,爸媽比較習慣美國的生活方式,因此,爸媽對拉霍較為放任。素妲哈並不喜歡年輕時的自己,也不懷念她以前的模樣、或是她做過的事情,她只覺得遺憾,卻說不出究竟遺憾些什麼。她以前看起來當然相當普通,一頭黑髮綁成兩條豬尾巴小辮子、或是馬尾辮,一年長髮及腰,下一年卻剪成跟桃樂絲•漢彌爾(Dorothy Hamill,譯註:美國花式滑冰選手,曾為一九七六年冬季奧運女子花式滑冰冠軍)一樣的髮型。她做的事情也相當平常:參加睡衣派對,在學校樂團吹奏黑管,挨家挨戶販賣巧克力糖。但她卻無法釋懷:即使已經成年,她仍希望能夠回到過去,改變一些事情,比方說,以前穿過的那些醜衣服、以前心中的不安全感、以前曾犯下的無心之過。
多虧了拉霍爾,家裡多了另一個人見證爸媽令人困惑的婚姻。他們不是不快樂,但也稱不上開心,而且從未表露出任何快樂或悲傷的情緒,這才是最讓素妲哈生氣的一點。她能理解父母吵架,甚至可以理解離婚這回事。她始終希望爸媽會流露出某些相愛的跡象,但足可告慰的只有幾張他們在倫敦時拍的照片。照片中媽媽瘦得讓人認不出來,頭髮是上美容院梳的,手肘挽著一個羊角形狀的皮包,連她那時候穿的紗麗都比較亮麗,褐色細紋、蠟染布製成的紗麗緊緊裹著她的身體,炫耀她的身材。爸爸穿著西裝、繫著黑色窄領帶、戴著太陽眼鏡,看起來似乎稍微摩登。素妲哈猜想,在那段日子裡,家家戶戶有個煤油暖爐,人人生平第一次看到雪,移民生活依然是個冒險。
衛藍德則令人震驚。忽然間,她爸媽察覺自己這輩子逃脫不了身為外國人的命運,興起了被困住的感覺。在倫敦的時候,她媽媽忙著攻讀蒙特梭利教育的證書,但搬到美國後,她沒有工作,也不開車,拉霍爾出生後,她媽媽胖了二十磅,她爸爸則收起摩登的西裝,改到平價百貨公司席爾斯購物。他們在衛藍德變得消極而謹慎,這個英格蘭小鎮的風俗習慣比在世界兩大城市謀生更令人困惑。他們倚賴他們的小孩,特別是素妲哈。她得跟爸爸解釋他必須把落葉裝進袋中,而不是只用耙子把葉子掃到家裡對面的樹林裡。她說得一口流暢的英文,因此打電話給百貨公司的維修部門、請他們派人過來維修家電用品的也是她。拉霍爾從來不認為他必須對爸媽提供這些協助,在素妲哈看來,爸媽對印度的思念好像一種慢性病,宛如患了癌症一樣時好時壞,拉霍爾在這方面卻不假以顏色。「沒有人強迫他們來這裡。」他常說,「爸為了賺錢才離開印度,媽沒有其他事情可做,所以跟他結婚。」拉霍爾就是這樣:他始終知曉家裡每個人的弱點,從來不讓素妲哈逃避她最不想面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