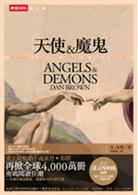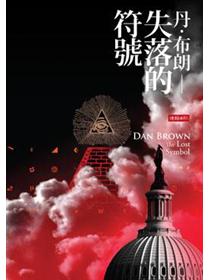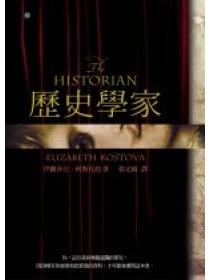防禦
人物往往會嚮往或抗拒追尋,若他們倡議追尋,便被譽為英勇或純潔的化身;若橫身阻攔,便被刻畫為邪惡或懦弱。
因此每個典型人物……常有他道德上的敵對,就像棋局中的黑子與白子一樣。
──《批評的剖析》諾斯洛普.弗萊
一七九○年春 法國蒙特格朗修道院
一群修女穿街而過,鮮潔的頭巾像海鳥的長翼般在頭上翻揚。修女們行經鎮上的巨大石門時,雞群和鵝群便急急閃到路邊,撲撲亂拍地踩過泥灘。她們穿過山谷中日日聚攏的晨霧,成雙成對地默默朝山頂傳來的鐘聲行去。
她們稱那泉水叫血泉 ─ le Printemps Sanglant。那年的櫻桃花開早了,遠在高山的積雪融化前便已開放,濕紅的花朵將細嫩的枝條都壓彎了。有人說,花兒開早是好兆頭,象徵漫漫嚴冬後的重生。可是接著下了幾場寒雨,枝上的花兒全受了凍,山谷裡蓋滿了染著褐色霜痕的紅花,彷若血跡乾涸的傷口。有人說,那也是另一種徵兆。
蒙特格朗修道院像顆突起的巨石,聳立在山谷頂的稜脊上。近千年來,這棟狀似堡壘的修道院一直與外隔絕,六、七層的牆圍層層疊疊,最原始的石歷經數百年的歲月後,早已經傾頹了。新的圍牆沿舊牆外而築,並且添上了飛扶壁。這是一棟建築的大雜燴,當地人對建築的模樣有著各式各樣的傳聞。蒙特格朗修道院是法國境內最古老完整的教堂建築,它背負了一道亙古的咒詛,這咒詛不久將被喚醒。
當沉沉的鐘聲響徹山谷時,其餘工作中的修女也紛紛抬起頭來。她們放下手裡的耙子和水管,走過一排排並列的櫻桃樹,攀上通往修道院的陡徑。
范蘿亭和米榭兒兩位年輕的見習修女,手勾著手走在長長的隊伍後面,小心翼翼地踩著沾泥的靴子跟著。這兩人跟嚴謹有序的修女們顯得格格不入,高大紅髮的米榭兒有雙長腿和寬實的肩膀,看起來不像修女,倒像健碩的農家女孩。她的修女服上罩著厚重的連身圍裙,紅紅的鬈髮垂落在頭巾後。走在她身邊的范蘿亭看起來雖然差不多高,卻相當孅弱。她皮膚蒼白近似半透明,垂及肩頭的淡金色頭髮,襯得她柔亮無比。范蘿亭的頭巾塞在修女服口袋裡,不甚情願地走在米榭兒身邊,一邊用靴子踢著泥巴。
兩位女孩是修道院中最年輕的修女,也是對表姊妹,由於法國一場大瘟疫,兩人幼時便成了孤兒。范蘿亭的祖父,年邁的迪里米伯爵將表姊妹託付給教會,並在死後留下一筆財產,確保兩人衣食無虞。
由於這樣的成長過程,使得姊妹倆分外焦孟不離。她們正處於年輕氣盛、難以羈絆的年紀,修道院院長便常聽年紀較長的修女抱怨說,兩人的行為不符修道院的常規;可是院長很清楚,對待年輕孩子最好順著毛摸,別去強壓她們。
其實院長十分偏愛這對失依的表姊妹,以院長這種性格和地位的人來說,這是相當異常的。老修女們若是知道院長一直以來也跟自己的兒時玩伴保持聯繫,一定會非常訝異。這位女子多年前與院長分離後,兩人一直相隔千里之遙。
走在陡坡上的米榭兒,一邊忙著將亂髮塞入頭巾裡,一邊拉著表妹的手,叨嫌她走路太慢。
「妳再這樣慢吞吞,小心院長又罰我們懺悔。」她說。
范蘿亭掙開手,繞了個圈,「世界洋溢著春之氣息哪!」她大聲揮手說,差點沒從懸崖邊翻出去;米榭兒將她從斜坡上拉開。「外面這麼的朝氣蓬勃,我們幹嘛把自己鎖在無聊的修道院裡?」
「因為我們是修女呀。」米榭兒噘嘴說,同時緊抓住范蘿亭,加快腳步。「為人類禱告是我們的職責。」可是從山谷底下冉冉升起的暖霧,夾帶著如此濃郁的櫻桃花香啊,米榭兒努力不讓那芳香影響自己。
「我們還不算修女啦,真是感謝上帝。」范蘿亭說,「還沒發誓前,我們只算是見習修女。我聽那些老修女說,軍人在法國四處搶奪修道院的財產,把教士抓起來,強迫他們走到巴黎。搞不好有些士兵會跑到這兒,也逼我走去巴黎,而且每晚帶我去聽歌劇,用我的鞋子喝香檳哩!」
「軍人才不像妳想的那麼討人喜歡呢。」米榭兒說,「畢竟他們的工作是殺人放火,而不是帶人去聽歌劇。」
「他們還不只那樣。」范蘿亭壓低嗓子,神秘兮兮地說。兩人已來到山巔,這裡的路拓得既平且寬,而且鋪著平實的石板,令人想到大城鎮裡的鬧街。道路兩側種著柏樹,底下就是櫻桃園的大片花樹,相較下顯得格外嚴謹,就跟修道院本身一樣突兀。
「我聽說,」范蘿亭在表姊耳邊悄聲說,「士兵會對修女做出可怕的事喲!例如,士兵要是在林子裡見到修女,他就會立刻把東西從褲子裡掏出來,塞到修女身體裡亂攪一通,等他弄完後,修女就會有寶寶了!」
「胡說什麼呀!」米榭兒怪叫一聲推開范蘿亭,拚命壓抑住嘴角的笑意。「妳當修女實在太六根不淨了。」
「我不就一直這麼說的嘛。」范蘿亭坦承,「我寧可當軍人的老婆,也不要當基督的妻子。」
兩個表姊妹走向修道院。修道院入口,由四組雙排柏樹植成的十字標記已經出現了。兩人穿過漸黑的霧氣和圍攏上來的柏樹,步入層層的修道院大門和偌大的中庭,一路走到修道院中心高聳的木門時,院鐘像喪鐘似地不斷在濃霧裡敲響。
兩人分別在門前停下來,刮淨靴上的泥巴,然後迅速穿過高聳的大門。她們都沒抬眼去看刻在入口石拱上的法蘭克語,但她們都知道上面寫了什麼,那些字早已烙印在她們腦海裡了:
詛咒那將這些高牆帶到世間的人,
唯有上帝之手能置國王於死地。
字句下刻著大大的粗體字:「卡洛魯斯.麥格納」(Carolus Magnus)。他是本樓的建築師,也是對那些意欲破壞大樓的人下咒的傢伙。這人是一千多年前,法蘭克帝國最偉大的統治者,法國人都稱他為查里曼大帝。
修道院的內牆陰冷幽暗,且覆著濕苔。內室可聽到見習修女的祈禱聲,以及念珠計禱聖母經、聖三光榮經和天主經時的輕叩聲。范蘿亭和米榭兒匆匆穿過小教堂,最後一批見習修女正乖乖跟著竊竊私語的老修女,來到院長書房所在的位置。一名年紀較大的修女匆匆地將落在後頭的幾個人趕進去,范蘿亭和米榭兒互望一眼,也跟了進去。
院長將眾人喚至書房,實在是非常奇怪的事,因為很少人會來這裡,就算有,也都是被叫進去訓誡的。范蘿亭常挨訓,是此處的常客。可是院鐘將所有修女都召來了,她們應該不會全是被叫到院長書房的吧?
大夥進入天花板低矮的大房間後,范蘿亭和米榭兒發現所有修女竟然真的都到齊了─有五十多個人。眾人成排地坐在面對院長書桌的長木椅上,竊竊私語著,顯然大家都覺得很不尋常。年輕的表姊妹走進來時,大夥看她們的表情似乎充滿了恐懼。兩姊妹在最後一排長椅上坐下來,范蘿亭緊握著米榭兒的手。
「這是什麼意思呀?」她小聲問道。
「我看不太妙。」米榭兒也小聲回答。「院長看起來好嚴肅,而且有兩個女的我從來沒見過。」
院長站在書房盡頭,一張發亮的大櫻桃木桌後,她看來雖老如發皺的舊羊皮紙,卻散發著一股懾人的威儀。向來穩斂靜定的院長,今天看來比平時更為嚴肅,修女們從沒見過她這個樣子。
兩位高碩、大手的陌生女子,像復仇天使般地站在院長兩側。其中一名黑髮白膚,眼神炯然;另一名跟米榭兒長得頗為神似,有著白皙的膚色和栗色的頭髮,但髮顏不若米榭兒的那般赤紅。這兩人雖然一看便知是修女,卻未做修女打扮,只是穿著簡約的素灰便服。
院長等所有修女坐定,關上房門,屋裡完全安靜下來後,才開口說話。范蘿亭總覺得院長的聲音很像碎裂的枯葉。
「孩子們,」院長交疊著手說,「千年以來,蒙特格朗修道院一直踞守在山上,克盡對世人的職責,全心侍奉上主。雖然我們過著出世的生活,卻未自絕於外界的動盪。在這小小的角落裡,我們接收到最新的災情,這消息也許會改變我們一向所享有的安寧。兩位站在我身邊的女士,便是為我們帶來消息的使者。在此為各位介紹亞莉桑汀.狄佛賓,」─院長向黑髮的女子示意─「以及瑪莉.夏綠蒂.狄柯黛,她們兩位一起主持北方坎城的女修道院,兩位修女不遠千里喬裝而來,為我們帶來警訊。請各位仔細聆聽她們所說的話,這件事攸關我們全體。」
院長語畢坐下,那名叫亞莉桑汀.狄佛賓的女子清清喉嚨,細聲發言,修女們得拉長耳朵才能聽得見,但她的話卻相當清晰。
「各位姊妹,」她說,「我們要說的事十分聳人聽聞,我們之中有人為了避世而入院,有人則是出於被迫才入院的,而非感受到聖召。」說到這兒,她烏光閃動的眼神直望向范蘿亭,害她連耳根都羞紅了。
「不論各位入院之初的目的何在,今天起都有了改變。夏綠蒂修女和我一路行經法國,非僅看到民不聊生,更親見路有餓殍,人們在街頭造亂搶食麵包,有如屠場;婦女們舉起戳著人頭的長矛在大街上遊晃,強暴凌辱時有所聞,更糟的是,連孩童都遭到殺害,人們在廣場上公然受到拷打,被憤怒的暴民五馬分屍……」修女們不再沉默了,耳語紛紛四起,亞莉桑汀繼續她血淋淋的陳述。
米榭兒覺得修女竟能如此平靜地描述這些事,實在非常詭異。亞莉桑汀陳述時,語氣輕柔平靜,不曾稍改,也並未發顫。米榭兒瞄向范蘿亭,見她瞪大眼睛聽得入神。亞莉桑汀等大夥稍稍安靜後,又繼續說:
「現在是四月了,去年十月,國王和皇后被一群憤怒的暴民從凡爾賽宮擄走,幽禁在巴黎杜葉里宮中。國王被迫簽署『人權宣言』,宣布人人生而平等。如今政府由國民議會所控制;國王無權干涉。我國已度過革命時期,變成混亂的無政府狀態了。更糟的是,國民議會發現國家已被國王虧空,國庫裡沒有黃金了。巴黎的人都相信國王活不過今年了。」
在座的修女們聽了震驚不已,紛紛交頭接耳起來。米榭兒輕輕握住范蘿亭的手,緊盯著發言者。這些事修女們前所未聞,也難以理解─拷問、無政府、弒君,怎麼可能啊?
院長用手拍著桌子要大家守序,眾人再次恢復安靜。這會兒亞莉桑汀坐下來,換夏綠蒂站到桌邊了。她的聲音宏亮,中氣十足。
「國民議會中有個野心極重,卻自稱神職人員的大壞蛋,此人是歐坦1主教。羅馬教會認為他是惡魔轉世,據說他與惡魔一樣,天生長著偶蹄,而且飲童血以維持青春,還舉行黑彌撒2。十月份時,這位主教建議國民議會沒收所有教會的財產,十一月二日,政治家米哈波(Mirabeau)在國民議會中,幫歐坦主教推動查封法案,結果法案通過了。二月十三日開始展開沒收行動,任何反抗的神職人員均遭逮捕下獄;二月十六日,歐坦主教獲選為國民議會主席,如今再也無人能夠阻止他了。」
修女們群情激動,忍不住驚呼出聲或表示抗議,其中又以夏綠蒂的聲音最為響亮。
「早在查封法案之前,歐坦主教便已對教會的法國財產做過調查了,雖然法案規定先查封男修道院,放過女修道院一馬,但我們知道主教一直在覬覦蒙特格朗修道院,也在修道院四周做過不少調查。我們就是趕來通報各位這件事的,千萬不可讓蒙特格朗的財產落入此人手裡。」
院長站起來,用手搭住夏綠蒂堅實的肩膀,望著一排排黑衣修女,看她們漿挺的帽子如鷗鳥興浪般地翻動。院長微微一笑,等待會兒說完話之後,這輩子只怕再也見不到這群長久以來受她照護的孩子了。
「現在各位跟我一樣清楚蒙特格朗的狀況了,」院長表示道,「雖然我已知道這個壞消息幾個月了,但我不希望在作決定前,驚擾到大家。兩位坎城的修女是應我邀請而來的,她們確認了我最擔心的事。」眾人陷入一片死寂,除了院長的聲音外,半點聲音都沒有。
「我年紀大了,隨時可能蒙主恩召,當初我進修道院時所發的誓,不只對天主所發而已。大約四十年前,我在即將擔任蒙特格朗修道院院長時,曾立誓保住一項秘密,必要時且不惜抵命相守。現在是我該體現那項誓約的時候了,可是在做這件事時,我必須跟各位分享一部分的秘密,並要求各位也發誓守密。我要說的故事很長,若說得慢,請各位耐心聽,等我說完了,各位便會明白,我們為什麼必須這麼做了。」
院長停下來,拿起放在桌前的銀杯啜了一口水,然後往下說道:
「今天是西元一七九○年四月四日,我的故事始於許多年前的四月四日。這故事是我的前輩告訴我的,多年以來,歷任院長交接時,都會把這個故事傳告給她的繼任者。現在,我也要將故事告訴各位……」
院長的故事 西元七八二年四月四日,為了慶祝查里曼大帝四十歲生日,亞琛3的東方城堡內大舉慶典,國內所有王卿貴族均受到大帝邀請。宏偉的宮廷圓頂上鑲著馬賽克,盤桓而上的階梯及陽台上擺滿了進口的棕櫚和花環。豎琴和琵琶在金燈銀籠齊明的大廳中,悠然奏響。身著紫色、深紅和金色服裝的朝臣們,在雜耍人員和偶戲之間穿梭遊巡。野熊、猛獅、長頸鹿和成箱成箱的鴿子被送入宮廷裡,大家為了國王的壽宴狂歡了好幾個星期。
慶典的重頭戲當然是壽誕當日了,當天國王在十八名子女、皇后和一群寵臣的簇擁下抵達宮中。查里曼大帝身長極高,體型因騎馬游泳而精實優雅,他膚色銅亮,髮鬚被陽光曬成了淡金色,渾身散發著武將與帝王的尊威。查里曼大帝身穿簡樸的毛織束腰外衣,罩著貼身貂皮外套,身佩長劍,越過宮廷時並與每位臣民打招呼,要眾人享用大廳桌上的佳餚美食。
國王為了今天準備一項特別節目。身為戰略天才的查里曼大帝,酷好一種遊戲,這遊戲又稱戰爭遊戲、王位爭霸─也就是西洋棋4。查里曼提議在他四十歲生日當天,與帝國境內的第一把棋師對奕─一位名叫葛林.法朗克的士兵。
葛林在喧天的喇叭聲中進宮,雜耍人員在他面前翻跳,年輕的女子將棕櫚葉和玫瑰花瓣撒在他行走的路徑上。葛林是個瘦削蒼白、面容嚴肅的年輕人,他有一雙灰眼,是西部軍隊的士兵。國王起身相迎時,葛林曲膝而跪。
八名做摩爾僕人打扮的黑奴扛著棋盤進入大廳,這批奴僕以及身上所扛的棋盤,是巴塞隆納的伊斯蘭國王 ─伊本.阿拉比所送的贈禮,為答謝四年前查里曼援助他們與庇里牛斯的巴斯克族作戰。在這場著名的戰役中,查里曼的愛將赫洛蘭德5撤軍時,戰死於納瓦拉的隆塞瓦勒隘口。自此之後,國王便不曾賽棋,或公開下過棋了。
眾人對擺在宮廷桌上的華麗棋組大表讚嘆,這些棋雖由阿拉伯一流工匠打造,卻帶有印度和波斯風格。有人認為,耶穌出生前四百多年,印度便已有西洋棋了,後來西元六四○年阿拉伯占領波斯時,才經由波斯傳入阿拉伯半島。
棋盤由純銀和純金煉鑄而成,每邊各長一公尺。這些精工細雕的金銀棋子上,裝飾著紅藍寶石、鑽石和翡翠。珠寶雖未切割,卻都經過打磨,有些大若鵪鶉蛋,寶石在宮廷燈火照耀下,璀璨生華,彷彿從內部散射出醉人的魅光。
那對稱為「王」的棋子足足有十五公分高,勾勒著一名騎在象背上的戴冠男子。「后」則坐在繡著珠飾的轎椅上。兩個主教是佩著奇珍異寶的大象;騎士是桀驁不馴的阿拉伯戰馬。車或城堡,又稱為Rukhkh ─是「戰車」的阿拉伯語─全刻成了馱負高椅的巨大駱駝。「卒」或我們現在所稱的兵,則是七公分高的步兵,他們的眼睛是小小的珠寶,劍柄上也泛著玉光。
查里曼大帝和葛林從兩邊走向棋盤。查里曼大帝抬起手,接著他說出的話,朝中熟識他的人聽了,都感到非常吃驚。
他以怪異的聲音說道:「我想打個賭。」查里曼大帝不是那種愛賭的人,眾朝臣不安地面面相覷。
「若是葛林士兵下贏我,我就把亞琛至庇里牛斯山巴斯克間的土地送給他,並讓長女嫁給葛林。若是他輸了,黎明時,則在本院中斬首。」
眾人一片譁然,大家都知道國王深愛他的女兒,曾經懇求她們在他有生之年莫要出嫁。
國王的摯友勃艮第公爵抓住他的手,將查里曼大帝拖到一旁。「你這算哪門子賭注?」他低聲問,「只有醉酒的粗漢才會打這種賭!」
查里曼大帝在桌邊坐下來,神情恍惚,公爵被他弄得一頭霧水,葛林也完全摸不著頭緒。他直視著公爵,然後二話不說,在棋盤邊坐下,接受國王的賭注。雙方選妥棋組,葛林運氣不錯,選到白棋,有先發的優勢。棋賽開始了。
也許是因為比賽緊張吧,但雙方走棋的專注程度與精準度,似乎超過了一般棋賽所應有,彷彿有隻看不見的手在棋盤上盤旋操弄,有時甚至覺得棋子是自己移動的。參賽者白著臉不發一語,眾朝臣則像鬼魅般團團圍住他們。
經過快一小時的對棋後,勃艮第公爵發現國王的舉止變得十分怪異,他眉頭緊蹙,恍神而心不在焉;葛林也顯得異常焦躁,動作變得倉卒不耐,額上沁著豆大的冷汗。兩名男子的眼睛都緊盯著棋盤,無法稍移。
這時查里曼大帝突然大吼一聲,站起來將棋盤翻倒,所有棋子悉數被掃到地上。眾朝臣紛紛退避,國王暴跳如雷,怒不可遏地扯著自己的頭髮,野獸似地狂捶自己的胸膛。葛林和勃艮第公爵衝到國王身邊,卻被他一把推開,最後動用了六名貴族才將國王制住。等他終於冷靜下來後,查里曼大帝一臉不解地望著四周,彷若長夢初醒。
「陛下,」葛林輕聲說著,從地上撿起一隻棋子交給查里曼大帝。「也許我們應該停賽了,棋子全打亂了,我連一步棋都想不起來。陛下,這組摩爾棋令我非常害怕,我覺得棋上附著邪惡的力量,逼你拿我的性命做賭注。」
在椅子上休息的查里曼大帝疲累地將手放在額上,默不作聲。
「葛林,」勃艮第公爵小心翼翼地說,「國王不迷信這一套,覺得那都是異端邪說。他嚴禁在宮廷裡施巫術和占卜預言─」
查里曼大帝打斷他,但聲音卻虛得像耗盡了力氣。「連我軍隊裡的士兵都相信巫術了,我還能如何在歐洲推廣基督教?」
「這種巫術在阿拉伯和東方行之已久,」葛林答道,「我並不相信,也不了解這種巫術,可是 ─」葛林彎下身看著國王說,「陛下不也感受到了?」
「我確實被怒氣衝昏了頭,一時無法控制自己。」查里曼大帝坦承道,「感覺上很像軍隊拂曉出擊前的心情,我實在說不上來。」
「可是天地間的事,都有其定數與道理。」葛林身後有人發話了。葛林轉過頭,看到將棋盤抬入屋內的八名黑奴之一。國王點點頭,要那摩爾人繼續往下說。
「我們家鄉瓦塔有個叫巴達威的古部族─意思是沙漠居民。他們的最高榮譽是拿血做賭注,據說唯有血的賭注可以破解黑血─大天使加百利從穆罕默德心臟中取出的黑血。陛下拿棋局做血注,以人的性命打賭,乃正義的最高形式。穆罕默德說:『天國能容許對伊斯蘭的懷疑與不信任,但無法容許不義。』」
「以血作為賭注,絕對是邪惡的。」查里曼大帝回答。葛林和勃艮第公爵訝異地看著國王,一小時前,他不是才親自賭過命嗎?
「不!」摩爾人堅持說,「以性命相賭,才能到達姑塔這片像天堂一樣的綠洲,如果你用Shatranj來賭,那麼Shatranj本身就會進行Sar!」
「Shatranj是摩爾人對西洋棋的稱呼,陛下。」葛林表示。
「那麼Sar又是什麼?」查里曼大帝緩緩站起來,俯視身邊每個人問。
「是『復仇』。」摩爾人不動聲色地答道,他彎身鞠躬,然後從國王身邊退開。
「我們再下一盤,」國王宣布,「這回不打賭了,純下棋,別管那些野蠻人和小孩憑空捏造的迷信了。」朝臣們又去擺棋,宮裡的人都鬆了一大口氣。查里曼大帝轉身拉著勃艮第公爵的手。
「我剛才真的跟人賭命了嗎?」他輕聲問。
公爵詫異地看著他。「怎麼?是啊,陛下,」他說,「您不記得了嗎?」
「不記得。」國王鬱鬱地說。
查里曼大帝和葛林再次坐下來對弈,經過激烈精彩的廝殺後,葛林終於贏了。國王將庇里牛斯山巴斯克區的土地賜給葛林,封他為「蒙特格朗的葛林」。國王非常欣賞葛林精湛的棋藝,主動表示要幫他打造塞堡,保護他贏得的領地。多年後,國王將兩人當年那場名局所用的棋組送與葛林,此後棋組便稱為「蒙特格朗棋組」。
「這就是蒙特格朗修道院的歷史。」院長為故事做結尾。她環顧默不作聲的修女,「多年之後,蒙特格朗的葛林病終前,將蒙特格朗領地的教堂遺贈出去,這要塞後來成為我們修道院,著名的蒙特格朗棋組也成了我們的院產。」
院長停頓了一會,不太確定如何往下說。最後她終於開口道。
「但葛林一直相信,蒙特格朗棋組受到可怕的詛咒,棋子交到他手裡之前,葛林早就聽說棋子上附有惡靈了。據說查里曼大帝的姪子夏洛特,在使用蒙特格朗棋盤下棋時遭到謀害。這套棋跟一些奇奇怪怪的血腥暴力事件,甚至是戰爭都沾上關係。
「最初從巴塞隆納將棋組送給查里曼的八名摩爾黑奴,哀求國王讓他們跟隨棋組一起到蒙特格朗,國王答應了。不久葛林便發現,塞堡裡有人在夜間進行神秘儀式,他十分確定摩爾人涉入其中。葛林對這份禮物漸漸感到害怕,視它為魔鬼的工具。葛林把棋子埋到塞堡中,並請查里曼大帝在牆上封下詛咒,以防他人讓棋子重見天日。國王雖不以為然,畢竟還是順了葛林的心意,因此今天我們才會在門上看到那些刻字。」
院長停下來,伸手扶住身後的椅子,她看起來虛弱而蒼白。亞莉桑汀站起來攙扶院長就坐。
「後來蒙特格朗棋組怎麼了?院長。」其中一名坐在前排的老修女問。
院長微微一笑。「我已經告訴過各位了,我們如果繼續留在修道院,就會有生命危險。我說過,法軍打算沒收教會財產,其實他們此時已在四處劫掠了。我還談到,有一項價值連城的寶物埋在本修道院牆裡,寶物也許附有惡靈,所以我若將自己在接任院長時發誓保守的秘密,告訴各位─也就是蒙特格朗棋組的秘密─各位應該不會太訝異吧。棋組仍然埋藏在這個房間的牆壁和地板裡,而且只有我知道每隻棋的確切位置。孩子們,我們的使命是將這組邪惡的棋子盡量分散到遠處,使欲奪取權力的野心分子永遠無法稱心取得整套棋組。因為蒙特格朗棋組擁有凌駕自然和人類理智的力量。
「雖然我們還有時間毀掉棋組,或將之損毀到無可辨識的程度,但我並不打算這麼做。因為擁有如此強大力量的物件,亦能施於善途,所以我才願意發誓封藏並保護蒙特格朗棋組。也許有一天歷史情境容許時,我們會再重整這些棋子,揭露它們黑暗的秘密。」
院長雖知道每隻棋子的位置,修道院全體修女仍花了幾乎兩星期的時間,才挖出所有蒙特格朗棋,並清理打磨乾淨。四位修女齊力將棋盤從石地中抬起來,棋盤整理妥當後,大夥發現棋盤的每個方格中都刻著奇怪的符號。每隻棋上也都雕有類似的符號,而且還有一塊布放在一個金屬製的大盒子裡。盒子每個角落都用蠟狀物質封住,想來應該是防霉用的吧。那是一塊深藍色的絨布,上面用金線和珠寶層層疊疊地繡著十二宮道的符號。布塊中央有兩條蛇狀的東西交纏成數字8的形狀,院長認為這塊布當時是用來遮覆蒙特格朗棋組,以免棋組在運送途中受到損壞。
第二個星期即將結束時,院長要修女們準備遠行。她私下單獨指派修女的去處,以免其他修女知道別人的去向,藉此降低每個人的風險。由於蒙特格朗棋組的棋數少於修道院修女人數,因此除了院長外,沒有人知道哪位修女帶了棋,哪位沒帶。
范蘿亭和米榭兒被叫進房時,院長坐在她的大書桌後,要她們坐到自己對面。書桌上躺了一隻閃閃發亮的蒙特格朗棋,一部分棋身用深藍色的繡布蓋著。
院長將手裡的筆擱到一旁,抬起眼。米榭兒和范蘿亭手拉著手坐下來,緊張地等著。
「院長,」范蘿亭衝口說,「希望您知道,我走了之後會非常想念您的,我知道我給您惹了不少麻煩,我真希望自己能乖一點,少給您添麻煩 ─ 」
「范蘿亭,」院長微微笑說,她看到米榭兒戳了范蘿亭一下,要她安靜。「妳想說什麼?妳怕我會把妳和米榭兒分開─所以才跟我道歉是吧?」范蘿亭不可置信地瞪著院長,奇怪她怎能看透自己的心意。
「無所謂,」院長接著說。她將一張紙推過櫻桃木桌,交給米榭兒。「這是將來負責照顧妳們的監護人姓名和住址,下面是我幫兩位安排的路途指示。」
「兩位耶。」范蘿亭大叫一聲,差點從椅子上滾下來。「噢,院長,妳幫我了結一大樁心願啦!」
院長大笑說:「我若不派妳們兩個一起去,范蘿亭,妳這丫頭為了留在表姊身邊,一定會設法破壞我的精心安排。何況啊,我有很好的理由派妳們兩人一起去。仔細聽我說,修道院裡每位修女都有人照顧了,家人願意接納她們回去的,我都讓她們回家。有些人,則安排朋友或遠親安頓她們。如果她們當初到修道院時帶了一筆錢,我也把錢退還給她們,由她們自行保管。沒錢的年輕女孩,便送到其他國家的好修道院。所有人的旅費和生活費都由我提供,以確保我的孩子能過得幸福。」院長交疊著手,繼續說道:「范蘿亭,妳在許多方面都很幸運哪。」她說,「妳祖父留給妳不少錢,我幫妳和表姊米榭兒都安排好了。雖然妳們沒有家人,卻有位教父願意照顧妳們。我收到他的回信,答應擔任妳們的監護人。說到這裡,我要講到第二個重點,一件很嚴肅的事。」
院長提到教父時,米榭兒瞄了范蘿亭一眼。此時她低頭看著手裡的紙,院長用恭整的粗字在上面寫道:「畫家,雅克.路易斯.大衛。」下面寫著一個巴黎的住址。米榭兒並不知道范蘿亭有教父。
院長又說:「我知道修道院關閉的消息傳出去後,法國有人會很不高興。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會面臨危險,尤其是來自歐坦主教方面的迫害,他一定會想知道我們從牆裡偷走了什麼。我們的行蹤無法完全避過他們的耳目,有的修女或許會被找到,而必須逃走。因此,我從我們之中挑了八個人,每人各帶一隻棋,這八人也都扮演收集站的角色,其他人需要逃跑時,可將棋留給她們,或指示她們去哪裡尋棋。范蘿亭,妳是八人中的一人。」
「我!」范蘿亭重重嚥著口水,喉嚨突然變得又乾又澀。「可是院長,我並不……我不會……」
「妳想說妳無法承擔這種重責大任是吧。」院長笑說,「這我也知道,我就全靠妳這位冷靜的表姊來幫我解決這個問題囉。」她看著米榭兒,米榭兒點頭表示同意。
「我會選擇這八位修女,並非單看她們的能力。」院長接續道,「而是就策略上的布置來做考量。妳的教父大衛住在巴黎,棋盤的中心位置是法國。身為知名藝術家,大衛深得貴族的尊重和友誼,但他也是國民議會的一員,被某些人視為激進革命分子。我相信必要時,大衛有能力保護妳們兩個,而且我已轉交他一大筆費用,讓他更心甘情願地照顧兩位。」
坐在桌子對面的院長看著兩名年輕女孩,「范蘿亭,這是命令,不是請求。」她正色道:「修道院的姊妹也許會遇到麻煩,到時妳得伸出援手。我把妳的名字和住址給了其他幾位已經返家的姊妹,妳得去巴黎照我的話做。妳已經十五歲了,應該了解生命中有些事物,比一時的任性來得重要。」院長聲色俱厲地說,接著表情一緩,跟平時一樣地看著范蘿亭,又加了一句:「何況,巴黎並不是個壞地方啊。」
范蘿亭也衝著院長笑道:「是啊,院長媽媽。那邊有歌劇,搞不好還有派對,據說仕女們會穿著華麗的長禮服─」米榭兒又捏了她一把。「我是說,我真的很感謝院長能如此的信任我們。」聽到這話,院長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她很多年沒這樣笑過了。
「很好很好,范蘿亭,妳們兩個可以去打包了。妳們明早天一亮就走,別拖拖拉拉的。」院長站起來從棋盤上拿起兩隻棋交給兩名見習修女。
范蘿亭和米榭兒輪流親吻院長的戒指,然後小心翼翼地捧著寶貴的棋來到書房門口,就在兩人要離去時,米榭兒轉身,首次開口發言。
「院長,我想請問一下。」她說,「那您要去哪兒?無論您去何處,我們都會思念您,祝福您的。」
「也許我會走一趟四十多年來一直想去的地方。」院長答道,「我有位朋友,自小分別後就一直沒見過了,當年哪─妳知道嗎?有時候,范蘿亭會讓我想到我那位兒時的玩伴,她是如此的活潑頑皮……」院長頓了頓,米榭兒心想,沒想到像院長這麼嚴肅的人,也會有熱切的渴望。
「院長,您的朋友住在法國嗎?」她問。
「不,」院長答道,「在俄國。」
翌日早晨,在撲灰的晨光中,兩名女子穿著便服,離開了蒙特格朗修道院,坐上一部裝滿乾草的馬車。馬車經過巨大的門拱,朝蜿蜒的山區而去。一股煙霧淡淡飄起,馬車駛向遠處山谷時,視線也跟著變模糊了。
她們忐忑不安地用披風裹住自己,心中滿懷感激,沒想到與世隔絕這麼久之後,再度入世,竟是為了上帝的使命。
可是在山頂上默默看著馬車緩緩駛進下方幽暗山谷的人,並不是上帝。修道院頂上一座覆雪的高峰上,一名騎著白馬的騎士目送著馬車消失在濃黑的霧色裡,然後不發一語地將馬兒調過頭,揚長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