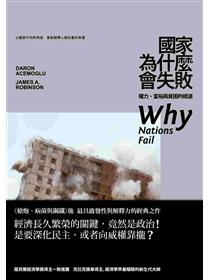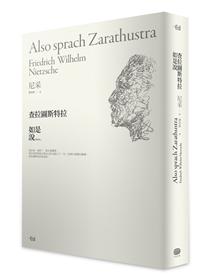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
鄂蘭有幸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本書是20世紀重要思想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於20世紀70年代完成的著作。這位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這裡所論的都是20世紀前半葉的知識份子,都是她身邊熟識的人。處在上一世紀上半葉的歐洲學術文化中心,一個最黑暗,也是思想文化最燦爛的年代,鄂蘭有幸與這些精采的人在同一時空中交會。
鄂蘭在這裡談他們的人生經歷,談他們在這個世界上的活動,也談大時代對他們的影響。由於對人物與時代的熟識,鄂蘭信手拈來,侃侃而談,一個時代的輪廓,躍然眼前。這些人各有不同的才華與信念,各人的專業與環境也大異其趣,唯一的共同點只有他們全都互不相識,而且他們全都走過了一個共同的時代(萊辛例外),一個政治大災難、道德大淪喪,藝術與科學卻突飛猛進的時代,這個時代鄂蘭稱之為「黑暗時代」一個動盪、飢餓、大屠殺、絕望、不公不義的時代。
人類的經驗與歷史,其實是不斷在重寫,與重演的,今天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已經走到一半,我們面對的世界,似乎還可以在鄂蘭的這些篇章中看到影子。
鄂蘭在這本書中評論了11位知識份子,包含了萊辛(1729-1781)、羅莎‧盧森堡(1871-1919)、安捷羅‧朱塞佩‧隆加尤里(1958-1963)、卡爾‧雅斯培(1883-1969)、伊薩‧迪內森(1885-1963)、賀曼‧布羅赫(1886-1951)、華特‧班雅明(1892-1940)、貝托爾特‧布萊希特(1898-1956)、華特馬爾‧居里安(1903-1954)、藍道‧賈雷爾(1914-1965)。
鄂蘭在她的寫作中,並不把他們視為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人物、時代精神的代言人、或是歷史的詮釋者。對•鄂蘭而言本書的寫作有些是感時之作,有些則是適逢其會。鄂蘭以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說是來自於凡夫俗子所發出的螢螢微光,正是基於這樣的信念,乃有了這組群像的勾勒。
作者簡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
被譽為是20世紀最偉大,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早年跟隨海德格、雅斯培。1933年納粹上台後流亡巴黎,1941年到美國,先後在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紐約新學院(New School)任教。她的著作如《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人類的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心智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皆是社會、政治哲學的扛鼎之著。鄂蘭於1975年去世後,美國學界出現「鄂蘭研究」,對於研究她的學者則稱為「鄂蘭派」,儼然成為一個學派之勢。
章節試閱
最後的歐洲人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二十世紀重要哲學家
Ⅰ駝子
菲瑪(Fama),這個貪得無饜的女神,有許多張面孔,她掌管的名聲當然也不例外,種類份量之多自不在話下,小者如封面故事為期一週的浮名,大者到垂諸青史的顯赫美名。在菲瑪的名譽榜中,還有一種名聲,能得到的人固然不多,想得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就是人死了之後才跑出來的身後名,只不過,這種名聲才真的不是浪得的虛名,若非貨真價實,還真是輪不到的。最有利可圖的主體既然都作了古,其為非賣品也就是必然的了。像這種非商業、非營利的死後名聲,在德國,今天倒是給了一個人,給了華特.班雅明和他的作品。說起班雅明這個猶太裔作家,名是有的,但又不是頂出名,只知道在希特勒掌權以及他移居國外之前,曾經為雜誌和報紙的文學副刊寫稿,為期不出十年。
一九四○年早秋,他選擇死亡時,知道他的人還寥寥無幾,當時,對他的親人和同時代的人來說,正是戰時最黑暗的時期,法國淪陷,英國受困,希特勒與史達林的條約尚未撕毀,歐洲這兩大警察國家的合作正弄得人心惶惶。事過十五年之後,他兩卷合為一冊的作品在德國出版,一夕之間洛陽紙貴,他那生前少有人知的大名也跟著散播開來。說到聲譽,光是最識貨的大行家所給的評價,不論有多高,對作家與藝術家來說都不足以餬口,非得社會大眾有口皆碑,即便不是為數極眾,那才是活得下去的保證,難怪有人會(附和西塞羅)說,「身後贏得的成功,在身前就成就了」,一切就都大不相同了!
說到身後之名,由於其不同一般,其實不能怪世人之不識貨,也怨不得文學界的墮落,更不能說,跑在時代前面的人活該只能嚐這樣的苦果 ──彷彿是說,在歷史的跑道上跑得太快的競賽者,由於迅若飆風,反而會一眨眼就消失在觀眾的視野之外了。其實剛好相反,身後能得大名者,活著的時候,通常已在同儕之間獲得了最高的認同。卡夫卡一九二四年去世的時候,出版的書沒有幾本,賣出去的,為數更是不到兩百,但文學界的朋友與區區可數的讀者,儘管只是偶然讀到他的短篇散文(當時他尚無小說問世),莫不為之傾倒,確信他必將成為現代散文的一代宗師。
這樣的評價,華特.班雅明也是在早年就獲得了;他年輕時的好友,當時仍然默默無聞的蕭勒姆(Gerhard Scholem)與他唯一的追隨者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固然不必說,兩人後來一起整理了他的遺稿與書信,1另外讓我們立刻想到的,則是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早在一九二四年班雅明論歌德的《親和力》(Elective Affinities)發表時,他就對班雅明大表肯定,至於布萊希特(Bertot Brecht),在他獲悉班雅明的噩耗時,據說曾表示,那乃是希特勒對德國文學所造成的最大損失。天才之完全不被賞識,這樣的事情是否真有,或者那根本只是自以為天才的人的妄想,我們雖然無法知道,但卻有理由相信,死後能得大名者,肯定是輪不到這些人的。
名聲之為物,是一種社會現象;正如塞尼卡(Seneca)既有智慧又見賣弄的說法:「名聲,不是一個人說了就算。」當然,友誼與愛情就另當別論了。任何一個社會,如果沒有層級之分,人與事也沒有分門別類的安排,那是不可能運作的。這種必然的分類乃是社會差別形成的基礎,這種差別,今天儘管有人大不以為然,但其為社會構成之要件,絕不下於平等之為政治的構成要件。重點在於,完全不同於我是「誰」這個問題,我是「什麼」這個問題,每個人在被別人問起時都必須作答,他的角色,他的功能,他絕不能回答說:我是獨一無二的,不只因為這樣的回答未免顯得傲慢,更因為這樣的回答完全沒有意義。至於班雅明的情形,仔細回顧一下便不難看出問題的癥結;當霍夫曼斯塔爾讀了這位籍籍無名的作者論歌德的長文之後,他的評語是「絕對無與倫比」,問題就出在這幾個字講得太貼切了,他寫的東西跟當時的文學根本無從比較,他的每篇文章永遠都獨具一格。
這樣看來,人之死後才得大名,似乎乃是無法歸類的宿命,他們的作品既非現存的等級可以安排,也沒有因為另闢蹊徑而讓自己成為未來的類型。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走卡夫卡的路子寫作,而下場之淒慘只是徒然突顯了卡夫卡的獨一無二,以及他那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獨創風格。對於這種人,社會所能做的頂多只是妥協,要叫它蓋個認可的印記那可真是千難萬難了。老實說吧,就如同一九二四年說卡夫卡是個短篇故事家和散文作家一樣,今天說班雅明是個文學評論家和散文家根本就是個誤解。
按照我們一般的參考架構來形容他的作品和他這個作家,若要做個充分的描述,就得用上一堆否定的陳述,譬如說,他學問淵博,但他不是學者;他研究的東西包括文本兼及詮釋,但他不是語文學家;他對宗教不感興趣,但卻迷神學以及用神學的方式去詮釋那些神聖不可侵犯的原文,但他不是神學家,尤其不喜歡《聖經》;他是個天生的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卻是寫一本完全用引文寫成的書;他是第一個翻譯普魯斯特(Proust)和聖約翰.佩斯(St.-John Perse)的德國人(與胡塞爾〔Franz Hessel〕合譯),之前還譯過波特萊爾(Baudelaire)的《巴黎圖畫》(Tableaux Parisiens),但他不是翻譯家;他寫書評,也寫文章評論在世的、已故的作家,但他不是文學評論家;他寫過一本有關德國巴洛克時代的書,還留下一堆未完成的有關十九世紀法國的研究,但他不是歷史家,也不是文學家或其他什麼家;至於他的思路頗富詩意,我將試著一談,但他既不是詩人也不是哲學家。
倒是有過那麼幾次,對於他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他還頂認真地做過一番界定,認為自己是個文學批評家,如果說他曾經立志要在人生中想達到什麼地位的話,那就是「德國文學唯一真正的批評家」(在蕭勒姆付梓的那幾封信中,有一封提到過這句話,那些寫給朋友的信,寫得還真是漂亮),除此之外,類似這種要成為社會有用份子的想法,他其實是相當排斥的,毫無疑問地,他認同的是波特萊爾的看法:「對我來說,做一個有用的人還真是件令人倒胃口的事。」在論《親和力》的那篇文章中,他在導言的部分,談到文學批評的任務,他曾經就自己的理路做過說明。開宗明義,他就為評論與批評做了一個分野(他自己並沒有提到過,或許根本不曾意識到,他之使用kritik,跟康德談到《純粹理性批判》時用這個字的用法相同,而一般來說,這個字的意思指的是「非難」)。
批評所關切的是藝術作品的真理內涵,評論所關切的則是作品的題材。兩者的關係由文學的基本法則所決定,根據此一法則,作品的真理內涵依賴於題材,因此,越是扣緊題材,也就越能夠跟題材渾然一體,唯其如此,作品的精神只要能夠從頭到尾深深根植於題材,縱使讀者是在隔了許久之後才讀到它,縱使作品在這個世界上已經褪色,還是能夠發現,「實在」(realia)在作品中卻是更加突顯了。這也就是說,在作品問世的初期,題材與精神是一體的,但時過境遷,兩者卻分開了,題材越來越突出,精神卻留在原處變得隱晦不明。因此,對後來的批評家來說,盡一切可能去解說題材顯著而不尋常的地方,也就成了先決條件。
我們大可把批評家喻為一個古文家,面對的是一張羊皮書,文本的內涵邈不可解,但字體筆畫還是依稀可辨。正如古文家會先從認識字體著手,批評家則必須從評註文本開始。從這項活動中,立刻會產生一項極為可貴的批評判斷準則,亦即,只有到了這個階段,批評家才能夠提出批評之所以為批評的各種基本問題──作品閃閃發光的精神內涵是否緣於題材,或者,題材的鮮活如故是否緣於精神內涵。因為,正是兩者在作品中分開時,它們才決定了作品的不朽。就此而言,藝術作品的歷史乃為批評提供了準備,這也正是歷史距離加強了作品的力量的原因。我們不妨打個比方,將不斷繁衍的作品視為火葬的柴堆,評論家大可比做是化學家,批評家則是煉金師。把木柴和灰燼留給前者,作為他分析唯一對象,而後者所關心的則是火焰本身的謎,亦即生命之謎。過去的柴木沉重,已逝生命的灰燼細微,批評家所要探討的無他,無非是那繼續燃燒於其上的生命之火的真理而已。
作為煉金師的批評家,所從事的不過就是這樣一種難登大雅的技藝,將實在界細微易逝的成分轉化為閃耀而永恆的真理之金,或更確切地說,針對此一神奇變形的歷史過程,加以觀察,做出解釋──至於這個比喻,不論我們是怎麼想的,跟我們通常將作家歸類為文學批評家的想法,顯然差了十萬八千里。
然而,在那些「身後贏得成功」的人的人生當中,除了無法歸類一事外,還有一個比較不客觀的因素,那就是壞運氣。這個在班雅明一生中相當突出的因素,在此不可不談,因為,以他這個從未夢想過死後名聲的人來說,對於這一點倒是相當在乎的。在他的作品中,乃至於在他平常的談話中,他經常談到的「小駝子」(little hunchback),是德國著名民間詩集《少年的魔號》(Des Knaben Wunderhorn)中的一個童話人物。
當我走進地窖,
去取葡萄美酒,
一個駝子過來,
奪走我的酒罐。
當我走進廚房,
打算弄碗湯喝,
一個駝子過來,
弄破我的湯碗。
這首詩是他在一本兒童讀物上讀到的,當時他還是個孩子,從此畢生不忘。但是,直到有一天(在寫完《柏林的童年:一九○○年前後》(A 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時),他預想到死亡,嘗試抓住「據說將在死神眼前一閃而過的……自己的『整個一生』」,以便弄清楚,到底是誰,是什麼東西,在他那麼幼小的時候就嚇著了他,而且纏著他直到死亡。就跟千千萬萬德國的母親一樣,童年時只要碰到倒楣的事情,他媽媽就會說:「砸鍋先生又來問候你了。」孩子當然明白這個怪裡怪氣的砸鍋先生指的是什麼,媽媽說的無非就是「小駝子」,有事沒事作弄小孩,要麼絆得你跌個大跤,要麼撞得你手裡的東西飛出去摔個粉碎。人長大了,童年時候不懂的事情總算弄明白了,也就是說,其實並不是自己盯著小駝子看──就像還是孩子時,一心想要弄明白,到底是什麼東西讓他那樣害怕──以至於得罪了他,反而是那個小駝子,是他一直在盯著他,至於砸鍋呢,反正就是倒楣。因為「只要一不小心被那個小人盯上了,自己既不當一回事,又不去防著那個小人。站在一堆碎片前面,他嚇呆了。」(《文集》〔Schriften〕I〕, 650-52)
最近,他的書信集出版,很幸運地讓我們能夠把班雅明的一生勾勒出一個更清楚的輪廓。說到這一點,如果把它當成是在處理一堆碎片,的確也是滿吸引人的,因為毫無疑問地,他自己就是這麼看的。問題是,他十分清楚那種神秘的互動,正如他對普魯斯特所給的評語:「脆弱與天才是不分家的」。談到他自己時,他完全同意雅各.里維耶(Jacques Rivie+`re)談到普魯斯特時所說的;里維耶是這樣說的:他「死於百無一用,連生個火、開扇窗都不會,也正因為這樣,他只好讓自己去寫作」(〈普魯斯特的畫像〉〔The Image of Proust〕)。跟普魯斯特一樣,「生活已經把他給壓垮了」,他卻束手無策,不知道該如何去「改變情況」(他這個人就跟夢遊者一樣,夢遊的時候絲毫不出差錯,但清醒的時候反倒愣頭愣腦,老是把自己帶到霉運當頭的地步,要不然就是走向霉運正好潛伏在那兒的地方。
正因為如此,一九三九年到四○年間的冬天,為了躲開轟炸的危險,他決定離開巴黎,找個安全的地方。誰知道,一顆炸彈也沒落在巴黎,反倒是他去的莫鎮〔Meaux〕,一個軍事中心,在法國那場莫須有的戰爭中,幾個月下來,成為少數幾個飽受威脅的地方)。但是,同普魯斯特一樣,他卻不以為忤,對這種詛咒報之以祝福,一再重複的,總是民間詩歌集最後面的那兩句禱詞,也正是這兩句禱詞,他拿來作為童年回憶錄的收尾:噢,親愛的孩子,我請求你,也為那個小駝子祈禱。
回顧起來,那張成就、才華、老實與霉運織成的巨網,糾纏著班雅明的一生,其實早從那篇開啟他寫作生涯的幸運的論文,我們就可以窺出蛛絲馬跡了。拜朋友推薦之賜,他的〈論歌德的《親和力》〉一文發表在霍夫曼斯塔爾的《新德國文粹》(Neue Deutsche Beitra+..ge, 1924-1925)上。這篇堪稱德語論文經典之作的研究,在整個德國文學批評的領域,以及在歌德研究的學術領域,迄今仍屬上上之作,但是,在此之前,卻曾多次遭到退稿。正當班雅明要「幫它找個接生者」的努力已經萬念俱灰時,霍夫曼斯塔爾的大表激賞適時來臨(《書信》〔Briefe〕I, 300)。但以當時的現實環境來說,這次機會卻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次關係重大的霉運,至於何以致此,顯然永遠無解。跨出這第一步,對物質上唯一的保障,就是為他取得一項資格,也就是跨過了到大學教書的門檻,而這正是班雅明當時的打算。
當然,這還不足以讓他養活自己──所謂的私人講師並不支薪──但有可能打動他父親資助他,直到他獲得一個全職教授資格為止,這種情形在當時是相當常見的。在一所不怎樣的大學,到教授底下去做個講師,結果往往會以災難收場,他跟他的朋友怎麼會不曉得這一點,直到今天,還是令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事。班雅明當時提交的那份研究:《德國悲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edy),如果那些參與其事的先生們說他們一個字都看不懂,想來必是可信的。他們怎麼會了解,一個作者最引以自豪的,居然會是「寫文章旁徵博引──隨你怎麼去想,一種最瘋狂的鑲嵌技巧」──何況還在那篇研究的前面大書特書所謂的六大格言,說什麼:「天下最珍貴的盡在於此矣。」(《書信》I, 366)那種情形,簡直就像不世出的大師打造了不世出的精品,卻擺到附近的跳蚤市場去賣。總之,一切都無關乎反猶太主義,也無關乎排外心態──班雅明是在瑞士取得學位,而且不曾拜在任何人的門下 ──也無關乎一般的學院偏見:只要是未經保證的,必屬次等貨色。
然而,砸鍋先生和霉運還是找上門來了,以當時德國的情形來說,正是他那篇論歌德的論文,搞砸了他到大學去教書的唯一機會。班雅明寫東西,多是基於真理越辯越明的心態,這一篇也不例外,而攻擊的矛頭則是指向龔道夫(Gundolf)論歌德的那本書。班雅明的批評火力十足,但他的本意絕非為了「打響名號」,一心想的反倒是,龔道夫以及那幫以史蒂芬.喬治(Stefan George)為首的文人應該能夠了解他的用心;這幫人以及他們所圍成的那個知識圈子,是他年輕時就已經耳熟能詳的;更何況,他似乎也沒有必要加入這個圈子,庇蔭於某人之下,好讓自己在學術界獲得認可,因為,這些人當時也才在學術界站穩腳跟而已。但不管怎麼說,千不該萬不該的是,他不該對著圈子裡那些論地位論能力都首屈一指的人一陣猛攻,弄得人人為之側目;後來他回顧這段往事時還說,他從此「很少與學術界打交道 ……更別說跟那些望重一時,如龔道夫、恩斯特.貝特拉姆(Ernst Bertram)者流了」(《書信》II, 523)。沒錯,事情就是這樣。他還沒能夠被大學接受之前,他的魯莽與霉運已經把他給公告周知於天下了。
然而,我們可不能說,他是故意不當一回事。相反地,他相當在意「砸鍋先生又來問候你了」,而且依我的看法,他比誰都更步步為營。問題是,面對可能的危險,他所採取的那套防衛措施,包括蕭勒姆提到的「中國式禮貌」,2全都怪裡怪氣、神秘兮兮的,全然沒有顧及真正的危險。就像戰爭初期從安全的巴黎逃到危險的莫鎮,他之為論歌德的論文擔心,根本就是杞人憂天;他擔心的是,文中有一段相當保留的批評,對象是霍夫曼斯塔爾那份刊物的主要投稿人魯道夫.博夏爾特(Rudolf Borchardt),有可能會造成霍夫曼斯塔爾的曲解。儘管如此,他又滿懷信心,這項「針對喬治學派(Georges school)意識形態的批判 ……立於不敗之地,很難叫他們忍得下這口氣」(《書信》I, 341)。
然而,對方根本無動於衷。因為,沒有人比班雅明更孤掌難鳴,根本沒有人在乎他,甚至霍夫曼斯塔爾的權威也改變不了這種情況,儘管班雅明初獲青睞時,曾經喜孜孜地說他是「新保護神」(《書信》I, 327),霍夫曼斯塔爾的聲音卻不能跟喬治學派的力量相提並論;在這個有影響力的團體裡面,就跟所有這類團體一樣,一切唯意識形態是問,臭味之所以相投,全是意識形態,無關乎地位與品味。喬治的追隨者們,儘管擺出一副超出政治的姿態,對於文壇的基本操作可是深諳門道,其嫻熟的程度不下於教授之精通學術政治,或御用文人與新聞記者之深悉「察言觀色」。
然而,班雅明卻是一竅不通。他一向不知道該如何應付這類事情,跟這一班人也向來湊不到一塊,對於「外界的威脅如狼群般逼近」,儘管讓他對人心世道已經了然於胸,他還是一籌莫展(《書信》I, 298)。就算他有心調整或跟別人合作,好歹讓自己的腳下穩固一點,到頭來還是把事情給搞砸。
二十世紀中葉,班雅明頗傾向於共產主義,他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寫了一篇論歌德的文章,雖然頗具份量,卻從未發表過,既沒有收在《俄羅斯大百科全書》(Great Russian Encyclopedia)中──本來是打算列入的──到了今天,在德國也還是未見天日。克勞斯.曼(Klaus Mann)曾經跟他約稿,為《文粹》(Die Sammlung)月刊寫了一篇評布萊希特《三便士故事》(Threepenny Novel)的稿子,但卻以退稿收場,只因為班雅明要求的酬勞是二百五十法郎──約十美元──而克勞斯.曼只肯付他一百五十法郎。這篇論布萊希特的東西,在他生前也就沒再出現過。
隨著社會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之遷往美國,最嚴重的困境也臨到了他的身上,這所原來隸屬於法蘭克福大學的研究院(今天已經重新歸建),當時是班雅明的主要經濟來源,其靈魂人物阿多諾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屬於「辯證唯物學派」,認為班雅明的思想是「非辯證的」,雖然「不脫唯物主義範疇,但絕非符合馬克思主義」,在他一篇論波特萊爾的論文中,「缺了中間要素」,而把「某些明顯屬於上層結構的要素……直接,甚至因果性地歸為下層結構」。結果使得他那篇〈波特萊爾筆下第二帝國時期的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the Works of Baudelaire)一文胎死腹中,未在該所的期刊上發表,也未收入他身後出版的文集(該文的兩章如今已發表,其中〈浪遊者〉〔Der Fl~#U00e2neur〕刊於《新評論》〔Die Neue Rundschau〕一九六七年十二月號,〈現代〉〔Die Moderne〕刊於《爭鳴》〔Das Argument〕一九六八年三月號)。
這一波的馬克思主義運動最是集怪異之大成,而由此產生的馬克思主義者,又以班雅明最為獨特。在理論方面,能夠吸引他的,自然是上層結構理論;這一部分,馬克思雖然著墨不多,但卻在運動中扮演著一個超乎尋常的角色,只因為加入此一運動的知識份子超乎尋常的多,而這些人又都只對上層結構有興趣。至於班雅明,他之運用此一理論,純粹是把它當作一種啟發式的方法論,對其歷史與哲學的背景則絲毫不感興趣。尤其吸引他的是,此一理論有關精神與其物質表現的緊密關係,以致四處都看得到波特萊爾〈對應〉(Correspondances)一詩的影子,亦即如果將精神與其物質表現適當地關聯起來,二者即可互為啟發,互為參照,到了最後,連詮釋與說明的工夫都可以省掉。班雅明所關切的,是把街景、股票交易市場、詩以及思想串聯起來的那一條線,正是這條線,使歷史學家與語言學家一眼就能夠認出它們是屬於同一個時代的。
阿多諾批評班雅明「把現實看得太單純」(《書信》II, 793),可以說是一針見血,但也正是這一點,班雅明自己念茲在茲。受到超現實主義強烈的影響,「試圖在現實最不起眼的地方,在現實的碎屑上抓住歷史的形象」(《書信》II, 685),班雅明特別著迷於極微小的東西,蕭勒姆曾經談到,他極想要在一張普通的筆記紙上寫滿一百行字,同時還特別著迷於克魯尼博物館(Muse+e Cluny)猶太區的那兩顆麥粒,「在那上面,刻上了整篇的『以色列祈禱文』(Shema Israel)」。
3對他來說,物體的大小與其意義成反比。這種偏好完全不可以怪癖視之,說起來,乃是來自於一種對他影響極為深遠的世界觀;至於此一世界觀則是起源於歌德的一項信念,亦即「元始現象」(Urpha+..nomen)的確實存在;所謂元始現象就是一種原初現象,是一種可以在宇宙表象中發現的具體東西,在其中,「意義」(Bedeutung,典型的歌德用語,在班雅明的作品中屢見不鮮)與表象、語言與事物、觀念與經驗都是同一的。物體越小,似乎越有可能以最集中的方式容納一切其他的東西;兩顆麥粒容納了整篇「以色列祈禱文」,亦即猶太教的全部精華,之所以感動他,道理在此;至微的精髓顯現於至微的實體,而其他的一切皆源於此二者,只不過在意義上無法與其本源相提並論罷了。換句話說,打從一開始,最讓班雅明著迷的並非觀念而是現象。「就萬物來說,弔詭的是,所謂的美就是物自身的顯現。」(《文集》II, 349)正是此一弔詭──或更簡單地說,顯現的妙不可言──乃是他終極關懷的核心。
這些思想,與馬克思主義和唯物辯證法相去何止十萬八千里,而其中心角色「浪遊者」4更是以各自的意義揭示自身:「過去一閃而逝的畫面」(〈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唯有閒逛的浪遊者才收到了訊息。班雅明的這種靜態因素,阿多諾一語道破:「想要正確了解班雅明,就必須去感受他句子背後的轉換,從極端的不安到某種靜止狀態,其實也就是動本身的靜止概念。」(《文集》I, XIX)很顯然地,沒有比這種想法更「不辯證」的,「歷史的天使」(〈歷史哲學的主題〉〔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不是辯證地向未來發展,而是將臉孔「朝向過去」。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連串的悲劇事件,他所看到的卻只是同一場災難,殘骸之上不斷地堆積殘骸,直堆到他的腳前。他(天使)很想停下來,叫醒死者,並將撞得粉碎的碎片黏合起來。」(這裡所指的,可能就是歷史的終結)「但是,暴風卻自天國吹來」,「令他無可抗拒地被推向他所背對的未來,同時,在他面前堆起來的殘骸則繼續堆向天空。這場暴風就是我們所稱的進步」。班雅明是在克利(Klee)的畫《新天使》(Angelus Novus)中看到這個天使,也就是在這個天使身上,浪遊者經歷了最後的轉型。正如浪遊者漫無目的的閒逛,即使是被人群推擠著,他仍然是掉轉了身子背對著人群,同樣地,「歷史的天使」也是什麼都沒有看見,只看到過去的廢墟不斷堆積,並被進步的暴風倒退著吹進未來。在思維上一貫在乎的,都是辯證的理解與理性的推求,居然有這樣的思想,看起來還真不可思議。
這樣的思想,論到其目標與終點,顯然不在於做出一般性的有效陳述,正如阿多諾的評語,而是代之以「比喻的陳述」(《書信》II, 785)。班雅明所關切的,是直接而實際展現的具體事實,是「意義」明顯的單一事件與偶然,因此,任何理論與「觀念」,若無法透過想像立即獲得精確的外形,他是不太感興趣的。對於這種非常複雜但卻高度寫實的思想模式,馬克思有關上層結構與下層結構的關聯,卻又不失為一種比喻的關聯。舉個例子來說──這可是相當符合班雅明的精神的──既然抽象的Vernunft(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動詞vernehmen(知覺、聽),那麼,我們便可以設想,一個屬於上層結構領域的字眼也可以在感官的下層結構中找到它的字源,或者反過來說,也就是將一個概念轉變成一個比喻了──條件是,對於這個「比喻」,我們是按著它的原意去理解,而不從metapherein(轉化)的寓言含義上去加以理解。
比喻是在建立一種關聯,是可以直接感知的,是無須加以解釋的,寓言則不然,往往是從抽象的觀念出發,再信手拈來某些東西作為代表。寓言要有意義就必須先加以解釋,就像謎語必須找出它的謎底,因此,寓言的象徵令人費解,總不免讓人想到猜謎語的不快,乃至於拿骷髏來代表死亡的寓意,沒有一點巧思還真做不到。荷馬以來,比喻開始成為詩歌傳達認知的要素,用來「對應」物理距離遙遠的事物,例如在《伊里亞德》中,希臘人因恐懼與悲傷而產生的心靈撕痛,與之對應的是西方與北方黑暗海域襲來的陣陣強風(《伊里亞德》IX, 1-8);又如一排又一排向戰場推進的大軍,對應的是大海的長浪在風的推波助瀾下,一波又一波撲向海岸,驚雷般衝上陸地(《伊里亞德》IV, 422-28)。
比喻是一種手法,詩意地表現世界的統一性。班雅明之所以晦澀難解,在於他不是詩人,卻是用詩在思考,因此很自然地把比喻視為語文最大的恩賜。語言的「轉移」使我們能夠把物質的形式變成無形的──「上帝是我們堅固的堡壘」──由此,上帝乃成為可以被經驗的。對他來說,把上層結構的理論理解成為比喻性思維,可說是輕而易舉,之所以如此,在於它可以毫不費力地避開「中介」,直接把上層結構與所謂「物質的」下層結構關聯起來,而這一物質的下層結構,對他來說就是感官經驗資料的全部。被別人貶為「庸俗的馬克思主義」或「非辯證的」思想,他顯然著迷不已。
班雅明的精神境界,看來確實得自於歌德,亦即得自於詩人而非哲學家,他的關切幾乎都是由詩人與小說家激發出來的,儘管他研究哲學,但卻發現,跟詩人溝通顯然比跟理論家打交道來得容易,不論是辯證的理論家還是形而上的理論家皆然。班雅明一生之中,「命運女神」對他二度青睞,是他與布萊希特的友誼,無疑地,其重要性也是無可比擬的,其特別處尤在於,一個德國當代最偉大的詩人與這個當代最重要的批評家碰頭了,更重要的是,兩個人都相當在乎這份友誼。但是,不旋踵就產生了相反的結果,他因此得罪了幾個朋友,並因此威脅到與社會研究院的關係,從他們的「暗示」,他有一萬個「聽話」的理由(《書信》II, 683),而他之所以因此犧牲掉自己與蕭勒姆的友誼,理由卻只有一個:蕭勒姆對朋友的死忠與寬宏。
阿多諾與蕭勒姆都認為布萊希特對班雅明帶來了「災難性的影響」(蕭勒姆語),5指的是班雅明在處理馬克思時明顯地非辯證,以及他與所有形而上學的決裂;麻煩的是,班雅明雖然慣於妥協,甚至根本無此必要時也會讓步,連表面上的應付也不肯,那是因為,我「對布萊希特作品的認同,在我的整個立場上,乃是最重要的戰略據點」(《書信》II, 594)。在布萊希特身上他看到的是一個具有罕見心智力量的詩人,這在當時,對他來說意義重大,至於那些左派份子,儘管辯證不離口,但在辯證思想上,布萊希特絕不輸給他們,而在心智上,卻又不尋常地貼近現實。跟布萊希特相交,他可以磨練布萊希特所謂的「樸素的思維」,布萊希特說:「重要的是學會樸素的思考。樸素的思維就是大事情的思維。」
班雅明則予以補充說:「有很多人,其觀念之辯證在於愛其巧……樸素的思想則剛好相反,雖然是辯證思維重要的部分,但其所指涉的不是別的,乃是實踐的理論……思想唯有樸素才能付諸行動。」6不過話又說回來,樸素思維之吸引班雅明,或許不在於它指涉的是實踐,而應該是現實,至於現實之顯現自身,對他來說,莫過於日常用語中的格言與成語。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說:「格言是樸素思維的學校。」而這種格言式與成語式的語言──如同卡夫卡之所為,經過他的手,語言的象徵有如靈感的泉源那樣清晰可辨,並提供了解開許多「謎題」的鑰匙──使得班雅明能夠寫出一手好散文,既具有獨特的魅力,又如此貼近於現實。
班雅明的一生,無論怎麼看,隨處都可見到那個小駝子。早在第三帝國還沒冒出來之前,小駝子的惡作劇就不斷,那些出版商,承諾班雅明的事情──為他審閱稿件及編輯期刊而支付年薪──全都在第一筆款子還沒支付之前就關門大吉。後來,小駝子倒是恩准了一本德國文學選集,裝訂精美,還附有出色的評論,準備以《德意志人》(Deutsche Menschen)為書名出版,題辭則是:「沒有名聲的榮耀/沒有光環的偉大/沒有報酬的莊嚴」;但不旋踵,小駝子卻反悔了,瑞士出版商破產,這本書竟在地下室中劃上了句點,並未能如班雅明之所願,在納粹統治下用一個筆名出版。一九六二年,這本選集被人在地下室發現,但也就是在那個時候,一個新的版本卻在德國問世了(還有幾件事情,開頭看起來不太好,後來卻有了轉機,好像也可以怪在小駝子身上。其中一件是亞利斯.聖雷日.雷日〔Alexis Saint-Le+ger Le+ger,亦即聖約翰.佩斯〕《安納貝斯》〔Anabase〕的翻譯,這本班雅明認為「不怎麼重要」的書,之所以會著手,跟翻譯普魯斯特一樣,是應霍夫曼斯塔爾之邀。
書雖然直到戰後仍未出版,但班雅明卻因此得與雷日結識;雷日為一外交官,乃說服法國政府在戰爭期間讓班雅明取得了法國的居留權,在當時,這是極少數難民才有的特權)。霉運之後,繼之而來的是「殘骸堆」,在西班牙邊界的災難發生之前,最後一次的打擊,是他自一九三八年以來就已經有預感的,他在巴黎生活唯一「物質與精神的支援」──紐約的社會研究院 ──將棄他而去(《書信》II, 839)。「對我在歐洲的情況極為不利的條件,有可能使我移民美國也為之泡湯」(《書信》II, 810),這是他在一九三九年四月寫下的,當時,阿多諾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寫信回絕他的波特萊爾譯文,打擊仍然餘痛未消(《書信》II, 790)。
蕭勒姆說得極為中肯,在現代作家中,僅次於普魯斯特,跟卡夫卡最為神似的就屬班雅明。無疑地,當班雅明寫道「要了解(卡夫卡的)作品,有一事不可不知,那就是他是一個失敗者」時(《書信》II, 614),他心裡想到的則是自己作品中的「廢墟地與災難區」。他之評論卡夫卡不作第二人想,用到自己身上卻也再適當不過:「失敗的情形不及備述,但卻不妨這樣說:一旦確定大勢已去,再怎麼努力看來也不過是一場夢」(《書信》II, 764)。他即使沒讀過卡夫卡,想法也會跟卡夫卡一樣。卡夫卡的作品,當他還僅讀過《司爐》(The Stoker)時,在論《親和力》一文中,他就引用了歌德關於希望的說法:「希望從他們頭上溜走,一如星辰之自天上墜落。」至於他對這一篇研究所下的結論,說起來,就更像出自卡夫卡的手筆了:「只因為有那些走投無路的人,希望才賜給了我們。」(《文集》I, 140)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即將移民美國的班雅明,在法國與西班牙的邊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很多。蓋世太保沒收了他在巴黎的寓所,其中包括他的藏書(他能夠從德國帶出來的「最珍貴的一半」),還有許多手稿,他更有理由擔心另外一些書和手稿,因為從巴黎飛往勞德(Lourdes,法國未淪陷區)之前,透過喬治.巴泰耶(George Bataille)存放在國家圖書館。7沒了藏書,他哪裡還活得下去?沒了手稿中那些取之不盡的引文和摘要,他靠什麼過日子?此外,美國對他一點吸引力也沒有,他過去就常說,到了那裡,除了用汽車載著他,到處展覽他這個「最後的歐洲人」外,他們可能會發現,他還真是一點用處都沒有。但是,導致他自殺的直接原因,卻是霉運一次非同小可的打擊。
法國維琪政府與第三帝國簽訂的停戰協議規定,從希特勒德國逃出來的難民──指留在法國境內的──除政治異議份子外,極有可能面臨遣返德國的命運。為了救助這一類難民,美國透過法國非佔領區內的領事館,發放為數極多的臨時簽證。值得注意的是,後來下場最慘的非政治反對人士的猶太人並不包括在內。但是,經過紐約社會研究院的奔走,班雅明被列入馬賽首批獲得簽證的人,並很快取得西班牙的過境簽證,以便前往里斯本搭船。然而,他當時正在申請的法國出境簽證尚未核准下來,而討好蓋世太保的法國政府,對德國難民的申請根本是一律打回票。
縱使如此,問題並不難解決,步行翻過山到西班牙的波港(Port Bou),有一條相當近而且不難走的路,更何況並無法國的邊界警衛看守。但對班雅明來說,心臟明顯的不好,再短的路他也受不了,只怕人雖到了命卻去了半條。他隨著一小群難民好不容易抵達了西班牙的邊境小鎮,才知道西班牙已在當天關閉了邊界,邊界官員拒絕受理馬賽簽發的簽證。難民原本要在次日循原路返回法國,但是,就在當天夜裡,班雅明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正因為此一自殺事件的影響,邊界官員同意放行,其他人乃得以前往葡萄牙。數星期之後,簽證禁令解除。班雅明如果早到一天,可以毫不費力地通過邊境;若是晚一天,人在馬賽就會知道無法從西班牙過境。但偏偏卻選中了那一天,災難於是降臨。
最後的歐洲人
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二十世紀重要哲學家
Ⅰ駝子
菲瑪(Fama),這個貪得無饜的女神,有許多張面孔,她掌管的名聲當然也不例外,種類份量之多自不在話下,小者如封面故事為期一週的浮名,大者到垂諸青史的顯赫美名。在菲瑪的名譽榜中,還有一種名聲,能得到的人固然不多,想得到的人更是少之又少,那就是人死了之後才跑出來的身後名,只不過,這種名聲才真的不是浪得的虛名,若非貨真價實,還真是輪不到的。最有利可圖的主體既然都作了古,其為非賣品也就是必然的了。像這種非商業、非營利的死後...
 32收藏
32收藏

 72二手徵求有驚喜
72二手徵求有驚喜



 32收藏
32收藏

 72二手徵求有驚喜
7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