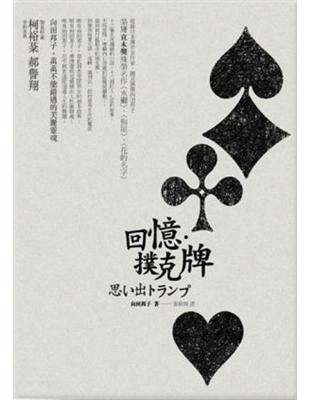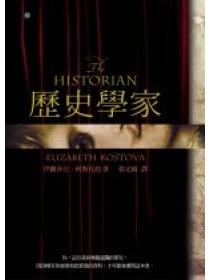花的名字
將剩布做成的墊子墊在電話底下時,丈夫松男曾說:「什麼呀,這是?」
「我從小家裡就沒有椅墊,不也一樣長大成人了嗎!」
言下之意是看不慣機器也跟人家學起了享受。
電話如果沒有東西墊著,鈴聲響時,聲音會太粗野、太刺耳。常子差點就要脫口這麼回答時,還好又將話吞了回去。因為在丈夫面前,什麼「神經大條」啦、「粗野」之類的字眼都是禁忌。
今年冬天起,常子開始有手腳冰冷的毛病。或許是這個原因,她看到赤裸的電話就擱在白色樹脂加工的底座上,總覺得電話屁股會好冷的樣子。當她半開玩笑地如此解釋時,松男便不再多說什麼,拿著浴巾一邊擦背一邊走進房間裡。
年紀都已經將近五十了,寬廣的背部有許多水珠滴流,似乎最近他又胖了一圈。
年輕的時候並不是這樣的。
在還談不上是夫妻吵架的小爭執中自知理虧時,丈夫會立即轉過瘦削的肩膀,腳步聲粗魯地回房間睡覺。他的背影彷彿仍堅持說:「那又怎麼樣!」
這麼說來,在那樣的夜晚,身旁的被窩肯定會有手伸過來。性急如他非得在當天把事情解決清楚,確定自己處於優勢才肯罷休。黑暗中被壓得死去活來時,常子總覺得這情景就像是刊在報紙角落的摔角勝負表一樣。一句話也不說,在常子的左耳邊吐出心中堆積的怨氣,突然間力道加重了。最後在自己的名號上面打上勝利的白星便呼呼大睡。
然而如今已不再有這種情形了。
不到五分鐘便能聽到他鼾聲大做。
二十五年的歲月,為丈夫的背增添了血肉。對於日常生活中的瑣事,他嘴裡或許會說幾句,但最後還是會聽從常子的意見。
聽見了「國歌」的聲音。
是來自隔壁鄰居家的電視機。不知道為什麼,似乎他們家總是要看到演奏國歌才肯關掉電視。
已經讀大學的兒子和女兒還在外面鬼混沒有回家。覺得電話鈴聲太吵、太刺耳,所以要墊塊布,或許正代表了常子經常一個人守在家中等候的證據吧?一家四口聚集在客廳喝茶聊天時,是不會聽見隔壁家的「國歌」的!
自從裝上墊子後,常子發現自己的內心裡似乎期待著有人打電話過來。電話鈴聲很明顯地變的圓潤溫暖許多了。為了測試這種變化,有電話過來是令人高興的。
而且最近電話的每次鈴響都能帶來好消息。大兒子的工作已經內定、丈夫高昇會計部經理等都是透過這具電話得知的。出門購物時不慎將母親遺留給她的錢包丟失了,接到超市店員「拾獲裡面錢財已被掏空的錢包一只」的通知,也是這溫馨祥和的鈴聲。
常子在廚房削馬鈴薯。因為是去年收成的馬鈴薯,上面發了許多芽。使用菜刀尖端挑掉芽眼時,想起了母親第一次教她使用菜刀的情景。記得當時削的也是馬鈴薯。
「馬鈴薯的芽眼有毒。」
印象中母親似乎還說過和薄荷一起食用會致死。一邊吃著咖哩飯和可樂餅,猛然想起白天在外面吃了薄荷糖,頓時擔心地不知所以。那是幾歲時候的事呢?
客廳裡電話鈴聲響了。
常子十分滿意這溫柔的響聲,很高興地答應了一聲,小跑步地上前接電話。
聲音愉悅地報上姓名後,
「請問是松男的太太嗎?」是以前沒聽過的女人聲音。
「請問哪裡找?」
對方沉默了一下說:「我是受妳先生照顧的人。」
這回輪到常子說不出話了。
覺得驚訝卻又不很意外。
這兩種感覺就像理髮廳紅藍兩色的旋轉招牌一樣,在腦海中不斷地轉動。
能否瞞著妳先生,我們見一面?就是今天,妳現在有沒有時間呢?對方的語氣像是談論別人的事情一樣。
黑色電話線路的那頭是一片黑暗,一個女人坐在黑暗中。看不見她的臉和身體,只知道她和自己一樣手拿著聽筒坐著。年紀或許是常子的一半,也可能再大一點,似乎不像是個生手。
常子發現自己經常把玩墊子四角垂掛的紅色流蘇,已經因為油垢有些髒了。怎麼還不到一個月,就變成如此討人厭的顏色了呢?
她跟對方約好傍晚在飯店的大廳見面。
「可是我不知道妳長的什麼樣子呀!」她才這麼回答,對方便輕笑一聲說:「我認識妳呀。」
為什麼她會認識我?難道是丈夫給她看過家人的照片嗎?常子知道自己的腋下開始冒汗了。
最後當常子問起女人名字時,不禁再一次驚嚇地說不出話來。因為她聽到是「Tsuneko」。心想丈夫居然找了一個跟自己一樣名字的女人,但立刻就發覺是她聽錯了,女人說的是「Tsuwako」。為了小心起見,常子又再問了一次。
「是Tsuwabuki(譯者註:山菊,因為用在人名,無法意譯,所以直接使用漢字石蕗)的Tsuwa。」
「就是寫成石蕗……」
「不,我的名字是用片假名寫的。」
掛上話筒後,常子呆坐在原地好一會兒。馬鈴薯的澱粉沾在黑色話筒上,留下了白色指印。
突然間她覺得好笑,笑的直不起腰來。因為她發現女人的名字居然跟花的名字一樣。
結婚之前,松男對花的名字幾乎一無所知。
櫻花、菊花和百合。
他所知道就是這些。但再仔細一問,似乎連這三種也會搞混了。
「唯一對櫻花,我很有自信。因為那是我中學時的校徽。」
看他自信滿滿的,便考他櫻花和梅花如何區別,頓時又變得不可靠了。
「也許還是算了吧。」
常子回到家後,不禁嘆了一口氣。
想到今後漫長的一生,要跟這個對什麼花開了什麼花謝了漠不關心的男人共渡,年方二十的常子覺得似乎太過悽涼了。
可是常子的母親卻突然對這樁婚事很感興趣。
她說這種男人才能讓妻子幸福。
「看妳爸爸就知道!」
常子的父親,說的好聽點是興趣廣泛,說的明白點則是樣樣精通卻窮困一生。拿起了魚,能夠裡乾淨做成生魚片;玩結繩,打得比母親做的還漂亮;也懂得女人和服的知識,選花樣配色他是一流,所以搭訕女人的甜言蜜語應該也很厲害吧?身為公務人員,一輩子沒什麼出頭;但似乎在常子所不知道的情況下有些風流韻事。
在母親的慫恿下,下一次跟松男見面時,他自言自語地表示:「我其實有缺陷。」
常子不禁抬頭看著這個比自己高出一個頭的大男人。
他說自己從小到大,父母便衣為要求要考上名門學校,成績要名列前茅。所以滿腦子裡都是數學、經濟學原理。一路走來只知道看著前方。
「假如我們能結婚,妳可以去學插花,然後回來教我。」
常子差點就要撲進松男懷裡。因為要顧到一個女孩子家的尊嚴她克制住自己,但松男立刻伸出青筋暴露的大手執起了常子的小手。
只要你不嫌棄,我願意教你。
不管是花的名字、魚的名字還是蔬菜的名字。
松男遵守了約定。
蜜月旅行一回來,就讓常子跟附近的花道老師學插花。一個禮拜一次的上課日,下班後他便直接回家。草草吃完晚餐,便要求常子表演今日所學,認真的眼神就像是觀摩手術的實習醫生一樣。嘴裡還不厭其煩地反覆詢問:「這是什麼花?」
學習插花的夜晚,也一定會動作粗魯地向常子求歡。新婚當時沒有發覺,直到婚後五年,在偶然的機會裡常子看到丈夫的記事簿才恍然大悟。
松男當天會將常子告訴她的花名記在記事簿上,就像這樣:
三月×日 喇叭水仙(黃色)
繡線菊(白色)
而且還會在當天的最後一個欄位上標上一個符號,寫上實行二字,並在旁邊加框。追溯之前的紀錄,幾乎毫無例外。
應該也是在那段期間吧?
丈夫有時會心情會很好地深夜回來。
說是被上司招待回家,看見上司夫人裝飾在和室裡的插花,用的是行家愛用的花材,同行的人裡面只有松男說的出花的名字。
丈夫不斷提起被上司夫婦誇獎「真是對你刮目相看呀」,然後五體投地地對常子說:「這都是妳的功勞。」
那是常子頭一次看見丈夫因為被上司賞識而高興莫名。想到這個人居然也有世俗的一面,雖然覺得內心有點失望,但聽到他說「因為妳的關係,讓我比較有人性了」,感覺倒也不壞。
關掉電燈後,心中有種準備接受丈夫粗魯求歡的心情。
或許是那一夜房事的關係吧?之後常子便小產了。如果出生的話,就是第三個小孩。
日常生活的鎖事從妻子那裡學習,當天晚上松男便用熱情回報的習慣,從這時候起也很自然地沒有了。
因為松男本來就是對時間、規則很一板一眼的人,也可能是因為小產的關係讓他有所警戒。
而且也沒有必要再教他什麼了。
鱸魚和鯔魚的不同。燕魚和鯧魚的味道差別。菠菜和小松菜。鴨兒芹和芹菜。
這些他都已經能夠區別了。
他也知道所謂的狗,並非只是一種動物。而是有秋田犬、土佐犬、柴犬、牧羊犬、大麥町等不同的種類。
然而習慣是很可怕的,她常常會不自覺地要求丈夫複習。
松男嘴裡雖然表示「真是囉唆,我都知道了啦」,卻還是回答:「像貍貓的是暹羅貓,像狐狸的是波斯貓。」
「反過來才對吧。」
這些細節,還是常子比較拿手。
只有一點仍然跟二十五年前一樣,如果不提醒他的話,一年到頭那怕汗流浹背他都會穿著冬衣。穿上常子遞給他的內衣褲,他說:「我不會配色。」
然後繫上常子幫他選好的領帶。婚喪喜慶等交際應酬、被屬下拜託當媒人的致詞等,也都是按照常子說的作。
除了被大女兒嘲笑是「具體白痴」外,他就跟普通的父親沒什麼兩樣。
雖然會做事,升遷也比別人快,但是他那一板一眼的個性和寫字難看的缺點,讓常子相信丈夫不會在外面拈花惹草。
可是他卻有了女人。
女人有著花的名字。丈夫會迷上那個女人,恐怕是因為名字的關係吧。
「我算是沒有白教他了。」常子喃喃自語,然後放聲大笑。
笑得很牽強。
回家拿網球拍的大女兒問她:「媽,妳怎麼了?」
這種事是無法對女兒啟齒的。
距離前往約好的地點,已經沒有時間可以上美容院了,頂多只能把馬鈴薯給削完。
在不自覺間,常子驚訝地發現自己居然狠狠地挖掉一大塊以前母親教她「有毒,吃了會死」的淡紅色芽眼。
自稱是Tsuwako的女人,三十出頭,好像是一間小酒吧的媽媽桑。穿著和化妝都很樸素,談吐沉穩,氣質不差。
是因為有了小孩嗎?還是想要遮羞費?還是有其他更嚴重的問題呢?來的路上,常子想了很多,卻沒有定論。抱著「水來土掩、兵來將擋」的心情赴約,卻發現情形完全不是她所想像的,常子覺得有些洩氣。
問對方用意何在。女人把玩了一下咖啡杯的把手後說:「我只是想讓妳知道有這麼樣的一個人存在而已。」
說完便凝視著飯店的庭園。
悶不吭聲也不能解決問題。於是常子滔滔不絕地說:妳知道嗎?我們夫妻去年剛過銀婚紀念。兒子也都到了就業、結婚的年紀了。我是不清楚我先生在外面有哪些交際應酬,但我們家的情形跟別人家不一樣,請妳了解……。
對方一句話也沒說。
「Tsuwako,這名字很少見呀。我先生應該馬上就能說出是石蕗花的Tsuwa吧?」
常子想等對方一回「是的」,就說出往事。那些花的名字都是我教給我先生的。
偏偏出乎意料地,
「沒有呀。」對方悠悠地回答:「倒是妳先生後來有說過,他問我:是不是妳媽懷孕的時候害喜(譯者註:因為害喜的日文發為「tsuwari」,有些諧音)的很厲害?」
說完露出溫和的笑容反問:「哪有父母會幫小孩取那種名字呢?」
Tsuwako還說出了一個意外的事實。
丈夫在酒吧裡都用「我家的老師」來稱呼常子。
「我家的老師……」
「他說妳什麼都知道,跟我正好相反。我是以笨出了名的。」
常子發現對方的和服穿的有些鬆散。還有說話的方式、攪動湯匙的動作也很遲緩。感覺有點像是發條鬆了,但也可能是在演戲。如果真的是在演戲,那麼最可怕的就是這種女人了。
什麼都知道的常子,結果卻是什麼都不知道。最後和對方各自付了咖啡錢分道回家。
那天晚上,丈夫和孩子們回來都很遲。
一個人坐在客廳時,只覺得身體內有滾滾洪流即將爆發。
說什麼「我有缺陷」,「請教我」,五體投地感謝說「都是妳的功勞」,那些究竟算是什麼?
丈夫標在記事簿裡的符號,到底代表了什麼樣的心情呢?
丈夫帶著跟平常一樣的表情回來了。
嚥下想要質問的千言萬語,常子問:「你知道石蕗花嗎?」
丈夫滿口酒臭味,不太耐煩地回答說:「石蕗花?是一種黃色的花吧?」
「你認識Tsuwako吧?」
一如要封住常子的嘴,丈夫裝傻說:「最近倒是很少見,那種花呀。」
看著丈夫往裡面走的背影,常子說:「打電話來了,那個人。究竟……」
這追擊的一槍,讓丈夫停下了腳步。
「都已經結束了。」說完繼續往房間裡走。
身體看起來似乎又胖了一圈。他的背影像是在說:「那又怎麼樣!」
教他東西的名字,因為派上用場而自鳴得意,其實是自己太狂妄了。就像以前幫植物施肥的經驗,小樹在不知不覺間已經長成了大樹。
花的名字。那又怎麼樣。
女人的名字。那又怎麼樣。
丈夫的背影如此說著。
女人的標準,二十五年來如一日;男人的尺度卻越來越大。
隔壁人家的電視又傳來了「國歌」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