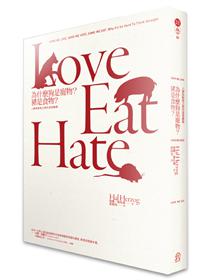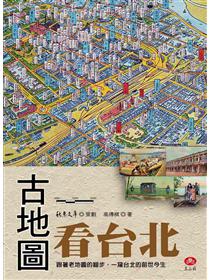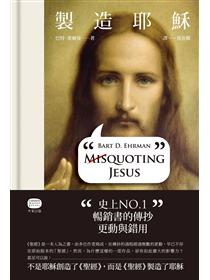疾病對新大陸的征服(摘自第一章 疾病史)
被稱為美洲印第安人的古代原住民都是狩獵採集者。至少在一萬兩千五百年前,一些原住民從亞洲經由冰河時期所造成的大陸橋,跨越白令海峽到達阿拉斯加,實際上冰河時期世界各大洋的海平面都已降低,在亞洲和北美之間的淺大陸棚則露出海面。根據遺傳學證據,最近有人提出某些原住民也許源自波里尼西亞(Polynesia)。橫越白令海峽並不是令人愉快的行程。大陸橋既荒涼、多霧且寒冷,因而某些學者臆測,人口壓力促使這樣的探險除了生存理由,不會再有什麼讓人不安的問題產生。換句話說,這類成功的遷移浪潮完全可以被歸納為冒險活動。
正如我們描述的那樣,這些狩獵採集者相對來說是健康的,穿越白令海峽的嚴酷考驗無疑會淘汰任何有病或虛弱者。此外,這些移民先驅在動物被馴化之前就離開了舊大陸,意味著他們除了自己,並沒有攜帶其他可行走的疾病帶原者(也許晚期的遷移浪潮會攜帶犬隻),在他們抵達美洲大陸之後,沒有遭遇到人類、疾病或是其他事物。
冰河時期大約於一萬年之前終止。冰帽融化,海水上升淹沒了大陸橋,並封鎖了這些新美洲人。同一時間,覆蓋北美洲的巨大冰川融化,為新抵達者展現一個完整的大陸。如果這些狩獵採集者曾經夢想過天堂,那麼此處即為天堂。
然而,新大陸有幾個令人驚愕不已的問題。首先,美洲大陸擁有幾種獨特疾病。例如︰洛磯山斑疹熱(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是一種今天自巴西到加拿大都可找到的美洲立克次體病(rickettsial disease)。儘管這種由蜱傳播的疾病,直到二十世紀才真正獲得鑑定,但人們可以聯想到這種疾病既感染現代居民,也感染了這個大陸的早期先民。那些遷徙到南美洲的群體,可能受到黏膜皮膚型萊什曼原蟲病(mucocutaneous leishmaniasis)侵襲,一種透過吸血沙蠅傳播的原蟲類疾病。到達安地斯山區的群體,則有感染卡里翁病(Carrión’s disease,也稱為奧羅亞熱〔Oroya fever〕或秘魯疣〔verruga Peruana〕)的危險。這種疾病也由吸血沙蠅傳播,該種疾病的毀容效果,在幾千年前的陶器器面已有描繪。另一種南美洲的地方性疾病為查加斯病(Chagas’disease)或稱美洲錐蟲病(American trypanosomiasis),該病可能起源於巴西。豚鼠和其他動物所攜帶的錐蟲屬原蟲(trypanosome protozoan)引發該病,由吸血錐蟲傳播給人類。
此外,還有一些野生動物疾病,例如與某些文明疾病競爭的旋毛蟲病和土拉倫斯菌病出現於新大陸農業革命的過程之中。瑪雅人(Maya)、阿茲提克人(Aztec)、印加人(Inca),以及北美洲的密西西比人(Mississippian),都進入定居農業生活,並建立複雜完整的城市文明,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同時間眾多健康問題也伴隨著生活模式變遷而來。一些類型的結核病流行起來,腸道寄生蟲和肝炎透過飲食在人與人之間傳播。品他病(pinta),由螺旋體菌(Treponema bacteria)所引起的嚴重疾病之一,由於氣候溫暖到足以著裝較少,使病菌很容易經由皮膚接觸而相互傳染,這似乎已經成為一個難題。其他螺旋體傳染病似乎也已出現,其中包括某類(顯而易見)非性病梅毒(non-venereal syphilis)。
但是,由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和其冒險同伴命名為「印第安人」的新大陸居民,成為了歐洲大量疾病的。他們已很難逃脫東半球所儲備的這些疾病,美國學者克羅斯比將這些疾病列出一份名單,其中包括天花、麻疹、白喉、砂眼(trachoma)、百日咳(whooping cough)、水痘、淋巴結鼠疫、瘧疾、傷寒、霍亂(cholera)、黃熱病、登革熱(dengue fever)、猩紅熱(scarlet fever)、阿米巴疾病(amoebic dysentery)、流行性感冒,以及腸道寄生蟲的感染。對於這一名單,也許還可以加上諸如︰斑疹傷寒、布氏桿菌病(brucellosis)、丹毒(erysipelas)、絲蟲病(filariasis)、腮腺炎、盤尾絲蟲病(onchocerciasis)、回歸熱(relapsing fever)、痲瘋病,可能還有鉤蟲病(hookworm disease)。
當哥倫布與其疾病到來時,沒有人知道存在有多少本土美洲人,也沒有人肯定確認他們所承受災難的人口統計數值。實際上,關於歐洲人所接觸的美洲人口的數量問題,始終是歷史統計與人類學研究貫穿二十世紀的熱烈爭議。在一九九二年哥倫布抵達美洲的五百週年學術成果研究中,就有針對此一尖銳課題的爭論。但是,無論人們傾向於接受高估計約一億人,還是較保守的五千萬人或者更少,但是其中有一點是一致的,亦即橫掃美洲的疾病大爆發,據說最終波及一四九二年人口總數的大約百分之九十。
在一四九三年,襲擊伊斯帕尼奧拉島(Island of Hispaniola)的第一次美洲流行病也許完全是一場豬流行性感冒。其他未知名的疾病隨之而至,以致西部印第安人的數量甚至在一五一八年天花正式出現於加勒比海地區之前,就一直在下降。天花伴隨著柯爾特斯(Hernando Cortés, 1485-1547)進入墨西哥,並搶先於皮薩羅(Pizarros)進入祕魯之前,兩度進行偉大的遠征,然而伴隨著疾病的向外擴散,卻扼殺了西班牙人從來沒有征服的其他數百萬人。在此之後,一次又一次的流行病像雨點般不斷落在美洲大陸。最嚴重的一次記錄是斑疹傷寒流行,根據報告直到十六世紀末在墨西哥高原共計約有兩百萬人病死。
人們只能想像這種恐怖︰年輕力壯者不斷地成為流行病的主要犧牲者,意味著只剩下極少數人從事播種、煮食、清掃的工作,並且照料兒童和老人。流行病以混亂的模式頻繁地進行襲擊,沒有留給人類恢復和免疫系統調節的時間。社會、政治、經濟和宗教生活完全崩潰,但奇蹟的是,有人發展出免疫能力得以倖免於難,並將這種免疫力傳遞下去。當人們開始具有這種能力,便使得墨西哥和安地斯山脈地區的人口數量得以逐漸恢復。
在北美洲,人口的下降(和恢復)都出現的較晚。在加勒比海地區和巴西各地,出現人口數嚴重下降後的特殊轉折,這一地區人口數下降實際等同於毀滅。然而,這些不同的統計事實,起因並不在於歐亞混血者的疾病,而是在於歐洲大陸的另一些群體身上源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某些疾病。
奠定解剖學基礎(摘自第五章 醫學科學)
人體系統解剖學研究對於鞏固醫學的地位而言,發揮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古代雅典的醫生認為人體是神聖的,並且避免解剖死屍以示尊敬。因此,儘管希波克拉底學派和其後的蓋倫學派對醫學曾作出許多貢獻,但在解剖學方面的認識卻很膚淺。類似身體神聖不可侵犯的理念(認為身體是屬於上帝而非自己的)導致羅馬教庭宣布反對解剖死者,平民百姓也對屍體解剖深感疑慮。直至一八三二年解剖法案通過,英國社會對於解剖還是存在根深柢固的敵意。如果看到柏克(William Burke)、海爾(William Hare)以及其他「掘屍人」(resurrection men)惡名昭彰的行為,便不會訝異當時社會的敵意。前述兩人在愛丁堡以謀殺獲取屍體,再賣給醫學院以供研究之用。
我們知道,堅實的解剖學和生理學基礎對科學的醫學至關重要,而醫學只有透過系統解剖才能得到發展。在中世紀時期,教會對解剖的禁錮漸漸放鬆了。十四世紀中葉,在黑死病流行期間,教皇批准驗屍以尋找瘟疫的根源;但直到一五三七年,教皇克雷孟特七世(Pope Clement VII)才終於允許將屍體解剖用於教學。無論如何,從十四世紀開始,解剖變得越來越普遍,尤其是在當時的科學研究中心──義大利。早期的解剖教學是在公共場合進行,幾乎成為一種市井奇觀,其目的不是為了研究而是為了說明──以便教授炫耀他的解剖知識。由一名解剖者持刀操作,教授則身著長袍,坐在高高的椅子上,從蓋倫的著作中朗讀相關章節,同時他的助手指向所提到的器官。十六世紀初期,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畫有約七百五十幅解剖圖。圖畫完全在私人的範圍內完成,也許是保密的,因而對醫學的發展沒有產生任何影響。
維薩里的研究成果為醫學帶來真正的突破。維薩里於一五一四年出生於布魯賽爾的藥劑師家庭,曾在巴黎、魯汶(Louvain)和帕多瓦求學,一五三七年在帕多瓦取得醫學學位後,即成為該地的教授。後來,他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及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1527-1598)的宮廷御醫。一五四三年,維薩里出版其名著《人體的構造》。在巴塞爾印刷的這本插圖精美的著作中,維薩里推崇觀察,並對蓋倫學說的許多論點提出挑戰,認為蓋倫的觀點是建立在對動物而非人的認識之上。他批評那些描繪「網神經叢」(plexus reticularis)的醫生,因為這些醫生只是在蓋倫的著作讀到,但卻從未真正在人體中見到那樣的架構。他也自責曾一度輕信蓋倫和其他解剖學家的說法。
維薩里的偉大貢獻在於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研究氛圍,並將解剖學研究基礎建立在透過觀察而得到的事實。儘管他的著作沒有驚人發現,但卻引發了一場思維策略的轉換。維薩里之後,對古老學說的盲目信奉,已喪失那種無可置疑的威權性,後世研究者決定將研究重點放在精確性和親身的直接觀察之上。維薩里的研究成果很快獲得承認︰當時首席外科醫生巴雷(Ambroise Paré, c. 1510-1590)於一五六四年所出版的經典外科學著作,其中關於解剖學的章節便採用維薩里的學說。
維薩里的著作中有關於骨骼、肌肉、神經系統、內臟及血管的確切描述和圖例。而其後繼者在更為深入細緻的層次,發展了維薩里的技術。一五六一年,維薩里的學生,帕多瓦的解剖學教授法洛比斯(Fallopius,即Gabrielle Falloppio, 1523-1562)出版了一部解剖學著作,闡述並修正維薩里學說的部分內容。法洛比斯的研究成果包括人的顱骨、耳朵以及女性生殖器的結構。他創造了陰道一詞,並描述了陰蒂,首先畫出從卵巢到子宮的管道。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未能指出被後人稱為法洛比斯管輸卵管的功能,直到兩個世紀以後,人們才意識到卵子是由卵巢產生的,並經由這些管道到達子宮。這足以說明早期的解剖學發展已經超過了生理學。
到十六世紀末葉,維薩里解剖學已經成為解剖學研究的黃金定律。另一位義大利先鋒人物歐斯塔修斯(Bartolommeo Eustachio, 1520-1574)發現了咽鼓管(Eustachian tube,從喉到中耳)以及心臟的歐氏瓣(Eustachian valve),還仔細探查腎臟與牙齒的結構。一六○三年,法洛比斯在帕多瓦的繼承人法布里修斯(Hieronymus Fabricius ab Acquapendente,即Girolamo Fabrizio, 1537-1619)出版了一本關於靜脈研究的著作,其中首次描述了靜脈瓣,並在不久後帶給英國醫生哈維很大啟發。稍後不久,帕多瓦的阿塞利(Gasparo Aselli, 1581-1625)開始集中研究腸系膜乳糜管,並證實其功能為輸送源自食物的乳糜。因而讓關於胃部的研究更為開展;萊登的希爾維斯(Franz de le Boë,即Franciscus Sylvius, 1614-1672)之後便歸納出關於消化過程的化學原理。腎臟結構方面的工作也有所進展。一六七○年,荷蘭醫生格拉夫(Regnier de Graaf, 1641-1673)提出一個高水準的人體生殖系統描述,並發現女性卵巢的格拉夫氏囊(Graafian vesicles)。
因此可知,維薩里的工作為人體器官的探索注入動力,當然也必須承認,文藝復興時期的研究從總體而言,對於結構的理解比對功能的理解更為透徹。無論如何,當時的理念和社會風氣促使解剖學成為醫學科學的基礎。
護理成為專業(摘自第六章 醫院與外科醫學)
一八三六年,佛雷德勒(Theodore Fliedner, 1800-1864)創立的女執事協會(Deaconess Institute)標誌護理專業的巨幅進步。佛雷德勒是德國杜塞爾多夫市(Düsseldorf)附近的開斯沃斯鎮(Kaiserswerth)的路德教派牧師。女執事協會設立宗旨是將女性培養成具有護理能力的執事人員,以使窮困貧民染病時得到幫助。它透過鼓勵婦女的使命感和奉獻精神,開闢讓名門淑女投身於護理事業的途徑。到一八六四年,學校已經培養訓練了大約一千六百名的女執事。一八四○年佛萊(Elizabeth Fry, 1740-1845)訪問開斯沃斯,返回倫敦後,她建立了護理協會(Institute of Nursing)。參加護理協會的婦女被稱為基督教慈善女教士(Protestant Sisters of Charity)──後來因為這個詞彙使基督徒感到刺耳,於是改稱「護理女士」(nursing sisters)。
在英國,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使公眾意識到需要新的護理模式。這場戰爭造就了一位女英雄──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南丁格爾出身名門望族,她發現從事護理工作符合自身殷切的期望,作為擺脫家庭的出路,並透過該項事業掌握自身命運。她在國外學習護理。一八五一年在開斯沃斯鎮停留三個月,一八五三年則在巴黎與慈光會(Sisters of Mercy)學習。南丁格爾深信護理的貢獻將會為大眾認同。當時從克里米亞發來一封由《泰唔士報》駐外記者羅素(W. H. Russell)撰寫的戰地快訊,披露了讓人深感震驚的消息,英軍傷兵一直由未受訓練的男護理員看護。戰時國務大臣賀伯特(Sidney Herbert)因而要求南丁格爾加以改善。南丁格爾於同年十一月四日,帶領三十八名護士抵達黑海沿岸的斯庫臺(Scutari)戰地醫院。不出六個月的時間,南丁格爾克服無數艱難困苦,終於使戰地醫院煥然一新,死亡率從百分之四十降至百分之二。
一八五六年這位「提燈女士」(lady with the lamp)的非凡成就,吸引公眾捐款四萬四千英磅,建立護士培養訓練體系。在與倫敦的聖湯馬斯醫院簽署病房培訓與醫學教育的協議之後,第一批南丁格爾式護士於一八六○年開始了課程學習。南丁格爾護理體系強調嚴格的紀律、團隊精神和獻身護理事業的精神。
南丁格爾從中下階層招攬一批品性良好的年輕女性作為「見習護士」(probationers)──這些人遵守紀律、易於訓練。南丁格爾學校成為教師和護理長(通常是嚴厲女士,但都相當慷慨,並沒有直接的個人護理經驗,注重德行多於實際)的來源。這些人又將南丁格爾的護理體系傳遍整個英國,進而發展至澳洲(一八六七年)、加拿大(一八七四年)和紐西蘭。
南丁格爾的護理理想也影響了美國。其著作《護理筆記》(Notes on Nursing)和《醫院筆記》(Notes on Hospital)進一步宣傳了她的護理改革成果︰強調清潔、新鮮空氣和生活規律。在美國類似的改革是由著名的狄克絲(Dorothea Dix, 1802-1887)開創的。南北戰爭爆發後,她立刻被任命為「聯邦軍隊的護理總監」(Superintenda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rmy Nurses)。
南丁格爾學校還是護理現代化的起點。紅十字會(Red Cross)的成立使護理專業進一步強化。一八五九年,瑞士銀行家杜南(Jean Henri Dunant, 1828-1910)親身經歷了奧地利與拿破崙三世法義聯軍的索菲里諾戰役(the battle of Solferino)。他極度憂慮傷兵缺乏醫療照顧,促使他於一八六四年創辦國際紅十字會。該協會對發展護理培訓發揮影響力,特別是對於歐洲低度開發地區和非西方世界。
在歐洲許多地方,宗教教義長期主導護理規範。護理的專業化發展十分緩慢艱難。在二十世紀初期,德國七萬五千名護理人員中,就有兩萬六千名天主教護士,以及一萬兩千名基督教護士。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魏瑪政府於一九二二年創立國家護士執照制度。在不到十年的時間,專業護士便超過教會護士的數量,比例為二比一。在世界各地護理事業也取得巨大進展。大約在一九○○年,奧斯勒爵士寫到︰「受過培養訓練護士的存在是人類之幸,與醫師和牧師相比,她的使命並不亞於任何一位。」
科學與道德(摘自第九章 醫學、社會和政府)
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階級衝突的暴力威脅降低。在英國,隨著選舉權擴大至部分男性工人階級,政治黨派也開始尋求工人階級的支持和認同。他們擴大初級教育,為市政紀念碑而投資,以軟化工人階層對於慈善機構和濟貧法的態度──至少是得到關注的婦女、兒童和病患。高等教育(對男性)受到鼓勵,尤其是在培養未來的公務員和教師,因其判斷能力和文化涵養可加強政府的威權性,並能防治民主過度發展。各類醫學組織在致力於提升政府威權和改善社會福利的進展中受益匪淺。
大約在一八五○年前後,「英國的狀態」成為跨黨派議題、醫生亦能自如參與其事。於此有助於醫生為得到政府註冊和保護而鬥爭;公共衛生事業隨之可被視為牽涉實驗室實驗與社會學統計的「科學」。賽門(John Simon, 1816-1904)是英國中央政府的第一位醫療官員,他在一八六○年代發起多項調查;他還是一八五八年《醫療改革法案》(Medical Reform Act)舉足輕重的支持者。作為一位具有德國理想主義背景,溫文儒雅的前外科醫師,他支持透過科學、行政和立法等方式,將「公共衛生」由政治運動議題轉化為能帶來效益、促進政府發展的事務。賽門的計畫在一八七○年代遭受挫折,然而重組行政機構有助於濟貧工作成為常軌。與此同時,由於天花的流行,隔離醫院的設立有所依據,地方衛生事業得以迅速發展,而隔離醫院之後被地方醫療衛生官員用做收容像白喉之類病患的場所。
一八六○年代後期,政府要求各城鎮任命衛生官員。衛生官員偕同醫生,共同倡導衛生學,鼓勵大眾增進對「生理學」知識的理解。但他們的威權也受到一定挑戰;對於正規醫學,尤其是對於醫學治療抱持懷疑態度的衛生改革者而言,健康法案也至關重要。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保健仍是一個道德目標──追求更好生活的基本原理,以及針對工業化的批評,支持者多為女性。
一八五○年代,南丁格爾由於在克里米亞戰爭的出色護理工作而聞名,於是護理工作成為單身女性發揮社會效用的一種嘗試,同時間護理也成為改善醫院衛生狀況和道德素質運動的重點。改革者認為,對內外科病患而言,醫院不應再是擁擠不堪的倉庫,而應建立在市郊或農村,有著通風良好和便於觀察的病房,成為有利於恢復健康的示範場所。這些關於醫院建設的新觀點引起當局興趣,尤其是體認到工人階級與慈善機構同樣有所貢獻。一八六○年代以後,地方醫院以體現「社區精神」的關鍵形象出現。
在維多利亞中期的英國,許多衛生運動倡導者是使用順勢療法醫師,以及其他反對正規療法人士。其中許多人不信奉國教,他們反對醫學壟斷,如同他們反對宗教壟斷和國家教會一樣。一八七○年前後,他們的抗爭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反對強制性接種天花疫苗,二是反對政府在有陸海軍隊駐紮的城市,進行強制性醫學檢查,以及必要時的住院治療。對改革者而言,醫學是一件有關良心的事情;那些遵照自然法則和上帝意志生活的人不需要治療,更確切地說,也不需要某些醫生認為科學發展必不可少的殘酷動物實驗。一八七○年左右,活體解剖成了英國公眾的主要談論話題。
醫學界也常置身於科學與宗教相抗的辯論。無論在英國或是在德國,進化論的辯論助長了存在已久的對「醫學唯物主義」(medical materialism)的懷疑。在法國,特別在一八七○年後,醫學共和派,包括不少知名議員,掀起爭取世俗教育以及醫療的抗爭。共和派發起運動,要求法國像英國一樣建立普通護士學校,以及要求當局在地方醫院「還俗」(laicise)護理工作。但是相關進展緩慢且不平衡,主因在於僱佣女教徒價格低廉並且可靠。
在討論精神錯亂疾病時,也可發現生理學模式和道德模式之間的衝突。無論是整體性抑或單純功能性原因,精神病都逐漸得以進行區分,並歸結為生理性原因。由於無人得以治癒,精神病院的治療主要還是「道德與保健」。儘管如此,醫學化有助於確保醫生掌握控制精神病院的權力,雖然這在十九世紀初期仍存在疑義。其中隱含一個事實︰精神病院內大多數的治療工作,是一般性的醫療而非精神病學治療,它可能透過將家庭問題醫學化,以及隨之進行的合法監禁,從而幫助病患家屬。
醫學和科學與日俱增的威信,有很大程度應歸功於實驗主義,特別是巴黎的巴納德以及德國大學的路德維希與助手,所進行的一系列知名動物生理實驗。實驗重點是對動物,最終則是對人體的生理過程進行測試和控制,這一點對於尋求臨床醫學與物理科學兩者關聯的醫學教育者而言,至關重要。政府和資本家也準備投資這些實驗,這些無疑都有助於提升社會福利和科學的權威。
無論在德國,還是美國新興或改革後的大學,或是英國的大學醫學院(特別是劍橋和倫敦大學),「科學化」醫療發展迅速。而在法國,以及由臨床醫學主宰的英國學校──倫敦醫院附設醫學院與地方性學校──發展速度相對較為緩慢。在英國,醫療科學化進程受到反對活體解剖的群眾運動影響,反對活體解剖常與衛生運動、女權運動,以及其他反對殘酷的運動相聯繫。有人認為十九世紀後期的醫學受益於(女性)情感和(男性)理智兩個層面,但是其中也不乏衝突。許多醫學討論試圖結合這兩方的要求︰醫生和善對待病患,並將患者視作獨特個體加以照料,但同時又要依據客觀的統計數據和實驗結果,來決定最佳的治療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