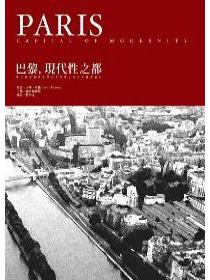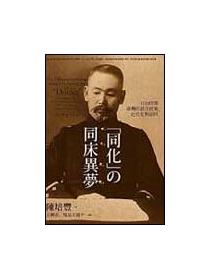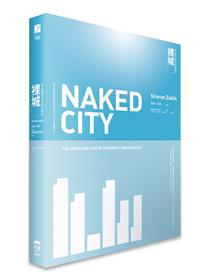本書探討十八世紀法國的思考方式。書中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什麼,而且包括他們怎麼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徑不是遵循知識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圖尚未標示的一個領域,在法國稱之為「心靈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這個類別在英文仍然無以名之,為了單純起見,不妨稱作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因為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種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那是人種誌(ethnography)觀察入微所看到的歷史。
「根據一名目擊的工人,賈克‧文森的印刷舖發生過最有趣的事情,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貓大屠殺。」羅伯.丹屯用這樣的破題句,開始探索十八世紀中葉法國技工所舉行的暴力儀式。在一系列妙筆生花的文章中,丹屯教授考掘啟蒙運動時代法國居住在都市、城鎮與鄉村的平凡人與不平凡人匪夷所思的世界觀。從法國農民陰森森的民間故事出發,一路逛到把盧梭和散佈省區各地的讀者扣在一起的浪漫情懷,丹屯引領讀者見識久遭誤解的思考與感受的方式。十八世紀法國人的文化有珍奇的一面,也有尋常的一面,丹屯一一召喚而出,藉以邀請讀者思索這一類的問題:為什麼巴黎的一群工匠覺得貓大屠殺那麼有趣?玩笑如何在舊制度的工人間發酵?《貓大屠殺》揭露一個文化的萬花筒視野,既熟悉又奇妙。羅伯.丹屯在本書提供了治療文化震盪所不可或缺而且入口難忘的一帖藥劑。
本書特色
「羅伯.丹屯具備新聞採訪記者追根究柢的好奇心,一絲不茍的學者窮本究源的敬業精神,以及小說家的敏感度。」——The New Republic
「慧心妙筆有創意,經常一針見血。」——Time
「文化震盪的一場演練。」——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內容摘要(引自作者序)
書中根據大異其趣的文本所帶出的驚訝,循聲窮追猛打。〈小紅帽〉的一個原始版本,貓大屠殺的一則記載,描敘一個城市的一段奇文,一名警探所保存的令人稱奇的檔案--這些文件不可能拿來代表十八世紀的思想,當作敲門磚卻綽綽有餘。書中討論的方式是從表達世界觀最含糊籠統的陳述著手,而後越來越精確。
第一章是民間傳說的考據,論及的故事在法國幾乎無人不曉,特別是在農村地區。第二章詮釋一群都市技工流傳的故事。循社會階梯往上爬,第三章說明都市生活對於地方上的資產階級到底有些什麼意義。隨後,場景轉到巴黎以及知識份子的世界--先是警方所見,他們有自成一格的方法形塑現實(第四章),其次是根據認識論從啟蒙運動的的主要文本挑選所得,這份文本就是《百科全書》的〈序論〉(第五章)。最後一章則說明盧梭和百科全書學派分道揚鑣一事如何掀啟思考與感受的新途徑,其要義可以從盧梭在世時的讀者的觀點重讀他的作品而體會出來。
作者簡介:
羅伯.丹屯(Robert Darnton)是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教授,也是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Prize)的評議委員。他的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於1983年獲美國書卷獎(American Book Award)提名。他的著作另還包括The Corpus of Clandestine Literature in France 1769-1789、The Kiss of Lamourette、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和最近出版的What Was Revolutionary About the French revolutaion。
章節試閱
第一篇
一、
農夫說故事:
鵝媽媽的意義
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有漏網之魚。說到那些未受啟蒙的民眾,他們的心智世界似乎是一去不返,難以追溯。要為普通人在18世紀找個立身之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竟至於搜尋他們的宇宙觀顯得愚不可及。但是,在知難而退之前,不妨暫且擱置懷疑之心,先來考慮一個故事——一個無人不知的故事,雖然大家熟悉的不是現在要提到的版本。這個版本卻是18世紀法國農家圍坐在爐火邊度過漫漫長冬時,用來打發上半夜時所說的,縱使細節不完全一樣,也是八九不離十。
從前有個小女孩,她遵照媽媽的吩咐,帶一些麵包和牛奶去給奶奶。這女孩穿越樹林的時候,一隻狼走向她,問她上哪兒去。
她回答:「去奶奶家。」
「妳走哪條路,尖尖的路還是針針的路?」
「針針的路。」
於是這狼走尖尖的路,早先一步來到奶奶的家。他殺了奶奶,把她的血倒進瓶子裡,把她的肉切成薄片,擺在盤子上。然後,他穿上奶奶的睡衣,躺在床上等候。
「叩、叩。」
「進來,我的小可愛。」
「哈囉,奶奶。我帶了些麵包和牛奶給妳。」
「我的小可愛,妳自己吃一些吧。桌上有肉也有酒。」
於是這小女孩看到東西就吃。她正吃著,一隻小貓開口說:「不要臉!吃妳奶奶的肉,還喝妳奶奶的血!」
狼接著說:「把衣服脫掉,上床來睡我旁邊。」
「我的圍巾要擺哪邊?」
「丟進火裡去;妳再也用不著了。」
這女孩一再重複同樣的問題,身上穿的一切——上衣、裙子、內衣和襪子——她一樣一樣地問。每一次,狼都是這樣回答:「丟進火裡去;妳再也用不著了。」
這女孩上了床,說:「奶奶,妳的毛好多啊!」
「我的小可愛,毛多才保暖。」
「奶奶,妳的肩膀好大啊!」
「我的小可愛,肩膀大方便扛木柴。」
「奶奶,妳的指甲好長啊!」
「我的小可愛,指甲長抓癢才過癮。」
「奶奶,妳的牙齒好大啊!」
「我的小可愛,牙齒大才方便吃妳。」
說著,狼把小女孩吃了。
這故事有什麼寓意?對小女生來說,教訓很清楚:和狼保持距離。對歷史學家而言,這故事觸及的是早期現代農民的心靈世界。怎麼說呢?如何著手詮釋這樣的一個文本?精神分析是一條路。學者已經徹底分析過民間故事,辨識出隱而不彰的象徵、無意識的母題(motifs)和心理機制。就拿佛洛姆(Erich Fromm)和布魯諾‧貝托海姆(Bruno Bettelheim)這兩位最知名的精神分析學家對於〈小紅帽〉(“Little Red Riding Hood”)的注解來示例舉隅。
佛洛姆把這個故事當作和初民社會中集體無意識有關的一則謎語來詮釋,「毫無困難」就破解其中的「象徵語言」而得出謎底。根據他的解釋,這故事涉及一個青少年面臨成人的性慾,其中隱而不彰的意義乃是透過象徵語言表現出來的。不過,他進行文本分析所用的版本和前面引錄的並不相同。事實上,他在他採用的版本中所看到的象徵仰賴許多細節,但那些細節在17和18世紀的農民所知道的版本裡頭根本不存在。換句話說,他大費周章地申論(子虛烏有的)紅色兜狀連頸帽是月經的象徵,女孩手裡拿的(子虛烏有的)瓶子是童貞的象徵,所以母親(子虛烏有的)告誡女兒不要偏離大路,以免誤闖禁地。狼是使人銷魂的男性。還有,在(子虛烏有的)獵人解救這女孩和她奶奶之後,被塞進狼肚子裡的兩個(子虛烏有的)石塊代表不孕,是對於打破性禁忌的懲罰。這麼看來,本著對於原始文本中遍尋不得的細節具有不可思議的敏感度,精神分析家把我們引入不曾存在過的心靈宇宙——至少在精神分析家誕生之前是不曾存在過的。
怎麼會把一個文本搞得那樣離譜?問題不在於專業方面的教條——因為精神分析家對於象徵的操作不需要比詩人來得嚴謹——而是無視於民間故事的歷史面向。
佛洛姆不會為指出資料來源而費心,不過顯然他的文本取自格林兄弟(the brothers Grimm)。這故事連同〈穿長統靴的貓〉(“Puss ’n Boots”)、〈藍鬍子〉(“Bluebeard”)和其他少數的故事,是惹內特‧哈森普夫盧格(Jeannette Hassenpflug)告訴格林兄弟的,這位小姐是他們在卡塞爾(Cassel)的鄰居,過從甚密;惹內特則是從她母親那兒聽來的,她母親來自法國的胡格諾(Huguenot)家庭。胡格諾人在逃避路易十四的迫害時,把這些故事帶到德國。不過,他們並不是直接從通俗的口述傳統(oral tradition)聽到這些故事。他們是查理‧佩羅(Charles Perrault)和瑪麗‧凱瑟琳‧奧努瓦(Marie Cathérine d’Aulnoy)等人在17世紀末時髦的巴黎名士界正流行童話故事時,從書上讀來的。佩羅是這個文類的健將,他倒是真的取材於一般民眾的口述傳統(主要來源可能是他兒子的奶媽)。但是他潤飾過這些故事,以便迎合在沙龍進進出出的那些世故的女性雅士和宮廷人士的品味——他在1697年首度刊行《鵝媽媽故事集》(Contes de ma mère l’oye)就是給那一批人看的。因此,經由哈森普夫盧格家人傳到格林的故事,既沒有多少德國風味,也難以代表民間傳統。事實上,格林兄弟看出那些故事的文學與法國化特性,因此在《兒童與家庭的童話》(Kinder-und Hausmärchen)發行第二版時刪掉了那些故事,唯一的例外是〈小紅帽〉。獨獨保留這一篇,顯然是因為惹內特‧哈森普夫盧格添枝加葉,從〈狼與小孩〉(“The Wolf and the Kids”,編號123的故事類型,這是依照安惕‧雅恩和司蒂斯‧湯普森所纂輯的標準分類碼;參見格林編碼5〈野狼和七隻小羊〉)移植過來一個快樂的結局;而〈狼與小孩〉正是德國最受歡迎的故事之一。所以說,小紅帽是挾帶法國血緣,輾轉經由德國,偷渡進入英國的文學傳統。她千里迢迢歷經脫胎換骨,從法國農民傳到佩羅家的奶媽,然後進入印刷廠,渡過萊茵河,回歸口述傳統,不過這一次是隨胡格諾人飄零異地,接著回歸書籍形式,這一回卻是產自條頓民族的樹林,而不是法國舊制度時代農村家庭的爐火邊。
佛洛姆以及其他不計其數的心理分析注解並不操心文本變異的問題——說真的,他們對這方面一無所知——因為他們得到了他們所要的故事。故事的開頭是青春期的性事(紅色兜狀連頸帽,這在法國的口述傳統中根本不存在),結尾是自我(ego)的勝利(逃出魔掌的女孩,她在法國的故事中通常是被吃掉),順利制伏本我(id,化身為狼,牠在傳統的文本裡從來不曾被殺死)。結尾皆大歡喜就是好事。
這個結局對於布魯諾‧貝托海姆來說特別重要。他是把〈小紅帽〉說得頭頭是道的精神分析家中的最後一個。在他看來,這個故事,一如所有這一類的故事,關鍵在於結尾的肯定訊息。他宣稱,童話故事快快樂樂的結局使得兒童得以面對他們自己的無意識慾望和恐懼,與其正面交鋒猶能全身而退,本我消聲匿跡而自我獲得勝利。在貝托海姆的版本中,本我就是〈小紅帽〉裡的惡棍,也就是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這個原則在女孩超過口腔固戀期(oral fixation,即〈韓森和葛蕾特〉〔“Hansel and Gretel”;格林編碼15〕所代表的那個階段)但尚未到達成人性階段的期間,把她引上偏僻之地。本我也是狼,狼也是父親,父親也是獵人,獵人也是自我,而且不知怎麼一回事又是超我(superego)。小紅帽為狼指出她祖母住的地方,無異於以戀父的方式設法除掉她的母親,因為母親在靈魂的經濟寓意體系(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soul)中也可以是祖母,而且在樹林兩邊的房子其實是同一棟,就像我們在〈韓森和葛蕾特〉所看到的,那兩棟房子在故事裡頭也就是母親的身體。如此左右逢源混合種種象徵,使得小紅帽有機會和她的父親同床共眠,這個父親就是狼,於是她的弒父戀母幻想有了發洩的管道。她最後大難不死,是因為她的父親以自我、超我、獵人三合一的姿態再度出現,並且剪開她那既是狼又是本我的父親的肚皮而救她出來,使她在更高級的存在層面上重生。這麼一來,人人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貝托海姆對象徵抱持寬容的觀點,因此和佛洛姆的密碼概念比起來,他對這個故事的詮釋不至於那麼機械化。不過他的詮釋也是基於一些未加質疑的文本假定。他廣徵博引學界對於格林和佩羅的注釋,顯示他多少意識到民間故事是學術研究的一環。儘管如此,他解讀〈小紅帽〉和其他故事時,卻完全無視於那些故事的歷史。他的處理方式簡直就像對待沙發上的病患,要他們平直躺下,完全不理會時間的先後次序,只尋求當下的理解。他不質疑故事的來源,也不擔心相同的故事在不同的文義格局可能有不同的意義,因為他知道靈魂如何運作,知道靈魂一向如何運作。然而,揆諸事實,民間故事是受到歷史條件制約的文獻。它們歷經許多世紀的演變,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自有不同的轉折。民間故事絕不是表達人的內在生命一成不變的運作途徑,而是意味著精神狀態本身歷經變遷。只要想像一下,用〈小紅帽〉原始的農民版本來哄我們自己的孩子睡覺,我們就能夠領會我們的心靈世界和祖先的心靈世界兩者之間的距離。這麼說來,這個故事的教訓或許應該是:謹防精神分析家——而且小心運用資料來源。我們似乎走上了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老路子。
然而,「似乎」畢竟不等於事實,因為〈小紅帽〉令人咋舌的非理性成分在理性時代似乎格格不入。事實上,就暴力與性而論,農民的版本比精神分析家的版本更勝一籌。(佛洛姆和貝托海姆根據格林兄弟和佩羅的說法,沒有提到祖母被狼吃掉,也沒有提到狼吃女孩之前要她脫衣服。)顯然,農夫提到禁忌並不需要使用密碼。......
二、
工人暴動:
聖塞佛倫街的貓大屠殺
根據一名目擊的工人,賈克‧文森(Jacques Vincent)的印刷舖所曾發生過最有趣的事情,是一場翻天覆地的貓大屠殺。這名工人叫做尼可拉‧孔塔(Nicolas Contat),他記述他自己在那一家印刷所當學徒的經歷時提到這個故事,時間是1730年代末期,地點在巴黎的聖塞佛倫街(rue Saint-Séverin。他說,學徒(apprentice)生涯苦不堪言。學徒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傑侯姆(Jerome),或多或少是孔塔以自己為摹本所虛構出來的人物,另一個是雷維耶(Léveillé)。他們睡在一個又髒又冷的房間,天還沒亮就起床,整天跑腿,還得忍受職工(journeymen)的侮辱和師傅的虐待,只有靠廚餘裹腹。特別惱人的是伙食,上不了師傅/主人〔這兩個稱呼在本章的用法中是同義詞〕的餐桌,他們得在廚房吃餐後殘留在盤子裡的碎屑。更慘的是,廚子暗地裡把剩魚剩肉拿去賣,拿貓食給學徒吃,盡是些太老、腐爛的肉,他們食不下嚥,丟給貓吃,貓卻調頭不吃。
最後那一項不合理的待遇使得孔塔把筆鋒轉向貓的主題。貓在他的敘事中佔有特殊的地位,在聖塞佛倫街的家居生活也一樣。師傅的妻子愛貓如命,尤其小灰是她的最愛。對貓鍾情似乎是印刷業的風氣,至少在師傅那個階層是這樣,也就是工人稱之為「資產階級」(bourgeois)的那個階層。有個資產階級養了25隻貓。他請來畫家為他的愛貓畫肖像,餵牠們吃烤禽肉。反觀學徒,他們卻得想法子應付在印刷區大肆繁殖、擾得他們生活難以為繼的巷弄貓陣。貓成群結隊在學徒髒兮兮的臥室屋頂徹夜叫春,他們根本不可能睡通宵。清晨四、五點的時候,傑侯姆和雷維耶睡眼惺忪爬下床,為最早來上班的職工開門,一身疲態揭開又一天的序幕,那些資產階級卻還在蒙頭大睡。師傅甚至不和他們一起工作,就像他不和他們同桌共餐。他把業務交給工頭處理,店裡難得看到他的蹤影,除非是來發洩火爆的脾氣,通常是拿學徒當出氣筒。
一天晚上,這兩個男孩決定自力救濟,糾正不平等的狀態。雷維耶有超人一等的模仿天分,他爬上屋頂,一直爬到靠近師傅臥室的地方,開始喵喵叫,聲聲悽厲,竟使得這個資產階級分子和他的妻子閤不了眼。一連幾天下來,他們不由得相信自己中了邪。不過,這師傅雖然是無比虔誠的教徒,他的妻子也向來告解不落人後,他們卻沒有去找神父,而是命令學徒去趕走群貓。師母傳下指示,特別交代最重要的是不許驚嚇到她的小灰。
傑侯姆和雷維耶喜出望外,開始執行任務,而且還有職工從旁協助。他們找來掃帚柄、印刷機的橫桿以及這行業中其他派得上用場的工具,看到貓就追打,首當其衝的就是小灰。雷維耶手持鐵桿,朝小灰的脊骨狠狠一擊,在一旁待命的傑侯姆當場把牠給了斷。接著,他們把死小灰醃在臭水溝裡,職工一伙人則忙著追趕其他的貓,貓在屋頂上逐戶逃竄,短棍在牠們的身後飛舞,見袋則躲的自然成了囊中物。他們把奄奄一息的貓裝進袋子,堆在庭院。然後,印刷所全部的人齊聚一堂,演出一場大審,衛兵、告解神父和刑吏一應俱全。把那些動物判刑,並且舉行臨終儀式之後,他們在臨時搭建的刑台上把牠們絞死。一陣哄笑驚動師母,她來到現場,看到一隻血淋淋的貓掛在繩套上擺盪,失聲尖叫。她想到那可能是小灰。大伙兒向她保證絕對不是;他們非常非常尊重師傅一家人,不會做出那種事。就在這時候,師傅現身了,但工人集體怠工卻令他火冒三丈,雖然他的妻子試著向他說明他們面臨更嚴重的一種以下犯上的威脅。師傅夫婦離去之後,大伙兒「歡欣」、「鬧成一團」而且「大笑」。
笑聲並沒有就這樣結束。後續的幾天,印刷工人想要偷閒尋開心,雷維耶就模擬當時的情景,重演不下20次。以詼諧的方式重演印刷舖生活的點點滴滴,用印刷業的行話來說就是「複本」(copies),從此成為他們的一大娛樂,用意是諷刺店裡面某個人的特性以達到羞辱的目的。一個成功的「複本」會惹得玩笑的標靶七竅生煙——店裡的行話叫「吊母山羊」(pendre la chèvre)——伙伴們則用「粗獷音樂」(“rough music”)捉弄他。他們會把排字盤擺在鉛字盤上,從這一頭滑到另一頭,拿木鎚重擊排版架,敲打餐具櫃,還像羊一般咩咩叫。咩咩的叫聲(行話叫bais〔「親親」〕)代表堆積在受害人身上的羞辱,就好像英文說某某人“gets your goat”(「把你給惹惱」)。孔塔強調說,雷維耶製造了凡人所知最有趣的「複本」,也引發了粗獷音樂中最雄偉的合唱。「複本」結合貓大屠殺所構成的這整個插曲醒人耳目,是傑侯姆整個印刷生涯中最開心的經驗。
可是,在現代讀者看來,這件事就算不至於讓人反感,也實在是沒什麼好笑的。一個青少年演出毫無自衛能力的動物慘遭屠殺的儀式,圍觀的一群大男人學羊一樣咩咩叫,拿他們的工具又敲又打的,哪有什麼幽默可言?我們笑不出來,這正說明了阻隔我們和工業化之前的歐洲工人之間的距離。察覺到那一段距離的存在可作為從事一項探究工作的起點,因為人類學家已經發現最不透光的地方似乎就是穿透異文化最理想的入口處。當你瞭解到對在地人特具意義,而你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東西,不論是一個笑話、一句諺語或一種儀式,你就能夠曉得從什麼地方抓得到可以迎刃而解的一套素昧平生的意義系統。掌握貓大屠殺的笑點所在,或許就有可能「掌握」舊制度之下技工文化(artisanal culture)的要素。
首先應該說明,我們不可能直接觀察殺貓之事。我們只有透過孔塔的敘述才能進行研究,而他是在事後大約20年才寫下來的。翟爾茲‧巴博(Giles Barber)對那個文本做了精湛的考據,既然在他那望重士林的版本已經有所闡明,孔塔的半虛構自傳的真實性不可能有懷疑的餘地。孔塔的敘事屬於印刷從業人員自傳書寫(autobiographical writing)的家系,這個家系從普拉特(Thomas Platter)、根特(Thomas Gent)、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黑斯蒂夫(Nicolas Restif de la Bretonne)、查爾茲‧曼比‧史密斯(Charles Manby Smith)一脈相承。印刷從業人員為了進入這一行,理所當然非要識字不可,至少就排字工人而言是這樣,他們是二、三或四個世紀以前少數能夠親筆記述自己的生活階層的一群人。雖然拼字上的錯誤和文法上的瑕疵在所難免,孔塔的記述或許是這一類著作當中內容最豐富的。可是我們不能夠把它當作忠實反映實際發生的事情。我們應該把它當作是一樁事件的孔塔版本,我們從中讀到他講故事的用心所在。它跟所有的說故事一樣,把故事的內容擺進一個有所指涉的框架,預設了聽故事的人可能會有的聯想與反應,並且為經驗的素材提供有意義的表達形式。但是,既然瞭解其意義所在是我們的首要之務,我們不應該為了書中有捏造的人物就因噎廢食。相反的,把他的敘事當作小說或有意義的偽造,我們可以用它來開拓民族學的文本分析(ethnological explication de texte)。
解讀孔塔的故事,大多數的讀者第一個想到的很可能是:貓屠殺一事是用拐彎抹角的方式攻擊師傅和他的妻子。孔塔把貓屠殺事件安插在述及工人全體和資產階級處境懸殊的脈絡中。此一懸殊的狀態遍及人生的基本要件,包括工作、食物和睡眠。不公不義的情形在學徒似乎特別顯著,他們所受的待遇簡直比動物還不如,因為動物還有機會「升遷」,高高坐在師傅的餐桌上本來應該是留給這些男孩的座椅。雖然學徒受到的非人待遇似乎最嚴重,文本卻清清楚楚告訴我們,殺貓之舉表達了全體工人普遍對於資產階級所懷的恨意:「師傅愛貓,於是〔工人〕恨貓」。主導屠殺之後,雷維耶成為印刷舖的英雄,因為「所有的工人都站在同一條陣線上跟師傅對立。說他們〔師傅〕的壞話,這就足夠博得全體印刷工人的敬重。」
歷史學家有個傾向,視技工製造業的時代為工業化開始之前一段充滿詩情畫意的時期。甚至有人把工坊描述成家庭的延伸,說那裡的師傅和職工有勞同擔,同桌共食,有時候甚至睡在同一個屋頂下。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使得1740年代巴黎印刷舖的氣氛變了質?
在17世紀下半葉,大型印刷廠在政府的支持下淘汰了大多數的小印刷舖,印刷廠師傅形成寡頭團體,攫取了這個行業的控制權。職工的處境惡化就是在這時候。雖然估計的數值不一,統計也不見得可靠,職工的人數似乎維持穩定:在1666年大約有335人,1701年有339人,1721年有340人。此期間,師傅的人數劇減超過一半,從83人降到36人,下限由於1686年的一紙詔書而固定下來。那意味著數量較少的工作場所卻容納數目更多的勞工,這和印刷機密度的統計數字所透露的不謀而合:在1644年,巴黎有75家印刷所,印刷機的台數總共是180;在1701年,印刷所15家,印刷機195台。趨勢如此,職工要想提高到和師傅平起平坐的地位,根本是緣木求魚。工人要想在同行中出人頭地,大概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和師傅的遺孀結婚,因為師傅的身分已經成為世襲的特權,不是夫傳妻就是父傳子。
職工也面臨由下而來的威脅,因為師傅越來越傾向於雇用「黑牌印刷工人」(alloués),也就是沒有達到雇用標準的印刷工人,這些人沒有經過學徒訓練的階段,而學徒訓練乃是理論上使職工晉身於師傅階層的資格。黑牌印刷工人只是廉價勞工的來源,印刷業的高級階層根本沒他們立足之地,1723年又有一紙詔書徹底阻絕他們鹹魚翻身的機會。他們處境之低微,可以從他們的稱呼顧名思義:他們是「待雇」(à louer),不是師傅的「職工」(compagnons)。他們是勞工成為商品這個趨勢的化身,不可能是同舟共濟的伙伴。孔塔當學徒和寫回憶錄就是在這樣背景,那是印刷業職工的艱困時代,當時在聖塞佛倫街上工的人載浮載沉都是險境,印刷業的高層有人要壓他們的頭,底層有人要絆他們的腳。
如何在工坊實地看出前述的一般趨勢?或許可以從納沙泰爾印刷公司(Société typographique de Neuchâtel,簡稱STN)的文件看出眉目。誠然,納沙泰爾印刷公司是在瑞士,而且該公司的業務是在孔塔寫回憶錄之後七年(1762)才展開的。不過印刷業在18世紀並沒有地域上的差別。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檔案有許許多多的細節吻合孔塔記載的經驗。(他們甚至提到同一個名叫柯拉〔Colas〕的工頭,他在皇家印刷廠〔Imprimerie Royale〕曾是傑侯姆的頭頂上司,1779年短期擔任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工頭。)那些檔案提供了近代初期,主人如何雇用、經營、解雇印刷工人的記錄,是流傳到現在絕無僅有的。
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薪資帳冊顯示,工人在印刷所通常只待幾個月。他們離職是因為和師傅爭吵、彼此打架、另謀高就,不然就是沒事幹了。雇用排字工人採用包工制,印刷業行話稱之為labeur或ouvrage。一旦排字的工作結束,就是解雇,這時候也得要解雇一些印刷工人,為的是維持排字部門和印刷房這兩半的均衡(就工作量而言,兩個排字工人通常搭配兩人一組的印刷工人)。工頭跳槽就雇用新手。雇用和解雇就這樣頻進頻出,很難得會連續兩個星期看到同一批勞工。傑侯姆在聖塞佛倫街的同事似乎也同樣頻進頻出。他們也是由於特定的「包工」而受雇,有時候也是和資產階級爭吵之後失去工作——這種情形屢見不鮮,竟至於孔塔在他的敘事所附俚語彙編就有這樣的條目:emporter son Saint Jean(帶走工具箱或去職,猶言「捲鋪蓋」)。只要在一家印刷所工作超過一年,就被看成ancien(資深,猶言「老人」)。有助於我們瞭解當時工作場所的其他俚語包括:une chèvre capitale(一陣火氣),se donner la gratte(動粗),prendre la barbe(喝醉),faire la déroute(上酒館一家接一家),promener sa chape(離職),faire des loups(欠一屁股的債)。
根據從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薪資帳冊統計收入與出貨的情形,即可看出暴力、酗酒和習慣性曠職有多嚴重。印刷工人上班是隨興所之,每個星期的工作量可以相差達一倍,一個星期的工作天數從4到6天不等,上班時間可以是從清晨四點到將近中午之間的任何時候。為了有所規範,師傅尋求人手無不特別強調勤勉和節制這兩項操守。如果碰巧找到熟手,那更理想。日內瓦有家勞工介紹所,他們推薦一個想要進入納沙泰爾印刷公司的排字工人,使用這樣的典型措辭:「他是個好工人,能勝任交付給他的任何工作,滴酒不沾,而且工作勤奮。」
納沙泰爾印刷公司仰賴勞工介紹所,因為該公司本身在納沙泰爾並沒有足夠的勞工來源,而且川流法國全境的印刷工人也有人手短缺的時候。勞工介紹所和雇主往來的信函透露了眾口鑠金對18世紀技工普遍的看法:懶散,輕浮,沒有定性,不可靠。他們不可信任,因此勞工介紹所不應該為他們預支旅費,而且雇主可以扣押他們的財物,用來擔保萬一他們領了工資就潛逃無蹤時可以抵扣。這一來,炒他們魷魚也可以了無愧疚,不管他們是否工作勤奮、是否有家庭需要撫養或是否有病在身。納沙泰爾印刷公司分門別類「訂購」他們,就好像在訂購紙張或字模。該公司抱怨里昂(Lyon)一家勞工介紹所「送來一雙爛貨,我們不得已遣送回去」,還訓了對方一頓,說他驗貨失職:「你送來給我們的人當中,有兩個已經平安抵達,可是病得太嚴重,可能傳染給別人;因此我們不能雇用他們,鎮上沒有人會讓他們住下來。所以,他們又離開了,取道貝桑松(Besançon),以便住進濟貧院。」里昂某書商建議他們,在印刷業不景氣期間解雇大多數的人手,以便挹注法國東部的人力需求,並且「給我們更大的權力管理野性不馴、未經調教的人種,我們實在管不住他們。」在歐洲的某些地方的某些時候,職工和師傅或許生活在一起,像幸福快樂的一家人,可是在18世紀法國和瑞士的印刷舖,絕不是那麼一回事。
孔塔本人相信那樣的情形一度存在。他描述傑侯姆的學徒生涯,一落筆就先提到印刷術剛發明時的黃金時代,印刷工人過著自由自在的日子,彼此平等,就像「共和國」的國民,按自己的法律和傳統管理,充分發揮兄弟間「同心共濟,相親相愛」的精神。他宣稱,那個共和國仍然以印刷工人協會(chapelle)的形態流傳在每一家印刷舖裡。但是政府已經解散共同的協會,黑牌印刷工人已經稀釋會員組織,職工已經被逐出師傅的階級,師傅已經撤退到吃得好又睡得好的隔離的世界。聖塞佛倫街的師傅吃不一樣的食物,維持不一樣的作息,說不一樣的語言。他的妻子和女兒跟花神父打情罵俏。她們養寵物。顯然,資產階級屬於不一樣的次文化,那個次文化最重要的特性是不工作。在引入貓大屠殺的記載時,孔塔擺明了要把工人的世界和師傅的世界作個對比,此一對比正是他貫串整個敘事的線索:「工人、學徒,每個人都在工作。只有師傅和師母在享受睡眠的美味。那使得傑侯姆和雷維耶心裡懷恨。他們決定不要成為僅有的倒楣鬼,他們要主人和女主人一起作伙伴。」也就是說,這兩個男孩要恢復神話的過去,那時的師傅和員工像朋友作伙一起工作。他們也許心裡還想著比較近期發生的小印刷舖銷聲匿跡。於是,他們殺死貓。
可是,為什麼是貓呢?又為什麼殺貓那麼有趣?回答這些問題,得要超越早期現代的勞工關係,進一步思考通俗儀式與象徵這個難解的主題。
多虧民俗學家,歷史學家對於早期現代人劃分曆年的儀式周期(ceremonial cycles)已經相當熟悉。這些周期當中,最重要的是狂歡節(Carnival)與大齋期(Lent),也就是一段狂歡期之後緊接著一段禁食期的周期。狂歡節期間,一般民眾暫時擱置常態的行為守則,儀式性地顛倒社會常規,或者是在遊行中恣情放縱以求驚世駭俗。狂歡節是以學徒為主的青年團體惡作劇的大好時機,他們組織自己的「隱修團」(“abbeys”),推舉隱修院院長(abbot)或國王,在他主持之下演出鬧新婚(charivaris)或戲仿大遊行,以粗獷音樂伴奏,為的是羞辱有紅杏出牆或受婚姻暴力的丈夫,或嫁了個小老公的新娘,或集違背傳統規範之大成的某個化身人物。狂歡節是一年當中歡笑、性與青春百無禁忌的旺季——年輕人在尚未被這個世界的秩序給同化與馴化之前,趁著大齋期嚴肅不苟的日子尚未到來,藉有限度的逸軌衝動測試社會規範的界限。到了懺悔節(Shrove Tuesday),也就是肥美星期二(Mardi Gras,大齋期開始的前一日),麥稈紮成以代表嘉年華之王(King Carnival,又稱Caramantran)的芻像接受一場受審與受刑的大典,狂歡節宣告結束。在某些鬧趣中,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勃艮第(Burgundy),群眾把貓遭受折磨變成一場粗獷音樂會。戲弄綠帽子丈夫或其他受害人的時候,年輕人抓起一隻貓,輪流傳遞,扯牠的毛,惹牠喵喵叫。他們稱之為「弄貓」(Faire le chat)。德國人把這樣的一場鬧新婚叫做「貓式音樂」(Katzenmusik),可能源自貓遭受折磨時發出的哀號。
貓在施洗者聖約翰(Saint John the Baptist)周期也佔有一席之地。聖約翰紀念日是6月24日,也就是夏至那一天。大伙兒在戶外放火,從火上跳過去,圍在四周跳舞,把具有魔力的物件丟進火堆,藉此為下半年驅煞祈福。最受青睞的就是貓——把貓綁起來裝進袋子裡,或是用繩子懸吊,或是綁在柱子上燒。巴黎人喜歡用布袋裝,然後放火燒;聖夏蒙(Saint Chamond)的「追貓族」(cour à miaud)則喜歡沿街追逐身上著火的貓。在勃艮第和洛林,人們圍繞類似火熊熊的五月柱(May pole)跳舞,柱子上就綁著一隻貓。在梅斯(Metz)地區,他們把成打的貓裝在一個籃子裡,擺在火堆上。此一儀式在梅斯可以用奇觀來形容,一直到1765年才被禁。鎮上的顯要參加遊行的行列,抵達Place du Grand-Saulcy之後,點燃柴堆,貓在哀號聲中化成灰燼時,在要塞列隊以待的來福槍手子彈齊發。雖然措施因地而異,要件各處皆同:節日篝火(feu de joie),加上獵巫(witch-hunting)的熱鬧氣氛。......
三、
資產階級梳理他的世界:
城市即文本
如果說農民的格林童話和技工的暴力儀式屬於在今天看來似乎不可思議的一個世界,我們或許期望能夠設身處地,深入18世紀資產階級的想法。機會來了,多虧另一份文本,獨具一格不下於孔塔記敘貓大屠殺。那是1768年所寫,對於蒙彼利埃(Montpellier)這個城市的描述,作者不詳,卻是如假包換的中產階級市民。確實,18世紀信筆而寫的非小說類充斥「描述」(“descriptions”)、旅行指南、曆書以及地方名勝與名人的業餘記載。使得我們說到的這個資產階級人士在這個文類中獨樹一幟的是,他執意要求完整。他要捕捉他生活於其中的那一整個城市,所以他一寫再寫,手稿足足有426頁,含括每一間小禮拜堂、每一個假髮製造商、每一隻流浪街頭的野狗。在他看來,蒙彼利埃市就是宇宙的中心。
他進行這樣一項龐大又詳盡的計劃,確實的原因無從判定。他的初衷也許是出版一本旅行指南之類的書,因為在他自己為《1768年所見蒙彼利埃市現況》(Etat et description de la ville de Montpellier fait en 1768;下文提及本書一律簡稱《現況》)寫的序文中,他做了這樣的說明:他要描述蒙彼利埃,採取的方式將有助於訪客,而且會「揭露一個城市的真貌,那個城市雖然規模不算特別大,卻在王國佔有傑出的地位」。聽他的語氣,他以自己的城市為榮,急於告訴我們有關那個城市的種種,仿如我們是佇立陌生的街角四顧茫然的外國人,他要幫我們帶路。他的立場並沒有不尋常的地方,倒是有個問題值得我們考慮:描述一個世界,這是怎麼一回事?假使我們感受到那樣的一股驅策力,也有那樣的精力,我們會如何把周遭的環境變成白紙黑字?以鳥瞰的觀點著手,然後迴旋漸降,緩緩聚焦於四通八達的幹道路口?或是像個外地人一樣,從鄉間穿過城郊到達市中心壯觀的建築群落,停在市政大廈或教堂或百貨公司的前面?也許我們會以社會學的方法組織描述的內容,從掌握市政的菁英由上而下,或是從工人由下而上。我們甚至可以敲響振奮人心的旋律,從國慶日演說或佈道大會落筆。可行的方法不勝枚舉,起碼多得讓人無從著手。說穿了,就算熱愛這個城市,而且紙張的供應源源不絕,怎麼可能以白紙黑字「揭露一個城市的真貌」?
不妨舉個廣為人知的例子,這個例子可以作為觀察18世紀蒙彼利埃圖的切入點:
倫敦。米迦勒節期(Michaelmas Term)剛過,大法官坐在倫敦的法院大廈裡。彆扭的11月天氣,街道一片泥濘仿如大水新近從地表消退,即使遇到長達四十英尺左右的巨龍,搖搖晃晃像侯本崗上超大型的蜥蜴,也沒什麼好驚訝的。煙囪冒出來的煙緩緩下降,形成一陣軟綿綿的黑霧氣,挾帶煤灰一片片大得像成熟的雪花——飄飄致哀,不難想像是為太陽送終。狗,在泥沼裡面貌難辨。馬,半斤八兩——濺得眼罩都是。行人,撐著傘推來擠去,一個個染上壞脾氣,在街道轉角的地方也沒得立足,那兒自從天亮(如果這一天曾經亮過的話)已經有成千上萬的行人失足滑倒,在層層的泥巴上頭添增新存款,就地沉澱緊緊黏貼人行道,以複利不斷累積。
說到狄更斯(Dickens)所描寫的倫敦,一言難盡。不過,從《廢屋》(Bleak House)的開頭摘引的這些句子足以看出,都市景觀可能負載多麼濃烈的情感、價值判斷與世界觀。污穢、雜亂、四處瀰漫的道德腐敗之氣息附著在老朽不堪的體制,此一景象有如萬無一失的標記,注明該段描述必定是狄更斯筆下的倫敦。我們的蒙彼利埃人定居在截然不同的一個世界。但是,他描述的同樣是憑自己的心思營造出來的世界,即使他沒有狄更斯那種傳達個人感受的文學才華。不管有沒有文學趣味,地方意識(the sense of place)是我們尋求人生定位所不可或缺的。發現到出身於舊制度看來尋常不過的資產階級用文字把它說出來,落筆如流水,這無異於碰上18世紀世界觀的一個基本成分。可是,如何彰顯意義所在呢?
閱讀這位作者的描述,困難重重不下於他當年動筆寫作。每一個語詞都在表達一個陌生的意識,試圖梳理一個如今已不存在的世界。要穿透那個意識,我們有必要對於描述的模式比對於描述的對象付出更大的專注。我們的作者是否運用標準的方案梳理都市地誌?他根據什麼條件劃分這個現象和那個現象?開始動筆時,他如何分門別類整理重大事件?我們的工作不是要揭露蒙彼利埃在1768年是什麼模樣,而是要瞭解我們的觀察家如何觀察蒙彼利埃。
不過,得先說明一下「資產階級」(“bourgeois”)這個立場鮮明的術語。這個術語傷人,教人聽了不是滋味,而且不精確,可是非用不可。歷史學家已經爭議了幾個世代,現在仍然爭論不休。在法國,它通常具有馬克思主義的含義。資產階級是擁有生產模式的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己之意識形態的某種「經濟人」(Economic Man)。他是18世紀的要角,那個世紀縱使談不上完全工業化,卻也是個大肆擴張的時代,根據法國人看待「盎格魯撒克遜」經濟的片面觀點來說就是「起飛」(“le take-off”)。面對經濟權力與政治無力的扞格——在1789年前夕貴族圖謀東山再起的時期尤其雪上添霜——資產階級形成階級意識,接著揭竿起義,領導包含農民和技工在內的民眾陣線掀起法國大革命。這支打擊武力能夠同心齊力,意識形態是一大主因,因為資產階級設法以自己的自由(特別是自由貿易)和平等(特別是摧毀貴族特權)理念滿足平民大眾。到了1789年,啟蒙運動已經大功告成:正如同最望眾士林的法國歷史學家在影響最深遠的法國教科書斬釘截鐵告訴一代讀者,「18世紀對資產階級懷有憧憬」。
中產階級(middle classes)的興起這個歷久常青的主題在18世紀的法國自成一格,係奠定於下述的歷史觀:歷史是經濟、社會與文化三個層面發生作用的過程。層次越深,力道越強勁。因此,經濟的變化引發社會結構的變化,最後則促成價值與觀念的改變。誠然有些歷史學家提出相當不一樣的觀點。羅蘭‧穆斯涅(Roland Mousnier)和他的學生構想出一套理論,主張舊制度乃是以法律規範和社會地位為基礎的禮制社會(society of orders)的理想圖像。馬克思主義學派中有個葛蘭西(Gramscian)傾向,認為在具有霸權地位的社會政治「集團」形成過程中,意識形態的力量具有若干程度的自主性。然而,自從1950年代以降,直到1970年代,法國歷史書寫的主流在於試圖創造以因果三層面模型(a three-tiered model of causality)為基礎的「總體」(“total”)歷史。
這個觀點把資產階級擺在舞台的正中央。身為生產模式的擁有者,在社會結構中不斷攀升,又是現代意識形態的擁護者,他注定要掃除橫梗在他眼前的一切。可是,沒有人對他有足夠的瞭解。他以沒有面貌的一個類別出現在歷史書籍。所以在1955年,三層面總體歷史觀的最高發言人厄涅斯特‧拉伯魯斯(Ernest Labrousse)發起一場運動,直搗資產階級在檔案堆中的藏身之處。根據社會-職業座標方格編纂出來的大量統計調查紛紛出爐,無非是要從18世紀的巴黎開始,為西方世界各地社會結構內的資產階級定位。事實證明巴黎非常棘手。菲雷(François Furet)和杜馬(Adeline Daumard)調查出1749年總共2,597件結婚證書,揭露一個由技工、店主、自由業者、王朝官員和貴族組成的都市社會,但是沒有製造業者,而且只有屈指可數的批發商。侯旭(Daniel Roche)和沃維勒(Michel Vovelle)就巴黎和夏特(Chartres)進行比較研究,得出類似的結論。每一個城市都有資產階級沒錯,不過他們是「舊制度的資產階級」——主要是「食利者」(rentiers),也就是靠年金和地租維生而不必工作,他們和馬克思主義史學(Marxist historiography)所界定的產業資產階級針鋒相對。誠然,在亞眠(Amiens)和里昂等紡織業中心可以找到製造業者,不過他們管理的通常是已經存在數世紀之久的那種外包企業,這和正開始改變英格蘭都市地景的機械化、製造廠生產毫無相似之處。打從法國有企業家以來,他們大體上出身於貴族。貴族的投資並不是僅限於採礦和冶金這些傳統的部門,而是遍及產業和商務的所有領域;反觀商人,他們通常在累積足夠的資金,可以像紳士一樣靠土地和租金或利息生活之後,立即退出商場。
隨專題論著持續湧現,一個城市接一個城市、一省接一省,舊制度的法國越看越覺得古老。最值得稱道的研究,如加登(Maurice Garden)研究里昂以及佩侯(Jean-Claude Perrot)研究卡恩(Caen),挖掘出一些真正的製造業者和批發商;不可否認他們是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但是比起在近代法國所有的城市大量增加而為數眾多的技工與零售商,可就顯得微不足道。可能除了麗里(Lille)和其他城市的一、二個地段,社會史家根本無從找出馬克思主義者所想像的生龍活虎、具備自我意識、促進工業化的階級。莫里諾(Michel Morineau)太離譜了,竟然辯稱經濟在整個18世紀依然停滯不前,又說拉伯魯斯在1930和1940年代製作的穀價上漲曲線圖所具現之經濟擴張的標準景象其實是錯覺——是馬爾薩斯指稱的人口壓力所致,無關乎生產力的增加。經濟體質不可能那麼脆弱,但是顯然尚未經歷一場產業革命,甚至連農業革命也無影無蹤。從海峽的法國這一岸來看,「起飛」是開始了,不過看來是「盎格魯撒克遜」特有的。
此一趨勢有如秋風掃落葉,一舉清除舊制度的三層模式中最低階層的現代性,同時也把第二個階層中大多數人口的進步動力侵蝕精光。前面提到「對資產階級懷有憧憬」的世紀,那個觀念哪兒去了?針對主要的思想中心,即省區(provincial,指巴黎以外的地區)學術機構,所做的大量社會學分析顯示,思想家屬於貴族、教士、政府官員、醫生和律師出身的傳統菁英。啟蒙運動書籍的讀者群看來差不多是同一批人,劇院的觀眾——即使是看「市民劇」(drames bourgeois)這個新劇種看到掉眼淚的那些人——甚至更吻合貴族階級的趣味。正如我們將在下一章看到的,作家群來自社會的每一個行業,只有產業界除外。當然,啟蒙運動文學依舊可以詮釋為「資產階級」,因為那個術語總可以和一套價值觀念相連繫,而那些價值觀總是可以在印刷品找到。可是,那個過程跟跑馬燈沒兩樣,只是冗詞贅語在兜圈子,比如說資產階級文學就是表達資產階級見解的文學,這根本扯不上社會史的邊。此所以學者全面回應「尋找資產階級」的呼聲,可是迄今資產階級仍然面貌難辨。
基於前述的經驗,把我們的蒙彼利埃人當作稀有物種的標本似乎太誇張了——尤其是考慮到我們無法確認他的身分時,益信其然。不過,根據文本所流露他的聲音,我們可以找出他大概的落點。他上劈下砍,劃出兩條分界,把自己和兩種人隔離開來,一種是貴族,另一種是民眾。我們還在扉頁間看到他無比率直的定見:引起他共鳴的是都市社會夾在中間的那個範圍,當中有醫生、律師、管理人員、「食利者」。他們在大多數的省區城市形成「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這些人屬於「舊制度的資產階級」。18世紀使用「資產階級」這個術語時,指的就是他們,而當時的辭書所定義的「資產階級」只不過是「城市的公民」,雖然辭書也注意到其形容詞的特殊用法,如「資產階級的房子」、「資產階級的湯」、「資產階級的酒」,而且書中所舉的副詞用法之例使人想起特定的一種生活方式:「他以資產階級的方式(bourgeoisement)生活,說話,思考。在中午,他以資產階級的方式進餐,跟家人一起,卻稱心如意而且胃口大開。」
從含蓄、切合時代背景的資產階級的觀念著手,我們應該可以將心比心進入《現況》;接著從內部下一番功夫,我們或許能夠在我們的作者藉他的文本所建構的世界中徜徉漫遊。
然而,與其莽撞突進,我們應該先回顧一下歷史學家所建構的蒙彼利埃,即使只是為了找出可以有所比較的地方,以便幫助我們瞭解即將面對的形勢。
18世紀的蒙彼利埃基本上是個行政中心兼市場,在法國南部的朗格多克(Languedoc)這一大片地區中僅次於吐魯茲和尼姆(Nîmes)的第三大都市。該市人口增加非常急速,從1710年大約2萬人增加到1789年大約3萬1千人——不只是因為像其他城市一樣從鄉村地區遷入大量人口,而且因為死亡率降低以及最重要的財富增加。經濟史家如今把「擴張的世紀」——也就是素來被認為是舊制度的最後一個階段——分成三個十年期,從1740到1770年;可是在蒙彼利埃,即使他們沒有促成經濟脫胎換骨,那些年頭也足使幾乎每一個人都生活得更安逸。收成好,價格健全,利潤從該城市的農業腹地源源流向其市場,又擴散到工坊和店舖。
蒙彼利埃畢竟不是曼徹斯特(Manchester)。它生產的是自從中古時代末期就已開始生產的物品,同樣是小規模的作業。試以銅綠(verdigris)的製造為例,以之為業的大約有800個家庭,每年帶來80萬銀元的收益。就在普通住家的地下室製造,把銅盤堆在陶缸裡頭,缸內注滿蒸餾酒。家中的女人每星期一次,刮取盤子表面的「醋酸銅」(“verdet”)。代理商挨家挨戶收集,再由像迪杭父子(François Durand et fils)這樣的大批發商行銷歐洲各地。蒙彼利埃人還製造其他的地方特產:撲克牌、香水和手套。他們有多達兩千人編織羊毛毯,以flassadas之名著稱,根據外包制在自己的房裡工作,織好的就堆在家裡等候經銷商登門收購。羊毛製品就整體而言是已經沒落了,但是省內其他地區所產製的布料卻是以蒙彼利埃為集散地(entrepôt)。1760年代,棉花工業開始發展,有些就在工廠裡,工廠在市區外圍的地帶拓展,雇用的工人數以百計。其中有許多是做印花布和手帕的,其需求量由於吸鼻煙的風氣漸開而大增。可是鼻煙和銅綠都不是促成產業革命的原料,而且工廠只不過是大量的工坊小規模自然發展的結果,裡頭的職工和雇主——相當於傑侯姆和他的「資產階級」——這些工作坊做活的方式兩百年來幾乎沒什麼不一樣。雖然經歷18世紀中葉的擴張,經濟仍然處於未開發狀態——也就是補鍋匠在門口敲敲打打,裁縫師坐在店舖窗口翹二郎腿,商人在賬房秤錢幣的那種經濟形態。
錢幣累積極其可觀,竟使得蒙彼利埃發展出類似寡頭集團的商業勢力。正如同其他的法國城市所看到的情形,商人慣於把資本從貿易轉移到土地和官職。只要在司法界和皇家官僚體系買到高階層的職位,他們立刻躋身貴族之列。最富裕的家庭——拉雅(Lajard)、迪杭、裴雷埃(Périé)和巴齊耶(Bazille)──掌控了蒙彼利埃的社會與文化生活,此一情形由於城裡實質上沒有古老的封建貴族而益形嚴重。蒙彼利埃雖然不是省級最高法院(parlement)所在地,卻是省內最重要的行政中心,是總督府(intendancy)座落之地,不乏省級的達官要人,也有若干王室行宮,富商巨賈的位階因而水漲船高。不過在1768年,城內人口畢竟只有2萬5千左右,位居頂層階級的人數不可能太多。菁英圈子幾乎每個人都彼此認識。參加音樂學會(Académie de Musique)的音樂會,在戲劇院(Salle de Spectacles)看戲,在皇家科學院(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聽演講,還有共濟會會員間的禮尚往來,都是他們聚首的場合。他們每天在帕魯海濱大道(Promenade du Peyrou)散步都有機會打照面,每個星期聚餐,尤其是星期天參加在聖皮埃爾大教堂(Cathédrale de Saint Pierre)舉行的彌撒之後共享大餐。他們當中有許多人也在里戈龐斯書店(Rigaud et Pons)和封塔內(Abraham Fontanel)的讀書會(cabinet littéraire)相聚,在那裡讀同樣的書,包括伏爾泰(Voltaire)、狄德羅(Diderot)和盧梭(Rousseau)的大量作品。
我們的作者在1768年動筆描述的就是這個城鎮——比上不足而比下有餘的一個相當繁榮進步的城市。不過,試圖比較事實(歷史學家呈現的蒙彼利埃)和對於事實的詮釋(《現狀》呈現的蒙彼利埃),不應該把他的描述和我們的描述拿來相提並論。理由是,詮釋與事實糾纏不清,我們永遠不可能分得清楚。我們也不可能跳過文本殺出一條生路直達文本所不能及的確實真相。其實,前面三個段落描述這個城市所採取的分類法正是我在這篇文章批判的對象。那種描述模式是1768年的這個蒙彼利埃人連作夢都想不到的。他從主教和教士開始,接著瀏覽市政當局,最後鳥瞰不同的社會「等級」(“estates”)和他們的習俗。文本的每一個章節循序逐次展開,好像是在進行一場校閱典禮。事實上,《現狀》的前半部讀起來有如播報列隊行進(procession)的實況——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在早期現代歐洲的每一個地方,列隊行進都是大事。亮相的行列展示頭銜(dignités)、身分(qualités)、團體(corps)和等級(états),這是當時認為社會秩序賴以維繫的四大要件。因此,我們的作者在描述他的城市時,採取的方式一如他的同胞安排他們的列隊行進。出入在所難免,整體的形勢並無二致,他把街頭的演出轉化成白紙黑字,因為列隊行進是都市社會傳統慣用的語法。
那麼,蒙彼利埃到底展示些什麼?根據《現狀》的前半部來推敲,一場典型的大列隊行進(procession générale)完全吻合當今所稱一個城市的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它以護送市政官員出席所有重要場合的禮衛隊帶出一陣五彩和聲浪揭開序幕:兩名指揮官一身紅裝,袖口鑲銀線花邊;六名掌旗官穿半藍半紅的禮服,手執銀質令杖和榮譽旌旗,佩帶鎮徽;八名戟兵持矛;一名號手穿紅色制服,鑲銀線花邊,在最前頭奏樂,為跟隨在後的達官顯要引路。
第一等級(教士)先上場,由一系列的宗教兄弟會開始:一隊白衣苦修修士(Pénitents Blancs),手持蠟燭,身穿白長袍,頭藏在連頸帽底下;接著是穿袋型衣,色調深淺有別的較小規模的修會——真十字會(La Vraie-Croix)、萬聖會(Tous les Saints)和聖保羅會(Saint Paul)。這個行列可能多達上百個團體,隨後出現一隊孤兒,身穿普濟院(Hôpital Général,當地的濟貧院)藍色與灰色的粗布制服。男童和女童分隊行進,後頭跟著院裡的6名輔導員,12名管理員,6名理事——這是在聲明該市盡心盡力照顧窮苦無依的人,同時藉此祈求天恩福澤,因為一般認為窮人特別容易蒙受上帝的慈悲。此所以他們經常以喪禮的行列行進,拿著蠟燭和布疋禮物。
隨後出場的是正規的教士,每一個修會都穿各自的傳統服裝,依照在蒙彼利埃成立的年代排定順序:帶頭的是多明我會(Dominicans)8個,其次是科德利埃會(Cordeliers)12個,奧古斯丁會(Augustins)3個,大加爾默羅會(Grands Carmes)3個,加爾默羅脫鞋會(Carmes Déchaussés)12個,慈恩天父會(Pères de la Merci)3個,嘉布遣會(Capucins)30個,靜思會(Récollets)20的,奧拉托利會(Oratorien)一個。隨後還有居家教士:牧師助理(curates)3個和代牧(vicars)11個,代表在城裡3個教區負責監督靈魂的牧師職責。
這時候,一個金、銀合鑄精雕,造形壯觀的十字架宣告主教蒞臨。他在行進的行列中,由主教座堂公禱團員(canons of the cathedral)簇擁著走在聖體餅(Host)之前,一襲粉紅大袍服表示他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同時也是莫吉歐兼孟菲杭伯爵(comte de Mauguio and Montferrand)、德拉馬蓋侯茲侯爵(marquis de la Marquerose)、索佛男爵(baron de Sauve)和德維昏納領主(seigneur de la Vérune),所轄土地每年的收益高達6萬銀元。沒錯,省區之內是有更古老的城市;納博那(Narbonne)、吐魯茲和阿爾比(Albi)都有「大」主教。但是,高級教士一起參加蒙彼利埃的省三級(Provincial Estates)列隊行進的時候,只有蒙彼利埃主教穿粉紅色出現在行列中。其他的23位都穿黑色,僅有的例外是納博那大主教,他也由於地位傑出而有權利穿粉紅色禮袍。在(相對於全省的)市列隊行進的場合,蒙彼利埃主教的粉紅袍服在公禱團員低調、黑色的教士袍和灰色的毛皮連頸帽襯托之下,非常醒目。公禱團員也是根據階級高低(依次為4名Dignitaires、4名Personnats和15名Simples Chanoines)排定行進的先後次序。接在後邊的是整個列隊行進中最莊嚴的部分,即聖體餅,展示在極其精美的遊行用祭壇上的聖體顯供台,上覆華蓋,由當地的6名行政官(consuls)撐支柱護駕。......
第一篇
一、
農夫說故事:
鵝媽媽的意義
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有漏網之魚。說到那些未受啟蒙的民眾,他們的心智世界似乎是一去不返,難以追溯。要為普通人在18世紀找個立身之處,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相當困難,竟至於搜尋他們的宇宙觀顯得愚不可及。但是,在知難而退之前,不妨暫且擱置懷疑之心,先來考慮一個故事——一個無人不知的故事,雖然大家熟悉的不是現在要提到的版本。這個版本卻是18世紀法國農家圍坐在爐火邊度過漫漫長冬時,用來打發上半夜時所說的,縱使細節不完全一樣,也是八九不離十。
從前...
作者序
序
本書探討18世紀法國的思考方式。書中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什麼,而且包括他們怎麼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徑不是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圖尚未標示的一個領域,在法國稱之為「心靈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這個類別在英文仍然無以名之,為了單純起見,不妨稱作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因為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那是民族誌(ethnography)觀察入微所看到的歷史。
大多數人難免認為文化史涉及高級文化,也就是大寫的Culture。小寫的文化史,如果不提希羅多德(Herodotus),可以追溯到布克哈特(Burckhardt);即便如此,世人仍感陌生,還大驚小怪的。因此,或許有必要稍加說明。有別於觀念史家(historian of ideas)追蹤形式上的思想從一個哲學家到另一個哲學家的承傳關係,民族誌歷史學家則研究尋常人如何理解這個世界。他試圖揭露他們的宇宙觀,陳明他們如何在心智上組織現實並且將之表現在行為中。他無意從市井中人找出哲學家,而是要看出市井生活如何尋求策略。尋常人在地面活動,學會「市井之道」——他們也能夠和哲學家一樣擁有自成一格的智能。不同的是,他們思考的不是根據邏輯命題,而是根據事物,或是他們自己的文化中唾手可得的任何其他事物,比如故事或儀式。
什麼東西有益於思考?25年前,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把這個問題應用在亞馬遜河流域的圖騰與禁忌。為什麼不試用在18世紀的法國?懷疑論者會回答,因為不可能和18世紀的法國人面談;意猶未盡的他還會補充說,檔案永遠不可能取代田野調查。說得沒錯,不過舊制度(the Old Regime,法國1789年大革命以前的王朝)的檔案多得出乎意料,不用擔心新問題在舊材料堆中沒有用武之地。進一步來說,可別以為人類學家從在地的語料供應人輕易就有所獲。他也一樣闖進幽暗不明而且無從對談的領域,他也必須解讀在地人對於其他在地人的思考內容所作的詮釋。心靈世界的矮樹叢,在原始林和在圖書館中一樣,是外人止步的。
但是,對於從實地考察回來的人而言,有件事似乎是再清楚不過的:別人畢竟是別人。別人的思考方式和我們不一樣。如果要瞭解他們的思考方式,我們應該從知己知彼著手。用歷史學家處理史料的觀點來看,這句話聽來可能只是老生常談,無非是告誡別犯時代誤置(anachronism)的毛病。然而,這句話還是值得重複申明,因為稍一不慎就可能會指鹿為馬還覺得心安理得,誤以為兩個世紀以前歐洲人就像我們今天一樣思考與感受,誤以為差別只在於他們頭戴假髮、腳穿木鞋。我們有必要不斷擺脫看過去覺得眼熟這樣的錯覺,有必要持續服用治療文化震撼的藥劑。
我相信,不會有比在檔案瀚海中漫遊更好的方法。一封舊制度時代的書信,讀了而不會讓人驚訝迭起,很難——從處處可見的牙劇痛如影隨形,到僅限於某些村落的耙牛屎馬糞展現堆肥功夫,無奇不有。祖先的至理名言,進到我們的耳朵成了鴨子聽雷。翻開18世紀的格言集,你會找到這樣的條目:「誰流鼻涕,就讓他擤鼻子」(He who is snotty, let him blow his nose)。看不懂一句格言、一個笑話、一個儀式,或一首詩時,我們知道其中必有通幽的曲徑。在文件最隱晦之處挑三揀四,或許能夠解開聞所未聞的意義系統。這樣的線索甚至可能引出令人嘖嘖稱奇的世界觀。
本書試圖探索這一類我們不熟悉的世界觀。書中根據大異其趣的文本所帶出的驚訝,循聲窮追猛逐。〈小紅帽〉的一個原始版本,貓大屠殺的一則記載,描敘一個城市的一段奇文,一名警探所保存的令人稱奇的檔案——這些文件不能拿來代表18世紀的思想,當作敲門磚卻綽綽有餘。書中討論的方式是從表達世界觀最含糊籠統的陳述著手,而後越來越精確。第一章是民間傳說的考據,論及的故事在法國幾乎無人不曉,尤其是在農村地區。第二章詮釋一群都市技工流傳的故事。循社會階梯往上爬,第三章說明都市生活對於外省(或鄉下)的資產階級到底有什麼意義。隨後場景轉到巴黎以及知識分子的世界——先是警方所見,他們有自成一格的方法形塑現實(第四章);其次是根據認識論從啟蒙運動的主要文本挑選所得,這份文本就是《百科全書》的〈序論〉(第五章)。最後一章則說明盧梭和百科全書學派分道揚鑣一事如何掀啟思考與感受的新途徑,用與盧梭同時代的讀者的觀點來重讀他的作品,就可以體會出這一新途徑的要義。
閱讀的概念乃是串連所有篇章的一貫之道,因為閱讀一個儀式或一個城市,和閱讀一則民間故事或一部哲學文本,並沒有兩樣。考據的模式容或有所不同,但是不論採用什麼模式,閱讀無非是為了尋求意義——當代人所銘記的意義,在他們人已作古,而且在他們所見的世界景象又時過境遷之後,仍能倖存的意義。因此,我試著讀出自己的一條路來貫穿18世紀,並且在我個人的詮釋之外附錄文本,以便讀者可以自行詮釋這些文本,然後和我唱反調。我並不期望一言而決,也不自命圓滿。本書沒有為舊制度之下所有社會團體與地理區域的觀念與態度提出一份清單,也沒有提供典型的案例研究,因為我不相信有所謂典型的農民或具有代表性的資產階級這樣的事。取而代之的是,我尋求文獻內容看來最豐富的旅程,循序漸進,不預設目標,一旦驚奇絆腳就立刻加快步伐。偏離人跡雜遝的途徑,這或許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方法論,卻有可能出奇致勝,從而享受某些奇觀異景,而那些景觀有可能是最具啟迪之功。我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文化史應該避免稀奇古怪或擁抱常態模式,因為我們無從計算「意義」的平均值,也不可能把「象徵」化約成最小公分母。
筆者坦承不求其系統化,這並非暗示因為人類學無奇不有,所以在文化史裡頭無事不可行。歷史的人類學模式自有其行規,即使此一模式對不帶感情的社會科學家而言,可能看來疑似文學。它起始於這樣的前提:個體無不透過通行的語法從事自我表達,我們在我們的文化所提供的網絡之內透過思考而學習對種種感受進行分類並瞭解事物的意義。因此,這個模式應該可以讓歷史學家發現思想的社會面向,並且從文獻梳理出意義,只要他們深入故紙堆探索其與周遭環境的關連,在文本與其文義格局之間來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條通路穿越陌生的心靈世界。
這樣的文化史屬於詮釋性的科學。由於文學趣味太濃厚,在英語世界似乎難以「驗明正身」,無法名正言順歸入正統的「科學」類別,在法國卻完全吻合人文科學(sciences humaines)。這個類別並不輕鬆,無法求其完美也是意料中的事,不過,即使在英語世界也犯不著因噎廢食。我們全體,包括法國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包括做學問的和種田的,都是在文化的束縛下從事活動,一如我們全都共享同樣的口語成規。所以,歷史學家應該看得出文化如何塑造思考方式,即使是最偉大的思想家也不例外。詩人或哲學家有可能把語言推到極限,卻也難免會有捉襟見肘的時候,以致一頭撞上「意義」的外圍框限。硬要突破那個框限,瘋狂也就為期不遠了——賀德林(Hölderlin)和尼采(Nietzsche)的命運就是現成的例子。不過,在那個範圍之內,立言大德之輩能夠測試並移動意義的疆界。因其如此,狄德羅和盧梭在論及18世紀法國「文化」的書中應該佔有一席之地。把他們和說故事的農民以及對貓展開大屠殺的老百姓相提並論,我放棄了通常對於菁英文化和通俗文化所做的區分,而試著說明知識分子和社會大眾如何應付類似的問題。
我瞭解偏離既定的歷史模式有其風險。有人會反對,說證據太薄弱,不足以深入作古已兩百年的農民的心思。也有人會覺得豈有此理,居然把貓大屠殺說得頭頭是道,還拿來和《百科全書》的〈序論〉相提並論。還有更多的讀者會感到猶豫,認為不遵照有系統的方法檢索經典文本的總目,卻挑選為數有限的怪文獻作為探討18世紀思想的敲門磚,未免武斷。對於這些反對的意見,我有合理的答覆,不過我不希望這篇序文變成方法論述。我寧願邀請讀者進入我自己的文本。讀者不見得信服,但是我希望他們會享受這一趟旅程。
譯序
呂健忠
如果把一個國家的文化比喻為一個有機體,本書可以說是從法國文化史取下一個組織切片,然後拿來做斷層掃描。不論這個比喻有沒有吸引力,展讀本書保證是不可能空手而還的寶山行。關於這座寶山的內容、研究方法的取捨,以及在學術版圖上的落點,原作者羅伯.丹屯教授在序文和結語已有說明。需要補充的,只有一句話:不喜歡學究氣的讀者,只要不理會注釋,將會發覺本書易讀易解又趣味橫生的一面。這裡要交代的是翻譯方面的問題,希望對中文讀者有幫助。
丹屯教授不是採取學術論文的規格,而是採用隨筆的體例,因此行文並不忌諱具有強烈文學趣味的措辭。由於這是原作者刻意的修辭策略,筆者在翻譯時謹守忠於原文的修辭技巧。讀者如果覺得譯文的某些措辭「好像有點奇怪」,很可能就是譯筆亦步亦趨的結果。只就一例而論,本書的後半部(第四章以後)一再出現的「文人共和國」,原文是“the republic of letters”。這個片語固然可以譯成中文讀者所熟悉的「文壇」,可是丹屯教授在第二章提到印刷工人也在追求他們的「共和國」,無非要傳達「階級(或社會等級)共和」的理想。法文另有le monde des lettres的說法,譯成英文即the world of letters,正是我們說的「文壇」或「文學界」,作者捨此就彼,顯然是考慮到 “republic” 在西洋文化史上的意涵。按英文的republic源自中古法文的republique,而這個法文單字在字源學上寓有「共產」,後來出現的引申義不限於「財富公有」,而是作狹義的政治名詞,隱含「平等」的「共和體制」。侯健把柏拉圖對話錄The Republic譯成《理想國》,這是正解;筆者使用「文人共和國」之稱,為的是強調晚出的引申義。
第一章提及民間故事,作者依學界慣例附有安惕‧雅恩(Antti Aarne)編纂,司蒂斯‧湯普森(Stith Thompson)英譯並擴增的The Types of the Folktale: A Classification and Bibliogrphy (Helsinki: Academia Scientiarum Fennica, 1961)書中的「故事類型」標準分類碼。那些民間故事,中文讀者未必熟悉,因此譯者依照該分類表列,增補2001年聯經版《格林童話全集》(林懷卿翻譯)的標題及其編號,以「格林編碼」注明(該中譯本未收錄者,格林編碼從缺)。格林童話故事裡頭的專有名詞,中譯一律依該版本。
丹屯教授開宗明義的切入點是小紅帽的故事。此處所謂的「紅帽」,英文稱red riding hood,根據《圖解服飾辭典》(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編,1985)的解釋,乃是披風和緊合抽碎褶式的連頸帽合成一件式,在顎下繫帶固定,正是許多〈小紅帽〉插圖可以看得到的。筆者雖然採用通俗的標題,內文卻依該辭典譯作「兜狀連頸帽」。單稱「連頸帽」,英文是指hood。在歐洲的服裝史上,hood有許多種形式,均無特定名稱,而統稱hood。在17世紀披肩與連頸帽分離而發展出獨立的帽子之前,hood是官服、禮服、僧袍的一個基本形制(Charlotte Mankey Calasibetta, Fairchild’s Dictionary of Fashion, rev. ed., 1998),正如我們可以在本書第三章描述列隊行進(procession)所看到的。
第二章所稱的「技工」(artisans),廣義包括學徒、學徒期滿的職工以及職工有成當起老闆的雇主,狹義則單指第二類,即職工。職工的英文 “journeyman”,字源本義為「做日工的人」。「雇主」的正式稱呼是master artisan,簡稱master,如本書的用法。這裡的 “master” 兼有「師傅」和「雇主」兩個意思,依次是筆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譯法,他們在18世紀已經躋身資產階級。此一背景說明應有助於一般讀者瞭解第二章的立論與第三章的部分段落。
也許有讀者會懷疑,把工人粗鄙無文的暴力遊戲說得天花亂墜一通,還披上學術的外衣,彷如在二百年前的法國連老粗也懂得舉行意義重大的文化儀式,太離譜了吧?這是正常的反應,不過我想建議這些讀者去參考查爾斯.提利的《法國人民抗爭史》(劉絮愷譯,共二冊,麥田,1999)。弱勢族群(如學徒和職工)以官方認可的方式,對既得利益階層(如招收學徒並雇用職工的師傅)展開抗爭,演出具有諷刺意義的「行動劇」,其標準劇碼之一就是「鬧新婚」(charivari)。特別提醒有興趣的讀者注意該書58-65和217-219頁提綱挈領的介紹(不過,「鬧新婚」和「資產階級」在該書都採音譯,分別為「夏利瓦里」和「布爾喬亞」)。
第五章的關鍵字是philosophe,這個法文單字在英文的同義字是philosopher。可是原作者在四、五、六這三章的遣字,顯然有意區隔這兩個同義字。筆者不敢確定丹屯教授用意所在,但為了明示差別,“philosophe” 一律譯作「哲人」,“philosopher” 則作「哲學家」。
第六章述及盧梭的《新艾洛伊絲》在法國掀啟的浪漫潮,焦點之一是盧梭為該書寫的對話體序文。慶幸的是,這部書信體小說有中譯本(李平漚、何三雅譯,共二冊,林鬱文化,1996),可是該譯本把原來擺在卷首的序文挪到卷末的〈附錄〉(下冊466-493頁),謹此提醒有心的讀者。
近年來,國人翻譯外語人名有揚棄英語掛帥、回歸原語發音的趨勢。「巴赫」逐漸取代「巴哈」即是一例。在法文翻譯,最顯著的例子是音譯 r 的時候,以注音符號的ㄏ取代ㄌ。筆者認同這樣的務本譯法,但也希望能夠兼顧約定成俗的譯名。因此,新古典主義劇作家Racine,我原本按通俗譯名作「拉辛」,卻在譯畢本書之後發覺國立藝術學院戲劇學群演出陸愛玲執導的Racine代表作Phèdre,她用的是「哈辛」,我斷然從善。Cicéro不是法國人,譯成中文讀者熟悉的「西塞羅」是理所當然。但是Roy,據我所知此間普遍作「羅伊」,主要是出現在英語系,因此本書提到這個法國姓,我就譯成比較接近法語唸法的「賀瓦」。歐洲史上赫赫有名的Rohan家族,我譯成「羅昂」,唯一的理由是我閱歷與記憶所及的都這麼譯。“Jean” 這個常見的法國名字,大陸地區普遍譯成「讓」,台灣地區好像譯作「尚」比較多,僵持不下,但是前者顯然比較「合音」,而且吻合此間以注音符號ㄖ音譯法語 j 的趨勢,所以我取前者。然而,由於法文的Jean等同於英文的John,在有必要指明或強調其共通性時(譬如出現在民間故事的小約翰,或與聖約翰有關的基督教典故),我就採用國人熟悉的譯名「約翰」。
一般人名至少不會有誤導之嫌,特定名詞就有可能。沿用本文開頭的比喻,本書掃描出來的是l’Ancien Régime的組織切片。我注意到一直有人把l’Ancien Régime譯為「舊政權」,我懷疑那是根據英譯Old Regime轉譯的。然而,法文的régime主要是指生活方式和社會體制。法國大革命前後之別,不只是在於政權的新舊(法國的每一個共和都是新政權),更在於總體文化新舊有別,所以我採用另一個既有的譯名「舊制度」——這裡的制度是社會制度,不只是政治制度而已。這兩個譯名的差別,本書的讀者務必牢記在心,否則難免觀雲海卻陷五里霧中。就像英文的citizen這個字,應用在現代社會,主要是「公民」的意思。但是14世紀源於法文的這個字,原本是指具有明確社會地位的城市(city)居民;本書用到這個字,幾乎都是這個意思,亦即「市民」,其中隱含社會階級的預設立場。具體地說,只有能夠根據法國舊制度之下社會三等級的傳統分類加以歸類的城市居民,才配稱為「市民」——特別要強調「傳統分類」,因為本書第三章所用到的分類法是從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觀點著眼。借用後現代論述的措辭,citizen作「市民」解,具有強烈的分化意識,刻意製造「凡我族類」和「非我族類」的壁壘——包括「都市」與「鄉村」的二分法——便於區隔「異己」(the Other,即晚近國內習用的「他者」)。可是,我卻經常讀到,有人呼籲大家群策群力,把台灣打造成現代的「市民社會」。
有一個常見的誤譯,也許不是頂嚴重,但因為是屢見屢錯,因此值得一提。歐洲各地(不限於法國)有個通俗的節慶活動,尤其是在慶祝仲夏夜(凱爾特人的大節日,基督教因襲,卻改稱聖約翰紀念日,此一典故是史特林堡的自然主義經典劇作《朱莉小姐》的背景)的時候,就是在空曠地堆木柴點火,原本驅煞辟邪的用意在18世紀可能已經消逝了。這個活動,法文作feu de joie(節日篝火,英文 “bonfire”),和現代的「放煙火」(feu d’artifice, “firework”)根本是兩回事。
前文提到法國舊制度之下社會三等級(僧侶、貴族和市民),這裡的「等級」,有時簡稱為「級」(如「省三級」或「三級會議」),法文是état。特別指出這一點,因為至少在本書的文義格局中,這字眼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是不一樣的,我希望能夠有效區隔兩者的差異。(在等級嚴明的舊制度社會,無法歸入三級分類的「級外之民」是沒有身分地位可言的,因此“gens sans état”是「沒有身分的人」。)同樣的道理,「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雖然有時候被當作同義詞使用,意涵畢竟不同。因此,原文使用 “bourgeoisie” 的場合,譯文作「資產階級」;如果是 “middle class”,譯文則作「中產階級」。必要的時候(如provincial〔省區〕在法國歷史上的特定含義),我會以括弧夾注的方式補充譯文無法求全之處;在不影響行文的流暢以及讀者對原作的判斷這兩個前提之下,我會把譯注化入正文——不過這種情形屈指可數。
拉雜寫下翻譯《貓大屠殺》的一些感想,無非是希望減少讀者在享受閱讀的樂趣時可能受到的干擾因素。多年來從事翻譯工作,我深深體會到克制創作慾的必要——雖然翻譯本身就是一門創作,創作慾的表現卻是翻譯品質的大敵。翻譯本書,我樂在其中,也獲益無窮,最大的期許是應該讓讀者也能分享到這樣的樂趣與獲益。
附記
本書中譯初稿完成迄今整整四年六個月,這一遷延竟然收之東隅,得有機會選入國立編譯館世界學術著作翻譯計劃。翻譯委員會的評審專家憑其精湛深厚的專業素養與一絲不茍的敬業精神,高高撐起審查寶鑑,筆者個人的翻譯疏失與閱歷局限無所遁形。由於此一機緣,筆者在付梓之前又將整部書稿從頭到尾一字不漏詳加覆核,對於評審所提具體的寶貴建議一一斟酌。有些建議,筆者從善如流;即使基於種種理由而另有主張,評審的意見仍有鞭策之功。本人珍惜這樣一個成長的機會,更為讀者慶幸這樣一個精益求精的結果。
關於譯序提及的翻譯事宜,有一點應予補充。第三章〈城市即文本〉數度出現「禮制」一詞,原文是“order”。這個英文字翻成「秩序」固然清晰易解,出現在本書中也的確大多數如此翻譯,但是我覺得「秩序」一詞無法確切表達法國大革命以前以序階為社會倫理之基礎的秩序觀。採用「禮制」這樣的譯法,我想表達的是《論語‧為政篇》所謂「齊之以禮」(朱熹注:「禮,謂制度品節也。」)的秩序觀,這起碼比較接近我所理解的原文,而這一層理解當然是我個人的詮釋。這個詮釋不可能萬無一失,讀者如有疑慮,閱讀該章時儘管把「禮制」改為「秩序」,可也。
序
本書探討18世紀法國的思考方式。書中試圖陳明的不只是人們想些什麼,而且包括他們怎麼思考——也就是他們如何闡明這個世界,賦予意義,並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徑不是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探入文化地圖尚未標示的一個領域,在法國稱之為「心靈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這個類別在英文仍然無以名之,為了單純起見,不妨稱作文化史(cultural history),因為那是以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的同一方式處理我們自己的文明。那是民族誌(ethnography)觀察入微所看到的歷史。
大多數人難免認為文化史涉及高級文化,也就是大...
目錄
中譯序
插圖目錄
謝辭
原作者序
一、農夫說故事:鵝媽媽的意義
二、工人暴動:聖塞佛倫街的貓大屠殺
三、資產階級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
四、警探整理他的檔案:文壇解剖
五、哲學家修剪知識樹:《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
六、讀者對盧梭的反應:捏造浪漫情
結語
注釋
索引
中譯序
插圖目錄
謝辭
原作者序
一、農夫說故事:鵝媽媽的意義
二、工人暴動:聖塞佛倫街的貓大屠殺
三、資產階級梳理他的世界:城市即文本
四、警探整理他的檔案:文壇解剖
五、哲學家修剪知識樹:《百科全書》的認識論策略
六、讀者對盧梭的反應:捏造浪漫情
結語
注釋
索引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1收藏
31收藏

 36二手徵求有驚喜
3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