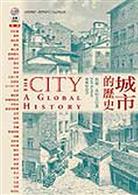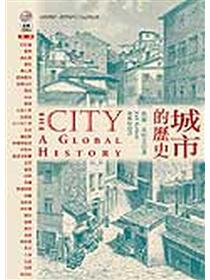「賣完了。」
賣完了?家得寶(Home Depot)的手電筒都賣完了?不可能。手電筒怎麼可能都賣完?
「你說什麼?」雷蒙.費南德茲問。
「對不起,」店員回答。「前兩個小時,店裡簡直亂成一團。我也希望倉庫還有些存貨,不過真的都沒了。全部賣完了。每只手電筒都賣光了。你過幾天再來吧。」
那晚稍早,雷蒙和艾咪準備晚餐時,地板開始搖晃。地震似乎一直持續著,櫥櫃裡的玻璃杯和盤子叮叮咚咚地晃個不停,牆上掛的兩幅畫也都掉了下來。接著燈熄了。雷蒙點燃原本為晚餐準備的蠟燭,他們獨自享用燭光晚餐,並不急著向外逃生。但顯然,有數百人比他們更早一步到家得寶找手電筒。
「喂,等一下,」店員說。「你不是雷蒙.費南德茲嗎?」
雷蒙只是笑笑,然後繼續前進。關於大家認出他這件事,他早已習以為常。他是史丹福繼約翰.馬克安諾(John McEnroe)之後的最佳網球選手,過去三年來奪得NCAA單打冠軍,去年還晉級到溫布頓網球公開賽的決賽。雷蒙或許是灣區最有名的二十歲青年。或許也是美國最有名的二十歲青年。雷蒙小時候,他母親是如何搭著小船逃離古巴、費盡千辛萬苦才抵達佛羅里達州,這段遭遇,即使不關心網球或運動的人也能朗朗上口。
「你認為我們運氣會比較好,買到牛奶或冰塊嗎?」他們一回到車上時,艾咪就問。「還是你覺得乾脆放棄算了?」
「要不要去海沃(Hayward)的大盒子看看?」
「大盒子?」
「就是那家新開的連鎖大賣場,裡頭有家得寶、山姆俱樂部(Sam’s Club)和鮑德斯書店(Borders’)。他們說,賣場後門的營業時間和前門不同。總之,行政劃分上算是不同的郵遞區號。那裡可能是我們買到牛奶的最佳機會,而且搞不好還有賣手電筒呢。或者是燈籠、雷射照明或是別的。他們應該什麼都有賣。」
「好吧。我車子油箱是滿的,就去碰碰運氣吧。」
大盒子在灣區甫開店即不得安寧。一次公投結果讓大盒子遠離舊金山。柏克萊居民則對試圖在該處開幕的門市遊行抗議。迄至目前,唯一一家順利開幕的門市,僅在奧克蘭南部的海沃。
艾咪和雷蒙行經聖馬提橋(San Mateo Bridge)接八八○號公路即至海沃。在大盒子打造下,家得寶就像便利商店,一整天燈火通明。大盒子的停車場之大,竟然有接駁巴士負責將開車前來的購物民眾接送至大門口。一旦進入賣場,大部分的顧客都會搭乘迷你接駁巴士。那是客製的大型高爾夫球車,可依固定路線載顧客至賣場各區,就像小汽車或台車一樣。有些父母帶小孩來這裡,就只為了搭乘迷你接駁巴士,在賣場各處免費試吃或領取贈品。有些家長還會把小孩放在賣場中央大型的樂高天地,然後逕自購物。
雷蒙和艾咪抵達大盒子時剛過午夜。停車場車雖多,他們最後還是找到空位停車,並搭上接駁巴士。不過,要抵達賣場還真是不容易。因為群情激憤的民眾在大門處蜂擁而上,不斷怒吼。雷蒙和艾咪一時之間還搞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遂跟著人潮向前擠去,終於看到實際情況。只見入口內側貼著一張大告示:只有今晚,店內所有商品售價皆漲一倍。原來是反促銷!而且照情況看來,一場公關災難正同時蔓延著。
賣場有位員工拿著擴音器、站在一疊敷蓋1(mulch)的袋子上,試圖安撫群眾。他解釋,這是奧瑪哈下的決定,他也無能為力。他手裡拿著一疊明信片和意見表亟欲送出,以平息群眾情緒、同時確保自身安危。不過,聚集在前門的群眾似乎對領明信片這事興趣缺缺。他們正在找更直接、更立即的反饋表和顧客滿意表。
在失控群眾身後的賣場大門,看來一如往常。小汽車忙碌穿梭其中,儘管額外收費,依然滿載購物乘客。「真不敢相信。」雷蒙低聲喃喃自語。「要走嗎?」他問艾咪。
「我要手電筒。而且若買得到牛奶的話,我也想買一些。反正都來了。我知道,他們是在敲竹槓,但我怕死了。我連一根蠟燭也沒有。在恢復正常以前,我們根本不知道這樣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
他們遂留下來,毫不費力就找到牛奶和手電筒。他們也選了一些電池以防萬一。現場只開放三個結帳櫃台,不過艾咪和雷蒙倒不介意比平常多花點時間排隊。
他們總有聊不完的話題。他們是大一在一場運動員獎學金的會議上認識的,那場會議是為了幫他們處理NCAA規則和法規的複雜部分而舉行。雷蒙那時向隔壁一位高的金髮排球選手借了一枝筆。開始交談後,才發現彼此幾乎毫無交集。她是美國一位市議員的千金,在喬治城長大,讀的是私立貴族學校。她主修生物並計畫上醫學院。雷蒙則在邁阿密的貧民窟成長。他的母親是個清潔婦。他念的是政治科學。她是金髮而他是黑髮。她打排球,他則打網球。他開玩笑說,起碼這兩種運動都有球網。儘管兩人之間存在差異,他們仍繼續聊著天。那晚,他邀她去看電影。很快地,無論是運動、練習、上課,還是寫作業之間的空檔,他們總是在一起。
艾咪和雷蒙站在大盒子結帳隊伍中,兩人的對話突然被前面隊伍裡刺耳的噪音給打斷。一位女子以西班牙文尖叫。這女人一手拿著一瓶嬰兒食品,另一手則將嬰兒揹在身後。這兩樣東西對櫃台人員而言都岌岌可危,於是她舉起雙手以求自保,然而,她以英文的懇求卻對眼前情況於事無補。接著,這女人停止尖叫,開始哭了起來。嬰兒看到媽媽哭泣,也跟著啼哭。收銀員靜佇一旁,正想辦法解決眼前的問題。
雷蒙走到隊伍前面,將手放在那女人肩上,以西班牙文輕聲對她說話。女人不哭了。接著嬰兒也不哭了。收銀員此時面露微笑,同時希望僵局就此結束。
雷蒙向隊伍中的民眾解釋,這個女人身上只有二十美元,但帳單卻要三十五美元。她怎會知道大盒子竟然獅子大開口、突然漲價一倍。因此當收銀員建議她退回一些商品時,她捉狂了。她怎可能不帶些食物和尿布回家給小孩用呢?
雷蒙摘下他的史丹福棒球帽,掏出兩塊錢放進去,並詢問隊伍中的其他民眾,是否也願意慷慨解囊。不到一分鐘,其他人紛紛上前湊齊了不足的十五美元。起先,那女人拒絕了大家的善款。但雷蒙依然輕聲跟她說話,最後,她收下了這筆錢,順利付了帳。雷蒙請艾咪自行結帳,他自己則和這個墨西哥女人又聊了一會。
艾咪從賣場出來後,發現雷蒙站在賣場門前一疊敷蓋的袋子上。在他旁邊的,是那位墨西哥婦女及她的孩子。再隔壁則是之前他們在賣場門口看到的那位大盒子員工。他看來一付想落跑的樣子。但雷蒙卻拿了大盒子的擴音器。那員工認為自己應該和公司資產形影不離。群眾愈聚愈多,也愈來愈安靜。凌晨一點,只見雷蒙.費南德茲拿著擴音器、站在一大疊敷蓋上,讓過往民眾不禁駐足停看,一探究竟。
「是什麼樣的店家,決定從饑童和關愛的母親身上獲取利益?我們必須傳送訊息給奧瑪哈!」群眾以吼聲回應表示贊成。艾咪為雷蒙的倡議和處事風格感到驚奇。他看來一如在網球場上的神態,輕鬆自在。雷蒙又繼續說了一會,引起群眾的好感以及對商家忿忿不平的情緒。要是他此時發號施令,賣場門前的每扇窗戶定會被大家碎成瓦礫。但他卻別有計畫。相反地,他降低了音調,放慢了語氣。他說著貧窮的絕望與約束企業力量的必要。群眾抬頭看著他,呆若木雞。他講完後,大家紛紛鼓掌致意並開始填寫投訴卡。
計畫失控
露絲.李柏的辦公室裡,一排排高及天花板的書架,有些書架上的書甚至得放成雙排,才得以讓更多書藉存放。在辦公室中央的大長桌上,則聳立著歪歪斜斜的書堆。
約莫每隔十年,為了平息同事的嘲笑或揶揄,露絲會清理她的書桌及辦公室中央的桌子。多年前的某個九月,就在她結束夏季打掃沒多久,整個辦公室看來光潔照人,露絲發現有個學生坐在桌前看書,同時啜飲著咖啡。她認出他是新來的研究所學生。於是她坐在桌後,等他開口自我介紹,並且告訴她來此的原因。可是,露絲安靜等了好幾分鐘,這位學生仍然讀著他的書。最後,露絲只好開口詢問,他是否需要幫忙。結果這才發現,他把她的辦公室當成系上圖書館了。他本以為可以坐在這裡念點書、寫些作業的。
這件事在系上相當出名,不過流傳重點卻在於露絲堆積如山的書以及研一學生的怪癖。說真的,露絲的辦公室就像系上圖書館,而她就像圖書館員。露絲確實讀過辦公室裡絕大部分的書,甚至還記得大部分的內容。因此在前網路時代,要找一段引言或事實,直接問露絲,往往可以找到最接近用Google搜尋的結果。
這是何以多年來她桌上總是書滿為患的原因之一。她的書桌也是如此,甚至連地板上也有堆積如山的書,儼然是一幅書市景觀,四處皆為高聳直立的天際線。露絲坐在書桌前,被她的圖書館淹沒,準備春季班第一堂課。但想到自己要上最後一班的經濟學,感覺畢竟十分奇特,思緒不禁漫遊飄忽。
她在這所大學工作已超過四十年。大部分時間都擔任經濟學教授,研究美國經濟史。她在任教生涯中期時立定志向,願當老師多於學者。在許多經濟系中,每年只有一位傑出老師會教有數百名學生選修的大型經濟學入門課。而露絲正是那位老師。
在她任教生涯的晚期,則成為教務長。後來,她真的沒有時間教書了,但仍堅持每年教授一班、選修人數只限二十名的資深研討會。她計畫在暑假退休,因此這是她最後一班。
她一進教室就找了最靠近黑板、佔據大半教室面積的大橡木桌前坐下,並且自我介紹。接著她從公事包中拿出一枝削好的Dixon Ticonderoga二號新鉛筆,放在桌前。
「沒有人可以做出一枝鉛筆。」
露絲說完後便不再繼續。她看著一張張學生的臉孔。他們並不清楚該如何回應。她在挑戰他們嗎?還是跟他們開玩笑?
有位學生舉了手。
「你叫什麼名字?」露絲問。
「喬許。」
「喬許,你的想法是什麼?沒有人可以做出一枝鉛筆。對或錯?贊成還是反對?」
「好像很可笑,」他找到機會說明,接著補充:「恕我冒昧,你可以在校園書店和所有鎮上買到鉛筆。大家隨處亂放。鉛筆真的到處都是。」
「那麼喬許,你可以做出一枝鉛筆嗎?」
「什麼?一枝鉛筆?當然不行。」
「為什麼當然不行?」
「我二十一歲,我……」
「那你認為我可以做出一枝鉛筆嗎?」
喬許把它當成修辭問題思考。自忖:兩個倒下,其餘約六十億的人可以離開。「我們或許運氣較好,可以參觀鉛筆工廠,在裡面找些比較好的鉛筆。」他說。
「其實,我參觀過鉛筆工廠,」露絲說。「但還是沒有人知道如何做出一枝鉛筆。你認為在鉛筆工廠裡會找到什麼呢?」
「有很多人在做鉛筆。」全班哄堂大笑,大家似乎輕鬆了點。「那裡有很多做鉛筆的設備,」喬許繼續表示。「有些是木頭。有些是鉛。有些是橡皮擦。然後作業員把這些材料全部放在一起。能有多難?」
「你有沒有想過,那些鉛是怎麼來的呢?」露絲問。
「我不知道,」喬許說。他從未想過這個問題。但他再接再厲。「他們可能拿一塊木板,打造成鉛筆的樣子,然後鑽一個洞,把鉛放進去。不對嗎?」
露絲搖搖頭。她又把手伸進公事包裡,取出一片薄木板。
「全世界只有一個地方製造這些西洋杉木板、並將它們賣給鉛筆工廠。在工廠裡,他們把十個皆為筆芯寬度的狹窄凹槽、放進每片木板裡,就像這樣。」
她手伸進公事包裡,掏出第二片附有十個凹槽的西洋杉木板。
「接著他們在凹槽內放入一些膠水,再把鉛放進每個凹槽內。當然那不是真正的鉛,而是石墨。有沒有人知道,石墨是從哪裡來的啊?」
無人回答。露絲繼續解釋。
「它存在於斯里蘭卡、墨西哥、中國和巴西的地底。在鉛筆工廠,他們把石墨和從密西西比州取得的黏土,再加上一些水混合後加以燒烤,溫度差不多是攝氏一○三八度。接著他們把烤好的東西翻滾出來,裁切成正確的長度。噹啷!就是我們所說的筆芯。他們將筆芯放進這些凹槽裡,再拿另一個凹面的西洋杉木板放在筆芯上面。於是變成了筆芯西洋杉三明治。看起來就像這樣。」
她又把手伸進公事包裡,拿出另一塊木板。
她繼續說明:「我真正要把話題帶回鉛筆工廠的內容,就是大廳的那枝鉛筆。可能有十公尺長。是真鉛筆附上橡皮擦的完美巨大模型。如果保羅.拜雅(Paul Bunyan,譯注:美國民間傳說中的伐木巨人)或金剛不小心經過,需要時可以派上用場。現在看看這塊西洋杉三明治。它上面烙著十枝鉛筆。我們得讓它們自由。因此會用特別的鋸子,從這塊木板上鋸下鉛筆。首先得裁下底部,看起來像這個樣子。你們可以看到露出來的鉛筆嗎?它們會變成傳統的六面鉛筆。在這裡你們可以看到它們是呈現半裁型。接著他們會把木板翻轉過來,再用鋸子穿過木板,然後出現十枝鉛筆。每枝鉛筆都會上三次漆,添上漂亮的黃鶯色。你們有沒有注意過,它們從未出現在你削好的筆尖上?他們是如何把漆上得這麼完美?」
「他們莫非是用極細的刷子上色的?」喬許猜測。
「沒錯。神明對一些小精靈施了魔法。被施了魔法的小精靈就用刷子把它們刷得漂漂亮亮的。其實,他們是把鉛筆做得過長。漆好後再把鉛筆尾端削掉一點邊,好讓鉛筆看起來乾淨整齊。我愛死了!這種作法比小精靈更讚!他們還不用擔心另一端是不是有點鈍,反正顧客根本看不到,因為被小小的鋁片和橡皮擦給蓋住了。裝好鋁片和橡皮擦後,他們再印上綠色的字母。也就是在光線正常的情況下,你們在蒼蠅身上看到的那種螢光綠。但你們知不知道,在這整個製造過程中,我最喜歡哪個步驟?就是刨西洋杉那段。他們從由三面鋸子裁成的西洋杉三明治中刻出鉛筆,每次用一面,留下一小撮西洋杉。環保署不會讓他們就這樣把這些東西丟掉。你們知道他們怎麼處理嗎?」
喬許開玩笑說:「用來蓋小精靈的小西洋杉屋嗎?」
「喬許,你進入狀況了,不是嗎?但錯了,他們並未依照環保署規定的棄置方式,相反地,他們讓火雞農場的農夫把這些刨剩的西洋杉屑拿走,做為火雞的床鋪。火雞喜歡坐在這些刨屑上面,因此農夫也樂於取用。鉛筆工廠必須把這些東西處理掉,如此一來還可以省下棄置處理費用。生活舒適的火雞則在十月坐在豪華的西洋杉床上,對於即將到來的十一月底的節日完全無覺無感,這件事對我而言感受極為強烈。」
露絲停頓下來,看著全班。
「一枝簡單的鉛筆,」她舉起鉛筆說著,並將它轉向面光處,冬陽透過大片窗戶,在牆上映照出一束束光線。「還有更簡單的東西嗎?可是製造一枝鉛筆卻幾乎是──」她停下來想著合適的用詞。「神奇的。要形容一樣東西是簡單的、世俗的同時又是神奇的,的確令人困惑是不是?然而它卻是井然有序的成果展現,就像一個爵士樂四重奏,當樂團成員散居各地時,演奏更臻完美。表面看來,有些事情根本不可能,但不知為何卻緊密結合,融為一體。妳叫什麼名字?」露絲指著一位坐在後面、看來毫無印象的女生問道。
「安潔雅。」
「安潔雅,妳認為呢?究竟神不神奇?」
「李柏教授,那很不錯。但畢竟只是一枝鉛筆,不是嗎?」
「妳確定嗎?這就是妳的結論嗎?只是一枝鉛筆?從一塊未經處理的簡單木板開始。有人砍下一棵種植在加州的西洋杉,運送至工廠。工廠的人把那棵樹做成木板。從砍樹、送到工廠、刨平、削好成形,看來似乎十分簡單的一個動作,卻花上數以千計的人力來處理這塊木板。有人製造砍樹的鋸子、有人開著載運木頭的卡車、有人在工廠將這些木頭裁切成形,還有人製造工廠裡用的機器,而為的不過就是這塊木頭。接著還要處理石墨加工事宜。在斯里蘭卡有無數的人在工作,把石墨從地裡取出來後送至工廠。鋁套圈則來自日本。橡皮擦是從韓國、有時是從加拿大進口的合成橡膠。在鉛筆塗上愉悅陽光般色彩的漆,則是從田納西州或紐澤西州來的。而這些都只是基本的組件。東西送到工廠後,所有工作者再將這些材料組合完畢。他們用另一大群人製造的機器設計並打造。沒有一個人可以獨力完成所有的步驟。它會花上數以千計人的一生。因此沒有人可以製造一枝鉛筆。」
「所以一枝鉛筆有多人的心血投入,」安潔雅說。「眾人分工合作。有什麼了不起?它的神奇之處在哪裡?」
「是誰指揮軍隊?」
「什麼?」
「是誰指揮軍隊?」
「什麼軍隊?」
「一群將這枝鉛筆從無到有製造出來的軍隊。是誰在負責的?這群效力的軍隊,他們的將軍在哪裡?鉛筆大王人在哪裡?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為什麼需要這樣一位將軍?」安潔雅問。
「每年都有人砍下正確數量的西洋杉,或是從地底取出正確數量的石墨,以製成所有的鉛筆,即使這兩種物品可以用來做成一千種其他的東西。為什麼總有足夠的數量供應製作?餐廳女侍從來不會對卡車司機說:『呃,抱歉──今天的咖啡已供應完畢。』工廠從來不缺西洋杉。無論你九月甚至一月時現身校園書店,不管你想要一枝還是一打,那裡總有數量充裕的鉛筆供你購買。書店從來不會告訴你:『對不起,鉛筆賣完了,請你七月再來一趟,我們的供應商屆時應可提供一些。』而這只是開端。是誰決定這個軍隊的人數?是誰決定他們的工作內容?是誰告訴全世界從事鉛筆製造的人該做什麼?何時做什麼?是誰確定所有的工人都善盡職責?不知為何,有一百萬人散居世界各地協力合作,可是這些工作卻沒有一個統籌負責的人。斯里蘭卡的石墨礦工從來不曾和那些將西洋杉運到鉛筆工廠的卡車司機溝通。這是何以它有如與其他散居全國各地的三人共同演奏爵士樂一樣。沒有腳本。沒有總譜。沒有指揮。這難道不特別嗎?」
全班靜默。大家不確定該如何回應。在課堂內受老師講課內容吸引可謂極不尋常,況且還是圖表之外的一枝鉛筆。
「注意這點,」露絲繼續表示,「注意一枝鉛筆的神奇,但這仍不夠值得注意。因為神奇之處隱藏於後。這有點像是靜樂,鉛筆的音樂。一旦了解箇中奧密後,你便能在腦海中聽見它的悠揚樂音。音樂之源、神奇之源即為亞當.史密斯所稱的『對於買賣、交易和以物易物的習性。』史密斯了解那種秩序可以在無人負責的情況下出現,並且執行上述命令,而這單純是從大家彼此買賣而來。你可以有個組織井然有序、但卻沒有組織者的系統。是什麼將這個系統結合在一起?是什麼建立了這個分工合作的網路,讓所有不同的人齊聚一堂、共同打造了我手中的這枝鉛筆?妳叫什麼名字?」
「艾咪。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當然。」
「妳說無人負責,可是妳提的那家鉛筆工廠是有老闆的。那裡的工人不光只是到工廠上班、做著份內工作,然後就噹啷!冒出一枝鉛筆了!還是有人負責訂購木頭、鋁、橡膠,雇用工人,監督工人,決定支付他們工資,有時還會裁員。有人則決定是否該買石墨或是在工廠製造。它並非真正自動自發完成的。還是有人在負責的。」
「那是個想像。」
「妳指的是什麼?」艾咪問。「是說那些人在組織中有許多自主權?」
「哦,那也是當然的,」露絲回答。「但我指的是更為複雜的層面。我的意思是說,『有位老闆在負責』這樣的說法只是一種想像。看起來像是老闆決定該雇用誰、該叫人走路、該支付工人多少工資、是否該擁有一家西洋杉農場或是向另一家公司購買西洋杉。這位老闆甚至不用決定這枝鉛筆的定價。」
「但是,這些若非由老闆作出的決定,那麼究竟是誰呢?」艾咪問。
「沒有人。」露絲停頓了一會、沒再繼續往下說,讓全班陷入沉思。教室突然變得非常安靜。露絲自忖,我愛教書也愛經濟學。「了解那些事情如何可能成真,正是我們要花上這季剩下時間所要了解的內容,」她說。「同時,還有作業!」她在教室前方踱步。「下堂課,想想這個世界上,在我們周遭,有什麼是自我組織性的東西。找找看哪些東西即使在無人負責的情況下,依然展現了秩序或目的。找找看。它們無所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