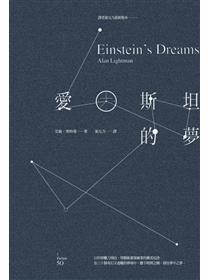一個天藍色的冬日,七歲的艾斯沙、瑞海兒與全家老小無不期待,全力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大事――住在英國倫敦的表姊蘇菲即將來訪印度,並與大家共度聖誕佳節。沒想到快樂的表象之下,卻醞釀著一股「恐怖」風暴,並在一天之內,悲劇性地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本書以一對孿生兄妹的故事,牽引出一個民族中愛與恨、哀傷與喜悅、貧與富、階級與種族等糾葛難解的問題。阿蘭達蒂‧洛伊以細膩的筆觸,巧妙的情節鋪陳,與魔幻寫實的文字風格將一部家族史無懈可擊地濃縮至短短數天中,充滿張力,讀來令人屏息。這是一部可比擬馬奎斯小說,百年難得一見,足以流傳久遠的文學經典。
作者簡介:
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 著
印度英籍的洛伊學的是建築,曾寫過兩本電影劇本。《微物之神》是她在三十七歲時所發表的的第一部小說創作,也是至今唯一的一部小說創作。一九九七年,洛伊初試啼聲即勇奪英國最具權威的文學大獎──「布克獎」(Booker Prize),震驚世界文壇。對於新人的獲獎,布克獎評審團主席比爾(Gillian Beer)教授表示:「我們(評審們)全都為這部動人的小說而著了迷。」獲獎之前,《微物之神》在一九九七年四月甫自英國出版時,便洛陽紙貴,一書難求;在美國出版後,也立刻躍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達數十週。本書已翻譯成四十餘種語言,在近三十個國家出版,總銷售量超過千萬冊。十多年來,洛伊的創作光芒可說得到了全球的矚目與肯定。
各界推薦
得獎紀錄:
英國「布克獎」得獎作品
美國《時代雜誌》年度最佳小說
英國BBC「大閱讀」票選百大小說
得獎紀錄:英國「布克獎」得獎作品
美國《時代雜誌》年度最佳小說
英國BBC「大閱讀」票選百大小說
章節試閱
1 天堂果菜醃製廠 阿耶門連的五月是一個炎熱、陰沉沉的月份。白日長而潮溼,河流縮小。黑烏鴉貪婪地吃著靜止、布滿灰塵的綠色芒果樹上那些鮮艷的果實。紅白蕉成熟了,菠蘿蜜脹裂開來。放浪形骸的青蠅在溢滿果香的空氣中,空茫茫地嗡嗡鳴叫著,然後撞在明亮的窗玻璃上,一命嗚呼,肥胖的身體在陽光下顯得不知所措。
夜,澄澈無雲,但瀰漫著懶散的情緒和沉重的期待。
但是到了六月,西南季風吹來。有三個月,風刮著,雨下著,偶爾刺眼、閃爍的太陽才露一下面,而興奮的孩子則趁機大玩一番。鄉間一片恣肆的綠,當插在地上作為籬笆的樹薯枝幹生根且開花時,界限變模糊了。磚牆出現綠苔,胡椒的藤蔓蜿蜒爬上電線桿,野生爬藤植物迸出鋁紅土岸,爬過淹水的道路,船在市集來回穿梭,而小魚兒出現在公共工程部於公路製造的坑洞積水裡。
當瑞海兒回到阿耶門連時,正下著雨,銀繩般斜斜的雨猛擊著鬆散的地面,像炮彈似地將泥土翻起。山上老房子陡陡的山形屋頂低垂下來,像是一頂拉得低低的帽子。布滿苔痕的牆已經鬆動了,而且因地面往上滲出的溼氣而微微膨脹。荒蕪、長滿野草的花園,充滿了小生命的耳語和疾行。矮樹叢中,一隻蛇鼠靠在一塊閃亮的石頭上摩擦身子。滿懷希望的黃色牛蛙在多浮渣的水塘巡行,想尋找配偶。一隻溼淋淋的貓鼬掠過散布著樹葉的車道。
房子本身看起來空蕩蕩的,門和窗都上了鎖。前陽臺光禿禿的沒有任何裝設,但是那輛有鍍鉻尾翼的天藍色普利茅斯仍停在外面;而在屋內,寶寶克加瑪仍然活著。
她是瑞海兒的姑婆,她外公的妹妹。她的真名是娜華蜜——娜華蜜.伊培,但是每個人都叫她寶寶,長到夠當姑媽的年紀時,她變成了寶寶克加瑪。然而,瑞海兒不是來看她的,孫姪女和姑婆都不曾對這件事懷著任何幻想。瑞海兒是來看她的哥哥艾斯沙的。他們是異卵雙胞胎,醫生稱他們為「雙胚子」,這是由兩個分開,但同時受精的卵生成的。艾斯沙——艾斯沙本,比瑞海兒早十八分鐘出生。
艾斯沙和瑞海兒不甚相像,向來都是如此。即使當他們還是手臂細瘦、胸部扁平、飽受寄生蟲折磨、梳著貓王式飛機頭的孩子時,帶著誇張微笑的親戚,或經常來到阿耶門連房子求捐獻的敘利亞正教主教,也不曾像問其他雙胞胎那樣地問他們「誰是誰」,或「哪位是哪位」。
混淆藏在更深入、更隱密的地方。
在早先那未定形的幾年,當記憶才剛剛開始,當生命充滿了開始,沒有結束,而一切都是永恆時,艾斯沙本和瑞海兒認為:在一起時,他們是「我」;分開時,他們是「我們」。彷彿他們是罕見的一對暹邏雙胞胎,身體分開,但本性卻相連。
現在,在這些年後,瑞海兒仍記得,她曾在一個晚上醒來,因艾斯沙的一個滑稽的夢而吃吃地笑著。
她甚至有其他她無權擁有的記憶。
例如,雖然她沒有在場,但是她記得在阿布希拉許戲院裡,賣柳橙和檸檬飲料的人對艾斯沙做了些什麼。她記得在前往馬德拉斯的馬德拉斯郵車上,艾斯沙所吃的番茄三明治的味道。 而這些只是瑣屑的事情。 不管怎樣,現在她認為艾斯沙和瑞海兒是「他們」,因為分開時,這兩個人不再是以前的「他們」,或他們曾經想像過的「他們」。 曾經。 現在,他們的生命有了一個尺寸和形式。艾斯沙有他自己的尺寸和形式,瑞海兒也有她自己的尺寸和形式。
邊緣、邊界、分界線和界限,在他們個別的地平線上出現,就像一群侏儒——有著長長的影子,在「模糊的末端」巡視的小矮人。柔和的半月形眼袋在他們的眼下形成了,現在他們和阿慕死時一樣大。三十一歲。
不算老。
也不算年輕。
一個可以活著,也可以死去的年齡。
他們幾乎是在公車上出生的,艾斯沙和瑞海兒。他們的父親開車載他們的母親阿慕到席隆的醫院生產,但這輛車子在阿薩姆一條蜿蜒的茶莊道路上故障了。他們丟下那輛車子,揮旗讓一輛擁擠的州交通部的公車停下來。坐在車上的乘客帶著一種窮人對於較富裕的人所懷有的奇怪憐憫讓位給他們,或者,他們這樣做只是因為看到阿慕奇大的肚子。在剩下的旅程中,艾斯沙和瑞海兒的父親必須抱住他們母親的肚子(以及肚子裡的他們),以免肚子搖搖晃晃。這是在他們離婚,而阿慕回到克洛拉居住之前。
艾斯沙認為,倘使他們在公車上出生,那麼他們這一生將可免費搭公車。不知他們從哪裡得知這類事情,或者如何得知這類事情。但是有幾年時間,這對雙胞胎對於他們的父母懷著一種隱約的不滿,因為父母毀掉了他們終生免費搭公車的權利。
他們也相信,倘使他們在過斑馬線時被車子撞死了,那麼政府會負擔他們的葬禮費用。他們十分肯定地認為,斑馬線就是為了這目的而存在的。免費的葬禮。當然了,阿耶門連沒有這種可以讓人被車撞死的斑馬線,甚至科塔亞姆——離此最近的一個鎮——也沒有。但是當他們坐兩個小時的車子去科沁時,曾在途中,從車窗看到了一些這樣的斑馬線。
政府從來沒有負擔蘇菲默爾的葬禮費用,因為她不是在斑馬線上被撞死的。她的葬禮是在阿耶門連的一間剛上漆的老教堂舉行的。她是艾斯沙和瑞海兒的表姊,也就是恰克舅舅的女兒。她從英國來拜訪他們。當她死時,艾斯沙和瑞海兒七歲,而蘇菲默爾快九歲了。她躺在一個孩子專用的小棺材裡。
有緞子襯裡。
黃銅把手閃閃發光。
她穿著克林普蘭黃色喇叭褲,髮上繫著緞帶,手裡拿著她喜愛的英國製時髦帥氣的袋子。她的面孔蒼白,而且布滿皺紋,就像洗衣者的一根在水裡泡了太久的拇指。教友們聚集在棺材四周,漆成黃色的教堂因憂傷的歌唱聲,而像喉嚨那樣膨脹著。留著卷曲鬍鬚的神父搖動著掛在鏈子上的乳香缽,而且不曾像一般星期日那樣對著嬰兒微笑。
祭壇上的長蠟燭彎曲了,但短蠟燭沒有彎曲。
葬禮上有一個佯稱是遠房親戚的老婦人,沒有人認識她,但她常常於葬禮中出現在屍體旁。一個對於葬禮上了癮的婦人?一個潛在的戀屍癖者?她將古龍水倒在一小塊生棉之上,然後帶著虔誠的模樣和溫和的挑戰神情,拿這塊生棉輕拭蘇菲默爾的額頭。蘇菲默爾聞到了古龍水和棺木的味道。
瑪格麗特克加瑪(蘇菲默爾的英國籍母親)不讓蘇非的生父——恰克,將手臂搭在她身上安慰她。
這一家人擠成一團站著。瑪格麗特克加瑪、恰克、寶寶克加瑪,以及她旁邊的嫂嫂瑪瑪奇——艾斯沙、瑞海兒的外婆以及蘇菲默爾的奶奶。瑪瑪奇幾乎看不見了,到屋外時,總是戴著墨鏡。她的眼淚從鏡片後滴下來,沿著她的顎部抖動著,就像屋頂邊的雨滴。她穿著那件乾爽、白裡透灰的紗麗,顯得瘦小而病懨懨。恰克是瑪瑪奇的獨生子,她自己的悲傷令她難過,而他的悲傷則將她擊垮了。
雖然他們容許阿慕、艾斯沙和瑞海兒參加葬禮,但是,他們叫這三人站在一旁,不能和其他家人在一起。沒有人看他們。
教堂裡非常熱,白星海芋花的白色邊緣起皺、卷曲。一隻蜜蜂死在棺材裡的一朵花裡。阿慕的手顫抖著,手中的讚美詩集也跟著顫抖。她的皮膚是冰冷的,艾斯沙靠著她站,幾乎還在睡夢中,疼痛的眼睛閃爍如玻璃,燃燒的臉頰貼在阿慕拿著讚美詩集那顫抖、赤裸的手臂上。
但是瑞海兒卻十分清醒,保持高度的警覺,而且因為正和「真實的生命」戰鬥著,而變得精疲力盡和脆弱。
她注意到蘇菲默爾醒來參加她自己的葬禮。她讓瑞海兒看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是黃色教堂剛剛上漆的高圓頂,瑞海兒以前不曾從裡面觀看它。它被漆成藍色,像天堂那樣,有飄浮的雲朵和颼颼作響、白煙尾巴與雲朵交叉的小噴射機。的確(我們必須說),躺在棺材裡往上看,比站在教堂座席中,被憂傷的臀部和讚美詩集包圍,更容易注意到這些東西。
瑞海兒想到有人費力地拿著刷子、稀釋劑和一罐罐的油漆爬到那兒,白色的油漆用來畫雲,藍色的油漆用來畫天堂,銀色的油漆用來畫飛機。她想像他爬到那兒,某個像維魯沙的男人,光著身子,閃閃發光,坐在一塊木板上,懸吊在教堂高圓頂中的鷹架上,在藍色的教堂天空畫銀色的噴射機。
她想到如果繩子斷裂了,會發生什麼事情。她想像他像一顆黑色的星星那般,從他自己創造的天空掉落下來,支離破碎地躺在發燙的教堂地板上,黑色的血像祕密般,從頭顱流出來。
那時,艾斯沙和瑞海兒已經知道這個世界有將人擊碎的其他方式。他們已經熟悉那氣味,令人噁心的香味,就像微風中即將凋謝的玫瑰的味道。
蘇菲默爾讓瑞海兒看的第二樣東西,是那隻蝙蝠寶寶。
在追悼儀式中,瑞海兒看著一隻黑色的小蝙蝠用牠那溫柔緊貼的卷爪,爬上寶寶克加瑪那件葬禮時穿的昂貴紗麗。當牠爬到她的紗麗和上衣之間,爬上她那團似有愁容的脂肪,爬上她赤裸的腰身時,她大聲尖叫,拿她的讚美詩集擊打空氣。教堂內的人停止歌唱,紛紛問「什麼事?怎麼了?」然後蝙蝠颼颼地旋飛,紗麗啪噠啪噠地翻動。
神色憂傷的神父用戴金戒的手指將卷曲的鬍鬚清理乾淨,彷彿幾隻隱密的蜘蛛突然在那兒結了網。
小蝙蝠往上飛入天空,變成一架噴射機,一架白煙尾巴沒有和雲交叉的噴射機。
只有瑞海兒注意到蘇菲默爾在棺材裡祕密地翻筋斗。
憂傷的歌唱聲又響起了,他們將那首憂傷的詩歌唱了兩遍,而黃色的教堂再次像喉嚨般因歌聲而膨脹著。 當他們將蘇菲默爾的棺材放入教堂後小墓園的地裡時,瑞海兒知道她還沒有死去。她替蘇菲默爾聆聽紅泥輕柔的聲音,以及將閃亮的棺材洋漆糟蹋的橘色鋁紅土的重擊聲。她透過光亮的棺木,透過棺材的緞子襯裡,聽到單調的砰砰聲。神色憂傷的神父的聲音因泥土和棺木的阻隔而變得模糊。 我們將這個離去孩子的靈魂 交在你手裡,最慈愛的天父。 我們將她的身體交給土地, 土歸於土,灰歸於灰,塵歸於塵。 在地裡,蘇菲默爾尖叫著,並以牙齒將緞子襯裡咬碎。但是你無法透過泥土和石頭聽到這些尖叫聲。 蘇菲默爾死了,因為她不能呼吸。
她被自己的葬禮殺死。塵歸於塵歸於塵歸於塵歸於塵。她的墓碑上寫著:「賜給我們的一道稍縱即逝的陽光。」
阿慕後來解釋說:「稍縱即逝」就是「太短暫」的意思。 葬禮後,阿慕帶著雙胞胎回到科塔亞姆警察局。他們很熟悉這個地方。前一天,他們在那兒度過很長的一段時間。他們料到瀰漫在牆上和家具上的那股嗆人的尿騷味會撲鼻而來,所以事先將鼻子捏緊。
阿慕要求見警察局的警官。當她被帶到他的辦公室時,她告訴他說,他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所以她要做一個供述。她要求見維魯沙。
巡官湯姆斯.馬修的髭鬚十分茂密雜亂,就像印度航空公司的印度大君像的髭鬚。但是,他的眼睛狡猾而貪婪。
他說:「妳不認為現在做這些都太遲了嗎?」他說的是科塔亞姆一地所用的粗糙的馬里亞勒姆語。當他說話時,眼睛瞪視著阿慕的胸部。他說警方該知道的事,他們都知道,也說科塔亞姆的警察不接受「維緒亞斯」(妓女)或其私生子的供述。阿慕說她會處理這件事。巡官湯姆斯.馬修繞過桌子,帶著警棍走向阿慕。
「如果我是妳,」他說:「我會安安靜靜地回家。」然後,他以警棍輕拍阿慕的胸部,溫柔地拍一拍,彷彿正從籃子裡指出哪幾顆芒果要人包起來送去給他。巡官湯姆斯.馬修似乎知道可以找誰的麻煩和不可以找誰的麻煩。警察具有這種直覺。
在他後面,一個紅藍相間的布告板上寫著:
禮貌
服務
忠誠
智慧
謙恭
效率
當他們離開警察局時,阿慕哭泣著,因此艾斯沙和瑞海兒沒有問她「維緒亞斯」是什麼意思,或者「私生子」是什麼意思。那是他們第一次看見他們的母親哭。她並沒有啜泣,她的臉像石頭般一動也不動,但是眼淚從她眼中湧出來,流下她僵硬的臉頰。這使得雙胞胎因害怕而難受。阿慕的眼淚使得目前一切似乎不真實的事物變真實了。他們搭公車回到阿耶門連,車掌是一個穿著卡其衣服的瘦削男人,他拉著公車的扶手朝他們滑行過來,然後讓他瘦骨如柴的臀部靠著椅背,並拿出打孔機對著阿慕喀喳地在車票上打孔。「去哪裡?」喀喳聲是有涵義的。瑞海兒可以聞到一疊公車票的味道,及車掌手上的鋼製公車扶手的酸味。
「他死了,」阿慕輕聲對他說:「我殺死了他。」
「阿耶門連。」艾斯沙趕緊說,免得車掌動怒。
他從阿慕的皮包裡拿出錢。車掌把車票給他們。艾斯沙小心翼翼地將車票折疊起來,放在口袋裡。然後,他伸出細小的手臂抱住他僵硬、流淚的母親。
兩星期後,艾斯沙被送走了。阿慕被迫將他送回到他父親那兒,後者當時已辭去了阿薩姆茶園的寂寞工作,搬到加爾各答為一個製造炭黑的公司工作。他已再婚,幾乎戒酒了,偶爾才會舊疾復發。
自那時起,艾斯沙和瑞海兒便沒有再見面了。
現在,二十三年後,他們的父親又將艾斯沙送回來了。他將他和一只行李箱及一封信一起送回到阿耶門連。寶寶克加瑪讓瑞海兒看那封信。信上的字跡是歪斜的、女性化的,像出自一位修會學校的女學生之手,但下面卻有他們父親的簽名,或者至少名字是他的。瑞海兒認不出那簽名。信上說,他(他們的父親)已經自製造炭黑的工作退休,而且正要移居澳洲,他已在那兒找到了一份在磚瓦工廠當警衛長的工作,但無法帶著艾斯沙和他一起去。他向阿耶門連的每一個人獻上他最大的祝福,並說如果他回到印度,他會來探望艾斯沙。但是他也說,他不太可能再回來了。
寶寶克加瑪告訴瑞海兒,她可以保存那封信。瑞海兒把信放回信封裡,信紙已經變軟了,像一塊布那樣地被折起來。
她已經忘了阿耶門連的季風空氣是多麼潮溼。膨脹的櫥子咯吱咯吱作響,鎖起的窗脹裂開來,書頁在封皮之間變軟、成波狀。不曾見過的昆蟲像意念般出現在黃昏裡,然後在寶寶克加瑪昏暗的四十瓦燈泡上將自己燒死。白天,牠們酥脆的、被焚化的屍體散布在地板和窗臺上,在克朱瑪莉亞將牠們掃到塑膠畚斗之前,空氣中散發著東西被燒的氣味。
仍然沒有變,那六月的雨。
天門敞開了,水往下敲打,使不情不願的老井甦醒過來,讓沒有豬的豬舍長出綠苔,對著靜止的茶色水坑做地毯式的轟炸,就像記憶對靜止的茶色心智進行轟炸那樣。草看起來溫潤、翠綠而滿足,快樂的紫色蚯蚓在泥濘中嬉戲,綠色的蕁麻點點頭,樹木彎下腰。
在更遠的地方,在風雨中,在河岸上,在白日突來的雷電交作的黑暗中,艾斯沙走著。他穿著一件接近濁紅色的粉紅圓領汗衫,經雨水潤溼後,汗衫的顏色變得更暗了。他知道瑞海兒已經來了。
艾斯沙向來是個安靜的孩子,因此,沒有人可以準確地指出他何時停止說話(幾月、幾日或哪一年)。這是指完全停止說話。事實上,這件事不是發生在某個「明確的時候」,而是一種漸漸封閉的過程,一種幾乎沒有人注意到的漸漸變安靜的過程,就彷彿他只是把話說完了,再也沒有話可說了。然而,艾斯沙的靜默從來不是笨拙的,從來不干擾人,也從來不吵鬧。與其說那是一種控告性、抗議性的沉默,不如說那是一種夏眠、一種冬眠,一種肺魚藉以度過乾季的方法的心理相對物;只是在艾斯沙的情況中,乾季似乎將永遠持續下去。
他漸漸獲得一種能力:融入任何他所在之處的背景中。他融入書架、花園、窗簾、門口和街道,顯得沒有生氣,使得未經訓練的眼睛幾乎看不到他的存在。陌生人和他同在一個房間裡,往往必須經過一段時間後才會注意到他,而且必須經過更長一段時間後,才注意到他不曾開口說話。有些人則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
艾斯沙只占據這個世界一個很小的地方。
蘇菲默爾的葬禮結束後,艾斯沙被送回到他父親那兒,而後者將他送到加爾各答一所男子學校就讀。他不是一個出類拔萃的學生,但也並非落在眾人之後,而且沒有哪一方面表現得特別差勁。在他的學年進度報告上,老師給他的評語一般是——「中等學生」或者「表現尚令人滿意」。「沒有參加團體活動」是另一個常見的抱怨,雖然他們不曾說明「團體活動」究竟是指什麼。 艾斯沙以中等成績自中學畢業,但拒絕上大學。他做了一件起初令他父親和繼母感到非常困窘的事:開始做家事。彷彿要以自己的方式謀生似的,他掃地、拖地、洗所有的衣物,並學會烹調和買蔬菜。坐在上了油、閃閃發光、堆成金字塔形蔬菜攤後的市集小販,漸漸認識他了,而且會在其他叫囂的顧客當中特別看顧他的需要。他們給他生鏽的錫箔罐,讓他裝選中的蔬菜。他從不討價還價,因為他們從不占他便宜。當蔬菜秤過了,他也付了錢,他們會將這些蔬菜放到他紅色的塑膠購物袋裡(洋蔥在底下,印度茄子和番茄在上面)。此外,他們會免費送他一枝胡荽,和一把紅番椒。艾斯沙搭擁擠的電車將這些東西帶回家。一個飄浮在噪音之海的安靜泡沫。
用餐時,如果想要某樣東西,他會站起來,自己去拿。
安靜一旦降臨,便停留在艾斯沙身上,在那兒擴散。它從他的頭伸展開來,用它潮溼的手臂擁抱他;它搖動他,帶他進入一種古老的、胎兒心跳的節奏;它讓他偷偷摸摸的長出吸根的觸毛,沿著頭顱的內部逐漸移動,吸他記憶的小山和小溪谷,驅逐舊的語句,將它們自他的舌尖撣走;它剝除他用來描述思想的話語,使得這些思想變成赤裸、麻木、說不出口。因此,對於一個觀察者而言,他幾乎是不存在的。在幾年之間,艾斯沙慢慢地退出這個世界。他已經習慣於住在他裡面那隻對過往噴出漆黑鎮定劑的不安的章魚。漸漸地,他沉默的理由被隱藏起來,被埋在這個事實的安慰人心的摺層深處。
庫布強是他所愛的一隻瞎眼、禿頭、患失禁症的十七歲雜種狗。當牠決定要上演一齣悽慘、拖得長長的死亡戲劇時,艾斯沙在牠最後的受苦階段一直照顧牠,彷彿他自己的生命正以某種方式倚賴這件事情。庫布強有最好的意圖,卻有最不可靠的膀胱。在牠生命的最後幾個月,牠會拖著身子走到建造在通往後花園那扇門下面、頂端裝有鉸鏈的狗吊門那兒,將頭從吊門伸出去,在「屋裡」搖搖晃晃地排出鮮黃色的尿液。然後,牠會帶著空了的膀胱和無愧的良心抬頭看著艾斯沙,牠那不透明的綠眼睛在灰色的頭顱中,就像滿是浮渣的水池。然後,牠會迂迴回到潮溼的軟墊上,在地板上留下溼足印。當庫布強奄奄一息地躺在軟墊上時,艾斯沙可以看到牠光滑的紫色眼球反映著臥室的窗,以及窗外的天空。有一次甚至反映出從那兒飛過的一隻鳥。艾斯沙經常沉浸於即將凋萎的玫瑰氣味中,且思忖著關於一個傷殘之人的記憶。因此對他而言,一個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擊的東西竟能存活下來,且竟被容許活下來,真是一個奇蹟。一隻飛鳥映在一隻老狗的眼球裡,這使得他大笑出聲。
庫布強死後,艾斯沙開始他的漫步。他連續走好幾個小時。起初,他只在鄰近一帶巡行,但是漸漸地,他愈走愈遠。
人們已經習慣在路上看到他,一個穿著體面、步伐安靜的男人。他的臉變黑了,布滿野外留下的痕跡,顯得粗糙,且被太陽曬出皺紋。他開始顯現出比實際年齡更有智慧的模樣,就像城市裡的一個漁夫,懷著海的奧祕。
由於又被送回來了,所以艾斯沙走遍了阿耶門連各地。
有些日子,他沿著河岸走,那裡散發著糞便,和用世界銀行的貸款買來的殺蟲劑的味道。大多數的魚都死了,存活的魚都患了腐鰭症,而且長了疔。
其他日子裡,他在路上走,經過那些以波斯灣國家的錢蓋起來,如剛烤的、加了糖衣的蛋糕的新房子,屋主是那些賣力而不快樂地在遠地工作的護士、石工、電線工人和銀行職員。他也經過那些滿懷不滿,因嫉妒而變綠,瑟縮在私有橡膠樹之間的私有車道上的老房子。每一棟房子都是一個搖搖欲墜的采邑,有自己的史詩。
他經過他的曾祖父為賤民階級的孩子所蓋的村莊學校。
經過蘇菲默爾的黃色教堂,經過阿耶門連的青年功夫俱樂部,經過為非賤民而設的蓓蕾育幼院,經過賣米、糖和一串串從屋頂懸垂下來的黃香蕉配給商店。關於虛構的南印度性愛妖魔的廉價軟性色情雜誌,被曬衣用的衣夾夾在自天花板垂下的繩子上。它們在溫暖的微風中懶洋洋地旋轉著,以躺臥在假血池中的成熟、赤裸的女人,誘惑著配給商店的誠實顧客。
有時候,艾斯沙會經過幸運印刷廠——老皮萊同志的印刷廠。以前這是共產黨在阿耶門連的辦公室,黨員在這兒舉行半夜的讀書會,那些振奮人心的馬克斯主義黨黨歌的歌詞也在這兒印出和散發。屋頂上飄揚的旗子已經老舊了,顯得無精打采。一面因失血而變黯淡的紅旗。
每天早晨,皮萊同志穿著一件變灰的艾爾帖克斯汗衫走出來,柔軟、白色的芒杜顯露出睪丸的輪廓,他以加了胡椒粉的溫暖椰子油塗抹自己,搓揉他如口香糖般欣然自骨頭延伸出來的老而鬆弛的肉。現在他是獨居的,他的妻子卡莉安已死於卵巢癌,兒子列寧則已搬到德里,成為外國大使館的設施承包商。
如果艾斯沙經過時,皮萊同志正在屋外為自己抹油,他必定會向艾斯沙打招呼。
「艾斯沙芒恩!早安,你又像每日一樣出來散步嗎?」他以高揚、尖銳的聲音呼叫。但是現在,那聲音已經破損、變細了,就像被削去皮的甘蔗。
艾斯沙會走過去,不粗魯,也不彬彬有禮,只是不發一語。
皮萊同志會用手拍打全身,以促進血液循環。他不知道經過這些年,艾斯沙是否仍認得自己,但他也不特別在意這一點。雖然皮萊同志在整件事情中扮演著一個不算小的角色,但是他不認為自己必須為發生的事情負任何個人責任。他將整個事件斥為不可避免之政治下的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一個「打破了蛋就煎蛋捲」之類的古老事件。但是基本上,當時的皮萊同志是一個政治人物,一個專業的煎蛋捲人,像一隻變色龍那樣在這世界穿梭,從不揭露自己,也從不顯示出隱藏自己的樣子,毫髮未損地自混亂局勢中脫身而出。
他是全阿耶門連第一個聽到瑞海兒歸來的人。這個消息只引發他的好奇心,沒有干擾他。對於皮萊同志而言,艾斯沙幾乎完全是一個陌生人,他是在極其突然而唐突的情況下被逐出阿耶門連,而且是許久之前的事情。但是皮萊同志認識瑞海兒,他看著她長大。他不知是什麼原因讓她回來,在這些年後。
在瑞海兒到來之前,艾斯沙的腦海裡一直十分平靜。但是現在,她帶來了經過的火車所發出的轟隆聲,帶來了坐在靠窗位時,落在身上的更迭的光和暗影。被鎖在外面多年的世界突然湧進來了,現在,在噪音之中,在火車、交通和音樂聲中,艾斯沙聽不到自己。一座水壩迸開來,兇猛的水襲捲了一切。彗星、小提琴、閱兵場、寂寞、雲朵、鬍鬚、偏執者、名單、旗子、地震和失望,都被捲入混亂的漩渦中。
而走在河岸上的艾斯沙感覺不到雨的潮溼,感覺不到那隻暫時跟著他,在他身邊,咯喳行走的發冷小狗突來的哆嗦。他經過古老的山竹果樹,爬上一塊伸入河流的鋁紅土凸出地的邊緣,然後蹲下來,在雨中搖擺身體。他鞋下的溼泥製造出一種刺耳、吸吮的聲音。發冷的小狗顫抖著,並且觀看著…
【更多精彩內容請翻閱本書】
1 天堂果菜醃製廠 阿耶門連的五月是一個炎熱、陰沉沉的月份。白日長而潮溼,河流縮小。黑烏鴉貪婪地吃著靜止、布滿灰塵的綠色芒果樹上那些鮮艷的果實。紅白蕉成熟了,菠蘿蜜脹裂開來。放浪形骸的青蠅在溢滿果香的空氣中,空茫茫地嗡嗡鳴叫著,然後撞在明亮的窗玻璃上,一命嗚呼,肥胖的身體在陽光下顯得不知所措。
夜,澄澈無雲,但瀰漫著懶散的情緒和沉重的期待。
但是到了六月,西南季風吹來。有三個月,風刮著,雨下著,偶爾刺眼、閃爍的太陽才露一下面,而興奮的孩子則趁機大玩一番。鄉間一片恣肆的綠,當插在地上作為籬笆...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8收藏
38收藏

 45二手徵求有驚喜
45二手徵求有驚喜




 38收藏
38收藏

 45二手徵求有驚喜
4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