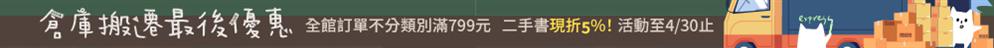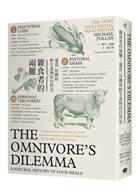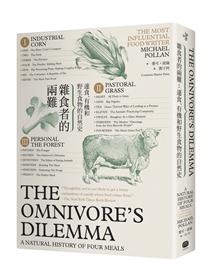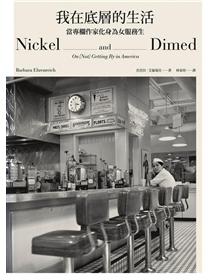燒掉一本書的方法不止一種,
而這個世界上到處都有點燃火柴的人
【華氏451度──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百大小說】
※特別收錄:作者特別撰寫之〈尾聲〉與〈後記〉,
當代奇幻大師尼爾.蓋曼(Neil Gaiman)專文導讀。
《華氏451度》是二十世紀的文學傑作,背景設在黯淡而貧乏的反烏托邦世界,
以一個壓制自由的未來社會、禁止人們擁有或閱讀書籍的故事,
深刻描寫出現代人在不自覺中,反受科技和娛樂禁錮的存在狀態。
「書本變薄,然後是濃縮、消化過的版本,最後成了摘要,摘要的摘要的摘要,二句話……」
故事中的世界,人們只談論一些無意義的事,快樂是最高指標,思考會帶來不必要的煩惱,
而書則是擾亂平靜的怪獸。
蒙塔格是一名打火員,
在他的世界裡,電視主宰著一切,文學則瀕臨滅絕;
打火員的工作成了放火而非滅火。
他的工作就是要摧毀非法的產品,也就是書籍,
以及藏匿這些書籍的房子。
蒙塔格從來不去質疑自己的行為造成了什麼樣的破壞和損失,
每天只是回到他無趣的生活和他的妻子蜜卓身邊,
而她的妻子整天只會陪著她的電視「家人」。
但這時,他遇見了古怪的年輕鄰居克萊莉絲,
她讓蒙塔格知道原來過去的世界裡,人們不必生活在恐懼中;
在現今的世界裡,還是有人可以透過書本裡的思想來看待一切,
不必仰賴電視中無腦的談話。
就在蜜卓自殺未遂、克萊莉絲突然消失之際,
目睹寧可與書盡皆毀滅的衝擊,蒙塔格開始質疑自己所知道的一切。
他開始在家裡藏書,而當他的偷竊行為遭人告發時,
這名打火員得開始亡命天涯……
◎大家都誤會了《華氏451度》──
作者雷.布萊伯利2007年在接受《洛杉磯週報》訪問時堅定表示:《華氏451度》並不是關於政府監控言論的故事,而是電視如何摧毀人們閱讀文學的興趣。
在這本書中的壞人不是國家,而是人。
和歐威爾《一九八四》不同的地方在於,《一九八四》中政府利用電視螢幕對人民洗腦,布萊伯利則預見了電視將會變得有如鴉片般引人上癮。布萊伯利在書中將電視比喻為「牆面」,裡頭的演員是「家人」,任誰只要是聽過某個粉絲重述電視節目的內容,直呼角色的名字如同自己的親戚或朋友一般,都能馬上了解這個比喻。
故事的主角蓋伊‧蒙塔格身為打火員,開始質疑為何自己靠著燒書賺錢。他最後退出了自己所處的權威文化,轉而加入一群人所形成的社群,他們記住整本書的內容,好將書保存下來,等待這個社會願意閱讀的時刻再次到來。
【本書特色】
※特別收錄作者雷.布萊伯利於1979、1982年所撰寫之尾聲與後記
※美國國會圖書館評選「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百大小說」
※榮獲雨果紀念文學獎(Retro Hugo Awards)最佳長篇小說、普羅米修斯名人堂獎(Prometheus Hall of Fame Award)
※出版逾60年,仍高踞亞馬遜百大暢銷排行榜,歷久不衰;美國超過一千所學校選作教材及推薦讀物!
作者簡介:
雷.布萊伯利
Ray Bradbury,1920~2012
美國小說家、散文家、劇作家、編劇、詩人。
雷‧布萊伯利的寫作生涯超過70年,2012年6月5日以91歲高齡辭世,他啟發了無數世代的讀者,讓他們勇於做夢、思考、創作。這位多產的作家一生寫出上百篇短篇故事,出版將近50本書,以及無數詩作、散文、劇作、舞台劇本、電視劇本和電影劇本,是當代最負盛名的作家之一。他的傑作包括《華氏451度》、《火星紀事》、《圖案人》、《蒲公英酒》,以及《闇夜嘉年華》。他為約翰‧休斯頓的經典改編電影《白鯨記》所寫的劇本曾經入圍奧斯卡獎。他將自己的65篇故事改編為電視劇本,以「雷‧布萊伯利劇場」的節目名稱播映,並以〈萬聖樹〉的電視劇本贏得艾美獎。
布萊伯利一生獲獎無數,其中包括於2000年獲得美國國家圖書基金會頒發的「美國文學傑出貢獻獎」,於2004年獲得美國國家藝術獎,2007年則是拿下「普立茲特殊貢獻獎」。
他這一輩子最喜歡掛在嘴上的故事,就是他在1932年遇見的嘉年華魔術師:電流先生。在電流先生表演結束之後,他面對十二歲的布萊伯利伸出手,以自己的寶劍碰觸這個小男孩令道:「永生不死!」後來,布萊伯利說:「我知道那是我所聽過最棒的點子,我開始每天寫作,從未停止。」
譯者簡介:
徐立妍
師大翻譯研究所筆譯組畢業,譯有《一九八四》、《污點》等多本作品,持續翻譯中。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各界推薦】
★「書中情節的影射非常駭人……布萊伯利對這個瘋狂世界的描述,竟與我們的世界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實在很了不起。」——《紐約時報》
★「內容描述的反烏托邦社會令人不寒而慄。」——《華盛頓郵報》
★「這本書是要提出警告,提醒我們所擁有的是多麼珍貴,而有時,我們卻不懂得珍惜。」——尼爾‧蓋曼,《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亞馬遜讀者五星書評】
★「布萊伯利數十年前寫了《華氏451度》,卻預視了未來世界的二十分鐘。……不過,我們還來得及阻止這樣的未來,或許吧。但倘若大眾仍舊較重視流行文化的價值,而忽略思考和教育的重要性,我們就會直接步入那樣的世界,開始燒書,知識分子亡命天涯。這本書讓我想要反抗權威。」──Ammy Woodbury
★「不得不讚嘆布萊伯利高明的表現主義手法,他以荒謬的敘述營造出全然超乎現實的氛圍,刻劃出故事主角的感受和想法。」──anybody else or “amanuet”
★「故事中的諷刺意味令人回味再三,打火弟兄的工作成了放火,這樣的轉折十分精采;而人們強記整本書的內容,為未來世代保存知識資產,如此安排也極具信服力。」──Lawrence Bernabo
★「在我看來,《華氏451度》無疑是布萊伯利最棒的作品。布萊伯利傑出的文字功力讓他的作品不落科幻小說的窠臼,並躍出該類型的藩籬之外。……他不僅神奇預測出牆面大小的平面電視,也預測出當前的社會趨勢,而教育、閱讀和理性思考即便未完全遭到破壞,也可說漸漸式微。」──Joanna Daneman
名人推薦:【各界推薦】
★「書中情節的影射非常駭人……布萊伯利對這個瘋狂世界的描述,竟與我們的世界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實在很了不起。」——《紐約時報》
★「內容描述的反烏托邦社會令人不寒而慄。」——《華盛頓郵報》
★「這本書是要提出警告,提醒我們所擁有的是多麼珍貴,而有時,我們卻不懂得珍惜。」——尼爾‧蓋曼,《紐約時報》暢銷作家
【亞馬遜讀者五星書評】
★「布萊伯利數十年前寫了《華氏451度》,卻預視了未來世界的二十分鐘。……不過,我們還來得及阻止這樣的未來,或許吧。但倘若大眾仍舊較重視流行文化...
章節試閱
二
篩子和沙
那一整個漫長的下午,他們就在閱讀中度過,外頭的天空降下冰冷的十一月雨,落在安靜的房子上。他們坐在大廳裡,少了橘色、黃色的繽紛色塊和沖天炮般的爆炸,沒有穿著金色網洞洋裝的女人和穿著黑色天鵝絨、從銀色帽子裡拉出四十五公斤重兔子的男人,那樣的起居室顯得如此空洞而灰暗。起居室裡一片死寂,蜜卓不斷往裡頭張望,表情空洞無神,而蒙塔格則在地板上踱步,回到原來的位置蹲下,又把同一頁大聲讀了有十次之多。
「『我們無法精準斷言友誼是何時形成,就像一點一滴要裝滿一個容器,最後終於滴下那滴液體,讓容器滿盈;所以說,經過一連串友好的善意,至少有一次盈滿了那顆心 。』」
蒙塔格坐著傾聽雨聲。
「這就是讓隔壁那個女孩如此特別的原因嗎?我一直努力要想通這一點。」
「她死了。老天,來談談活人好嗎?」
蒙塔格渾身發抖,從大廳走向廚房,沒有回頭看他的妻子,他在那裡站了良久,看著雨滴打在窗戶上,然後才又回到灰暗的大廳中,等顫抖平息。
他翻開另一本書。
「『最愛的話題,我自己。』」
他瞇起眼睛盯著牆,「『最愛的話題,我自己。』」
「那一句我懂。」蜜卓說。
「可是克萊莉絲最愛的話題並不是她自己,而是其他的一切,還有我。這麼多年來,她是我第一個真正喜歡的人。她是我記憶中第一個直直看著我的人,好像我有多了不起。」他拿起兩本書,「這些人已經死了好久,但是我知道,他們所說的或多或少都指向克萊莉絲。」
在前門外的雨中,傳來一聲微弱的抓撓聲。
蒙塔格僵住了,他看見蜜卓往後緊靠著牆壁,倒抽一口氣。
「有人──在門口──為什麼應門的語音沒有告訴我們──」
「我關掉了。」
從門檻下傳來緩慢而具試探性的嗅聞聲,吐出一口電子蒸汽。
蜜卓笑了,「只是一隻狗,什麼嘛!要我把牠趕走嗎?」
「留在原地別動!」
一陣靜默。冷冷的雨下著,一股藍色電子的氣味從上鎖的門底下吹送進屋裡。
「回去做事吧。」蒙塔格悄聲說。
蜜卓踢了本書,「書又不是人。你在看書,而我環顧四周,什麼人也沒有!」
他瞪視著死灰的起居室,彷彿一片海洋水域,只要打開電子太陽就會充滿生命。
「聽著,我的『家人』是人。他們會告訴我一些事情;我笑,他們也會笑!更別提還有各種繽紛的顏色!」蜜卓說道。
「對,我知道。」
「再說,要是畢提隊長知道有這些書──」她想了一下,臉上露出驚異的表情,然後轉為驚恐。「他可能會來燒了房子,還有我的『家人』。太可怕了!想想我們投資了多少錢。我為什麼要讀?為了什麼?」
「為了什麼!為什麼!」蒙塔格說,「那天晚上我看到世界上最該死的一條蛇,沒有生命卻栩栩如生,能看見東西卻又是瞎的。妳想瞧瞧那條蛇嗎?就在急診醫院裡,他們會歸檔報告,記錄那條蛇從妳體內吸出的所有廢物!妳想看他們的檔案嗎?或許妳得查蓋伊‧蒙塔格,或者查『恐懼』或『戰爭』。妳想親眼目睹昨晚燒掉的那棟房子嗎?耙耙那裡的灰,找找放火燒了自己房子那個女人的骨骸!克萊莉絲‧麥可勒蘭呢?我們要去哪裡找她?太平間!妳聽!」
轟炸機掠過天際,飛越房子上空,尖叫、低鳴、呼嘯著,猶如一座無比巨大、隱形的風扇在虛空中兀自轉動。
「我的老天,每個小時都有這麼多該死的東西在天上飛!我們這一輩子,怎麼無時無刻都有那些該死的轟炸機飛上去!為什麼沒人想談這件事?從二○二二年以來,我們主動宣戰也打贏了兩次原子戰爭!是因為我們在家裡玩得太開心,以致忘了外面的世界?還是因為我們如此富足,所以根本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我聽過傳言,這個世界在為飢餓所苦,我們卻吃得很飽。真是如此,全世界都在勞動,但我們只顧著享樂才會這麼惹人厭?這麼多年來,我也聽過有關憎恨的傳聞,雖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妳知道原因嗎?我真的不知道!或許這些書能讓我們更靠近洞口一些,或許能阻止我們再次犯下那個瘋狂的錯誤!我沒聽過妳起居室裡的那些白痴渾蛋談論這些。天啊,小蜜,妳還不懂嗎?一天一個小時、兩個小時,讀這些書,說不定……」
電話響了,蜜卓馬上抓起電話。
「安!」她笑著說,「是啊,白小丑今晚要演出!」
蒙塔格走到廚房,把書扔著。「蒙塔格,」他心想,「你真的很傻。我們這樣又能如何?要把書交出去嗎?別再想了!」他打開書,耳邊迴盪著蜜卓的笑聲。
可憐的小蜜,他思忖著,可憐的蒙塔格,你也是一團迷糊。但你要上哪找人幫忙?這麼晚了去哪裡找老師?
等等。他閉上眼睛。對了,當然了。他發現自己又想起一年前那個綠色公園,最近那個地方經常在他腦海中浮現,而現在他憶起那天在城市公園裡發生的事──穿著黑色西裝的老人好像迅速把什麼東西藏進他的外套裡。
……老人跳了起來,好像要跑走。蒙塔格說:「等等!」
「我什麼也沒做!」老人顫抖喊道。
「沒人說你做了什麼。」
他們在綠色柔和的光線中坐了好一會兒沒有說話,然後蒙塔格談起天氣,老人則用虛弱的聲音回應。這是一次奇怪而安靜的會面。老人坦承自己是一名退休的英文教授,四十年前,當最後一所文學院也因為招募不到學生和贊助人關閉後,他便被迫出來面對如今的世界。他的名字叫法柏,等到他終於卸下心防,說話的聲音便有了抑揚頓挫,並望著天空、樹木和綠色公園。一個小時過去後,他對蒙塔格說了什麼,蒙塔格感覺那是一首無韻詩。然後,老人更大膽了些,說了其他話,也是一首詩。法柏的手搭在外套左邊的口袋上,溫柔的吐出這些話,蒙塔格知道,如果他伸出手,也許會從那男人的外套裡抽出一本詩集。但他並沒有這麼做,他的手仍放在膝蓋上,麻木而無用。「我不談論事情,先生,我只談論事情的意義。我坐在這裡,知道我活著。」法柏說道。
就這麼簡單,真的。一小時的獨白,一首詩、一句評論。然後,法柏在不確定蒙塔格打火員身分的情況下,在一張紙上寫下自己的住址,手還止不住的顫抖。「讓你記著,倘若你決定生我的氣,就有用了。」他說。
「我沒生氣。」蒙塔格驚訝的說。
蜜卓在大廳裡發出尖銳的笑聲。
蒙塔格走進臥室翻閱放在衣櫃裡的檔案夾,上頭有個標簽寫著:待調查(?)法柏的名字便記錄其中。他沒有交出這份文件,也沒有塗掉它。
他用備用電話撥了號碼,遠端的電話線路呼叫法柏的名字十餘次,這位教授才以虛弱的聲音接起。蒙塔格表明自己的身分,電話那頭則是一陣長長的靜默。「是,蒙塔格先生,有什麼事嗎?」
「法柏教授,我想問個有點奇怪的問題。國內還剩下幾本《聖經》?」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我想知道這本書到底還有沒有。」
「這是什麼陷阱吧!我不隨便跟人講電話!」
「還有多少本莎士比亞和柏拉圖?」
「沒有!你和我一樣清楚。沒有!」
法柏結束這場對話。
蒙塔格放下電話。沒有。他當然知道,打火站牆上就列著這些書的清單,但他想聽法柏親口說出來。
大廳裡,蜜卓的臉上盡是興奮。「噢,太太們要過來了!」
蒙塔格拿了本書給她看,「這是舊約和新約,還有……」
「不要又提那個!」
「這可能是世上最後一本了。」
「你今晚得交回去,對吧?畢提隊長知道你有一本,對不對?」
「我想他不知道我偷了哪本書。可是我要選哪一本來代替呢?要交出傑佛遜先生嗎?還是梭羅先生?誰比較沒價值?如果我選了一個替代品,而畢提又知道我偷了哪一本,他便會猜到我們家裡有一整座圖書館!」
蜜卓癟起嘴說,「看你做的好事,你會害死我們!我和《聖經》哪個比較重要?」她開始尖叫,坐在那裡像個因自身高溫而融化的蠟製娃娃。
他彷彿能聽見畢提的聲音:「坐下,蒙塔格。你看,輕柔得彷似花朵的花瓣。點燃第一頁,點燃第二頁,每一頁都化作黑色蝴蝶,很美吧?點燃第三頁,從那一秒開始便是連續不斷的黑煙──那些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愚蠢事物、一切不實的承諾、所有引自別人口中的想法和過時的哲學,一章接著一章。」畢提坐著,微微冒汗,地板上則散落一群又一群黑蛾,一場風暴便摧毀了牠們。
蜜卓的尖叫才開始就結束了。蒙塔格並未在意,「只有一件事要做,在今晚結束之前,在我把這本書交給畢提之前,我得複製一本。」
「你今晚會看白小丑,那太太們可以過來吧?」蜜卓喊道。
蒙塔格停在門口,轉過身去,「小蜜?」
一陣沉默之後,「什麼事?」
「小蜜,白小丑愛妳嗎?」
沒有回答。
「小蜜,妳的──」他舔了舔脣,「妳的『家人』愛妳嗎?非常、非常愛妳,全心全意愛妳嗎,小蜜?」
他感覺她瞅著他的頸後,緩緩眨眼,「你為什麼要問這麼奇怪的問題?」
他覺得好想哭,但他的眼睛或嘴巴毫無反應。
「如果你看見外面那隻狗,幫我踢牠一下。」蜜卓說。
他遲疑了一會兒,聽著門外的動靜,然後打開門走了出去。
雨已經停了,澄澈的天空中,太陽正準備下山。街道上、草坪上和門廊前空無一物。他重重的嘆了口氣。
他砰地關上門。
他搭上地鐵。
我麻木了,他思忖著。我臉上這種麻木感是何時真正開始的?身體上的呢?那天晚上我踢到藥瓶,感覺就像踢到埋在土裡的地雷。
麻木感會過去的,他心想。這需要時間,但我做得到,或者法柏可以幫我。某個地方有人可以幫我找回昔日的面孔和身體,回復原來的樣子。就連笑容,他思索著,那烙印在臉上熟悉的笑容也不見了。沒那笑容,我一片茫然。
地鐵站在他眼前飛掠而過,奶油色磁磚、黑色噴射機,奶油色磁磚、黑色噴射機,交替了好幾次,接著是黑暗、更多黑暗,以及這一切的總和。
他還小的時候,有一次坐在海邊一處黃色沙丘上,那是個憂鬱、炎熱的夏日正午,他試著在篩子裡裝滿沙,因為某個壞心眼的表哥說:「把這篩子裝滿就給你一角。」而他裝得愈快,沙子漏得也愈快,發出熾熱的低語。他的手累了,沙子燙得像要沸騰,篩子依然是空的。他在七月中旬坐在那裡,感覺淚水從臉頰滾落。
如今,孤獨的地鐵列車載著他匆匆掠過城鎮死寂的地底,搖晃著他,他想起那篩子可怕的運作原理,低頭看見自己拿著翻開的《聖經》。這個由抽吸力驅動的列車上還有其他人,他手上拿著書,心中升起一個愚蠢的念頭:如果我很快把整本書讀完,也許還有一點沙子留在篩子裡。但是他一邊讀,那些文字卻無情的從他的指縫間溜走。他心想,再過幾小時,畢提會在那裡,然後我會把書交出去,所以絕不能漏掉隻字片語,每一行都要記住,我下定決心要做到。
他把書緊緊握在手裡。
車廂內的喇叭聲大響。
「丹漢牌潔齒劑。」
閉嘴,蒙塔格心想。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
「丹漢牌潔齒劑。」
他也不勞苦──
「丹漢牌──」
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閉嘴,閉嘴。
「潔齒劑!」
他把書整本攤開,快速翻過書頁,像個盲人般撫摸頁面,檢視著個別文字的形狀,眼睛眨也不眨。
「丹漢牌,靈丹的丹──」
他也不勞苦,也不……
一把熾熱的沙子咻地流出空篩子。
「丹漢牌做到了!」
你想野地裡的、野地裡的、野地裡的……
「丹漢牌牙齒除垢劑。」
「閉嘴、閉嘴、閉嘴!」這話是懇求。如此聲嘶力竭的吶喊,蒙塔格發現自己站了起來,吵鬧車廂中的乘客則是詫異地瞪視、往後退開,遠離這一臉瘋癲、嫌惡的男子,他乾燥的嘴脣含糊不清地快速移動,手裡還拿著翻開的書。適才還坐著的人們,腳會隨著廣告節奏打拍子:丹漢牌潔齒劑、丹漢牌阿丹牙齒除垢劑、丹漢牌潔齒劑、潔齒劑、潔齒劑,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那些人的嘴角還微微抽動:潔齒劑、潔齒劑、潔齒劑。列車上的廣播對著蒙塔格嘔吐,像是要報仇一樣,播放一連串用錫、紅銅、銀、鉻和黃銅敲打出來的音樂,強烈的衝擊讓人們都屈服了,他們沒有跑走,也無處可逃。巨大的氣墊列車向下駛進地底通道。
「野地裡的百合花。」
「丹漢牌。」
「我說百合花!」
人們盯著他看。
「叫警衛。」
「這男人瘋──」
「諾爾觀景台!」一聲叫喊。
「丹漢牌。」有人低聲說。
蒙塔格的嘴幾乎沒有動:「野地裡的……」
列車車門唰地開啟,蒙塔格卻呆立著,直到車門發出抽氣聲、準備關上時,他才躍過其他乘客,腦中高聲尖叫,及時從門縫中擠了出去。他踩著白色地磚跑上隧道,無視電扶梯的存在,他想要感覺自己的腳在動、手臂擺動,肺部緊縮、再放鬆,感覺自己的喉嚨盈滿了空氣而乾渴。一道聲音從他身後飄來:「丹漢牌、丹漢牌、丹漢牌。」列車發出如蛇般的嘶嘶聲,消失在洞穴中。
「是誰?」
「是我,蒙塔格。」
「你想幹嘛?」
「讓我進去。」
「我什麼也沒做!」
「只有我一個人,該死的。」
「你發誓?」
「我發誓!」
前門慢慢打開,法柏探出頭張望,他在光線下顯得很老、很脆弱,而且極度恐懼。老人看起來像是好幾年沒踏出家門,他和屋裡的白色水泥牆看起來沒兩樣,他的嘴脣、臉頰毫無血色,頭髮花白,眼珠子的顏色也褪了,在那片淡藍中摻了白。然後他的視線落在蒙塔格手臂下夾著的書,他看起來不再那麼蒼老,也不再那麼脆弱。他的恐懼漸漸消失了。
「對不起,人總得小心點。」
他看著蒙塔格夾在手臂下的書,忍不住說:「所以,是真的。」
蒙塔格走進去,門關了起來。
「請坐。」法柏往後退,好像擔心如果他移開視線,那本書就會消失一樣。在他身後,臥室的門敞開著,房間裡散落的機件和金屬工具布滿桌面,蒙塔格看了一眼,而法柏發現他注意到那裡,便急忙轉身去關上臥室房門,站在那裡,用顫抖的手握著門把。隨後,他又繼續看著蒙塔格,眼神不太確定,蒙塔格現在坐著,書就放在大腿上。「那本書──你從哪裡──?」
「我偷的。」
法柏第一次抬起眼來,直視蒙塔格的臉,「你很勇敢。」
蒙塔格說,「不,我的妻子快死了,還有個朋友已經死了。有個人或許會成為我的朋友,但還不到二十四小時前被燒死了。你是我認識的人中唯一有可能幫我的,幫我看清楚,看清楚……」
法柏的手在膝蓋上扭動,「我可以看看嗎?」
「不好意思。」蒙塔格把書給他。
「已經好久了。我不是虔誠的人,但是已經好久了。」法柏翻過書頁,一下停住讀讀這裡、讀讀那裡。「就跟我記得的一樣好。天啊,這些日子以來,他們把我們的『起居室』變成什麼樣子,如今基督也是『家人』的一員了,我總懷疑,上帝看見我們讓耶穌打扮起來,祂還認不認得自己的兒子,還是該說,沉淪於打扮了呢?祂現在是一根普通的薄荷糖棒,倘若不是在影射某種每位信徒的必需品,就只是糖結晶和糖精罷了。」法柏聞了聞書,「你知道書聞起來像是肉豆蔻或某種異國香料嗎?我小時候很喜歡聞。天啊,以前有好多好棒的書,然而我們都放棄了。」法柏翻過書頁,「蒙塔格先生,在你眼前的是一名懦夫,很久以前,我就看出事情的發展,但我默不作聲。我曾是清白之人,當時沒有人會聽『罪人』的話,我本可出言反對、抗爭,卻選擇沉默不語,於是自己也成了罪人。最後,他們立下燒書的制度,並利用打火員執行,而我抗議了幾次就放棄了,那時已經沒人跟我一起抗議或吶喊。現在,一切都太遲了。」法柏闔上《聖經》。「好了,看來你要告訴我此行的目的?」
「沒有人願意傾聽,我無法對那幾面牆說話,他們一直對著我吼;我也無法對我妻子說話,她只聽牆的。我只希望有人能聽聽我要說的話,倘若我說得夠久,也許那些話會有點道理。我也希望你能教我理解我所讀到的內容。」
法柏仔細端詳蒙塔格削瘦、有著藍色下巴的臉,「你是怎麼覺醒的?是什麼打掉了你手中的火炬?」
「我不知道。我們擁有一切快樂的必需品,我們卻不快樂。我們還少了什麼。我環顧四周,唯一一樣我知道絕對缺少的就是書。我已經燒書燒了十年、十二年,所以我想書本或許能幫上忙。」
「你真是無可救藥的浪漫。」法柏說道,「倘若這番話不是認真的,就好笑了。你需要的不是書,而是曾經寫在書裡的某些內容;那些『起居室裡的家人』也會需要它們。廣播和電視也可以投射出這極大的細節和覺察,但是卻沒有。不、不,你要找的根本不是書!哪裡找得到你就往哪裡去,在舊的留聲機唱片裡、老電影裡,還有老朋友身上;在大自然裡尋找,在你自己身上尋找。書只是一種容器,儲存許多我們害怕自己可能會遺忘的智識。書本身並沒有魔力,完全沒有,魔力只存在於書中所記載的內容,它能拼湊起整個宇宙的片段,成為我們的衣裳。當然,你不會知道這些,你還無法理解我現在說的這一切的含義。你的直覺是對的,這才重要。我們缺少了三樣東西。
「第一樣:你知道像這樣的書為何這麼重要嗎?因為書有質量。質量是什麼意思呢?對我來說,就是質地。這本書有毛孔、有特徵,它可以放到顯微鏡下檢視,你會在鏡片下看見生命,無窮豐富的生命自眼前流過。毛孔愈多,你在這張紙上每平方吋所紀錄的生命細節也就愈真實,你也會變得更『文學』。總之,那是我的定義。述說細節,鮮明的細節。好作家經常觸碰到生命,二流作家只是很快摸上一把,爛作家則會強暴生命,並將之留待蒼蠅享用。
「現在你知道為何有人憎恨、討厭書了嗎?它們會顯示生命臉上的毛孔。在安樂中的人只想看見月光般瑩白的蠟像臉,沒有毛孔、沒有毛髮,也沒有表情。我們生活的時代,花兒努力倚靠著花兒存活,而不是仰賴豐沛的雨水和黑色沃土。就連煙火,如此美麗的東西,都是來自於土地中的化學反應,但我們卻認為自己不必完成生命循環、回歸現實,便能種植、餵養花朵和煙火。你聽過海克力斯和安泰俄斯的傳說嗎?安泰俄斯這個巨人力士穩穩站在土地上便擁有無窮的力量,於是海克力斯將他舉起,使其在空中無根可依,便輕易擊倒了他。倘若這個傳說在這座城市、這個時代毫無值得學習之處,那我就完全瘋了。好了,這是我們需要的第一樣東西──質量,資訊的質地。」
「那第二樣呢?」
「空閒。」
「噢,我們下班後有很多時間。」
「沒錯。但是有時間思考嗎?下班後能做什麼,開車時速飆至一百哩,開到除了眼前的危險其他什麼也想不了,不然就是玩某種遊戲,或坐在某個房間裡,無法反駁四面電視牆對你所說的一切。為什麼?電視是『即時』的,馬上就有回應,自有其重要性,但電視牆會告訴你該想什麼,一股腦兒塞給你,那肯定沒錯,感覺如此正當,它催促著你快快下定結論,那是他們要你這麼做的,你的心智根本沒時間抗議:『胡說八道!』」
「可是那些『家人』是人啊。」
「你說什麼?」
「我妻子說書本不是『真的』。」
「感謝老天,是這樣沒錯。你可以闔上書說:『等等。』你是主宰。但是,一旦你在電視起居室裡播下種子,有誰能夠掙脫那隻緊箍著你的爪子?爪子會把你養成任何它想要的樣子!那個環境就跟這個世界一樣真實,它成了現實,它就是現實。你可以用理論辯倒一本書,而我窮盡一身的知識和懷疑論,卻從來辯不倒一個百人組成的交響樂團、全彩畫質和立體影像,在那些漂亮的起居室裡成為房間的一部分。你也看見了,我的起居室裡只有四面水泥牆,而我這裡,」他拿出兩個小小的橡膠耳塞,「我搭地鐵噴射列車時都會塞進耳裡。」
「丹漢牌潔齒劑;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線。」蒙塔格閉上眼睛說。「我們要怎麼做?書能派上用場嗎?」
「除非我們能得到第三樣必需品。第一樣,我說過了,是資訊的質量;第二樣:有空閒能消化資訊;然後,第三樣:我們從前面兩樣必需品的互動中所學到的,也要有權利能付諸行動。我想一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家加上一個變節的打火員,到了這個地步也很難再做什麼了……」
「我可以拿到書。」
「你這是在冒險。」
「將死之人就是有這個好處,既然已經沒什麼好失去的,大可放手一搏。」
「是了,你說這話很有趣。」法柏笑著說,「你甚至沒讀過呢!」
「書裡有像這樣的句子嗎?但我只是腦中突然浮現這句話!」
「這樣更好,你不是故意說好聽話,不為了我、為了誰,甚至不為你自己。」
蒙塔格傾身向前,「今天下午我在想,若那些書真有什麼價值,我們或許應該找一台印刷機再多印幾本。」
「我們?」
「你和我。」
「喔,不行!」法柏坐直了身子。
「先聽聽我的計畫──」
「如果你非得告訴我,我就要請你離開了。」
「難道你一點興趣也沒有?」
「那可能會害我惹上麻煩被燒死。我或許可以聽你說,但唯一的可能是打火員制度被燒光殆盡,用什麼方法我不知道。如果你覺得我們可以多印一些書,想辦法把書藏進全國打火員的家裡,在這些縱火犯之間散播懷疑的種子,那我就會說,幹得好啊!」
「栽贓書本,開啟警報,讓打火員的家燒起來,你是這個意思嗎?」
法柏揚起眉毛瞅著蒙塔格,一副不認識他的樣子,「我在開玩笑。」
「倘若你覺得這個計畫值得一試,我就相信你說的,相信這會有幫助。」
「你無法保證那種事!畢竟,我們在還擁有一切我們需要的書本時,仍堅持從最高的懸崖往下跳。不過,我們確實需要喘息,也需要知識。或許,過了一千年,我們會找個矮一點的懸崖來跳。這些書會提醒我們,我們是怎樣的渾蛋和笨蛋,就像凱撒的禁衛軍在大街上、熱鬧的凱旋遊行中低語:『記住,凱撒,汝乃凡人之身。』我們大多數人都無法四處奔波、與眾人交談、認識世界上所有城市,我們沒有時間、金錢,也沒有那麼多朋友。蒙塔格,你所要尋找的東西就在這世界上,但是對一個普通人來說,要想見識其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唯一方法就在書本裡。不要求保證,也不要期待光靠一樣東西便能得救,或是仰賴某個人、一台機器、一座圖書館。自己想辦法救自己吧,縱使不幸溺斃,至少死的時候還知道自己正往岸邊游去。」
法柏站起來,開始在房裡踱步。
「怎麼樣?」蒙塔格問。
「你是絕對認真的?」
「絕對。」
「這個計畫十分狡猾,連我自己都這麼想。」法柏神色緊張地瞥向他臥室的房門。「讓國內的打火站成為叛國的溫床,燃燒、摧毀,令火蜥蜴自噬其尾!喝,天啊!」
「我有張清單,記錄了所有打火員的住處,只要有某種地下──」
「不能相信任何人,這是最棘手的。除了你和我,還有誰能放這把火?」
「難道沒有像你這樣的教授,或以前是作家、歷史學家、語言學家……?」
「要死的還是老的?」
「愈老愈好,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你知道的有十幾個,承認吧!」
「噢,光是演員就有很多個,他們已經好幾年沒能演出皮藍德羅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或是莎士比亞的戲了,因為當中有太多對世界的精闢觀察。我們可以利用他們的怒氣。我們也可以利用那些歷史學家真誠的憤怒,他們四十年來都沒法寫一行字。沒錯,我們或許可以組織課程,教導思考和閱讀。」
「沒錯!」
「但那只是隔靴搔癢。整個文化被轟出一個大洞,骨架得整個熔掉,重新鑄造。老天啊,這可不像回頭拾起你半個世紀前放下一本書那麼簡單。記住,其實根本不需要打火員,大眾是自己停止閱讀的,你們這些打火員偶爾像馬戲團一樣表演,燒毀幾棟房子,大家便聚集過來看漂亮的火花,而這不過是餘興節目罷了,不這麼做也能維持社會秩序。現在幾乎沒人起身反抗了,即使有,大部分就像我一樣,很容易害怕。你跳舞能跳得比白小丑快嗎?喊得比『小撇步先生』、還有起居室裡的『家人』大聲嗎?果真如此,你的想法就能獲勝,蒙塔格。不管怎麼樣,你都是個傻瓜。人們玩得可開心了。」
「他們在自殺!還有殺人!」
在他們談話的同時,一架轟炸戰鬥機持續往東飛行,兩人此時才停下來豎耳傾聽,感覺那股強大的噴射引擎聲在體內振動。
「有點耐心,蒙塔格,讓戰爭關閉『家人』的聲音。我們的文明像是要把自己甩開一樣,都快支離破碎了,你得離那台離心機遠一點。」
「一旦那台機器爆炸,必須要有人準備好才行。」
「什麼?某人引用米爾頓(John Milton)的話嗎?說我還記得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戲劇?提醒存活下來的人,人類也有良善的一面,是嗎?他們只會收集石頭互相丟擲。蒙塔格,回家吧,好好睡一覺。何必浪費你最後的這段時日,在籠子裡跑來跑去,否認自己是隻松鼠呢?」
「那麼你一點都不在乎了嗎?」
「我在乎到都病了。」
「但你不肯幫我?」
「晚安,晚安。」
蒙塔格拿起《聖經》,他看到自己的手動了起來,一臉驚訝。
「你想要這個嗎?」
法柏說:「我願意拿右手來換。」
蒙塔格站在原地,等待下一件事情的發生。他的雙手自己動了起來,像是兩個人互助合作,開始撕下那本書的書頁,那雙手撕掉了扉頁,然後是第一頁,接著第二頁。
「笨蛋,你在做什麼!」法柏躍起身來,猶如被人襲擊般撲向蒙塔格。蒙塔格將他推開,雙手繼續動作。又有六張書頁掉到地上,他撿起來,在法柏面前將紙張揉成一團。
「不要,噢,不要!」老人懇求道。
「誰能阻止我?我是打火員,我可以燒了你!」
老人站立看著他,「你不會的。」
「我可以!」
「那本書,不要再撕了。」法柏的身子往下沉進椅子裡,臉色極為蒼白,嘴脣發顫。「不要讓我覺得更無力,你想怎麼樣?」
「我要你教我。」
「好吧,好吧。」
蒙塔格把書放下,攤開揉皺了的紙團、鋪平,而老人疲累的望著。
法柏搖搖頭,仿若大夢初醒。
「蒙塔格,你有錢嗎?」
「有一點,四、五百塊吧。怎麼了?」
「把錢帶來。我知道有個人,半世紀前在大學裡負責校園報紙印刷。那一年,我在新學期第一天去上課,發現只有一名學生選修『戲劇選讀:從埃斯庫羅斯至歐尼爾』這門課。你懂嗎?如同一座美麗的冰雕在陽光下溶化。我記得報紙猶如巨大飛蛾般死去,沒人想要報紙回歸這世上,沒人想念。然後那時,政府發現這種情況多麼有利,只要讓人們讀些慷慨激昂的空話、感受胃部一記重擊,便利用那些吞火人助長情勢。所以,蒙塔格,有了這位失業的印刷師傅,或許我們可以開始印幾本書,等待戰爭破壞目前的常規,給予我們所需的動力。只要幾顆炸彈,所有房子裡牆上的那些『家人』就像只懂嬉鬧的鼠輩,都得閉嘴!在這片寂靜之中,我們在舞台上的低語便能傳播出去。」
他們站在那裡瞅著桌上的書。
「我一直想記下來,」蒙塔格說,「但該死的,我一轉頭就會忘記。天啊,我好想知道些什麼可以對隊長說。他讀的夠多,所以他知道一切的答案,似乎如此。他的聲音如同奶油般,我擔心他一勸,我又會走回老路。不過是一個星期前,我從煤油管中壓出煤油時,還心想:天啊,真好玩!」
老人點點頭,「凡無建設者則燒毀。自有歷史和未成年罪犯以來,便是如此。」
「原來我就是這樣。」
「我們每個人多少都有。」
蒙塔格往前門走去,「你有什麼方法可以幫我面對打火隊隊長嗎?今晚我需要一把傘避雨。我真的擔心死了,他要是再抓到我,我恐怕就會淹死。」
老人沒說話,但又緊張的瞥了他的臥房一眼。蒙塔格注意到他的眼神,「怎麼樣?」
老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屏住呼吸,然後才吐出來。他又重複了一次,閉上雙眼,緊抿著脣,最後終於吐氣。「蒙塔格……」
老人轉過身說:「來吧,原本我真的會就這樣讓你走出我家。我真是個膽小的老傻瓜。」
二
篩子和沙
那一整個漫長的下午,他們就在閱讀中度過,外頭的天空降下冰冷的十一月雨,落在安靜的房子上。他們坐在大廳裡,少了橘色、黃色的繽紛色塊和沖天炮般的爆炸,沒有穿著金色網洞洋裝的女人和穿著黑色天鵝絨、從銀色帽子裡拉出四十五公斤重兔子的男人,那樣的起居室顯得如此空洞而灰暗。起居室裡一片死寂,蜜卓不斷往裡頭張望,表情空洞無神,而蒙塔格則在地板上踱步,回到原來的位置蹲下,又把同一頁大聲讀了有十次之多。
「『我們無法精準斷言友誼是何時形成,就像一點一滴要裝滿一個容器,最後終於滴下那滴液體,讓容器...
推薦序
導讀
──尼爾‧蓋曼(Neil Gaiman)
有時候,作家所描寫的是一個尚不存在的世界。我們這麼做有上百種原因,(因為人總是要向前看、不要回頭望比較好;因為我們必須照亮前方的道路,希望人類或害怕人類踏上這條路;因為未來的世界似乎比當今的世界更加引人入勝,或更有趣;因為我們得警告你、鼓勵你,去檢視和想像。)為什麼要描寫明天過後,以及接下來的所有明天?有多少人在寫故事,原因就有多少個。
這本書是要提出警告,提醒我們所擁有的是多麼珍貴,而有時,我們卻不懂得珍惜。
有三種句型讓作家得以描寫尚不存在的世界(你可以稱之為科幻小說或預言〔寓言〕小說,你想稱作什麼都可以),這三句話很簡單:
倘若……會如何?
假如……的話
照這樣下去……
「倘若……會如何?」讓我們有改變的機會,得以抽離現實生活。(倘若明天外星人降臨地球,給予人類所想要的一切,但要付出代價,那會如何?)
「假如……的話」讓我們得以一探明日世界的榮景與危險。(假如狗可以說話的話;假如我是隱形人的話。)
「照這樣下去……」則是三者之中最具預言性的句型,不過這句話倒不是想要在一團雜亂的混沌中預測明確的未來。「照這樣下去……」這類小說其實是擷取今日生活中的某種元素,即某個清楚而明顯的事件,而且通常會讓人感到困擾,然後詢問這件事若繼續發展下去,影響力愈來愈大、愈來愈普及,足以改變我們思考和行為模式,屆時會發生什麼事?(照這樣下去,各地的通訊方式都會變成透過以簡訊或電腦傳送,以後人與人之間非經由機器的直接對話將會是違法行為。)
這樣的提問充滿了警告意味,讓我們去探究需要處處提防的世界。
人們認為(但人們想錯了)預言小說是在預測未來,其實並非如此;或者,就算是這樣,預測的結果大概也很差勁。未來有無限可能,受到各種因素、億萬種變因所影響,而人類總慣於聽信預言說未來會是如何,然後又做出很不一樣的決定。
預言小說真正擅長描寫的不是未來,而是現在,敘述某一個令人困擾或危險的面向,加以延伸、推論,將這個面向發展成一篇故事,讓當代的人能夠從不同角度和不同位置看待自己當下的行為,是一種警示。
《華氏四五一度》正是一部預言小說,這是一個「照這樣下去……」的故事。雷‧布萊伯利寫的是他的現在,卻是我們的過去。他提醒我們注意某些事,有些顯而易見,而有些在過了半世紀之後,比較不容易看的出來。
聽好:
如果某人告訴你一個故事在講什麼,他或許說的沒錯。
如果某人告訴你所有的故事在講什麼,那絕對說錯了。
不管是什麼故事,都包含了許多元素,說的是故事作者本身;說的是作者所看見的世界,他如何面對以及在這樣的世界生活;說的是作者如何選擇字句,而這些字句如何發揮作用;說的是這個故事本身,還有故事裡所發生的事;說的是故事中的人們;故事是為了爭論;故事是為了表達意見。
作者認為一個故事在講什麼,他的意見絕對正確,也一定是真的:畢竟,這本書寫成時,作者就在現場。他想出了每一個字,知道自己為何選擇了這個字而非其他。然而,作者是屬於他那個時代的人,即使是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看出他這本書究竟在講什麼。
一九五三年之後已經過了半世紀以上。一九五三年的美國,廣播還算是新穎的媒體,卻已經開始嚴重沒落──廣播叱吒的黃金時代持續了約三十年,但如今出現了引領騷動的新媒體:電視,迅速崛起。而廣播中的戲劇和喜劇節目,若非永遠結束,就是得重新設計視覺橋段,好在「傻子箱」上搬演。
美國的新聞頻道對於未成年犯罪的現象提出警告:青少年危險駕駛、認為人生就是要尋求刺激。冷戰也持續進行:這場屬於俄羅斯和美國及其兩造盟友之間的戰爭,無人扔下炸彈或發射子彈,因為只消一顆炸彈便足以傾覆整個世界,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並且將會是永遠無法回頭的核子戰爭。參議員舉行公聽會,揪出隱身在我們身邊的共產黨員,採取行動要消滅漫畫書。到了晚上,全家人都聚在電視機前面。
一九五○年代的笑話是這麼說的,過去你只要看到房子的燈亮了,就知道有人在家;現在你得看到房子的燈暗了,才知道有人在家。因為電視機很小,又是黑白畫面,必須把燈關掉才看的清楚。
「照這樣下去……」雷‧布萊伯利心想,「以後不再有人閱讀了。」於是,《華氏四五一度》就此展開。他曾經寫過一篇短篇故事〈人行道〉,描述有個人遭到警方逮捕,而他被攔下來的原因只因為他出門散步。這篇故事就融入了他所建構的世界,十七歲的克萊莉絲‧麥可勒蘭喜歡出門散步,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出門隨意走走的世界。
「倘若……打火員的工作是放火,而非滅火,會如何?」布萊伯利思索著,現在他開始看見故事的樣貌了。他編出一名打火員叫蓋伊‧蒙塔格,從火焰中救出一本書,而未將之燒毀。
「假如書本可以保存下來……」他想,如果摧毀了所有實體書,還能怎麼保存書本呢?
布萊伯利寫了一篇故事叫〈打火員〉,這個故事要求作者寫長一點,他所創造的世界要求他再多寫一點。
他跑到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鮑威爾圖書館,那裡的地下室有以小時計費的出租打字機,只要把硬幣投入打字機旁邊的小盒子裡就可以了。雷‧布萊伯利把錢投入盒子,敲出了他的故事。若是一時沒有靈感,需要一點啟發時,或是他想伸伸腿的時候,他就會在圖書館裡晃一晃,看看那裡的書。
然後,他的故事完成了。
他打電話給洛杉磯消防局,問他們紙張的燃點是幾度。華氏四五一度,某人這麼回答。他的書名就是這麼來的,真假與否並不重要。
這本書出版之後,大受歡迎,讀者非常喜愛這本書,並且熱烈討論。他們說,這本小說寫的是審查制度、寫的是心智控制、寫的是人性;寫的是政府控制我們的生活,寫的是書本。
法蘭索瓦‧楚浮將它改編成電影,只是電影的結局似乎比布萊伯利所寫的還要黑暗,看來將書的內容記在腦中並不如布萊伯利所想的安全,不過又是一條死路罷了。
我還是個小男孩時讀了《華氏四五一度》,我並不了解蓋伊‧蒙塔格,也不明白為何他會做出他所做的事,但是我能理解驅動著他的那股對書本的熱愛。書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而那些巨大如牆面的電視螢幕看來未來感十足,令人難以置信,一如我也無法理解電視上的人可以和我對話,只要有劇本便能參與電視演出。《華氏四五一度》並不是我最喜愛的書,這本書實在太黑暗、太陰沉了。不過後來我在《銀色蝗蟲》(《火星紀事》在英國出版時的書名)中讀到一篇故事叫〈厄瑟之二〉,我發現當中所敘述的情節:寫作和想像都是犯罪,讀起來如此熟悉,而感到無比興奮。
我在青少年時期又重讀了一次《華氏四五一度》,這本書成了一本談論獨立的書,寫的是關於自我思考。它在寫珍惜書本,以及在書本封面底下所隱含的不同意見,描寫我們身為人類如何從燃燒書本開始,最後也燒掉人命。
在我成年之後再讀這本書,我發現自己又對它讚嘆不已。當然,書中囊括了以上所提到的,但這也是一部反映時代的作品。書中描寫的四面電視牆是一九五○年代的電視:搭配交響樂團演出的綜藝節目、低俗的喜劇演員、肥皂劇。這個世界,充斥著開車飛快的瘋狂青少年,四處尋求刺激;處在一場永無止盡的冷戰,偶爾會有火光四射的場景;這裡的妻子們似乎都沒有工作,除了她們的丈夫沒有屬於自己的身分;這裡有獵犬追逐著壞人(即使只是機器獵犬),這樣的世界感覺上是緊緊依附一九五○年代的基礎而生。
今天若有一位年輕讀者發現了這本書,或者是未來的讀者,他必須先想像出一個過去,然後再想像屬於那個過去的未來。
即便如此,這本書的核心價值並不會受到影響,而布萊伯利提出的質疑依然有所憑據,並且非常重要。
為什麼我們需要書本裡的內容?詩詞、散文、故事?每個作者各有不同見解。作者是人,都是不可靠且愚蠢的,故事畢竟是編出來的,說的是從未存在過的人,以及從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為什麼我們要讀?又何必在乎?
說故事的人和故事本身非常不同,我們絕不能忘記這點。
想法(尤其是寫下來的想法)非常特別,這是我們傳遞故事和思想的方法,從這一代傳到下一代。若是我們失去了想法,就會失去共享的歷史,我們會失去許多讓我們生而為人的特質。而虛構的故事能培養我們的同理心:讓我們鑽進其他人的腦袋裡,賦與我們從他人眼中窺探世界的能力。虛構出的故事是謊言,述說著真實的樣貌,一次又一次。
我認識雷‧布萊伯利一直到他過世有三十年了,我實在非常幸運。他很風趣有禮,而且總是活力充沛(即使在他晚年,老到幾乎看不見了,還必須靠輪椅行動,他依然如此)。他很在乎一事一物,全心全意且毫無保留,他在乎玩具、童年和電影,在乎書本,他在乎故事。
這本書說的是在乎事物,這是寫給書本的情書,但我想也可以說是寫給人們的情書,寫給一九二○年代伊利諾州沃基根那個世界的情書,那是雷‧布萊伯利成長的世界,他將這個世界寫成了綠意鎮,存在於記錄他童年時光的《蒲公英酒》中,永垂不朽。
正如一開始我所說的:如果某人告訴你一個故事在講什麼,他或許說的沒錯;如果某人告訴你所有的故事在講什麼,那絕對說錯了。因此,我所告訴你有關《華氏四五一度》的一切,告訴你雷‧布萊伯利這本了不起的作品提出什麼警告,都是不完整的。書裡說的是這些沒錯,但還不只如此,說的是你從字裡行間能夠發現什麼。
(最後說一句,這些日子以來,我們總擔心、辯論著電子書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書,我很喜歡雷‧布萊伯利最後對書本的定義是多麼寬廣,他點醒了我們,不該只憑封面評斷書本的好壞,在這些封面之間存在著一些書,完全是人類的樣貌。)
二○一三年四月
導讀
──尼爾‧蓋曼(Neil Gaiman)
有時候,作家所描寫的是一個尚不存在的世界。我們這麼做有上百種原因,(因為人總是要向前看、不要回頭望比較好;因為我們必須照亮前方的道路,希望人類或害怕人類踏上這條路;因為未來的世界似乎比當今的世界更加引人入勝,或更有趣;因為我們得警告你、鼓勵你,去檢視和想像。)為什麼要描寫明天過後,以及接下來的所有明天?有多少人在寫故事,原因就有多少個。
這本書是要提出警告,提醒我們所擁有的是多麼珍貴,而有時,我們卻不懂得珍惜。
有三種句型讓作家得以描寫尚不存在的世界(你可以...
目錄
※導讀:尼爾‧蓋曼(Neil Gaiman)
第一部 火爐和火蜥蜴
第二部 篩子和沙
第三部 烈焰
◎後記:投入一角硬幣後
◎尾聲
※導讀:尼爾‧蓋曼(Neil Gaiman)
第一部 火爐和火蜥蜴
第二部 篩子和沙
第三部 烈焰
◎後記:投入一角硬幣後
◎尾聲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