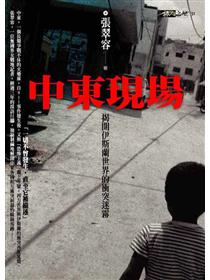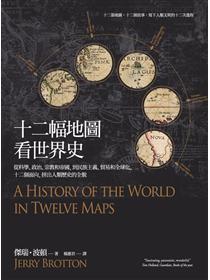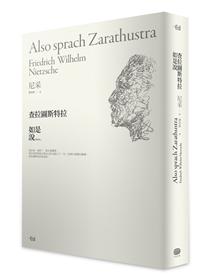章節試閱
PART I→美國後院的前沿地
第一章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
從何處而來,往何處去,都不是重要的了。
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
到山谷、到平原、到峻嶺,
到任何能夠走到的地方去當主人。
──墨西哥革命代表小說家阿蘇耶拉(Mariano Azuela, 1873-1952)
阿蘇耶拉寫下不少有關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的重要作品。而他所身處的時代,正是墨西哥體現「高地酋」(caudillo)①獨裁軍人高壓統治最嚴峻的時代,當時的廸亞斯將軍(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逐步以「貴族政治」取代前任遺留下來的「平民政治」,結果引發革命。
墨西哥文壇人才輩出,於一九九○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墨西哥詩人帕斯(Octavio Paz , 1914-1998),對現代詩壇影響尤巨。對他而言,寫一首詩就像執行一次革命行動,這是一種不斷自我革新的理念。在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中,他更道盡了西班牙語在拉丁美洲作為移植語言,在拉美文學中所產生的作用。
墨西哥富足的表象
一到達墨西哥城機場,眼前一片繽紛撩亂的景象,沒錯,我終於踏足在拉美的土地上。
我站在墨西哥城市中心,大都會的氣派,百聞不如一見,有不少朋友來過此地開會,各種的國際會議,無論是學術的、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甚至是社會運動的會議,都會在此地舉行,墨城真是一個中心,而且堪稱拉美大阿哥,試數數哪一個領域,不是由墨城牽頭的?
投資界談金磚四國,又或新興市市場,肯定離不開拉美地區的墨西哥。
拉美的石油儲量和產量僅次於中東地區,其中墨西哥是該地區石油產量最高的國家,墨西哥國家石油公司(Petroleos Mexicanos,簡稱Pemex)於二○○八年更成為拉美石油行業收入最高的企業②。
此外,墨西哥又是美國企圖在拉美建立自由貿易區的第一個實驗站,一九九四年墨西哥正式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自此,墨西哥與美國的經濟一體化便成為拉美地區的樣板與典範③。
墨西哥的咖啡令我呷第一口即咳了數聲,可是,坐在城中一流的咖啡廳是如此賞心樂事,多麼有格調,多麼有品味,天花板的雕刻一絲不苟,掛在餐廳一角的油畫也甚有來頭,我最喜歡的就是緩緩播放出來的一首墨西哥音樂,一如現場的柔和燈光,整個氣氛令四周的顧客只願喁喁細語,鬈曲的棕色頭髮,長長睫目下的圓大眼睛,如大珠小珠落玉盤的西班牙語,加上畢挺的西裝和端正卻又跟上潮流的女裝西裙,他們是來自墨西哥的華爾街,出類拔萃的精英,戰後新興的階級。
多謝我在以色列認識的記者朱利亞安,他把我帶來此地,體驗一下墨西哥的繁榮和優雅,他是一位自由主義者,認為墨西哥與美國合作才能創造雙嬴的局面。他壓低聲音說:「難道要去學古巴嗎?」跟著他「噗」的一聲笑了起來,聳聳肩,再說:「沒錯,跨國資本進來墨西哥是要牟取暴利,但我們也因此得到快速的發展。」
朱利亞安所指的發展,乃是墨西哥戰後實行自由經濟政策所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這與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相類似,當時墨西哥有「美洲獅」之稱,分享「美洲獅」聲譽的還有巴西、阿根廷和智利。
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間,當時的發展理論强調,經濟發展得從追求GNP高速增長開始,並以「先增長、後分配」為發展策略,在這策略下,社會公義無奈靠邊站。
由於墨西哥財富高度集中在一小撮大財團手中,增長而不分配讓社會階級鴻溝愈益嚴重。
試想想,一個僅由二十二個強大的墨西哥金融集團和其他二十個外國集團組成的小型核心團體,已霸占了整個墨西哥市場,而國內的出口商也只有十個生產集團,他們的壟斷地位令其他企業根本無法生產,在這情況下,即使經濟增長如何快速,對普羅大眾而言,完全毫無意義,這只不過反映著一小部分經濟精英的財富又膨脹了。
高增長帶動高通膨,人們基本生活受到威脅,紛紛北望美國尋找出路,使墨西哥出現大量移民潮、偷渡潮,而墨西哥的經濟竟然也依賴在外的數百萬墨西哥人賺來的外滙支持。
無論如何,朱利亞安還是極力向我展示墨西哥富足的一面:琳瑯滿目的各種商品、高貴優雅的中產文化、鳥語花香的花園洋房、紅酒、名車、美食……
第二天,他又帶我去探望他一位來自古巴的朋友黛麗絲。黛麗絲打扮男性化,四、五十歲,自己一身創立製作公司,辦公室裡滿是錄影帶、照片、海報、書籍、器材等等,十分混亂,她抽著古巴大雪茄,一派女中豪傑。她一見我,先來個大擁抱,知我是記者後,便大數古巴這個共產祖國的不是,墨西哥相比之下,有偌大的自由空間,讓她可以實踐古巴不能做的事,例如創業、出遊、買房子……
她說:「在古巴,人容易得精神病,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因發揮不了才能,加上生活逼人而自殺,官方不許報導這等現象。」我瞪大眼睛,第一次聽聞古巴的精神病和自殺率奇高。黛麗絲繼續煞有介事告訴我古巴人出走的原因,在她心中,墨西哥是天堂。
但,我心中有數,墨西哥擁有世界首富,例如電訊鉅子,卡洛斯.斯利姆.埃戶(Carlos Slim Helu),其身家在二○○七年一度超越美國微軟公司比爾蓋茲,躍升《財富雜誌》富豪榜全球第一位,僅此而已,他們遮掩不了其背後的千瘡百孔,還有浩浩蕩蕩的窮人群,令人一看便震驚。
走在墨西哥城的市中心,氣勢磅礴的商業大樓,工商企業大部分由外資控制,金融業如銀行則全屬歐美機構,例如Bancomer、Banamex、Bital、BBVA、花旗集團及匯豐銀行。這是怎樣來的?最初,國家表示注資救本土財團,把企業變成優質後,則又高價賣給外資,例如Banamex在五週內獲注資一百五十億後由花旗集團收購,本土的大股東獲益巨大④。
結果,本地企業在市場的占有率只有百分之十,其他全屬跨國公司擁有,農業垮了,工業完了,金融業屬於國際資本,令國家依賴外資的程度幾乎達百分之一百,經濟結構脆弱,只要外資有什麼風吹草動,國家即面臨崩潰。發生在一九七六年、八二年及九四年的金融危機,以至一九八二年由墨西哥所引起的全球債務危機,都是值得深思的例子。
我與朱利亞安一討論上述的問題,便會沒完沒了。
朱利亞安的弟弟李奧普度為一名紀錄片導演,他的眼睛就是他的攝錄鏡頭,而他手中的攝影機就是他的一隻眼睛,我驚訝兩者的透澈。他與哥哥乃是一個向左走,一個往右跑。一次,我受邀到他們家裡吃晚飯,兩兄弟一講起國家大事,便很容易爆發爭論。當時(二○○六年七月)墨西哥正進行如火如荼的大選。
他們是分裂中的墨西哥縮影。
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李奧普度要拍攝邊境區加工場(西班牙語稱Maquiladora)的故事,特邀我一同前往觀察,這是一趟艱苦的旅程,但李奧普度這位免費導遊也實在令我大開眼界。
想不到,七月的墨西哥城一早一晚是如此的清涼,我們就在冷風中於朦朧的月色裡進發。在顛沛的公路上,我想到《巧克力情人》(Como agua para chocolate,港譯《濃情朱古力》)這一部經典墨西哥電影,我經常這樣苦中作樂。
或許,墨西哥的巧克力真的是甜得醉人,如有機會一定要嘗試一下。此際,我的思緒隨著無邊的夏月奔馳,沒有政治,卻出現了一首墨西哥無名詩人的詩作〈蛇〉:
牠喜歡漫漫長夜
因為有黑暗做牠搏鬥的對手
在牠的尾巴掃過的每一塊石頭上
火星四起,火光四射
背負黑暗就是背負火焰
在黑暗與火焰鬥得最激烈的時候
蛇的背上伸出了羽毛
這羽毛永遠不會被薰黑
也永遠不會被燒焦
這羽毛將帶著蛇飛行
黑夜愈沉
牠將飛得更高
墨西哥與美國的陸地接壤邊境特別長,遠望那一條界線,我感到哭笑不得。因著密切的地理關係,美國自然視墨西哥為第一個大後院,大後院的意思是……
我想到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⑤。
這是一個似乎已過了時的理論,但隨著美國於二○○八年正式引發的金融海嘯,它又回來了。
原本為拉美政經情況量身訂造的一種學術解說,倒頭來卻呈現出第三世界的普及性,它或許還有不完善之處,有對手如西方發展理論派甚至猛烈批評之,但依賴理論是屬於拉美的。
阿根廷經濟學家普雷畢齊(Raul Prebisch)首先提倡並發揚光大,他指出,强國經濟發展成一個世界中心,其他較不發達國家成為這個中心的邊陲,並依賴中心生存,為中心服務,因而令自己變得異常脆弱。在此,美國社會學學者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承接依賴理論,發展出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一時之間,拉美成為發展理論的焦點與範式。
或許,拉美是對抗資本全球化最早的一個地區,代表歐洲資本擴張的西班牙首先看上了拉美豐富資源,以最快、最狠的速度把這地區捲入原始資本累積的洪流,納入了他們的首個擴張範圍,使得拉美成為世界現代資本體系牢牢困窒而不斷出現反彈的典型例子。
閱讀拉美歷史就是閱讀一頁重要的全球化歷史;閱讀拉美歷史就是閱讀一頁中心與邊陲之間角力的歷史(見附錄二)。
在漫長的邊境地區,有震耳欲聾的機器聲,自「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於一九九四年正式生效後,美資公司終於可以自由汲取墨國廉價勞動力,因此,在邊境一帶地區,湧現大量血汗工廠(sweatshop),來自墨西哥窮困地區的居民,紛紛跑到此地尋找工作,而美國廠商也前來尋找廉價勞工,並享有邊境區内出入口免稅特惠政策。
一時之間,自由貿易製造了很多幻想,與此同時,境界線卻出現更嚴密的鐵絲網,更堅實的圍牆,我不敢靠近,與邊境界線一樣長的血淚故事,與亂草一同在孤獨的空氣裡哭訴。
像這樣的情景,同樣出現在中美洲的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整個中美洲是一個龐大的國際加工廠,停不了的機器,流不盡的血汗。
墨西哥勞工幻想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可鼓勵更多美國投資和貿易,那麼他們便可得益於製造業加工區的擴大,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可惜,殘酷的現實很快告訴他們,投資與貿易的增長不等於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在赤裸裸的自由招牌面前,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令勞工缺乏議價能力,當生產力上升,工資卻反之下跌,人們無法脫貧。事實上,墨西哥生活於貧窮線下的人數,從一九九四年的百分之五十.九七,上升至二○○八年的百分之六十多。
我在李奧普度的引介下,訪問了兩母女,她們離開農村,加入名牌運動鞋加工廠的生產線,媽媽謙卑地表示有一份工作已很滿足,她沒有想得太多,省下微薄的工資來貼補家計,她向我說:「自貿易協議實施以來,這裡的確增加了很多工作機會,我想,有工作總比沒工作好,是嗎?」
但女兒卻氣憤表示,媽媽不自知地賠上她的寶貴健康,狗臉的歲月,吃人的機器,工廠空氣中瀰漫著烏黑的粒子,刺鼻的臭味。
我聯想到年前去探望一個中國農村家庭,這源起於我在以巴地區採訪時認識了一位來自江蘇農村的黃大哥,他因農村無以為繼,冒險往以巴地區工作,結果客死異鄉。他臨死前向工友留下我的電話號碼,囑咐其家人找我幫忙。
我走進黃大哥的故鄉,農村已面目全非,大部分土地出租給外資紡織廠,黃大哥的兒子小鵬在紡織廠工作,一天十二小時,一星期七天,做一天計一天工資,沒有有薪假期,更沒有任何福利。
小鵬告訴我,他們工廠分兩班,日班由早上七時至晚上七時,晚班由七時到第二天早上七時。我瞪大眼睛,一天二十四小時,機器就是這樣不停轉動?
小鵬及他媽媽帶我走到黃大哥墓前拜祭。黃大嫂禁不住哭喊,說:「我們來了,張記者也來了,你安息吧!」
在一片渺無人煙的空地上,一個個的荒墳在雜草裡默然屹立,而黃大嫂一邊哭著,一邊撒著溪錢(廣東語:亡者用的金錢),漫天溪錢飛舞著,忽然一陣風吹過,黃大嫂隨風遠望,沉默了一會,心情突轉豁然,咧嘴向我說:「黃大哥剛才已乘風來看過我們了。」
然後,黃大嫂心滿意足回家去,但我的心隱隱作痛,農村人的純樸,卻成為被剝削的對象。這裡的雜草,墨西哥的亂草,一樣在風中發出呼呼的哭訴聲。
工人們的前路如看不見彼岸的黑洞,不過,我在此看到彼此的命運,從中國到墨西哥。
誰欺騙了你的自由?
我在工廠裡繼續走動觀察,從墨西哥工人們身邊經過,他們望著我這位外來客,滿臉灰塵汗水,竟還向我展示燦爛的笑容,點頭表示bienvenida(歡迎)!
Bienvenida!美國廠商自由湧入,但美國卻不斷收緊移民政策,明顯是衝著墨西哥而來,兩國接壤的邊境經常發生流血事件,引發不少悲劇。據統計數字,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接近四百萬黑市勞工企圖偷渡到美國,有不少就此枉送性命。
美國軍警在邊境上嚴守著,惟恐墨西哥的混亂狀態如傳染病蔓延到美國境內:走私販毒、黑市勞工、偷渡者……
「要錢不要人」,墨西哥人經常把這句話掛在口邊,指控美國。
墨西哥的「亂」和與美國的關係,可算是拉美地區的一個樣板。
了解墨西哥後,穿過美洲的肚臍,再往南美洲,我們便可有個概念,何謂拉美化?
墨西哥經濟學者赫拉斯(Carlos A. A. Rojas)指拉美化即貧困化,這是由於拉美在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嚴重失衡情况,其主要特徵包括:外資主導型開放經濟下出現階段性經濟高速增長,只重增長卻不公平分配,加上威權統治導致官商勾结、政治腐敗,法紀不彰,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原來拉美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地方,階級異常分化⑥。這一不均衡發展導致城鄉差距加大,人與自然得不到和諧發展,加上輕視教育福利等社會保障,社會治安惡化。
有學者進一步認為,問題核心在於外資主導型開放經濟下,令拉美喪失對本國經濟和資源的控制權而付出代價。
無論如何,拉美地區被譏為「有增長、沒發展」,單看數據可以嚇人一跳。例如貧困人口比例從一九八○年代的平均百分之四十,不斷上升至二○○三年的百分之四十五,整個地區有二.二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百分之一的地區人口便占了百分之四十三的地區財富⑦。
環望世界,有多少地方正在拉美化?近年,有中國學者關注中國有否出現拉美化現象⑧。
我和李奧普度談到拉美化的怪現象,也談到北美自由貿易的怪現象。紐西蘭的奧克蘭研究所有以下的研究:自由貿易不平等。墨西哥完全打開大門後,美國仍然繼續農業補貼政策,美國農民可大量生產廉價農產品,並挾優勢湧入墨西哥,例如玉米,令入口產量翻了幾翻,單是二○○三年已高達八百萬噸,令人咋舌。
眾所周知,玉米是拉美主要糧食之一,面對美國玉米生產優勢,墨西哥玉米農民無法競爭,紛紛被逼離開農地,另謀發展;諷刺的是,他們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受害者,結果還是擺脫不了自由貿易的枷鎖,在血汗工廠工作的工人,有多少正是剛放下犂頭的農民?!
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現在,墨西哥的進口糧食竟然占了該國的糧食供應百分之四十;反之,墨西哥的本土農業卻不斷萎縮。
李奧普度無奈地苦笑,說:「這就是作為後院的悲劇,到頭來人民什麼都沒有!」
與美國為鄰,是宿命,是詛咒,還是祝福?在墨西哥,有一句流行的順口溜:「我們離天堂太遠,離美國太近。」
對,墨西哥的政經架構乃是按美國模式而建立的。自一九一七年制訂民主憲法後,墨西哥的民主正式制度化,但這種制度經常給國民譏笑為只有外殼,內裡有太多可供操弄的空間,貪污舞弊,是墨西哥政治的一大特色。
一九一七年以前,墨西哥人經歷了三十五年總統迪亞茲(Porfirio Diaz)獨裁統治,一九一七年以後,卻又有統治墨西哥達七十二年的建制革命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無論是迪亞茲或是建制革命黨,都是以服務外資及大企業為主要政策。
結果到了二千年,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以為牢不可破的建制革命黨,結果輸了大選,由另一個政黨,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上台,墨西哥人指墨西哥革命黨不是敗給國家行動黨,而是敗給他們過去極度腐敗的政績。
但,諷刺的是,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Vincent Fox)接任總統後,競選時所承諾的改革一一落空,一方面由於國家行動黨在國會屬少數黨,令福克斯施政困難,另一方面,曾任可口可樂領導層的福克斯,與工商界關係千絲萬縷,最後也逃不出聽命於大企業的金剛箍,令貧窮不僅沒有改善,反之擴大,而他在任內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則激發更大的社會矛盾⑨。
二○○六年,又是大選年,但這一年對拉美人而言有著更大的意義,因為從二○○六年開始,拉美國家逐一向左轉。而在墨西哥,這一年的大選,差點兒也跟著顛覆了該國過去的政治版圖,為人民帶來短暫的革命美夢。
那麼,我就把鏡頭對準二○○六年的大選,來一個歷史的定格。這回亦不例外,歷史的時鐘在廣場上擺盪著。
二○○六年大選的歷史定格
每一個首都總會有一個廣場,或與廣場相若的地方,讓人民感到他們的實在、他們的虛無;他們的力量、他們的渺小。
廣場,是一個人民與政府角力的聚焦之地,無論在民主國家,或是獨裁國家,皆如是。
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土地珍貴,容不下一個廣場,但有個維多利亞公園。公園入口處即可見象徵殖民歷史的維多利亞女皇像,總在人群之中正襟危坐,窺視公園裡所發生的一切。這個維園,不會完全屬於人民,只不過人民以為他們完全占領了維園罷了!
在墨西哥城,位處市中心最具代表性的蘇家諾廣場(Plaza Zocalo),在歷史上無數次給人民占領。至於轟動墨國的一九六八年一場學生運動,也一樣從廣場開始,這是與蘇家諾廣場同樣知名的三文化廣場(Plza de las Tres Culturas),結果遭血腥鎮壓,悲壯收場,墨西哥知名女作家兼記者艾蓮娜.波尼亞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曾就此寫成感人的《泰第勞哥大屠殺》(Tlatelolco Massacre),又名《墨西哥大屠殺》,我在墨西哥城訪問了她。
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大選則如火如荼,我走訪她的家,一個位於墨西哥城市郊的高尚住宅區Chimalistac。
由於艾蓮娜本身是記者也是作家,這令我想到波蘭已故記者兼作家卡普欽斯基,他們兩位同樣強調街頭文學,也一樣享有國際聲譽。
湊巧地艾蓮娜的父輩血統亦是波蘭人,而且來自皇室貴族,她母親則是墨西哥人。
這樣一位貴族後裔,她卻選擇走進墨西哥底層去記錄。她曾這樣說,她的文字就是無聲者的聲音。
她說:「我們是自己的版圖,我們寫因為我們可以,我們都是拉丁美洲的女人。」
她寫女人,特別是來自貧窮的女人。
我與她的訪談,也是從女人開始。
問:艾蓮娜,其實你有很多選選擇,你出身在巴黎,父親來自波蘭,經常到美國講學,但為什麼選擇墨西哥?選擇西班牙語?
答:我母親是墨西哥人,我愛我的母親,以及她所屬的土地,就像拉丁美洲人視土地如母親一樣,深深愛著他們的母親。
問:為什麼你經常強調女性作家這個身份,特別是你的拉丁美洲女性的身份?
答:我覺得,女性一直遭到錯誤的表述,而拉美女作家更是如此,因為她們都是來自貧窮無助的角度。整個拉美,貧窮是這麼普遍,令人不怎麼當一回事。但作為一名女作家,你會很容易自覺你和窮人的邊緣身份,你要和他們站在一起。
問:對,《這裡在凝望你,耶穌》(Here’s Looking at You, Jesus)一書中,就是敘述了一位農民婦女參與墨西哥革命的事蹟,這是一個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故事,你卻用小說的方式去寫。但你又偏偏愛記錄,用記者技巧去仔細採訪,去調查,你不放過每一個人,特別是街頭上的人。你認為在你雙重身份中的記者角色,對你有什麼影響?
答:記者的身份讓我有機會去問,多於去答。如果要我告訴你,影響我寫作至深的是什麼?我會說,那就是街頭的聲音。
問:那是一種怎樣的聲音?
答:那是屬於失掉聲音者的聲音,囚室中的哲學家,流動的叫賣者。他們受著各種各樣的迫害,即使他們的語言,都是脆弱的。沒有了語言,便沒有了身份。
問:你所指的是窮人與女性?這是你作品永恆的主題,是嗎?
答:還有其他受壓迫者,在這裡多不勝數,窮人與女性在其中有一種獨特的代表性。
問:對,你的《墨西哥大屠殺》真是一本令人感到震撼的書,當我細閱書中一九六八年學運的受害者個案時,實在無法釋懷。據估計,有二百多名示威學生遭軍警殺害。他們只是用和平方式去抗議獨裁政府剝削了他們的自由。聽聞,霍克斯(Vicente Fox Quesada)政府剛出了一份報告,承認前政府使用了過份的暴力,這是怎樣的一回事?
答:就是僅此一份報告而已,他們沒有特別追究或賠償。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政府就是用屠殺的方式去對待異己,然後埋藏真相,剝奪我們的記憶。在這個充滿謊言和偷竊的國家,沒有比去揭發真相更重要。你知嗎?在這裡,沒有人不去偷,政客偷得最狠。
問:因此,你要記錄,切切實實去記錄。但,你也有參與政治,你為什麼去支持奧布拉多?
答:正因為他沒有去偷,也沒有撒謊。噓!你知道嗎?在墨西哥,如果你知道一位政治人物竟然不去偷,也不撒謊,這是多麼的一件大奇聞啊!廉潔的政治,這對墨西哥人是如此重要呢!因此,當奧布拉多參選時,老百姓用最大的熱情去支持他。在蘇家諾中央廣場上,即使社會的邊緣人士,也都現身了。他們很有秩序,用各種方式為奧布拉多助選,你看見了嗎?
問:我有看見,的確是聲勢浩大的隊部。你與奧布拉多認識很久嗎?
答:沒有,大選前我與他只有幾面之緣,但他來找我,我覺得墨西哥是時候要轉變了,整個拉丁美洲都在變,墨西哥能趕上這個大潮流嗎?她會錯失這個機會嗎?
問:知識分子在當中的角色是……
答:墨西哥的老百姓都盼望知識分子能出頭,作家的每一句話都可以發揮一定的影響力,他們都在等待我們開口、介入!
問:就好像查巴達運動領導人馬哥斯,他原本是大學教授嗎?
答:我不認識他,但他成功把一個原本已被遺忘的查帕斯省,再次受人關注,這是他的功勞,還有當地的婦女,她們是底層中的底層,現在她們都明白要掌握自己的命運,這真讓人感動呢!馬哥斯發揮了他的作用。事實上,墨西哥的社會運動愈來愈強大,你打算去了解嗎?我兒子也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分子,有機會給你介紹吧。好了,我要外出了,要為奧布拉多站台。
其後,她跑到蘇家諾廣場去。
在大選的日子,人民在廣場上表達他們的訴求,那些原住民、政黨支持者、草根苦主、無家可歸者……在綠色與白色的巨大墨西哥國旗飄揚下扎營不走,他們播放出最強勁的口號與歌曲。
這個廣場很有趣,只要細心觀察,你會發覺它四周受到總統府、市政府、大教堂的包圍、俯視。
與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一樣,墨西哥人嚴守天主教的作息,一到星期天,所有店舖關門(少部分例外),大街小巷冷冷清清,只有教堂鐘聲叮叮噹噹響個不停。不過,在大選日(七月二日),熱情的選民紛紛跑到投票站,弄得市面鬧哄哄。一位墨西哥記者朋友領我觀察大選情況,看到投票站外長長的人龍,我感嘆地說,這表示墨國情況到了不能不改變的時候了。
這次兩大陣營鬥個你死我活,而選民也嚴重分裂,兩個主要候選人在選前的勝算只相差百分之三至五。希望維持現狀、穩定發展的選民會支持國家行動黨的卡德隆(Felipe Calderon),他是上任總統福克斯的繼任人,擁抱自由經濟的同時,也賣弄一下他對低下層的關注;但另一民主革命黨(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D)的奧布拉多(Lopez Obrador)則不諱言,大黨派對低下層的福利承諾,一旦當選,怎樣可以實踐?到頭來就可能一如福克斯,再次令選民失望。
二○○六年七月的大選不但特別,而且重要,國際傳媒各就各位,美國也在密切關注,這個就在他們腳下的拉美石油國家,會否受到南美左翼風潮的骨牌效應影響?然而她與美國關係更為緊密,除了在地理上與美國相連外,她又是美國全球第三大貿易夥伴,美國是墨西哥石油的最大輸出國。
諷刺的是,因墨西哥缺乏相應的技術,惟有依靠美國提煉原油再輸入墨國,但油價已翻了幾番。據統計,墨西哥有百分之四十的汽油來自美國。
在墨西哥,大家都抱怨油價太貴,老百姓未能從產油工業得益,反而加大了貧富差距。
墨西哥普羅大眾指責美國跨國企業操控墨國最大的天然資源──石油,指責現任總統福克斯官商勾結、腐敗無能,只淪為美國的傀儡。
「我們需要一場革命!」墨西哥社會出現嚴重的階級與經濟分化,分析家指出,墨國已為一場聲勢浩大的階級革命拉開序幕,北面的中產精英對抗南面的勞動階層及印第安原住民。中產精英要求維持現狀,高舉國家行動黨的藍色黨旗,他們的主席卡德隆終於以半個百分點勝出成為總統。
卡德隆與前一任總統福克斯同屬一個政黨,曾在福克斯政府中當過石油部長一段短時期,主張石油私有化,加強執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對美關係,是美國商界的忠實夥伴。
事實上,墨西哥自一九三八年由民族主義將軍卡德納斯(Lazaro Cardenas)國有化石油產業以來,沒有人夠膽挑戰,直到二千年國家行動黨的福克斯上台,跟著輪到卡德隆,他們均先後提出石油私有化,並成為政黨之爭。
墨國的勞苦大眾則把希望投射到奧布拉多身上。奧布拉多提出以滅貧掃盲為主的社會經濟模式,主張石油維持國有,資源重新分配,檢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公現象。但,我留意到,他在演說中對於美國和商界關係總是小心翼翼,避重就輕,可是,卡德隆陣營一開始即已把他打成共產黨同謀,並將他和古巴的卡斯楚和委內瑞拉的查韋斯相提並論,一樣是危險人物。
墨西哥窮人則要把奧布拉多吹捧成為他們的救世主,一群熱情的支持者更在廣場上擺放了一系列革命家的肖像,從墨國獨立運動英雄伊達哥(Miguel Hidalgo)、拉美革命英雄切.格瓦拉,到越南的胡志明、中國的毛澤東,再加上奧布拉多,造就了他們的革命夢想。
大選結果卡德隆竟以百分之零.五險勝,點票過程具爭議,因有百多萬票不翼而飛和數十萬票發現在垃圾箱裡。落敗的民主革命黨不滿大選出現舞弊情況,支持者呼喊:還我公平選票,Voto por Voto, Cassilla por Cassilla?
在墨西哥大選日,我意想不到有那麼多國際觀察員來到這個國家監察選舉,他們不是什麼國家代表團,而是一些民間組織或個人自掏腰包,跑來為墨西哥人民打氣。
在酒店認識一群來自加拿大的觀察員,他們都屬於一個叫「Common Borders」(共同疆界)的組織。這個組織專門觀察拉丁美洲的大選,計有秘魯、智利、薩爾瓦多、玻利維亞、厄瓜多,很快他們又會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
他們一致表示這次墨國大選很特別,首先各政黨投入大選的經費可算是前所未有,而且動員能力驚人,從知識分子到草根農民,全國都弄得沸騰起來。就好像拔河比賽,拉扯得各不相讓,把社會狠狠地撕裂成兩邊,並互相撞擊,令人感到七級地震即將發生。墨國外資當然不希望左派上場,這裡的傳媒與之很是配合。
你隨便與任何一位墨西哥人說起大選,他╱她都會滔滔不絕,並指墨西哥對美國太重要,美國絕不容許左派勝出。很多中美洲國家由於要排斥左派當選,導致內戰發生,民不聊生,留下的傷痕久久未能癒合。
在一大群國際觀察員當中,我認識兩位來自挪威的女孩,還有一位法國男孩全副「武裝」——拿著專業攝影機、照相機,戴太陽帽,穿上防水風衣、皮靴,充滿精力到處跑,拍下他所見證的一切。
墨西哥有一個民間影音團體,在重要日子都會免費借出器材,讓更多人可以攝錄見聞,即使外國人如我,也可借用。但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要求借用者留下一份他們的見聞紀錄,其目的是可讓他們獲知不同借用者的不同觀點與角度。
由於墨西哥民間社會長時期與政府抗爭,社會運動組織湧現,而且變得國際化,墨國的社運組織與國際公民社會有豐富的交流,例如墨國北部城市瓦哈卡(Oaxaca)的教師運動,便獲國際公民社會的同情和支持⑩。
至於上述兩位挪威女孩,她們前來墨西哥城觀選之前,原來一直在南部查帕斯(Chiapas)協助農民。她們還熱情地邀請我到查帕斯探訪她們所屬的組織,以及附近不同部落的農村。她們告訴我,由於世界各地來墨西哥參與社運的何其多,因此,墨國政府設計出一種社會運動簽證,沒有申請該簽證的,一律不可參與各種遊行集會,我聽得好奇又半信半疑。
大選當天結束之際,有傳聞指有一百萬張選票不翼而飛,國際組織與當地團體(包括學生等)組成一個龐大遊行隊伍,反對貪污的大選、受操弄的大選。
當有關當局宣布大選結果後,墨西哥城開始竊竊私語,我在酒店認識的一位美國人即時大笑,指這與美國二千年那次大選何其相似,而酒店內的守衛則很氣憤,認為是美國協助右派阻撓左派的奧布拉多當選成為總統。
勝出者也不必太高興,墨西哥社會嚴重分裂,失敗陣營會返回原有崗位,繼續他們的革命之旅。而卡德隆上台後,他所提倡的石油私有化處處受阻,後來以改革代替,二○○八年由能源部向國會提交改革草案,建議擴大與外商合作領域,引起社會上爭論不休,令原本分裂的社會更加分裂。
在大選日,墨西哥城知名學府國立自治大學(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於下午舉行了一場反選舉的音樂會,地點是大學大禮堂,這大禮堂正是以切.格瓦拉命名。
我跟著一班同學跑到大禮堂,校園區沿途可見不少具革命內容的壁畫,在鮮艷奪目的顏色裡裹藏了震撼人心的革命信息。其中一幅壁畫,頭頂上印有一大行字句︰Education is Revolution(教育就是革命)。
當中有一活躍於社會運動的學生伯查,他向我說:「你來墨西哥,不能不了解這裡的社會運動為什麼如此蓬勃?」
遺世獨立的查帕斯自治區
第二天,他即帶我坐公車到一爭議性小鎮阿丹哥(Atenco)。一上車,即可看見司機位置旁有一聖母瑪利亞像,在聖像下面便是切.格瓦拉像,兩個像一上一下,和諧地並存,也真夠諷刺。司機知我好奇,向我說了一大堆西班牙話,之後,豎起大拇指,並問我有什麼看法?
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在我身旁的伯查連忙翻譯,說︰「他問你支不支持他們的革命?」
經過幾個小時後,終於來到阿丹哥,隨處可見的政治標語,令我大開眼界,這裡真不愧為墨西哥人所共知的政治鄉鎮。當我正墮入沉思時,一位小女孩拿著兩把長刀從我面前經過,她還故意捉弄我,向我耍弄了兩下長刀,霍霍有聲,嚇得我瞪大眼睛。
她大笑起來,我忍不住問她多大,她舉起八隻手指,啊!才八歲,怎麼耍弄刀劍而毫無懼色?她指著牆壁,上面有一蒙面婦女肖像,也是一樣手持長刀,旁邊寫著︰我們不要大選,只要革命,就讓我們每人拿起長刀來,保衞尊嚴與土地。
不久,一大群示威者出現,個個手持長刀,準備坐車到墨西哥城遊行去。我嘖嘖稱奇,在香港,怎會有如此兇猛的示威?!聽聞阿丹哥不久前因人民抗議政府沒收他們的土地來興建機場,發生大規模衝突,數十人死傷、被捕,而長刀,正是他們抗爭的重要武器。
其後,伯查帶我到墨西哥城附近村鎮了解當地的貧困情況。那裡有一個社區,不少居民沿著已棄置的火車路軌建立他們的居所。細看之下,他們的房子是一些破爛的貨櫃車,一家幾口就這樣住在密不透風的貨櫃裡。
這令我想起印尼雅加達的貧民窟,還有菲律賓的垃圾山;世界人口有多少活在貧窮線之下,每天只能賺取數美元來維生?如果墨西哥政府不正視貧窮的問題,相信這個壓力鍋很快便會爆炸。如果表面的經濟繁榮沒有穩定的社會作為基礎,那麼繁榮永遠只能是表面,如肥皂泡泡,一刺即破。
我舉起相機欲拍下火車路軌上的生活情況,一位拿著水壺的居民怒目而視,伯查催促我趕快離開,並告訴我,他們可以很暴力。
在火車路軌社區的附近有一間雜貨店,貨架上竟然有大麻與一些我不太懂的毒品。我有點驚訝,伯查聳聳肩,表示政府無力管制毒品。一個窮字,令這裡的毒品氾濫,而他們販賣毒品的主要市場就是美國。
伯查問,美國為什麼也無能力控制毒品?美國黑市市場對毒品的需求量之大,也令人咋舌。美國不但需要墨西哥的石油,毒品更成為兩地罪惡之源。現在,墨西哥最大的難題,就是毒梟的政商勢力龐大,毒品問題很難解决,在美墨邊境,每天都上演殘酷血腥的毒品爭奪戰,上萬人死亡。
當墨西哥年長一代的作家仍然哀嘆上世紀革命壯志未酬,年輕一代作家卻只為目前的社會暴力憂心,他們不少作品反映墨國社會問題︰教育、治安、失業、販毒……
從墨西哥所面對的種種複雜難題,我們的話題很容易扯到革命去,伯查興奮起來,他提到墨西哥的神秘革命家副總司令馬哥斯(Subcomandante Macros),他是何許人也?眾說紛紜。
伯查得意地表示,他真名為Rafael Sebastian Guillen Vicente,原來就是他的大師兄,在國立自治大學唸哲學和傳播碩士,論文乃研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權力理論,但深受左翼政治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81-1937)的影響。
我記得有人指他曾在國立人類學院任教授,後來聽說他應該在碩士畢業後留在母校教傳播哲學,總之,大家都有不同的說法。無論如何,他被視為墨西哥以至拉丁美洲的現代革命家,則是毋庸置疑。
無論如何,馬哥斯放下一切,隻身跑到墨西哥南部查帕斯地區領導農民革命,組成查巴達民族解放軍(Zapatista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⑪,並帶上鴨嘴帽,把面蒙起來,其他查帕達的成員也一起蒙面,人稱之為蒙面騎士,成為了一支世界矚目的反企業全球化革命軍。最令人嘖嘖稱奇的,就是他透過對現代傳播的知識,利用互聯網、短訊等科技將查巴斯的人權情況向世界發放,讓原本不為人知的查帕斯地區,一度成為國際傳媒的焦點。
每一場革命,都是一場解放土地的革命。在拉美地區,因土地引發農民起義事件屢見不鮮,在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交替期間,便曾出現一位傑出的農民革命家查巴塔(Emiliano Zapata, 1877-1919),領導南部原住民爭取土地和自由,他並呼應北部由馬德羅領導的新興工人階級抗爭行動,爆發出轟轟烈烈的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
頭頂著墨西哥大草帽,一身農民打扮的查巴塔,自此成為農民的精神象徵。我在墨西哥城的國立自治大學校園裡,見到他的肖像海報,在薩帕斯省當然也見到他的肖像海報,而現在的查巴達運動便以查巴塔命名,自稱要繼承這位農民革命家的遺志,馬哥斯更進一步說:「我們是五百年前的產物!」
究竟查帕斯是一個什麼樣的地區?
由於他的存在,每年吸引無數國際社會運動人士來到墨西哥,令這一場農民革命增添濃厚的浪漫色彩。
從墨西哥城到南部查帕斯,需要十三個小時至十六個小時不等,友人建議我坐最貴的那一種公車,比較安全。果然不負期望,這裡的高價巴士比美國灰狗好得多,由於貴(七十五美元一程),沒有太多人乘坐,我可以在巴士上好好睡一個晚上。
該地與瓜地馬拉接壤,我就以此為我在墨西哥的最後一個站,下一站往瓜地馬拉。
公車停在查帕斯的一個著名山城叫聖克里斯托巴(San Cristobal de las Casas),一陣清新空氣撲面而來,這使我想起上一次到玻利維亞印加山區的感覺。這裡是查帕斯的旅遊勝地,到處可見小客棧與餐廳,還有嬉皮風格的旅客到處流連,附近有馬雅村落和其他原住民部落,從山區到叢林,都可以滿足來獵奇的外國人。
在查帕斯,我就以聖.格斯度波爾為基地。美麗而優閒的小鎮以前曾發生過政府軍與游擊隊激烈衝突,其中的恩恩怨怨,該從哪裡說起?這裡的居民都會搶著與你細說從頭。
一九一○年革命後,政府承諾從大地主和教會手中取回土地給農民,結果未有實現,一直到六、七十年代,長期執政的建制革命黨誘騙薩柏斯農民,讓出部分土地,讓外國財團在該地興建水壩,完工後,居民便可以享受免費電力,結果水壩是建好了,但水電費不僅不是免費,反而比過去更貴,有些地方甚至無電力供應,居民大呼上當。
其實更早之前,資源豐富的查帕斯已是外資垂涎之地,居民用盡各種方式,捍衛自己的土地權益,衝突頻生,這令我想到印尼的亞齊省和伊里安查亞省、柬埔寨的柏寧省,這都是我曾經採訪過的地方。日光之下無新事,來到薩柏斯又是相類似的故事。
所不同者,查帕斯農民以更大的決心,來向西方財團說不,一九九四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落實,激發起薩柏斯原住農民高聲說「受夠了」,薩柏斯解放軍於焉誕生,其領袖馬哥斯立刻吸引世界的注意。
一到達,我馬上聯絡當地的人權組織,他們告訴我,查帕斯會在八月舉行聯邦政府選舉,省長和市長選舉也包括在內,因此聞名於世的墨西哥叢林游擊隊查巴達會暫時處於低調狀態。他們和聯邦政府共同發出紅色警告,政府方面惟恐游擊隊出來破壞選舉,而游擊隊則防範軍方在大選期間向他們採取鎮壓手段。
右派卡德隆勝出後,游擊隊嚴陣以待,很多屬游擊隊的自治村落都對外界異常敏感,如果誤闖禁區,恐怕會遭到很大麻煩,年前他們便扣留了一名美國遊客,擾攘一番後才釋放他。
我沒有受到該名美國遊客的遭遇所嚇倒,再次試圖上山了解情況。
但這回我真是要認輸了,紅色警告牌懸掛著,任我怎樣遊說,也難窺見游擊隊的真貌。我與人權組織聯絡,他們表示,連他們也難上山提供協助,何況是我這名外來人。其中一位在查帕斯已有九年的人權工作者巴西布告訴我,那些激進原住民自治村落,由於過去受到欺壓,對外來人並不信任,如沒有准許證,勢難跨越檢查站,進入他們的家園。
當他們說不,就是不,他們亟需別人的尊重,若有人硬闖,即表示不尊重,他們便會不客氣了。
巴西布看見我一臉失望,表示可詳細講解查帕斯自治區的運作,聊以補償。
他說,自治區算是遺世獨立的一個異數,可算是國中之國,它有著自己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體系,原來一直被剝削教育機會的原住民女孩,在自治區內可以平等上學,參與生產,甚至加入解放軍軍隊,拿起槍來。
自治區裡有幾十個村社,村社按各自優勢種植,豢養禽畜、製造手工藝品,然後以物易物,來滿足大家的基本生活需求。
自一九九四年開始鬥爭以來,他們為實驗這一個理想國而付出多少血與淚,甚至生命?!站在一片翠綠的山區上,卻感到天地蒼茫,風與樹葉磨擦得沙沙作響,如亡者的納喊聲,催促後人繼續上路。
可是,我仍想了解這裡的農民革命。首先,我在山區採訪一個曾經歷屠殺名叫Acteal的村莊,一九九七年和二○○二年該村莊農民曾因捍衛土地起義,一九九七年墨西哥軍方鎮壓當地起義農民,殺死了四十五人,但現在他們渴望能以和平手段抗爭。
奇怪的是,曾在香港大學擺設的羞愧之柱(Pillar of Shame)巨型雕塑,竟然就放置在紀念堂外,旁邊有一幅標語︰土地與尊嚴不能賣!
Acteal村民尚算友善,村長邀請我一同前往村內的教堂憑弔屠殺受害者,村民所有死者的照片懸掛在牆上,整齊排列。我一看之下,竟然全是婦孺及少年人,墨西哥軍方之狠,可見一斑。
村長為我這位遠道而來的記者,特別把村裡的所有重要人物都請了過來,他們輪流將原住農民的鬥爭史重說一遍,並給我一些影印材料,明顯地他們習慣接待記者,知道記者的需要。他們還帶我參觀這一條村舍,探訪了好幾個村民家庭,他們居住在由茅草搭建而成的房子,過著幾乎一無所有的生活。可是,他們表示,擁有屋瓦遮頂的房子已比以前好,過去他們只能當農奴。查巴達運動對他們而言,是一場解放運動,他們比以前更自主了。
現在政府軍在每一個自治村落都設有軍事哨站,還默許大量民兵存在,企圖以此瓦解自治村落的運作。
一位頭帶奶白色大濶邊墨西哥帽、身穿濶身衣袍、身型肥胖的農民經過我身邊,向我微笑打招呼,一小女孩跟上來,背着小弟弟,右手則拖着另外一個小弟,他們眼神充滿好奇。小女孩指向另一方,以土語告訴我什麼似的,還用左手作蒙面狀,然後豎起大姆指。原來她要告訴我,一個查巴達村莊。
離Acteal不遠處有另一個村莊,是查巴達游擊隊勢力範圍,每個村民都會拿起長刀來保衞自己的土地,他們成立革命軍,設置防衞鐵絲網、檢查站,外來人須得到許可證才可進入。
我試圖走近,站在門口的兩名大約十五、六歲原住民守衛兵即目露兇光,眼筋紅紅的,擺了個驅趕姿勢,此時我才認真明白那些勸我聽話的非政府組織,這些組織的工作人員,大多是西方人士,查巴達運動的同情者,他們在這裡一住便五年、七年,甚至十多年,對查巴達運動成員脾性瞭如指掌,例如希拉莉.克萊因(Hilary Klein),她曾在查巴達婦女合作社工作達六年,專門研究婦女在查巴達運動所扮演的角色,她與查巴達成員之間的感情比兄弟姐妹還深厚。
查巴達實在滿足了很多西方人士的浪漫情懷,記者稍有批評,他們即群起為查巴達運動辯護。
在涼風陣陣的山城裡,晚上依然熱鬧非常,我和一些非政府組織成員在酒店的庭園裡圍在一起,手拿義大利薄餅和啤酒,我忍受著濃濃的菸味,聽他們高談闊論,靜待他們洩露風聲的時候。
在查帕斯省,政治遊客絡繹不絕,駐守墨西哥超過二十年的資深記者洛斯(John Ross)便曾撰文批評查帕斯已成為政治旅遊景點,此點我完全同意,當我走進查帕斯每一個角落,永遠擺脫不了那些查巴達游擊蒙面布娃娃,還有相關的紀念品,一如切.格瓦拉被商品化一樣,令人啼笑皆非。
洛斯憂心,西方人士大量消費和無限投射在查巴達運動,而使得運動起變化;他進一步表示,多年以來馬哥斯獨領風騷,這也不是一件好事,其他成員就在他的光芒背後,無法現身出來。
無論如何,查巴達運動已成為反企業全國化的圖騰,同時也是原住農民抗爭的典範。
從薩柏斯一直延伸至瓜地馬拉,都是古老馬雅族原住民的文化之鄉。
我走訪查帕斯省的農民,他們表示,二○○六年的大選中,他們不相信任何候選人,連奧布拉多也不相信,因為在他的競選政綱中,只不斷強調窮人,卻絕口不提印第安原住農民的獨特苦況,企圖將他們的問題輕易撥入廣義的貧窮問題。
那些原住農民強調人與土地的自然關係與權利,可是墨西哥政府要熱情擁抱全球化和自由經濟,連農民土地也推到市場自由買賣,並取消任何津貼政策,令他們更缺乏資源和技術改善耕種,遂無以為計,走上起義之路。
其實,在發展中國家處於全球化的過程中,農民所面對的挑戰,政府有責任給予照顧,這是歐洲國家遲遲不願放棄農民補貼的原因,因為它隨時會變成棘手的政治問題,這都是中國可汲取的教訓和借鏡。
不過,在拉丁美洲,其所要應付的不但是農民問題,還有印第安原住民的問題。在墨西哥,原住民雖占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可是,這牽涉的不是一個數目,而是人權。在與墨西哥人有限的接觸中,我發現即使不是原住民,一個普通的墨西哥居民,他們對土地也擁有濃厚的感情,他們經常把美國百多年前吞併墨西哥土地之歷史掛在口邊,對土地感情盡顯露於此。
人類的歷史是一頁土地爭奪與文明毀滅和重建的歷史,查巴達運動則把拉丁美洲原住民運動正式搬上國際舞台,從墨西哥南部到瓜地馬拉,有來自古文明的馬雅人故事,而我的下一站,就是瓜地馬拉。
註釋:
① 高地酋乃是從西班牙語caudillo翻譯而來,泛指拉美在十九世紀獨立後出現的軍人獨裁統治現象。可參考《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作者湯世鑄,知書房出版,一九九六。
②見拉美著名經濟咨詢公司Economatica二○○八年報告,http://www.economatica.com。
③參見In search of an understanding with the United States.(Mexico-US relations)(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一文, Denv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cy電子期刊,二○○一年十二月,作者Juan Rebolledo Gout。
④Mexico’s Other Crisis: Foreign Banks,作者Kent Paterson, CorpWatch, May 15, 2009. 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5356
⑤參見蕭新煌《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出版,一九八五;或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ontentions, Arguments, Alternatives(2rd edition),作者Richard Peet with Elaine Hartwick, 2003, Guilford Press.
⑥二○○六年世界銀行發展報告(World Bank economic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⑦拉美政治學科二○○五年發展報告。
⑧拉美化和中國拉美化之憂:江漢大學學報二○○五年十二月。
⑨參見John W. Sherman, Latin America in Crisis, p.168-170, Westview Press, 2000.
⑩參見〈Teacher Rebellion in Oaxaca〉一文,作者John Gibler, Global Exchange, 21/08/2006.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countries/americas/mexico/dispatches/4162.html
⑪參考吳音寧:《蒙面叢林》,台灣印刻出版,二○○三年。
第三章 薩爾瓦多:揮不掉的依賴主義幽靈
我是溫柔、祥和
一朶的花
可是,柔美不是一幅牆
用以掩飾不幸
我看見不公
反擊與抗爭
來自那些普通的人
在我颤慄的眼睛前爆發。
取代荒謬的憐憫
偽善的同情
我的憤怒一湧而出
我與兄弟姊妹聯成一線
每一反擊讓我傷痛
每一吶喊讓我觸動
不在那腦袋或耳朶
而在於心坎裡。
我潔白的温柔倒下了
倒在饑餓者腳下
我明白自己在頭巾裡飲泣
一件新衣裳掛在血肉上
我在春天的掙扎中揮動著手臂
熱血在抗爭
我身軀橄欖的綠
以及燃燒的熱情在撩動我
……還有無論怎樣
我繼續如以往般感到
和平愛好者
我欲為它鬥爭──瘋狂地
因為從一開始
我已夢想著和平。
──薩爾瓦多游擊隊詩人拉米瑞茲(Lil Milagro Ramirez, 1946-1979)①
好不奢侈,享受著一種特權,就這樣在瓜地馬拉我登上了這部豪華長途公車「帝王品質」(King Quality)。公車緩緩駛向東南面,往薩爾瓦多方向行走。
沿路上,窗外景致大都是破落的農村,有點灰茫茫,揮之不去。偶有出現大幅宣傳路牌,豎在路旁,指這個區已被徵用發展計畫俱樂部、遊樂場,又或私人屋苑等等,有不少名堂。
發展令下,居民仍是我行我素,在東歪西斜的茅屋前繼續進行小買賣,腐爛的水果上有蒼蠅嗡嗡作響,還有那些刨冰,顏色紅得發紫。芭蕉樹下的赤腳小孩遠見「帝王品質」經過,高興地趨前揮手,然後衝呀衝,企圖衝出命運的迷霧。
「帝王品質」漸漸離開了瓜地馬拉,而我也在不斷的搖晃裡進入夢鄉。我的夢鄉,他們的夢鄉,報時鳥一再出現,嘰咕地大叫了一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們仍須努力!
我嚇了一跳,瞪大眼晴,瓜地馬拉邊境官員上來檢查護照,跟著是薩爾瓦多的邊境官員,過程簡單。
原來兩國只相差五個小時的車程,我真不願意離開這部「帝王品質」,深知一下車我又要艱苦作戰了。
人人都說薩爾瓦多治安奇差,首都聖薩爾瓦多更是中美洲的罪惡之城,但我心想,在拉美這個地區,哪一個城市是安全的?
薩爾瓦多,多美麗的名字,其原本意思在西班牙語裡即救贖,這反映了多少人的心聲,救世主在哪裡?救贖在哪裡?這也確實幽了這個地方一默。
這種反諷也出現在她極不尋常、極不對稱的歷史裡,一個面積才二萬多平方公里的小國,卻曾是引人矚目的世界焦點,大家不會忘記八十年代的薩爾瓦多,在美國的控制下扮演了美國後院中的後院,這個深深藏於中美洲的後院與瓜地馬拉不遑多讓,一樣經歷了殘暴的軍人獨裁和漫長痛苦的內戰。
這一度是「後院」的裂痕,從墨西哥開始裂開,愈裂愈寬,把當地人民的靈魂也撕開了,一直延伸至南美洲,一發不可收拾。
我就是在這一個風暴眼?想到此,我一下車即衝入另一部出租車,趕快往旅館去。
美元化與私有化潛藏無數災難
晚上八時多,整個城市處於一片漆黑中。奇怪的是,出租車卻異常簇新,空調的車箱裡有一陣陣玫瑰花幽香,司機穿著整齊的白恤衫,專業地詢問客人要往哪裡去。
我想到墨西哥城的綠色甲蟲車,有人指那是賊車,曾發生過乘客給搶劫強暴,而瓜地馬拉城的出租車司機,則愛漫天殺價。
但,薩爾瓦多那部出租車司機按公價收費,他們的專業外表也可讓乘客不至太過驚恐,坐在車裡,有時會懷疑這裡真的是薩爾瓦多嗎?沒想到,出租車收費驚人,五分鐘路程便要八美元,不僅出租車,電話費也令人咋舌。我在旅館打一通本地電話便要一美元三分鐘。
在薩爾瓦多,國家貨幣單位就是美元,都說是美國後院了,做個美元附屬區,又何妨?
後來認識一位薩爾瓦多經濟學者艾伯圖,談到薩國在二○○一年實施美元化政策,原來背後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原因。
當時總統佛洛瑞斯(Francisco Flores)指美元化可降低利率,控制通膨,加強投資者的信心,可是,這都是表面原因,他其實是唯恐左派有機會上台,改變既有的經濟政策,因此,佛洛瑞斯先下手為強,美元化令左派更難推翻目前這一套新自由經濟政策,因為它的確是一個炸彈,不小心錯碰某一條線便會爆炸②。
我走進餐廳,跑到市集,既使在街角的小雜貨店舖買份報紙和小吃,都感到物價不菲,一如我第一天抵達即受盡高價出租車與電話費。在我抱怨前,當地人已先向我抱怨,美元化不僅沒有改善通膨,反之令物價上漲了百分之百,我一聽便感咋舌,不知當初佛洛瑞斯邏輯何在?
艾伯圖說,美元化政策不是沒有好處,但好處只對富人而言,對老百姓來說,這真是一場災難。
當我投訴出租車車費昂貴時,司機即皺眉頭表示,這是美元化的錯,自美元化政策推出後,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人們無法負擔車資,這裡的觀光遊客幾乎是零,他每天望天打卦。
我在餐廳與侍應生閒聊時,他告訴我:「原本國家的貨幣叫哥倫尼(colon:一美元對八.七五哥幣),以前我拿著二十個哥倫尼便可應付每月基本飲食所需,現在五十美元也不夠,我們的薪金卻沒有隨著美元化而上升。」
在網咖,我又與一名年輕的職員聊天。他找不到全職工作,他下午在網咖兼職,早上又有另一份兼職,兩份才合共八十美元一個月,跟著他列出了一盤數,他與哥哥合租一所公寓,每人三十美元,上網月費每人二十五美元,水電費十美元,餘下的十五美元,連一天三餐也不夠,但他還有女朋友,拍拖時不敢上館子,在路邊買兩份冰淇淋吃了了事。
「上網月費這麽貴?」我問。小夥子無奈聳聳肩,說:「電訊業私有化後,卻向某一財團靠攏,出現壟斷,電訊包括電話變成是老百姓的奢侈品。可是,我們年輕人卻不能不上網呢。」
這與墨西哥的情況不也一樣嗎?小夥子神神秘秘拿出他一個珍藏的哥倫尼硬幣給我看,上面刻有哥倫布的畫像,他發出輕蔑的笑聲,說:「哥倫尼這個名稱乃是由哥倫布而來的,我想,在拉美地區,就只有我們公然以國家貨幣來紀念他。現在哥倫布不重要了,換來林肯、華盛頓。」他一再展露輕蔑的表情,把硬幣一拋,放回袋中。
小夥子二十歲,一九九二年內戰完結時,他才幾歲,屬薩國新生一代,家境貧窮,內戰結束以來,低下層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失業率高,他認為自己能夠找到兩份兼職,算是不錯。
說到前景,他竟用哲學的口吻反問我:「連國家也沒有身份,你認為我這一個小市民還可以做什麼?」他一臉憤世嫉俗,新生一代似乎也逃脫不了上一代的怨恨。
非政府組織「全國發展基金會」主任魯必奧(Roberto Rubio)指美元化開始時的確降低了銀行利率,有助購置房地產和貸款,但利率很快又升回美元化以前的水平。
不少專家發現,薩國的金融機構任意妄為,即使利率降低,那些發信用咭機構亦可以收取利率百分之三十至五十,而那些銀行更可惡,複雜的服務費使借貸成本一樣昂貴,對中小企業非常不利。
「熟知內情的人都知道,美元化只對外資有利,政府與本地的大財團樂於與外資勾結。」我新相識的一位藝術家班卡(Blanca)憤憤不平說。
事實上,右翼政黨「國家共和聯盟」(Nationalist Republic Alliance, ARENA)於二○○九年中下台前仍堅決捍衛美元化,當年他們推出此一政策時,已言明這是自一九九二年內戰以來一項自由市場政策的延伸。
在一次記者會中,當時薩國的ARENA官員就無條件簽署中美洲自由協定(CAFTA,見附錄三)作辯解時,也一併把他們認為美元化的正面效果,神態英明地一一列出。
「薩爾瓦多的經濟繼續得益於自由市場的承諾,以及謹慎的財政管理,自一九九二年和平協議履行後,經濟以穩定和溫和步伐成長,貧窮從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六十六,銳減至二○○六年百分之三十點七,經濟的改善歸功於銀行,電網、公積金、電力等全面私有化,還有遞減入口稅,取消商品價格控制,加強版權的執行等等,使得薩爾瓦多再度成為吸引外資的地方。美元化進一步把薩國溶入全球經營體系裡,我們將會從全球化中獲益。」③
是真還是假?
我跑到首都的西北部,一個遠離市中心的地區,發現竟然有如此巨大的差別。如果市中心是地獄,那該區就是天堂。所有大使館、工商、金融機構幾乎全部集中在這裡,一片井井有條,祥和、現代化,還有快餐店雲集的一條街,大部分是美資開設的Friday、Harvey、Burger King,擁有一種如洛杉磯某一個小鎮的風情。這個小鎮沒有過去的傷痕,也沒有歷史的記憶,這樣,那些緊握政經大權的決策者,才可以大膽向全球化邁進。
陪伴我的經濟學家艾伯圖說,過去靠咖啡、糖大發利市的白人莊園主,現在已走入了這個商業核心地帶,運籌帷幄。
網咖小夥子那個哥倫尼硬幣又在我面前出現,它被拋到半空中,然後消失。
被視為地獄的市中心,不時出現一大群示威者,他們抗議公營醫院私有化、國立大學私有化④。
薩爾瓦多國立大學便曾在二○○六年發生過一場抵抗私有化和爭取自主權的學生運動,學生與軍警衝突,有人遭到槍斃,跟著校園氣氛緊張,但慢慢又平靜下來。
平靜中有一股暗流。當我探訪該校的學生會時,他們正準備下一波的行動。
學生會領袖是一名三年級新聞系學生海森堡,他與我談到美國急於在中美洲推行「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下一步政府便會計畫將大學私有化,到時平民百姓子弟更難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
海森堡說,政府有責任推廣教育,不能把所有大學私有化。但,薩爾瓦多領導人肚滿腸肥,政府卻經常以沒有資源為由,使得國立大學一窮二白,有學生連書籍費也沒有能力支付。
在薩國流行一些順口溜,其中便有這句︰「我們的領導人上台時兩袖清風,下台時已成億萬富翁。」
至於薩國人口,有三成文盲,過半生活在貧窮線下。這都是與薩國官方數字不同的聯合國統計。文盲與貧窮使薩國的公民社會發展不起來。海森堡告訴我,在大學,電腦竟然是罕有的學習工具,更遑論有機會上網。我表示驚訝,對於我們是理所當然之事,在這裡卻是如此困難。
那些學生領袖大多奉古巴的卡斯楚為革命偶像。在薩爾瓦多國立大學校園裡,到處都可看到卡斯楚的肖像和古巴國旗,這真使我為之側目。此外,八○年遭受暗殺的薩國解放神學代表人物羅梅羅大主教(Monsignor Oscar Romero)⑤,當然還有切.格瓦拉,對學生而言,這是他們的三大偶像。三大偶像的海報不但懸掛在校園的露天地方,並且在課室裡飄揚著。
當西方傳媒甚至亞洲等地,都視卡斯楚為反面人物,但在中美洲,大家對他的評價卻較為複雜。有趣的是,當中以年輕人與老革命家對卡斯楚推崇備至,這可能是一種抗議美國的方式吧。不過,富人對這位當今世上仍在世的第一代現代革命家,則是負面多於正面。
可是,對仍懷有理想的年輕人與經歷過戰爭的長者來說,他們正面對自己社會的各種問題,從毒品到文盲、暴力、惡劣治安等等,心裡自然仰望加勒比海彼岸的古巴,那裡沒有毒品、文盲、暴力,並且擁有良好的教育和醫療,他們經常這樣羨慕古巴和讚賞卡斯楚。當然,他們都是從某一個距離看。
第二天,海森堡即有所行動,他與其他同學去支援一個組織的訴求,這組織叫「薩爾瓦多農村發展委員會」,他們抗議政府企圖私有化飲用水供應。南美洲玻利維亞便曾就這個議題爆發過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最後成功阻止政府連飲用水也出售給財團⑥。
從私有化飲用水供應到私有化大學,海森堡認為學生與普羅大眾都面對相同的命運,因此,他們一定要站在一起。
自CAFTA於二○○六年正式實施以來,薩國社會內部開始蘊釀變化。
海森堡不知從哪裡弄來一輛殘舊的汽車,他邀請我同往,還有好幾位同學,擠在原本已經不甚寬躺的車廂內。
這部車真的很殘舊,路不崎嶇,它卻走得隆隆作響。我們經過一條大河。海森堡請我留意一下水質,說:「水,在薩爾瓦多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這裡的污染令我們難以忍受。現在只有一半人口有能力負擔潔淨的飲用水,而水源都已受到水銀和重金屬的污染,其主要元兇是企業肆無忌憚地生產,政府又沒有好好處理廢料,貧窮人口又缺乏環保意識等等。」
此時,我看見一群男女老幼在河邊的垃圾堆裡拾荒,有一小孩找到幾塊切開的爛西瓜,便立刻往口裡塞。
海森堡嘆息說:「污染的飲用水,令勞動人口健康下降,結果不也是影響本國經濟嗎!政府不去用心改善,反而企圖把飲用水私有化算了。可是,水是屬於人民的資源,生活的必需品,怎可變成商品讓財團壟斷?!難道人民負擔不了市場的價格,他們便不能享受飲用水?」
CAFTA把薩國不同的領域逐步私有化,政府從傷痕累累的國家抽身,新自由經濟政策隨著CAFTA走上高潮。
極力推銷CAFTA的美國前任總統布希在電視畫面上向美國人民說,美國是為了確立中美洲的自由民主,才與他們簽下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這是一項有利於中美洲戰後重建民主的貿易協議書。
薩國人民摸不著頭腦。
前車可鑑,一九八○年代的內戰是怎樣來的?
左右勢力對壘,政變頻生
薩爾瓦多在一八二一年從西班牙人手中取得獨立前,由十四個歐洲白人精英家族控制全國經濟,獨立後這些家族繼續掌握政經大權,排斥薩國原住民。原住民領袖阿基勞(Anastasio Aquino)起來反抗,雖功敗垂成,卻不失薩國人民愛戴,被奉為民族英雄。
一八四一年中美洲聯邦解體,薩爾瓦多自始擁有自己的主權、憲法。
與其他拉美國家的殖民經濟模式一樣,以集中一至二種產品或原物料出口為主。從十九至二十世紀初,薩爾瓦多的咖啡種植成為國家財富來源,而這財富則由上述家族掌控,他們占全國人口才百分之二。
在這樣一個財富高度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的社會,老百姓經歷極端貧苦受壓的環境,他們渴望公義、人道、共享的情緒日漸高漲。到了一九三二年一場起義行動終於爆發了,領導人就是中美洲社會主義黨創辦者奥斯汀.馬蒂(Augstin Farabundo Marti),後來內戰時與親美獨裁政權對抗的革命組織馬蒂民族解放陣線(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MLN)為了紀念他,便以他姓氏作為黨名的開頭。
每次的起義,軍方都用最殘忍的手段回應,而在每一場的屠殺,原住民更是首當其衝。這不僅是薩爾瓦多,還有墨西哥、瓜地馬拉和其他拉美國家,他們擁有著共同的故事,當中的軍人政權和美國,被當地人視為互相勾結的劊子手。
電視畫面再次出現美國總統,但不是布希,時光倒流回到一九七七年,人稱之為人權總統的卡特(Jimmy Carter),一樣表示要協助推動薩爾瓦多的民主,但他暗地裡所支持的,卻是薩國當時的羅梅洛(Carlos Humberto Romero)軍事獨裁政府,美國向其輸出的軍事援助源源不絕。
羅梅洛一上台不久,即大開殺戒,一年多之內便有七千人遇害,直至一九八○年有四名美籍修女在進行救援任務時遭強姦謀殺,卡特才暫停對獨裁政府的軍援。
不過,當一九八一年美國另一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上任後,便很快恢復對羅梅洛的軍援,而且增加至一九八五年的五億美元之多,以瓦解人民發起的左翼游擊活動。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冷戰的高峰時期,也是中美洲獨立後的革命高峰期,如一串鞭炮霹靂啪啦在中美洲燃燒,就像躺在中美洲的火山帶互為影響。
尼加拉瓜一九七九年革命成功,鼓舞了仍處於水深火熱的鄰國人民,當時薩爾瓦多左右勢力對壘,國家在極度分裂狀態中,導致政變頻生。各派游擊隊聯合力量,FMLN由此誕生。
無論是卡特或是雷根,他們不惜一切介入薩國軍事政變行動,又軍援右翼政權,並協助組織了當時令人聞風喪膽的死亡隊(death squads)。這一支專門從事暗殺、綁架和虐待的民兵隊,猶如幽靈使者到處流竄,不少革命人士遭到殘殺,連平民百姓也不能倖免,戰爭中遇害的共有七萬五千人,六千人失蹤,這種死亡文化就此在薩國生根。
人命,輕於鴻毛!
一九八○年,深受人民愛戴的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遭到刺殺,誘發了內戰,而美國替ARENA極右政權撐腰,令內戰無法停下來,一直至一九九二年才結束。
在這個時候,雷根又在電視畫面上出現,他正襟危坐,向國民解釋軍事介入薩國的原因,他說:「薩爾瓦多比華盛頓離德克薩斯州更近!」
我入住的旅館:國際旅館(International house),老闆泰亞素.肯那尼斯(Tirso Canales)便曾在內戰時參與過游擊活動,之前為記者、評論員,他同時也是一名詩人。
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家,個子不高,鼻樑上頂著一付厚厚的眼鏡,他喜歡每天早晨在旅館偏廳一角看書、閱報,然後伏案執筆,評論時事。
陽光想抓住他也住不住,他的角落太隱閉了。或者,他不希望客人騷擾他,可是,我卻經常向他問這個問那個,特別是他的往事。
他給我看一份西班牙報紙,有一版是該報記者對他的訪問,我豎起拇指,果然來頭不小,泰亞素微笑一下,說:「我早在六十年代已採訪過古巴革命,與卡斯楚和切.格瓦拉見過面。」
他得意地拿出他和上述兩位古巴領導人的合照,還有革命家的海報,和他的革命詩集,問我買不買?我怔了一怔,他有點尷尬,為什麼我不爽快答應?好讓他快快轉個話題。
我明白,在薩爾瓦多,生活不易,有不少人靠海外親友的匯款接濟。事實上,僑匯乃為薩國的經濟支柱之一,約占GDP的百分之十七。內戰時期,大量難民湧到鄰國和美國,跟著也有不少移居到海外。現時估計共有二百九十萬僑民在外,百分之九十七居於美國。
當日落西山,泰亞素便第一時間把旅館大門的大閘拉下,而旅館對面的小雜貨店更是二十四小時重門深鎖,四周圍有鐵柵,貨品從鐵柵之間傳送到客人手上。
與瓜地馬拉一樣,薩國飽受內戰後遺症,社會失序,人命得不到尊重,土匪毒販橫行,治安問題永遠是中美洲國家的主要議題。
在友人介紹下認識一名美國記者,他正在聖薩爾瓦多拍攝有關街頭罪犯如何衝擊薩國的經濟成長,而他竟然真的訪問了兩個主要派系的頭頭。原來,在薩爾瓦多,嚴重影響街頭治安的兩派為MS13街和MS16街,名稱很怪吧!
MS13街成員主要為當年內戰時逃亡到洛杉磯者,在洛杉磯生活無計,遂與當地罪犯連群結黨;內戰結束後由美國遣返回薩爾瓦多,但仍與洛杉磯的犯罪集團有聯絡,在自己國家幹起勾當來。
至於 MS16街派系,他們大多是前哥倫比亞的步兵,主要從事販毒工作。薩爾瓦多乃是哥倫比亞向美國販賣毒品的中繼站,然後經墨西哥轉到美國去。這條從南美洲經中美洲到美國的販毒路線,就好像一條黑暗隧道,令中美洲成為一個異常暴力的地區。
泰亞素告訴我,戰後游擊隊員如何重回正常生活,也是一個大問題。他便僱請了不少前游擊隊成員在旅館工作。內戰結束後,前游擊隊成員願意放下武器者,有些加入已轉型為政黨的FMLN,參與主流政治;有些則做起生意來,包括經營貿易、旅館、餐廳等。
我問泰亞素,搞革命與做生意有什麼不同?他大笑說︰「在薩爾瓦多,做生意比搞革命更困難。但我們這種人,是沒有人僱請的,幸好家族留下這棟房子,我把它轉為旅館維生,生活總算過得去。要知道,薩爾瓦多貧富極為懸殊,親美大商家控制了國家百分之八十的財富,而一九八九年戰後掌政二十年的ARENA,是典型的美國附庸。」
在旅館碰上一群美國傳教士,我們和泰亞素一起坐在旅館裡憂心忡忡地看著電視新聞報導中東地區衝突的消息,詩人不覺得遙遠,他一針見血指出,一切都是擴張主義所引起。他告訴我,小小的薩爾瓦多過去亦曾企圖入侵鄰國宏都拉斯,入侵當然要找藉口,和以色列占領巴勒斯坦一樣,歸根究柢都是因為要擴張領土,要在地區操控制大權。
以色列在前線打,美國則在後面指揮、支援,以色列是美國在中東的忠實盟友,同時也是代理人,當然以國也有自己的議程。詩人慨嘆日光之下無新事,七、八十年代的中美洲,美國介入之深,與現在介入中東無異。
其實,阿拉伯裔與拉丁裔沒有什麼分別。我們可能有一種印象——阿拉伯人是很重的,拉丁裔是很輕的。前者愛擁抱民族的歷史包袱,把自己拖得很重、很重;後者則容易笑著忘記於輕快的舞姿與音樂裡,拿起一瓶香檳,就什麼都可以忘記。一個沉思於過去,另一個活在今天,他們用不同的方式來面對同一種痛苦?
從阿拉伯半島沙漠到美洲中部,想想,有多少國家,黎巴嫩、伊拉克,又或薩爾瓦多、尼加拉瓜,他們有什麼不同?一閉上眼睛,記憶可能會轉到八十年代,同樣的烽煙四起,人們流離失所,他們竟然分享同一歷史,同一命運。
一位阿拉伯人,在沙漠公路上某一雜貨店門前,頭纏著黑白方格圖案的頭巾,吸著阿拉伯水菸,他在默默打量著我——這個來自東方的女子,如何解讀他們的歷史創傷?
在車水馬龍的薩爾瓦多首都聖薩爾瓦多,總有幽暗的角落,罪犯在窺探路過的獵物,他們對政治已失去了興趣,眼中只有錢!錢!錢!
阿拉伯半島上硝煙仍在,中美洲內戰卻已成過去,兩地人民手中卻同樣繼續拿著槍。薩爾瓦多有人不諱言他們家藏有槍枝,以應付戰後失序的環境;我在巴格達僱請的翻譯穆罕默德,他家一樣有槍械,他說他們身處的環境無法無天。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世界弄得如此地步?中美洲,一個完全超乎我們想像的暴力世界!
薩爾瓦多內戰持續,也實在拜美國支持軍人政府所賜。
美國在中美洲設立臭名遠播的「美洲學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根據「美洲學校監察」組織(School of the Americas Watch)資料庫顯示,這所美國軍事訓練學校在拉美地區共訓練出超過六萬名成員,專門用各種殘暴手段對付右翼政權眼中的革命分子和異議人士,有「死亡隊」之稱。
一九九六年,《華盛頓郵報》揭露該校一份具爭議的培訓手冊,當中鼓吹對抗爭者施用行刑、暗殺、恐嚇、虐待及其他違反人權的手段,有人更指責該校導師與中美洲軍人獨裁政權侵犯人權事件有直接關係。
美國國會議員約翰.甘迺迪便曾這樣說:「美洲學校是一所有史以來訓練最多獨裁者的軍事學校!」
現在,整個中美洲民間社會都要求撤走「美洲學校」。
談到「美洲學校」,泰亞素搖頭說,這是美國侵害中美洲國家主權的舉動,直到現在,中美洲國家仍未能擺脫這只幽靈。美國過去製造了多少獨裁軍人?七、八十年代,薩爾瓦多軍人政府欺壓人民,人民反彈,組織游擊隊,成立解放陣線FMLN,當年他們漸漸取得勝利之際,雷根上場,以大量金錢和軍力支援右翼政權,令內戰停不了,人民苦不堪言。
詩人未忘由美國訓練的精銳部隊Atlacatl Battalion⑦如何屠殺山區村民,聽得我也戚戚然。在旅館廚房工作的一名婦人歌莉,原來就是其中一名受害者,她家鄉在薩爾瓦多東部山區El Mozote,家人遇害後,她毅然拿起長槍加入游擊隊陣營。
她向我提起當年事,眼眶仍忍不住紅起來,突然她除下身上紅色的圍裙,當作游擊隊的旗幟,搖旗吶喊起來,雙手變成機關槍,不斷砰砰砰,重演當年往事。
泰亞素在我耳邊低聲說︰「她的兒子剛出生才幾個月,也在該次屠殺中遇害,從此她沒有再婚,生孩子。」
我決意探訪El Mozote。
「草寇」原來也是藝術家
沒幾天,我離開了聖薩爾瓦多,跳上一部長途公車,先往東邊的San Miguel,然後再轉車到El Mozote。
下午到達San Miguel,公車已陸續停駛。該地環境破落,有蕭條感覺,猶如一個遭遺棄了的工業小鎮,路上的人都是行單影隻,不時詭異地望我一眼,我加速步伐,衝入一家歌莉介紹的旅館。
第二天上山區,首先前往Perguin,這是FMLN在內戰打游擊的基地,然後再去El Mozote。
前一段路坐公車,在顛沛的山路上再中途轉換當地的小型貨車,一上車便坐在一名農夫身旁,他戴著一頂奶白色的闊邊草帽,黑黝皺摺的臉孔向我綻開慈祥的笑容,我禮貌地也回了個微笑,然後不經意四處張望,赫然發現他腰纏一把鋒利的大關刀,這突然令我有點忐忑不安。
其後有不少類似打扮的農夫上車,人人一把大關刀,他們站在我面前,刀,也跟著在我面前搖晃著,刀光劍影,我坐得戰戰兢兢。
一旁的美國旅客取笑我,認為我少見多怪、小題大做,人家是農夫,刀用來耕作,也用來對付土匪,要知道,山區農村偏遠,警察不到,加上多年內戰,農民習慣帶刀自保,更何況刀有其耕作的實際作用,這已漸漸融入他們的生活文化當中。
到達目的地,傷痕累累的村落,環望四周,青山依舊,但對當地居民而言,卻有不少人臉已改。
Preguin和El Mozote都很相像,一排排頗為整潔別緻的混凝土房屋靜靜坐落在山邊,享受著陽光的擁抱。這景致倒讓我有點驚訝,我還以為會像墨西哥查巴達貧窮的山區,很明顯這裡有不少重建的建築物。
學校、教堂、社區會堂,還有一個小廣場,人們悠閒地躺著、坐著、聽著教堂的鐘聲,和學校傳出學童們的嬉戲聲。此情此景,如果不是有個悼念戰爭亡者的博物館,我怎樣也聯想不到當年的大屠殺。
曾活躍一時的解放神學追隨者當中,還有一小批神職人員留守在這些山區村社,繼續主持他們的人民教會。
我在El Mozote碰上美國過來的修女Annie Griffin,她如以往一樣,為薩國人權奔波,她說︰「最重要的還是教曉村民從戰爭中再次站起來,活出希望。」
淳樸的村民努力重整人生的秩序。我在Preguin遇到一名當地旅遊局辦事處的導遊艾迪,原來他在八十年代曾參加過轟轟烈烈的游擊戰。他領著我到附件一個小廣場,也是該地的地標,他自豪地告訴我,游擊隊成員就在這個廣場上號召愛國人士,力抗殘暴的軍事政權。艾迪說︰「那些獨裁者都是親美傀儡,他們殺害同胞,傷害國家利益。」⑧
艾迪在Preguin出生,參加游擊活動時才十七歲,他以詩人自居,從小就愛寫詩,他說︰「都是愛國詩,我把詩作配以音樂,當不需作戰時,我和同志們在廣場上又彈吉他又唱歌,吸引不少村民加入我們的游擊隊伍中,有很多詩人和音樂家呢!」
對我而言,這真是不可思議。他們被當時政府傳媒形容為山上「草寇」,但「草寇」卻原來也是藝術家,藝術家拿起武器打游擊,成為一種鮮為外人留意的特色。
戰後,艾迪面對生活問題,唯有當起導遊來,反正Preguin及El Mozote都已變成旅遊景點,遊人前來憑弔,又或作特殊觀光,由前游擊隊成員帶領別有一番風景。
為了增加收入,艾迪把過去游擊隊歌曲集結成CD,十美元一張,我買了三張捧場,艾迪高興之餘,拿出吉他坐在廣場為我彈奏澎湃的歌曲。
「抹去過往的哀傷,唱出今天的希望,起來,起來!薩爾瓦多受壓迫的人民,一起打造我們的明天。」
薩國人民終於有選票趕走執政達二十年之久的國家共和聯盟,這個被視為親美的右翼政黨,其創辦人道布依桑(Roberto d’Aubuisson)在內戰期間與美國合力炮製死亡隊,造成數以萬計受害者,主要為平民百姓。
即使以平民總統姿態在二○○四年出現的薩卡(Antonio Saca),承諾改善貧富差距及關注低下層議題,最後還是未有成功,並且在CAFTA立場上與普羅大眾意見相左,最後更跟隨美國定出反恐法,藉機打壓群眾運動,結果在二○○九年的總統大選中,敗給革命黨FMLN候選人富內斯(Mauricio Funes),為薩爾瓦多頑固的政治生態帶來重大的政策突破。
FMLN能夠突圍而出,有不少分析家都稱奇。
在競選期間,ARENA啟動抹黑機制,而薩國親美媒體也樂於配合,指富內斯所代表的FMLN是一個犯罪集團,又散播美國不支持富內斯等資訊,企圖擾亂人心。
薩國這次的大選,乃是美國第一位黑人總統歐巴馬上任後第一次拉美選舉,亦是測試歐巴馬對拉美的政策,會否如他競選時的口號:轉變!
富內斯也是以「轉變」為他的競選口號。人心思變,拉出美洲一片新天空。可是,薩爾瓦多可謂是積勞成疾,雖不至於病入膏肓,但一籮籮的難題,足以成為富內斯的巨大挑戰,特別是經濟問題,薩爾瓦多依賴美國之深,令富內斯勝出後即不得不公開表示,他渴望與美國繼續維持友好合作關係。
我回到國際旅館,老闆泰亞素是悲觀主義者,一直認為革命不可能再出現,而薩爾瓦多的革命土壤亦早已消失,人民為生活奔波發愁,加上近年活躍的新教福音派,如鴉片般令人失去反抗的能力。總之,泰亞素可以數出不少「革命不再來」的原因。
但,年輕一代不屈服,就好像海森堡,還有艾迪的革命之歌,高唱:轉變!轉變!
革命,在薩爾瓦多,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拿著艾迪售賣給我的CD,繼續拉美的旅程。
註釋:
①(此詩作為本書作者自譯)薩爾瓦多上世紀七十年代內戰期間,有不少作家詩人參與游擊隊,對抗殘暴右翼政權和美國干預,他們用詩來激勵士氣,遂孕育出與別不同的游擊隊詩作。
②參見ECONOMY-EL SALVADOR: Dollarisation Backfires, Fuelling Price Hikes,作者Raúl Gutiérrez, IPS, 5, Feb, 2008. http://ipsnews.net/news.asp?idnews=41071
③參見El Salvador’s CAFTA Imperative, Business Week, 20, June, 2005.
④有關中美洲私有化計畫,其中包括教育,可參考世界銀行報告。www.worldbank.org
⑤從瓜地馬拉、薩爾瓦多,一直到尼加拉瓜等中美洲國家,乃是解放神學活躍地區,單在薩爾瓦多,便有兩位拉丁美洲解放神學最重要的神父,除了已故大主教羅梅羅(O. Romero)外,還有仍在世的索布里諾(Jon Sobrino)。
⑥有關薩爾瓦多對用水私有化的抗爭,有一個美國民間組織Project Censored有詳細紀錄。http://www.projectcensored.org/top-stories/articles/11-el-salvadors-water-privatization-and-the-global-war-on-terror/
⑦Atlacatl Battalion乃是由美洲學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訓練出來的。美洲學校由美國軍事部門成立,中美洲的基地在巴拿馬。Atlacatl Battalion第一隊在巴拿馬受訓成功後,即於一九八一年返回薩爾瓦多,參與多場殘忍的反革命屠殺行動,而他們行動的背後有美軍駐薩爾瓦多特種部隊支援。Atlacatl Battalion於一九九二年根據新簽署的和平協議解散。
⑧有關 El Mozote的屠殺內情,可參考Human Remains-Exhumation process-Forensic medicine-2001-Firearms Identification in Support of Identifying a Mass Execution at El Mozote, El Salvador(Historical Archaeology,作者Douglas Scott)。該報告有詳盡紀錄。此外,美國在薩爾瓦多的不名譽干涉,引起美國國內民間組識聲援薩國人民,其中最龐大的是Committe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 of El Salvador(www.cispes.org)。
PART I→美國後院的前沿地第一章 墨西哥:全球化下的拉美化從何處而來,往何處去,都不是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行動,前進,永遠前進,永遠不要停止,到山谷、到平原、到峻嶺,到任何能夠走到的地方去當主人。──墨西哥革命代表小說家阿蘇耶拉(Mariano Azuela, 1873-1952)阿蘇耶拉寫下不少有關一九一○年墨西哥革命的重要作品。而他所身處的時代,正是墨西哥體現「高地酋」(caudillo)①獨裁軍人高壓統治最嚴峻的時代,當時的廸亞斯將軍(José de la Cruz Porfirio Díaz Mori)逐步以「貴族政治」取代前任遺...
 41收藏
41收藏

 25二手徵求有驚喜
25二手徵求有驚喜




 41收藏
41收藏

 25二手徵求有驚喜
25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