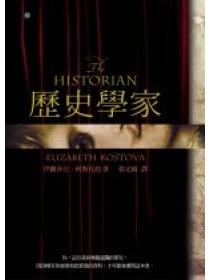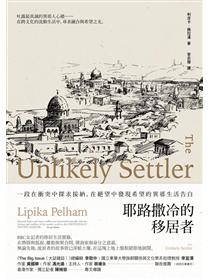聲音,到底是實體,還是想像與回憶?
侯孝賢、王家衛、蔡明亮、魏德聖 推薦
榮獲七座金馬獎最佳錄音獎、第五十四屆坎城影展高等技術大獎、國家文藝獎、法國南特影展舉辦杜篤之個人回顧展……他是台灣電影史上獨一無二的名字——杜篤之。
本書詳述他數十年來的電影歷程,包括早期中影時期的工作經驗,其後多次與楊德昌、王家衛、侯孝賢、蔡明亮等國際知名大導合作,再與二十一世紀台灣電影新世代導演如魏德聖等人的相互激盪。由土法煉鋼而終至與世界接軌,經由錄音技術的演進,見證電影大師們的一代風範。
好的電影令人永難忘懷,走過三十多年的電影路,杜篤之就是一部台灣新電影的活歷史。
作者簡介:
張靚蓓
知名影評人、傳記作者。曾著有《十年一覺電影夢—李安》、《不見不散—蔡明亮與李康生》、《電影靈魂深度的溝通者——廖慶松》等書,譯有《再見楚浮》、《埃及與古代近東,大都會美術館全集1》等書。
章節試閱
第三章 楊德昌與杜篤之
「楊德昌的電影是每個地方都精準的控制住(under control),然後再來演,看似真的,其實都是控制住的。」認識楊德昌二十七年的杜篤之,對楊導知之甚深,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到《獨立時代》、《一一》一路走來,舉凡楊德昌的電影,錄音一定由杜篤之擔綱,就在為臺灣電影的聲音創作屢建新里程碑,就在為電影聲效水準拚出一片天、拚上國際影壇的同時,兩人也結下一輩子的交情。
杜篤之說:「楊德昌是影響我最深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位是侯孝賢導演。」
新舊夾縫中茁壯的幼苗
楊德昌與杜篤之是拍《一九○五年的冬天》時認識的,該片由余為政執導,楊德昌編劇。之前小杜早就聽余為政及余為彥說起過楊德昌,一見面,才發現,「哇,這小子原來這麼高大!」
《一九○五年的冬天》杜篤之首次正式擔任音效師,可以自己作主設計音效,這一趟他是做出來了。小杜對聲音的觀點,新導演亦有同感,新導演知道他喜歡弄些不同的東西,不喜歡用老方法,新導演也想創新,經常私下找他幫忙,小杜很受鼓舞,每天生活都很豐富,做什麼事都很滿足,兩人從《光陰的故事》起開始合作。「我們做了不少新嘗試,那個年代電影都是事後配音,拍《光陰》時,我們捨配音員,啟用非配音員,結果被批評得一無是處,配音員們說︰『你怎麼錄成這副德性?講話咬字不清、國語發音不準……』」全都衝著杜篤之而來。
在錄音的專業領域裡,杜篤之顛覆以往配音觀念之舉,導致他開始頻遭抵制,也開始面對一個新舊交替的陣痛階段;而外在的大環境裡,一番驚天動地的變革也正蓄勢待發。不只電影,還有臺灣。
當時小杜正在中影上班,因此啥事也得做。就在忙新電影、實驗音效新做法的同時,他還為「國民大會」、「世界反共聯盟」等會議錄音。「有次反共聯盟主席谷正綱在台上宣讀大會宣言,當時文稿都是擁護三民主義、推翻共產主義之類的話。老先生眼睛一花,跳行了,脫口而出,我們擁護共產主義!好在台下沒人聽,大家都在夢周公;老外反正也聽不懂;翻譯也沒亦步亦趨的口譯,因為都有稿子,全是照稿翻。我當時就坐在主席台旁邊錄谷正綱的講演,貴賓席上都是來自各國的國會議員,裡面有個法國議員猛盯著我瞧,我發現後也瞪了回去。」
一如他回瞪眼神裡的無畏、好奇,在那個荒謬的年代裡,新機已然萌芽。
《海灘的一天》起追求「聲音擬真」
入行以來,杜篤之不斷學習、鑽研,多年累積,對於音效已有些自己的想法與做法,卻苦無機會實現。此時經由楊德昌一帶,就在「腦力激蕩、多方討論、動手實踐、檢驗成果」四階段的持續磨練下,思緒頓開,新意泉湧而出。在「聲音擬真」的領域裡,他終於可以知行合一,探索「意念」與「執行」的零距離。
杜篤之說:「楊德昌曾經拿塔可夫斯基的(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給我看,他的片子都是事後配音,配得真好,當時心裡就以此為追求對象。」
「他點頭,我就像打了一劑強心針」
那時候每實驗出一個新東西,杜篤之一定請兩位導演過目,一是楊德昌、一是張毅,尤其是楊德昌,「這方面楊德昌帶得滿不錯的,在技術新知上,他影響我很大。我剛開始嘗試新東西時,他就告訴我,這個對,這個很猛、很棒。他那麼嚴格,知道的又多,我又在乎他,他說好,我就很放心;他點頭,我就像打了一劑強心針,繼續努力,再做更多的東西(語氣十分興奮)。有時他會告訴我,這個細節不夠或空間感不像。我便去想,要怎麼做才像?真是攪盡腦汁。」
《海灘的一天》之前,兩人只合作過《光陰的故事》,對於音效的變革,想法還很初步,許多東西尚未成熟。拍攝《海灘》時,楊德昌帶著小杜開始實驗各種新做法,「當時改革的動力十分強勁,每一部的差異都很明顯。譬如《海灘》張艾嘉配音時,我們要求連『吞口水、張嘴、呼吸聲……』等一些細微的動作都要配出聲音來。是從《海灘》開始,我才懂得這麼要求,也因為大家都願意配合;其實這個對演員來說是很困難的,以前配音,演員只要講對白即可,現在她還要多做一些嘴巴的動作,譬如真正去吞咽口水……那時候只要效果可以更好、聽起來更真實,大家都樂於嘗試,包括張艾嘉也願意做。而且我們一看,這個效果還真是好。」
片中張艾嘉的家是棟日式房屋,許多室內戲都是踩在地板上演出。以前要做日式地板的音效,都是弄塊桌板放在地上,人走在上面做效果。「《海灘》進行後置錄音時,我們找來中影搭景的木工師傅,完全按照日式地板材質,做了一方約五、六坪大小的地板,我們就在上面錄走路、跑步的聲音,連踩在舊地板上咿咿壓壓的聲音都有。這塊地板後來沿用了很久。」
「我們配音都配到銀幕後面去了!」
「《海灘的一天》後製期間,我們還試著加環境音、加雜音等做法,想盡辦法收集各種室內空聲,用入片中;就算沒有聲音,也補個空聲上去。片中我放了許多室內背景噪音(room tone)、空音,這方面我以前做得不很完整,包括《光陰》時,也只是有些想法,做點模擬,但還不夠。當時沒什麼資源,所以我們才會配音配到銀幕後面去。」
「其實從《海灘》一路到《牯嶺街》,我們追求的就是『空間立體』聲效。以前電影都是事後配音,我們儘量模擬空間身歷聲。譬如一個人從遠處走到鏡頭前,我們模擬的不是『聲音的由小而大』,而是使用『空間變化』來讓人覺得『聲音的由遠而近』。因為距離遠時,迴音較大;距離近時,迴音較小。我是運用『直接聲音』與『迴音聲音』的不同比例,錄下聲音變化時的空間感,以此來營造聲音的遠近感。這個法子我以前就知道,熟練之後,再想出更多手法來表現這個效果。」
「因為中影沒有製作回音模擬的『殘響』設備,我就用真實空間去製造。我的經驗是,最佳效果就是『真實的迴音』,『真實的迴音』要怎麼做?我們就在錄音室裡製造。中影的錄音室很大,銀幕是塊白布,直接吊掛在半空中,隔開幕前幕後,幕後是個類似禮堂的舞臺,該處未經吸音處理,那裡的聲音反而很有空間感、迴音很真實。其中嘎嘎角角逐一摸透之後,我知道,在這個角落,迴音比較小;在那個角落,迴音比較大。為了追求聲效的真實空間感,從《海灘的一天》起,我們跑到幕後,一邊反看銀幕畫面一邊做音效。我在幕後擺上幾根麥克風,掌握各個麥克風的位置及效果,需要近的聲音時,便把這隻麥克風打開;需要遠的聲音時,則將那隻麥克風打開。錄音過程中,得自己琢磨,聲量要開到多大,聽起來那個迴音、空間感才像。」
《海灘的一天》可謂杜篤之個人在「事後配音」上一個革命性轉變的開始,也有個比較明顯的成績。記得當年該片在香港放映時,大家都以為是同步錄音。導演徐克還很驚訝,「啊,現在臺灣的同步錄音已經做得這麼好了!」
《海灘》之後,杜篤之再接再厲,兩年後的《小逃犯》,他首度向導演張佩成提出「不用配樂、以音效代替」的建議,自行設計音效,充分運用「空聲」效果,成績斐然,該片音效也令他拿下生平第一座電影獎——「亞太影展」最佳音效。
及至《恐怖份子》,其聲音的擬真效果更是出眾,當年一位英國導演在中影放映室看完該片後,曾驚訝的對楊德昌稱讚該片同步錄音的成績時,楊德昌只是笑,同時介紹杜篤之說:「這是事後配音,都是他做的!」
在小杜心裡,楊德昌就是老大;而楊德昌也曾這樣形容杜篤之:「我相信我們在互相交友或工作當中,都給了對方非常多的信心,我們有把握可以做得更好,這是非常重要,非常幸運的,我們處於這種狀態裡。我覺得那個時代有一些狀態,我們很幸運在這種環境下長大,這和現在年青人花許多時間去背一些雜訊是很不同的。」
趕片接力,追著時間跑
每次後製期間,杜篤之多是夜以繼日的趕片,《海灘的一天》亦然。
「那還不是趕金馬獎,是趕亞太影展截止日。我知道《海灘》要代表中影參加亞太,時間十分緊迫,於是幾天幾夜沒睡,助理兩班輪流,我就撐在那裡一直做,到了第三還是第四天,實在太累,本來撐不下去,心想做到天亮,今天就該暫停了,因為真的是精神不繼。
「沒想到天一亮,大概早上六、七點,楊德昌跑來說:『哇,不得了了,今天晚上六點鐘要看片,要看到拷貝。』
「以前每次熬夜熬到天亮,我都會跑到室外去透透氣,楊德昌來的時候,我剛透氣回來沒多久,一聽晚上就要,我的精神全來了,忽然間人就醒了,也不累了,立即全組動員,我開始企劃流程,好讓後面的人也有事做。」
因為以前的錄音設備老舊,效率不高,《海灘的一天》當時只完成了五分之一,還有五分之四的工作沒做。正常流程是杜篤之在士林外雙溪中影錄音室內將所有後製混音完成後,再給下兩個部門去「過光學帶」及「套片、印片」。當時「過光學」要去北投,「套片、印片」得到深坑,三個部門分隔三地,若照原來的程式,不足以應變此等緊急狀況,於是調整作業流程,大家分頭並進,「我趕著先做一本,一做完就找人快送去北投過光學。從外雙溪到北投,大概要三、四十分鐘,來回一個多小時,送件人一放下片子馬上趕回外雙溪來拿另一本;在這一個多小時裡,我得做完下一本,讓他再帶回北投。因此,北投、深坑那段路得另外安排專人送片,剪接室的人就等在深坑做套片、印片;深坑這邊一沖好片,趕緊印一本,再派專人送至新聞局給評審看。」《海灘》就如此做一本送一本的給評審委員看片,連中間休息的吃飯時間都盤算在內,能爭一刻是一刻。
整個路程分成三段,送片信差也有三批,就在「外雙溪、北投」、「北投、深坑」,「深坑、臺北市天津街新聞局」之間來來回回的跑,每段路程都是專人專車運送底片。《海灘》一卷大概十分鐘,總共有十幾卷,片子超長,參展版本兩個半小時。「那天我一路做到下午五點多,我的工作結束,但睡不著,因為整個人仍處於亢奮狀態,還去關心後面的進度。當天有車的朋友全被調來幫忙送片,有個朋友在高架橋上和人家擦撞,朋友一鑽出車子,掏出名片丟給對方就說:『我現在沒時間跟你們吵,你再來找我好了,我要趕著走!』」真是分秒必爭。
《青梅竹馬》,合作無間
所有細節都聽到了!
提起趕片,小杜可謂經驗豐富。《海灘的一天》是趕亞太影展截止日,《青梅竹馬》則是趕上片時間,《青梅竹馬》更是緊迫到只給他五天時間完成「做音效、配對白、混音」的後製工作。為了趕上片的最後期限,杜篤之三天兩夜沒睡,先做出一個版本上片,並計畫以後重做。他當下決定,所有時間儘量給演員配音,「因為那是真的表演,無法重來;也就是說,這次你要求演員這麼說,下次他再配,心情不同,說話的感覺也會不一樣。」五天裡他花了三天多來配演員對白,音效只用了一天多時間,還好該片沒什麼音樂,對白、音效錄好之後,混音一天完成,隨即上片。本來打算重做,但仔細一看,覺得這個版本還滿好的,就沒有重配。時間雖趕,但該做的、該注意的細節,他們並沒有放過。
楊德昌與杜篤之還克難的用Beta帶(1&3/4錄影機quality)將《青梅竹馬》的聲音版本拷下留存,因為當時的臺灣電影院無法巨細靡遺的呈現出他們苦心經營的聲效全貌;於是變個法子,用專業帶拷下,在自家客廳裡以專業設備放映,杜篤之說:「真過癮,都聽到了。」可惜那款錄影機目前已經停產了。
在《青梅竹馬》的音效上,兩人費心經營出許多細節,譬如為了呈現迪化街老屋牆外街燈明滅、三更半夜的氣氛戲,他倆趁夜深人靜時開車直奔陽明山,專程去錄下汽車來回行駛的「唰唰——」聲,當晚還在山上迷路,繞了老半天都繞不出來。
但這些環境音、空間轉換、衣服摩擦……的細膩聲效,在當時臺灣一般電影院裡放映時是聽不到的,因為都被機器的雜聲給遮蓋了。以前每次做完電影聲效,杜篤之常想,到了電影院裡大概只剩下六成;若是拷貝或戲院聲效系統不好,可能只聽到四成;通常重放的效果都不好,大家也就不理了。但他心裡清楚,一旦拿到設備精良的戲院去映演,這些細節還是可以出得來的。
一九八五年楊德昌帶著《青梅竹馬》遠赴義大利出席都靈影展,特別從當地寫了封明信片寄來告訴杜篤之︰「哎,都聽到了,在臺灣都沒聽到,很悶!」都靈的電影院首次證明了他們在聲效上所下的工夫沒有白費。更沒想到的是,這份努力,在台灣電影聲效上逐步形成一個傳承,一如楊德昌的這封書簡,時隔多年,經驗重現。二○○六年四月,《宅變》製片人葉育萍至義大利參展,該片一放完,她便高興的當場從義大利撥電話回來說:「杜哥,我們所做的聲效在這裡全都表現出來了,而且劇場效果很好。」電話裡她情緒依舊很High,同時還致電給做音樂的鄭偉傑,一起分享喜悅。同年九月,當二十八歲的鄭有傑帶著他首度執導的劇情長片《一年之初》參加第六十三屆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時,也身歷其境,鄭導演說:「我好像在看另一部電影!」該片的聲音細節及豐富令《一年之初》的攝影師包軒鳴(John Pollack)興奮的說:「我回去要給杜哥及林強一個大大的擁抱!」
從《青梅竹馬》到《一年之初》,從楊德昌到鄭有傑,二十多年過去了,杜篤之的聲音工程一再讓導演們站在國際影壇上與世界各國好手比拚之際,都能驕傲的說:「我們一點也不失禮。」
《恐怖份子》,事後配音的極致,是該轉變的時候了!
對「配樂」的看法
楊德昌的電影裡從來少有配樂,從《海灘的一天》起便是如此,尤其是《青梅竹馬》和《恐怖份子》,《青梅竹馬》只有一段馬友友的大提琴,《恐怖份子》僅用了一首老歌,象徵楊導母親的那個年代;《一一》算是楊德昌電影裡比較有音樂的。
杜篤之說︰「楊德昌其他電影裡雖無配樂,可是卻有很多音樂。我們大多把音樂做成環境音,放在背景聲音裡,歌聲或從收音機裡傳來,或從隔壁鄰居家中飄送過來……這些背景音樂又與電影氣氛相合,就用這個方法。」如《恐怖份子》最後一幕李立群坐在那裡,砰的一聲舉槍自盡,然後聽到一些聲音細節:水聲、鮮血滴落水中……剛開始自別處傳來的樂聲其實就是蔡琴的歌,之後逐漸轉成配樂。
每當做這些改變時,杜篤之總覺得很過癮,「基本上我們的出發點是,不企圖用配樂去影響觀眾怎麼看電影,因為配樂會統一觀眾的感動點。若沒有音樂,未經渲染,你可以更自主、更透明的來看這部電影。每個人的背景不同,感動人的位置、時間點也不同,有的女生早已痛哭流涕了,有的男生卻要到很後面才會感動。這些都是自發的,都是觀眾自己與影片互動之後所產生的情感。這份記憶可以留存,你看完回去,甚至兩、三個月之後,可能都還記得,這個東西才是最珍貴的。」
「一部電影下了音樂以後,可能有十個『落點』讓你在觀看當下有所感動,但人人的感動點都差不多,因為都被音樂給催眠了,隨著音樂的起落點及節奏走,他早設計好了,他要從這個點開始煽你,要你感動。但是沒有音樂的電影,可能你到最後一刻才很感動,甚至沒有。但是,一次都沒被感動的這部電影,可能會被你記上好幾個月,因為所有情感是由你內在自我生發時,是你自己的感受,而非你直接或間接的被規範在某一點上要被感動;就像炒菜沒加味精,是個『原味』。」杜篤之不是反對音樂,他只想試著說,你也可以嘗嘗「原味」,但並非每部電影都合適這麼做。
「我們不想統一感動點。譬如《恐怖份子》,非常理性的說故事,在理性敍述當中,你會有些感動,但人人感動的位置不一樣。」這個想法其實和他一向對聲音的看法有關,正如他所言:「聽不見的聲音,才是最好的聲音。」自然的成為那個環境中理所當然的一部份,但是這個自然,是再造的自然;所有的理所當然,都是精準設計、思慮周密、心理轉折……等各方面合理推演的結果,並非天生如此。但作品裡的情感之真,則是戲裡戲外、無分軒輊,正所謂「戲假情真」!
「事後配音」的巔峰,個人發展階段的分水嶺
楊德昌、杜篤之經常討論聲效要怎麼變、如何做,《恐》片中幾場頗有新意的音效,就這樣變出來了。
「照片貼滿整個牆面,風吹過去,照片飄起來」的這場戲,他們是真將照片貼滿一牆,但不能用電風扇吹,因為會有馬達、風扇旋轉的聲音,而是用三夾板搧,「因為板子很大,一搧,牆面上所有照片便開始飄。」
又如「槍聲」,即片尾李立群槍殺太太繆騫人及金士傑的那幕戲。李立群射殺金士傑時,子彈先擦到門、繼而射穿金士傑,再穿破玻璃,這段聲音非常之細膩複雜,包括子彈飛射過程裡所碰到的不同狀況、射穿不同材質(木頭、人體、玻璃)的層層聲效——如子彈與木材碰撞聲,子彈穿入、穿出人體,玻璃破碎,水流下來……所有細節均精確、自然的呈現,難度極高,但也容易被忽略,因為這些都不是外顯易見的東西。但這些看似不起眼的元素,每一細微處都照顧到或被漏失掉,卻關係著最後成品的整體成績,有它,順理成章,恰如其分;少了它,不單美中不足,且足以造成扼腕之憾!
《恐怖份子》乃杜篤之「事後配音」階段的代表作,這是個分水嶺,該片擬仿同步錄音聲效,真實感引起國際影壇囑目,咸認為臺灣電影的聲音技術突破多年瓶頸,已達同步錄音效果。
對杜篤之來說,如何使用對白來控制演員、讓演員做得更好,如何運用技術、使聲音兜得更準,如何仿真空間感、以製造仿同步錄音的音效……早就易如反掌。但在「事後配音」水準已達顛峰之際,他也正面臨瓶頸。「我們最大的限制是經費和時間,你想做久一點,不可能給你那麼多時間,多點時間就得多花錢;是還有精進的空間,可是我們沒那麼多錢了。要更好,得花更多力氣,才能再好一點點,竭盡資源也只能做到這樣,那個曲線已達飽和了。因為不是現場同步錄音,有些效果會受限,是該突破轉型了,加上當時我又有一些同步錄音的經驗。」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聲音的時代感
「我拍《牯嶺街》最主要是覺得,那一段歷史是我親眼目睹的歷史,如果我不為那段歷史留下一個很真實的作品的話,那段歷史就會消失了。所以不管以後哪個時代的人來看這部電影,我覺得基本上我替那個時代做了一點事,我很誠實的把那個時代的狀態放到電影裡。
這個意思我在片頭的字幕中就提出來了,不然那個時代是非常容易消失的。因為當時的權力當局不希望當時的記錄被留下來,事後的人也不希望回想那段時間。其實很簡單,台灣有今天就是因為那段時間,而且是那段時間的台北。我為什麼拍《牯嶺街》,就這麼簡單。」(註5)
——楊德昌
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杜篤之是件大事,「做的成績也滿對得起自己的。」
當時小杜任職中影,平時有戲可做,生活不成問題。但為了等《牯》片,曾有兩年時間他不外接其他片子,且推掉了三個大案子,其中之一是關錦鵬的《三個女人的故事》,得去香港、紐約出外景;還有就是許鞍華的《客途秋恨》,要到大陸、日本拍攝。那個年頭能跑這些地方真的很難得,誰不想去?但為了《牯嶺街》,他全回掉了。《牯嶺街》開拍之前,工作人員之間曾流傳著一則順口溜︰「荷花荷花幾月開,一月開;一月不開幾月開,二月開……」就這樣一個月又一個月,延了快一年。
當時的情形是,告訴你下個月要拍,下個月不能拍,於是再等。後來許鞍華跟小杜說︰「你又沒拍,又不來幫我弄,現在我的片子聲音要怎麼辦?」
那時候杜篤之已經做過《悲情城市》,有些聲音後製的基礎,於是請許導演把片子拿來台灣,由他完成後製。「做了些報表,聲音該怎麼弄,就照規矩幫她給做出來。」
但是這個「等待」很值得,《牯嶺街》在台灣電影音效上完成了幾項創舉:杜篤之首度啟用台灣第一套正規的現場同步錄音設備,進行該片的同步錄音;該片也是當時唯一在台灣自行完成全部後製混音的電影。
現場收音
麥克風的位置、單聲道的概念
杜篤之說:「拍完《悲情城市》之後,侯導送給我一套現場同步錄音設備,有多支無線電麥克風,正規精良的調音台、答錄機,設備完好。我用它拍的第一部電影就是《牯嶺街》。一九九○年八月八日《牯嶺街》開鏡,就在淡江高中,是早上的通告,可是要到下午太陽才照得進來。我早上十點多收到這套設備,於是將錄音推車組裝起來,中班就拿去現場,新開張,還是熱的,當天就取名為『快餐車』,我記得是楊德昌還是余為彥取的。」
拍《悲情城市》時,小杜真的可以全片同步錄音了,但設備不是很夠,做的東西雖然很喜歡,但總覺得有些遺憾。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及至《牯嶺街》,有了「快餐車」,小杜不再囿於設備不足,又能往上突破了。「當時做什麼都很勤奮,『快餐車』很好,我每天錄得非常過癮。之前我們已有『空間/迴音/遠近』的概念,現在當然要把它做得很美。怎麼美?譬如鏡位擺在此處,人從學校走廊那頭一路過來,遠處不理它,迴音很大就讓它大吧!當人走近、當他靠近我麥克風的那一剎那,時間、地點的準頭,我得拿捏得十分精確。關鍵即在於,當他走近麥克風的這個『近』,要從『何時、何地』開始算起?其實就看畫面上的感覺,我得留神畫面中『人與鏡頭』的關係,以此來判定麥克風該放在哪個位置。譬如畫面走在兩間教室門外,我就將麥克風架設在路徑上。當你走近時,聲音就在你感受到的那個位置上。」
《牯嶺街》一開始即出現五○年代建國中學旁、美新處後面的華國片廠畫面,其實是以士林的中影片場冒充的:「老片廠的房頂都是那個樣子,只是華國的攝影棚沒中影的兩個棚這麼大、這麼好。中影攝影棚屋頂天橋的規格都很標準;當年華國片廠的棚比較矮,天橋的結構也差點兒。片廠聲音都是現場錄的,回聲的空間感很好。可惜當時我們是用單聲道的概念做東西,沒有杜比身歷聲五.一聲道的概念,如果有的話,那個戲會更過癮。單聲道雖能聽出裡面有空間感、立體感,聲音有遠近;但聽不出左右、前後的空間感,兩者效果不同。」
直到《少年口也,安啦!》,杜篤之才開始做杜比立體音效.「每樣新器材帶給我的不是限制,而是更大的突破,以前做不到的,現在可以輕易完成,同時還可以嘗試其他新做法。」
第三章 楊德昌與杜篤之「楊德昌的電影是每個地方都精準的控制住(under control),然後再來演,看似真的,其實都是控制住的。」認識楊德昌二十七年的杜篤之,對楊導知之甚深,從《光陰的故事》、《海灘的一天》、《青梅竹馬》、《恐怖份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到《獨立時代》、《一一》一路走來,舉凡楊德昌的電影,錄音一定由杜篤之擔綱,就在為臺灣電影的聲音創作屢建新里程碑,就在為電影聲效水準拚出一片天、拚上國際影壇的同時,兩人也結下一輩子的交情。杜篤之說:「楊德昌是影響我最深的兩個人之一,另一位是侯孝...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3收藏
13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