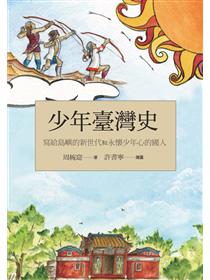讓我們一起追索,那些被遺落在過去,以及被深藏於現代的台灣人的歷史。
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
我喜歡中國第一個教西洋史的女教授陳衡哲說的,歷史「乃是要求我們明白他的」。在那之前還有兩句,她說,「歷史不是叫我們哭的,也不是叫我們笑的」,我倒想修成「歷史既要我們哭,也要我們笑」。
文化無法一筆抹掉或整段切除,她以一種基因性的型態存在與傳承。我們必須肯認原住民、中國和日本文化共給了台灣滋養,然後,才能真正瞭解自己是誰。
作者簡介:
陳柔縉
台灣雲林縣生(1964),台灣大學法律系司法組畢業(1986)。
曾任:聯合報政治組記者、新新聞周刊資深記者,現為專欄作家。
著有:《私房政治──25位政治名人的政壇秘聞》(1993)
《總統是我家親戚》(1994)
《總統的親戚》(1999)
《台灣西方文明初體驗》(2005)獲聯合報非文學類十大好書、新聞局最佳人文圖書金鼎獎
《宮前町九十番地》(2006)獲中國時報開卷中文類十大好書
《囍事台灣》(2007)
章節試閱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
最近這個冬天,我在一個民間學苑上課,講日本時代的衣食住行,八十歲白髮學員不少,那是他們親身存在的時空,所以,也是去採訪。
一天上課前,一位女學員很禮貌來致歉,我請他們寫一個自己與日本時代相關的故事,她說她在戰爭結束前兩個月出生,沒有故事,另一方面也忙,還沒能回家鄉問老母親有甚麼值得說的記憶。
我第一個反應,笑稱,「哦!你也當過日本人!有日本名字嗎?」然後,聊著聊著,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跑出來。
她說,戰時美軍飛機來轟炸,有一天,飛機又到村子頭上,全家急成一團要逃,阿公叫母親快跑,「查某仔不要緊啦!」不要管躺在床上的小女嬰。阿公重男輕女,但母親捨不得,還是趕緊抱起,躲到屋外的防空壕。後來發現,空襲過去,房內的床留有彈痕。她笑著說:「要不是媽媽,我早就沒命了!」
不是沒有故事,只待發現。
我也想到自己家裡的戰爭記憶。
我們住的鄉鎮挨在濁水溪南不遠,阿公約有三甲地,一甲的溪埔地租給佃農。「日人尾」〈台灣人稱日本時代最後幾年〉,美軍轟炸機B29動不動就來空襲,農人在田間無法安心耕種,佃農「做無」〈沒有收成〉,索性把地還回來。一下子,鐵線草長得奇高,阿公借了親戚的牛去翻土,爸爸跟在牛後面用腳把草踩進土裡。阿公又跟阿衡仔叔公討了短短的蕃薯藤苗。叔公不保證種得起來,但當時農田荒蕪,作物缺乏,能得點小苗,阿公已非常感謝。結果,鐵線草埋進土裡,成了最好的有機肥料,半年後,蕃薯個個肥大;爸爸跟我說這個故事時,用雙掌合捧來形容。
戰爭的最後一、兩年,台灣各方面更形殘破,一切物資都少,米和豬肉要配給,對農家這兩項監控得厲害,對蕃薯卻放任自由。於是,阿公每一天去田裡挖蕃薯,每天載一牛車回來,約莫一千台斤,倒在家後巷子。鄉人聞風而來,一天就賣得一千圓。一千圓是非常大的錢,小學老師一個月才領四、五十圓。爸爸說,「賣到心會燒」。
阿公先前在公學校後方買了一塊地,欠日本勸業銀行台南支店三千多圓,十幾年還不完,利息壓力愈來愈重,沒想到賣幾天蕃薯,就還清了。這塊地後來分給爸爸這一房,也是我們兄弟姐妹五人能繳出學費、安然成年的後盾。雖然,那塊地不得不賣掉,但故事永遠留下來了。
我總鼓吹朋友,回家去問阿公阿媽爸爸媽媽,去幫他們做口述回憶。由於日本時代記憶曾經長期無心被撫觸,此時再去挖掘,相信更會有許多意外,驚聞許多從來不知道的家族舊事,激盪難歇。
一位好朋友真去和她爸爸聊了,就大呼驚奇,長到四十幾歲,她從不知道祖父留過學,唸過東京的「目白中學校」,終於才知道為什麼家裡有坐在雪地的泛黃照片、為什麼有刻著「目白」的網球優勝紀念牌。
時代不專屬於誰,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記憶不能只靠幾座古蹟和英雄書上的幾個人,故事不計大小,都值得流傳。誰又能預料哪個故事會在哪個心靈發光與發熱呢?
懷念的鐵路便當
北海道名寄市原有全日本最北的鐵路便當,日夜守護,歷經四代。即將屆滿一百年之前,卻因老闆要照顧生病的太太,不得不熄燈休業。覆雪的月台,將不再有「便當、便當」叫賣聲,陪伴旅客孤獨的腳步。
現在台灣人大口吃便當,以「便當」來指稱飯包,就從日本來的,源於日本統治台灣的年代。
日本時代的便當寫做「辨當」或「弁當」,是日文的漢詞。日本時代,台灣人圖其方便,直接借用不少日文漢詞,例如「見本」(樣本)、「口座」(銀行戶頭)、「注射」(打針)等等,再以福佬話發音,而不流行轉換成適當的中文翻譯。「辨當」也是如此,頻繁出現在當時的中文書寫裡。
「便當」兩字,雖未普遍,戰前倒也已經出現。一九一一年,台南一家糖蜜會社,十幾個員工,有台灣人,也有日本人,興致勃勃跑去安平海邊,辦了海灘運動會。當時,中文報紙就報導說,老闆和職員「均帶便當。充為午飯」。
日本的「鐵路便當」,他們專稱「弁」,「」是「車站」,「弁」就是「弁當」。日本第一個弁於一八八五年由木縣的宇都宮賣出。當年日本開通東京上野到宇都宮的鐵道,鐵道會社請求站前白木屋旅館製作販售。便當形式很簡單,竹片包著兩丸飯糰加黃蘿蔔乾。便當價格五錢,跟鰻魚飯賣十錢比起來,被認為並不便宜。今天,到宇都宮站,還可以看見便當包裝強調是從「弁發祥地」賣出。
台灣的鐵路便當起於何時,難以確認,不過,鐵路各站的便當菜色,報紙提供了一點線索。一九一四年,報紙評比了桃園、苗栗、新竹和台中四站的便當,仔細記錄菜色。前三者大同小異,以桃園站便當來說,用的是日本米炊的飯,配菜有炸土魠一片、鹽煎旗魚一片、炸筍兩片、煮豆少許、鰻魚八幡卷一個和醃漬蘿蔔兩片。台中站便當稍微不同,煮物一片、煮藤豆(類似豌豆)、魚板三片、蒟蒻兩片、蓮藕和醃漬蘿蔔各兩片來搭配白飯。看得出來,當時的鐵路便當全然和風。
以前有在月台叫賣的鐵路便當,像一九一○年代,打狗(高雄)站的便當,曾由日式料理店「滋養亭」承辦。另一種鐵道便當出自火車站附近的旅館和餐廳,像新竹站前,就有一家塚迺屋旅館,聲稱是鐵路便當的「元祖」(鼻祖);不過,究竟是新竹當地或全台的第一家,不得而知。而台北市最高級的西洋旅館「臺灣鐵道旅館」則調製了洋式便當,旅客預訂,即送到火車站內。
洋人吃的鐵道便當該是甚麼樣子?台灣前輩畫家奉為老師的石川欽一郎一九二二年到歐洲訪遊,他畫筆下的便當小販,揹著圓盆,胸前滿是誘人口水的餐食。石川欽一郎還表示,各國鐵道便當以義大利最便宜,內有兩個圓麵包、半熟的蛋兩個、三條大香腸、起司一大片、水果,再加一小瓶葡萄酒。
台灣進入三○年代後半期,因日本侵華,社會大變調,鐵路便當則小突變。一九三八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滿一年當天,台灣的火車站統一推出「愛國辨當」。平時在月台叫賣的普通便當、炒蕎麥麵、炒米粉,一律禁絕,只准賣這色便當,裡頭只放白飯糰、梅干和黃蘿蔔乾。
日本便當都是冷的,經歷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慢慢習慣吃冷便當,這個飲食文化卻和戰後大陸移來的外省人不同。前工業委員會化工組組長嚴演存在《早年之台灣》回憶說,外省人「生活習慣也和本省人不盡相同。例如台灣人中午吃便當,外省人一般非吃熱飯不可」。
祖籍江蘇、生於北京的作家張天心(一九二四年生)在〈便當之戀〉文中也寫道,來台前,他「不但沒有吃過『便當』,也從來沒有聽過『便當』這個名詞。」第一次在台灣吃便當,是一九五○年代的事,而且在火車上吃的。沒想到「蓬萊米飯是那樣柔軟清香,炸肉片或炸魚片是那麼酥脆鮮嫩」,而黃蘿蔔「看起來有點像化了
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最近這個冬天,我在一個民間學苑上課,講日本時代的衣食住行,八十歲白髮學員不少,那是他們親身存在的時空,所以,也是去採訪。一天上課前,一位女學員很禮貌來致歉,我請他們寫一個自己與日本時代相關的故事,她說她在戰爭結束前兩個月出生,沒有故事,另一方面也忙,還沒能回家鄉問老母親有甚麼值得說的記憶。我第一個反應,笑稱,「哦!你也當過日本人!有日本名字嗎?」然後,聊著聊著,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跑出來。她說,戰時美軍飛機來轟炸,有一天,飛機又到村子頭上,全家急成一團要逃,阿公叫母親快跑,「查...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9收藏
49收藏

 42二手徵求有驚喜
4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