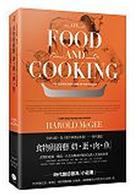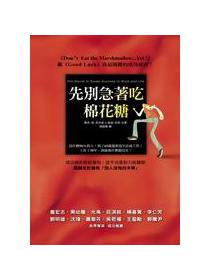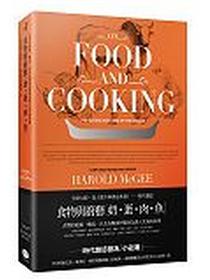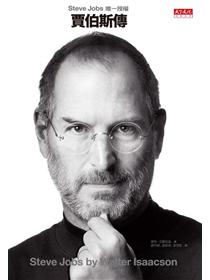五百年的沒落史
若要追溯我家族的興起,那真是古早古早以前的事了。那是個盜匪橫行,民智未開的時代,人們常常要為出沒不定的盜匪提心吊膽,於是人民決定央請武力較強的強盜來保護他們,幫他們抵禦武力較弱的強盜。於是,源源不斷的保護費流進了我祖先的口袋,金額之龐大,讓我們修築起美麗的城堡。我們的第一座城堡建於第十世紀,座落於圖林根的薩勒河畔,名字就叫笙堡,意思是美麗城堡。十二世紀中葉,紅鬍子王腓特烈一世主政期間,我們的領土逐漸擴張到了幕德蘭地區,並且重新在格勞豪建立了我們的大本營。這座新城堡跟一般擁有護城河的城堡很不一樣,它的壕溝並沒有引水防禦--因為根本用不著,大棕熊自會幫我們看家,再兇猛的敵人看到牠們都要退避三舍。直到十八世紀,我們才統治了如今的薩克森西南部。同時間,維丁家族被封為選帝侯,幾世紀以來他們就覬覦我們在幕德蘭的統治權,並不斷向我們挑釁。隨著其政治勢力不斷擴張,我們也越來越無力招架。
薩克森王國在一八○三年徹底併吞了我們的領土。但在一百五十年後,也就是當蘇聯佔領東德後,我們才真正被趕出了宮殿--被共產黨給趕出來。這些皇宮,當然包括了父親童年時居住的維荷瑟堡。那裡的花園一望無際,訓練得幕德蘭人走起路來婀娜多姿。不過那時,我們家族的勢力早已勢微,財富也大不如前了。戰後,蘇聯佔領軍沒收了家族的所有財產,其實不過是為我們幾世紀以來的沒落劃下了「理所當然」的句點:從擁有自己獨立的小王國及領土,一路沒落到成為空有頭銜的平民貴族。但在沒落的過程中,我們卻練就了一身「承受失去」的功夫,日後更成為我們家族生存的最大優勢。
父親和母親,此二人絕對有資格榮獲「高水準窮人」的封號。身為大時代的兒女,他們都經歷了離鄉背井的逃難命運。父親十六歲時,首先帶著祖母和他五個年幼的弟妹逃往西德,然後又獨自返回幕德蘭。他之所以敢回去,是因為他認為蘇聯佔領軍也沒什麼好怕的。回去之後雖然被捕,但很快又被釋放了,理由是:他可是專程從西方聯軍那裡回來的投奔義士!另外還有件事也很有趣,當他潛進父母住過的皇宮去搶救家當時,他挑選的標準真可謂不同凡響!他既沒拿珠寶,也沒拿純銀餐具,只拿了一對公羊角--這是他跟祖父去狩獵時,生平第一件戰利品。
我母親則遲至一九五一年,史達林主政的恐怖時期,才從匈牙利逃至西方。當年她二十一歲。當她從滿是水蛭的奧地利新移民湖上岸時,她對匈牙利已毫無眷戀了--至少物質上是如此,因為她在匈牙利早就一無所有了。在共產黨統治下的匈牙利,母親因為貴族身分而被批鬥成無產階級的敵人,甚至連應徵清潔婦都被拒於門外。
父母親在西德經濟起飛的時期相識、相戀,並結婚。結婚時,他們除了必要的東西外,實在身無長物。他們在柏林的工人區坦培霍夫找到一間狹小的出租公寓,大姊瑪雅就是在那裡出生的。後來又搬到司圖加特,二姊葛羅莉亞是在那裡出生的。之後因父親受聘於電台「德國之音」任駐外記者,被派遣去非洲,所以我們便舉家遷非。六○年代中期一直到六○年代末,我們都一直留在非洲。首先住在多哥的首都洛美,那裡是哥哥的出生地,後來又遷往索馬利亞的首都摩加迪休,但無論住哪裡,德國之音駐外記者的微薄薪水,在非洲都能讓我們過得闊綽如貴族。
登陸月球的那一年,我在摩加迪休出生。同一年索馬利亞爆發內戰,父母親被迫返回德國。無憂無慮--至少經濟上是如此--的非洲插曲正式結束了。他們又在德國落地生根。當時正值德國經濟繁榮的階段,整個社會籠罩在富裕的氣氛中,但我的童年卻沒有感受到這股富裕氣氛。父母親的生活方式可謂「克勤克儉」。同學家的冰箱都塞滿了各式各樣的零食,吃巧克力成了小孩子的基本人權。但是我們家冰箱除了一罐牛奶外,總是空無一物--至少在我的記憶中是如此。
整個童年期間,餐桌上的食物永遠是馬鈴薯和荷包蛋。什麼「度假」啦、「零用錢」啦,我都是聽同班同學說的,在我家從沒發生過。可是我們家卻佈置得高尚優雅,甚至比大部分的有錢同學家還要漂亮。母親的裝潢功力一流,她所應用的「新貧時尚藝術」更是令人大大折服:她用美麗花邊包裹起三夾板書架,以抱枕及華麗桌巾為IKEA廉價家具變身。當其他人為彰顯自己的身分地位,追逐著各種流行與象徵時,我父母卻將節儉的美德與藝術發揮得令人嘆為觀止。父親最常穿的是一件補了又補的夾克外套,和一條皮長褲--他捨不得穿布做的長褲,因為怕弄破了。我的衣服則基本上全來自哥哥穿不下的,或接收自堂哥、表哥。每次只要媽媽依照可怕的慣例說:兒子們,咱們去買衣服,我的治裝費一定是全被省下來了。
父親除了是德國之音的駐外記者之外,他還是個「環保志工」:他樂於當大自然的守護者。過世前幾年,他還代表家鄉出任幕德蘭地區的國會代表。但這個職位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意義和目的只在於:能為森林和狩獵請命。在兒時的記憶裡,我總覺得打獵是又濕又冷,得穿著厚厚的黃夾克,跟著大夥兒一起慌張地去圍獵,「快!快!快跟上來!」,跟父親一起埋伏在高處,只要我輕輕一動或稍稍發出點聲響,就會被立刻制止,所以我總是要憋著氣呼吸。父親開的永遠都是最便宜、最爛的車子。他的俄國車拉達,他的皮褲,還有他那穿得都快磨破的舊襯衫,每次都讓我覺得好丟臉!但如今我終於了解,其實他是個多麼風格獨具的人。每當我回想起,他穿著破舊的深色西裝走進國會殿堂的那一幕,啊,多麼不同凡響!比起其他清一色穿高級西裝的同僚們,他真是出色太多了。
貧富兩界的走私者
今天我終於了解:父母的「節儉功力」不僅是為了實際需要,還遵循著某種美學原則。鈴木愛作曾在《射藝之禪》中談及「日本武士的佗寂精神」,所闡述的中心思想是「不足的美感」與「儉約的美感」。武士從來不會因衣衫襤褸、外表醜陋而遭人憎惡--裝扮華麗、奢侈浪費才是「無情」的行為及表現。歐洲版的佗寂美學,當屬由我父母發揚至臻境。一只茶壺唯有出現裂縫或黏補過後,父親才會覺得它具有美感,一件夾克一定要舊到沒有人肯穿了,父親才會樂於天天穿它。
雖然後來二姊葛羅莉亞嫁給了突恩暨塔克希斯侯爵,但我們家的生活並沒有因此而改變,畢竟我們已經很熟悉怎麼當個有錢人家的窮親戚了。戰後我們家族一直都跟有錢親戚走得很近。祖母在流亡時曾經帶著她年幼的孩子們去投靠祖父的妹妹,這位姑婆嫁進了馬克西米連家族,這個家族可是在歐洲擁有最多森林的富豪。姑婆的丈夫非常慷慨--這在當時非常罕見--將他位於博登湖畔聖山皇宮的一部分,借給祖母跟她那八個孩子居住。祖母在那裡住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父母親買了自己的房子,才把祖母接過來住。除此之外,我和哥哥姊姊們的童年,有大半時間也都是在有錢親戚的皇宮或森林裡渡過的。但是父母常告誡我們,絕對不可以將自己和親戚們的生活混淆在一起。我記得有一次,我只是請僕人幫我拿了杯可樂,還是其他什麼小東西--我已經不太記得了,卻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爸媽說:小孩子絕對不可以使喚僕人。
對我而言,貧富齊聚一堂乃再平常不過的事了。但有錢人和沒錢人之間,總是隔著一條無法踰越的界線。有人說,打獵和舉行慶典時,貴族們會不分貧富全員到齊,或許沒錯,但更正確的是,那些沒錢的親戚其實是很不受歡迎的。在不算很富有的有錢貴族裡,威斯特法倫男爵之行徑堪稱是經典:戰後,他為了怕窮親戚風擁而至,嗷嗷待哺成為他的負擔,他乾脆壯士斷腕,把一大部分的皇宮給拆了。過去整個家族的大家長會一肩扛起所有責任,照顧全部族人,並且義無反顧拯救落難親友,甚至給予長期援助,那個時代似乎早就絕跡了。他們的後繼者徹底終結了這種風範與擔當,並且不再願意跟窮親戚們打交道、做朋友了。
不過,如今就算是有錢貴族,也已經很少人會雇用一大堆傭人、住在皇宮般的豪宅裡。影響所及,窮貴族和富貴族也越來越難分辨。長期寄住在有錢親戚家的可能性越來越低。那個被親戚邀去喝茶,一喝就是三十年的時代,已經完全過去了。縱使那些最有錢的貴族家庭,那些二十年前還居住在皇宮裡的貴族,也大約都在十年前搬進較小的行宮,而今更是換到實用簡潔的花園別墅裡。所有貴族如今都過著「現代生活」,也因此,窮貴族和富貴族之間的來往也更貧乏。事實上,百分之九十的貴族是向人租房子的無殼蝸牛,情況好一點的話就是住在鄉下那種一整排並列,一棟一戶的普通房子裡。其實,他們過的就是一般人的生活:開著老舊的二手車,每天為工作而忙碌--如果他還算幸運有份工作的話。
得知我被裁員後,有位同事跟我說:「沒問題啦!你根本用不著煩惱!」那口氣就好像,只要名字裡有個「封」字的人,在窩瓦河對岸就一定還有大片農莊等著他去回歸鄉野。看來我得甘冒被罵得狗血淋頭的危險,不惜犧牲大家對貴族的美好想像與傳說,把事實說出來:德國貴族裡除了五根手指頭數得出來的少數幾家人以外,大部分的人早就不再是擁有大片土地的富豪了,他們早已淪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裡面對現實生活的普通老百姓。
在我少年時期,過世的二姊夫約翰納斯•封•突恩暨塔克希斯侯爵很喜歡叫我當他的小跟班,所以讓我有機會遊走於貧富兩界,看遍知書達禮窮人和寡廉鮮恥富人之百態。但我也為此付出了許多代價,經常要冒適應不良的風險:今天坐在阿拉伯石油王子、印度土財主、歐美富豪的身邊把酒言歡,明天卻得回學校當個窮學生,或者,後來工作後,得回崗位上當個落魄的自由記者。最後搞得我一輩子都得跟「麗茲酒店侍應生症候群」周旋奮戰;這是發生在麗茲酒店高級侍應生身上的一種「奢華病毒」,受此病毒殘害的傢伙一直無法適應生活中的兩種極端:白天他接觸到的生活型態都是美輪美奐,揮金如土的奢華人生,但下了班,卻得回到只有兩間房的狹小公寓,聽著漏水的水龍頭不斷滴答作響。
一方面基於對父母節儉性格的反感,一方面基於對浮華世界的嚮往,我開始發展出許多特殊嗜好,比方說,坐頭等艙的嗜好。每次當母親載我到慕尼黑坐火車時,在她面前,我一定登上二等車廂。等火車一開,看不到她的身影時,我就迅速換到頭等艙。我總是小心翼翼地不讓家人知道我的嗜好,否則一定會惹來訕笑。有一次媽媽在我的口袋裡發現了一張柏蘭特精品店的收據--我請他們幫我印製昂貴的私人專用信紙--她認為一定是對方搞錯了。還有一次,一個在巴登—巴登「布蘭諾爾花園飯店」工作的表親跟母親說,我曾到那裡住過一夜,母親同樣斬釘截鐵地跟對方說,一定是他看錯了。
長大後搬出父母家,我和幾個朋友在倫敦合租了一間公寓。那時候,雖然我收入還不錯,有段時間甚至非常好,但花錢如流水,常常錢剛到手就沒了。不過很幸運,錢來錢去一切都還蠻順利,錢總是有辦法源源不絕地從提款機裡流出來,簡直像自來水一樣。但有一天忽然驚覺:我連在加油站或火車站的小商店裡,都能買到兩手提得滿滿的;刷牙時更是讓水龍頭的水不斷嘩啦啦地流,好像水聲是刷牙時非有不可的伴奏一樣。更離譜的是,開車時,如果錢從口袋裡掉了出來,我竟然連彎下腰去撿都懶。於是我覺悟了:原來我的奢侈、我的浪費,是對父母親克勤克儉的一種可笑反抗。不過卻也同時意識到:原來父母發揮得淋漓盡致的「放棄藝術」,不僅是基於儉樸的美學原則,還基於實際效用--為了讓享受達到最優化。
最早提出這種理論的人是伊比鳩魯:人要節制享受,並不是因為感官享受不好,而是為了要避免過度放縱後,隨之而來的惡果。對伊比鳩魯而言,暫時放棄享受,其實是為了提升享受的能力。一味縱情享受的人,到後來,無論得到什麼再珍貴的東西也會覺得索然無味。經濟學家稱之為「邊際效用遞減」:到達某個高峰或最高點之後,無論再怎麼增加都無法產生差別了。比方說,像海涅•帝森這麼有錢的富翁,他在客房廁所裡多掛一幅畢卡索真跡,會讓他覺得生活品質提高許多嗎?再打個比方,如果讓尼可•佛度每個禮拜專程飛去阿拉伯,陪酋長的兒子打幾個小時的高爾夫,你想,富可敵國的阿拉伯王子會覺得這件事有什麼了不起嗎?
在目前這個供給過剩的社會裡,消費者註定要失望!整個經濟體系不斷透過各種越來越精緻的洗腦手法,企圖叫我們相信:幸福是可以購買的。但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這根本是謊言。許多健康食品,從充滿異國風情的印度茶到纖體巧克力布丁,消費工業不斷企圖要矇蔽我們。所以,無可否認的:我們需要一個全新的「奢華概念」!無論擁有多少金錢和物質都無法讓你獲得富足,唯有「觀念正確」才能獲得真正的富足。
這些觀念包括了:願意放棄--放棄所有人都在追求的東西;自主性--不拿別人的生活標準來衡量自己的生活;正確的態度--經濟狀況走下坡,並不代表天要塌下來了,它反而是一種契機,是我們改善生活型態的大好機會。就像馬克思•弗里斯所說:危機是種特殊的生產狀態,只有處在災難威脅中才能體會。
在這個強調一致性、標準化的時代裡,或許危機就是轉機,我們應該在這一片和諧之中攪個局,也就是說:不要再聽信那些行銷伎倆了。雖然咖啡連鎖店不斷向我們推銷「超頂級」特調咖啡,但我們沒道理非聽不可啊!我們還是可以大大方方地點杯黑咖啡,既不要糖也不要奶精。難道,只因為行銷部某位仁兄在狂喜中突發奇想,決定叫一般的杯子做「出色超級杯」,大家就非得要跟著他這麼叫?還有就是「芝麻菜」的例子:原本,再前衛的沙拉都不會想到要放芝麻菜,因為這種菜的味道實在太苦。後來不知道哪個天才,竟然用義大利文Rucola來取代德文的Rauke。從此之後芝麻菜便謂為流行,德國境內幾乎沒有一道菜不「加進」或「擺上」芝麻菜的。在德國景氣最好的「新經濟榮景」期間,全德國從北到南,從漢堡的愛彭多夫到慕尼黑的綠森林,所有人都一窩蜂流行吃芝麻菜。為滿足超高的市場需求,布蘭登堡和麥克倫堡—佛波門附近的農民簡直全卯足了勁種植芝麻菜。
「變窮」就是「優質管理」
只有一種方法能讓你縱使沒錢也很富裕,那就是:先把自己的各種需求徹底檢查一遍。看看有沒有哪些需求,是你沒有它反而會更富有的。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比方說:手機。你真的需要手機嗎?當今之世,失聯似乎成了一種特權。難到唯有賓拉登之徒才享受這類特權的資格?還有網路,你真的需要網路嗎?世界銀行的總裁詹姆士•渥芬森竟說:最窮的窮人都應該有獲得乾淨飲水權利,以及自由進出「資訊高速公路」的權利。也就是說,沒有辦法接觸網路的人,就像是被新經濟革命摒除在外一樣,只能淪為數據時代最等而下之的人。但讓我們回頭想想:透過網路和全世界的同好聊天,玩線上遊戲,這真的是生活必需品嗎?或者,其實好奢侈?也許,如今最大的奢侈,反而是能夠不在乎這些東西,能夠放棄它們?古希臘時代總用「白痴」來稱呼那些不願意參與公共事務的人。但今天,在這個所有人都跟社會脈動息息相關,每個人都被公共事物團團包圍的時代裡,「白痴」的意義或許跟當初的意義剛好相反。如今,沒有能力從社會網絡的牽絆中抽身的人,才叫白痴。
其實,當我們被迫不得不跳脫開來,不得不對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做一番總檢討時,我們反而有機會認清,什麼才是生活中最彌足珍貴、真正奢侈的東西。「變窮」能讓我們學習到,如何判斷事情優先順序,如何分辨出什麼才是最重要的。套句專業經理人的話--他們這批人「最懂」效率了,如今的天下幾乎全掌握在他們的手裡--:我們終於可以重新把重點放在核心業務上,並且進行「優質管理」。就像企業界現正推行得如火如荼的「緊縮成本」政策一樣,我們也應該以此因應現代生活。該怎麼做,才能過得既節儉,又能贏得生活品質?--別急,讓我在書中為你慢慢剖析!
首先我必須聲明,我絕對無意毀謗任何一種休閒事業或享受,連影射的意思的沒有。我只是想要對某些現象提出一些質疑--這應該沒問題吧!現在大家一窩風流行短期度假,難道沒有別的事情比它更享受了嗎?難道大吃大喝那些所謂的「美食」,真的就很享受了嗎?或者--其實更像是活受罪?我們原本寄望透過這些活動能讓生活變得更美好,絕不是想把生活搞得更糟糕。「享受」原本是促使人類願意和世界接觸的重要動機。沒有了快樂、不能享受,人類的心靈就會枯萎。只有懦夫和假道學才會說,我們應該捨棄物質,謝絕任何形式的享受,並遵循苦行、徹底禁慾。就像戴奧吉尼斯那樣,自願過著髒兮兮的苦日子,選擇住在桶子裡,對一切都無動於衷,拒絕任何形式的舒適。其實像他這樣子的苦行,根本不能叫做藝術,所以也就無從衍生出我所要提倡的「放棄藝術」了。真正的藝術是一種能力:首先要能分辦什麼是真正的美好事物,其次要能拿捏分寸,懂得如何讓自己將這些美好事物享受到最高點,最「恰如其分」。所以,放棄的藝術--其實是贏得「真享受」不可或缺的大前提。
如果真想擁有優質享受,優質的幸福人生,有項原則必須牢記於心:一個人越任性、依賴的東西越多,就越容易感到貧窮。因為他會老是處在不滿足的狀態中。許多有錢人其實都活得很貧窮--絲質襯衫熨得不夠平整,總統從他身邊走過沒跟他握手,轎車司機滿嘴蒜頭味--反正看什麼都不順眼,覺得什麼都不對勁。絕大多數的富人都過得很不快樂。有關這一點,我們每個人都該好好反省,因為,跟其他地方的許多人相比,我們已經算是有錢人了。那些看起來還蠻快樂的有錢人,通常是比較懂得「自我節制」的人。無論是早上那杯「非喝不可」的卡布奇諾,或是查爾斯王子吃飯時一定得隨身攜帶、「非它們不可」的銀製刀叉,其實都沒有那麼重要;「非它不可」--說這種話的人,其實是在自動投降;想以個人力量對抗庸俗、霸道的大眾文化,勝算的確不大。如果真想獲勝,關鍵就在:你要讓自己「沒它也行」,千萬不要認為,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是非它不可、絕不可以放棄的。
為了對抗非理性的消費意識,本書將提供一些「生活藝術」供大家參考。若能適時學會,並成為「沒錢也不改其樂」的人,那麼你很快就能成為眾人艷羨的新時代菁英了。新時代來臨後,日子過得不順心的,將會是那些家有恆產的人,他們將一天到晚害怕失去目前的優勢與財富。所以囉!擁有越少的人,失去的也就越少。如果,你也能擁有像納博可夫一樣的自信,那麼你什麼也不需要,就能成其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