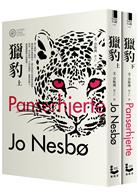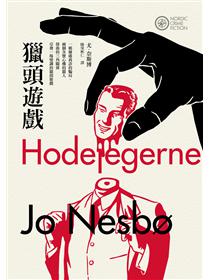【一】1972-1981 傳說(短篇小說集)
【上卷】仍然在殷勤地閃耀著/強說的愁/怎一個愁字了得/緣/女之甦/儷人行/陌上花/喬太守新記/蝴蝶記
【下卷】扶桑一枝/青青子衿/子夜歌/春風吹又生/思想起/臘梅三弄/五月晴/剪春蘿/某年某月某一天/椰子結在棕櫚上/傳說
【二】1977-1979 淡江記(散文集)
【第一卷:陽光歲月】牧羊橋‧再見/販書記/人世微波/有一段路像這樣/錯裡錯/桃花潭水深千尺/鐘/清明節/風箏的話/星期六的下午/招財進寶/寫在春天/如霧起時/假鳳虛凰
【第二卷:風吹花開】大風起兮/如夢令/江山美人/相見歡/無題/談《赤地之戀》/梨園素人/仙緣如花
【第三卷:天地情兮】我夢海棠/鵲橋仙/長亭更短亭/之子于歸/花問/月兒像檸檬/懷沙
【三】1982-1987 炎夏之都(短篇小說集)
【上卷】畫眉記/伊甸不再/安安的假期/最藍的藍/風櫃來的人/最想念的季節/這一天/荷葉‧蓮花‧藕
【下卷】敘前塵/外婆家的暑假/童年往事/柯那一班/桃樹人家有事/炎夏之都/世夢
【四】1988-1990 世紀末的華麗(短篇小說集)
柴師父/尼羅河女兒/肉身菩薩/帶我去吧,月光/紅玫瑰呼叫你/世紀末的華麗/恍如昨日/失去的假期/日神的後裔
【五】1980-2003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雜文集)
【輯一:前三三與後三三】燙手的熱山芋/無事/華崗的夜/折楊柳/記得當時年紀小/尋春問臘到蓬萊/碧螺春/我夢且不言/采薇‧采風/月入歌扇‧花承節鼓/衣香/夏釣/提筆/伯利恆的星/戲外戲/他/有所思/竹崎一日/想做/七樓的天空
【輯二:如是我聞】一杯看劍氣/玲瓏塔來塔玲瓏/鳳凰花發海南天/如是我聞/人身報得/有信‧有仁/女孩/同修同行,同福同慧/與石頭相遇/弱點的張大春
【輯三:蜚長流短】賴聲川的戲/我們能,大陸也能/另一種戰場/我也成了觀光客/從《人間》想起/馬尼拉的落日/陳先生和他的書店/抓住字/關於「台北的銀座」/一個舞台兩齣戲/《武惡》的魅力
【輯四:單身不貴族】說明一下/女人與衣服/關於吃醋/旅途中的男心/第二代探親/從不是上班族/髮型與心情/日本/做家事/特殊朋友/文學的童年/租屋今昔/小說獎/單身不貴族
【輯五:站在左邊】上言加餐飯/秭歸/走吃千里/陸沉之都/來自遠方的眼光/廢墟裏的新天使/站在左邊
【附錄】舞鶴對談朱天文 / Michael Berry 訪談朱天文與侯孝賢
【六】1981-2000 黃金盟誓之書(散文集)
【輯一:家,是用稿紙糊起來的】朝陽庭花聞兒語/寶寶/兩歲/山花紅/我歌月徘徊/素讀《八二三注》/春衫行/雲上遊/吾家有犬/美國舞男/E.T.回家/給爸爸的信/拔牙/家,是用稿紙糊起來的
【輯二:綠楊三月時】記多摩川/一花開/吹夢到西洲/隴上歌/俺自喜人比花低/綠楊三月時/四本書
【輯三:重逢】老地方/惜歲/外公的留聲機/拍片的假期/遇張/重逢/桃樹人家/家有小老虎/歲末的願望/聞吠起舞
【輯四:記胡蘭成八書】獄中之書/懺情之書/優曇婆羅之書/黃金盟誓之書/神話解謎之書/彌撒之書/阿難之書/忘情之書
【輯五:父後三年】做小金魚的人/揮別的手勢/花憶前身
【七】1982-2006 最好的時光(電影作品集)
【上卷:電影本事、分場劇本】小畢的故事/戀戀風塵/悲情城市/好男好女/南國再見,南國/海上花/千禧曼波/咖啡時光/最好的時光/紅汽球的旅行
【中卷:一部電影的開始到完成】源起/劇本討論/拍攝/剪接/出片
【下卷:關於電影】下海記/我們的安安呀/拍片隨記/初論侯孝賢/記夏威夷影展/《童年往事》製作/《青梅竹馬》訪蔡琴/金沙的日子/請注意大陸電影的發展/楊德昌與侯孝賢/給另一種電影一個生存的空間/電影與小說/明伯伯/一杯看劍氣/《悲情城市》十三問/歲月偷換了東豐街/寫給小川紳介/雲塊前接法/新的碑誌/這次他開始動了/《海上花》的美術製作/《海上花》的拍攝
【八】2008 巫言(長篇小說)
【第一章:巫看】巫看/菩薩低眉/世紀初/不結伴的旅行者(1)/不結伴的旅行者(2)
【第二章:巫時】不結伴的旅行者(3)/巫時/E界
【第三章:巫事】巫事(1)/e-mail & V8/螢光妹/巫事(2)
【第四章:巫途】巫途(1)/不結伴的旅行者(4)/巫途(5)
【第五章:巫界】二二九/二二九,浣衣日/巫界(1)/巫界(2)/巫界(3)唐諾導讀:關於《巫言》
作者簡介:
朱天文
山東臨朐人,1956年生於高雄鳳山。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出身文學家族,高一即開始寫作,曾主編《三三集刊》、《三三雜誌》,並任三三書坊發行人,現專事寫作。1982年,朱天文因為在報刊發表小說〈小畢的故事〉而與陳坤厚、侯孝賢結識,從此與台灣「新電影」導演、編劇、影評人往來頻繁,多方參與新電影的發展。自1983年與侯孝賢合作《風櫃來的人》之後,成為長期的合作夥伴,期間不斷出版和新電影導演所合作的電影劇本及原著小說,與電影各自成為獨立的作品。
曾獲聯合報第一屆小說獎第三名、中國時報第五屆時報文學獎甄選短篇小說優等獎,1994年並以《荒人手記》獲得首屆時報文學百萬小說獎。著有小說集《喬太守新記》、《傳說》、《小畢的故事》、《最想念的季節》、《炎夏之都》、《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電影小說選》、《花憶前身》,散文集《淡江記》、《三姐妹》、《下午茶話題》,電影劇本《戀戀風塵》、《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好男好女》、《千禧曼波》、《珈琲時光》、《最好的時光》、《紅氣球的旅行》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名家談朱天文
◎丁亞民:約是日本語吧,有句話是「女心」,這兩字望著真好,天文的人是那樣深那樣曲折婉轉,真是那女心無限了。
◎王德威:因著對官能世界的誘惑有著由衷好奇,對時間及回憶的虛惘有著切身焦慮;朱天文最好的作品掌握了道德與頹廢間的二律悖反關係,使她的世紀末視野,超越了顧影自憐的局限。
◎胡蘭成:那些好句子都是天文的人。
◎袁瓊瓊:天文的柔情大概託在散文裡;小說就一直地簡潔俐落,沒有忸怩之態,不帶廢辭廢筆,有種泱泱大氣。
◎黃錦樹:朱天文不僅從胡蘭成那裡習得神姬之舞而已。而是學了一整套的世界觀、認識論,它提供了一個整體的觀照,包含了文明/文化起源觀、歷史觀、美學觀等等...她的「後四十回」寫作修行毋寧是緘默的,她的關切不在那些易逝的、流變的「現象」,而是一些更為「本質」的事物。
◎詹宏志:一逕描寫熱鬧的、炫目的、芳香的事物,卻透露了腐爛前、衰敗前的有機分解,這位技藝圓熟、見解融達的朱天文是來到她寫作生涯的高處了。
◎舞鶴:在生活中,朱天文「讀物閱人」,物不離人,書寫來自她對「現實存有」的熱情;「物的情迷」正是她小說的特色,這種情迷頗似所謂「物之哀」,它也使作品中常出現的類「博物誌」書寫具有文學的美。
媒體推薦:
朱天文用《巫言》雕出心中的龍 /2008.01金石堂《出版情報》.文 蘇惠昭
還是從胡蘭成說起。
農曆年前好長一段時日,朱天文伏匿在家中校稿,夜以繼日,由最早的《傳說》開始,依時間序是《淡江記》《炎夏之都》《世紀末的華麗》《有思,乃在大海南》《黃金盟誓之書》《最好的時光》,以及她創作七年多,方才完成的二十萬字小說《巫言》,八本書跨越三十多年,如果以25歲作為分界點,25歲之前的作品如今讀起來,「哈!濫情到像神經病。」朱天文感覺到臉微微發熱,狠狠刮了自己一頓「如果不是為了存檔,留下紀錄,我寧可拿去銷毀。」
朱天文25歲那年,胡蘭成去世,而她開始下山。是的,下山。因為一段仙緣,朱天文姊妹親受胡蘭成調教,「吟哦詩禮中國,想像日月江山」。胡蘭成扮演智慧老人,賜給青春正盛的朱天文姊妹視野和高度,並且呼一口仙氣,把一生學問的總結灌進「三三集刊」一群才情洋溢的少男少女腦袋裡,「就像畫龍點睛吧!他點了睛,但我們卻還不知那龍長什麼樣子。」
張愛玲與胡蘭成,張愛玲的文學如今受到神樣的供奉,而胡蘭成至今還仍歸不了檔。
那麼對創作者來說,朱天文問自己,那樣輕而易舉就空降在顛峰,這究竟是幸還是不幸?她不敢給答案,只知道25歲以後自己就開始下山,一直一直的往山下走,求知識,累經驗,「花了快三十年只為了去畫出那條龍」。
朱天文以文字畫龍。
《世紀末的華麗》是朱天文畫龍的第一筆,「勾勒都會意志下疲憊眾生的存在狀態和精神狀態」文學評論家黃錦樹語;《荒人手記》如同「某類現代知識分子的懺悔錄」,這一短篇一長篇,黃錦樹都將之讀成「朱天文對『蘭師』的致敬致祭之文」,對朱天文來說,這也都是「畫龍」的過程,她越來越清楚看見龍的樣子,但要精確描述那龍,就必須「格物」,致知於人世間每一件細瑣俗凡的人情、物件、故事,不可思議的是,這又是她在與主流社會幾乎隔絕的狀態下靠著大量閱讀、日行餵貓溜狗和偶爾的出門或旅行完成,「我越來越是一個觀察者,包括觀察自己」,這也是朱天文七年多來寫作《巫言》的背景。
站在社會邊緣的邊緣觀看一切也明白一切,這樣的人即巫,而巫人的書桌即是巫界,朱天文伏首巫界以文字召喚意象,意欲寫出「巫事」與「巫途」,有時候沒日沒夜的於紙上施法,有時候又飄然他去,是以荒疏許多時日。
巫人寫紅酒族:「她們節衣縮食,練得一口紅酒經。其實她們喝紅酒的歷史老早在酒商炒作之前,為了酒裡的單寧酸說是健身、瀝脂而喝起來的,當時她們更喝別的酒。又其實喝酒是餘事,酒杯,才是主題。她們嚴格區分白蘭地酒杯、葡萄酒杯、香檳杯之間的差異」。巫人寫馬市長:「……故而存活下來的首長物種中,仔細考察,馬市長的眼睛是關上的。初步研判,因為帥,他不能打開眼睛。一打開,就會放電。為免電著群眾,以及自群眾迴向回來的電擊倒自己,馬市長將眼睛偽裝成淡漠無神的三白眼即、豬眼,形成了絕緣體、防護罩。」
更多時後巫人是在「我」的小宇宙裡穿行和考掘。
終於完成那一刻,「寫完了」朱天文用平常的語氣對朱天心說。朱天心驚問:「妳是不是該戲劇性一點?」
50歲,交出《巫言》,朱天文下得山來,在平闊無風的大地上,雕了一尾自己的龍,點上眼睛。
名人推薦:名家談朱天文
◎丁亞民:約是日本語吧,有句話是「女心」,這兩字望著真好,天文的人是那樣深那樣曲折婉轉,真是那女心無限了。
◎王德威:因著對官能世界的誘惑有著由衷好奇,對時間及回憶的虛惘有著切身焦慮;朱天文最好的作品掌握了道德與頹廢間的二律悖反關係,使她的世紀末視野,超越了顧影自憐的局限。
◎胡蘭成:那些好句子都是天文的人。
◎袁瓊瓊:天文的柔情大概託在散文裡;小說就一直地簡潔俐落,沒有忸怩之態,不帶廢辭廢筆,有種泱泱大氣。
◎黃錦樹:朱天文不僅從胡蘭成那裡習得神姬之舞而已。而是學了一整...
章節試閱
凝視朱天文──舞鶴對談朱天文(2-1)
舞 鶴:九四年《荒人手記》後,妳避居家中,極少公開活動,十年熬成「巫」,令人欣喜終於「巫」開口說話了。成巫的過程如何,安坐巫位感覺鄭重猶帶輕微的騷動嗎或悲欣交集,長篇《巫言》的動機、慾望是什麼?我閉居淡水那十年,長期處於「無言」中,最後幾乎不能開口說話,之後十年也似「巫言」說個不停,其實在蘊淌著的仍是無言之流。
朱天文:其實《巫言》目前只寫了一半,所以我還在坐牢,完全被它禁錮住的,不得脫離,我希望今年能寫完,就脫離它自由了。九四年寫完《荒人》,我快樂跟好友們說,可以去當白癡幾年了。白癡的意思,是相對於寫小說時候的狀態而言。如果說,一字一字在寫小說的時候是動員了我整個人的全部,那麼非寫小說狀態時,不管是看書,再難再難的無論什麼書,或不管是被逼寫些文論雜文,或寫電影劇本,我簡直都覺得不過只動員到整個人的表皮部分。真的,就是表皮。是個感官的人,常識的人,即便寫,是寫我已經知道的。只有寫小說,恐怕才有機會,寫我以為我自己都不可能會知道的。巫之為巫,也許是在能夠動員到那未知無名的世界,將之喚出,賦予形狀和名字。
這動員的狀態,令人怯步,總以自己還沒準備好準備夠做理由,四處晃盪當白癡,料不到一晃十年。再提筆,你問我慾望是什麼,是癮吧,巫癮。動機呢?我覺得白癡歲月應該結束了,否則,我會真的成了一個無用的人。在〈花憶前身〉裡,我說寫完《荒人》是我對胡蘭成老師昔年教誨的悲願已了,花之前身,黃錦樹曾評論嚴厲指出,這是毫不保留攤開底牌了,會不會從此格局已定難創新局。幸好眼前有你為例,當時你決定結束淡水十年閉居,似乎是,知道自己的時間表到了,出關下山。若沒有那十年,就不會有後來的你那幾本書。我但願我也能夠是。
舞 鶴:〈巫看〉中,悟境迷情常發生於目光相對之時,神來之筆也常落在目光相對之處,電光石火不忍、不能、不捨多看,是「低眉」隱藏的更深含意嗎?〈巫時〉最後也有如此目光一對,引發隨後整章〈E界〉。
朱天文:是的,有句俗爛之極的話說,「多情卻是總無情」,也就是低眉吧。因為你知道,抬眼去看時,意味著你已開始接納,跟付出。這接納付出是不可能半途而廢的,它是負擔,是責任,即便對方終結了,你這一方甚至還無法終結。你深知那負擔之重,所以只好慎始──低眉吧。也許這是我一生要修的功課,人我之際,物我之際,我總是困在其中。
舞 鶴:「物的情迷」是妳小說的特色,〈巫看〉中挽救廢棄物轉向「永生重生投胎再生」十分動人,猶如荒人養魚同其生死,這種情迷頗似所謂「物之哀」,它也使妳常出現的類「博物誌」書寫具有文學的美。我一向無心於物,後來無心於人,書寫于我是無心假借、弄假成熱情,但這熱情只止於書寫。在生活中,妳「讀物閱人」,物不離人,書寫來自妳對「現實存有」的情熱嗎,或另有內在的、神祕的、不可言說的深淵?
朱天文:沒錯,對現實存有的熱情,對物的情迷。這似乎是所有女性的天賦,不獨我然。只不過我永遠被無以名之的各種細節所困,在現實生活裡糾纏得拖不動,這也是為什麼,只好垂下眼簾不去看。我父親曾講他小時候親族裡有一個陰陽眼小孩,黃昏到來就早早躺上床闔上眼睛免得看到許多東西,很痛苦,後來英年早逝。物之情迷,是不是會內化為你說的內在的,神祕的,不可言說的深淵呢?逐物迷己,我好像活在一個泛靈的世界裡,連塑膠都有靈,這種人是不是畸人,幾近乎精神病?
舞 鶴:〈巫看〉魅影畫龍點睛,何妨多說幾句有關「魅影」。
朱天文:《歌劇魅影》的魅影,用你的話說是,「更明的亮光同時更深的暗影」。舞臺上魅影永遠戴著骨白色面具,造成亮的部分更亮,暗的部分更暗的,絕望的效果。魅影又錯誤,又失敗,此二者卻引動著巫者抬起眼簾,寄予深凝不移的注目。
舞 鶴:「格物」很難,活用「格物」在小說敘事中更難,必需適切地拿捏精細入博大。〈世紀末的華麗〉格了服飾時尚,《荒人手記》格了同性戀衍及的知識,《巫言》可能格了現象不忍看的。在我,往往書寫前以「小說田野」的方式進行一段長時間的格物,有意無意間在日常中格物,累積到一定的厚度深度它自會吵著進入書寫。如此格物當然比不上妳類「專業式」的格物。很早以前妳就意識到「格物」的必要嗎?如何下功夫「格物」,妳發展出一套方法將「格物」運作在書寫嗎?
朱天文:你提出格物很有意思,好像沒聽見過誰這樣來談小說。格物對我而言,也許是本能。
波赫士有一篇小說叫〈強記者傅涅斯〉,描述傅涅斯在一次一匹灰藍馬把他摔下來的那個落雨的午後以前,他跟大部分人類一樣,眼盲、耳聾、嘴啞、心裡恍惚、記憶模糊,從馬上摔下來,他失去了知覺,醒來時,眼前的一切顯得既龐雜又鮮明,強烈到他承受不了,連最遙遠、最瑣細的記憶也是。好比人們平常可以看見一張桌子上的三個杯子,傅涅斯卻可以看見一株葡萄樹藤上所有的葉子、捲鬚和葡萄。他默記著某年某月某日破曉時分南方天空雲朵的形狀,且這些雲朵馬上跟他僅看過一次的某本皮革封面上的紋路並比,跟某次戰役裡一支船槳在某河划起的線條比較。而且他的每一個視覺意象都跟力感、熱感等相關連。他可以掌握一直變幻不停的火焰不可勝數的灰燼,一次時間拖長的守靈過程中一個死人的許多不同的臉部變化。他可以持續不斷辨識出腐爛、疲憊的寧靜進展,能夠察覺死亡、潮濕的推移。他是世上唯一澄明的觀察者,能夠在一瞬間觀察到一個形式繁複而同時並存的世界,其精密程度簡直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但是,但是別忘了,他幾乎沒有能力做一般性的抽象思考。好比狗,他難以了解概括性的符號狗字,是代表那麼多大小形狀不同的狗。三點九分從側面所見的狗,三點十分從前面所見的狗,兩者名稱竟然相同,令他困惑不解。思考是在忘記差別,做一般化、抽象化的工夫。而在傅涅斯過分豐饒的世界裡,除了細節和緊密相連接的局部細節以外,別無其它任何東西。
這故事也許可以當做是一個格物的極致,一個隱喻。我會感同身受,因為有時也到了簡直承受不了的地步。再說一次,所以菩薩必須低眉。也許,書寫反而給了我機會,讓我能夠把細節作一番思考。
舞 鶴:第二部分〈巫時〉四章,文字內涵各自獨立,像四種不同風格的演示,前兩章貼近書寫者的生活,由個別經驗發展到「吾身」生活的整體層面,更將自身投影到與書寫者生活迥異的生活場域「E界」,最後特寫青春小兒女的情感糾結。E代世界相反吾身生活,小兒女恩怨大異於第一章智識座談,文字的質感、節奏、氛圍精準展現出分殊的內涵,相反相成了〈巫時〉吾身。在此,是否有意呈顯書寫者駕馭各種敘述文體的能力,或是讓業已熟練的各式文字風格作一回統合展示。
朱天文:沒錯。《巫言》是寫到三萬字的時候,才確定可以這樣寫下去了。兩條平行線,一條是巫者其人其事其生活,一條是巫者之言,即、他寫的小說。你看他生活過成那副德性,他會寫出什麼樣的小說呢?他生活裡的元素如何相關不相關的轉化為小說。其間的思維,跟想像力。
舞 鶴:書寫新潮、前衛的題材,需要足夠的認知和勇氣,就「創新」而言十分可貴。但,是否讀者必需先作功課,勤讀賽車雜誌勤看電視賽車節目才能讀懂〈E界〉著迷的「一級方程式」,最好先讀工具書《迷幻異域》、《搖滾怒女》才知道為什麼「快樂丸英格蘭」、什麼是銳舞中的「硬蕊」,這好比讀者必要一定程度理解李維史陀和傅柯,才可能領會《荒人手記》中對兩人獨到、精闢的見解。類此,妳認為是普遍性的知識和現象,或是「敘事認同」原本既存於書寫中,都不是問題。
朱天文:是的,我認為敘事認同已存於書寫中,不成問題。事實上,小說家如果有特權,這算是他的特權吧。他完全可以不採用推理的手段而抵達結論。不必交代出處,不必做註。甚至誤植,錯讀,譬如錯讀李維史陀或傅柯,借他當跳板一躍而遨翔,六經皆我註腳。這方面,我是毫無愧色在使用特權的。
舞 鶴:回頭看短篇〈尼羅河的女兒〉,就了知十幾年後妳在〈E界〉、〈螢光妹〉仍保持著對時尚新潮青春世代的好奇心。對照二十幾年前的〈家‧是用稿紙糊起來的〉,〈巫時〉中的家庭生活世故滄桑中有一雙灰漠慵迷的眼睛在凝看。我總覺得〈E界〉後兩章可以寫得更好,不因貼切題材的節奏、強拍而減弱了創新妳獨有的特色,容我這麼說,一個真正走過E界的文學青年若有創作天分他會寫出這兩章。
朱天文:〈E界〉和〈螢光妹〉的來源,是兩年前參加電影《千禧曼波》劇本工作時遇見的人跟事。我始終感到還消化不夠,目前只能寫到這樣。說不定全書完成後,再回頭來改這兩章。
舞 鶴:《巫言》長期分散寫作,相較《荒人手記》集中一段時日書寫,兩者的書寫情境感受不同嗎?不同的狀況是否會造成作品的調子、樣式明顯差別,寫完或告一段落時妳清楚知道寫得「好」或「壞」嗎?於我,集中書寫因為長期融入書寫完成時恍恍惚惚不知好壞也不在意好或壞,分散寫作每每都知「寫壞了」「寫得不足」還要修改,變成一種長時間的折磨。會不會是一種「甜蜜的折磨」,所以千方百計延宕書寫。
朱天文:不,絕不是甜蜜的折磨。
如果不算之前零散的棄稿階段,我是二○○○年六月著手寫此長篇,寫了幾個月停下,去參加《千禧曼波》電影劇本工作。次年坎城影展回來拾筆再寫時,靈光一閃把原來的題目《謀殺與創造之時》改掉,確定為《巫言》,寫到年底又停。二○○二年仲春再寫,分篇目,訂出〈巫看〉、〈巫時〉、〈巫事〉、〈巫途〉、〈巫族〉五篇,寫到秋天又停。目前完成的〈巫看〉部分在印刻發表。〈巫時〉部分已拆散在報紙副刊發表。秋天我會寫完〈巫事〉仍然交給印刻。
這分散寫作的幾年間,失去自由如坐牢。每次,倉促火急被借調出牢,做些世間事,做完就拖東賴西的延宕著回牢,同時又被良心譴責催逼,最後只得自動報到入囚。而且完全如你所說,這一拉開距離之後再走入,都是從「唉呀怎麼寫成這副德行」為開始,修改剪貼,也像暖身暖夠了才接續往下寫。所以整個過程似乎是,越寫越漫長,沒完沒了。其實寫好寫壞,當下往往不知,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反而有時越改越乾淨,太乾淨了變成枯澀或疏冷,或越往藝術境界去而過度森嚴。總之,我實在該給自己一個期限喊卡了。
舞 鶴:過往的小說中,妳酷冷的凝看如米亞或熱情的詠嘆如荒人,這兩者在妳的文學生命中可能都有其來源、承傳。如今,幽默一躍成為《巫言》最重要的質素,可能是妳近十年內最大的轉變。嘲諷是我書寫時的本能,因為低調,轉成幽默,也因為嘲諷背後有憤怒很快被察覺出這幽默是屬黑色的。妳覺知屬於妳自己的幽默嗎?幽默但不到「黑色的」,它源自何處,變化的歷程如何?
朱天文:我真高興你說《荒人》是熱情的詠歎,這是第一次我聽人這樣說,因為大多時候它都被看成頹廢荒涼的。而你提出幽默,也讓我受寵若驚,因為我一直認為自己是二楞子。我從來沒覺知過我有幽默。經你這樣一提,想想,你說你是低調,我想我也是。
巫者,及巫者其言,天心最近愛引用卡夫卡的話說:「小說家是在拆生命的房子,拿這個磚塊去蓋小說的房子。」《巫言》好像恰巧在描繪這幅圖像。早先這個長篇叫《謀殺與創造之時》,是馬修‧史卡德探案系列中的一本書名拿來當題目,意思是,生活中你謀殺了些什麼,於是小說裡你創造了些什麼。史卡德的探案過程,根本就像創作過程。現在發展成《巫言》,這拆毀生命的圖像,因為低調,我無法把它描繪成壯烈,連悲傷(對不起用你的書名)都無法,自然也不會叫苦或辯護,最後只能出之以荒謬,和無奈。你指出的幽默,是這個嗎?
舞 鶴:成熟到智慧不自覺轉化為幽默,是一種超越帶著生命的恬美,真正有幽默的書寫都懂得放鬆自我悠遊于書寫這個動作中。舉日本作家為例,芥川龍之介耽溺於個人強烈的藝術性,川端康成執著傳統的美,兩者無意也無能翻越藝術與美築成的高牆,而夏目漱石有幽默,不僅能寫藝術美的作品《草枕》、《夢十夜》,他不攀高他繞過牆角便豁然開朗寫出《三四郎》、《我是貓》,夏目比芥川、川端格局大有大氣,在於幽默。
讀妳的長篇,于我,是一種享受。那種「離題」式的寫法,頗得我心,在我的第一個長篇曾大量使用括弧括弧再括弧、離題離題再離題,當時也有批評懷疑究竟是不是小說,其實守住固定題旨範疇和主線支線的寫法早被顛覆,「精準」早已不是最高的標竿,書寫自由與書寫真實是更為緊要的。「離題」為了自由與真實。我詫異何時妳成熟了這種書寫長篇的觀念。
凝視朱天文──舞鶴對談朱天文(2-2)
●續〈凝視朱天文──舞鶴對談朱天文〉
..........................................................................................................................
朱天文:謝謝你。同業是最嚴格,最挑剔的。你說享受讀長篇,對我真是莫大鼓勵。寫到離題的路上,是像侏羅紀公園裡說恐龍蛋「生命會自己找到出路」,超出你的預想跟掌握,卻可能是最精采的部分。
舞 鶴:內容與形式並重是既成的書寫概念,但小說常因負載過重的內容矮化形式,我特別著意於形式的創新,而這創新具體落實在文字和構句上,文字織網構句、構句滋長構句,後來構句本身彷彿有它自己的生命力,不顧原先書寫怎樣的內容。妳的文字一向典雅並肩華麗,臻於「優美」的極致,不過《巫言》顯然放鬆文字、意象的緊密,疏散內在對極美的自我索求,但維持一貫與內容的協調。這是妳一貫的書寫理念嗎?替內容尋找合適的形式,形式只為內容才有正當的存在,有時我會釋放文字讓它在每個當下自由組構,妳認為這會是一種「書寫的破壞」嗎?妳曾經想過形式可能決定內容嗎,怎樣的形式書寫出怎樣的內容?
朱天文:我比較傾向於,替內容尋找合適的形式,形式只為內容才有正當的存在。但這個說法,可以再說得細膩些。
就說《巫言》,最早廢棄掉的一些開頭有叫《往星中去》,有叫《瓦解的時間》。一九九九年春末我從紐約回來,在紐約時曾完全變成一個癡心的書迷按私家偵探史卡德的生活動線走逛了一趟,回來很澎湃。覺得史卡德的所有探案過程,可與一個小說家的創作過程,並比對照來寫,就定名《謀殺與創造之時》。有幾個月,我就把手邊能找到有關紐約的書都找出來看,重看張北海的全部書,各種深深淺淺的遊旅書,紐約建築的書結果岔途去看了好些建築書,重看十四本史卡德探案並作筆記,書桌上舖滿一大張紐約市地鐵圖。當時我想做的似乎是,就像有一種錶做成透明狀把內部的齒輪構造暴露可見,我也想把創作過程暴露可見,同時既是構造同時又是成品。但這個,我又一點也不想用後設的寫法。有句話說,孟賁力大但無法把自己從地上舉起,同理,小說成品能夠同時分析小說自己嗎?這其實根本不是個事,我顯然庸人自擾,但不知為何,當時對我卻極具魅力,蠢蠢欲動在那裡的,只是不知該如何賦予它形狀。
而浮在眼前的意象,就是一張目光含在低垂眼簾裡的臉,名之為菩薩低眉,就從這裡下筆開始寫。一直寫到三萬字左右,我才確定,沒錯,就是用這種寫法寫下去,我高興跟好友說,我找到容器了。
這個容器,用到目前為止,它幫我至少解決了之前很長一段時間我克服不了的難關(所以棄稿數次),就是說,我無法用單一一種敘述觀點,單一一種敘述腔調,來完成一部長篇。以後怎樣不知,至少目前這個階段,用統一的敘述觀點跟腔調寫長篇,對我是不能成立,也無法支撐下去的。
所以從順序上來看,似乎是先有蠢蠢欲動的東西,然後想盡辦法把那東西叫出來賦予形狀。然後,最好的時候,你又覺得這個形狀就是這個內容,不可能還有內容了。然後我了解,作家成熟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他肯定會有一個念頭:把順序倒過來。就是說,給自己設下限制,佈置障礙,定出一些奇怪又嚴苛的遊戲規則,逼自己放棄一向嫻熟的伎倆,沒辦法了,因而逼生出來什麼新東西亦未可知。這是形式決定內容的可能性嗎?成熟書寫者至少都有過這種書寫破壞的慾望和意圖吧。這方面來看,你跑得比我野,也比我遠。
舞 鶴:書寫往往是當下寫就的,這「當下」有謂之「即興」,從來「即興」一直被認為是創作的點綴,強調「即興」事實為了成就原有的機制,掌控得宜絕對必要,才算正式才算正經,因此修修改改或下筆有萬鈞重。我早就野放掌控,珍惜當下出現的,它保留了最多的直覺,可能真實就蘊含在其中,盡量我不修飾「當下」。在〈巫看〉的細節裡似乎有些是「當下」在寫作,它沒有明顯「選樣」的痕跡,當然可能選樣不自覺已先藏好以備當下,但這跟事先擬妥綱要細目以及事後一修再改是不同的。在「當下」與「掌控」間妳如何安位。
朱天文:其實最過癮的時候是失去掌控力的時候,即興當下帶著你跑,說它是起乩也罷,是下筆如有神助也罷,如果書寫這件事有回報,這個就是回報。可惜年紀越大,成熟度越高,這種回報來得也越少。
舞 鶴:我書寫時,從未考慮「好讀」或「可讀性」,唯在顧及題旨時作必要的「節制」。《巫言》較《荒人手記》好讀,書寫前妳思考過新作的可讀性嗎?
朱天文:應該這麼說,我是在做削去法,削去所有我已經厭煩有的甚至快到受不了要銳叫
地步的東西。譬如《荒人》裡的那些「四字真言」,有說是森嚴的寶石切割原則,鍾阿城是說以詩在寫小說,密度高──太高了些。我就想擺脫它因此用大白話來寫一次看看。又譬如《荒人》裡談生談死,檢點靈魂,這我也想擺脫。更別說情慾書寫,夢境潛意識之類了,我就想,不碰「性」一個字,看會寫出什麼來?阿城一本書叫《常識與通識》,我想試試貼著常識面來寫如何?還有,我說喂,不要用工具書,不要用典。我還把括引給侯孝賢導演的一句廣告詞拿來規範自己:「深度是隱藏的,藏在哪裡?藏在表面。」我想試試只寫表面。以上這些,是我有意識在做的,做下去當然不見得全是。我不知這些是否構成了你說的可讀性。
舞 鶴:妳有句名言「我寫故我在」,創作于妳是以全生命的。年少以來我也如是夢想,不過十年淡水極簡、疏離的生活洗掉了太多,禁忌的以及執迷的,現今,我在具足,也不反對文明教育人生需有「具體的存在意義」,活著至少做一件事,最好是自己可以做得最好的那件事。妳仍以全生命書寫嗎?
朱天文:你引我的句子我寫故我在,是在虧我了。這個《荒人》的姿態,多麼狂誕,如今令我也臉紅。就像你十年淡水洗掉了種種,如今其實除了寫小說,我什麼也不行,離開小說,我是個無用之人啊。
舞 鶴:我一向不喜「知識分子菁英的」,我到部落魯凱、泰雅現今在阿美,多少有意掃除自己太藝術、太文學的,當然不帶十九世紀末延到二三○年代知識菁英放逐自己到普羅大眾的「拯救」、「贖罪」的執念,但我自然相與親近的是所謂少知識的「平民」,我書寫的人物幾乎全是「低下階層的」平民,我在小說中從不引用學術大師也不作知識論述。在知識普及的今天,問題不如以前那般嚴重,然而區隔還是存在的,「平民」自古以來不親文字,文字在他們的生活中不是必需品。妳為誰而寫?妳的作品顯示書寫者是個知識菁英,超高水準的,或者這對妳從來不是個問題。
朱天文:我很羨慕你能寫低下階層平民,這一塊世界我毫無辦法,只有投降的份。老實說,一旦進入小說動員狀態,我只能全神貫注從渾沌之中設法喚出形狀,只能做這件事,他顧無暇。我是今天寫時,從前面順下來看一次,檢查昨天寫的草稿,一邊謄清一邊修改,然後繼續往下寫草稿。檢查時,是用自己的鑑賞力在檢查,或我心中一些高手的眼光在檢查。若這些眼光是讀者,他們就是。說我是為他們而寫,也可以。基本上,寫文論雜文或電影劇本,我是力求溝通,甚至有很清楚的一群溝通對象。寫小說,是無意於溝通的。
舞 鶴:九○年代後,妳的書寫頗具「世界性」,妳的長篇內含了無數世界各地的「著名土產」,目今資訊通路如猛獸橫行,可能「世界性」或「全球化」才是正當的。八○年代我閱讀愈廣泛愈把自己侷限在所生所長的土地,九○年後重新書寫小說只寫這個小島台灣,我非看重意識強勢的人所以並非「本土意識形態」在操控,單純因緣這土地是我成長熟悉的,而熟悉中深藏著更多的陌生,我決定優先去熟悉這些不知有多少的陌生。有時,我也難免懷疑這種「地域性」、「區隔性」是否窄化甚至窒息了書寫,正如有時我也疑惑為何妳的小說除了極小部分的都會台北外很少觸及台灣。
朱天文:說老實話,我只能寫我熟知,有感的。換言之,我不是不寫,是沒有能力寫,不會寫,也寫不來。非不為也,不能也。至於地域性區隔性,我以為,越是全球化,越是要並存地域性區隔性。這在生物學上,是偉大的生物多樣性,絕對需要珍惜持護的。何況舉世滔滔不可擋,若不是有足夠的自覺,簡直會對一己之獨特性實踐不下去。我敬重你的自覺和選擇。我寫巫者,但願也能呈現出某時某刻某特殊時空下唯一只在台灣才可能產生的獨特性,在不同面向上,與你的獨特性呼應。
舞 鶴:長篇小說的最大可能在於呈現整體的綜合,多年前我逐漸成形這個理念,一個人生命的總總可以文學的手法融入長篇的細節內,選擇某個題旨範疇只是借用,書寫者自由出入外內,書寫免於沒完沒了,對於如此長篇小說的生命,生活中沒有什麼是白花的,沒有什麼不能寫入一個長篇的。我如是讀《荒人手記》,雖然規模小了些,但根本沒有「賣弄」、「枝蔓太多」、「偽百科全書式」這些批評指謂的問題,它是一個自足的自我爆裂同時自我諧合的小宇宙。若有可能,書寫者一生也只能寫出一部、或兩部這樣的長篇,《巫言》顯然非此類,期盼妳的另一部「書寫生命任何面向、最大可能性」的長篇。
朱天文:是啊,生活中沒有什麼是白花的,沒有什麼不能寫入一個長篇的,這是小說家的幸運,身負一種載體,於是雜七雜八連生活連閱讀連不管什麼垃圾訊息,最終,都會在這載體裡提煉凝融為一種樣貌呈現於世。一個出口。一次權柄,命名的權柄。如今寫作對我而言是,以一己的血肉之軀抵抗四周舖天蓋地充斥著的綜藝化,虛擬化,贗品化。我們有的就是我們真實的血肉之軀。
舞 鶴:未來十年內,妳會完全確立當代重要小說家的地位,是不需謙讓、不必推卻、不容逃避的。而這,必要再書寫至少二三個足堪典範的長篇,必要在成熟之上催促以堅強,強度與韌性。巫者必有非常人的強韌,足以因應內在的不安無明、外在的騷亂動盪。巫說巫言,妳說是嗎。
朱天文:謝謝你。上次見面,你鼓勵我未來十年當寫三本書出來,三年寫一本,其實合理。我因此反省自己過往對於寫作,太恃才太率性了,缺乏責任感也沒有紀律,這是暴殄天物。記得布袋戲國寶李天祿九十歲時有人採訪他,問他總結一生有什麼話要說,他用台語說:「人生要奮志。」我但願像你無言閉居淡水十年,出來後便說話說個不停。我應當要有這個做為巫者身分的自覺。它是一個命定,所以它是一個責任,不容逃避的。
凝視朱天文──舞鶴對談朱天文(2-1)
舞 鶴:九四年《荒人手記》後,妳避居家中,極少公開活動,十年熬成「巫」,令人欣喜終於「巫」開口說話了。成巫的過程如何,安坐巫位感覺鄭重猶帶輕微的騷動嗎或悲欣交集,長篇《巫言》的動機、慾望是什麼?我閉居淡水那十年,長期處於「無言」中,最後幾乎不能開口說話,之後十年也似「巫言」說個不停,其實在蘊淌著的仍是無言之流。
朱天文:其實《巫言》目前只寫了一半,所以我還在坐牢,完全被它禁錮住的,不得脫離,我希望今年能寫完,就脫離它自由了。九四年寫完《荒人》,我快樂跟好友們...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