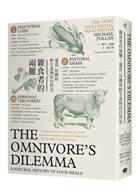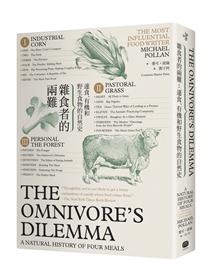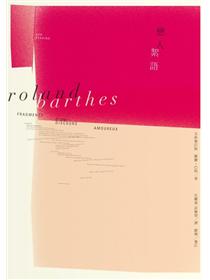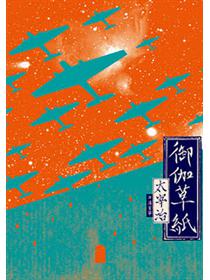一桶阿蒙蒂亞度酒
弗度納托(Fortunato)傷害我無數次我都盡量忍了下來;可是這回他居然敢侮辱我,我發誓一定要報復。不過只要了解我個性的人,就會知道我不是虛張聲勢。我終究要討回公道,主意已經打定了──由於義無反顧地打定主意,讓我完全不顧忌這件事的危險性。我不但要懲罰他,更要在懲罰他之後能全身而退。假如報仇後又給人倒打一耙,那仇就等於沒報。再者報仇的人如果沒讓對方知道你對他的懲罰,那麼仇也等於沒報。
有一點要說明的是,不論在言行舉止上,我都沒讓弗度納托對我的心懷不軌起疑。我一如往常對他笑容可掬,只是他渾然不覺如今我之所以笑,是因為想到他未來悲慘的下場。
這個弗度納托雖然在其他方面都是個值得尊敬,甚至敬畏的人,但他卻有個弱點。他對於自己鑑賞葡萄酒的能力十分自豪。義大利人當中,真正懂得品酒的實在寥寥可數。他們所顯現的熱衷多半迎合時間和環境的需求,頂多只能在英國獲奧地利富翁面前冒充行家。在鑑識繪畫與珠寶方面,弗度納托和其他義大利人一樣,只是個半吊子──但是在陳年佳釀上,他還真是個道地的行家。在這方面我與他在伯仲之間:我自己十分懂得鑑賞義大利佳釀,而且只要有能力就會大量買進。
在嘉年華時節進行得最熱烈的期間,有一天傍晚薄暮時分,我遇見了這位朋友。由於他已經喝了不少酒,便熱情地與我打招呼。他的穿著花俏,一襲緊身的彩條禮服,頭戴一頂掛著小鈴鐺的圓錐形高帽。我見到他很高興,心裡還想,剛才實在不該那麼用力握他的手。
我對他說:「親愛的弗度納托,遇見你可真巧。你今天的氣色好極了!我剛收到一大桶的酒,對方說是阿蒙蒂亞度酒,我卻有點懷疑。」
「怎麼會?」他說:「阿蒙蒂亞度酒?而且一大桶?不可能!何況還在嘉年華期間!」
「我也很懷疑。」我回答。「不過我實在夠蠢,沒先來請教你就付了阿蒙蒂亞度酒的價錢給對方。因為當時找不到你,我又怕錯失良機。」
「阿蒙蒂亞度!」
「我也很懷疑。」
「阿蒙蒂亞度!」
「我一定要搞清楚。」
「阿蒙蒂亞度!」
「既然你有事,我正想去找路哲西。若說誰還有點鑑賞能力的話,應該就非他莫屬了。他會告訴我——」
「路哲西根本分不清阿蒙蒂亞度酒跟雪利酒的差別。」
「可是有些笨蛋卻還是說他的品味和你不相上下。」
「來,我們走。」
「去哪裡?」
「到你家地窖。」
「這可不行,好朋友;我可不能占你便宜,我明白你有事在身。路哲西——」
「我沒事──走吧!」
「這可不行,好朋友;我在意的不是你有事,而是我注意到你得了重感冒。地窖裡潮濕得令人受不了,而且到處結滿硝石。」
「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走吧。感冒根本沒什麼。阿蒙蒂亞度!你上當了。至於路哲西,他根本連雪利酒和阿蒙蒂亞度都分不清楚。」
弗度納托說著就抓起了我的手臂。我戴上黑絲面具,裹緊身上的及膝披風,故意脫脫拉拉地讓他忍不住要催我趕快回家。
家裡沒有僕人;他們都以嘉年華節為由出門狂歡去了。我告訴過他們,天亮前不會回家,並且清楚交代他們不准在屋裡吵鬧。我十分清楚只要這麼囑咐他們,我前腳才跨出門,他們後腳就會一個個溜之大吉。
我從他們的火台拿了兩支火把,一支遞給弗度納托,然後帶領他經過幾個房間,到通往地窖的拱門。我走下一段蜿蜒的長梯,沿路不斷提醒走在後面的他要當心。我們終於走到樓梯下面,一同站在蒙特雷索(Montresors)家墓窖潮溼的地上。
我朋友的步履踉蹌,每跨出一步,帽子上的鈴鐺就響個不停。
「那桶酒呢?」他說。
「還要再走過去。」我說:「不過你注意看窖壁上有閃閃發光的白色網狀物。」
他轉身看我,用醉醺醺的迷濛眼神注視我的眼睛。
「是硝石嗎?」他終於問。
「是硝石。」我回答。「你這樣咳嗽多久了?」
「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可憐的朋友有好幾分鐘根本沒辦法回答我。
「這沒什麼!」他終於說。
「來。」我堅決地說:「我們回去,你的身體健康要緊。你有錢,受尊重,有人敬慕,受人愛戴;你是幸福的,像我以前一樣。別人可捨不得見你生病。至於我,則是無關緊要。我們回去,免得你生病,我可擔不起這個責任。何況,還有路哲西──」
「別再說了。」他說。「咳嗽根本不礙事,要不了我的命,我不會咳死的。」
「沒錯,沒錯。」我回答:「其實我並不想沒事亂嚇唬你;不過你還是應該當心。來喝點梅鐸酒可以驅驅溼氣。」
我從一長排擺在擱架上的梅鐸酒抽出一瓶,敲斷瓶頸。
「喝吧!」我說著把酒遞給了他。
他用斜眼瞄我,把酒瓶拿到嘴邊。他先停頓一下,再會意地對我點頭,這一點頭,帽子上的鈴鐺又叮叮作響。
「敬長眠在我們周圍的人。」我說。
「我敬你長命百歲。」
他又拉著我的手臂,繼續往前走。
「這些地窖還真大。」他說。
「蒙特雷索曾經是個興旺的大家族。」我回答。
「我忘了你們的族徽是什麼樣子了。」
「一隻人的金色大腳,襯底是藍色;那隻腳踩住一條挺立的蛇,蛇的毒牙反過來咬住腳跟。」
「徽上的銘文呢?」
「有仇必報。」
「說得好!」他說。
酒的作用使他眼睛發亮,鈴鐺作響。梅鐸酒也使我自己的想像愈發活躍。我們經過由成堆的白骨和大小酒桶疊成的牆壁,進入地下墓窖最深的地方。我又停下腳步,這回我大膽抓住弗度納托的上臂。
「硝石!」我說:「你看,愈來愈多了,像青苔一樣掛在地窖上。我們現在來到河床底下,溼氣凝結成的水珠從屍骨間滴下來。走吧,趁現在還來得及,我們快回去。你的咳嗽──」
「沒事。」他說:「繼續往前走,不過先喝瓶梅鐸酒再走。」
我敲破一瓶「德格拉夫」(De Grave),他一口氣就把它喝光。他眼露凶光,然後大笑起來,用我看不太懂的手勢往上一扔。
我訝異地看著他。他又做了一次同樣的動作──古怪的動作。
「你不懂?」他說。
「我不懂。」我回答。
「那麼你就不是我的兄弟了。」
「怎麼說?」
「你不是共濟會會員。」
「是的,是的。」我說:「我是,我是。」
「你?不可能!共濟會員?」
「我是共濟會員。」
「證明給我看。」他說。
「就是這個。」我邊回答,邊從及膝披風的摺層底下拿出一把泥水匠用的抹刀。
「你在開玩笑。」他叫了一聲,往後倒退幾步。「不過我們還是繼續去找那桶阿蒙蒂亞度酒吧。」
「就這麼辦。」我說著把工具收回披風底下,又伸出手扶他。他重重地倚住我的手,我們繼續往前尋找那桶阿蒙蒂亞度酒。我們經過幾個低矮的拱門,下樓梯,走一段路,又往下,最後進入一個很深的洞穴,裡面污濁的空氣使我們的火把只剩微微的火光,而不成火焰。
在地窖最遠端的盡頭,有另一個較小的洞穴。它的壁邊排列著人類的骨骸,以巴黎大墓穴的方式,堆疊到拱頂。這墓穴內部的三面穴壁都是以這種方式排列,第四面壁的白骨則倒了下來,散亂在地上,有個地方甚至堆成一座小山。我們看到在這面散亂的骨牆裡,還有一個更深的地窖,深約四呎,寬三呎,高六七呎,看起來似乎沒什麼特別的作用,只是墓穴天頂兩大支柱之間的空隙,背後是堅硬的花崗岩壁。
弗度納托舉高他微弱的火炬,拼命想看清凹穴深處究竟是什麼,卻徒勞無功,因為火光昏暗,我們根本看不見洞穴盡頭。
「往前走。」我說:「阿蒙蒂亞度酒就在裡面。至於路哲西──」
「他是個白痴。」我的朋友打岔道,一面踉蹌地往前走,我立即跟了上去。他一下子就走到凹穴盡頭,發現石牆擋住了他的去路,便愣愣地站在原地。頃刻間,我已經把他拴在花崗岩上。花崗岩表面上有兩根鐵環,水平相距兩呎。其中一個掛著短短的鐵鍊,另一個掛著鎖頭。我把鍊子繞住他的腰,幾秒鐘就鎖住了他。他驚愕得忘了反抗。我把鑰匙抽了出來,退出凹穴。
「用手摸摸牆壁。」我說:「你一定會摸到硝石。這裡真的很潮濕,我再一次求你回去。你不要?那麼我只好離開你了。不過離開之前,讓我先為你略盡綿薄之力,替你效勞。」
「阿蒙蒂亞度酒!」我的朋友突然脫口而出,驚魂仍未定。
「沒錯。」我回答:「阿蒙蒂亞度酒。」
我邊說,邊在剛才提過的那堆死人骨頭忙了起來。我把那些骨頭扔開,很快就找到砌牆的石塊和灰泥。我開始用這些材料和抹刀,努力地在凹穴入口砌牆。
第一層石塊還沒砌好,我就發現弗度納托的酒已經醒了大半。我之所以會發現,是因為從凹穴深處傳來一聲低吟。那不像醉漢發出的呻吟。接著好久都沒有聲音,似乎故意保持沉默。我砌上第二層,第三層,第四層;然後我聽見鍊子猛烈拉扯的聲音,噪音持續了好幾分鐘。我為了聽得更過癮,索性停下手上的工作,坐在骨堆上聽。鍊子的鐺鐺聲終於停止時,我又繼續砌牆,一口氣砌完第五層、第六層和第七層。這時候牆幾乎和我胸口一樣高,我又停止砌牆,舉起火把在新砌的牆上,讓微弱的火光照進牆裡面的人。
裡面被鍊子鎖住的人突然發出一連串淒厲的尖叫聲,彷彿猛力將我往後推了一把。一時之間,我躊躇不前──不由自主地發抖。我抽出配劍,用劍探索凹穴裡的情況。但一轉念,我又安心了。我伸出手按住墓穴堅固的質地,感到滿意。我又走向牆壁,回應他的尖叫。我模仿他叫,火上加油,用音量和聲勢壓過他。聽我這麼叫,尖叫的人便安靜了下來。
現在已是午夜時分,我的工作將近尾聲。我砌完了第八層、第九層和第十層。第十一層和最後一層也完成了一部份;現在只剩最後一塊石磚砌上去,便大功告成。我吃力地搬起沉重的石塊;我把它的一部份擺到預定的位置。但就在此時,凹穴裡傳來低沉的笑聲,令我毛骨悚然,緊接著傳來悲傷的聲音,我幾乎認不出是高貴的弗度納托在說話。他說──
「哈!哈!哈!──嘻!嘻!──你這玩笑開得真好──妙極了。待會兒我們回到屋裡可以好好笑個夠──呵!呵!呵!──還可以一邊喝酒──呵!呵!呵!」
「阿蒙蒂亞多酒!」我說。
「嘿!嘿!嘿!──嘿!嘿!嘿!──對,阿蒙蒂亞度酒。不過現在時候是不是不早了?弗度納托夫人和其他人會不會在家裡等我們?我們走吧。」
「好。」我說:「我們走吧。」
「看在上帝的慈愛份上,蒙特雷索!」
「是的。」我說:「看在上帝的慈愛份上!」
可是說完這句話之後,我就聽不到回答了。我失去了耐心,便大叫:
「弗度納托!」
還是沒有回應。我將火把扔進那僅剩的缺口,讓它掉進裡面。結果只傳來鈴鐺的叮叮作響,我開始覺得胸口不舒服──因為墓穴太潮濕的緣故。我趕緊完成我的工作,使勁把最後一塊石磚推到定位,塗上灰泥。我把剛才那些白骨重新堆疊起來。半世紀以來,沒人打擾過這些骸骨。願死者安息地下!
阿蒙蒂亞度的詛咒
勞倫斯.卜洛克著
一九六一年,我朋友唐.威斯特雷克(Don Westlake)未能奪得愛倫坡獎時,我知道自己很想得獎。
他才剛發表《傭兵》(The Mercenaries),獲提名角逐愛倫坡最佳長篇推理小說新人獎。別人把愛倫坡的人像抱回家了(其實那是科幻小說老手所寫的第一部推理小說,儘管名義上符合遊戲規則,但實質上似乎有可議之處),我們全都安慰唐提名就已經是足夠的肯定,他表面上也假裝相信我們的話。我們不需要替他感到惋惜;如今他有一整櫃的愛倫坡人像,以及一整綑的提名證書。總之,重點不在他。
重點在我。
一九六一年,我開始出版平裝本的犯罪小說,幾年後又出精裝本。雖然不能說我一心一意想贏得愛倫坡獎,不過我還是對自己有所期許。我在七零年代中期以奇普.哈里森(Chip Harrison)的筆名出過一本書,這也是書中主述者的名字。那本書題獻給「芭芭拉.本翰,紐蓋特.卡倫德,約翰.狄克森.卡爾,以及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愛倫坡獎委員會」。
芭芭拉.本翰是《出版者周刊》小說類首要的評審。紐蓋特.卡倫德是樂評家哈洛德.史康柏(Harold Schonberg)在《紐約時報書評》的犯罪專欄所使用的筆名。而約翰.狄克森.卡爾則是密室內的大師,擔任《愛勒利昆恩推理雜誌》的推理作品評審。
我厚著臉皮題獻給他們,結果毫無效果。至少沒起什麼作用就是了。卡倫德在他的專欄提起了這本書和書中的獻辭,至於它在文學方面的價值則隻字未提。卡爾與本翰完全沒注意到,而愛倫坡獎提名的時間已近,奇普.哈里森仍不聞不問。
可是大約一年以後,我的馬修.史卡德(Mathew Schudder)系列小說之一,《謀殺與創造的時候到了》(Time to Murder and Create)獲得最佳平裝本小說提名,我去參加晚宴,自信滿滿地以為自己穩操勝券,結果卻希望落空。得獎者另有其人。我驚愕地坐在那兒,無法自我安慰地向別人說提名就是足夠的肯定。
過了兩年,我又被提名了,這回是以《八百萬種死法》入圍,角逐最佳小說獎項。「提名就是足夠的肯定。」我喃喃自語著往回家的路上走。
我花了許多年的時間才明白自己遲遲不能得獎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為了一個詛咒。
阿蒙蒂亞度的詛咒。
***
直到最近,我才發覺這詛咒的嚴重性。查爾斯.阿爾戴(Charles Ardai)為他的「犯罪疑雲」收錄編輯我早期的作品,他指出我在小說中提起「一桶阿蒙蒂亞度酒」是勞勃.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作品,他委婉地問我把愛倫坡的作品張冠李戴,是不是故意的,暗指這錯誤是小說人物所犯的錯。
我回答這錯誤不是小說中人犯的錯,而是我自己犯的錯,請他絕對可以更正。
這時機恰到好處,因為它顯然是一連串時運不濟的主因。
我必須承認這樣的誤植,絕非單純的打字失誤,只限於一本不太起眼的書中所犯的錯。雖然這是我公開把愛倫坡的經典之作誤認為史蒂文森作品唯一的一次,不過打從我初次閱讀這個短篇小說起,就搞不清作者是誰。假如我沒記錯的話(讀者應該已經可以看出我的記憶力有多壞),那已是五十七年前,我七年級時的事。
我們的英文課本包括了一小本藍色的短篇小說集,其中有一篇是「一桶阿蒙蒂亞度酒」,有一篇是史蒂文森寫的東西(我依稀記得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說叫「巴倫特雷大師」,但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是長篇小說。所以我實在不曉得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說究竟是哪一個,而我也不在乎,上天見諒)。
我不知道關於七年級的事我還記得什麼,可是「一桶阿蒙蒂亞度酒」卻讓我印象深刻,盤桓不去。
「看在上帝的慈愛份上,蒙特雷索!」
「是的。」我說:「看在上帝的慈愛份上。」
今天已經沒有人這麼寫了,即使在當時我就知道了。但不知為什麼,我卻記得作者的名字縮寫是R. L. S.,而非E. A. P.。偶爾聊天時提起,就會有人說,我指的是愛倫坡,不是嗎?然後我會說當然是,從善如流地接受對方的糾正──但維持不了多久,因為我的記憶莫名奇妙地對史蒂文森忠心耿耿。
其實我憑什麼奢望贏得愛倫坡獎呢?如果紅襪隊那麼久無法贏得世界大賽冠軍,只因小氣的老闆把貝比.魯斯交換出去,那麼我又憑什麼敢奢望呢?
***
後來當然一切都改觀了。
因為我開始和一位年輕女子交往,她的名字叫琳恩.伍德。
你可能會問,這和解除阿蒙蒂亞度詛咒有什麼關係?等我告訴你伍德小姐的母親叫艾蜜莉.坡以後,也許答案就會見分曉。
她並非我認識的人當中第一個姓坡的。早在八年級時,也就是我看過蒙特雷索和爛名弗度納托的故事僅僅一年後,我們班轉來一位同學,名叫威廉.坡。他家剛從阿拉巴馬搬來北方,使他因而成為紐約州水牛城一家小學六六年班裡的異類。我們毫不留情地嘲笑他的口音──如今回想起這件事,我完全不懷疑它絕對又助長了詛咒的力量。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問過他和坡有無血緣關係,不過他八成會答說有,因為他們全都這樣。我是指姓坡的人。
當然,他們沒一個是坡的直系後代,因為這可憐的傢伙身後並未留下兒女。不過他有許多旁系子孫,其中一位叫艾蜜莉,而她有個女兒叫琳恩。
讀者,我娶了她。
就在一年內,我的短篇小說「在黎明曙光下」(By the Dawn’s Early Light)入圍角逐愛倫坡獎。琳恩和我出席了當時已被我戲稱為「永遠的伴娘」的晚宴,這次我回家時,卻帶著我新娘的曾曾曾舅公的陶瓷人像。
我不好意思地承認,接下來那幾年,我的櫃子上又多添了幾座陶瓷人像。巧合嗎?
我可不這麼想。
勞倫斯.卜洛克曾經在紐約公園部於愛倫坡布朗克斯故居所舉辦的一場活動中,朗讀他的「鐘」,而且無視於大眾的反對,一兩年後又在一場類似的盛會上表演了一次。他擔任Akashic即將出版的文選,《曼哈頓黑色作品二──經典》(Manhattan Noir II──Classics),他特別將「大鴉」收錄其中,認為在讀者的推想中,再黑也沒有這個黑了。正如前文所述,他和愛倫坡在其餘方面唯一的關係,就是經由婚姻而來。不過他確實收集了不少這位大作家的半身像,當他在寫這篇文章時,抬頭就可以看見架子上的五座人像。
黑貓
我即將要寫的這個故事荒誕不經卻又真實平凡,我並不期望或奢求別人相信。如果連我以自己的理性都無法接受,卻還指望別人相信,那我簡直是瘋了。但是我並沒有瘋,也絕對不是作夢。不過明天我就要離開人世,所以今天我要一吐為快,卸下心靈的重擔。我當下的目的是把居家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明白簡要、不添加個人意見地鋪陳於世人面前。這些事件的後果不但驚嚇到我、折磨了我,也徹底毀滅我。然而我並不打算多加解釋。在我看來,這些事幾乎只讓我感到恐懼,但是對於許多人來說,這些事倒沒那麼恐怖,而是非常怪誕離奇。將來或許會發現某種智識,可以替我的幻想找到正常的解釋,某種比我自己的智識更冷靜、合乎邏輯、且不容易激動的智識,能夠把我以恐懼的心情面對的情況,看成是一連串稀鬆平常的因果關係。
我從十分幼小的時候起,就以性情溫順且厚道著稱。我甚至因為心腸太軟而成為同伴嘲笑的對象。我特別喜歡小動物,父母寵愛我,讓我養各式各樣的寵物。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寵物身上,覺得世上再沒比餵食和撫摸寵物更快樂的事了。這種性格特質隨著我年齡增長也變得更加顯著,到我成年時,成為我快樂的主要來源之一。對於那些喜愛狗兒的忠實與伶俐的人而言,我無須多費唇舌解釋從中得到什麼樣性質與程度的滿足。對於那些常有機會遭遇人類虛情假意和背信忘義的人而言,動物那種無私和犧牲的愛,必定令他們有極深的感觸。
我早婚,而且欣然發現妻子的性情與我近似。她注意到我對養寵物的偏好,一有機會就引進優良的品種。我們養了鳥、金魚、一隻良種狗、兔子、一隻小猴子,以及一隻貓。
那隻貓非常漂亮,體型很大,全身都是黑色的,而且絕頂聰明。說到他的聰明,我那心中充滿迷信思想的妻子就常提起普遍的古老傳說,認為所有黑貓都是女巫的化身。倒不是因為她對這看法非常認真,我之所以提起,純粹是因為下筆的時候恰好想起。
布魯托──那隻貓的名字──是我最喜愛的寵物與玩伴。他完全由我來餵,我在家裡走到哪他就跟到哪,我甚至難以阻止他跟我上街。
我們的友誼就這樣持續了好幾年,這段期間,我由於嚴重酗酒的緣故,整個人的脾氣和性格產生了劇烈的變化,(我羞愧地承認)變得愈來愈糟。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怒無常、更暴躁易怒,也更不在乎他人的感受。我放任自己對妻子惡言相向,到後來甚至對她動粗。我的寵物當然也清楚感受到我性情的轉變。我不僅忽視牠們,還虐待牠們。不過對於布魯托,我仍保有足夠的關心,因此還不至於對他施暴,但是那些兔子、猴子或狗,不論是碰巧經過或有意親近,只要一靠近我,就慘遭我虐待。但是我的病情逐漸加深──還有什麼病比酗酒更嚴重!──後來就連當時因衰老而脾氣變得有些暴躁的布魯托,也開始嘗到我壞脾氣的滋味。
有一天晚上,我從城裡常去的酒館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裡,隱約覺得那隻貓在躲避我。我一把抓住他,他被我的粗暴驚嚇到,便對著我的手咬一口,造成了輕傷。我立刻暴怒不已,變得連我也不認識自己。我原本的靈魂似乎一下子飛出軀殼,由烈酒所慫恿的凶狠惡毒滲透了體內的每一個細胞。我從背心口袋抽出一把筆刀,打開刀子,抓住那隻可憐的貓的喉嚨,不疾不徐地挖出他一隻眼珠!寫下這件可惡的殘忍暴行時,我覺得面紅耳赤,渾身發燒和發抖。第二天早晨我恢復理智時──當睡眠消除了夜裡的怒火時──我為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既驚恐又懊悔;不過那頂多只是種微弱且含糊的感覺,我的內心深處依然無動於衷。我再度縱情酗酒,不久之後,酒精就淹沒了我對自己此一行為的所有記憶。
同時,那隻貓的傷勢逐漸復原。被挖掉眼珠的眼窩看起來的確非常恐怖,不過他好像不再感覺疼痛了。他像以往一樣在屋裡四處走動,但可想而知,只要我一靠近他便立刻驚慌而逃。當時我還殘存著昔日的軟心腸,眼見曾經那麼愛我的動物如今明顯討厭我,起初還有些難過。但這種感覺很快就轉變成惱怒,最後彷彿要把我弄到萬劫不復的地步,那種「偏執」的心態又出現了。關於這種心態,在哲學上根本尚未論及。然而就像我相信自己的靈魂存在,我也相信偏執是人類心理上一種原始的衝動──是決定人的性格的原始官能或情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誰不曾時常發現自己做壞事或愚行唯一的原因,純粹是明知故犯?我們難道不就因為明知道不可犯法,反而故意無視於自己最理智的判斷,偏偏以身試法?正如我剛才所說的,這種偏執的變態心理終於導致我最後的墮落。就是這種違背自我的莫名慾望──違反自己的本性──驅使我繼續並完成對那無辜小動物的加害。有一天早晨,我冷酷地把一條套索套住他的脖子,吊死他時我淚水盈眶,內心充滿悔恨,卻因為我知道他曾經愛過我,因為我知道他沒有得罪我,所以我才把他吊死──因為我知道我這麼做罪孽深重,足以令我的靈魂萬劫不復──如果有所謂的靈魂不朽的話──即使是最慈悲最可畏的上帝都無法以無限的慈悲來寬恕我。
就在我做出這種令人髮指的暴行當天晚上,我在睡夢中被失火的驚叫吵醒。床頭的帷幔都已經著了火,整棟屋子陷入熊熊大火中。我、妻子和一個僕人千辛萬苦才從火場中逃出。房子徹底燒毀,我所有的財產化為灰燼,失望之餘,從此以後我只好聽天由命。
然而我還不致於軟弱到想在那場火災與我的暴行之間,找出因果關係。但我要詳細描述一連串的事實,希望不會遺漏任何一個可能相關的環節。失火第二天,我重回大火所留下的廢墟。除了一片牆之外,所有的牆壁全都倒塌了。這是位於房子中央的一片間隔牆,不太厚,正是我床頭後面靠著的牆。牆上有一大部分灰泥沒被火燒毀──我認為是因為最近才剛粉刷過的關係。有許多人在這堵牆四周圍觀,似乎正在仔細研究這面牆的某一部分。人群中不斷傳出「奇怪」、「詭異」和類似的驚嘆,引起了我的好奇。我走近一看,只見白色的牆上好像有一個大貓的淺浮雕,那隻貓的模樣逼真得令人吃驚,脖子上還套著一條繩子。
我乍見這幻影時──除了幻影之外,我實在無法將它視為別的──驚愕恐懼到極點。但冷靜思考之後,總算令我鬆了口氣。我記得那隻貓是被吊死在房子旁邊的一座花園,失火的時候,花園裡立刻擠滿了人──一定有人割斷吊貓的繩索,把貓從某扇開著的窗戶扔進我房間。這麼做的用意很可能是為了把睡夢中的我叫醒。其他牆壁倒塌,把我暴行的受害者壓進剛粉刷過的灰泥,石灰、大火,再加上燃燒屍體發出的氨,就形成了我所看見的貓浮雕。
儘管我輕易地便對我的理智,即使沒有全對我的良心,以剛才的說明解釋了這件驚人的事實,但它依然對我的幻想留下了難以抹滅的印象。有好幾個月的時間,貓的幻影在我腦中揮之不去;而在這段期間,有種模糊的感覺又回到我心中,像是悔恨,又像不是。我甚至開始惋惜失去了那隻貓,開始在我現在經常光顧的低級場所,尋找相同品種和類似長相的貓,取代他的地位。
有天晚上,我半醉半醒地坐在一家惡名昭彰的下流酒館時,突然注意到一樣黑色的東西,那黑色的東西蹲在一只大酒桶上──那些杜松子酒或萊姆酒的大酒桶便是酒館內最主要的陳設。我持續看著那酒桶上方好幾分鐘,令我驚奇的是,剛才居然沒發現那東西的存在。我走了過去,伸手摸了摸那東西。那是隻黑貓──非常大的貓──幾乎有布魯托那麼大,而且除了一點之外,各方面都很像。布魯托渾身上下沒有一根白毛,但這隻貓的胸前卻有一塊不太明顯但極大的白斑,幾乎覆蓋了整個胸部。
我一摸他,他立刻站了起來,大聲地咕嚕咕嚕,對著我的手摩擦身體,似乎很高興我注意到他。這正是我要找的貓。我立即主動向老闆提議要買下牠,但老闆說貓不是他的──他不知貓是打哪來的──以前從沒見過。我繼續撫摸那隻貓,當我準備回家時,貓也作勢要跟我走。我讓牠跟著我,沿路還不時俯下身拍拍牠。一回到家中,牠很快就適應了環境,即刻成為我妻子的寵物。
至於我自己,不久就打心底對牠產生了反感。這與我原本的預期正好相反,我不知道怎麼回事,也不明白為何會如此,牠明顯喜歡我,反而令我厭煩和不耐。逐漸地,厭煩和不耐轉變成強烈的憎恨。我盡量躲著牠,內疚再加上對於上次殘忍行為的記憶,制止我傷害牠。有好幾個星期的時間,我沒有打過牠,也不曾用其他的方式虐待牠。可是漸漸的,非常緩慢的,我只要一見到牠就有說不出來的厭惡,打心底不願見到牠那不祥的模樣,就像想要逃離瘟疫一樣。
無疑地我對那隻貓的憎恨之所以加深是因為,在我帶牠回家的第二天早晨就發現,牠和布魯托一樣,少了一隻眼睛。不過這情況反而使牠更受我妻子寵愛,正如我已經說過的,妻子具有慈善心腸,這原本是我顯著的特質,也是我眾多最單純與最純潔的快樂泉源。
不過我越是討厭那隻貓,牠反而對我越是親熱。牠寸步不離地跟著我,那種緊迫盯人的程度是讀者所無法想像的。我一坐下,牠立刻蹲在我椅子底下,或跳到我腿上,對著我身上摩擦,纏著我不放,令我極端厭惡。如果我起身要走,牠就會鑽到我兩腳之間,害我差點跌倒,不然就用牠又長又尖的爪子抓住我衣服,這樣子爬到我胸口。在這種情況下,雖然我恨不得一拳把牠打死,卻還是忍下來了,這多少是因為我還記得自己上次造的孽,但最主要的──我還是坦白招認吧──還是因為我非常懼怕這隻貓。
這恐懼不全然是對某種具體邪惡的畏懼,但我又不知該如何對此下定義。我幾乎羞於承認──沒錯,即使在這死囚牢裡我也幾乎羞於承認──那隻貓在我內心激起的恐懼之所以日益嚴重,竟然是因為某個最普通的妄想所引起的。我妻子曾經不只一次要我注意我剛才提過的那塊白斑的特徵,那是這隻古怪的貓和被我殺害那隻之間,唯一看得出的差別。讀者應該記得這塊白班雖然很大,但起初並不明顯。可是漸漸的,在不知不覺中──慢得幾乎難以察覺,我的理智因而有很長一段時間硬把它解釋為幻覺──那塊白班終於顯現出清楚的輪廓。那輪廓呈現出一樣東西,令我一提起就渾身發抖,也正是為了這樣東西,我才討厭和畏懼這怪物,要是我敢的話,早就把它除掉了──它現在是一種可怕東西的圖形──絞刑架的圖形!──噢,代表恐怖與罪惡,痛苦與死亡,令人可悲又畏懼的刑具!
現在我悲慘到極點,世上沒有人會比我更加悽慘了。一隻沒有理性的畜牲──牠的同類才被我漫不經心地殺害──一隻沒有理性的畜牲,居然為我這個依上帝形象創造出來的人,帶來這麼多不堪忍受的苦惱!唉!無論是白天或黑夜,我再也享受不到安寧之福!白天的時候,那隻貓連一刻也不讓我獨處,夜裡的時候,我每小時從難以言喻的恐怖惡夢中驚醒,醒來總發現那傢伙熱呼呼的氣息吹在我臉上,而牠沉重的軀體──一種我無法擺脫的實質夢魘──永遠壓在我心上!
在這些折磨的壓迫下,我心中僅存的些微良知終於徹底低頭了。邪念成為我唯一的知心朋友,心中充滿了最陰險和邪惡的念頭。我原本喜怒無常的個性也變本加厲,擴大為對所有事和所有人都看不順眼,憎恨怨怒;現在我盲目地放縱自己,經常突然大發脾氣,毫不收斂,而我任勞任怨的妻子,唉,是最常忍受我脾氣、最有耐心的受害者。
有一天,為了處理某件普通的家務事,她陪我一起進入我們那棟老舊建築的地窖,我們因山窮水盡,不得不遷居此處。那隻貓跟著我走下陡直的階梯,絆了我一跤,令我險些一頭往下栽,氣得我幾乎發狂。盛怒中我暫時忘卻了令我遲遲不敢下手的幼稚恐懼心理,舉起斧頭,對準那隻貓砍下,當然,如果斧頭照我預料地往下落,那隻貓就會當場喪命。可是我妻子一把攔住了我。這一攔更令我惱羞成怒,彷彿著了魔般,從她手中抽回我的手臂,把斧頭砍進她腦袋。她一聲都沒吭就倒地死了。
我既已犯下如此可怕的凶案,就立刻開始仔細思考該如何藏匿她的屍體。我知道不論白天或晚上,只要把她的屍體搬出屋外,都有被鄰居看見的危險。我腦子裡出現了許多辦法,一下子考慮要把屍體剁成碎片,用火燒毀;一下子又決定在地窖的地板挖個墳。甚至打算把屍體扔進院子裡的水井──或考慮把屍體裝進箱子,像處理一般貨物般,找個搬運工來把它運出屋子。最後我終於想出一個比所有辦法都理想的對策。我決定把屍體砌進地窖的牆壁裡,就像書中所記載的中世紀修士把受害者砌進牆壁一樣。
這地窖若用於此一目的倒極為合適。它的牆壁砌得鬆鬆散散的,而且最近才剛用粗糙的灰泥重新塗過,由於空氣潮濕的關係,尚未變硬。不僅如此,有道牆突出一塊,那兒原本是個假煙囪或假壁爐,如今填平了,看起來就跟地窖裡的其他牆壁一樣。我覺得有自信可以挖出這部分牆壁的磚塊,把屍體塞進裡面,再把整面牆像以前一樣封好,這樣任誰也看不出絲毫破綻。
我的這番估計並沒差錯,我用一支鐵撬輕易就把磚塊挖鬆,小心翼翼把屍體靠緊內牆,保持直立的姿勢,然後不費什麼力氣就把牆壁恢復成原狀。我採取所有必要的防範措施,我取來灰泥灰、沙子和毛髮,攪拌出和原本一樣的舊泥漿,再非常仔細地塗抹在新砌的磚塊上。完工之後,我對一切感到非常滿意,那面牆看不出絲毫被拆過的痕跡。地上的垃圾,我也十分細心地收拾乾淨。我得意義地環顧四週,自言自語著:「看來辛苦了半天,總算沒有白費。」
我的下一步是尋找造成這一切不幸的罪魁禍首;我終於下定決心弄死牠。要是當時我能找到那隻畜牲,牠絕對是死路一條,不過看來那隻機伶的貓被我剛才的暴怒給嚇跑了,不敢在我怒氣未消的時候現身。可惡的貓不在眼前,使我心中感到如釋重負,這感覺簡直難以想像和言喻。到了夜裡牠也沒露面;因此自從牠來到家中之後,我終於能安安穩穩睡一整夜;沒錯,即使靈魂背負著惡行的重擔,我還是睡著了。
第二天與第三天過去了,折磨我的那隻貓依然沒來,我又能像個自由自在的人那樣呼吸了。那怪物已經嚇得永遠逃離了這棟屋子!我再也不會看見牠了!我真是開心到極點!我所犯下的罪孽很少令我良心不安,有少數幾人問起我妻子,但這些都被我輕易應付打發掉了,警方甚至到屋裡進行搜索,當然什麼也沒發現。我覺得我的未來高枕無憂。
在我殺害妻子之後的第四天,有一批警察突然上門來,進到屋裡,又仔細搜索了屋子一遍。不過我覺得我藏屍的地點十分保險,因此一點也不慌張。警方要我陪他們一起搜索,他們搜查得非常徹底,任何角落都不放過。終於,在第三還是第四次搜索時,他們走下了地窖。我神色自若,態度從容,心跳平靜得像毫不知情的無辜熟睡者。我從地窖的這頭走到另一頭,雙手交叉胸前,悠然地走來走去。警方感到十分滿意,正準備離去。我心中的快活難以壓抑,忍不住想要開口說話,就算是一句也好,只要能紓發內心的得意,讓他們更加確信我的清白無辜。
「各位先生,」他們爬上階梯時,我終於開口了,「我很高興能消除你們的懷疑,祝大家身體健康,並再度向各位表示我的敬意。順帶一提,警官們,這--這是一棟建造得非常好的房子。」(我迫切地想說幾句不著痕跡的話,幾乎不知道自己說了什麼。)──「我可以說這是棟建造得極為堅固的房子。這些牆壁──你們要走了嗎,各位?──這些牆壁砌得非常扎實。」說到這裡,我以狂妄的虛張聲勢,竟然用手裡拿著的手杖,重重敲擊一面牆,而牆壁的那部分磚塊後面,就站著我愛妻的屍體。
但願上帝保佑我脫離惡魔的毒手!我敲擊牆壁的餘音才剛結束,墳裡就響起了一個聲音回應我!──那是一聲哭叫,起初有點模糊和斷斷續續,像小孩子的啜泣,接著很快就擴大為又長又響亮的尖叫,非常怪異,完全不像人聲──哀號──悲鳴,有點恐怖,又像是得意,彷彿只有從地獄才可能發出的聲音,就像下地獄的靈魂痛苦的呻吟,也像為靈魂墜入地獄而欣喜若狂的惡魔所發出的歡呼。
當時我心裡的想法,說來就可笑。我昏頭脹腦,跌跌撞撞地走到對牆,階梯上那群警察一時之間由於驚嚇過度,都愣在原地。下一刻就有十幾隻結實的胳臂開始挖牆,整片牆便倒了下來。屍體赫然豎立在大家眼前,已嚴重腐爛,凝結出血塊。而在屍體頭頂上,就坐著張大血紅的口和炯炯獨眼的可恨惡貓,牠不但以詭計引誘我殺害妻子,又發出告密的聲音把我送上絞刑台。原來我竟然把這怪物也一起封進墳墓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