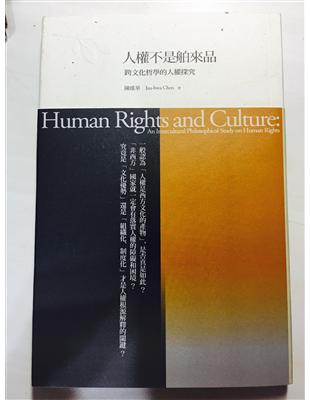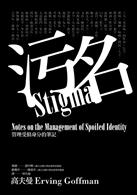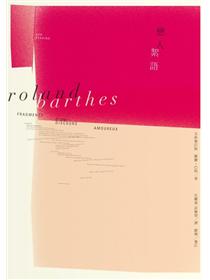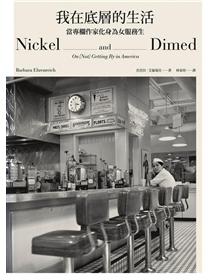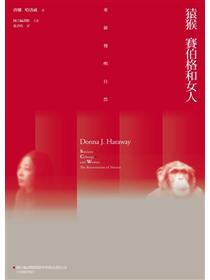第一章 最壞的年代、最好的年代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在《雙城記》(The Tale of Two Cities)曾經說過:「那曾是最好的年代,那曾是最壞的年代」(It was the best of times,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我認為倒過來說:「那曾是最壞的年代,那曾是最好的年代」,可以給二次戰後的世界,下一個最好的註腳。當時人們生活在廢墟裡;卻達成建立聯合國及通過〈世界人權宣言〉。面對戰爭的殘酷和不人道,尤其是日本軍國主義及納粹的大屠殺,人類必須面對有史以來最沈痛的一擊;警惕自己,不要重蹈覆轍。
一九四八年,在冷戰即將開始的前夕,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為全球人權治理拉開序幕,提供人權法理及思想的基礎。當時參與起草這份文件的五十幾個創始的會員國,各自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利益盤算,很多國家不是剛擺脫歐洲殖民、宣佈獨立,就是準備要獨立,再加上當時美蘇冷戰、西方與阿拉伯國家對立的以巴問題,非常不利於共識的形成。儘管如此,〈世界人權宣言〉三十條中,有二十三條獲得所有會員國的全體一致的贊同。而且最後,在沒有任何國家投反對票的情況下,通過這份劃時代的人權文件。(Glendon, 2001:169-171)
在複雜的國際關係、隱藏的衝突氣氛,為什麼當時〈世界人權宣言〉可以通過呢?在起草及討論這份文件時,部分國家曾經因為國家主權受干預的問題(英國、蘇聯及部分東歐國家),以及與文化傳統對待女性的方式不一致(阿拉伯國家),強烈反對〈世界人權宣言〉的條文。為什麼這些國家在最後表決時,並沒有投下反對票?現實的國際利益、迥異的意識型態及不同的文化背景難道不會構成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最大阻礙?
一般人都有〈世界人權宣言〉乃淵源於「西方」的粗略印象,卻很少人仔細研究成立聯合國及起草〈世界人權宣言〉時,歐、美、拉丁美洲、非洲及亞、澳等國所扮演的角色。戰後的歐洲滿目瘡痍,自顧不暇;蘇聯進軍東歐,接管部分納粹佔領過區域。英國因擔心殖民成為國際人權的議題,避之唯恐不及。美國也因為菲律賓及安理會永久席次的問題,尷尬不已。反而是很多被殖民的小國,期待聯合國及建立國際的人權標準,可以早日脫離被殖民及被外來強權宰制的命運。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強權國家反而擔憂建立國際的人權標準,會影響其國際勢力。
仔細檢討起草〈世界人權宣言〉的過程,會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檢視〈世界人權宣言〉與各個文化傳統之間的關連。「文化差異」在世界各國共同起草一份世界性的人權法案時,扮演著何種角色呢?「文化差異」可以作為理由,說明為甚麼有些國家對部分條文的內容採取保留的態度?除了「文化差異」的理由之外,還有其他更強的理由嗎?國際權力的不均等關係,以及現實的國際利益之衡量,說不定比「文化差異」來得更根本?說不定「文化差異」並沒有一般想像的那樣嚴重,而國際權力的角力才是左右影響〈世界人權宣言〉的關鍵因素?一般認為「西方」文化傳統的人權概念以公民與政治權利為主;「非西方」則強調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但這樣的截然二分無法說明:為何大部分的國家不但認同公民、政治權利,也同樣認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之保障?而部分不認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納入〈世界人權宣言〉的國家,到底是基於文化傳統的差異,還是現實利益的考量?還很難說。
正式將戰爭、貧窮、疾病和殘暴等理解為「人權侵害」,其實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才有的事。那些以往被認為是無法避免、自然形成的悲劇,經過深刻的集體反省後,才知道那其實是集權統治者對權力貪得無厭的野心,以及各國的放任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尤其人們具體反省德國納粹政權及日本軍國主義的興起,意識到集權統治通常始於對特定族群的人權迫害,先整肅異己,然後發動全面的戰爭來滿足其霸權。當德國的納粹,義大利的法西斯及日本軍國主義興起時,都是始於壓制國內言論自由,清除內部反對勢力。而當時世界各國採取懷柔放任的政策,任由其不斷坐大,反而促成其勢無忌憚地向外擴張。
人權作為普世價值是〈世界人權宣言〉通過後的重要宣示,維護人權不再只是特定政府或國家的責任,而是所有國家及所有族群及所有個人的責任。達賴喇嘛在一九九三年維也納會議的演講【 】中提到「普遍的責任」為人權的普世價值作了最好的詮釋。(http://www.tibet.com/DL/vienna.html)當人們期待自身權利應保障的同時,亦肩負維護其他人基本人權應受保障的責任。我們在面對他人被迫害、監禁和受酷刑時,不應只是慶幸這樣的事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反而應該承擔維護人權的責任,伸出援手,並和受壓迫者一起反抗強權。如果眼睜睜看到他人受壓迫,徒有不平之鳴而沒有實際的作為,違反人權作為普世價值的意義。
起草〈世界人權宣言〉在於建立國際的人權標準,同時亦宣示維護人權是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責任。在要求世界各國必須遵守這樣的標準之同時,也要求所有人必須對於這樣的標準做出承諾。基於人權是全世界所有人共同的責任,維護人權的工作無國界限制。任何政府或任何區域違反人權,獲知消息的個人和團體,都有責任表達違反人權的關懷。
第一節 「在灰燼中,我發光」【 】?
很多人都有一種錯誤的印象,就是聯合國的成立是「西方」強權所主導,誤認聯合國是「西方大國」的重要貢獻。不過,實際卻恰好相反,大國如當時的美國、蘇聯、英國,都曾擔憂主權受干預,而強力反對聯合國的〈憲章〉以維護特定個人及族群的人權及自主權為名,介入她們的內政及外交事務。
當時美、英國都有殖民地要求獨立的顧慮,蘇聯則因為正入侵東歐,唯恐聯合國介入。相反地,亞洲及南美的國家代表們非常積極參與,她們在舊金山會議中不斷爭取發言的機會,並且堅持人權及自主權的原則,極力避免聯合國成為強權角力的場所。尤其是那些曾經被殖民且渴望追求獨立的國家之代表,她們最能深刻體會失去自由的悲哀,對於聯合國應該普遍地維護人權,深表贊同。如果沒有那些國家的那些代表們的努力,不但不可能有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之成立,也不可能有創立人權委員會,以及起草人權宣言之提案。
另一個廣為流傳的誤解是認為:「〈世界人權宣言〉根源於『西方』文化,不適用於『非西方』國家。」【 】這類說法通常是由於不理會〈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及各國參與這個文件討論的過程,而單純訴諸所謂「西方的個人主義」(Pollis & Schwab, 1980:1-2)或「西方人文及人道的傳統」(Lenk, 1998:25)。這些學者直接斷言〈世界人權宣言〉源於西方的歷史、思想與文化傳統,不適用於「非西方」。這些文獻通常沒有說明他們列出的思想及人權歷史文件、「西方的個人主義」、「西方人文及人道的傳統」及「西方文化傳統」到底和〈世界人權宣言〉的內容有何具體關連,而是粗略地列出思想脈絡及部分歷史文件,彼此所提到的項目也都有部分差異,也沒有提出指涉項目的標準何在,大部分顯得相當隨性及任意。而另一方面,追隨這些錯誤想法的伊斯蘭學者及亞洲政治領導人,則認為有所謂人權的「伊斯蘭價值」及「亞洲價值」直接斷言〈世界人權宣言〉所建立的國際人權標準只屬於「西方」,並不適用於伊斯蘭世界及部分亞洲國家。
為了釐清以上種種誤解,我們必須回顧整個〈世界人權宣言〉起草過程,並且分析它在文化差異方面的重要意義。因為,直至今日,成立聯合國及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仍然是人類檢討對自由的壓迫,涵蓋的國家最廣、標準最為明確的偉大成就。雖然,這樣的成就,和世界各地因受到壓制而被犧牲的人們付出之嚴重代價相比,可能微不足道。但讓這些侵害被看見、檢視、反思,並提出預防的對策,讓所有的國家同意共同簽署,都是過去前所未有的貢獻。回顧成立聯合國及通過〈世界人權宣言〉的詳細經過,不僅有助於釐清一般對於〈世界人權宣言〉乃「西方」文化產物的誤解,而且更可以顯示不同的國家及族群,即使有許多文化的差異和隔閡,卻不會妨礙她們理解差異、尊重差異,達成追求維護人權的基本共識。而最值得一提的部分,其實是文化差異不但沒有阻礙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反而成為各國發展自身人權文化的主要動力,增進彼此的相互理解,豐富國際人權標準應用在實際保障人權時的各種可行性。
〈聯合國憲章〉:強權與人權的拉扯
一九四一年,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美國總統羅斯福公開發表「四個自由」【 】的演講,鼓舞受到戰區波及的國家及人民,起來反抗德國納粹、法西斯及日本軍國主義之侵略,爭取每一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當時,有很多被殖民的國家,紛紛起而響應,聯合對抗這些發動戰爭的國家。因此,從一九四三年開始,建立一個強而有力的國際組織以維護國際和平,成為各國戰後協商的主要目標。一九四四年美、英、蘇、中四國開始籌畫成立聯合國的草案,而草案中四強及法國在安理會擁有否決權最受矚目,成為大會協商的焦點。這份草案是〈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的前身,人權只被約略提到一次,而且在非常不明顯的段落中。不過,「人權」在一九四五年的〈憲章〉中,不但出現在序言及第一條強調人權保障作為最醒目的地方,而且前後總共出現七次,轉變之快,耐人尋味。〈憲章〉最後的結果,恐怕也是參與起草的四強始料未及的吧!
聯合國成立後,在部分會員國的堅持下,經濟、社會理事會陸續建制,其下成立人權委員會,起草〈世界人權宣言〉。而經過一年的密集協商,一九四八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建立國際間可接受的人權標準,跨出人類歷史上制度化保障人權的第一步。
在聯合國成立六十年之後,即使有官僚化及制度僵化的問題,這個涵蓋全球一百九十幾個會員國的國際組織依然有其無可取代的地位。這個全球最大的國際組織在成立時,充滿著各式各樣意想不到的困艱和險阻,讓參與的各方幾度想要放棄談判和協商。重要的轉捩點其實是納粹集中營的暴行曝光,引發全球性的恐怖與震驚,造成強大的輿論壓力,導致強權國家願意讓步,接受人權納入憲章,以及之後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世界人權概念的出現,其實是建立在成千上萬人的無辜犧牲,讓人類不得不正視人權保障的重要性。
在〈憲章〉中強調人權,等於公開向全世界宣示:人權事務不受國家主權的限制,必須接受國際的審視和干預。而這點也正好是當時列強反對將人權納入憲章的主要理由,它們擔心國家「內政」會受到牽制,而影響彼此勢力的消長,所以力求這樣的干預不會影響其內政,所以在〈憲章〉加入了主權的條款。Bielefeldt 和Glendon都提到〈憲章〉有相互矛盾之處。第一條第三款:「對於所有人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及第二條第七款:「禁止對於他國內部事務的干預」。既然人權有其跨越國家管轄的普世意義,為何又禁止對於「內部事務」的干預呢?(Bielefeldt, 1998:1;Glendon, 2001:19-20)最簡單的解決之道當然是詳細界定「國內事務」的範圍,使得制度及系統性的人權侵害不會因為〈憲章〉二條第七款而不受干預。儘管如此,〈憲章〉第一條和第二條的爭議,還是埋下日後人權與主權的爭議。對於不願意遵守人權承諾的國家,「主權不容干預」或「國內事務」成為公開違反人權的藉口。
試著想像一個像希特勒一樣的政權,當它開始進行剝奪特定族群的權利時,〈憲章〉到底能不能讓國際社會信守其保障人權的承諾呢?(Glendon, 2001:20)而且,當集權統治者單方、片面地以第二條第七款作為保護傘,立法對付特定的族群或個人,甚至威脅不排除以武力對付特定的族群尋求獨立。這些單方、片面且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可以因為第二條第七款而不受干預嗎?既然,成立聯合國的目的,在於防止類似希特勒的集權再次興起。聯合國若姑息特定國家的人權侵害,形同違背〈憲章〉賦予它的重責大任。
以台灣為例,過去各種具有武力為後盾的「條例」,專門用來對付政治犯的各種罪名,包括的懲治「叛亂」、整肅「匪諜」,就是透過單方、片面且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惡法(rule by evil law),直接侵害人權的案例。目前中國用來對付法輪功學員及維權人士的各種罪名,也非常類似,如「敵對份子」、「散播邪教」、「陰謀煽動顛覆政府」及「民族分裂份子」等。這些以剷除政治不同意見者的法律和手段,侵害人權或拒絕予以意見不同的人權保障,還能算是國內事務嗎?聯合國如果坐視這些人權侵害日益擴大,會重蹈過去國家同盟(League of Nations)讓霸權危害世界和平的覆轍。台灣藉由民主化的過程,逐步揚棄過去惡法造成的人民基本自由之侵害。相較之下,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不過,〈憲章〉會有這樣矛盾的出現,其實正好反映聯合國成立過程所遭遇的困境:強國為所欲為、弱國為所必須為。最早提聯合國構想的是美國羅斯福總統,他期待組織所有愛好和平國家,建立維護和平的有效體制,來取代過去列強壟斷所有國際勢力的陳舊系統(Glendon, 2001:4)。雖然很多國家有這樣的共識和目標,在現實政治的利益糾葛,卻很難擺脫強國、弱國實力懸殊的現實困境。Glendon曾引用希臘城邦Melos居民在面對雅典大軍攻擊時的一段話,說明弱國的處境:
「你們,和我們一樣心知肚明,正義在世界上只存在於勢力相當的兩個陣營,強者做他們能力可以做到的事,弱者則屈服在他們必須做的事」(Glendon, 2001:XV)。
如何讓強權國家做該做的事,是聯合國最大的考驗。在政治理想與殘酷的現實中,聯合國只能透過不斷重申最初的理想,提醒各國理想並未達成。另一方聯合國自身必須成為一個聽得到嚴厲批判、自我檢驗且不斷改革的地方,而這樣的任務有賴於眾多像Melos一樣微小的國家的共同努力。
一九四五年,聯合國在於美國舊金山成立,由當時向德、日宣戰的國家所共同組成。聯合國構想是美國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三年聖誕夜總統談話提出的,他認為過去成立的國際組織,也就是國家同盟功效不彰,無法維護世界和平,因而需要成立新的世界性組織。於是,一九四四年英、美、蘇、中四強代表聚集鄧巴頓橡園(Dumbarton Oaks)討論起草聯合國憲章。英國及蘇聯反對美國將人權放入憲章之提案,尤其反對人權保障放入憲章正式的條文。不過,英蘇並不反對在討論經濟及社會議題時提到人權。四強因而做成決議,只有在社會及經濟安全保障時提及人權。鄧巴頓橡園最重要的議題其實是安理會的組織架構,尤其是永久會員國是否具有否決權的問題,因爭論不休無法獲得共識。(Glendon, 2001:6)一九四五年,邱吉爾、羅斯福及史達林在雅爾達召開會議,達成四強安理會具否決權的共識,並接受邱吉爾的建議,增加法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永久會員國。
雖然,列強在一九四四年鄧巴頓橡園的〈憲章〉草案只同意在最後涉及經濟及社會議題時提到人權。不過,一九四五年最後通過的聯合國憲章總共七次,包括序言、第一、十三、五十五、六十二、六十八及七十六條。序言不但確認人之人權、尊嚴及價值的基本信念,而且特別強調男性/女性、大/小國家之平等。在陳述聯合和國成立目的時,〈憲章〉開宗明義地宣示:
「對於所有人人權及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引自朱榮貴主編,第一冊附錄,2001:345。)
而在經濟社會理事會的任務及工作部分,〈憲章〉明確提到成立提升人權的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隸屬於經濟社會理事會。〈憲章〉從草案到正式通過,它的內容會出現這麼多的差距,如果沒有很多小國的齊心努力,不可能有最後〈憲章〉的成果。
首先,在憲章進入舊金山會議正式討論之前,英美蘇三強其實都各有盤算。由於彼此利益衝突,談判有可能顧此失彼,必須守住自身政府設定的底線,而且步步為營。當時的情勢頗為複雜:在亞洲,代表中國的中華民國政府正為國、共內戰而自顧不暇,並不真正在意〈憲章〉的內容。在歐洲,邱吉爾擔心蘇聯會乘機佔領或分割戰後的歐洲國家,歐洲重建必須仰賴歐洲各國的合作。他當時盤算成立歐洲理事會,以類似美國的聯邦政府的形式,希望快速、有效地統合歐洲各國展開重建的工作,以抵制蘇聯的勢力在東歐不斷地擴張。(Glendon, 2001:5-6; Klebes, 1997:543)
在列強三國協商的過程中,對邱吉爾及英國外交部而言,維持住大英帝國殖民及在亞洲的商業、經濟及政治在戰後國際勢力的影響力,才是他考量的重點。所以,英國一方面必須防範蘇聯乘機在歐洲坐大;另一方面必須防範美國藉由「民族自治」的策略,奪取其殖民地經濟、商業的利益。雅爾達會議時,勢力橫跨歐亞的史達林政府要求英、美政府必須做出承諾,協助其防範戰後德軍勢力反撲。其實,當時蘇聯的勢力其實已經進入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而且在雅爾達會議兩週前,蘇聯的紅軍已經進駐華沙,並且承認親蘇的波蘭共黨所組成的臨時政府。相較之下,美國羅斯福總統比較支持人權能入〈憲章〉,不過對於鄧巴頓橡園草案只提到一次人權,他並沒有表示任何異議,最多,也只是對於蘇聯反對人權入〈憲章〉的態度,甚表驚異而已。(Glendon, 2001: 6)從英蘇美中的態度來看,如何打贏戰爭、穩固自身勢力其實是首要考量。而維護人權的普遍,只有在不影響其現實利益的前提下,才勉強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