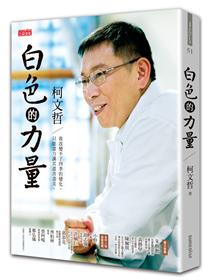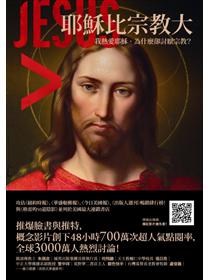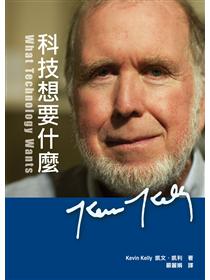一個台灣母親的日記
我每天與她擦身而過。三十年如一日。
聽見她和別人談話。
「三十年?好像還是昨天的事!」
她有時到台北市二二八和平公園看花看樹,在公園的咖啡館看眼前的風景,有時到中山北路上「台北光點」(原來是美軍駐台大使官邸,經整修後改為藝文場所。)的電影院看電影、在附設的咖啡廳吃餐點;也是因為喜歡這裡的花園風景而選上它給自己一些享受。
她是一位兩個兒女的媽媽、也是三個孫兒的阿嬤(台灣人稱「祖母」為阿嬤)。她有歡笑的時候,也有悲泣的時候。我以為我很了解她,和她一樣的好記憶,記下了許多大時代的小故事──別人的、以及自己的故事。從她攝影機的鏡頭、錄攝影機的鏡頭,保存了隨著歲月增長益為豐富的畫面,時間越久,那些影像越吸引人去細細看它。但有什麼會比她的日記更逼近真實、更細膩、更微妙、更千絲萬縷引人走入幻化實境?
她讓我看她的日記,我驚訝她的坦誠相見,為我能與她的創作同步而雀躍。一個藝術家,把自己獻給摯愛、把自己獻給台灣──用這樣的創作方式傾洩她的愛和熱情──烈焰灼身,她已品嘗過,她願再有一次機會與你共享;只因她深信真愛不會灼身,深信藝術能昇華為超完美的幸福。
1公園風景
眼前這一片風景,真是讓我快樂!
主要是樹林──年代很久的樹,多種不同科目,在這剛透著冷意冬天正午,舒展曼妙枝幹,彷彿伸出無數隻手,托著依然綠意盎然的葉叢。縱然灰雲蔽空,來自宇宙的光依是明亮,那曼妙枝幹無數隻手愉悅地迎接光亮,連被冷風吹過的樹梢枝葉,也雀躍地微微燦笑,整片樹林展臂捧起上天灑下豐裕的亮光。
樹林地上,落葉不多。空氣中劃過一陣陣風,沒有吹落多少枯葉。樹林間,地上有幾處花圃,艷麗、深深淺淺的紅花,那一點點艷紅,讓整片風景拉開張力,相互誇炫顏色的美麗。綠葉紅花,各有它們種種變化,越細細看,越發瞧見裡面千變萬化,看不勝看。
然而,有一小塊甘蔗園,更是搶眼。它有自己的翠綠柔魅,一節節細長圓滾的身體裡多汁甜蜜的生命,連綿成剪不斷的鎖鏈,從根底纏繞緊緊綑綁,穿透土地與子民,跨越這恆長歲月時空。它看過多少人來人往,今日與我相看。
這幾年,我特別覺得尷尬。台灣加入WTO,原來盛產的東西,很多迅速消失。甘蔗本身產品──糖,似乎被土地取代,你會以為「甘蔗」是「土地」(泥巴),而不是「糖」(可以吃,很甜,很吸引人)。當然,若說「泥巴」可以吃,也不為過,網路新聞上確實有人吃泥巴補身體。「甘蔗」甚至會跳過「土地」,直接以「金山」、「新台幣財富」植入子民腦袋,讓一些特權階級慾火焚燒,甘願跳進火獄。
和「糖」相似的難兄難弟──「鹽」,也有讓人哭笑不得的遭遇。
「這綠島像一隻船,在月夜裡漂呀漂」,不管是大綠島、小綠島,四周環海的國土,原是盛產「鹽」,變成只有在南部臨海的村莊留下一座小「鹽山」作為觀光景點,「鹽工廠」改而生產冰棒、化妝品、牙膏;而子民要吃的「鹽」,則從外國進口(你會以為,海洋國家沒有海洋了?!)
你肚子裡正在消化的青菜、水果,很大的比例是從外國進口。對付加入WTO產生的這些問題,憂愁的作田人被鼓勵,轉往加值產業、精緻產業。
眼前,這片美麗的風景,午後在園中走動的人增多了些。附近上班族,穿行過林間,享受午間休息時刻。近年來,外勞增加後,這兒常見外勞推著神情消沉的老人坐輪椅來曬太陽、透氣。(如果請不起外勞──雖然工資廉價,還是有很多家庭請不起──就像傳統景象:老夫婦相扶持散步健身、一家三代在樹林裡享受天倫之樂、老人會的成員相伴坐在樹蔭下長椅聊天……)
也是風景裡面的小小咖啡館,音響流瀉著老社運人士熟悉的越戰時期西洋流行音樂(有多少老社運人士已經在音樂重複播放中凋謝,化作春泥?或舉步蹣跚?)。是在嘲諷嗎?現在不比越戰時期平和,或更慘烈;拜科技之賜,敵對凶險化作無形,子民的焦慮從臉容上也看不到。
鳥群從樹林中愉悅地飛出,我的心像牠們一樣快樂。牠們知道,我不再被煎熬捆綁。牠們知道,那曾經乾枯的沙漠,已變成美麗秘密花園。那些曾經綑綁的魔法師很驚訝,嫉妒又羨慕吧?
2聽到阿薇死了
(「阿薇死了。」小羊說話的聲音總是輕柔,這句話從她口中說出來,她的神容依是貫有的平靜。人死了,這麼大的事,而且阿薇是大家的好朋友,那麼年輕青春,小羊還是貫有的平靜,真令我雙重衝擊!但想想,小羊在兩次大政治事件中,她的未婚夫──後來是她的丈夫,兩次被捕坐大牢,那種驚懼、憤怒的日子裡,她即便在最強烈的抗爭中,也是文靜得奇怪!想及此,我的雙重衝擊減去了一半。)
如果沒有那麼一個聚餐,老天!我要到哪一天才會知道阿薇死了?
那天的聚餐,連連衝擊,現場有人打架,多少位知名人士勸架,那架還真不容易收場!(老頭兒脾氣火爆,果然名不虛傳!一把年紀了,小個子,卻征戰不已!看來,全世界也只有大俠敢壓他的氣焰。)
老頭兒的女粉絲火爆不輸給他,兩人有時一起打出去(大俠只有一個人對付他倆,可是,他們的陣仗就好像少林寺真的開打!),有時,老頭兒和女粉絲,一個接一個打出去。這麼多名人勸架,說也奇怪,就像電視不斷重播政壇混戰,勸了半天,皮包、鞋子、椅子、玻璃杯……齊飛,吼吼叫叫,不認輸的、恐嚇的、挑釁,打中、沒打中、勸架反而被打,實在和電視上很像。
(我雖然也被老頭兒和女粉絲衝過來好幾波給嚇到,忍不住想著:難道老頭兒和女粉絲真是電視看多了,耳濡目染?依樣比畫?名人在議場勸架跟在餐廳勸架,都一個樣?)
終於,打架好不容易勸熄了火。小羊的丈夫元寶來晚,他坐定聽旁邊人談到剛才那一幕,竟然笑開說:
「我一點也不奇怪!他們之前在我家已經打過一架了!」
「什麼?什麼時候的事?」大家紛紛問,卻也沒有特別注意聽元寶描述這兩個(加上女粉絲,三個)脾氣火爆是對等的。
「老人家不甘心兒子把命奉獻了,落得沒沒無聞,從兒子死了以後,一直不平,說這樣不公平,鄭南榕有紀念館,他兒子沒有。」
「這怎麼比?根本不能比!一個是做基層,到處給人家幫忙助選、聲援社運,以前就是沒沒無聞。另外一個是宣佈要以身殉道時,已經很有知名度了!」
老頭兒和女粉絲總算給在座幾位名人面子,靜靜坐了一陣,聽幾位人士發言。或許還有別的事要忙,沒吃什麼東西就先退席。
他們離開後,有人問大俠:「剛才到底怎麼回事?怎麼突然打起來了?」
聽大俠說明,才知道是「鬱卒」!
「鬱卒?誰鬱卒?」
「老頭說他鬱卒,我說,大家都受過苦,不要埋怨!」大俠說著,比畫對方找人打架拳腳齊發。
「他要打架,我奉陪,那個女的也凶過來,我不會看她是女的就讓她打我!」
聽了大俠說「老頭說他鬱卒,我說,大家都受過苦,不要埋怨!」我一陣心酸。大俠剛出獄的時候,我的老闆鄭南榕派我去採訪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本人。以後,大俠和太太都到林義雄家改為傳播上帝福音的「義光教會」當志工。他們那個「藏匿案」,牽連的大都是長老教會人士,大俠家是史達拉最後藏身地,大俠一家人都為仗義助人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我和他們夫妻成為好朋友。大俠的妻子慢慢恢復了笑容。大俠面容上的風霜卻日日添增,好像這些年裡這兒真飄下雪!
打架的衝擊過後,接著而來的是一場風雨前的電光。很有戲劇效果。元寶打出預告片,透露史達拉大老要搞一場「大的」。
「他已經準備了露營車,車上什麼裝備都有,他這個人專搞大的,車子往那裡一擺,他就不走啦!聽說已經串聯得很可觀。」
我不以為然。我說,每年這個時節都會有拿紅旗的勞工抗爭。
「順便搭列車吧!」
「不是順便搭列車!其他路線的也會來!」
「總是這樣呀!社運裡,大家都擠在一把傘下面,在裡面還是分得很清楚。不缺席,也不被收編。」
「這次不一樣啦!某某年的學運,後來逼得李登輝和留老大合作修憲。留老大那時把我找去。上次被他相中,是『美麗島』後期,我那時才幾歲呀?本來是史達拉在做的。這次,史達拉和留老大也在較勁。」
「元寶總是被人相中。『白血瘤』不是也相中過?」
「以前哪裡知道那是『白血瘤』?吃人肉不吐骨頭!」
「元寶,你現在還有沒有在老地方當顧問?」
「全都解聘了!預算全都刪了!」
「失業?」
「我們一堆都失業了!」
「最好不要跟李登輝有瓜葛。」
「上次修憲不錯啊!還有要修的,上次來不及修,各路結集往陽明山上衝,都要失控了!」
「現在一提到修憲,就怕怕!」
「問題是,你們看『長孫的長孫』過得了關嗎?」
「過不了。」
「會拖垮……」
「可是,如果發展超乎預料,誰有那麼大的自信?」
「制度還在啊?正的出缺,副的扶正。」
「我不贊成。我會公開呼籲史達拉:別跟魔鬼打交道!」大俠說,嚴肅而堅定。
「我也不贊成。」我接著說:「你們可能沒有在工運待過,又紅又專的那一派,根本不可能一起做事。」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經由這個聚餐,我才知道阿薇已經死了,幾個月前離世?
這麼多人跟她是好朋友,竟然沒有一個安息聚會。
這些年的變化太大了。老朋友不一定一年能見一次面。尤其,一些老朋友是在最高階層服務,除非特別有緣,不然恐怕老死不相往來;仍有老友誼、或是早已視若陌路──都會是「老死不相往來」。
想到阿薇。
她從日本回來,健康檢查發現得了三期癌症,同時摘除子宮和卵巢。我去陪她幾天。陪她到植物園去散步,享受那美麗的園景。鼓勵她勇敢地作化療。
有一段時間,好朋友輪流陪她。後來,聽說,她這生中很重要的一位男友從國外回來陪她,是這個原因?或是,我被她的悲劇落到極深的痛苦裡?我沒有再去陪她,只跟她通電話。
幾個月之後,於這樣的場合,聽到她已經死了,幾個月前。
為什麼是經由這樣?
她是那麼單純,像天使一般可愛的女孩。
卻是在這般如火獄的現實中,傳來她的死訊!
唉!只有天使能穿越火獄的現實?!
3除夕&新年初一
除夕忙到初一凌晨兩點才睡,很累卻很愉快。雨聲和遠遠近近連續不斷的鞭炮聲,是在台灣鄉土過年特有的氣氛。感謝主賜給我這麼美好的年夜,和家人聚餐,用skype和遠在國外的親人通電話,skype視訊可以讓我們看到彼此。夜深後,我不免想著,這麼快樂的年夜,我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
這是我多年來少有的在家裡快樂地過年。其實,我生活裡滿滿的憂慮,入睡後的惡夢頻律太高,我的夢比時局還要恐怖,好像提醒我白天令人不安的時局潛藏更多、更直接壓迫身心、更具體的形勢佈滿事實!
帶著白天快樂準備年夜飯、準備過年需要的種種佈新,帶著滿意、滿足和感恩惜福的心情入眠,卻一腳踩進惡夢夢境。夢到新戒嚴國度裡,我倔強地勇抗如希特勒興起之際亢奮的軍民!我被嘲笑,被羞辱。(那些嘻嘻哈哈的軍人掀起我的裙子!真恐怖!他們更是笑得厲害!我在這麼壞的狀況下,還繼續發揮抗爭精神,怒斥他們:「你們雖然穿了整齊的衣服,但是你們整齊的衣服底下是更卑鄙的靈魂!」)
初一一早起來,煎年糕。把一鍋盛了米糕、饅頭、可以夾素食或是蜜汁火腿的刈包,整鍋放進電鍋保溫。再洗一堆新鮮棗子,放在客廳桌上。不論是平常或過年,看到翠綠的新鮮棗子,就讓我想起阿樺。他生前和高雄縣農權會農夫們相處,農夫教他辨識一種棗子可以摘下來賣。
(現在還有誰會拼命為理想、為信仰獻出生命?大環境沒有這個氣氛。)
我和家人拜年,請家人隨意用餐,我說,我吃吃年糕、早餐後,還要睡。媽媽說,我這幾天太累了,要我多睡。
(這就是恢復單身的好處,自由自在。可別說我不愛做家事,我會做,做得好好的。)
我的臥室就是我的書房,就是我的工作室。從除夕到初一,即使再忙,我還是會花時間做我自己的事。好像當了母親,情況總是不會改變,工作的時候,孩子總是在身邊繞著;儘管事實上,孩子早已離得遠遠的。
下午補眠,夢境依是熟悉。女兒還是唸幼稚園的樣子,她告訴我,女兒買給她一個手錶,好幾萬塊新台幣。我想,那是當然。女兒在米國大城市有很好的工作,買個高級手錶給女兒戴,很符合她灑脫的個性。
夢裡,我怎麼沒有詫異,唸幼稚園樣子的女兒,和買手錶的媽媽,都是女兒?我只是懊惱著,我忙自己的事,沒能碰見「買手錶的女兒──就是現在年紀的女兒」,她對我還是不滿,不讓我看到她。
醒過來,心酸很久。我記得夢中,唸幼稚園樣子的女兒,還騎著小三輪車戴弟弟。兒子仍是那麼小,甜甜笑得可愛。
夢像連續劇,我無法拒絕看的連續劇。
事實也是。現實怎樣令人憂煩,卻是由不得你不看的連續劇。
但我卻有著不曾享受的快樂、滿意和滿足。
以前,過年往往是最艱辛抗爭,不知道下一秒鐘身在何處?
我不得不自問: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
再過五十天,總統大選就會分曉。這句話,近來常掛在人們嘴上。但漸漸,五十數字會改。我覺得呼吸的空間越來越小。這小小的間隙,就是通往惡夢夢境的小徑……
4農曆年初二
過年期間,網路新聞較少。媒體、記者也要過年。
以前我在報社當文教記者時,過年前,採訪組同仁排年假,我們預知過年期間報紙的版面變得簡單,篇幅少很多,記者的工作量減少、要交出的稿件字數額也比平常少很多;真的有過年的氣氛。
「蓬萊島雜誌事件」、「陳文成博士命案」使我兩次被迫離開報社。第二次被迫離開報社,確定無法再申請復職,當時萬分依依不捨,特別是,之前主管曾告訴我將接跑醫藥新聞,那是我很有興趣的採訪路線。竟然擦身而過!之後捲入更敏感的政圈。很長的時間,過年於我,是與一般人背道而馳,幾乎忽略過年的傳統意義,只是盡一點點如蜻蜓點水般為人子女的責任,抽出一絲絲心神陪一下家人,就趕著跑自己的抗爭行程。回想花了那麼多年浸在政圈裡,過著非人生活,實在可怕!
這次立委選舉,慘綠的慘敗,敗得跌破許多人眼鏡!有些人似乎非常非常意外,彷彿賭徒一瞬間翻牌,不敢相信竟玩了一場「零和遊戲」,手中的籌碼輸光光!就像Discovery紀錄片拉斯維加斯專輯中的豪賭客,呆呆看著牌局,那一臉神情──不敢相信、不願相信、卻是事實擺在眼前!
多年來,TW的政客為了拉攏某一方選票,是否開放賭禁,風聲放了收、收了又放,來來回回玩了好幾手,終究還沒要開放賭禁、開設觀光賭場。但是,TW活生生上演的賭劇,可真是真人演出!驚險無與倫比!
一場立委選舉下來,北部指標地區,台北市綠營掛零。台北縣只拿兩席,學運出身的眾明星只剩一席,加上空降部隊一位真正來自歌壇的歌星披綠戰袍奪下一席。兩顆星而已。
這是驗收綠營三十年民主運動的成績單。
「哇塞!倒退到黨外時期!比黨外時期還慘!」
「黨外時期台北市還沒有掛零!」
「美麗島事件之後,家屬參選拿的票創紀錄、席位也大突破!為日後政黨輪替奠下基礎!」
「到底是怎麼輸的?!」
「這是突然發生的嗎?」
「從石頭裡蹦出來的嗎?」
「那政黨輪替後,八年來的豐沛資源流失到那裡去了?」
「從台北市凱達格蘭大道出發的紅衫軍領導人史達拉和留老大,終於復仇了!」
「史達拉和留老大,笑得出來嗎?K一黨獨大後,他們反而沒有混的空間,沒有再當傭兵的條件。」
「人生一趟,能看到綠營打破TW歷史『富不過三代』,執政兩任就回到從前,我們真是不虛此生,親眼看到歷史怎麼來、怎麼去?」
「慘!」
「可是,有那麼多人高興他們大大勝選啊!」
「你看那個賣燒餅的老伯伯,這幾天笑得多溫馨呀!本來他是天天生氣、臭罵,見到客人上門就指著牆上的電視新聞臭罵,現在脾氣好多啦!看到人就笑,講話客客氣氣!問候你一家老的小的。」
「賣燒餅的老伯伯不要高興得太早!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以後可沒有小黨生存的空間。沒有財富,選舉根本沒有你玩的份!多少政客花錢如流水,還不是落選、破產!你們小老百姓以後再臭罵吧!看誰理你?」
「馬科的他媽說,被罵就是表示進步;當然是有進步!倒不是說馬科被罵罵得好、罵得對,而是李登輝說得對:要逼K走本土路線。馬科的一票人不都是綠營走什麼路線,他們也走什麼路線!」
「這才滑稽!馬科要學綠營走本土路線,綠營要學馬科搶中間選民的票!李登輝要他的崇拜者黃土派轉型,改走中間偏左關心弱勢!真是大風吹,換位子!你學我,我學你,他學我。」
「你還相信他們開的漫天支票啊?他們包山包海,左右統獨、統中含獨、獨中可統、既右又左、既左又右,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他有的是時間跟你論辯,他們又不要上班,調一調舉債上限,協商協商,沒錢也可以分享權力,這就叫做『協商共生』!」
「這樣,我也會當黨政官大員!」
「問題是,你發現新大陸太晚!這一塊美味上好肉,早在你還是『憂鬱少女』、『少年維特的煩惱』時,由天才集團訂下了終身享受不盡的保單。打從那時期,天才集團所說的『有意義的少數』、『社運進軍新國會』,就是職業政治工作人的終身職保障,落選敗選換老闆都難過不到他,你還傻呼呼地難過得活不下去,他永遠不會失業,年資照增照算,薪水和以後的退休金一毛都不會少,不管西進紅中,或是東進靠老美,他照樣天天爬升、年年高升、儲金、現金、股票、基金、房地產,年年增加!賭你一碗牛肉麵──你孫子的孫子投票選總統,還是這個集團的徒子徒孫在搶大位!你孫子的孫子照樣還是被動員出來扛轎、拉票加綁票!」
「我現在才領悟我老爸說,他少年從軍被K騙了一輩子的意思!要自己親身走過,用一輩子青春當學費,才真正學到了教訓!」
「什麼叫作『有意義的少數』、『社運進軍新國會』?有那麼好康的事?『訂下了終身享受不盡的保單』?幾十年前『社運進軍新國會』,那幾十年後的今天『新國會』指的是什麼?現在不是有最新的『新國會』?」
「『有意義的少數』是說:一個人、或是一個半人(那半個人,意思是說『兼差亦可,可以有一半的上班時間在他爸他媽的祖產、家族事業、或繼承的家業上班,選舉到的時候,多捐一些政治獻金,政治獻金也可以抵稅;所以說,賺好幾番啦!』)──解釋『那半個人』,差一點說得太遠,忘了正題。再說一遍吧,『有意義的少數』是說:一個人、或是一個半人可以出發打天下,奪權,不要拋頭顱灑熱血也可以革命取得執政──得天下!」
「太誇張了!怎麼可能?你不是說過,K是世界上少數掌握最長統治權的組織?是世界上少有的獨裁集團?哪那麼容易把它革命取得執政──得天下?!」
「是不是真的?信不信由你!聽說天才集團的始祖,到老美取經,老美的深深喉嚨──就是說,調教出『水門案』那個關鍵人物『深喉嚨』的師傅,把一套比CIA還厲害的功夫傳授給他,那是可以在不管那一種體制裡都能夠對付老共。K是被老共打得落荒逃到TW,既然有了深深喉嚨的絕招功夫,K怎麼會打不倒?這也沒有什麼大學問,老共不是最會搞正反辨證、拉一個打一個、人海戰術、蹲點、聯合次要打擊主要;用老共反老共──K和老共,生生世世不是彼此彼此,互為對方生存戰鬥意志,死的是人家的孩子!只要找好接班字號人物,完成形式程序,就可以放一天休假,什麼也不會發生。」
「既然內容沒有什麼大學問,何必還要拖那麼長的時間競選,勞民傷財?」
「競選時間本來就定得很短啊!哪裡想到,TW賭性太深,賭徒太多,搞得天天在選舉、年年有選舉、大選小選一大堆!立委選不上,回頭佈署選地方民意代表,地方民意代表再往下擠選里長。什麼都選不上,也可以弄個競選幹事、助理。不然,摸摸門路,包工程。或是從組織後援會,從零做起,總是有參與的管道。」
「誰說一定要『參與』?」
「人家台大政治博士還留美、留歐,苦修好幾個博士回來,大學待過、財團基金會待過、財團的媒體待過,一山望過一山高,後來還是覺悟到:『參與』、『決策』的重要!不是書本說的『做大官不重要』,『做大事才重要』;而是『距離權勢最近的最重要』!『參與決策』、『我作決策』最重要!說『公僕為人民服務』,騙小孩的!沒有『公僕』,只有抱著政治獻金『服務未來不服務的公僕』。幸運的話,『未來不服務的公僕』當選,看他是不是還對你說一聲『你好嗎?』、還跟你點一點頭,若是走過你前面,眼睛也不看你一眼(以示你在他的選民名單裡,雖然有投他一票,但你的財經社會地位太低,他根本不會浪費一秒在你身上。一點也不足為奇。)」
「那那那……」結結巴巴。
「你想說什麼?」
「TW人的尊嚴、改變TW的命運、TW加入UN、獨立建國!」
「你看可能嗎?也許可能吧!也許有奮鬥就會有改變,一點一點的改變。」
5農曆年初五
網路氣象報告,農曆年前後一波波冷鋒過境,是入冬以來最冷。過年後,還有冷鋒接著來。這種陰溼冷天,卻到處可見綠樹,我的臥室毛玻璃窗上總是映著矇矇綠葉影,不時隨風搖動;寶島的氣候特色盡入眼簾!
很長的時間,我不看報紙,不看電視新聞。電視的開關總是擺在Discovery紀錄片頻道,有時轉往電影台。走在商街走廊,我避免目光接觸到販賣報紙的攤位,連一版頭條特大號的新聞標題也別想鑽進我的視線!不過,往往躲不過商店、餐館牆壁上的電視影音,一些聳動的即時新聞就這樣鑽進我的視線。其中一例就是中正廟改名衝突中,一位電視採訪記者被拼裝車碾過血淋淋的鏡頭!
(我喜愛採訪,當記者原是我的本行;我會願意像這位記者一樣,冒著危險跑新聞嗎?當然不會。我連進入新聞界都不想了!但是我尊敬這位走過鬼門關的記者,這件悲劇使我心情久久沉重。那麼多沒有營養的東西,卻要耗費人的寶貴時間、生命去推陳出來,可悲又可悲!)
雖然不喜歡看新聞,只在網路上看看,腦袋裡還是塞進了沒完沒了的人間廝殺、打混。一些真人真事的連續劇,往往令我拍案叫絕!
話說,渾沌戒嚴時期,未來的諸家天才幫眾,準備生產叫做「突破黨禁」的產品。(日後人們才知道,天才幫眾堂口甚多,不勝枚舉。有一個人一個幫,絕不收入門弟子;如名號「虎大」者。但是,他為了要與別的眾幫眾堂口競爭,卻也不禁止到處冒出打著「虎大」招牌的徒子徒孫,「虎大」本人不與之劃清界線,有時還順勢利用。而真正是他雇用的屬下,他不否認也不承認這些屬下被視為正宗「虎大」子弟兵。他的不否認也不承認,人們姑且就稱之實乃──他的名片印著綠色的圖印:「有容乃大」。「有容乃大」把他其貌不揚的三角臉妝扮得有智慧、有愛心,真真發揮助選功能,讓他從小地方民意代表,步步高升。不過,他並不是每戰皆捷,他幾次落選跌到谷底,他終還是沒被擠出擂台。)
你絕沒想到,有一天,人們在談時事時會把「虎大」例在第一順序,就像渾沌戒嚴時期,沒人會想到有那麼多個平淡得可以放進路口行人潮中,一個個都和三角臉擠爭第一順序,而好些個氣宇不凡的明星,把第一張板凳坐熱轉到坐涼,還有明星本來被賭徒相中是未來總統,卻意外英年早逝。
於是,黑馬一一爆出,在命中該上場的「虎大」還在坐冷板凳時,不按照劇本上演的「突破黨禁」,意外在寶島出世。綽號「長孫的長孫」,也意外在寶島坐上總統大位。而渾沌戒嚴時期,未來的諸家天才幫眾裡,一人一把號的樂團,剛剛好把中華民國設計藍圖裡的眾多官位填滿;有時候彼此換換位子,有時候實踐轉型正義,刪一些、或空缺不補。讀者不健忘的話,有些榮譽職分贈敵我各方,上上下下,官運隨人轉。
現世,沒有比綠營在農曆年前立委大選慘敗更大的新聞了(世界各國著名媒體都有報導)。
過年期間,莫非記者沒新聞可寫?竟然有一則網路新聞被台獨基本教義派大量e-mail傳往世界各地(形似當年黨外「批康」之前的累積能量,現世報?);「打不死的蟑螂」被一家通訊社小美眉描述得成「蓋世奇才」(好萊塢新片搶農曆年黃金檔期,正在寶島各大影院上映,片中男主角是美國一位青壯派政客,幫阿富汗爭取金援擊退俄軍)。
小美眉描述「打不死的蟑螂」,在綠營立委大選慘敗後,依然瀟灑,力抗綠營營內競爭對手搞鬥爭,不僅保住了自己的官位,也保住了一大票老闆的生財之道。(大老闆們不需要再升官,官位都已經坐滿自家人。再升,得和敵我各方人馬修憲制憲,那是做不到的事。敵我各方人馬都說得很清楚:「在憲法一中之下,那是做不到的事。」)
這新聞實在是很新鮮。綠營立委選輸,輸到比黨外「批康」之際還不知令人非議到地平線以下多少層地獄,可當年「批康」英雄「打不死的蟑螂」還一派瀟灑,迷死通訊社的小美眉,描述他對付記者「令人又愛又恨」,他的老闆之一也對著眾記者帥哥美眉說:「我知道你們記者帥哥美眉就是對『打不死的蟑螂』有興趣。」
布農族青壯作家伐伐曾描述,布農族族語把藍分成「像深潭的藍」、「最藍的藍」、「像好天氣的藍」,伐伐原住民的智慧能否教綠營,如何分別真的綠與假的綠?可惜伐伐以四十九歲英年,在農曆年前因心肌梗塞去世(和大魏突然過世同樣的疾病,同樣令人嘆息!)。
現在搶抱綠旗,就和戒嚴時期搶抱黨外招牌一樣,死不鬆手。
現在一些政客搶搭西進中國列車,就像黨外時期爭取海外台灣同鄉會設立的獎金,唯恐落人之後。
那些「打不死的蟑螂」蟑螂群,以前囊括海外台灣同鄉會設立的獎金,卻轉個身換上西進紅袍;蟑螂群還是有本領要海外台灣同鄉自己花錢買飛機票回來投票,是誰活該如此?








 二手徵求有驚喜
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