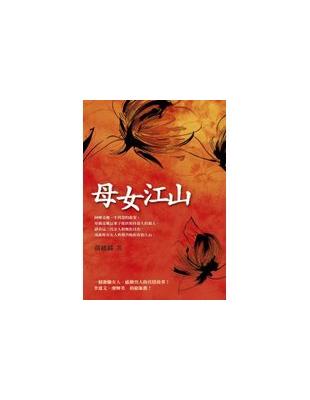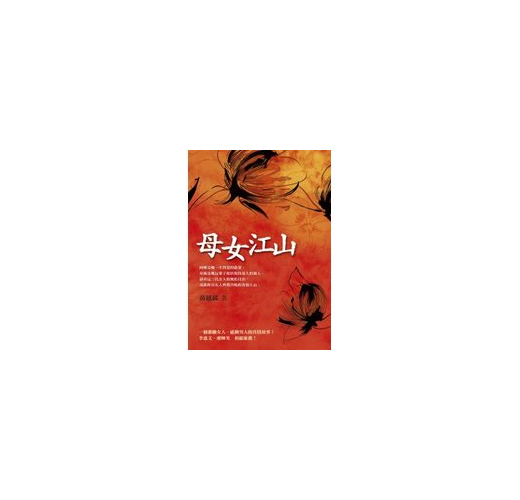■ 阿嬤說人要「量積福」
一位校園的女性清潔工,打掃到一間學術論壇會議室門口,聽到裡面有激烈的爭論,不覺放下腳步和手上工作,好奇地探頭聆聽,原來是兩派學說各執己見,正為「遺傳」與「環境」之影響與差異展開辯論。清潔婦納悶地聽了一下子,臉上突然露出不屑的神情,搖了搖頭,自言自語道:「唉!讀書人還真會找碴,這種事有什麼值得爭辯的,小孩生出來後像父親就是遺傳,像隔壁的不就是環境了嗎?」
常有人問我什麼叫愛心?我總謙卑的回答:「熱情、憐憫加付出,但不求回饋。」雖然西方有句諺語:「Killed by Kindness.」也就是所謂「好心沒好報」,但若因愛心的付出被錯怪,總比自己去錯怪別人的愛心要來得心安不是嗎?至少心理壓力與負擔少一些,離憂鬱症就可以遠一點。價值觀這東西是很難用有形或等質來衡量的,自己心中的那把尺才是價值的度量衡;當個平凡人對外在的異樣眼光、誤解及負面的回響,情緒上是很難不去理會或在乎,但如果太在意或不能用同理心理解,就易被影響、動搖及扭曲。
當你的價值觀確立,並變成生活中心思想的一部分時,一旦把它運用在言語或付諸行動時,你的態度就會不知不覺地散發,以及傳遞出屬於你對某種價值觀內化的精神,久而久之,在無形中就變成你個人獨特的氣質與魅力。事實上,很多的價值觀是由觀察、學習、發展與創意中得來的智慧,集大成而演變成自己的一套中心思想。
我阿嬤生於清末民初的中國,是屬於裹小腳的閨秀行列。她雖生錯了時代,但在她被封閉的小腳上卻支撐著博大無比的睿智;雖然我有母親,但從小與阿嬤同眠共枕了十幾年,也算是隔代教養中的受惠者,一直到我婚後生了第三胎時,她老人家才過世。在這段漫長歲月裡,從她身上汲取不少老生常談的菁華,讓我的人生路上,處處攜帶著她遺留下、讓我拈來就可用的錦囊妙計和舉一反三的範本,足以陪伴我披荊斬棘,並給自己找到堅強勇敢與活下去的支撐點。
更因為她能感同身受女性被迫裹小腳這件非人道的行為,並引以為憾,所以她給了我們這群兒孫晚輩很充分的自由,尤其鼓勵女性千萬不要妄自菲薄,時代總是在往前走。
阿嬤曾幽默地表示她長壽的意外收穫,就是她雖一生平凡,但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卻比她氣短而先走了,包括大清帝國的光緒、溥儀,中華民國的孫中山、袁世凱、黎元洪、蔣介石、蔣經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關於這點,父親更是長壽,但他的看法可就比阿嬤悲觀多了,他說:「人活得越老,朋友就越少,縱然有錢,一旦老了也未必能來得及買到真心的朋友,何況人老到一個程度,你連接受自家人挑戰的勇氣都沒了,哪來心情交新朋友?」
母親由中國福建廈門初抵台灣,雖然閩南話是她的母語,但到底生活習慣及文化上的隔閡與差異,導致她剛到台灣時頗受婆家的刁難與歧視(雖然後來均化解並互通有佳),加上又懷了身孕,於是只好向她遠在天邊的母親求援。阿嬤不忍女兒受苦,只好放棄在中國的一片江山,倉皇中攜金帶銀地乘著最後一艘三舨舢,茫茫大海上幾乎除了喝水、沒什麼進食地顛簸了數天,才抵達布袋港(當時的父親與友人在布袋港創業經營船務報關行),從此隨我們一家人輾轉遷徙,一住就是三十多年,最後壽終正寢在台灣。
她常感慨說人要活得夠久,檢驗人情世故的機會就多;但人要自己走得夠遠,才能有深刻的體驗與應驗。因此,阿嬤常用兒孫自有兒孫福、不為兒孫做馬牛,來強調子女成長後獨立的重要性;更以「父母疼兒女有如長流水,而子女回饋父母乃樹梢風搖」不成比例的意境,來告誡親情的無奈與鎢毋須執著。她又把「行善」比喻成人行道,隨時隨地拈來就可做。但「作事業」則像開火車,要有目的地往前衝;停站是為了加油,而「冒險」則像獨木舟,汪洋大海中一切得靠運氣、毅力和對希望的擁抱。
阿嬤雖然對黃家的每個孫兒孫女都疼愛有加,但對我則較偏心,每次從台北回到新營老家,阿嬤和母親總會張羅準備一些家常菜或乾糧,以及土產等伴手禮讓我帶回與同居的弟妹分享。對不論購物和攜物均嫌麻煩的我而言,她們最常用的說服語句就是:「人如鳥飛,人到物就到。」
有一次,我堅持不帶任何行李,結果看她老人家有些失望,不忍心之餘,只好諂媚地安慰她:「阿嬤!我現有的行李中都已裝滿對您無形的思念,再也裝不下那些用錢就可買到的東西了。」阿嬤沉默了一下,用古錐的表情回道:「那我就用你我咱兩人加倍的無形思念來煮這些有形的東西,豈不是更無價?」果然是狠角色,想虛偽搪塞一下,還是被她的機智反應給識破了。那天回程,我只好大包小包一肩扛,應驗了「乞食(乞丐)過溪,行李特別多」的無奈。
阿嬤對我的愛總是無法想忘就忘得了,記得我懷老三時,回台探親,但不知道子宮的前置胎盤剝落已出了狀況,下體老是見血怕小產,偏偏我的婦產科主治大夫在馬尼拉,於是看了中醫並開出安胎藥,每天只能稍安勿躁地躺著,而阿嬤三寸金蓮的小腳上撐著她肥胖的體重,還要為我煎藥,然後再辛苦地爬上二樓端給我喝,而且一定要看我喝完她才放心,回憶到這裡,我的淚水竟模糊了草稿的字跡。
阿嬤在人際關係的溝通中,自有其一貫的主張,包括:
一、「先禮後兵」,理由是見面三分情,先尊重對方,如果對方也以禮相待,則可化干戈為玉帛,否則給對方空間,相對的就是給自己時間來累積過招中「知己知彼」的能量,吵架或爭執總沒好話,但如果能先儲備好足以佐證或反駁對方不合邏輯的論述與錯誤事證,一旦雙方非不得已開了戰,己方雖未必能馬上旗開得勝,至少也不致立刻潰不成軍;所以「禮不可廢」或「先禮後兵」雖不全然呼應了「兵不厭詐」的孫子兵法說,但對阿嬤而言,「算帳或開戰前就要先存好『相罵本』(爭執的本錢)」,莫當潑婦或耍無賴的流氓,同時也是君子之爭的基本原則。
二、「理直氣壯」則是當仁不讓的不二法門。阿嬤常說一個有膽識的人是要有智慧的,否則有勇無謀變成「小不忍則亂大謀」,會因草率魯莽而易出亂子。而「有識無膽」往往是知識分子的悲哀,口說不練沒有行動力,卻又老在避風頭撿功邀中遊走,此乃偽君子也。
三、「打蛇七寸」則是強調人以和為貴,凡事過猶不及均傷感,且得饒人處且饒人,人既非聖賢,孰能無過?不要趕盡殺絕,要給人留餘地;簡言之,冤家宜解不宜結。
四、最後相當重要的則是要「量積福」。因為心胸度量的寬窄足以影響發展成就的高低,有度量才有悲天憫人的慷慨,更是愛心的特質。
以前家裡環境不錯的時候,經常有些鄉下務農的親戚會來借錢,因為農夫是看天吃飯,若不是因為子女眾多要註冊,就是由於天公不作美,遇到收成不好,只得寅吃卯糧,希望能先借到錢,等到下次收成後再連本帶利償還。我印象中很深刻的一次是母親還未開口,阿嬤就直接告訴對方說:「天打天晟,一枝草一點露,利息就不用算了,與其要還我們利息,不如在收成時,尤其是收成番薯時,田地別翻得太徹底,讓那些窮人家的小孩可以跟在後面偷撿幾條番薯回去充飢吧!」
■ 一時風光,一世慈悲
父親的中年危機是離開政壇,又意外面臨藥廠經營不善,船務報關公司被捲款逃逸到香港,而其中尤以出自善意、為其好友當銀行貸款的連帶保證人,但對方卻在無預警下惡性跳票並倒會;如此排山倒海被一波又一波而來的經濟危機幾乎令人無法招架,全家頓時處在慘淡的困境中。儘管風雲驟變,幸運的是父母親都還能勇於面對,分頭主動外出找工作來貼補家用;母親更放下身段,典當了所有的珍貴手飾,由旗袍改穿長褲,高跟鞋換平底繡花鞋;阿嬤也想盡辦法縮衣節食來維持家計。
由於父親曾擔任兩屆民意代表,雖然已卸任了,但仍有官辦報社繼續免費供應報紙,於是阿嬤就在「窮則變,變則通」的靈感下,拿麵粉勾茨煮成漿糊,再將十六開的全張報紙裁剪成八正方或十六正方,每張對摺後,兩邊再塗漿糊封口成型;她不但動員全家小孩在寫完功課後就得開始一起糊紙袋,還特派我每隔幾天下課後,將糊好的一大疊紙袋綑綁好,用腳踏車載去賣給菜市場裡頭姓陳那家最大的雜貨店。
嬤命難違下,我只好硬著頭皮嘗試去完成這項任務。那時我已經是高一生了,如果家境不是突遭惡化,想來正屬情竇初開,一定不知天高地厚,還很天真地跟同學們玩鬧嬉戲在一起吧!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這是鼓勵要成功就得忍受挑戰,但只要你是曾經有機會面對殘酷的挑戰或經驗者,即使不傷及你身體上的任何一根汗毛,卻已深深地在你的自尊心上刻劃下難以撫平的傷痕。
這家雜貨店在父親從政期間幾乎有事就來請託,而我們更是他的忠實老主顧,母親為人一向海派又愛面子,所以很少去秤斤計兩,進貨補貨恁由老闆說了算,因此還記得家道風光時,雜貨店老闆從蝦米到魚翅,從油、鹽、醬、醋到應景禮盒,幾乎一手張羅包辦,月初就到我家來清點貨色,然後月中跟月底分別再來結帳。
由於家中每天人來人往,開飯總是好幾桌,又是正餐又是點心,還有應酬不了的禮尚往來,所以就連肉攤販也是每兩天就送一大堆肉品,甚至還主動到我們家的廚房裡炸豬油,冷卻後再一壺一壺分裝備用,並將炸豬油剩下的「油渣」剁碎後,以紅蔥頭爆香,加入香菇末及醬油膏等佐料熬煮成肉燥。
俗話說,好漢不提當年勇,但藉小故事提醒切莫忘記世態淡涼下滄桑的教訓,也唯有寒天飲水者冷暖自知啊!當我兩手牽著腳踏車,後座載著一大疊綑綁好的紙袋打算賣給雜貨店的老闆時,老闆以為我是來跟他買東西,還笑咪咪地叫了我一聲「大小姐」。當我說明來意後,其臉色馬上一沉,心不甘情不願地叫旁邊的小夥計將紙袋拿到秤上,秤一秤重量,然後沒好氣地拉開嗓門說:「紙袋曬得不夠乾,想偷重啊!」當下我有如犯了滔天大罪,汗顏地低下頭,從眼角掃過的路人彷彿都在對我投以鄙視的眼光,頓時整個腦子一片空白,耳朵卻嗡嗡作響,手心更直冒冷汗。
羞愧中又聽到男夥計不耐地問著老闆:「今天的到底要不要收嘛!」我強忍著鼻頭已酸而眼眶裡直打轉的淚水,手指用力暗掐著手心,不斷地警惕自己千萬不能耍脾氣,一定要忍耐完成任務,否則家中就有斷炊之危,於是硬擠出笑容,委婉地跟老闆說:「真歹勢,這次可能曬不夠乾,下次我一定等完全曬乾了再送過來。」只見他又開始帶著笑容,用親切的語調招呼著來來往往的顧客,但就是不再正眼瞧我一下,只順勢揮了揮手,叫小夥計跟我算帳,還提醒他要記得扣沒曬乾部分的重量錢。
返家途中,我一面用力踩著腳踏車,一面任由淚水撲簌簌地流個不停,再強的寒風也吹不乾淚跡的傷痕。方進家門,我立刻從口袋掏出賣掉紙袋的錢,生氣地扔在阿嬤面前,委屈掩面地抽搐了起來。阿嬤聽完來龍去脈後,深嘆了口氣,用冷靜的口吻溫和地跟我說:「圓的人扁,扁的人圓,世間風水是輪流轉;昨天咱是甲方他是乙方,今天他是甲方咱是乙方,人生起起落落,沒有什麼了不起,不用太難過,別忘了囂張總無落魄來得久,妳可貴的眼淚剛才沒有在這種現實的小人面前流是對的,因為不值得。」
十多年後,我們家風重振,母親一向慈悲且健忘,所以不計前嫌又變成了這家雜貨店的主顧客,但對我而言,也許我早已不難過也不記恨了,但卻還是寧可選擇把此人當作空氣。
■ 以堅強成就家人的愛
大女兒Elisa婚後買了新房子,無論如何邀我去小住一番,在她家的後花園裡,她如數家珍地告訴我種了哪些花花草草和青菜水果,閒聊間一樣感慨,如果她外祖母(我母親)也在的話該有多幸福,因為她很懷念在新營與阿公阿嬤共處那近一年的歲月,她覺得倔強是咱家母系的基因遺傳,但一顆體貼對方的心卻又不衝突地存在彼此的親情血液中,她也補充了一則自己與外祖母之間的陳年往事。
在Elisa的印象中,她外祖母是很明顯的重男輕女者,從不叫她哥哥Edwin做事也罷,責罵起來也不同調。記得有次佛祖生日要拜拜,台灣一般家庭的神明供桌都會以正面安神位,側座安祖位,母親要Elisa上二樓去把香爐拿下來,結果才九歲的她根本分不清哪個屬神明、哪個又屬祖靈,於是錯把敬祖用的香爐拿了下來,被她外祖母大大斥責一番。
結果,她挾著壓抑、委屈、憤怒與羞愧等各種複雜的情緒而反彈,生氣地轉身直奔二樓躲起來賭氣,而她外祖母也懶得理她。巧合的是,當天近傍晚時,有人送來一個大蛋糕。Elisa從小就嘴饞且愛吃,因此綽號叫「阿肥仔」(胖妞),她躲在二樓,從樓梯縫看見阿公開始在切蛋糕時,心中已十指大動就快流口水了,可是礙於自尊心而只能望梅止渴,可是就在這時候,她卻意外與外祖母的眼神交會,嚇得立刻將頭縮回去;接著她看到外祖母雖仍擺張撲克臉不作聲,卻比手勢叫她下樓吃蛋糕,於是Elisa藉機下台階,嬤孫倆在彼此的倔強中,捧出溫柔的心適時給予對方感動。
當我們變成單親家庭後,我把三個孩子從菲律賓帶回台灣,暫時寄居新營老家,並插班就讀我過去的母校公誠小學。
後來因我在台北工作,三個孩子在隔代教養下,雖有親人的關照,但終究與父母親的愛是有差別的,加上在學校裡有語言隔閡、功課進度不能配合,以及同學們的種種歧視與後遺症,因此一年後,大兒子Edwin在某一天夜闌人靜,母子相依聊天時,突然問我一句:「Mom, Where is our real Home?」(何處才是兒家?)淚水幾乎同時出現在我們彼此的臉上,於是我跟他們三人討論並作出決定。殁了父親而身為母親的我又必須在大都會工作,無法全心全職的照顧,對年紀尚小的孩子們而言,其心靈上的滿足總是缺角的,既然在台灣生活不適性且費用又高,但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並不快樂,不妨就讓他們重返其出生的原成長地,較易恢復昔日名列前茅的自在與自信,只是從此兄妹三人必須更團結、更堅強才行,因為一旦他們三人逕自重回菲律賓就學,則將面對我仍須留在台灣賺錢的現實,如此一來,他們勢必真正陷入既沒爹又沒娘的辛苦處境。
最後,孩子們還是選擇回去馬尼拉,於是我先辭去在台灣各大學客座講師的教學工作,改成自由業,孩子們的就學及生活等一切安頓好後,從剛開始的不放心,我每個月抽空自台灣飛菲律賓回去看他們一趟;直到較安定後,改成兩、三個月回去一趟;到最後演變成一年中他們放暑假來看我,而聖誔節我回去跟他們過年。當時兒子十二歲,大女兒十歲,小女兒才八歲。
就這樣,他們三兄妹每天清晨五、六點就得自己摸黑起床,打點一切並趕搭校車去上學。套一句「歲月如梭」來比喻,一下子這個孩子小學畢業,另一個又進了高中,等這個高中的畢業,大學的那位卻還在就讀,他們三個人必須從小就學習合作張羅食衣住行,雖然當地傭人工資便宜,但不敢請全天候者,怕孩子們一上學放空城,隨時可以來個大搬家,因此只能請位星期六、日來清掃及洗衣服的臨時工。
至於家事方面的分配,大兒子掌管門戶及兩位妹妹的人身安全,還有每天外出倒垃圾的工作;大女兒則負責採購及煮飯做菜,而小女兒則負責清洗碗盤及協助廚房工作等;一旦考上大學到畢業為止,幾乎都保持績優,並主動去兼家教賺零用錢。大女兒曾因星期假日需到傳統市場買菜,以致被菜販喊叫「太太」而尷尬不已。試想她的同學中,又有誰像她才十一、二歲就得定期上市場買菜?但也因此造就了她廚藝出眾、又能享受美食的基礎。
三個孩子個別的成長經驗與記憶中,都有一段故意塵封不想多談的隱私,卻又彼此可感受到的辛酸,其中包括小女兒才八歲,逢颱風、停電的日子,小小年紀就必須獨自試圖在沒有父母陪伴的黑夜抵抗恐懼的侵犯,小時候她沒安全感、最愛哭,可是長大後卻很少流淚,我不禁捫心自問,難道不是童年時代哭了也沒用所造成的刻意堅強嗎?兒子更跟我提起當年幾次和妹妹們感冒或生病發燒到快四十℃時,連昏睡或夢魘中叫的喊的,竟然都是:「媽,我痛苦得快死了,但還是要告訴您,我好想您,我好愛您,多希望您能在身邊……」等共同語言。而就是這樣彼此靠著愛的堅定信念,以及追求未來全家團圓的希望,歷經了十四年,我由衷以他們為傲的這三位雖平凡卻勇敢、堅強又乖巧的子女,終於陸續畢業於國立菲律賓大學後,我們母子四人才得以在台灣完成一張正式的全家福照片,至於中間空白的那段影像,只能各憑意願去完成片斷的拼湊了。
■ 那段沉香之戀
少女懷春,初戀對女性而言,即使只是曇花一現,但仍會像顆珍珠般地用錦緞包好,深鎖在內心深處,或在一個只屬於自己的秘密花園裡,偶爾拿出來回顧、細嚼、陶醉或想像一番。儘管年代已久,記憶也失修,但仍無損那份塵封下的純潔;也因為天真才純潔,而純度越高的愛情,才更能令人感動與回味。
母親的初戀如果像首詩歌,可惜正譜好曲子,還來不及上弦,情絲就被截斷了。由於阿嬤的極力反對,礙於母命難違的壓力,她最後選擇了無奈的分手,造成終生的遺憾與永遠無法彌補的歉意。如果是男女雙方因另有心儀或外遇的對象,導致不願再受欺騙而分手也就算了,偏偏強勢介入的第三者不是他人,而是自己相依為命的母親時,亂了分寸和糾葛在愛情與親情拔河困惑中的她,必須作出影響她未來、甚至影響一生的抉擇。
如果忠於自己的感覺,繼續墜入愛河,可能未來的命運會如自己母親的預言,是場不得超生的災難。但若為了盡孝道而選擇無法割捨的親情,對自己和戀愛的對象又何嘗公平?對熱戀中的情侶而言,失戀的痛苦除了令人心枯且氣如游絲、彷彿已到了生命的盡頭外,在爭取戀愛自由的過程,幾經抗議、掙扎、衝突與矛盾相連扣的行動失敗後,母親終究還是在「送君千里,終須一別」的不捨下,作出了她心不甘情不願、卻與其長痛不如短痛的分手決定。從此,母親與阿嬤母女之間也永遠存在著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與嫌隙的屏障。即使阿嬤將其餘生奉獻給黃家,並盡心盡力地共同扶育了八個孫兒女們作為贖罪,但母親秘密心房某個角落的小門窗,仍是緊閉且任其蒙塵。
當我無意間闖進了母親早已荒蕪的秘密花園,注視著那株本應璀璨含苞待放的百合花,卻因早熟而凋零地被遺忘在不見陽光的角落。面對母親徐徐幽幽地吞吐著這段沉香的情愫時,我除了啞口無言外,依然只能沉默以對。一位為女兒願意用生命來承擔其幸福風險的愛情加害者,居然是我一生中最摯愛的阿嬷;而另一位為了成全親情、選擇放棄愛情的無辜受害者,竟然同時是我的母親。
一直誤以為談戀愛是屬於年輕人的專利,上了年紀的人似乎就應把熱情澆熄或保持冷靜的緘默,否則暴露在陽光下,更凸顯出逾期的尷尬與不堪回首的齷齪。這是對長者們何等的誤解與歧視,人活在世上,為了生存必須和生活的條件與環境妥協,但真正支撐每個人繼續活下去的卻是愛的力量。愛的滿足與需求不分年齡大小,只要有心跳的對象,就會對愛情有一份期盼。
愛情和麵包都重要,若能取得平衡更好。物慾是無止境的誘惑與權力擴張或填補的表相,愛情則是觸動內心深處的吶喊,令生命力舞蹈在多采多姿的旋律中發光發亮,即使結局俗不可耐或不盡如人意,但好歹在自己歲月長河的流沙中,曾甜蜜暈眩或幸福醃漬過,更可供給斷層的回憶,帶來無限的遐想空間與意象的告白。
母親是我兒女們的阿嬤,她留下的紀念品縱使再高貴也有市場行情,但她跟我分享的愛情故事卻足以留傳給子孫,做不切割的情史,攀藤在生命共同體的歷史脈絡中,令古老城堡的閣樓裡珍藏著無價的浪漫繪本,有興趣就可登上瀏覽並憑弔一番。
也許因為這個難以磨滅的切身之痛,讓母親不想犯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錯誤,所以她從來不過問兒女們的戀愛與結婚的對象,再不滿意的媳婦或女婿,她最多也只會覺得自己運氣差、無福消受,因為在她的觀念裡,媳婦、女婿均是外來接枝的品種,要多給適應的時間和包容的空間,才能與老幹融合成一體。何況天下的姻親都是愛屋及烏的延伸,兒子、女兒不孝,又何必牽扯或怪罪在別人家的兒女身上?母親可與離婚後的媳婦情深更甚於兒子,就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上。
我擁有母親這段感傷的秘密是在阿嬤還健在的時候,但我就是提不起勇氣再去跟阿嬤求證。即使阿嬤真的做出對不起母親的決定也已於事無補,何況,換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母親委曲求全後的處境,也算是建立在進可攻退可守且游刃有餘的空間裡;阿嬤替她作決定、選擇了父親,雖稱不上是慧眼識英雄,至少也圓了兒女成群、老伴攜手壽終正寢的世俗夢。
而她們母女最嚴重的一次衝突背後,那段為人所不知的故事,卻成了我從小隱瞞母親的秘密。至今我才恍然大悟,原來母親心中不願觸摸的痛,在透過父親婚後的風流韻事,讓它有如傷口上再被凌遲的痛恨感,而這種傷痛原本就不是她應承受的,於是當丈夫感情不忠而出軌時,她很自然地就會把這筆帳轉為無形的恨意,並直接投射到其母親(我阿嬤)的身上,因為她的母親才是剝奪她追求屬於自己幸福的原凶,同時也是讓她不得不去面對、接受及容忍丈夫感情背叛的不堪時的幫凶。
對於我這個年紀才十一、二歲的單純小女孩,經年累月在成年人、尤其是親人複雜的情緒中,也許不夠聰明到能領會出他們彼此互不相同的立場與爭執內容的各持己見,但至少學會了如何由觀察中,慢慢試著去了解自己在這個家庭的地位與存在價值;但也因為長存的這道被逼迫心智早熟的門檻,讓自己獨背了十字架,走了很長的一段歲月。
關於這段母親所不知情的另一個秘密故事,則是發生在某個仲夏夜,我因為怕熱又長了痱子,幾乎每天都需要靠阿嬤一面搖著芭蕉扇,一面幫我抓背止癢灑明星花露水,才能漸漸入眠。可是那夜,我突然被熱浪給沖醒了,醒來時卻看不到躺在身旁替我搖扇的阿嬤,反而在摸黑中隱約看到阿嬤略肥胖的背影正偉聳地站立在床鋪中央,我不禁害怕的大喊一聲:「阿嬤!」馬上跳起身子,上前將她緊緊抱住。
原來阿嬤對磨難生活的忍耐,與母親經常言語間的衝突;由失望、憤怒甚至已飽和到了臨界點,因此她選擇用結束生命來抗議。雖然我個子小,但很機靈,當下用非常俐落的手腳,把阿嬤攀上樑柱的繩索用力給拉扯下來,然後綑成圓圈狀,慌張地下床找個地方將它藏起來,再跑回阿嬤身邊時,阿嬤仍是無言地流著淚,像尊憂傷呆坐的女彌勒佛,除了沒笑容外,恐怕心中也已無慈悲可言。
那一夜,阿嬤跟我說了一堆不是我年齡可以理解或承諾的交代,像是:「妳母親心中也很苦,妳將來要好好孝順她……」之類的話,但對我而言,最害怕的就是阿嬤會再度離我而去,所以我又驚又急地跟著哭,並跪著懇求她老人家,一定要答應我不能再尋死,否則我也不要活了……阿嬤最後終於點頭,勉強擠出一句:「好!我一定要活著看妳長大結婚生子才死。」
這件事在阿嬤的交代下,我守口如瓶了數十年,直到母親告訴我,她這段苦情戀的前因後果,且事隔多年,阿嬤已去世,而我也早為人母,才將這段已形同石沉大海、永不見天日的故事,輾轉並委婉地跟母親提及。母親聽完紅了眼眶,同時長嘆了口氣,卻沒讓淚水流下來,或許是不願在我面前示弱,但也可能歷史太久遠了,已引不起她太多的激動。
總之,母親心中一直有阿嬤,而阿嬤心中更只有母親。但即使親如母女,是否能和平且契合的相親相愛,恐怕不是單挑血緣關係就能有答案的。不過可確定的是,她們彼此曾共同走過女人一生一世的風風雨雨,如今也都已寬心放下並安息了,所有生前的種種恩怨,恐怕在我擁有她們的秘密之前,早已消弭、寬恕或原諒對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