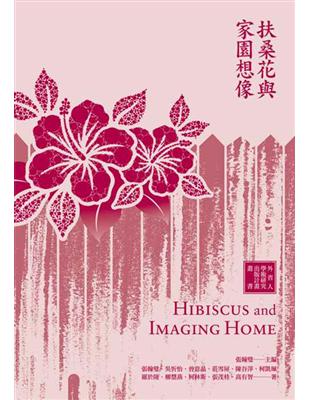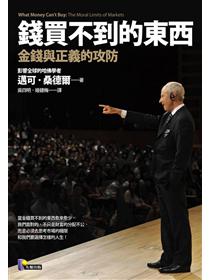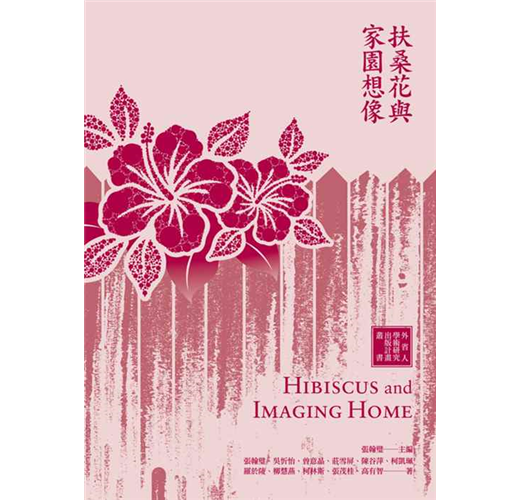一二三、到台灣:扶桑花與家園想像
張翰璧(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時間,看得見嗎?模糊的記憶中看見自己剪著短髮,在眷村的巷弄中,和玩伴們一邊唸著「一二三,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阿里山上有神木,明年一定回大陸」,一邊飛躍地跳著橡皮筋。依稀看見扶桑花築起的「家」界,夏天盛開的朵朵大紅花,以及秋天撲鼻的桂花香,我記憶中家園的圍籬是「扶桑花」。扶桑花是典型的熱帶花卉,也是台灣的公園或鄉間常見的圍籬植物,不但在緊密接觸的眷村中區隔出「家」的空間界限,也為眷村記憶抹上一筆絢麗。扶桑花開的季節,不論大人小孩都感染了好心情,媽媽們閒話種植心得並交換各自的品種,小孩則忙著在扶桑花叢間玩「躲貓貓」、摘花心、吸花蜜、被處罰……時間流轉中,扶桑花的品種愈來愈多、花開得愈來愈美,慢慢的,砌磚圍牆取代了扶桑花圍籬,最後卻連同房子一起不見了……這就是我記憶中的「家」:原本日漸成形,轉眼間卻整個消逝!那麼,其他人的記憶與想像又是什麼?似乎大不相同,卻又各取所需。現在,當我們要正經討論或自由回想「扶桑」或「竹」籬笆時,赫然發現「它」不在了,建築物拆了、老人凋零了、第二代遷居了……我終於知道,時間,看得見。
「眷村」是什麼?是歷史的產物,也是台灣社會的一部分。正因「眷村」已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以從不同的立場、在不同的場合,聊聊眷村的經驗。然而編輯本書的目的,是希望跨越「日常生活」來聊眷村事,在知識層次討論「眷村」及其相關議題。本書選了十篇文章,作者們從不同的學科背景、用不同的書寫方式,描述、說明或建構「眷村」的意涵,作者們不見得都有眷村的生長經驗,也不盡然是所謂「外省第N代」身分,他們只是單純從個人關懷與不同學科立場出發,告訴讀者他們眼中的「眷村」。
本書的編輯主要分成三個主軸:「想像眷村」、「眷村生活的多樣性」以及「變遷中的家園」,加上不可或缺的三篇附錄。
想像眷村 「眷村」記憶了什麼?記憶有許多載體:(1)口述傳統;(2)歷史文件或回憶錄等;(3)影像、照片或雕像;(4)儀式;(5)空間等。記憶和歷史似乎都不甚客觀,兩者都是我們對「過去」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選擇、詮釋,甚或扭曲,而且這些記憶的建構與想像過程都涉及詮釋者的社會脈絡。換言之,記憶是由社會團體所建構,社會團體決定什麼值得懷念和它將如何被記得。團體成員認同他們所屬團體的重大事件,他們記得這些是/不是他們親身經歷的事件,甚至變成他們生活的一部分。本書作者之一吳忻怡從「書寫文本」的角度討論眷村文學,「眷村文學」這個名詞曾零星出現在各別文章,學術界與文學批評界卻缺乏較為統一的定義或內涵。忻怡嘗試從作者背景、文章意圖、文本脈絡等三個面向,一一檢視其定義為「眷村文學」的適切性。除了檢視「眷村文學」的定義,呈現眷村族群與眷村文學的多樣化與多元性外,也將書寫過程視為一種文化實踐,希望因著這樣的書寫,讓眷村人珍視、保有生命經驗,也讓非眷村人看見同樣真實而值得尊重的生活過程。不管是漳州人、泉州人、福佬人、客家人,還是本省人、外省人、眷村人,每種人群分類背後,除了隱含對我族的認同、對他者的疑懼,也同時包括一段又一段落地生根的艱辛歷程。這個辛苦而費時的在地化過程,從來就不簡單,也絕對不只一種固定的模式。眷村人透過眷村文學訴說的當然只是其中一種,但絕對值得認真對待與理解。
然而,「眷村」文本不等於真實生活中的「眷村」,這個空間提供眷村內/外的人不同想像與詮釋,即使同是眷村內的生活者,建構的眷村經驗也大不相同,更不必然承襲父系的族群認同。曾意晶的文章就是要處理不同的生活經驗如何反映在「眷村文學」中,成為「眷村內/外」成員的部分集體記憶。成長於「眷村」的外省作家,諸如袁瓊瓊、蘇偉貞、張大春、張國立、蕭颯等,往往將眷村經驗反映在初期書寫的舞台,不論是瑣記兒女的愛戀心事、鄰里是非,到辯證家國歷史、反思記憶想像或操演情欲政治;在此同時,眷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習性、經歷的歷史事件,與外省族群散發的氣息或性格,也由作家一併建構於文本中。呈現在作家文本中的眷村經驗,可說是一種族群歷史的再創造。當然,這種文化歷史的創新也具有內在的差異,就如意晶文章後半段對利格拉樂.阿女烏「弱勢中的弱勢」的經驗描述,挑戰「眷村」=「外省人」的錯誤刻板印象,也展現眷村經驗中交織的族群(外省與原住民)、階級(父親的軍階)、性別(父系與母系)等經驗。
如果「眷村」文學呈現竹籬笆裡的差異與多樣性,則圍籬外的人又如何想像「眷村」?莊雪屏指出,平時有關眷村的議題很少擠上報紙版面,弔詭的是,眷村相關報導的比例每到選舉往往大幅成長。記者用公式化的「類型化說故事」方法,蒐集新聞事件、評論並建構一個所欲達成的結構和內容,使報導落入可以預測的刻板情節。甚至不論資深記者或年輕記者,總會跟隨原先的公式,運用標準化的想像、陳腔濫調的角度和觀點,以及早已深植記者與編輯心中的劇本,「建構」所謂的「眷村意象」。於是,眷村新聞的操作方式也就愈益老調重彈,眷村「挺藍」、「老夫少妻」等刻版化印象於焉產生。具象與空間意義上的「眷村」逐漸在台灣地表消失,但因媒體習於將眷村題材與政治產生關聯,而衍生了族群關係上無限推演的抽象等號:「眷村」=「外省人」=「泛藍」=「親中」=「統一」=「賣台」……。上述「政治同質性」意象的建構與立場推演,使閱聽大眾只注意到眷村的「政治性格」,卻忽略眷村內部的「社會性格」。在媒體操作上,「眷村」成為封閉的「族群之島」,實質的社會基礎(空間的逐漸消失、世代的更迭等)雖日漸消失,抽象的政治界限卻依然存在。如果媒體與社會大眾能以「不了解『眷村』,就不了解台灣社會」的新視角,重新解讀「眷村」、重探眷村的社會性,會發現眷村絕不僅止於我們以前理解的眷村。
眷村生活的多樣性 事實上,「眷村」不只是眷村,眷村內也不只雄壯威武的男性,眷村的特殊在於人文薈萃,包容南腔北調,也融合各省風俗,藉由男主人的同袍之誼,外省、本省、客家及原住民媽媽的和諧相處,眷屬們進入眷村也感受到丈夫們「親愛精誠」的情操;在初為人婦與人母之際,為了生活所需及延續生命,彼此在遠親不如近鄰的實踐下也互相扶持、守望相助,親如家人,所以眷村特別有人情味。眷村獨特的群體融合,安慰了軍人的思鄉情切,也共同撫育在台土生土長的「二世祖」(眷村第二代),此後再也沒有「何處是家鄉」的感慨,取而代之的是子女教養的話題,也就是有妻有子的家庭意識。
陳谷萍描述這些隨婚姻展開跨族群生活與建構生活網絡的女性,是如何從另一種角度建構眷村的集體記憶。這群具有不同地域、族群背景的婦女,進入國家體制集體生活的過程是:在她們的生命周期裡,歷經路徑相似的生活樣貌,從相異的生活背景到集體生活,她們日漸發展出一套屬於女人之間的溝通模式,透過女性的共通母職經驗與特殊經濟互助關係,使眷村婦女間的情誼得以超越原生的族群身分,並形塑眷村內特殊的人際網絡。透過眷村女性的生活經驗,從女性的位置發聲,彰顯眷村女性的生命能動力。
然而還有一種村,是眷村外的「村」。它們從軍眷制度面來說不算「眷村」,但從文化的角度觀察,他們和「眷村」又形成有意義的類比與對照,例如寶藏巖、大陳新村、一些退輔會安置榮民的集體農場(梨山、清境農場)。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政權,但仍保有海南島、金門、馬祖以及浙江沿海的舟山群島、大陳島。爾後國民政府的軍隊陸續撤出海南島與舟山群島,大陳島變成國民政府在最北邊的重要軍事基地。柯凱珮以大陳新村為例,說明全台大陳新村的規畫與分布,主要是依據大陳居民原本的職業加以分配,捕漁維生的居民分配在花蓮、台東、宜蘭和高雄四個縣分靠海的地區;農墾為業的居民則集中在屏東縣。公務員在這批移民中人數較少,分配至台北縣、新竹、南投。根據調查,大陳義胞人數約一萬八千兩百多人,身分皆為平民百姓,與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播遷來台隨行的軍隊眷屬形態不同。
在台灣本土化運動的浪潮下,大陳居民不諱言這對自己的「外省」族群身分造成衝擊,社會上對本省/外省的區隔,雖更明確定位大陳人雖屬於一九四九年之後來台的外省族群,但其實大陳人與一般人認知的壟斷台灣多數政治社會資源的外省菁英,以及受到國防部補助的眷村居民有著相當差異,他們早期雖獲得政府的「義胞」安置,但大陳人今天在台灣的成就,絕大部分得靠自己的努力與「拚命」才能獲得。
變遷中的家園 述說完眷村文學(眷村內部生命史)、媒體眷村意象(從眷村外部投注的凝視),並從女性與「村外村」(大陳新村)的觀點呈現眷村文化與集體記憶的多樣性,接著就是社會變遷中的「眷村」:「家園」經歷怎樣的變化?「籬笆隔絕了外界」,不對,應該說是籬笆內的人情味吸引著每個成員,這向心力不但使軀體附著其上,也使每個人的心圍繞於其間。這道藩籬使人有家的歸屬感,卻也禁錮了想飛的心。無論一世祖或二世祖,幾乎沒人敢想像眷村四周藩籬拆除的景象,因為眷村是純化度極高的社區,也是一世祖解甲歸田後僅剩的一塊角落。說透了些,一世祖們一輩子在軍隊與眷村這兩點一線之間移動,單純到已無力再適應籬笆外的生活,籬笆內不但是人,還有心。另一方面,所有人幾乎都認為應拆除那突兀存在社會中三十餘年的低矮眷舍,使每個人都融入主流社會;而人丁越來越興旺(眷村第三代也誕生了),原有眷舍不敷需求;同時也要改變眷村等於落後及被遺棄的社會觀感。
一九七○年代,因「私有化」成為重要政策方向,使「眷村社會」進一步面臨變遷與複雜化。羅於陵描述「家園」的解體與重構:眷舍「私有化」不僅代表眷村的空間形式與意象產生巨大變革,也使原本分布在都市中央的塊狀、水平地景形式,在短時間內被「毀滅式」地改造。原有的眷村空間意象正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展現「現代性」的高層集合國宅社區,重要的是,「私有化」使原本靜態且封閉的眷村社區結構趨向複雜化,甚至也改變老眷村人及一般社會大眾心目中的眷村印象,而且是永遠地改變。
眷村空間形式的改變,不僅使內部結構變得複雜,在改建為國宅的過程中,我們也看到分別以兩種不同基礎(自治會和眷權會)為首的社會動員,其要求介入眷村改建過程的行為,給予規劃單位極大的壓力,甚至發生「強住國宅」等集體抗爭事件。在改建過程的社會動員中,我們觀察到不同世代的眷村成員在社會結構和認知上的差異,以及一種跨越軍階而普遍存在的「受難的」文化經驗。眷村的社會和空間似乎正處於轉化的歷史時刻,而在改造的過程中,「眷村」的既有社會網絡和文化經驗是否面臨解體危機?早年台灣社會對「眷村」的刻板印象是否會隨著眷村環境的變遷而產生變化?眷村內部又實際產生什麼改變本質的化學作用?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提供了眷村意象再解讀的素材,用以捕捉並描繪新舊眷村在歷經變遷時的不同面貌。
「眷村」改建了,「眷村文化」也不同了。柳慧燕以四四南村的遷建(建成國宅的眷村標準範例)為例,說明「眷村」不只屬於眷村居民,自興建到改建,他們的生活空間與內涵都受政治與社會的強力干涉。其中耐人尋味的,不是改建後老眷戶在空間使用及鄰里關係上的改變,而是相較於其他眷改案例(或眷改基地),「四四南村」竟引起社會各階層、領域的廣泛討論;我們在此看到可能干預一個民間社群的所有力量:政府、文化保存及建築規劃等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外籍人士、眷村原眷戶、學校教育單位、媒體、關心眷村議題的市民等。即使對整個都市計畫來說,眷村實質空間環境有必要改善,但我們也不能賦予主流族群這種權力:使其以強勢態度將已漸趨邊緣化的眷村族群,固鎖在一個封閉的界限中,不論這個封閉的形式是指消極的任其頹敗傾倒,或積極以毀滅手法進行改造。其中最可議的是整個眷改政策擬定的動機和其操作的方式。眷村不一定要被這麼巨大的力量,改造成我們如今所見的異質化居住形式。
籬笆終於倒了,國宅大樓拔地而起,群體融合悄然再現,不同於前次一世祖籬笆裡的內聚性,這次則是外向型的二世祖與外界融合;一顆顆育成的珍珠落在大海的各個角落,而養珠的老蚌只能拄著柺杖、獨坐在午後的大樓中庭。當初籬笆的築成代表落地生根建立家園,如今有形的籬笆或許倒了,但心中那道守護家園三、四十年的藩籬卻永遠存在。
不了解眷村,就難以完整說明與研究台灣的歷史。「眷村」一詞從何時被正式使用?學理上沒有完整的解釋,有的只是官方法規對「眷村」的若干定義。「眷村」集體聚落的意象其實廣泛存在於許多行業,但國府部隊形成的眷村數量與人口實在過於龐大,與台灣社會文化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社會大眾及學術社群也就習慣把「眷村」與「軍隊」劃上等號,研究眷村也等於同時研究一部分的台灣現代社會史與軍事史,著實有令人著迷的魅力及吸引力。柯林斯(筆名)介紹「眷村」源流,從國家政策發展的角度,對眷村的興建、財務來源、命名與分布等,清楚記錄「眷村」如何經過由上而下的政策推動切入「台灣社會」,成為台灣社會發展不可忽略的現場。
相對於柯林斯的文章,張茂桂則透過「族群學者」與「眷村子弟」的雙重觀點,在客觀立場外,感性地娓娓道來眷村一二事。該文最重要的觀點,是從國際政治的架構中分析「眷村」意涵:因國際政治與軍事對抗的緣故,必須冷漠牽動大量人口的遷移,但夾雜其間的卻是真實生命情感的出入,這是受到大歷史影響的具體生命過程。眷村確實是在國共戰爭下,經過軍隊與政府的安頓規劃,藉助民間「捐助」等種種條件,所進行的一種「落地生根」的「造家」,也是「造村」。在此空間裡,鄉親與故舊、軍人與百姓、男人與女人,因種種幾近「不可能」的劫後餘生機緣而聚在一起,共同構築一個「臨時」卻又「情感緊密」的生育和養育空間,大家共同形構「眷村」的內涵,並經由「眷村」推動族群融合,書寫台灣歷史。
相對於眷村改建導致解體,眷村保存運動則展現將「眷村」視為「台灣史」一部分的積極力量。高有智採訪幾位眷村文化保存工作者,當時人數雖不多,但從北到南、從台灣本島到離島,只要曾有眷村的地方,就有他們付出耕耘的行跡;這些人來自不同領域、身處不同角落,藉由各種方式,試圖喚起台灣社會對眷村文化保存運動的重視,台灣社會方能得知,原來不只「外省人」關心眷村族群,也有河洛人、客家人,甚至還有外國人;這也打破了族群藩籬,如同眷村向來也不是單純「外省人」的家庭。眷村文化工作者的熱情,讓眷村文化沒有就此消失,這是對眷村回憶的眷戀,也是對文化保存的眷念,這共同見證眷村文化保存工作的跨越性意義,也說明「籬笆」(不管是竹籬笆或扶桑花圍籬)是籬笆內/外的人共同建構出的台灣文化,也是台灣所有人記憶的一部分。
時間看得見!圍籬的拆除就像從台灣地理空間上拔除「眷村」,眷村第一代逐漸老化與凋零,加速具體「眷村」符號的消失,也說明族群融合(或是「外省人」的在地化)的發展在持續進行。然而上述過程中,台灣社會失去的是過去六十年來曾真實存在於這個社會、於你我生活中的重要元素,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曾經存在於這個社會中的「過去」,「歷史」將離我們愈來愈遠。
歷史是通過不同的個人經驗對話而形成,只有傾聽大眾的聲音,才能了解與人民息息相關的過去。然而,當眷村逐漸拆除,我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利用「過去」?如何讓自己與「過去」產生連結?甚至,用什麼方式能再現「過去」?本書是在此題旨之下的一次嘗試,這些文章或有各自的記憶框架與觀點,但我們希望書中所表現與建構的內容,不僅僅是「眷村」與「眷村生活」,也將是對「台灣」與「台灣社會」的一次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