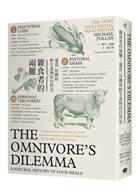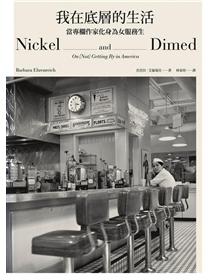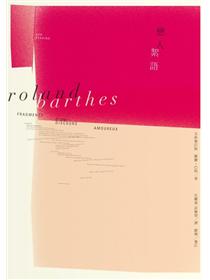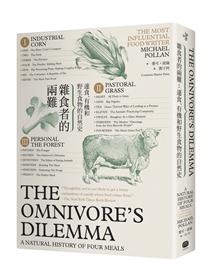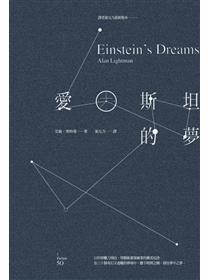而未來在我面前破滅
世上有座城市,總是企圖活在過去。縱使家家戶戶牽了電線,裝了網路,擁有無線電話和起碼五支以上的遙控器,夏天吹冷氣,冬季開暖爐,連開瓶器都電動化,他們依然假裝活在十八世紀,不斷翻修舊建築,盡力維護街道的原本模樣,收集雕花骨瓷杯盤,特愛手工肥皂的香氣,家裡電視藏在櫃子,時常忘記電影其實也是一種新科技。對他們來說,街上正在發生的事情都很俗氣,東西擺在博物館裡比較值得尊敬,人死了比活著更有價值,只要還在呼吸的人,他們通通沒有興趣。他們總愛長時間坐在咖啡館除了抽煙以外什麼都不做,忽視腳底下因為電車來去而不時發作的小地震,著迷談論早已遠颺的古代吟遊詩人,彷彿透過朗誦古老詩句,天天走在角度相同的街影之下,躺進式樣復古的皮沙發,摸著那些細心收來的古董藝術,整座城市包括他們自己都將不朽。
而有另一座城市,拼命想要擺脫過去。他們曾有輝煌的歷史,見識過帝國的風采,如今巍峨宮殿依然雄偉,色彩卻已褪了瑰麗,庭院鋪上時光的塵土,屋脊長滿除不盡的雜草,庫房裡積放曾經稀世的珍寶,全像失去了青春容顏的美婦,悶不吭聲等待遭人拋棄的命運。於是他們拉倒房舍,拓寬巷道,將河川蓋頂,砍掉祖先親手種植的大樹,只為了停泊辛苦買來的進口洋車。他們燒掉破爛古籍,唾棄那些過時的字眼,使用大量外來語以充當新時代語彙。新就是真理,只要老舊,便引以為恥。他們一心一意築高樓,拉高了城市地平線,加深了城市的陰影,太陽昇得越高,那些扎眼的殘破宮闕便會自然落入新樓的黑影裡,就像灰塵被掃進地毯下。聞著新裳的特有味道,指間紅寶閃耀如血,資產曲線猶如搭電梯一樣火速爬高,當他們開香檳慶祝新樓落成,瓶蓋隨氣泡噴向高空,月亮顯得如此近,彷彿一舉手就能摘取。曾經偉大的城市,如今當起暴發戶,渴望使用剛掙來的新財富買來一個新身分,從此這座城市包括他們自己將脫胎換骨,獲得新生。
第三座城市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他們只活在當下。這一刻。不多一秒,不少一秒。他們不需看錶,因為每個人體內均有一座上緊發條的時鐘,不等鬧鐘醒,他們早已塞車滿城,擠爆地鐵公車,坐在辦公室電腦前,捲上商店鐵門,等不及充分利用他們眼中即將結束的一天。時間對他們來說不具任何意義,因為已經消失的昨日代表從不存在,尚未發生的明日只是個不具形體的抽象概念,唯有抓在手心的今日才是一輩子。他們想像不了海洋的年紀,沒空理會深夜墓園的竊竊私語,如果他們望著城裡的鐘樓沉思,那也是為了衡量保留鐘樓之後的觀光資源與拆除鐘樓之後的快速道路究竟哪一項帶來最多經濟利益。他們永遠在路上奔跑,像灰姑娘一樣趕在午夜鐘響之前享受人生的饗宴。他們拼裝他們的城市,如同灰姑娘臨時拼湊她的宴會裝扮,南瓜當馬車,老鼠當馬伕,窗簾當華服,玻璃當鞋履,一直到了宴會,即便已在心愛王子懷中,與他翩翩起舞,瞥見自己在大廳長鏡裡的美麗身影,她心中依然不踏實,拼命提醒自己眼前一切皆非真實,過了今夜,均將消失。再光燦華麗的夜晚,對他們來說,畢竟春夢一場。隔夜醒來,他們已經忘了昨夜王子的英俊容顏,懶得追問明日整座城市還在不在,對這座城市包括他們自己來說,只要趕在半夜之前提早收工五分鐘,忽然拉長了的今天已令他們有活著的喜悅。
接著,我住進了第四座城市,過去屬於未來,現在就是未來。未來不是未來式,而是現在進行式。
(節錄稿)
我慾望一座城市
所有城市的不幸皆大不相同,所有城市的幸福卻大同小異。有些自認不幸的城市於是想要藉由改頭換面來扭轉命運,就像拿著明星照片上整型診所,要求整成跟明星一模一樣的長相,以為有了神似的容貌,就能遇見傳說中那道叫做幸福的壯麗彩虹,高掛城市天際。
別的城市有高架橋和環城快速道路,我也要。別的城市有六星級飯店和歌劇院,我也要。別的城市有金融區和股票交易所,我也要。別的城市還有高達雲端的摩天巨廈,花樣產品從地面堆到天花板的百貨商城,居高臨下賞夜景的頂級時尚酒吧,不用走路就能送行人抵達目的地的自動扶梯,寬闊足以讓八輛車同時併駛的林蔭大道,任何死角都有路燈終夜不熄,地下三十公尺深的地鐵上也收得到手機訊號。我要,我全要。
這座曾經住過王宮貴族的歷史古都頓成一片灰塵滿天的巨型工地。滿街瀰漫的並不是晨光閃耀林蔭的翠綠氤氳,也不是河面泛光的迷濛水霧,而是夾雜了汽車烏煙、餐廳廚房油煙、工廠廢氣、各式機器瘴氣,以及大量人工建地所揚起的刺鼻塵霧。人類對城市幸福的渴望化身一只鋼搥,持續重擊大地,日日夜夜猛鑿地面,走在路上總感到腳底不時輕微地震,處處可見新近才硬生生挖開的地洞,長寬各一百公尺,彷彿昨夜外星飛碟急速噴射離去之後留下的巨坑,又像一張貪婪的龐然大嘴朝天張開,等待一棟金光閃爍的巨廈從空墜落。路面老是凹凸不平,人行道坑坑洞洞是常態,管線埋了又拆,水泥敷了又敲,空氣飄浮著粒粒可見的微塵,房屋裝修噪音變成永恆的城市背景音樂,生活在城裡的每一天都感覺像是古代長途旅客剛進驛站,疲憊,口乾舌燥,渾身肌肉酸痛,沾滿沿途風塵;而,這趟旅程尚未結束,依然路迢迢。事實上,永遠不會結束。因為城市之旅並沒有終點。
城市只會不斷成長。就像一個孩子不可能永遠八歲,城市也不會停留在第八世紀。人類的慾望代代更新,他們對生命的夢想透過物質凝塑不同長相的空間。城市因為人們不同階段的生活習慣而更換,而變化,而消長,而改裝。有時,一條彎曲的街道被拉直了;有時,幢幢矮房讓叢叢高樓取代;有時,平坦田野割出一條條運河,運河長滿水草之後又填平成一圈圈高速道路;有時,擠滿貧民家庭的舊社區強制改建成復古風味的高級購物區;有時,遭到資本遺棄的廢棄碼頭進駐了藝術家工作室。八世紀人類生活裡不存在的高速公路、機場、辦公大樓、地下鐵、巨無霸商場、抽水馬桶、污水系統、網路線路,到了二十一世紀通通變成難以想像缺乏的城市要件。沒有了這些條件,城市就不幸福。管你古樹參天,寺廟庭院幽深,石雕拱橋下流水悠悠,少了手機訊號,沒裝冷氣,再怎麼冬暖夏涼的木屋都不能使這座古都的歷史更顯魅力。
人們對城市幸福的想像越來越統一。當城市旨在滿足最多數人生活需求,不免像輪胎尺寸一樣追求規格化,在意的是可重複性。無論何時何人來自何地,只要進入這座城市,都能像電器插上母體電源,立即搭建起一套有模有樣的個人生活。活在城市,就像活在一座組裝傢俱城,裡頭所有零件都保證互相兼容,每個進城的人漫步其中,隨手拿起什麼材料,就能拿回去像拼裝櫥櫃一樣拼裝自己的人生。雖強調自己動手做,拼裝出來的結果卻如同一模子刻出來的相像。
相似的不只是我們的慾望,相似的不只是我們的人生圖像,根本相似的其實是我們不知不覺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為了容納這套相仿的生活,逐漸擁有相仿的城市。可以犧牲一點容許散步的綠地,不能沒有十秒鐘內升到七十層頂樓的高速電梯;沒法想像少了購物商城的日子,卻能過著缺乏新鮮氧氣的生活;儘可一再拓寬車道,就算人行道走到一半突然不見也無所謂。現代都市人的生命規格就刻印在城市藍圖裡。我們雙腳懸空,呼吸人造空氣,為自己打造了恆溫健身房,靠機器鍛鍊身體,同時,卻懶得爬樓梯或過馬路,出門就攔車,進門就翻倒沙發上,砍了綠樹然後天天從商店冷凍櫃買包在塑膠盒裡的生菜沙拉。我們對生命安排的優先順序拼裝出我們的城市。我們要速度,要方便,要移動,要安全,要舒適,既怕熱又怕冷,想要看見椰子樹的倒影,但不想遭到蚊蟲追趕。為了掌控生活環境,我們必須創造自己的大自然。
城市起初只是人類自然群居的一塊地方,好比河馬群住水塘、獅群佔據草原,而今城市代表了超越本能的動物文明。其他動物不控制自然,牠們只遵循自然,順從自然,偶而,耍點小聰明欺騙自然,替自己爭取多一點活命的時間。唯有人類決定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甚至擁有自己的自然。城市即是人類為自己打造的大自然。城市固然優雅細緻,難免也野蠻殘忍,因為大自然的特質即為如此。即使是人造大自然,仍舊逃不過達爾文的演化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走在城市街道,依然看見多少沒能生存下來的動物屍骸,曝曬白日下,默默腐朽,路人匆匆走過,無暇掬把同情淚,視之為自然的必然。
人造大自然甚至比真實大自然更兇猛。為了取得能源,讓人造大自然這個主題樂園運行無礙,為了容納更多更多遊客,讓他們品嚐童話般的物質生活,城市勢力一直在擴張,如蠶寶寶吞食豢養牠的蠶葉,城市逐步吞噬掉供養它的田野、山丘、溪流、森林、沙漠。
彷如火山岩漿的紅舌往外漫流,城市規模向外積極擴張。
南方那座海岸城市於是向海洋開戰。裝滿蔚藍海水的港口正一點點萎縮,關於荒唐水手的故事早已被穿西裝打領帶的金融族所取代。當港口的功能從海路轉為空路,購物中心的營業總額超過停泊船隻繳納的管理費用,一夕之間,路永遠不夠用,地永遠不嫌多,海水卻已經太過張揚,必須削減它的版圖。孩子記憶中的城市有地鐵,有高樓,有高級服裝旗艦店,有地板清潔劑的香味,卻不再有海洋的顏色、海鳥的叫聲或密不見縫的林地。然,他不覺得有什麼不妥。不似他的先輩,他不需要港口停泊他的船隻;他需要一個乾淨明亮的停車場停放他的保時捷跑車。海洋不是他城市的要素,他可以沒有海洋,卻不能沒有游泳池、電腦、手機和愛迪達跑鞋。城市圍繞著他的期待而建造。港灣可以填平,人們的慾望不能停止。記憶縱然寫出美麗詩文,人類已經前往其他地方尋找他的詩意。
城市沿著時光軌道向前滾動。人們對生活模式的慾念在後推動。人類不能每晚手無寸鐵躺在燦爛星空下露天睡覺,也不能住在自然博物館般的史前環境裡。城市本身並不會開口說話,而它的存在卻敘說了一整部人類生活史。
每一座建造完畢的城,都是一個人類夢想的實現。高築岩巖的山城,傍河而居的水鄉,沙地綠洲的蜃樓,人類建築城市,為了建造自己的生活,城市的出現只是人類生活文明的結果。城市之所以美好、先進、精緻,因為人類美好、先進、精緻;城市偉大,因為人類偉大。同樣地,城市之所以墮落、腐敗、醜陋,因為人類墮落、腐敗、醜陋;城市邪惡,因為人類邪惡。
我如何慾望我的城市,我就得到如何的城市。確實,除了人類,其他生靈果真沒有如此強大的意志與能力能夠戰勝自然的力量。剷平百年榕樹為了開一間已經夠多分店的時裝舖子,移山為了開一條稍嫌多餘的高速公路,填海為了建一棟錦上添花的豪華飯店,然而我依然感覺不到生命的喜悅,一股純粹生物性的疲憊反倒淹沒了我,令我覺得蒼老,脆弱,而且無助。
因為,在城裡,慾望是簡單的,快樂卻是複雜的。
美麗陌生人
目光來自四面八方。
電梯口,捷運車廂中,公車站牌前,商場裡,天橋上,畫廊內,機場櫃台,陌生人猶如秋日落葉紛飛,颯颯吹過彼此的身旁。飄過的不只一個個匆忙的身影,更有那些似有若無的目光,帶點評斷,包含好奇,有時節制,有時鹵莽, 輕輕地拂過你我的肩頭。
看似一個必須的轉身,又似一個無意的抬頭,也似一個心無旁騖的空眺,碎步擺臀踩著高跟鞋的粉領上班族,站在車廂內倚窗憂鬱的中學生,西裝畢挺大步邁進餐廳的商人,帶著高級行李箱和太陽眼鏡等著登記上機的旅客,週末坐在酒吧吧臺有一搭沒一搭喝酒的男子,以及穿著短褲在雜貨鋪子選購義大利麵條的女孩,自以為謹慎地將自己流轉的眼神深藏在不經意的日常動作裡,悄然無聲地送了出去。
假意視若無睹,卻又仔細打量。蜻蜓點水,跳躍而去,然而,留下脈脈含情的印象。那些目光不想讓人知道,但暗地期待著回應。
看見,與被看見,同時在光天化日下發生。
屬於城市的情歌旋律濃烈地低哼著,是的,你這個美麗的陌生人。在洶湧的人潮之中,如同奇蹟,我偏偏看見了你。不是誰,就是你。我不能呼吸,也不能言語。卻落得只能眼睜睜地望著你從我眼前離去。你從人群中來,又將回去人群。我還來不及與你相戀,卻已嚐盡分離的苦味。
誘惑無所不在,勾引跟著隨機發生。城市裡,上街再不是一個簡單的動作。人們在家裡盡情邋遢,連腳都懶得洗就上床,若情人嫌臭,就怨恨對方不愛自己,卻為了想像中即將相遇的那個陌生人,梳頭化妝,刮毛潔齒,結上最好的領帶,塞下最緊的牛仔褲,穿上最白的襯衫,確保自己容光煥發,絕對綽約多姿,這才出門去。
在這個什麼都無法承諾的時代,人們卻仍嚮往陌生人的愛意。我懷疑,他們要的已不是濃情蜜意,而僅僅是一種無害的喜愛。沒有要求,沒有佔有,更沒有後來的失望以及恨不得從未相遇的悔恨。他們要的是暫時的好感,沒有將來的調情,剎那的愉悅。一段臨時起意的愛情,隨著任一方下車之後就會嘎然終止。
一個再怎麼深愛自己的人都能透過長期相處而發現你的破綻,即使是自己的母親。陌生人卻永遠沒有這個機會。他跟你的情緣只有飛機上的五個小時,公車上的十五分鐘,餐廳裡的四十分鐘,甚至只有從地下道走上來時擦身而過的三秒鐘。
他只能看見你那天花了心思喬裝的外表。他看見你那染了茶色的濃密捲髮,你隨意圈出蛇腰的寬皮帶,和你千挑萬選的超酷提袋,但看不見你的白髮、鬆肚腩、薪資數字、學歷文憑、智商資質和公寓長相。他只瞧見當下站在他面前的那個你。來歷不明,出身不詳,沒有歷史也不會有未來。除了你刻意顯露在外的線索以外,關於你這個人,他無從下手。
他只能這樣遇見你。美麗的陌生人。
既是純粹視覺的感官吸引,又是想像勝過實際的精神愛戀。驚鴻一瞥,證實了一見鍾情的可能,允諾心心相印的甜蜜,更見證了你的內外兼美,實在耀眼,讓人不能將視線移開。
如果他愛你,他就只能愛站在他眼前的那個你。那個一晃而過卻註定令他印象深刻的你。你們不會激烈爭吵,抓傷彼此的臉頰,咆哮可怕的言辭,也無法目睹對方逐漸老去的悲涼。你們的戀愛雖無法直到天荒地老,卻比任何一段你所知道的愛情更地久天長。
有誰能抗拒這種純粹的好感,還來不及形成任何偏見的愛慕。像一顆口香糖,一入口就涼爽芬芳,五分鐘後吐掉,毫無負擔,不傷人生筋骨,還令口齒清香。又像一朵隨時準備盛開的蓓蕾,可是,你我都明白,這朵花之所以令人神往,正因為她永遠含苞待放。
街頭的愛情難免膚淺。而,人們就愛這股膚淺味。拿來調劑單調的城市風景,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