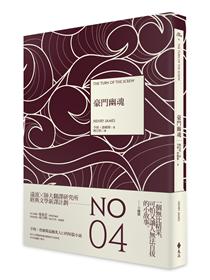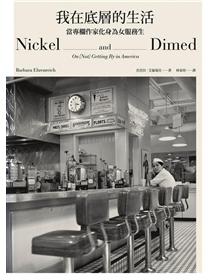愛倫坡獎終身大師獎得主勞倫斯‧卜洛克最新力作
在馬修.史卡德酗酒與戒酒之間的空白處,斟上《烈酒一滴》。
借用米基.巴魯的話來說,史卡德的生命在這兒拐了個彎。真的只有一個推理小說家幾乎能接近難以取代的約翰‧麥唐諾,他就是卜洛克。──史蒂芬.金
卜洛克堪稱當今最優秀的推理小說家,他至今創作不輟,作品中屢屢出現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且驚艷的元素。──華爾街日報
美國小說當中,最篤定、最具辨識度的聲音。──馬丁‧克魯茲‧史密斯(Martin Cruz Smith) 《高爾基公園》作者
《奧德賽》故事中,迷航的猶力西士曾航入冥府,見到了母親和一干特洛伊戰友的亡靈,在那裡,先知提瑞西阿斯給了他最慷慨的贈禮,告訴他可以毫無痛苦的死去,這個禮物,人愈到老年才愈知其珍貴。在每一回探案過程中,史卡德總會有一兩句縈繞不去的話語,用於自省,用於感傷,也反覆變形用於練嘴皮子的玩笑,《烈酒一滴》這回是:「神啊,請賜我貞節之心,但不是現在。」
神啊,請讓我保持清醒,但不是現在;請讓我不起偷盜之心,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慷慨、勤奮、無私無我,但不是現在;請別讓我打人,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拒吃零食,但不是現在……──唐諾
這是酗酒者馬修變成戒酒者馬修的故事。它的敘事跟《酒店關門之後》一樣,也是回述。但書裡的馬修是一九八二年、八三年的樣子。那是馬修剛剛開始戒酒的時候。也是《八百萬種死法》之後,《刀鋒之先》之前的這段時間。前一本還是酗酒的馬修,但下一本就是戒了酒的馬修,雖然依然是馬修,但這個關鍵轉捩點,卻是馬修故事的一個空白片段,也是峰迴路轉又出現在作家腦海的故事。
馬修.史卡德正在對抗他的心魔。他被迫離開紐約市警察局,他也放棄了喝酒。他的身心狀態面臨嚴重的衝擊,與女友珍的關係也岌岌可危。這時他碰上了傑克.艾勒里,一個當年在布朗克斯一起長大的兒時玩伴。 他們像是硬幣的兩面:史卡德曾經偵破的案件,卻是艾勒里犯下的。 在史卡德身上,艾勒里看到自己曾有機會變成的善良公民。在艾勒里身上,史卡德看到他期望獲得卻來之不易的清醒。
然後艾勒里死了,就在一瞬之間,彷彿是要試圖彌補過去的罪惡。他看到什麼呢?就讓他這麼死去嗎?艾勒里沒有家庭,沒有朋友,為誰去討回公道呢?但史卡德還是不情願地開始了他自行展開的私下調查,線索就是艾勒里列的一張意圖修正錯誤的名單。凶手就在這份名單裡,史卡德怕的不是尋找凶手的過程,反倒是沉浸在艾勒里的世界很可能導致他重新投向酒吧的懷抱。
失落、懷舊、救贖,卜洛克用《烈酒一滴》尋找這一切的源頭,重建馬修.史卡德系列登上美國偵探小說頂峰的這條路。
卜洛克來台受訪時曾描述,他想寫一個還沒有網路、手機的年代,人們無法用Google查詢很多事情,身為偵探也非得一個個人去問,一個個地點去跑。而且那時的馬修才剛戒酒,許多的忍耐與適應讓他的視野與眼界更不同於以往。
就卜洛克迷來說,這是一個馬修系列的空白時段,是可以去跟著新書細究馬修人生的空間。對新讀者來說,卜洛克的文字與馬修的迷人魅力,必然會再度使人一翻開書就為他著迷。
作者簡介:
勞倫斯‧卜洛克Lawrence Block
是當今最知名的推理小說作家,曾獲美國推理小說作家協會頒贈大師獎表彰其終身成就,曾五度獲得知名的愛倫坡獎、夏姆斯獎與尼洛.伍爾夫獎,以及法國、德國、日本等國所頒發的各大推理獎項。他還曾獲得英國犯罪小說作家協會所頒發的鑽石匕首獎,成為繼莎拉‧派瑞斯基與艾德.麥可班恩之後第三位獲此獎的美國作家。
卜洛克目前著有超過五十本書以及多部短篇小說,已在臉譜出版的系列作有「馬修.史卡德系列」、「雅賊系列」、「密探系列」及「殺手系列」等。
譯者簡介:
易萃雯
湖南省攸縣人,曾任中廣編譯,譯作有《惡之源》、《丹恩咒詛》、《強力毒藥》、《八百萬種死法》、《父之罪》、《蝙蝠俠的幫手》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導讀】祭神如神在
唐諾
《烈酒一滴》,是日後才想起來說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伴當時仍是雕刻家珍而不是妓女伊蓮.馬岱,這是它的碳十四同位素,告訴我們此事發生在八百萬種死法稍後,因為我們也已經知道了,珍後來會死於癌症,死得很清醒但疼痛不堪(這兩件事為什麼總是連在一起?)。而珍正是把馬修.史卡德一把拉進去戒酒聚會的人,用米基.巴魯一開始的話來說,史卡德的生命在這兒曾拐了個彎。
《烈酒一滴》也順便幫我們補了一小塊記憶碎片,之前我們並不知道史卡德和珍的分手過程。當時,史卡德和我們的心思嚴重集中在那些接踵而來的謀殺案件上頭,那同時也是紐約最殘酷的時日。
「在這一杯酒與下一杯酒之間,橫亙著綿長的時間。」──卜洛克說這段引言道中了這本書的要義,我們還不完全知道他的意思,但我們起碼先看出來一種時間的特殊形狀,只有通過記憶,時間才會變成這個奇特的模樣。我們知道,回想的時間和生活中正向進行的時間不同,回想的時間比較馴服,它可依我們意思重組,可以一眨眼五年十年呼嘯而過(所以就別再隨便眨眼了,我們短暫的人生禁不起這樣),也可以幾乎凝結成形一樣,讓你拿在手上慢慢看、反覆看、翻過來倒過去挑自己想要的看。就像這次的謀殺故事,死者傑克.艾勒里是史卡德失落的童年玩伴,要講述清楚他何以死亡,得從幾十年前回想起,用卜洛克喜歡的說法是,傑克.艾勒里花了幾十年時間,才讓他有理由在那一天額頭一槍、嘴巴一槍的死掉。但這一切不過是葛洛根酒店的一個晚上,也許還不足以裝滿一整個晚上,史卡德和米基.巴魯談的顯然不止這個謀殺,他們至少還談到米基.巴魯的年輕妻子,他的屠夫父親和三個兄弟。這個晚上,傑克.艾勒里的嘎然而止一生,也許真的只活在米基.巴魯這一杯到下一杯的十二年陳年Jameson威士忌之間。
均勻而行的現實時間,形狀上乃至於實質上都像一道鐵鍊,我們隸屬於它聽命於它行動,破壞它因此意味著解放;也就是說,我們通過回想,翻轉我們和時間的主從關係,我們一次得回一部分的自己。
但我們今天較特殊的困難是,我們似乎活在一個人類歷史最不合適回想事情的時代,好像總有什麼會跳出來打斷我們的回想,說不大清楚究竟是我們自己或是整個世界,還是說共謀一樣,不知不覺中世界已成功說服了我們,把它講成是一件不急乃至於不宜不當壯夫不該做的事,以至於我們好像漸漸失去了回想事情的能力了。我的意思是,回憶的啟動也許是自然發生的,但要認真想下去還是得有依據有方法才行,人的記憶不是一張鉅細靡遺整張攤開的大圖,它比較像一座密林一個洞窟,你得找到路才能進去,我們生活裡的記憶觸動,只負責把人帶到密林之前洞窟之前而已。
《烈酒一滴》這個謀殺故事,幾乎只穿行於昔日一次次的戒酒聚會之間,事實上,就連傑克.艾勒里之死,也幾乎一開始就可確定是他努力戒酒且過度忠誠遵循戒酒協會的宗教性規章所導致(對此,史卡德一直保持他極其文雅的懷疑和嘲諷),我們幾乎可以說,這樁老謀殺的真正主體是戒酒協會,從起因到每一處關鍵,沒戒酒協會,傑克.艾勒里也不會死(或以其他方式、在其他時間其他地點不干史卡德事的死);而這個葛洛根不眠之夜的史卡德,他回憶的真正主體也是戒酒協會,那些日子,那些事那些相關的人,畢竟再怎麼說,戒酒協會(而非艾勒里)才真正是史卡德生命中無可替代的豐碩東西。艾勒里案的真正重要性在於,它是一把特殊的記憶之鑰,某一扇特殊的記憶之門只能由它打開;同時,它還是一道特殊的記憶回溯之路,故事(尤其是謀殺故事)要求被有頭有尾的講述出來,需要有足夠的相關細節來裝填它,因此,史卡德說給米基.巴魯聽的同時,也是自己回憶的熾烈進行,記憶被重新翻尋、發現、確認並補滿,包括那些沒事不會想的、那些原本以為想不起來的、以及那些不願再自虐去想的。
不是這樣嗎?否則我們怎麼會多知道珍離開的這段經過?怎麼還會再次聽到史卡德講小女孩的誤殺(史卡德已經很久不想此事了)?怎麼又補充了一堆已故老好人吉姆.法柏的諄諄叮囑?
但艾勒里案不是《往事追憶錄》,沒辦法一次打開全部往事,在人難以窮盡碎片凌亂堆放的記憶密林裡,它只想起、吸附、整理戒酒協會相關的這一小部分;一個故事只進行一次回憶,這樣才能深入、才可望完整,其他的記憶得等下一個不同故事來喚醒它們。所以到這裡,我們得換一種較正確的說法,一個故事不是一條路,而是一條記憶甬道。
前頭我們所說,回憶要進行下去得有依據有方法,指的正是,你得試著找出這樣一條一條的甬道來。
提前出現的時間甬道
《烈酒一滴》很容易眼熟的讓人想起多年前《的酒店關門之後》,如果說這回是戒酒協會的謀殺,那次則必定是酒店酒吧的謀殺──人喝酒也死,不喝酒也死,我們何去何從?
《酒店關門之後》,當時,彷彿某種深怕講錯、吞吞吐吐的預言,我一直相信這不僅是馬修.史卡德故事一次極特殊的書寫而已。我以為,這還是一次洩露,遲早史卡德得以這樣的回想方式說故事給我們聽,等他自己也真正老了時,屆時不這樣還有其他辦法嗎?
當然,任誰都看得出《酒店關門之後》外表的異樣,最明顯是時間的不連續,一直跟著正常時間作息、以穩定節奏累積年歲和閱歷的史卡德,忽然像坐上時光機器般站在很久很久以後的「未來」,回頭來看當下發生的謀殺;或者說,他好像做了一個夢,夢中的自己是個年老很多、兒子早已長成獨立的史卡德,裡頭的人,裡頭的酒店和整個世界,也跟著是年老很多的模樣,在時間的加速飛逝中老的老,死的死,逃的逃。
仔細想,做夢的說法好像比時光機器的說法要對,因為夢只能依據當下猜想未來,執迷而且一廂情願,當下的夢隻身探進未來,其實那一刻它並不完全知道未來的事;它夢不到還沒出現的人,夢不到還沒發生的重大意外、謀殺以及死亡,也不確知日後吉姆.法柏的死法或陪同米基.巴魯彷彿去了一趟地獄歸來,夢裡更不會有九一一,這些,否則史卡德怎麼會不講呢?
也就是說,當時的史卡德連同已存在的所有人並不真的年老,唯一確知老去死去的是這一間間酒店(現實裡的紐約市領先小說時間一步,「提前」揭示了這些酒店的命運),酒店的未來結果和酒店的此時此刻兩點連成一直線,出現了一條標標準準的時光甬道,我說,這才是《酒店關門之後》真正特殊而且最富啟示性的地方。
其實每一個故事都是一次回想
我們都不確知未來真的會發生何事,所以很多人明智的不信未來如不再相信有神,把握當下,做你自己云云。但米蘭.昆德拉狠狠的把我們僅有的當下也挖掉,他指出來,由於當下並未完成,當下每一件事仍在發展之中,它們的得失、它們的結果、它們的意義,全蜿蜒伸入到濃霧般的未來,如果我們不知道未來,我們如何能說自己知道當下,有能力掌握當下呢?
這也是難以駁斥的沉重一擊。是啊,所以波赫士不信每天即時報導的大眾媒體,他說真正影響深遠的大事情都開始於不起眼的角落和樣子,即使你當時在場親眼目睹它發生都認不出來,包括就發生在你身上的事,認得某個人或接受了某件工作云云。波赫士選用的實例是耶穌的誕生,誰會曉得,在兩千年前人類文明邊陲又邊陲的某一個貧窮木匠人家的某一個晚上,例行也似的生了個小男嬰,這會是歷史驚天動地的開始?日後房龍在《人類的故事》這一章告訴我們,以下他要講的是一個馬槽和一個帝國的故事,「奇怪的是,馬槽居然打敗了帝國」。但房龍說得太客氣了,其實這個馬槽還差一點占領了全世界,還一直統治著日月星辰整個宇宙。
虔信的宗教人士會駁斥這個實例,因為依《聖經》乃至於日後教會的說法,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包括當晚的諸天頌讚,三位東方來的博士智者還算準時間不早不遲的抵達云云;也包括惡人那邊,希律王儘管不確定是這一晚,但他起碼知道就是這一年,所以他下令把這一年境內出生的嬰兒全殺了,寧殺錯不放過──
但這個駁斥其實恰恰好證實我們所說的,因為這全是日後回想的成果,是通過回憶重新裝填起來的故事;也就是說,這是基督教會最重要的一條時間甬道,而且還是交通最繁忙的時間甬道,兩千年來絡繹不絕,都發展成捷運了。
回到史卡德故事來。我要說的是,我們再仔細點看,史卡德的每一樁案件,乍看像是時間順向的、摸索前進的,但其實都是結案之後才回頭一次完整的說出來。我們可以把《烈酒一滴》的當晚場景變一下,不是在葛洛根面向米基.巴魯,而是在某個無何有時空的酒店裡講給你我聽,差不多就像這樣子。這當然不是服膺調查中不洩露的官方守則那一套,而是因為,故事只有通過回想才能編纂起來,事情得告一段落我們才知道該選哪些看以及該怎麼想怎麼說,所有的故事都是回想,每一部小說都是一條時間甬道。
福克納曾經這麼描述過人的時間處境,他說,我們就像背著身坐在一輛疾駛的汽車上,未來看不見,現在一閃即逝如一抹影子,我們真正能看清楚的只有過去。
問題便在於怎麼樣才算過去、才算事情告一段落──一般而言,手起刀落,從生到死只一瞬,一部推理小說一次殺人總是幾天內完成,甚至就一個度假一頓晚餐;但馬修.史卡德(或卜洛克)喜歡帶著調侃指出來,有些謀殺是很緩慢很耐心的,一次殺死你一點點,所以我們知道幾乎所有的夫妻都用一輩子時間謀殺彼此,所以,在這回《烈酒一滴》裡,史卡德他們還多扯一種殺人方法,每隔幾天寄瓶上好美酒給某人,持續十幾二十年,他不死於酗酒,也必定死於戒酒如傑克.艾勒里,他在接到第一瓶酒那一刻已被惡魔抓住了,無可遁逃。
每天,發生於我們當下的所有事,其實時間尺度都不等長,有幾天的,有幾年的,也有很多長過我們一生的,我們根本等不到結局,也有根本就不附帶結局的,像一朵沒開就萎去的花,凡此種種。史卡德(或卜洛克)一次一次開這樣的玩笑,一次一次重複指向那些更長時間尺度的東西,我們差不多可確定了,他知道自己順利講出來的有頭有尾故事也就那麼幾個,更多的,他仍在等仍在想,等某個結局的來臨,或想辦法發明出某種結局,好把故事說出來,是這樣子吧。
遠遠的火車汽笛聲音
我自己小時候家住宜蘭火車站不遠,在那燒煤的蒸汽火車頭時代,火車進站出站,那種尖利的汽笛聲音是很可怕的,還曾經穿透入睡眠化為噩夢;但我那個愛看美國西部拓荒電影的二哥告訴我,很奇怪,如果把火車置放在空曠的大地之上,從很遠的地方來聽,同樣的汽笛聲音就好聽了,有某種遼闊的悲涼感覺──快五十年了,我一直記得這事,當時我二哥是高中文藝青年的年紀,我覺得他好聰明。
一樁靠得很近、可以很快講出來的謀殺故事,我們對其結局通常有很嚴格的認知限定,它必須破案,而且凶手必須被懲罰。懲罰的極致當然是死亡,但我們對死亡仍有挑剔,凶手可以在負隅拒捕被打死(有時我們更喜歡這樣,因為對司法有信心的人並不多),也可以自知無所遁逃自殺云云,但我們假設,如果凶手搶在破案之前,忽然不管是撞車、是急病死掉了,這就尷尬了,我們對這樣的結果總有某種說不出的不踏實之感,我們甚至會把這種方式的死亡想成是成功的遁逃,媽的算他狗運好!
但現實人生會不會這樣?機率上當然絕對有的,比方說,英國最有名的開膛手傑克案、美國的黃道帶連續殺人案大概都是如此,上帝搶在人的司法系統之前破案逮捕不是嗎?
但這樣的不成故事,這樣的結局,如果把它置放在一個極其空曠的大時間裡,我們遠遠的聽它,很奇怪,它好像自動就成立了,善惡禍福得失蒸汽般上昇,彷彿由天地接管此事,命運吸納了謀殺,也吸納了死亡──
這不是古老斯多噶學派的自我療癒技倆,這是自自然然的時間奇妙力量,斯多噶學派不過是模仿了它,人工的複製了它而已。這是什麼?這是時間給我們啼笑皆非的贈禮,有時候你幾乎要相信它是故意的──你苦苦等待這個結局、這條甬道的完成,但它卻給你另一條甬道,也許還不止一條,連同那些你原來以為長過你一生不見盡頭的、以及那些花一樣根本沒所謂結局的。
讓我沒有痛苦的死去,但不是現在
很多系列性的故事是沒老年的,故事中的時間像咬自己尾巴的狗原地打轉。我女兒告訴我,像日本的小學生偵探柯南,算算時間也應該長回高中生工藤新一的模樣了,但現實的壞消息是,據說作者本人才離了婚,得付大筆贍養費,因此時間得繼續被攔著,保持它聚寶盆的樣式。
史卡德的系列故事,一開始就不智的啟動了時間之流,如同我們現實人生一樣青春難駐回不了頭,這原是令人擔心的,因為流速不難估算,時間的終點立等可取──可不是嗎?現在不就全到了?妓女從良了,把人生弄得無可損失如馬克思說無產階級的惡漢娶了損失不起的年輕妻子,偵探自己幸福了或至少生命的重大關口全闖過來了,更糟糕是其他人一個個死掉,在《每個人都死了》那一案尤其像出清存貨一般。這些,現實人生正常無比,但卻一直是系列故事天條也似的大忌。系列故事最忌諱固定班底的死亡,你寧可讓他搬家,讓他出國,讓他傷心走開,或讓他掉入河中墜落懸崖,但切記不要被找到屍體(腐爛不可辨識的屍體可以),得讓他維持於可死可不死的靈動狀態。
紐約也變好了,不是從此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不是罪犯殺人犯一夕間全失去想像力和實踐能力,而是曾經滄海。
時間即將抵達盡頭會怎樣?兩種,一是很快這一切都結束,互道珍重;另一種則是好整以暇,可以穿越多條而且多樣的時間甬道,通往過去通不到的記憶,說出那些時間不流動、老年不來臨的人講不出來的故事。這裡,告訴大家一件神奇但不致洩露案情的事,《烈酒一滴》裡,一瓶打開來的上好波本威士忌(不摻毒藥和任何添加物)、一房間的酒香,居然可以是凶手的謀殺凶器,這怎麼可能成立?但還真的可成立。
我們當然希望史卡德故事是後者,《烈酒一滴》是好整以暇的開始,只因為能一路走到這裡的偵探絕無僅有,就連昔日的菲力普.馬羅也嘎然止於中年的結束,我們可以想像一個《一千零一夜》模樣的畫面,死亡就近在曙光的那一頭,當故事講完它就來了,所以珊佐魯德一個接一個故事講下去,記得的,然後殘缺不全的,然後遺忘的依稀彷彿的,再然後未曾發生但理應有的……史卡德和米基.巴魯也可以這樣。
《奧德賽》故事中,迷航的猶力西士曾航入冥府,見到了母親和一干特洛伊戰友的亡靈,在那裡,先知提瑞西阿斯給了他最慷慨的贈禮,告訴他可以毫無痛苦的死去,這個禮物,人愈到老年才愈知其珍貴。在每一回探案過程中,史卡德總會有一兩句縈繞不去的話語,用於自省,用於感傷,也反覆變形用於練嘴皮子的玩笑,《烈酒一滴》這回是:「神啊,請賜我貞節之心,但不是現在。」
神啊,請讓我保持清醒,但不是現在;請讓我不起偷盜之心,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慷慨、勤奮、無私無我,但不是現在;請別讓我打人,但不是現在;請讓我拒吃零食,但不是現在……
是的,請讓我們毫無痛苦的死去,但不是現在。
名人推薦:【導讀】祭神如神在
唐諾
《烈酒一滴》,是日後才想起來說的故事。故事中的女伴當時仍是雕刻家珍而不是妓女伊蓮.馬岱,這是它的碳十四同位素,告訴我們此事發生在八百萬種死法稍後,因為我們也已經知道了,珍後來會死於癌症,死得很清醒但疼痛不堪(這兩件事為什麼總是連在一起?)。而珍正是把馬修.史卡德一把拉進去戒酒聚會的人,用米基.巴魯一開始的話來說,史卡德的生命在這兒曾拐了個彎。
《烈酒一滴》也順便幫我們補了一小塊記憶碎片,之前我們並不知道史卡德和珍的分手過程。當時,史卡德和我們的心思嚴重集...
章節試閱
某天深夜‥‥‥
「我常在想,」米基.巴魯說:「如果生命拐個彎的話,我會是什麼樣的景況。」
此時我們坐在葛洛根開放屋,亦即他經營多年的店面。這一帶整體生活的優質化對葛洛根起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酒館本身其實裡裡外外都沒有多大變化,不過當地的老顧客泰半不是死了便是已經遷徙他方,如今來訪的客層顯然比較溫文且較紳士風。這裡提供健力士黑啤和生啤酒,還有多種高品質的單一麥芽蘇格蘭威士忌以及其他高檔威士忌。登門造訪的顧客得以指著牆面上的彈孔相互訝嘆,也可以一來一往交換酒吧老闆過去光榮與不光榮的事蹟。有些事蹟確實是真的。
此時顧客都已散盡,酒保也拉上了鐵門。椅子都架到桌上了,好方便隔天一大早過來的小男生打掃拖地。門已上了鎖,所有的燈也都熄了──只除了我倆頭頂上那盞鉛罩的玻璃燈。我們隔著桌子對坐,手裡捧著華特芙大酒杯,他喝威士忌,我喝蘇打水。
近幾年來,我們已經不像以往那樣常常聊到深夜。我們雖然年事已高,但並無意願移居到佛羅里達,每天一早便趕到附近的家庭式餐廳,點一客清晨特餐消磨時光;但我們也沒有興致進行深夜的漫漫長聊,搞到隔早天光出來時還睜著眼睛不睡覺。我們已經過了那種年齡。
近來他喝得比較少了。約莫一年前,他娶了個比他年輕許多的老婆,她名叫克莉絲汀.何蘭德。這樁婚姻嚇到了所有人──不過我的妻子伊蓮除外,她指著天發誓說她早就看出端倪來了。婚姻當然改變了他──至少每天到了日頭下山以後,他就有個理由得回家了。他喝的還是十二年的陳年Jameson威士忌,也絕對喝乾,只是減了量,而且某些時日裡,他甚至是滴酒不沾。「我仍然有慾望要喝,」他說過:「不過不像以前那樣不喝會死。那種飢渴已經離開我了,不過我可不知道它跑哪兒去了。」
早些年前,我們習慣各自喝著自己喜愛的飲料,通宵熬夜漫漫長談,也能共享偶爾出現的沉默時光:然後破曉時分一到,他便會套上他父親留給他的血跡斑斑的屠夫圍裙準備上工。週日他則照慣例到肉品包裝區的聖本納天主堂去望彌撒,偶爾我會與他同行。
世事難免改變。肉品包裝區現在變時髦了,成了雅痞的大本營,而往常生意興隆的肉品包裝公司則大半都倒閉了,一家家改裝成餐館或者公寓樓房。聖本納區原本是愛爾蘭天主教的牧區,如今則成了瓜達魯佩聖母會的所在地。
我想不起最後一次看到米基套上那條圍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今晚是我們難得一次的把杯夜談,想來是因為我們都覺得有這需要吧,要不我們應該早就回到家了。這麼談著談著,米基現出若有所思的表情。
「生命拐個彎,」我說。「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但有時候,」他說:「我覺得生命不可能拐彎,我覺得我注定了就是要走這條路。之所以這樣想,是因為我做的生意就跟獵狗的牙齒一樣乾淨──俗話都說獵狗的牙齒,你說到底原因何在(譯註:原文是clean as a hound’s tooth)?」
「不知道。」
「待我回家問克莉絲汀吧,」他說:「她會馬上往電腦前一坐,三十秒就把答案從網路上叫出來。重點是我得記得問她才行,」他對著一個私密的念頭笑起來。「這一路走來,我是不知不覺成了職業罪犯,」他道:「說來這方面我可不是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因為在我住的街區,犯罪根本就是家常便飯,方圓好幾里的範圍等於就是個職業學校。」
「而你則是榮譽畢業生。」
「沒錯。而且我搞不好還會代表畢業生致詞呢──如果小小偷跟小流氓們也能得著這種機會的話。不過你曉得,我們那一帶不是每個男孩都注定了要過一輩子的犯罪生活。我父親就頗受敬重。他是──噯,為了尊重他的在天之靈,我就別提他是做什麼的好了,何況其實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的確。」
「總之呢,他頗受尊敬,每天都是早晨起床,然後上工。而我三個兄弟選擇的路也都比我要高尚。一個當了神父──嗯,只是沒撐多久,因為他失去了信念。而約翰呢,他做生意還真發了,是他那一行的頂尖人物。至於丹尼斯嘛,說來也真可憐,卻是死在越戰。記得我跟你提過,有一回我就是專程搭機到華盛頓去看紀念碑上刻的他的名字。」
「是。」
「神父我鐵定做不來,把性侵祭壇男童當成沉悶工作裡的娛樂,對我來說可是難上加難。而且我也無法想像自己跟約翰一樣,到處鞠躬哈腰點數鈔票。不過你猜不猜得出我起過什麼念頭?我哪,我曾經想過要走你那條路呢。」
「你是說當警察?」
「有這麼難以置信嗎?」
「不會啊。」
「記得小時候,」他說:「我覺得當警察是男人最大的榮耀。穿一身筆挺帥氣的制服站在街頭指揮交通,還能幫忙小孩安全過馬路,外加保護大家不被壞人欺負,」他咧嘴一笑。「壞人啊壞人。我那時哪知道壞人是怎麼個壞法啊。不過我們那個街區還真有幾個孩子最後穿上了藍色制服喲。其中一個,叫提摩太.路尼的,其實跟我們大家都沒啥不同。後來聽說他搶銀行,或者幫吸血鬼追討高利貸的時候,其實大家都不驚訝。」
我們繼續談起人生的路有可能如何發展,而人的選擇又有多少。最後這個問題頗為引人深思,於是我倆便花了幾分鐘想了想,並讓沉默蔓延開來。之後他說:「那你呢?」
「我?」
「你小時候可不知道你會當上警察吧。」
「噯,完全沒想到。我從來沒有立志要戴警徽。總之後來我參加了一個入學考,古早時代的那種考試只有智障才會被刷掉,所以我就進了警校,然後我就成了警察。」
「當初你有可能走上另外一條路嗎?」
「你是說不知不覺混進黑道嗎?」這我想了想。「應該沒有什麼天生的高貴品格擋掉這種可能吧,」我說:「不過我得承認我從來沒有把自己染黑的慾望。」
「喔。」
「小時候我住布朗克斯時有個好友(譯註:Bronx是紐約的五區之一,住民大半為南美洲人以及黑人),」我回憶道:「後來我們搬家了,兩人就沒再聯絡。不過多年後我又碰到他兩次。」
「而他已經走上另外那條路。」
「沒錯,」我說。「他沒有爬到大哥的等級,不過他是混進了黑道沒錯。有一回我是在警分局透過雙面鏡牆看到他的(譯註:雙面鏡牆隔開兩個房間,只有其中一間的人看得到另一間的人),之後又失聯了。幾年後,我們再次碰了面,不過這是你我認識以前的事了。」
「當時你還喝酒嗎?」
「沒有,不過那時我才戒沒多久,不到一年吧。說來還挺好玩的,發生在他身上的事。」
「哦,」他說:「願聞其詳。」
******
我想不起第一回看到傑克.艾勒里是什麼時候,不過應該是我在布朗克斯住過的那幾年總沒錯。我們念同一所小學,我低他一屆,所以下課時偶爾會在教室外的走廊或者操場看到他,有時則在放學後瞧見他跟一夥人在打棍球或牆球(譯註:原文為stickball or stoopball,這兩種遊戲都是棒球的變種玩法)。後來我們逐漸熟識到可以相互用對方的姓而非名字打招呼──這是小男生之間很奇怪的默契。如果當時有人問我對傑克.艾勒里有什麼感覺,我大概會說他還好,而且想來他對我的感覺應該也一樣。總之,我們當時的交情差不多就是那樣,所以能說的也僅止於此。
之後我父親的事業逐漸衰落,所以他就關了店,帶著我們遷徙他方,而我和傑克.艾勒里也就有整整二十年不見。再次見到他時,我覺得這人頗為眼熟,但卻想不起名字。我不知道當時他能否認出我來,因為其實他並沒有機會看見我。我是透過雙面鏡牆看著他的。
那是一九七○或者七一年的事了。當時的我已經做了好幾年警探,駐紮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六分局,那時查爾斯街上的戰前建築還沒拆掉,舊分局便設在該處。但之後不久,上級把我們遷到西十街新蓋的樓房,然後就竄出一個頭腦靈光的傢伙買下我們的舊樓,把它改裝成合作商店以及公寓,還給建築取了個名字叫「輝煌」,想來是要對歷史致敬吧。
幾年後紐約警局大樓(One Police Plaza)蓋成之後,中央大街老舊的警察總局基本上也是遭到同樣的命運。
不過我講的事是發生在查爾斯街舊分局的二樓,當時傑克.艾勒里是排成一列的五名白種男性之一,他們的年齡約莫是三十八、九,四十出頭,他排在四號。這五人身高介於五呎九與六呎一之間,清一色穿著牛仔褲以及開襟運動衫,他們就那麼排排站好,等著一名他們看不見的女人指認是誰拿了槍抵住她,要搶她收銀機裡的錢。
她體格魁梧,年約五十,看來完全不適合扮演家庭用品店的老闆娘。如果她當老師的話,所有的學生大概天天都會飽受驚嚇。我當時在場的身分只是旁觀者,因為這個案子不歸我管。主管此案的是個叫羅尼根的便衣警,我就站在他旁邊。房裡有個助理檢察官,他站在女人旁邊,另外還有個瘦瘦高高的男孩,西裝邋裡邋遢,看來是官派的義務律師。
早年我在布魯克林當警員時,和我搭檔的老鳥名叫文森.馬哈菲,他教了我不下幾百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要偷空到指認罪犯的現場旁觀。他告訴我,如果想熟識當地的黑道,這麼做可比一本本翻看罪犯的大頭照有用多了。如此一來,不但可以仔細研究他們的表情和肢體語言,也比較容易抓住他們的特色登入腦袋存檔。更何況,他說,這是免費的秀場,何樂而不飽眼福呢?
於是我在第六分局時,就開始養成到指認現場觀看嫌犯的習慣。而在我講的故事裡的這個下午,我就是在觀察這五名男子,助理檢察官則在一旁跟女人說慢慢想不用急。「連想都不用想了,我知道是誰,」她說。羅尼根登時面露喜色。「是三號。」
助理檢察官問她是否確定,語氣是在暗示她要重新回想整個過程,而律師男孩則清清喉嚨,好像是準備打回票。
根本沒這個必要。「我是百分之百肯定,」她說。「就是那個婊子養的搶了我,這話我可以在你,在上帝以及所有人的面前大聲宣告。」
她宣告是三號後,羅尼根臉上的喜色立刻遁形。其他人魚貫走出房間時,他和我還留著沒走。我問他,他有三號的什麼資料。
「他是哈德遜街那家市場的副理,」他說。「人好到不行,每次都很樂於幫忙,不過看來我們已經不能再用他充當嫌犯了。這已經是第三次有人相中他了。其實啊,他是那種連在公共電話投幣孔瞧見一毛錢都會擺回去的人。」
「他的長相有點邪門倒是真的,」我說。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嘴唇歪了些。其實肉眼看不太出來,不過整張臉就會因此顯得有那麼一點點不對稱,所以很難讓人信任。總之,這是他最後一次出這種任務了。」
「除非是他自己惹上麻煩,」我表示。「說來,你本來屬意的到底是誰?」
「還是你先講吧,你相中了哪一個?」
「四號。」
「英雄所見略同。我應該找你當見證人的,馬修。這到底是你的警察直覺在發聲呢,還是你認出此人?」
「應該說是她宣告答案時,他臉上的表情露了餡。我知道他們啥也聽不見,不過他應該是感知到了什麼,曉得自己已經脫險。」
「這我倒沒發現。」
「不過不論有無發現這點,我應該還是會選中他的。他看來很眼熟,只是我想不出原因。」
「噯,他有前科紀錄啊。也許你是在哪一本大頭照裡看到他俊俏的臉。高低傑克,這是他的綽號。有印象了嗎?」
沒有。我問到他的姓,然後重複唸著:「傑克.艾勒里,傑克.艾勒里,」霎時我的腦子喀擦一下。
「我們是兒時玩伴,」我說。「天老爺,打從小學分開以後,我就沒再見過他呢。」
「嗯,」羅尼根說:「看來兩位是走上了天差地遠的人生路啦。」
再下一次看到他,已是多年後了。在那段期間,我離開了紐約警局,從西歐榭的家搬到哥倫布圓環西邊的一個旅館房間。我沒有另找工作,不過工作都會自動找上我,然後我就會以無照私探的身分開始辦案。我從不記錄自己的開銷,也不提供書面報告,雇我的人都是以現金酬報。現金中,有幾些可以支付我的旅館錢,還有更大一筆則是供我在鄰近一家酒吧喝酒,我的三餐幾乎都是在那兒吃的,我大半的客戶都是約在那裡碰頭,我泰半的光陰是在那裡打發掉的。而扣掉這些還剩下的錢,我會用來買匯票,寄到西歐榭去。之後,經歷過太多太多的意識空白和太多的宿醉,外加幾趟戒毒中心之旅,和至少一次的中風經驗,我終於在某一天醒悟過來:我擱著吧台上的一杯酒沒碰,一步步走到匿名戒酒協會的某個會場。以前我就參加過這種聚會,也試圖要保持清醒不醉,不過想來當時我並沒有準備好,但這次我應該是準備好了。「我名叫馬修,」我告訴滿滿一屋子的人:「我是酒鬼。」
這話我從來沒有說過──沒有整句說出來過,而說了以後也無法保證我就一定可以不醉。我永遠無法保證自己清醒不醉,清醒不醉的境界永遠存在著未知數;不過當天我離開會場時,倒真覺得自己的裡頭有了改變。那天我沒喝酒,隔天也沒有,再隔一天也一樣,之後我持續參加聚會,清醒的日子便那樣一個個串連起來。說起來,我再次碰到傑克.艾勒里時,應該是我保持不醉的兩個半月之後吧。我於十一月十三號喝下最後一杯,所以那天應該是一月的最後一週或者二月的頭一週吧,我想。
我知道不可能滿了三個月,因為我還記得那天我舉起手來,告知眾人我戒了幾天酒,而這個儀式是只有未滿九十天的人才需要執行的。「我名叫馬修,」你要這樣說:「我是酒鬼,今天是我的第七十七天。」然後大家會說:「嗨,馬修,」然後便輪到下一個發言。
那天的會場在東十九街,預定有三個人演講。第二個人講完後,是中場交誼時間,會有竹籃傳遞在眾人之間請大家自由奉獻,滿了戒酒期的人則會在此時起立宣告,以博得眾人掌聲,而眾位新人則會宣布他們是戒酒第幾天做為回報。接著第三名講者便會說出他的故事並準時於十點結束,好讓大家都可以回家休息。
我正往外走時,有人叫起我名字,我一回頭,便瞧見了傑克.艾勒里。我的座椅在前排,所以早先一直沒注意到他。不過我一眼瞥去,便認出他來。他看來比上次站在雙面鏡牆的另一頭要老,他的臉露出的絕對不只是歲月的痕跡而已。聚會場所的座椅當天沒收費,是因為費用已經預繳過了。
「你認不出我了吧,」他說。
「當然認得。你是傑克.艾勒里。」
「天老爺,你的記憶真是一流。當年我們幾歲啊,十二、三吧?」
「記得我是十二,你十三。」
「你父親開鞋店,我記得,」他說。「你好像比我低一屆,然後某一天我發現好像有一陣子沒看到你了,而且沒人知道你去了哪裡。後來我路過鞋店時,才發現店子已經收了。」
「他有很多事業都是不了了之。」
「不過他倒真是個大好人,這我還記得。你的父親史卡德先生。有一回,我媽還真給他嚇到了呢。你爸店裡有那麼台機器,只要站在機器的開口處,就會有張X光片秀出我們腳的影像。原本她已經打定主意要幫我買新鞋的,可你爸說我的腳很快還會長大,不用急著買。『好個誠實的人哪,小傑,』回家的路上她跟我說。『他其實大可以撈我一筆錢,可是他沒有。』」
「那是他事業成功的秘訣之一。」
「嗯,總之我媽印象深刻。布朗克斯的早年時光還真是叫人回味。說來這會兒咱倆都是清醒的,有時間喝杯咖啡嗎,馬修?」
某天深夜‥‥‥
「我常在想,」米基.巴魯說:「如果生命拐個彎的話,我會是什麼樣的景況。」
此時我們坐在葛洛根開放屋,亦即他經營多年的店面。這一帶整體生活的優質化對葛洛根起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酒館本身其實裡裡外外都沒有多大變化,不過當地的老顧客泰半不是死了便是已經遷徙他方,如今來訪的客層顯然比較溫文且較紳士風。這裡提供健力士黑啤和生啤酒,還有多種高品質的單一麥芽蘇格蘭威士忌以及其他高檔威士忌。登門造訪的顧客得以指著牆面上的彈孔相互訝嘆,也可以一來一往交換酒吧老闆過去光榮與不光榮的事蹟。有些事蹟確...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