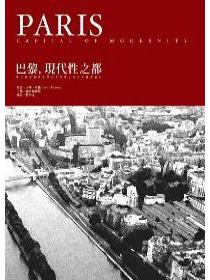《追憶逝水年華》第二卷《在少女花影下》承襲第一卷優雅精鍊的文字風格,敘述主人翁年少時期的人生回憶。在第二卷的第二部中,敘事者擺脫了失戀的陰霾,和外婆來到了明媚的海邊度假勝地巴爾貝克,見識了上流社會的驕奢浮誇。
外婆向他介紹了維爾巴里西斯侯爵夫人,也因此認識了她的外孫──年輕的聖盧-昂-布雷侯爵,這位頭髮、眼睛、皮膚以及舉止,都透著一股優雅的味道的年輕人,很快地就與敘事者成為好朋友。聖盧的良好教養,都讓他感受到與過去友人截然不同的可愛之處。同時,海灘上一群少女的倩影,吸引著敘事者的目光。此時的他每日穿梭在上流社會的沙龍中,因而結識了畫家埃爾斯蒂爾。反正心裡懸懸念念的那幫海灘上的少女不在眼前,所以他才毅然答應外婆的要求來探望埃爾斯蒂爾。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他的畫室裡體驗到的精神上的愉悅,並不妨礙敘事者感受周圍的環境。
但怎麼也料想不到,隨意地望著窗外的鄉間小路,在驀然間,他在埃爾斯蒂爾的畫室外的鄉間小路,看見了少女中那個推著自行車的女孩,她踩著快捷的步子往前走來,他看著她在樹下笑盈盈地向埃爾斯蒂爾點頭致意,敘事者心裡明白埃爾斯蒂爾能把他介紹給女孩,也因此順利地結識了她,漸漸陷入愛河……同時,在這個夏日時分,在內心激盪出充滿甜蜜、苦澀交戰的思慕之情。
作者簡介:
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 1871.7-1922.11)
出生在巴黎一個藝術氣氛濃郁的家庭,但從小就因哮喘病而被「逐出了童年時代的伊甸園」。他的氣質內向而敏感,對母親的依戀,對文學的傾心,為以後的創作埋下了種子。他青年時代經常出入上流社會沙龍,在熟悉日後作品中人物的同時,看穿了這個社會的虛幻。父母相繼去世後,他痛感「幸福的歲月是逝去的歲月」,開始寫作《追憶逝水年華》。在生命的最後十四年中寫成的這部巨著,猶如枝葉常青的參天大樹,屹立於文學之林的最高處。他借助於不由自主的回憶(無意識聯想),將逝去歲月的點點滴滴重現在讀者眼前,使時間在藝術中得以永存。
譯者簡介:
周克希
畢業於復旦大學數學系,曾從事黎曼幾何研究與教學。 1984年起翻譯文學作品,先後譯有《三劍客》、《王家大道》、《追憶逝水年華(節本)》、《包法利夫人》、《小王子》等小說,與人合譯作品有《基督山伯爵》、《追憶似水年華(第5卷)》等。在時報出版的譯作為:《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第一部貢布雷》、《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第二部斯萬的愛情/第三部地方與地名:地方》等。
章節試閱
我不知道,在我讓自己相信這個女孩跟其他女性都不一樣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地方粗獷的景色為她增添了魅力,但我知道,她確實是為這個地方增添了魅力。我想,倘若我真能時時刻刻和她在一起,肩並肩地走向湍流,走向奶牛,走向火車,永遠在她身邊,感覺得到她瞭解我,在她心裡有我的位置,那樣的生活該是多麼甜蜜啊。我盼著她來解開其中奧祕,帶我領略鄉村生活和晨曦的魅力。我對她招手,讓她過來給我一杯牛奶咖啡。我要她注意我。她沒看見,我就喊她。在她高大的身軀上,那張臉膛閃著金光和鮮豔的玫瑰色,像是透過燈光照亮的彩繪玻璃看見似的。她快步走來,我目不轉睛地望著她那越來越大的臉龐,它就像一輪容你直視的太陽,正在朝你趨近,你越來越近地注視著它,紅彤彤的金色光芒照得你頭暈目眩。她那炯炯的目光向我投來,可就在這時列車員關上了車門,列車啟動了;我目送她離開車站,返回那條小路,現在天完全亮了:我正遠離黎明而去。我不知道我這麼興奮激動是由她引起的,抑或我因在她身邊感到的愉悅大半來自我的這種激動,反正她與我的快樂已然交融在一起,再次見到她的欲望,首先就是別讓這種興奮的狀態完全消失,別讓曾經(即便是在她不知情時)和這種狀態密切關聯的這位女孩就此與我分離的一種精神上的欲望。這並不僅僅因為這種狀態是令人愉快的。更重要的是(如同琴弦繃得更緊或綴線振動得更快時,音響或顏色會有所改變)它賦予了我所見到的事物一種全新的色調,引領我作為其中的一個角色,進入一個陌生的、奇妙無比的天地。火車越開越快,依稀還能看見那美麗少女的身影,她儼然是另一種生活的組成部分,那種生活由一條窄窄的地帶跟我所熟悉的生活隔開了。在這種生活中,周圍事物所喚起的感覺,和往常完全不同;而現在從中出來,我覺得心在死去一般。要想感受到這種生活的溫馨,我只要住得離這個小站近一些,能每天早晨到女孩這裡來買一杯牛奶咖啡就可以了。可是,唉!我正在越來越快地朝它奔去的那種生活,她是不會出現在其中了,而我之所以能接受那種生活,正是因為我設想有一天我還會乘坐同一輛火車,停在這同一個車站。這個設想還有一個好處。要從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不計利害關係的角度出發,去分析、深化一種曾經有過的愉快的印象,是必須作出努力的,為了迴避這種努力,我們心裡原來就有著利己的、主動的、實用的、無所謂的、懶惰的、離心的傾向,這一設想,恰恰為精神狀態的這種傾向提供了養分。而另一方面,我們還是願意讓這一印象繼續留存的,所以我們喜歡想像它在未來會是怎樣的,巧妙地為它的再現作好準備。這樣做,於瞭解它的本質並無絲毫裨益,卻使我們無須費神在頭腦中複製,就有可能從外界重新感受這一印象。
有些城鎮的名字,維茲萊和夏特爾也好,布日和博韋也好,都是當地大教堂的簡稱。我們經常採用這種以偏概全的命名法,結果——假如這些城鎮我們還不熟悉的話——就把這個名字整個刻進腦子裡,從此,當我們看著這個名字想像這座城鎮——我們還沒見過的這座城鎮——的模樣的時候,這個名字就會——猶如鑄模似的——給它印上風格雷同的同樣那些刻紋,把它變成一種大教堂。然而巴爾貝克這個字體有幾分像波斯文的藍底白字的名字,我是在一座火車站上看見的。我快步走出車站,穿過車站前的那條大街。我打聽海灘在哪裡,說我想去看教堂和大海。人家好像不明白我想說什麼。我這是在巴爾貝克老城,在巴爾貝克陸地,既沒有什麼海灘,也沒有什麼海港。沒錯,在傳說中,顯聖的基督的確是漁民從海裡找到的;教堂就在離我幾公尺開外的地方,教堂裡的一扇彩繪玻璃上,畫的就是這個故事,修建教堂大殿和鐘樓的石頭,也確實是從海浪拍擊的峭壁上開採的。可是,被我想成舔到教堂腳下的這座大海,是在五哩開外,在巴爾貝克海灘那裡呢。教堂圓頂旁的鐘樓,因為我曾經在書上讀到過,說它本身就是一座籽粒聚集、群鳥盤旋的諾曼第懸崖,所以在我的印象中,鐘樓底座始終是浪花飛濺的。其實,這座鐘樓矗立在一個廣場上,兩條有軌電車的線路在這裡交會。鐘樓對面是一家咖啡館,招牌上寫著檯球兩個金字;在它背後,只見一片屋宇,不見半根桅桿。教堂——除了咖啡館、方才我問訊的路人,以及我還得回去的火車站,這座教堂也成了我關注的對象——融合在周圍的景物中,好似一種偶然,好似這個已近黃昏的下午的產物,此刻它那軟綿綿、圓鼓鼓的穹頂在天空的映襯下,猶如一枚果子,屋宇煙囪沐浴其中的那同一片陽光,催熟了它紅嫣嫣、金燦燦,彷彿入口即化的果皮。但當我認出了眾使徒的雕像——我曾在特洛卡德羅博物館見過他們澆鑄的塑像,就滿腦子淨想著這些雕像的永恆意義,別的什麼也不想了。這些雕像站在教堂大門的門洞裡,列隊等候在聖母像兩旁,就像在歡迎我。它們臉容和藹而親切,鼻子微塌,弓著腰,彷彿有一天會唱著哈利路亞迎上前來似的。不過我注意到,它們的表情是呆滯的,如同死人一般,只有在你繞著它們轉的時候,才會有所變化。我心想:是這裡,這就是巴爾貝克教堂。這個彷彿知曉自己的榮耀的廣場,是世上唯一擁有這座巴爾貝克教堂的地方。在這以前我見過的,僅僅是這座教堂、這些使徒以及門廊裡的聖母雕像的著名照片,只是些拓片。現在我見到的,是真正的教堂,真正的雕像;它們是獨一無二的,是照片所遠遠不能相比的。
但也不一定。這就好比一個年輕人,到了考試或決鬥那天,當他想到自己擁有的知識和要用行動來證實的勇氣時,教師的提問或他射出的子彈,在他眼裡就不值一提了。同樣,原來在我的頭腦中,門廊裡的聖母像遠非我以前見過的那些複製品所能相比,歲月流逝、世事滄桑可以讓這些複製品面目全非乃至銷毀殆盡,但這座聖母像卻是容貌依舊、屹立不倒的,它是完美無瑕,有著普遍價值的,所以當我現在看到這座我在腦海中成百上千次雕過的聖母像就在眼前,看到它就不過是座石頭雕像,在我舉臂可及的地方,我不禁感到非常驚訝。這座聖母像緊挨著一張競選海報,任由我用手杖尖去觸碰,它連著廣場,朝向大街的出口,躲不過咖啡館和電車調度亭裡投來的目光,臉上領受著落日餘暉——稍後,再過幾個小時,就會換成街燈的亮光——的這一半(那另一半則由銀行貼現分理處領受),而且和這家銀行分支機搆共同承受糕餅店灶間的陣陣怪味。遊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倘若我想在石頭上留個簽名,這尊著名的聖母像,這尊迄今被我賦予神聖而不可褻瀆之美的、巴爾貝克獨一無二(唉,也就是說只有這麼一個)的聖母像,這尊和附近房舍一樣沾滿煙炱的聖母像,也只能把我用粉筆頭寫下的名字,展示在每個前來瞻仰的遊人面前。於是,這件不朽的藝術珍品,這件我心儀已久的傑作,終於在我心目中——如同這座教堂一樣——淪為了一座矮小的老婦石像,我可以量她的高度,也可以數她的皺紋。
時間過得很快,該回車站了。我要在火車站等外婆和弗朗索瓦茲一起去巴爾貝克海灘。我想起以前讀過的對巴爾貝克的描寫,想起斯萬說的那句話:「精美之至,和錫耶納一樣美。」我沒法掩飾心中的失望,只能怪事情不湊巧,自己心情不好,過於疲勞,不會欣賞,我安慰自己說,沒去過的城市還多著呢,說不定我很快就會去那些地方,或是漫步在細雨如珠的坎佩萊街頭,傾聽屋簷清脆的滴水聲,或是穿過阿旺橋那玫瑰色中透著綠意的夕照。可是要說巴爾貝克,從我踏上這片土地起,我就像把一個本應密封得嚴嚴實實的名字給打了開來,並且從這個不慎開啟的口子裡,放出了原先一直生活在這個地名中的種種景象:電車,咖啡館,廣場上的行人,銀行貼現分理處,它們經受不住外部的壓力,先是在地名內部鼓起,然後從中噴薄而出(地名本身旋即重又閉合),簇擁在波斯風味的教堂周圍。從此,提到巴爾貝克的地名,我就想到了這一切。
在通往巴爾貝克海濱的當地小火車上,我找到了外婆,但她是一個人——她打發弗朗索瓦茲先動身來巴爾貝克,好預先作些準備,沒想到她指點有誤,弗朗索瓦茲乘上了反方向的列車。這時候,不用說,弗朗索瓦茲的火車正在全速駛往南特,她說不定要到波爾多才會醒呢。外婆的車廂裡彌漫著轉瞬即逝的餘暉和午後持續難消的暑熱(前者照亮了外婆的臉,讓我清楚地看到她是怎樣為後者所累的),我剛坐下,外婆就笑吟吟地問我:「巴爾貝克怎麼樣?」她以為我一定滿心喜悅,所以問這話時臉上洋溢著希望的光芒,我一時倒不敢告訴她我很失望了。再說,身子越來越接近它早晚得適應的地方,腦子裡尋尋覓覓的印象也就不那麼揮之不去了。臨了,旅程還剩一個多小時路程,我就在心裡揣摩起巴爾貝克大酒店經理的模樣來了,此刻我於他還是不存在的,我真想到時候引我見他的不是外婆,而是某一位更有氣派,不像外婆那樣見面就要糾纏打折的同伴。我覺得這位經理一定傲氣十足,但又想不出他到底是怎麼個模樣。
火車到達巴爾貝克海灘前,在一個又一個小車站邊停靠,這些站名(安卡鎮、馬庫鎮、多鎮、庫勒弗爾橋、阿朗布鎮、聖老馬爾斯、埃爾蒙鎮、梅納鎮)聽上去都挺奇怪的,可要是在哪本書上讀到這些名字,又會覺得它們同貢布雷附近的鎮名有些關係。不過,兩首樂曲即使都由相同的音符組成,但只要和聲和配器不同,在一個音樂家聽來就是不一樣的。同樣,這些陰鬱的地名讓人想起的儘是沙子、曠野和鹽,「鎮」鎮這個字,就像「鴿子飛」裡的飛字,一下子就無影無蹤了,讓我沒法聯想起魯森鎮或馬丁鎮那些地名。因為在「廳」裡吃飯時常聽姑婆說起這兩個鎮的名字,它們在我心中被蒙上了一層柔和的光澤,其中攙和著果醬的甜味、柴火和貝戈特某本書的書頁的氣味,以及對面房子砂岩的色彩,直至今日,當這兩個鎮名如同氣泡似的從記憶深處升騰而起,穿越層層疊疊的中間層,到達記憶表層之時,它們仍然保持著那股特有的魅力。
這些小車站從沙丘上俯瞰遠處的大海,或位於顏色綠得刺眼的山崗腳下,已然準備睡去。山崗的形狀讓人看著就不舒服,活像你剛走近旅館的房間,迎面看到的一張長沙發,山崗上有幾座別墅,再往下是一個網球場,有時是賭場,門前的旗子在涼風中獵獵作響,門內則空空蕩蕩,一派惶惶不安的氣氛。就這樣,這些小車站第一次向我展示了這裡的人們,當然我看到的只是他們的外表——戴著白色遮陽帽的打網球的人;土生土長的車站站長,屋旁種著檉柳和玫瑰;一位沿著我所不熟悉的生活軌道過日子的夫人,頭戴扁平的狹邊草帽,呼喚她的獵兔犬歸來,走進燈火已經點亮的木屋——這些日常中顯出奇怪、親切中透著倨傲的景象,無情地刺傷了我陌生的目光和落寞的心。
我和外婆走進巴爾貝克大酒店大堂的時候,我的心又被重重地刺了一下。面對著仿大理石的寬敞樓梯,聽著外婆一個勁地和酒店經理殺價,全然不顧周圍那些陌生人投以不屑的不友好的目光——我們接下去可是要和這些人共同相處的呀。酒店經理是個不倒翁似的矮胖子,那副尊容,那副嗓音,讓人不敢恭維(擠痘痘落下了臉上的瘢痕,地域遙遠的祖籍和滿世界亂跑的童年,落下了南腔北調的口音),他身穿出入社交場合的常禮服,眼睛裡射出心理學家的目光,慢車一到,他總把那些闊佬當成愛還價的客人,把到酒店來順手牽羊的小偷當成闊佬!他大概忘了自己的月薪還不到五百法郎,總是從心底裡瞧不起那些把五百法郎,或者如他所說的二十五個路易看成一筆不小的錢的客人,把他們一律歸入不配來住大酒店的賤民之列。沒錯,在這家豪華的酒店裡,有的客人付的房錢並不很貴,照樣可以受到禮遇,前提是酒店經理能確定這些客人注意開支是由於吝嗇,而不是由於沒錢。吝嗇是一種毛病,在每個社會階層都可能碰到,因此不能因為客人吝嗇就對他失禮。有沒有社會地位,是經理唯一注意的事情,而他眼裡的社會地位,就是他認為足以表明這種地位的標誌,諸如走進大廳不脫帽子,穿高爾夫球褲和束腰短大衣,從軋花皮匣子裡取出一支箍著金絲紅線的雪茄(可惜的是,所有這些體面的標誌,我都沾不上邊)。他愛用一些他以為很講究的說法,其中有語病也渾然不覺。
我坐在大堂的長凳上等外婆,看著外婆裝腔作勢地問經理:「你們這裡,房價怎麼算啊?……喔!比我的預算貴得多囉。」經理聽著她講,帽子也不摘下,嘴裡還吹著口哨,外婆卻並不生氣。而我,一心只想能隱身在心靈深處,藏匿在永無休止的思緒後面,不讓臉上留下一絲一毫表情,一絲一毫有生氣的東西——就像有些動物面臨傷害時,出於抑制作用的本能,一動不動地裝死,——我對這個環境完全不習慣,看著眼前的人們那麼習慣自如,就變得加倍敏感起來,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只有努力讓自己麻木才行。此刻在我眼前的,有一位舉止優雅的夫人,經理對她畢恭畢敬,對跟在她身後的那條小狗也體貼有加,還有一位剛從外面回來的年輕人,衣著講究,樣子有些可笑,帽子上插著根翎毛,正在問「有沒有我的信」,還有那些沿著仿大理石樓梯拾級而上的男男女女,瞧他們的神氣,就像是回到了家裡。與此同時,幾位看上去並無接待經驗,卻有著總接待頭銜的先生,朝我板著臉,把邁諾斯、埃阿科斯和拉達曼堤斯的目光(我的靈魂袒露在這目光下,猶如袒露在一片全無遮擋的陌生世界中)向我射來。稍遠處,在一塊長玻璃後面,一些人坐在閱覽室裡,我若要描寫這個閱覽室,恐怕非得從但丁的《神曲》中依次引用有關天堂和地獄的描寫不可:想到這些有福之人有幸在裡面安靜地看書,我想必會選些描寫天堂的段落;但想到外婆要是不顧我的感受,硬要我也進去,我會感到多麼恐懼,這時我恐怕就要選描寫地獄的段落了。
過了一會兒,我的孤獨感變得更強烈了。我跟外婆說,我不大舒服,我覺得我們得回巴黎了,外婆沒說什麼,只說了句她出去買點東西,不管我們是走是留,這些東西都用得著(我後來才知道,那都是給我買的,弗朗索瓦茲把我可能要用的東西都隨身帶走了)。我信步在街上走著,等外婆回來。街上行人熙熙攘攘,炎熱不亞於室內,理髮店和一家糕點鋪都還沒打烊,顧客在糕點鋪裡吃霜淇淋,臉朝著杜蓋-特魯安的銅像。我驚奇地看到,竟然有這麼多跟我不同的人,酒店經理何不勸我到城裡到處走走、消遣消遣呢,那樣我就可以知道,一個使我痛苦不堪的所在(全然陌生的住處),在有些人眼前真可能就是酒店廣告上說的「樂園」呢。廣告也許有些誇張,卻是迎合某一個顧客群口味的。對這一消費群的顧客而言,這本廣告小冊子不僅激起了他們到大酒店來享用「珍饈佳餚」、一睹「遊樂場美妙風光」的欲望,而且激起了他們的好奇心,因為這是「時尚女王的裁決,誰要是拒不執行女王的裁決,就將立即被判為庸夫俗子,但凡有良好教養者,諒必無人願冒此風險」。
我擔心自己讓外婆感到失望了,所以就更離不開她。她大概真的對我沒有信心,覺得我連這點勞累都受不了,就沒法指望旅行會對我有好處了。我決定回酒店去等她。酒店經理親自為我按了一個按鈕:一個我還不認識、人稱lift的角色登場了(他高踞於酒店最高處,相當於諾曼第教堂的頂塔所在的位置,好似玻璃棚裡的一位攝影師,或者演奏室裡的一位管風琴師),只見他快速朝我而下,有如馴養的松鼠那般敏捷,受制中不失靈巧。隨後,他又帶著我沿一根立柱升向這座商業殿堂的穹頂。在每一層樓,通道樓梯兩側呈扇形排列著幽暗的走廊上,時而有收拾房間的侍女抱著長枕頭走過。我想把自己最富有激情的夢中見到的表情,賦予侍女那張在暮色中顯得朦朧的臉,但從她瞥來的目光中,我看到的卻是對一個微不足道的人物的厭惡神情。由每層一個廁所形成的那排玻璃豎窗,把這個了無詩意的所在照得半明半暗,在無窮無盡的上升過程中,為了驅散我在穿越這神祕的寂靜時感到的莫名恐慌,我開口跟年輕的管風琴師搭腔——這位旅途相遇的藝匠、幽禁中的伴侶,始終在他的龐然大物上拉音栓、推音管。我為自己占了這麼大的地方、給他添了這麼多麻煩,向他表示歉意,問他我是否妨礙了他的演奏。我一心討好這位演奏高手,所以不光表示了我的好奇,而且誠懇地傾訴了我的仰慕。可是他沒有搭理我。或許我的話讓他感到驚訝了,或許他是在專心工作,或許他是出於禮貌,或許他是有些耳背,所以看上去態度有些生硬,或許他對這個地方充滿了敬畏感,生怕會出事,或許他是懶得動腦子,要不就是經理這麼關照過。
我不知道,在我讓自己相信這個女孩跟其他女性都不一樣的時候,是不是這個地方粗獷的景色為她增添了魅力,但我知道,她確實是為這個地方增添了魅力。我想,倘若我真能時時刻刻和她在一起,肩並肩地走向湍流,走向奶牛,走向火車,永遠在她身邊,感覺得到她瞭解我,在她心裡有我的位置,那樣的生活該是多麼甜蜜啊。我盼著她來解開其中奧祕,帶我領略鄉村生活和晨曦的魅力。我對她招手,讓她過來給我一杯牛奶咖啡。我要她注意我。她沒看見,我就喊她。在她高大的身軀上,那張臉膛閃著金光和鮮豔的玫瑰色,像是透過燈光照亮的彩繪玻璃看見似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8收藏
8收藏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8收藏
8收藏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17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