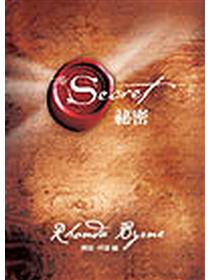艾未未在紐約的「那些爛事兒」
文/ 萬靜、崔迪
二十四歲的艾未未來到紐約,生活隨心所欲,有時一天吃五頓飯,有時只吃一頓。實在很無聊的時候,艾未未會對著鏡子舉著相機自拍,有時裸著,有時穿著,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給別人拍的照片則是「不想看」。這些照片一放就是二十年,直到2009被北京三影堂攝影藝術中心從一萬多張照片裡整理出兩百四十六張,組成艾未未自傳性的攝影展「紐約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議採訪他的記者去看他這個攝影展:「去看了就會知道我為什麽會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覺得到一個地方,最重要的是獲得它的極大值。對我來說,美國這個社會能獲得的極大值,並不是所謂的美國夢,即由於你個人某種努力變得更有錢,更有社會地位。」對艾未未來說,極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間,可以過得更荒誕一些,更無聊一些。
艾未未的無聊時期那些近乎「老照片」的攝影展,意外獲得廣東美術館和中山大學共同設立的沙飛攝影獎青睞,與紀實攝影家張新民一起,成為今年的攝影創作獎得主。
「為什麽是艾未未?」不少人質疑。評委之一的顧錚反問:「為什麽不是艾未未?」
「可以毫不客氣地說,把所有中國留學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沒有我的照片豐富。」艾未未調侃地說。
2009年5月18日,艾未未的這部分照片,將與沙飛攝影獎其他獲獎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廣東美術館附近的嶺南匯會展覽館展出。
2009年10月艾未未在德國還將有「非常遺撼」個展,「在希特勒為自己蓋的第一座美術館裡,我想做兩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對這次的四川大地震做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表達。」
十年「畢卡索」
1981年,艾未未放棄了「在北京電影學院珍貴的讀書機會」,跟隨女友去了美國。對大部分人來說,艾未未這樣一個剛從新疆來的小孩,語言不通,更別說英語,又沒有錢,去美國幹什麽?「我回家去了。」艾未未總是這樣回答,「實際上並不是我多麽嚮往美國,而是北京我實在待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機場的路上告訴母親:「十年以後你們能再見到一個畢卡索回來。」
去紐約前,艾未未在「沉悶古老」的費城待了半年,瘋狂學英語;然後去陽光燦爛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舊讓他感到非常無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腦都被太陽蒸發了」。
1983年,艾未未去紐約的帕森設計學院 (Parsons School of Design)學習。一年後,他的藝術史課程沒通過,有一說是因為他逃課太多。學校停止發放獎學金後,。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走人,也不再去定期註冊居留證,成為紐約「非法居住者」中的一員。
艾未未住在第七街的地下室公寓,是中國人在紐約屈指可數的幾個著名的落脚點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應,認識的不認識的,總能過來住下一陣。住過他那裡的,有等待成名的藝術青年,還有一些到紐約碰運氣的留學生。還總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掛個越洋電話回國。
艾未未在紐約跟小偷打成一片,哪個中國人東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從哪裡找回來。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過來。那時國內正在「嚴打」。他沒想到哥哥會那麽全能,在紐約幾乎什麽工作都做過:打掃屋子、鋤草、帶小孩,還當過建築工、電工、搬運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櫥裡除了幻燈機、打字機,還堆過電鑽、電鋸、電焊槍之類的工具。
兩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時間,在紐約街頭貼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廣告。電話亭裡、商店的玻璃門上、地鐵車站裡、公園的樹幹上,到處都是:「我們有專業的技術,熱情周到的服務,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錢,就能將舊房變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畫家一樣,艾未未也在紐約街頭給人畫過像。畫像的以年輕的戀人為多。往往他們先凑過來斜著腦袋看上一會,然後男的便會開口問女的有沒興趣,女的總是回「你說呢?」在去紐澤西州大西洋賭城「提款」前,這是他的謀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頭畫畫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過,拷起來扔到一輛警車裡。罪名是沒有執照,非法經營。「跟中國的城管幹的事情差不多。不過美國的警察不能打人。」
便衣會在畫家收錢的時候衝上來抓現行犯,甚至還會有便衣坐在那兒讓畫家畫,畫完了再討價還價,然後付錢的同時抓人。如果是免費給人畫,他們就奈何不了你。
艾未未沒被抓過,被抓也沒什麽大不了的。警察二十四小時內就得放人,給你一個出庭的罰單,讓議定某個時間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頂多罰款一、二十美元。
自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兩年時間,變成了大西洋城的賭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錢的時候,只需要在那兒花個一天一夜的時間,就能夠賺三千到五千美元。」
那時候只要艾未未打電話給大西洋城,他們都會派車到紐約來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輛超長的凱迪拉克緩緩停下,一個黑人帶著白手套把車門給他打開,艾未未從地下室鑽出來跳進去,駛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這個傢伙一定是販毒的。」艾未未計算了一下,紐約到大西洋城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兩年當中,我屁股離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兩百次。」
艾未未「根本不讀書」
文/周文翰
除了著名詩人艾青之子的身份外,艾未未還有不少可以讓人羨慕的頭銜:旅美藝術家、中國前衛藝術代表、「鳥巢」設計者赫爾佐格和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 Architekten)事務所的中國顧問、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的副導演等。這一次,他的身份是書房主人。
問艾未未「愛讀什麼書?」,他常會說「我根本不讀書」——但是他「翻書」,出去旅行的時候會習慣性地帶兩本書,閒暇的時候翻翻。在他住所二樓書房裡的多數書籍都是畫冊或者圖文書、設計類和藝術類的書居多,確實適合翻看而不是閱讀。而注重文字的書,則在一樓的另一個書房。書房透露出艾未未和書離不開的關係,他讀書、買書、出書,還燒過書。
未讀書,先燒書
艾未未是詩人艾青的兒子,從小就看到家裡有很多書。那時候他隨父母在新疆石河子農場生活——艾青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不滿一歲的艾未未就隨父母到黑龍江農墾農場,1959年轉到新疆石河子墾區,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
「因為父親在法國待過,也喜歡美術,所以家裡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畫冊,印刷製作都非常精美,他也非常愛惜書,不愛借書給別人,在家裡讀書的時候也很仔細,我們是不能亂翻、折角的。」雖然小時候還讀不懂,但艾未未也常常懷著鄭重的心情翻翻書。艾未未正經讀的第一本書是《三國演義》。那年他十一歲,自我意識逐漸成熟。
但是當1966年之後,這些書成了麻煩,「不燒不行啊,因為一波一波造反派來抄家,翻批註、筆記找反動罪證,我父親不得不燒了。」因為書太多,父親燒不過來,正上小學二年級的艾未未也叫同班同學來幫忙一起燒書,「因為很多畫冊都有封套,紙張很精緻,我就想把封套取下來送給同學包書,但是有的我們怎麼抽也取不下來。」他和父親一起看著一堆書燒成灰燼。邊上是他們拆下來的硬紙板,「那些封套的精美是現在很多書比不了的。」
之後的文化荒蕪年代,「書籍特別珍貴,眼睛特別饑渴,首先是書少,如果誰有一本書就非常了不起,會在愛讀書的人之間傳來傳去。那時候石河子墾區的文學青年都互相認識,誰有什麼書就會來借,有人從很遠的地方來借書,也沒說上什麼話,接過書後點一下頭;有的人很仔細,讀完還自己包上書皮,送來的時候也不說話,好像書本身就承載了好多東西。」
有人從黨校帶來《反杜林論》、《共産黨宣言》等等「馬恩列斯」的著作,書印得非常漂亮,設計很好,白紙上醒目的紅字,上面還印有「內部資料」的字樣,「看上去很嚇人,我就讀這樣的書。」艾未未的父親看到他讀這類革命領袖著作覺得很好笑,說他「小小年紀懂什麼啊,是不是長大了想做指導員?」
後來他父親待遇改善,一些藏書發還給家裡,艾未未得以看到全套的《外國文學》、《譯林》一類的翻譯文學雜誌,全是上世紀1950年代開始出的,每一期都有中短篇小說,有蘇聯、智利這些國家的小說家的作品,其中蘇聯的還是「供內部批判用」,和國內小說家模式化的寫作相比更吸引人,所以非常熱門,「凡是帶『譯』字的書都借來借去。」
送書和買書
上世紀1970年代末翻譯家楊憲益送給艾未未幾本畫冊,其中一本是竇加,一本是梵谷,一本是馬奈,是小本的,當時北京還沒有,製作非常精美。因為是外文,有人借去還邊查字典邊注在旁邊。還有美國藝術家賈斯伯瓊斯(Jasper Johns)的畫冊,他一看上面是美國國旗、地圖之類的,由於當時他對藝術的認識還停留在梵谷那個階段,所以覺得「畫的是什麼啊,能算藝術嗎?就扔一邊去了。但是後來到美國,這是我特別喜歡的一個藝術家。一直看他的畫冊,以及之後接觸到杜象的創作,對我影響很大。」
1981年,他到美國後買的第一本書是《安迪.沃荷的普普人生》,「有點繞來繞去想到哪說哪的風格,很有意思,至今還在我的書房裡。」從這本書中也可以發現艾未未說話風格的部分來源。他在紐約到處搬家,靠打零工生活,所以沒有買動輒幾十美元的書籍,而是經常去書店看書,翻看自己感興趣的書。他曾經在格林威治村不遠的東村住過十年,那裡是紐約作家、藝術家聚集的地方,有三家書店比較有名,一家書店賣的全部是舊書,號稱一本一本擺的話有八英里長,都是文學藝術類圖書,他成天沒事就到書店中亂翻。
藝術家艾未未
文/ 謝小韞
可以沒有藝術,但不能沒有生活……對我來說,沒有人生,只有瞬間……
──艾未未
艾未未是誰?
對我而言,他只是一位藝術家。
有人說他是社會運動者、建築師、人道關懷者,但本質上,他仍然只是一位藝術家。他說,他不喜歡被冠上這些頭銜,他只是一個人,做了一些事而已。
2009年7月,日本東京森美術館為他舉辦個展,我也應邀參加開幕酒會,並約他談談2011年底,在台北市立美術館策辦他在台灣第一次個展的可能性。他知道我來自台灣,以靦腆的笑容及柔和的語調說,他很嚮往去台灣,台灣的民主政治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引導我看他的作品,並說,他在台灣的展覽要有很多新的創作才行。
那晚的開幕典禮賓客雲集,把森美術館的茶會大廳擠得黑壓壓的一片,艾未未在圍繞寒暄的人群裡,顯得有些不自在,卻始終保持靦腆的微笑,好像與現場歡樂的氣氛完全無關似的。
第二次跟他相見,是2009年年底。他應中原大學之邀,來台講學一周,我約他來看北美館的「蔡國強特展」及未來他可能會展出的場地。他瞥見地下室的演講廳門口,有一個立牌寫著「因藝術家臨時取消檔期,特此致歉」,於是促狹地照了一張相片,說:「這是很好的展出方式,說不定我的展覽,也要立一張像這樣的牌子!」
這是他第一次來台灣,我招待他吃欣葉餐廳的台菜。他對烏魚子這道菜讚不絕口,雖然烏魚子的大量膽固醇對他的體型而言不是很適合,但他可不忌口,以「人要活在當下」為辭,笑呵呵地大口大口地享用美食。
第三次是在2010年5月,我去參觀上海世博時,與北美館展覽組長吳昭瑩順道去北京草場地艾未未工作室,洽談2011年10月在台北市立美術館舉辦艾未未特展的規畫內容。
北京在奧運後,整個城市從一位典雅的老姑娘,像做了小針美容似地,一張臉頓時時髦豔麗起來,可是脖子以下,仍是老樣子。老樣子有老樣子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