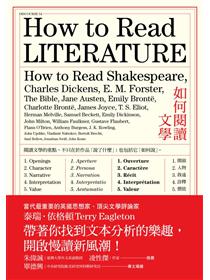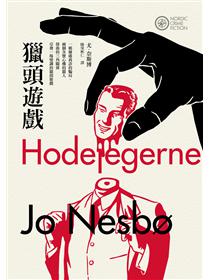呂健忠譯注的《易卜生戲劇集》是繁體中文戲劇出版界的盛事,全套五冊共十五部劇本,完整呈現易卜生為現代戲劇拓土開疆的創作歷程。
身為現代戲劇的開宗祖師,易卜生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生涯中,有四十年是在摸索如何從浪漫風格破繭而出,繼之以開發中產階級散文劇的無限潛能,到最後終於孕育出佛洛伊德心理劇。他在暮氣沉沉的歐洲劇壇發動一人革命的過程,以及他成就戲劇宗師的革命志業,都可以在這套劇集一覽無遺。
易卜生的戲劇美學落實在他對於愛情倫理、婚姻倫理與社會倫理的關懷,他對於兩性關係前瞻視野,以及他視舞台寫實為展現人生視野與心靈景象的媒介。他的人性洞察力可以和莎士比亞相提並論,運用社會大眾日常的語言,呈現其精闢的觀點於讀者與觀眾熟悉的社會情境。
《小艾歐夫》是易卜生劇場情慾意涵最濃烈的作品,劇中呈現易卜生散文劇所見最崇高的理想。有論者譽其為「易卜生浪漫情慾的典範之作」,劇中探討身體意識對家庭倫理可能造成的影響:一旦否認身體是成長過程的一個面向,性愛觀隨之偏差,這樣的人生如何尋找出路?
《約翰‧蓋柏瑞‧卜克曼》描述雄心萬丈的金融家為了事業野心,不惜讓渡情人。他在劇中和一對雙包胎姊妹爭奪一個年輕人,三個大人各懷私心,年輕人卻堅持自己的願景,不經意化解上一代的恩怨情仇。執迷不悟的人注定作繭自縛,活出自己才是掌握幸福的不二法門。
《復甦》是易卜生五十年創作生涯的「收場戲」,劇中透過兩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的「復活日」呈現四個主題:1.重新審視婚姻倫理,如《玩偶家族》;2.尋求真愛的意義,如《羅斯莫莊園》;3.追尋失落的記憶,如《營造師傅》;4.探討個體/人心的解放,這是易卜生全集最深刻的洞識。
本書特色
1.譯者累積二十餘年翻譯西洋文學經典的經驗,繼莎士比亞和希臘悲劇之後,以十年的時間完成這一套劇集的翻譯,為中文世界提供迄今最接近易卜生精神的版本:以詩人的心態、才情和洞識從事劇本創作。
2.使用當代中產階級的語言,揭發其茍安心態,呈現個體心靈尋求解放的可能,使劇本在深度、廣度與趣味同時具備足以頡頏小說的藝術價值和可讀性。
3.提供中譯本所見最周全、最適切的注釋,一來有助於讀者跨越時間、地理與文化的鴻溝,二來有助於讀者欣賞易卜生經營寫實主義、開發象徵主義、探討潛意識心理的戲劇美學。
作者簡介:
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
挪威詩人及劇作家,擅長以逼真的手法呈現當代的問題,使中產階級寫實主義成為現代劇場美學的標竿。
易卜生早期的作品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愛情喜劇》及《勃朗德》這兩部詩劇可以看到浪漫題材如何展現現實的關懷。散文劇在《青年同盟》初試啼聲之後,從《社會棟樑》到《全民公敵》全面批判中產階級虛偽與自私自利的心態。易卜生開創寫實戲劇的路線,卻又突破寫實主義的框限,從《野鴨》到《海妲.蓋柏樂》可以看到他如何積極開發象徵主義的戲劇潛能。晚期的作品轉而探討潛意識的衝動,從《營造師傅》到《復甦》無異於宣告佛洛伊德心理劇的誕生。
易卜生的劇作是現代戲劇的羅馬,現代戲劇所有的道路都是以他為起點或終點,故被冠以「現代戲劇之父」的稱號。
譯者簡介:
呂健忠
當代傑出翻譯家,除在大學外文系授課外,矢志翻譯西洋經典,推廣經典閱讀。已出版重要譯作包括《馬克白:逐行注釋新譯本》、《利西翠妲》、《新編西洋文學概論》、《近代西洋文學》、《英國文學史略》、《變形記》、《情慾幽林:西洋上古情慾文學選集》、《情慾花園:西洋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情慾文選》、《丘比德與賽姬︰女性心靈的發展》、《奧瑞斯泰亞:逐行注釋全譯本》、馬基維利《論李維羅馬史》與《君主論》、奧維德《變形記》、《索福克里斯全集I:伊底帕斯三部曲》、《索福克里斯全集II:特洛伊四部曲》等。
章節試閱
2. 成就戲劇宗師的革命志業(五之五)
易卜生最後四部劇本有個共通的題材:雄心萬丈的男人夾在生命情態殊異的兩個女人之間。由此引出一個共通的主題:男人把女性的慾望工具化,依自己的需要決定用或不用。工具化的結果是女人在感情的領域處境堪憐。有人檢討十九世紀自殺的主題所呈現的女性特質,指出女性自殺的故事傳統上集中在情場失意與貞操被奪這兩個主題,吻合女人為愛而活,男人卻為自己而活(Higonnet 103-18)。這樣的觀察在《小艾歐夫》特能引起共鳴,不只因為該劇是易卜生劇場情慾意涵最濃烈的作品,也因為劇中呈現易卜生散文劇所見最崇高的理想。
第一代的評論家非議《小艾歐夫》「展現一幅身心疾病圖」,深感慶幸「那不是常態人性的命運」(Egan 340-1),並非無的放矢,雖然流露典型的維多利亞式道學口吻。比較持平的說法是,該劇為「易卜生浪漫情慾的典範之作」,「劇中探討性反常—否認身體是成長過程的一個面向,以避免觸犯禁忌或禁慾的性罪行」(Durbach 1982: 105)。阿梅旭與妻子作愛,在亢奮的狀態下叫出「艾歐夫」,睡在一旁的獨生子艾歐夫受驚摔落地上,導致殘障。「艾歐夫」這個名字原本是小時候他在遊戲場合,把相依為命的妹妹阿絲塔打扮成小男生時使用的暱稱。長大後,他的才華吸引了出身富裕的瑞塔。瑞塔允諾保障他們兩兄妹無後顧之憂,因此順利嫁給阿梅旭。婚後生子,阿梅旭沿用「艾歐夫」為孩子命名,此即劇名所稱的「小艾歐夫」。
這樣一個佛洛伊德式精神分析有機會大展所長的劇情背景,對從事創作已達半個世紀的易卜生形成莫大的挑戰。手稿顯示他修改的過程幾乎無異於重新創造,尤其是對於人物關係的重新界定(McFarlane 1977: 8-10, 17-22),畢竟他要在對情慾仍然敏感的年代探索因為被列為禁忌而沒有人跡的感情地帶。結果,我們讀到的是在易卜生戲劇集中最沒有戲劇意味的劇本,卻使用最工筆細描的寫實筆觸,不同的草稿顯示創作者對於這些細節所下功夫之深,為的就是在劇場貫徹「經營寫實幻覺」的初衷(Tennant 77-8)。
孩子發生意外事故,阿梅旭體認到人生責任之重大,從此獻身於哲學著作《人的責任》,夫妻性疏離遂不可免。「這個癥候太熟悉了,性的結局是死亡、殘廢與罪惡」(Durbach 1982: 161)。然而,阿梅旭追求的人生意義其實僅止於抽象的宣示,他的才華只不過是瑞塔婚前一廂情願的認定。就像《營造師傅》的索爾尼斯要滿足希珥德對於英雄崇拜的幻想,阿梅旭的男性尊嚴促使他非要維持哲學家的形象不可。他的思想不足以寫出哲學論著,用於耍嘴皮折服拙於推理的瑞塔倒是綽綽有餘,他的口頭禪「變化的法則」就是在這樣的時機產生大妙用。更可議的是,他婚後依然擺脫不了童年時代對阿絲塔的性幻想,而且以寫作為刻意疏離性關係的藉口。這和他透過性幻想逃避可能隨性而來的「責任」是同樣的心理,都是在逃避身體現實及其隨之而來的現實壓力。
劇情從阿梅旭覺悟到自己根本不是哲學家的料子揭開序幕。他放棄哲學論著的寫作計劃,理由是要在兒子身上具體實踐身為人父的責任。他要以行動取代理論,動機不難理解:人生不能沒有具體的目標。選定目標確有必要,問題在於動機,他依然無視於自己身為人夫的責任。由此可見他仍然怯於面對自己,仍然在逃避婚姻的責任。他端出推理的架勢,說他對她「性」趣不再乃是合乎無常律這個人類行為的通則,他稱之為「變化的法則」,堅持他教育艾歐夫的計劃是出於他希望兒子快樂的心願。瑞塔卻憑其直觀的生命感受一針見血戳破丈夫的說詞,說他的動機「不是出於對他〔艾歐夫〕的愛。摸摸自己的良心。」他的「使命情結」和《野鴨》的葛瑞格斯異曲同工,同樣因為心理的偏差而把「使命」攬上身,不同的是葛瑞格斯為了照亮自己黑暗的生命圖像而不惜燃燒別人的家庭幸福,阿梅旭卻是為了維持膨脹的自我形象而不幸擠壓自己的家庭幸福。在易卜生的舞台世界,沒有愛情的婚姻是道德原罪。阿梅旭得要等到他能夠對自己坦誠才可望得到救贖。易卜生為他安排一個救贖的機會:就在他說出自己的新使命的那一天,小艾歐夫溺水死亡。
瑞塔是易卜生筆下最性感的女人,她的性感源自她坦然面對自己的身體需求,既不壓抑也不做作。性慾,尤其是女人的情慾之歡,是十九世紀歐洲主流文學視而不見的一片領域,易卜生刻劃瑞塔這個異數則是見人所未見。或許有人覺得易卜生言過其實,「但是瑞塔被誇大的性驅力未嘗不是源自她的丈夫同樣過度獻身於他的理想」(Esslin 79)。《羅斯莫莊園》的貝阿塔,因為嫁給性趣缺缺的丈夫,常期壓抑當然饑渴,結果卻把丈夫給嚇壞了。阿梅旭的情形雖有不同,落花有「慾」而流水無情則一。一如在《羅斯莫莊園》和《海洋女兒》都可見到的情形,指責別人心靈不健全往往是為了否認自己所造成而使別人感到困擾的行為,藉顛覆真相以規避責任,阿梅旭也有這樣的傾向。誠然,瑞塔在阿梅旭身上激發的是「恐懼」多於慾望,此所以她一心想重拾新婚時的濃情蜜意而不可得:「阿梅旭排斥瑞塔,不是像他自己宣稱的因為他要獻身於『更高尚的本分』,而是因為他再也不要勉強自己跟妻子作愛」(Templeton 155)。瑞塔的浪漫情慾可比擬於《海洋女兒》劇中艾梨妲的浪漫幻想,她們兩個人的故事都涉及如何應付被男性伴侶給剝奪了的感情領域。可是在《小艾歐夫》,景況更悽慘,賭注更高,結局則更不確定,其中涉及的損失不是由於選擇,而是源自死亡—獨生子之死。
艾歐夫死後,夫妻的反應大不相同。「阿梅旭在John Northan所稱『受到冒犯的利己主義』—這是因計劃受挫而產生的怨懟心理—和形而上的思索這兩者之間游移,瑞塔卻是感同身受,同時對孩子、阿梅旭和她自己感到絕望。……一如《野鴨》劇中的吉娜,瑞塔『緊盯著這個孩子』;一如亞馬,阿梅旭想到的是這孩子的生命對他的意義」(Templeton 154)。不同的反應傳達不同的人生態度。事後,阿梅旭躲入樹林一角,向阿絲塔尋求慰藉,同時也在逃避瑞塔,也就是逃避婚姻現實。瑞塔找丈夫分享悲慟,卻演成互相控訴的場面。阿梅旭自我標榜是好爸爸,因為他為了艾歐夫犧牲寫作的計畫。瑞塔當然不會輕易放過這樣自欺欺人的說詞:她已經看出阿梅旭欲以《人的責任》這本倫理哲學論著成就名山事業根本是白日夢,也看出他開始懷疑自己根本沒什麼生平志業可言。有福同享固然好,共患難談何容易。阿梅旭說對了一句話:「悲傷使人狠心又醜陋。」這是他第一次看到真實的自我。看得到真實的自我就有機會擺脫過去的陰霾,只是承擔不起責任的人通常也缺乏行動力。
比起阿梅旭,以感情為依歸的瑞塔擁有更豐富的生命情態和更寬廣的生命幅度。她原本也有極端自我中心的一面,易卜生就是以她的自我中心為架構情節的主樑。「《小艾歐夫》劇中,衝突存在於母職與順情隨性的女性情慾兩者之間」(Esslin 79)。母職是社會角色應盡的本分,情慾則涉及個人的主體意識。《營造師傅》劇中的艾琳‧索爾尼斯把母親的本分無限上綱,導致一對雙胞胎營養不良而夭折,在終其餘生的無性婚姻生活中無法從喪子之痛復元。瑞塔處在與艾琳對立的一端。瑞塔拒絕接受無性婚姻所反映的不只是她對丈夫的慾望:性認同是自我的一部分,瑞塔奮戰阿梅旭是為她的自主性而戰。
為了彰顯瑞塔的人格特質,易卜生苦心孤詣為她量身訂製創造一個陪襯人物,即阿梅旭的妹妹阿絲塔,而且在後半齣戲才透露這一對兄妹沒有血緣關係。艾歐夫死後,阿梅旭乍然喪失人生的目標,為了逃避現實而盼望重溫婚前他和妹妹共享的伊甸園。在這節骨眼,阿絲塔說出他們不是兄妹,因為她是她母親的私生子。阿絲塔說這一來「一切全都改觀」,意思是他們不再能夠以兄妹關係掩飾彼此的感情。阿梅旭堅持他們的關係還是同樣神聖,因為他要的是不因性慾而複雜化的愛,也就是不必作愛就能擁有愛,這卻不是阿絲塔所要的。眼看在性方面被阿梅旭拒絕,阿絲塔接受卜傑姆求婚,「存心藉由她與另外一個男人的關係埋葬她對阿梅旭的愛」(Templeton 158)。阿絲塔還是原來的阿絲塔,瑞塔可就不一樣。第三幕寫的就是瑞塔的蛻變以及阿梅旭受到的影響。追根究柢,小艾歐夫之死使她領悟到自己的感情生活過度自我中心,因而忽視自己的兒子。她的自我意識使她敢於面對自己的過去,也因此理直氣壯反駁阿梅旭所謂紅顏禍水之類的指控,並且一筆勾消自己對阿絲塔的醋勁。瑞塔以博愛取代阿梅旭的復仇心,要開放莊園接納那些目睹小艾歐夫溺水卻見死不救的野孩子,新的自我就這樣從舊自我的灰燼中浴火重生。本劇以青春洋溢而活力四射的瑞塔在明媚的陽光下揭開序幕,收場則是瑞塔身著喪服在薄暮籠罩之下,不過晨曦可待。瑞塔的生活重心原本是她與一個男人的情慾關係,後來一變而為嘗試在現實世界活出責任。
瑞塔為自己同時也為阿梅旭而活,阿絲塔卻不只是為阿梅旭而活,甚至是藉他而活。瑞塔要求的是為自己而快樂,阿絲塔卻是在阿梅旭的快樂中找到自己的快樂。在阿絲塔對比之下,我們赫然發覺瑞塔的人生觀原來是「活出自己」,是具體實踐《玩偶家族》的諾拉所稱「為自己盡本分」是生而為人最神聖的責任這個婦女解放宣言,同時印證蘇格拉底在《答辯詞》所說「不加檢討的人生不值得活」。她的蛻變「是女性主義啟蒙的典範。女人一把推開愛情三角關係,接著選擇一項志業」(Templeton 161)。因其如此,阿梅旭終於能夠在妻子的引領下找到實踐「人的責任」的可行之道,找到以愛取代恨的動力源頭。
易卜生從社會問題轉而專注於自我的本質之後,越來越著重於人物關係的網絡世界,尤其是家庭世界的兩性關係。《小艾歐夫》呈現那個小世界的複雜面,人物之精簡、筆觸之含蓄、關係之錯綜、轉折之劇烈、劇情之緊湊與寄意之深遠,毫無疑問是集易卜生戲劇風格之大成。阿梅旭決定把餘生奉獻給獨生子,這也意味著兒子的地位比妻子優先。可是對瑞塔而言,妻子的身分永遠比母親的身分優先。這個情況使得身兼妹妹、小姑與阿姨三重身分的阿絲塔得以「乘虛而入」扮演起母親的角色。阿絲塔這個「代理母親」甚至還有更優先的一個身分:妻子準代理人。阿梅旭和瑞塔的婚姻根本就是心理學所謂置換作用和昇華作用的結果,他把自己對阿絲塔的性幻想轉化成社會倫理所容許的兩性關係。劇中第一幕用於類比瑞塔之性饑渴的鼠娘,由於年輕時遇人不淑,終生懷恨而成為害人精,摔落峽灣溺斃的小艾歐夫只是眾多受害名單之一。兒子之死促使瑞塔有生以來第一次檢視自己的感情世界,原本就是性情中人的她終於在第三幕逆轉鼠娘的作為,把峽灣下的野孩子接上山,大大小小一個個成為她家中的新艾歐夫。死亡發揮觸媒的作用,引出一部婚姻啟示錄:只要接受社會責任,家庭的犧牲是有可能帶來救贖(Weinstein 293-318)。死亡(thanatos)與情慾(eros)互相激盪產生大愛(agape),從瑞塔的喪子經驗隱約可以察覺到地中海盆地從大母神信仰轉變為基督教文化所透露的情慾史。愛可以有更廣博也更深刻的意義,否則無法適應拓展不已的生命視野。
孩子這個家庭變數在《約翰‧蓋柏瑞‧卜克曼》再度成為劇情結構的樞紐。但是在《小艾歐夫》,阿梅旭和瑞塔後來瞭解到為兒子之死互相怪罪對方無法撫平傷痛,雙雙希望阿絲塔留在他們身邊取代一去不回的艾歐夫,既可以當夫妻關係的潤滑劑,又可以使夫妻有共同的寄託。由於阿絲塔的拒絕,這一對夫婦終於有機會明白未來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可能求之於別人的憐憫施捨。小艾歐夫的意外死亡引發一場造山運動,把相關人士推到生平不曾體驗過的存在高度。《約翰‧蓋柏瑞‧卜克曼》劇中,剛成年的耶哈特面對父母和阿姨各懷私心,寄望他代為完成人生願望的三面親情圍攻之下,自主選擇當下快活的人生之道揚長而去,上一代恩怨情仇相形之下只是一場惡夢。
惡夢的肇因在於標題人物卜克曼本身的人格特質。他是銀行總裁,素懷鴻鵠之志,一心想創建多角經營的跨國大企業集團,卻挪用客戶存款,東窗事發被捕入獄。出獄後,他在住家據守二樓自閉八年,繼續編織企業帝國的美夢,隨時準備接待相關人士前來恭迎他復出金融界。妻子耿希珥在樓下聽他來回踱步八年,加上八年牢獄之災,夫妻十六年不相往來,跟雙胞胎情敵不相往來的時間一樣長。雖然耿希珥把他形容為「一匹病狼在籠子裡踱步」,卜克曼看自己卻有如德國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在巴黎植物園看到的豹:
由於鐵欄杆來來回回的行列,
他目光煥散不再有眼神。
彷彿有鐵條一千根,
千根鐵條的後面沒有世界。
他跨出柔順卻有力的腳步,
同心圓越兜越細小,
像環繞軸心的儀式舞蹈,
雄偉的意志陷入恍惚。
只偶爾他瞳孔的簾幕默默掀啟,
容許一個影像穿透
四肢因緊張而靜止的肌肉,
又闖入他的心,當下消逝無跡。
卜克曼認為自己是龍困淺灘,其實他只不過是個對權力和財富執迷不悟的幻想家。他的價值觀只有一個標準:「對我的野心有什麼助益」(McFarlane 1977: 26)。
劇情以埃臘造訪孿生妹妹耿希珥揭開序幕。埃臘是卜克曼的初戀情侶,雖然早就被他出賣以換取權勢,依然無怨無悔守候他一輩子。她在卜克曼夫婦最慘澹而耶哈特最需要親情的成長期,一手撫養耶哈特,視如己出。如今她重病在身,來日不多,希望能爭取到耶哈特繼承她的姓。可是耿希珥早為兒子規劃了人生的道路:把家道中興的使命強加在兒子身上。至於卜克曼本人,他等不到(借用前引里爾克的措詞)闖入心扉的那「一個影像」,眼看著耶哈特先後拒絕成為媽媽和阿姨的傀儡兒子,一時動心,也寄望耶哈特實現他未了的心願,因此邀他齊心協力為企業烏托邦奮鬥。三個大人殊途同歸,都把對於孩子的期望無限上綱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彷彿孩子是他們的玩偶。但是耶哈特自有主見,認定充分實現自我才是最重要的事,至於社會的成規、養育的恩情、兒子的本分云云,只是「一個瘋子講故事,單字片語充斥,沒什麼意義」。因此,他追尋自己的快樂人生去了,家庭的創傷留待自殘的上一代自行去痊癒。
耶哈特是年輕世代的諾拉。《玩偶家族》呈現女人在父權社會的處境,《約翰‧蓋柏瑞‧卜克曼》呈現孩子在傳統家庭的處境。只就台灣社會來說,傳統所信「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在晚近開始受到質疑,原因不一而足,易卜生刻劃的耶哈特讓我們見識到其中一端。質言之,就是長輩對下一代投射過多主觀的意願,因此產生不切實際的期望,甚至期望孩子有朝一日能滿足長輩的虛榮,和我們在小艾歐夫身上看到的殊無二致。耶哈特毅然甩脫親情禮教的包袱,因此上一代的幽靈不至於殃及下一代猶陰魂不散。在布萊希特的《高加索灰闌記》(1949)把「親情迷思」敷演成氣勢磅礡的劇場史詩之前半個世紀,易卜生先聲奪人闡明親情非關天性。埃臘以歡樂人生取代重責大任,固然提供給耶哈特更寬廣的生命空間,卻在人生的最後關頭要以恩情作為網羅耶哈特的囚牢,其情固然可憫,其行之蠢實不下於耿希珥。兩姊妹都是傳統行為模式的囚徒,執迷之心半斤八兩。耶哈特憑自由意志選擇大他七歲並且遭丈夫遺棄的帆妮‧衛爾屯為寄情的對象,徹底擺脫上一代烏煙瘴氣的家庭泥淖。在沒有愛情基礎的婚姻被視為道德原罪的易卜生劇場,耶哈特出道德原罪的污泥而不染,又一次見證愛的救贖力量。
最後一場戲,卜克曼和埃臘攀登當年定情的觀景台,又見一望無垠的「自由開闊地」在眼前展開,可是鳥瞰全景徒然揭露「被雪給淹沒了」的「人生夢境」。隨後趕到的耿希珥雖然終於領會到爭鬥一場歸徒勞,因而隔著卜克曼的屍體與埃臘握手言和,舞台上深雪枯樹卻引人聯想《復甦》劇中伊瑞妮對魯貝克所說「我們這些死去的人甦醒的時候……看出我們不曾活過」。劇情雖以雙胞胎姊妹的和解收場,她們其實是以共同的愛人為戰場,在他的屍體上收割生命的苦果。兩對久別之後試圖破鏡重圓的情侶都沒能攻頂成功,一如《營造師傅》劇中不顧生命危險攀登塔頂的悲劇,易卜生利用垂直透視景(vertical scenography)—他晚年四劇共通的內在結構—呈現重拾舊情之不可能,斯景斯情如斯人。孟克(Edvard Munch, 1863-1944)的評論可以說是蓋棺論定:「《約翰‧蓋柏瑞‧卜克曼》是北歐藝術最雄渾的冬景。」這句話的內容和說這句話的人一樣重要,因為孟克身為表現主義藝術的先驅,對於景觀的呈現和感情的力道有同樣深刻的洞察力。
卜克曼是礦工的兒子,他所夢想的企業帝國是以採礦為本,說來不足為奇。他抱病冒大風雪登山遠眺,以黑暗王國的精靈為傾訴對象的內心獨白是易卜生劇本中最詩情畫意的段落之一:
我看到鐵礦的礦脈對我伸出曲折、蔓延、招引的手臂。我見過他們在我眼前像活生生的鬼魂—那時候我提著燈站在銀行的保險庫。那時候你們渴望獲得自由。我試過了。可是我力量不足。你們的財寶沉陷深淵。(張開兩臂。)現在夜深萬籟寂,我在這裡跟你們說悄悄話。我愛你們,你們躺在那兒,安安靜靜無聲無息在黑暗深淵中。我愛你們,你們的財富奮力掙扎要出世—我看到你們行進的行列,權力和榮耀閃閃發光—我愛你們,愛你們,愛你們。
可見批評卜克曼無情得要附加但書:此情非彼情。他目中無「人」;只要有利可圖,天底下無不可交易者—包括心愛的女人。易卜生在他生平所寫的最後一部詩劇《培爾‧金特》,以標題人物為十九世紀人的代表,生平事業的高峰就是資本家營建金融帝國的角色,功虧一簣實乃他的性格適應不來那樣的角色。反觀卜克曼,由於「謀殺愛心」這個萬惡不赦的罪行,根本就不夠格扮演那樣的角色。他只是見財路而眼開,看不到人間有溫情,空有理想卻毫無品味,認為自己有權力獨享一套與眾不同的道德標準。他夢想的企業烏托邦根本就是《勃朗德》劇中葛德說的冰雪教堂,裡裡外外都有暴風雪肆虐無已—就像易卜生為本劇設定的舞台佈景。
「只有屈指可數的劇作家像易卜生那樣,顯示對於解放的渴望與夢想、自我的實現、釋放被禁錮的力量—以及人對於自己的渴望與夢想所作的承諾—會在內心產生反作用力,帶來毀滅、失望、冷漠、死亡」(Hageberg 15)。引文正是卜克曼的寫照。他雖然不切實際,甚至不近人情,縱使出身寒微,仍足以勾引出我們的恐懼與憐憫之情:可信易卜生是以古典悲劇的格局呈現卜克曼的命運。判斷劇本是否為經典的一個可靠指標在於是否經得起多種詮釋。「舉例而言,1914年戰爭爆發以前,北歐的製作通常把卜克曼塑造成尼采的姿態,1916年則成了戰時的投機客,三十年代是火柴大王克呂格,四十年代則是希特勒」(Meyer 127)。在令人應接不暇的許多詮釋當中,最膾炙人口的或許是1985年柏格曼(Ingmar Bergman)執導的一場製作。
柏格曼的開場戲呈現卜克曼太太像沒有生命的玩偶動也不動坐在她的沙發上,預示整場演出所彌漫絕望與行屍走肉的麻木感:甚至在對白開始之前,靈魂謀殺就已經發生了。為了表達「劇力萬鈞盡在於高度濃縮的結構」,舞台以極簡而有象徵意味的表現主義佈景凸顯人物關係,呈現雙胞胎姊妹的第一場對手戲如下。埃臘臉色死灰,一聲不響如夢中人影毫無預警出現在敞開的門口,彷彿撐得飽滿而瀕臨爆炸的不祥之兆又一次籠罩卜克曼家族。姊妹間越來越激烈的衝突實質上是靜態的,幾乎沒有動作,連視線交接也只維持最低的限度。那是具有強烈腐蝕性的內在張力,而不是仰賴訴諸感官的自然主義元素。一場爭奪耶哈特的殊死鬥其實是延續多年前爭奪他父親的那一場戰鬥。甚至在帆妮‧衛爾屯太太和耶哈特進場時,卜克曼太太依然僵坐在原位,陷在她唯我獨尊的世界動彈不得。有別於易卜生的背景是以過去的富麗堂皇對比當前落魄的處境,柏格曼要以環境呈現環境中的人物,以內在而主觀的世界為唯一的現/真實,因此改弦更張。畫有戰鬥殘暴景象的一大片背景帷幕,引人聯想博斯(Hironymus Bosch, 1450-1561)暴力充斥而情景扭曲的繪畫,貼切反映卜克曼對自己的看法:在他為勝利而奮鬥的中途,有人在背後耍詐把他擊倒。與此呼應的是本幕的佈景:樓下起居室雖然高度風格化卻有真實感,樓上的房間根本不像適合人居的環境,倒像是監牢(Marker and Marker 209-16)。
就執迷終生至死不悔來說,卜克曼的生命其實無異於監牢。監牢人生雖生猶死,走得出監牢才看得出先前的死亡狀態,才有可能復活甦醒。易卜生花了半個世紀寫多采多姿的覺醒人生,最後以《復甦》作為《玩偶家族》以降總共十二部劇作的「收場戲」。這個標題直譯作「我們這些死人甦醒的時候」。「我們」在劇中指涉的對象有三:上了年紀的雕塑家魯貝克,他年輕貌美的妻子梅雅,他剛出道時的模特兒伊瑞妮。「死人醒過來」則影射復活和甦醒這兩個貫串全劇的字眼,而這兩個字眼,就魯貝克的成名作《復活日》的文義格局而論,根本是二而一。因此,「我們這些死人甦醒的時候」也就是「我們這些死人」的「復活日」。《復甦》就是寫兩個女人與一個男人的「復活日」。
先來看魯貝克的「死亡」。年輕時候,他一心一意要創造一件曠世鉅作,以純潔無瑕的處女悠悠甦醒時的神情呈現基督教復活日的喜悅。作品完成時,模特兒伊瑞妮氣憤魯貝克所流露的「女人工具論」觀點,只是把她當成創作的靈感,而不是把她當作一個女人看待,於是不告而別。又見達芙妮的變形主題:女性為了捍衛身體的自主權,不惜放棄向來熟悉的生命形式,以「眼不見為淨」的策略閃避「女人工具論」的觀點。伊瑞妮的具體作法是自暴自棄,捕捉可以洩憤的獵物。至於魯貝克,他失去伊瑞妮之後,對於人生、人性和復活的概念改變了,因此重新創造他的雕塑,藉以表達他後來體驗到的真實。結果,雕塑的主題不再是復活日使人醒悟「光明與榮耀」的「純潔女人」,而是男男女女「帶有野獸的臉隱藏在人的面具底下」從大地的裂縫蜂擁而出。藉甦醒隱喻復活的人間清純女子這個孤單的形體變成背景人像,前景則多了魯貝克的自畫像,神情「懊悔」,無法掙脫地殼,復活一事可望不可及,只能逗留在他自己一手創造的地獄,永生永世帶罪懊惱。
時過境遷,魯貝克帶著梅雅在溫泉聖地渡假,邂逅已成行屍走肉的伊瑞妮。魯貝克犧牲感情生活,換來功成名就,卻造成伊瑞妮的感情創傷。正如Jrgen Dines Johansen(110)說的,「伊瑞妮試圖彌補魯貝克帶給她的自戀創傷,她的命運就這樣注定了」。他接著一針見血點破伊瑞妮的情慾心理特質:
由於她〔伊瑞妮〕的自戀,別人的慾望只是讓她體驗別人對她的美所流露的讚賞之情。這在她而言並沒有釋放任何(有指涉對象的)慾望。儘管如此,她意在言外指出自己複雜的性關係,迫使兩個丈夫發瘋。然而,性和慾一旦解離,對他方不再有慾望—且不提愛—那麼性可能害人又害己,她則落得精神病(psychosis)的下場,如佛洛伊德所稱的自戀神經症(narcissistic neurosis),依她自己的說法是無法挽回的失落感引起的。接二連三的追求者和情人無法彌補原先的失落和遇人不淑的感覺。對男性慾望的輕蔑和因控制男性慾望而來的自戀滿足感一變而為自卑、行屍走肉和性冷感。(Johansen 111)
如今,雕塑家和模特兒久別重逢,舊情復燃,猶如槁木死灰的人生再現生機。而梅雅,她也遇到一個可以帶給她滿足的男人,一個名叫琅嘉的獵人—獵熊人,但也同樣善於獵捕女人。「然而,」再引Johansen的觀察:
梅雅選擇琅嘉,只用「甦醒」指涉她的人生抉擇,也就是突破婚姻枷鎖。就她而論,「甦醒」意味著從內〔心態〕、外〔婚姻〕雙重限制獲得解放。伊瑞妮把「甦醒」用在不同的意義。對她來說,「甦醒」不是解放,因為即使從精神死亡的狀態復原,人面對鋪天蓋地而來使人粉身碎骨的經驗還是無能為力。因此,就伊瑞妮而論,「甦醒」意味著領悟到荒廢的人生與失落的幸福—並且承認悲慘是自己招來的。錐心蝕骨的洞見是「我們這些死人悠悠甦醒時—發覺自己不曾活過」。劇中使用「復活」,就是等同於前述「甦醒」的第二個意義。(Johansen 118)
把睡眠和死亡劃上等號有其源遠流長的傳統,如傅瑞哲《金枝》論「睡眠時靈魂出竅」(Frazer 198-200)告訴我們的。雖然古老的信仰在現代社會只淪為譬喻修辭,對於精神境界的渴望還是有可能帶來超越的意義。「復活日」這個標題一箭雙鵰,既指明基督教的背景,也影射與基督教信仰不相容的對於不朽的渴望。魯貝克藉甦醒的女人呈現他的不朽之夢,這意味著他心目中的不朽源自大母神信仰對於肉體的崇拜(參見筆者譯注《情慾幽林》20-39)。易卜生提出這樣的質疑:現世必朽的肉體能夠具現生命不朽的信心嗎?伊瑞妮不告而別之後,魯貝克賦予《復活日》新的面貌,他轉向後的風格透露了線索:
復活不再表現為確切不疑,而是表現為不可能。焦慮取代狂喜。魯貝克不再是把現實理想化的藝術家,而是對世間人類的苦難發抒洞識的評論家。純潔的女人這個感情用事的形體起身仰望天國,這是學院派沙龍藝術的一個例子,如今讓位給表現主義式結合人與獸的形體。換句話說,魯貝克已經成為現代藝術家。
魯貝克的雕塑簡直是以西紐雷利的壁畫《肉體復活》(Luca Signorelli, La Resurrezione della Carne, 1499-1502)為範本。兩者都是以「肉體在復活日甦醒」為主題。也看得出相同的情境:人們群聚在地殼外,有的殘廢、容貌似獸,有的是還沒有長出肉的骷髏。Frode Helland提醒我們注意中景地面的女性形體:她站在中央遠處,她的臉偏轉向上承接變容的光,可是雖然如此,她或許「有一點消沉」,就像魯貝克說的。西紐雷利壁畫中距離我們最近的是前景轉頭背對上帝和人類的男子,陷入愁思。造形類似的沉思者也出現在羅丹的青銅雕塑《地獄門》(Rodin, La Porte de lnter, 1880-1917),彷彿在思索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亡魂得不到自由,其中特別跟我們的主題相關的是為了真愛而永遠沉淪的帕歐婁與弗蘭切絲卡。上述作品,包括雕塑、壁畫和劇本,無不是步踵米開朗基羅《甦醒中的奴隸》(Michelangelo, The Awakening Slave, 1532?),把宗教題材應用在現代、世俗的情境。但是米開朗基羅大劈大鑿的半成品斧痕更能看出父權社會的神話創造(mythopoetic)所標榜的陽剛原則,就是琅嘉以斬熊筋類比劈大理石塊時說的,非要讓硬材料甘拜下風才罷手。和獵熊人不一樣的是,藝術家面對的是自己的同類,應運而生的就是沉思的母題。彎腰低頭又僵硬踡跼是呈現憂鬱的標準姿勢,西紐雷利壁畫的前景人像、魯貝克的自畫像和羅丹的《沉思者》(1880-81),都是這樣的姿勢。然而,羅丹的《沉思者》藉肌肉的張力表達思考的密度,呈現的是創造者的形象,魯貝克的自畫像卻比較接近路卡斯(Lacas van Leyden, 1494-1533)畫筆下手臂低垂支撐上半身的懊悔神情,顯然是被罪壓得抬不起頭。按魯貝克自己的說法,他是「因罪孽深重而彎腰低頭……為虛度的生命感到懊悔」。他的說法足以宣判「無慾則剛」這個陽物神話的破產。
魯貝克畫自己在溪邊陷入沉思,想要溝通幾乎臻於神聖化的理想和人形其外而獸性其內的現實經驗是緣木求魚,自哀自憐溢於形表。自哀自憐是自戀的表徵。他和伊瑞妮分手後,他的人際關係萎縮成藏身幕後窺視人性的醜陋藉以尋覓創作的快感,結果就是,和伊瑞妮一樣,他的自戀把自我封閉成一灘感情的死水,無法付出也無法接納,只是不斷地蒸發。魯貝克從此「跟她〔伊瑞妮〕一樣,打心坎裡感受到存在的空虛;他彷彿同時喪失創作才華和性能力。怪不得他汲汲營營要重新體驗年輕時靈感源源不絕的創意以及對於一往情深的女人隱忍不發的性熱望」(Johansen 113)。
往者已矣,如今既已從雖生猶死的狀態甦醒,魯貝克和伊瑞妮相偕實現早年的許諾。於是魯貝克帶著伊瑞妮攀登山巔,去迎接日出,「見識這世間所有的榮耀」。結果遇上雪崩,倒是追求感官的梅雅和琅嘉逃過一劫。又見實現諾言的主題,又是不落俗套的殉情記,而且仍然看到易卜生一貫打破傳統劇情的收煞方式:不尋求文學正義(poetic justice),不依賴妥協化解衝突,徹底泯除善惡二元論的道德觀點。追尋精神價值的情侶逃不過死亡的伺候,同樣情慾出軌而耽溺於感官的梅雅卻得到解脫,「自由得像隻鳥」,顯然違背文學正義的原則,天道寧論?其實不然。在《羅斯莫莊園》,我們已經看到自殺不是用來逃避,而是選擇勇敢面對自己,不過殉情的要義仍落實於基督教信義宗(即路德會)的文義格局之內,多少具有贖罪的意涵。在《復甦》,殉情卻已臻於形而上的層次,劇中體現柏拉圖之愛(Platonic love)的真諦,即美足以激勵人的心智和靈魂專注於精神價值,進而透過愛思索神聖的奧秘。情侶的結合既是彼此滿足對方追尋完整的經驗,同時又是尋求生命圓滿的許諾。
肉體復活本身的意義並不完整;「復活」繼之以「變容」,這才是「過渡到生命與光明」(Jakobsen 75)。按福音書的記載,耶穌先預言自己的受難和死亡,「六天後,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約翰兩兄弟,悄悄上了高山。在他們面前,耶穌的形像變了;他的面貌明亮有如太陽,衣服潔白如光」(〈馬太福音〉17.1-2)。不過,保羅在傳教時,寫信給他在歐洲建立的第一個教會,對於變容有所引申:「我們是天上的公民;我們一心等候我們的救主,就是主耶穌基督從天上降臨。他要運用那使萬有歸服於他的能力,來改變我們這脆弱必死的身體,使我們跟他一樣,有榮耀的身體」(〈腓立比書〉3.20-21)。
復活是起身的動作,變容是在山上發生的,合而言之表達的是「向上朝榮耀與光明」的動作,也就是挪威文的“op”或英文的“up”所表達的意涵。與之呼應的是劇情的發展:第一幕在谷地,第二幕爬上山腰,第三幕登上山巔。在這第三個階段,「魯貝克和伊瑞妮又一次見到榮耀和變容。我們就這樣從樂園似的情境,途經世間的墮落與人生,最後回到樂園」(Jakobsen 73)。回想當初在創作時,雕塑家與模特兒的神聖經驗,一如伊甸園的情況,曾面臨情慾衝動的威脅,伊瑞妮這個化身為「純潔女人」的模特兒和魯貝克雙雙感受到慾望蠢蠢欲動。然而,正如Frode Helland以易卜生早年在義大利從古典雕塑領悟希臘悲劇精神的經驗,比較奧維德所述皮梅林的神話和《復甦》,指出「魯貝克和皮梅林一樣,喜愛雕像甚於喜愛真正的女人」,雖然一個使雕像成為女人,另一個使女人成為雕像,這兩位雕塑家在Helland看來一樣自戀,談不上創造,而只是在複製自身的經驗。自戀心態是真情摯愛的大殺手,「控制慾是這種虛情假愛的一個重要成分」。怪不得在伊瑞妮所幻想迎向日出的情景中,她和魯貝克竟然以類似《營造師傅》劇中希珥德和索爾尼斯那種仰慕者與藝術大師的關係出現。鑒於《復甦》豐富的《新約》典故,我們很難不去聯想易卜生有意以魯貝克和伊瑞妮類比教主和追隨者的關係—這裡說的「教主」當然是指耶穌。拉斐爾的《基督變容》(Raphael, La Transfiguration du Christ, 1519-20)圖中,跟主題人物同樣凸出的就是清純女子無視於人群訝異的跪姿。
雪崩就發生在他們穿越濃霧要「直上在黎明中亮閃閃的最高峰」的時候。雖然濃霧險阻,「迎向日出」仍然有光明的許諾在焉。從兩性關係的角度觀照「日出」這個喻象,我們赫然發覺《營造師傅》的老師傅是在「追隨」青春女郎潛意識的情慾幻想時看到日出,《復甦》卻是模特兒在「仰望」藝術大師的想像眼界時看到日出。情境雖然有別,卻雙雙指出歧路燈的所在—在兩性世界,顧盼不足以自雄,倒是想要超脫現實的託寓衝動(allegorical impluse)足以帶來「致命的誘惑」。
3. 結語
易卜生的革命事業,一言以蔽之,在於他「挑戰了劇場功能最基本的假定—他的作品沒有創造一個社群,而是造成社群的分裂」(Williams 171)。在亞瑟‧米勒看來,易卜生「具體展現希臘悲劇的精神,特別是希臘悲劇所呈現因擺脫不了以往的過失而造成當前的禍殃」(Miller 1994: 229)。過去的經驗就是個體的歷史,人物因歷史而有深度。可以這麼說:易卜生個人的成就濃縮了雅典悲劇三雄所鋪陳的戲劇景觀。一如埃斯庫羅斯使得酒神祭典所用的戲詞具備文學的價值,易卜生使得中產階級社會的生活語言成為戲劇文學的表達媒介。又如索福克里斯讓我們體會到人生困境與人性光輝的辯證關係,易卜生呈現個體在當代社會奮力要梳理生命的意義。而且,不讓尤瑞匹底斯筆下的女性心理啟示錄專美於前,易卜生披露了唯有捐棄性別成見始足以領略的人性之謎,特別是女性之謎。
人性之謎可以有其美感,這也是莎士比亞傳奇劇令人著迷之處。不同的是,莎士比亞高舉明鏡照自然,鏡面反映人性的五光十色,易卜生卻是高舉明燈照人群,燈前曝露人格的隱密世界。蕭伯納說「易卜生填補了莎士比亞留下的空白。他給我們的不是我們自己,而是我們處在我們自己的情境」(Wisenthal 218)。易卜生劇場化舞台為論壇,不是要娛樂觀眾,而是要激發讀者/觀眾的想像,演員尤其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他置換傳統賴以區分性別特徵的人格特質,而且由於劇情不再循線性邏輯發展,演員必須體現卡珊卓的眼界,呈現過去、現在與未來三合一的立體經驗。就此而論,易卜生在創作路線上的進展不啻是預告契訶夫式書寫人生困境的自然主義將取代史特林堡在《茱莉小姐》所推到極致的那種強調環境與遺傳的舊式自然主義。
不妨以具體的例子說明易卜生的新猷。易卜生在世時所受到最無情的批評倒不在於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而是他中期的劇作,從《野鴨》到《海妲‧蓋柏樂》,被視為費解,甚至說是他故作神秘。他有意識地從日常生活瑣碎的現實經驗探討潛意識的行為動機,並且展現他過人的洞察力。尤其是他把「不確定原理」引入戲劇,此舉為戲劇技巧帶來根本的大變革,使得契訶夫得以精益求精,深入探索對白的潛文本。一葉可以知秋者如《海妲‧蓋柏樂》劇中海妲一出場就惹出的帽子事件和緊接著神來一筆的拖鞋事件,這畢竟只是茶壺裡的風波。《羅斯莫莊園》最後一場戲,羅斯莫和瑞蓓卡一直在摸索真正的動機:就是因為不可能通透明白對方的愛是純潔的,羅斯莫和瑞蓓卡只有心甘情願為愛而死才能確認彼此的摯愛。在另一方面,這兩位主角之所以相偕殉情,有可能是由於體認到自己面臨無法突破的社會規範,也無法伸張根本的自由。這麼說來,這一場戲就是跟存在有關的悲劇。相對而言,莎士比亞筆下的殉情,不論是懵懂少年陰差陽錯的憾事如《羅密歐與茱麗葉》,或是成熟男女感天動地的癡情如《安東尼與克琉珮翠》(Antony and Cleopatra),線索無不清晰可解,如此稜角分明的現象卻不是我們所熟悉的人生。易卜生在1880年代下半葉以後的作品告訴我們事有不然,並且刺激我們去思索何以然。
何以然?一個可能的答案是,易卜生不像莎士比亞劇場那樣提供我們素所熟悉的觀點,而是新開一扇窗,窗外展現我們稍一失神就錯過的景觀視野。隨著散文劇越寫越成熟,他的劇本越到晚期越深邃、越精煉也越像小說,此一發展脈絡就反映在他的舞台佈景。他從呈現浪漫素材的室外景抽身,轉向室內景呈現寫實的議題,最後突破牆壁的樊籬並賦予遠比早期作品更豐富的象徵意義。早有論者指出,易卜生劇場的「室內景是內在生命的圖像,是想像的領域」(Aarseth 26),也就是歐尼爾寫《長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 Journey into Night, 1940完成,1956首演)總結自己的一生所展現的藝術造境。易卜生開啟走進劇場探討社會人的傳統,卻折向內在的空間領域,特別是女性的生命空間。就展現女性的生命空間而論,他的戲劇造詣把尤瑞匹底斯所開創對於女性心理的關懷往新的疆界大幅拓展,跨越了現代主義的門檻。早在《勃朗德》,我們就在阿葛妮絲看到女性憑其纖細的感受所展現的直觀洞識,她是易卜生筆下在父權社會捅蜂窩的女角原型。然而,正如Joan Templeton的《易卜生的女人》指出的,這些女性人物都在從事自我認同的戰爭,她們的生活與角色受到太多包袱的掣肘,總是被禁錮在家庭倫常、品德甚至情慾的牢網,使得她們探索自我實現的過程難以為繼。尤有進者,易卜生的社會寫實散文劇創作期正值歐洲婦女解放運動風起雲湧的年代,他看出根本沒有所謂的「婦女問題」;問題出在父權體制之下女性的社會地位,其核心議題應當是兩性關係的重新界定。「易卜生不以性別二元論區分人類,這使得他成為Gissing所稱『性別無政府狀態』(“sexual anarchy”)的先驅……。什麼是『他的』以及什麼是『她的』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末年再度張牙舞爪,這使得易卜生又拔頭籌,不只是在現代主義,而且也在後現代主義成為開路先鋒」(Templeton 329)。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歐洲文化有一道既深且廣的裂痕,在光明的一側展現政治與知識大解放的光輝,在黑暗的一面籠罩帝國主義與殖民事業的陰影。易卜生一以貫之的創作目標在於解放社會大眾的想像,使他們對於自我有個比較適當的觀念。要從自欺欺人的觀念獲得解放,首先得探索經歷時間洪流的沖刷而殘存下來的觀念。現在的自我就是那些殘存的觀念造就的,也就是帶來衝突而且使我們不得自由的那些勢力與權力。衝突在莎士比亞看來是毀滅的因子,在易卜生看來卻是自我調適的契機。自從散文劇創作之初,他為當代挪威甚至整個歐洲揭櫫社會良知的用心昭然若揭。《愛情喜劇》的天娥空有才情卻困在繭中,浪漫英雄如勞鷹只能遠走高飛。接著《勃朗德》闡明意志有賴柔情加以調劑。從《社會棟樑》開始,易卜生火力全開,點明真實與自由是社會賴以奠定永固根基的兩大支柱,《玩偶家族》毫不留情批判父權體制賴以維繫和諧表象的性別成見與偏見,《幽靈》進一步指出對那樣的成見與偏見採取妥協所可能產生的後果。可是在《全民公敵》,堅持專業良知竟得付出與社會為敵的代價,易卜生對於前述立心立命的創作使命開始有了疑慮。接著《野鴨》揭露師心自用的理想主義者以使命感為幌子遂逞私怨的假道學嘴臉。易卜生看似不再衝鋒陷陣,其實他只是改了番號,降下吉訶德式理想的大纛,轉而思索人性之謎。他看出解放之道首在人心;人心不改,那麼社會與體制的改造只不過是口水戰爭與文字遊戲。
在易卜生的劇本中,隨真實的人生與藝術而呈現的是無法一言而決的新觀念,不只是挑戰既有的演出風格,更是質疑傳統的觀念與文化。Archer所稱的這些「新戲劇」為當時歐洲文化界和文藝界領袖群倫的人物表達出共同的心聲,其讀者與觀眾集合了知識階層具備高度批判意識而且通常叛逆成性的人士。歐洲在1880年代普遍接納易卜生獨立開創的新戲劇的同時,也為莎士比亞和哈辛(Jean Racine, 1639-1699)所繼承進而發揚光大的悲劇傳統發出訃聞。在傳統的悲劇,錯誤無從彌補,易卜生的劇本卻讓我們看到有人重新審視自己的所作所為,進而採取解放的行動以彌補過去所犯的錯誤。他在戲劇的領域「發明一種語言,接著還必須教導他的讀者如何使用那種語言」(Steiner 293)。這一篇長序和各劇本的譯注應該有助於中文讀者熟悉那一種語言。
易卜生寫十九世紀的挪威人發生在挪威的事,卻能超越地理隔閡、年代差異與文化鴻溝而產生普世的價值,成為人類文明共同的遺產,那是因為他以挪威背景為戲劇眼界的隱喻空間,所思、所寫、所呈現無不是世間普遍看到的人性與人類普遍遭遇的困境。挪威是北歐精靈充斥的世界。在哈洛‧卜倫看來,「易卜生的精髓就是北歐精靈。不管北歐精靈在挪威的民俗傳說裡有什麼意涵,易卜生的北歐精靈是他自身原創性的象徵,是他自身精神的印記。」他的戲劇心理學就是以北歐精靈的意象為中心。在他筆下,北歐精靈的特性是有關人類心靈圖像的問題,晚期劇作尤其如此。那些作品雖具備寫實主義的外觀,「骨子裡卻是極盡魔幻詭奇之能事」(Bloom 520-21)。從這一套戲劇集可以欣賞到現代戲劇之父獨立開創的劇場景觀如何「極盡魔幻詭奇之能事」,並且「重新發現」在日常經驗中從自己的眼角指縫一閃而過的許多浮光掠影竟也潛藏既豐富又深刻的意義。經得起逐字推敲逐字琢磨的散文劇創作並不多見,易卜生的劇本是其一,因此我很樂意把這套劇集獻給雅好經典閱讀的有心人。
2. 成就戲劇宗師的革命志業(五之五)
易卜生最後四部劇本有個共通的題材:雄心萬丈的男人夾在生命情態殊異的兩個女人之間。由此引出一個共通的主題:男人把女性的慾望工具化,依自己的需要決定用或不用。工具化的結果是女人在感情的領域處境堪憐。有人檢討十九世紀自殺的主題所呈現的女性特質,指出女性自殺的故事傳統上集中在情場失意與貞操被奪這兩個主題,吻合女人為愛而活,男人卻為自己而活(Higonnet 103-18)。這樣的觀察在《小艾歐夫》特能引起共鳴,不只因為該劇是易卜生劇場情慾意涵最濃烈的作品,也因為劇中呈現易卜生散...
目錄
易卜生戲劇年表
附錄:易卜生專屬網站
現代戲劇的羅馬:易卜生小論
發動一人革命的戲劇宗師
成就戲劇宗師的革命志業(五之五)
劇本
小艾歐夫Little Eyolf(1894)
約翰‧蓋柏瑞‧卜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1896)
復甦When We Dead Awaken(1899)
易卜生戲劇年表
附錄:易卜生專屬網站
現代戲劇的羅馬:易卜生小論
發動一人革命的戲劇宗師
成就戲劇宗師的革命志業(五之五)
劇本
小艾歐夫Little Eyolf(1894)
約翰‧蓋柏瑞‧卜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1896)
復甦When We Dead Awaken(1899)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5收藏
5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



 5收藏
5收藏

 6二手徵求有驚喜
6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