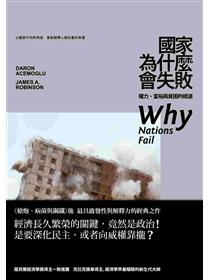☆ 南方朔/專文導讀。
☆ 改編為電影作品,預定2014年於法國上映。
☆ 唐德里羅繼《白噪音》之後,最迷惑人心的死亡之書!
☆ 英國《衛報》將《身體藝術家》與《等待果陀》作者、後現代主義大師貝克特的作品並列!
丈夫舉槍自盡之後,
她卻找到了他仍活著的證據……
美國當代文學巨匠 唐.德里羅
繼《白噪音》之後,最迷惑人心的死亡之書
原著改編搬上大銀幕,即將上映!
★ 南方朔/專文導讀
他們新婚不久,丈夫六十多歲,是過氣的藝術片導演。她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三十多歲,是身體藝術家。
某天早晨,兩人邊吃早餐邊聊天,氣氛並不融洽。妻子提到房子裡似乎有怪聲,彷彿有第三者潛伏在不知名的角落。而後來丈夫說要出去晃晃,沒想到,他卻是驅車去了第一任妻子位於曼哈頓的公寓,在那裡舉槍自盡。
葬禮過後,當妻子獨自回到海邊的住所,卻發現屋裡真的有個「第三者」。這個男人能說出她丈夫說過的話,也能說出她和丈夫生前的對話,字字句句相同,就連抑揚頓挫都一模一樣……他,到底是誰?
《身體藝術家》是唐.德里羅繼《白噪音》之後,最引爆話題的死亡之書。故事由一場死亡早餐展開,自溺於苦行生活與妄想世界的未亡人,從天而降的神祕男子,以及兩人之間充滿玄機的對話,揭示了生活中由零碎瑣事所構成的脆弱秩序。故事主角讓人聯想到「行為藝術教母」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其個人與空間、時間的關係,賦予了小說哲學上的興味,《衛報》亦將《身體藝術家》與後現代主義大師貝克特的作品相提並論。此書更被視為唐.德里羅獻給二十一世紀最炫迷前衛之作。
作者簡介:
唐.德里羅(Don DeLillo)
美國四大名家之一,多次獲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且呼聲極高。他也是「美國藝術與文學科學院」院士,迄今已出版十餘本長篇小說和三本劇作,另著有諸多短篇小說和隨筆。有評論因他對後現代生存境遇的描繪,而稱他是「另一種類型的巴爾扎克」。
唐.德里羅於1936年出生在紐約一個義大利移民家庭,童年時隨父母遷居賓州。大學時期學習神學、哲學和歷史,但他並不喜歡學校生活,倒是從現代派繪畫、爵士樂、歐洲電影和格林威治村的先鋒藝術獲得樂趣和教益。1958年大學畢業後,唐.德里羅就職於一家廣告代理公司,並在業餘時間從事文學創作。
他的小說先後獲得「哥根哈姆獎」、「美國藝術與文學科學院文學獎」。1985年出版的《白噪音》,是他奠定文壇地位的重要作品。此書不但摘下該年度的「美國國家圖書獎」,入選「時代雜誌100大小說」,更被譽為美國後現代主義文學最具經典性的代表作。學者馬克.奧斯蒂恩稱譽此書為「美國死亡之書」。
1989年,唐.德里羅突發奇想要寫何梅尼,1992年,他便以這部名為《毛二世》的小說榮獲「國際筆會/福克納獎」。而後在1997年,他出版一部八百多頁的巨著《地獄》,描繪了二十世紀整整後半個世紀的美國社會,對美國和世界文壇産生了巨大的震撼。這部作品不同於其他議題嚴肅的小說,很意外地,成了國際第一暢銷書。
唐.德里羅的作品所造成的影響力是全面性的,不僅大學課堂講授他的《白噪音》,當今許多美國名家以他為師,流行歌手寫歌稱頌他,保羅.奧斯特更將《巨獸》及《沒落之鄉》獻給他以表崇敬之意,而英國文學大師馬丁.艾米斯則推崇他是「美國當代最偉大的作家」。他的著作已跨越了時間與地域的藩籬,在數十年來,始終緊貼著現代人的生活脈動且影響了無數讀者;而唐.德里羅這個名字,亦將會永遠屹立在世界文學史的不朽地位。
譯者簡介:
梁永安
台灣大學哲學碩士,譯有《毛二世》、《大都會》、《如此燦爛,這個城市》、《此刻──柯慈與保羅.奧斯特書信集》等。
章節試閱
她坐在電腦螢幕前觀看。有什麼力量驅策她這樣做,而這力量真實得足以讓她在畫面毫無動靜時繼續堅持。現在是科特卡的凌晨三點,而她等著一輛車子出現——但不是想知道車裡坐了些什麼人。吸引她的只是科特卡這個事實本身。它被裝在一個不為所動的框架裡,在妳看著它的時候是個如其所是的事實。妳邊看著它邊注意螢幕角落那個顯示當地時間的數字鐘。科特卡是另一個世界,但它卻活生生地擺在眼前,讓妳可以看得到它此時、此分、此秒的真實模樣。
她想像有誰也許會一面看著一輛汽車午夜出現在科特卡入城公路的網路畫面,一面手淫。這個思緒讓她失笑。她自己劈柴。她每天總要騰出時間看科特卡的網路直播畫面。她不知道提供這影音串流直播的人用意何在,但把它當成一種隨機的行為藝術。死寂鐘點最是讓人受用。因為那可以清空她的心靈,讓她感受到其他地方的深深寂靜。看著一個剝去一切而只剩下兩線車道的地點讓人覺得玄之又玄。那兩線車道一條進城、一條出城,「進」與「出」這兩個真實同時發生,而數字鐘的數字變動則讓人感受到一種奇怪和空洞的緊迫感。她看著秒鐘逐漸累積成為分鐘,分鐘逐漸累積成為小時,等著一輛疾馳的汽車出現。
她的作家朋友瑪麗拉從紐約打來電話。
「妳還好吧?」
「妳認為我應該怎樣回答?」
「我不知道。但妳不孤單嗎?」
「每個人都是孤單的。但我的感覺不同,要另一個字眼才能形容。」
「我說不準,但難道妳不認為妳有讓自己更好過的方法。」
「妳應該找別人談這類話題,我不在行。」
「別把自己隔離開來。妳現在需要的是生活在熟悉的人事物中間。孤單對妳沒有好處。我知道妳對他的死是什麼感覺,知道那有多麼摧折心肝,唉。但妳不應該龜縮起來的。我知道妳鐵了心。但妳必須想辦法走出來而不是陷進去。別龜縮起來。」
「妳正在做什麼?」
「吃東西。看著窗外。跟妳講電話。」瑪麗拉說。
「妳吃什麼?」
「胡蘿蔔切條。」
「那不叫吃東西。」
「我知道。我要瘦身。『電影論壇』正在播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妳對他的了解沒那麼久遠。看一看可以增加妳的認識。」
她在早上聽到那怪聲,其神祕色彩就像她第一次聽見的時候一樣鮮明。大約三個月前頭一次聽到這種怪聲之後,她和雷伊一起上樓查看。雷伊聲稱怪聲是一隻被困在屋子某處的松鼠或浣熊引起的。但她卻認為這聲音帶有鬼祟味道,具有某種可量度的性質,不可能是動物引起。它讓人有一種近乎可感應的感覺,就像有什麼東西正在以我們呼吸的方式呼吸,以我們移動的方式移動。就像是發自一個脫落了空間的身體。不過他們找遍每個角落都一無所獲。
這一次她是在廚房聽到那聲音。她拿著一杯茶上樓查看。位於二樓走廊尾端的幾間房間都沒有異樣。三樓一片幽暗,燈泡全壞了,大部分家具皆已搬走。接著她爬上通往屋頂塔樓的短樓梯。她先是探頭到塔樓裡左看右看,只見裡面的空間相當寬敞,堆滿雜物。等她整個人站在塔樓地板之時,手上的茶已冷掉。她戳了戳厚紙皮箱裡疊成一層層的衣物,又翻了翻皮革文件夾裡的發脆文件。塔樓裡還有一隻貓頭鷹標本和一疊沒裝框的水彩畫。那些水彩畫已經皺捲得厲害。她看見一片樹葉就在窗外旋轉。那是一片琥珀色小樹葉,其更上方有一根跨過屋頂的樹枝。但沒有跡象顯示,樹葉是靠著什麼幼蟲所吐的絲或小鳥的築巢物質而吊掛在樹枝下面。它只是懸浮在半空,兀自打轉。
第二天,她在位於三樓走廊末端那間大房間更裡面的小房間發現了他。他個子細小,骨肉勻稱,讓她起初還以為他是個小孩。他一頭黃棕色頭髮,睡眼惺忪,看似剛從深睡中醒來,或是剛從麻醉狀態醒來。
他坐在床緣,只穿著內衣褲。在頭幾秒鐘,她認為這個相遇乃是無可避免的。她回溯了從最初有跡象顯示這屋子裡另有別人到此刻她發現他的整個過程,只覺得她的每個直覺分毫不差,全都獲得了印證。
※
她看著他。
「告訴我,你躲在這屋子多久了?」
他沒抬頭。他身上散透著一種怪異感,讓她聽到自己說的話在房間裡迴盪,顯得可以預測而了無新意。她沒有害怕的感覺。他有一種棄嬰的味道(一個被丟棄又被別人撿到的棄嬰),而撿到他的那個人(她猜)就是她。
「你一直在這裡。」她說,每說一個字便停頓一下,把話說得清晰分明。
他看著她。光是這個微微抬頭和仰起下巴和眼睛的動作,便讓他像是發生了什麼變化似的,顯得年紀要比原先大上一些。除了年紀變大一些,他還變得微微潮溼,額頭和兩頰泛著汗光。
他說了些什麼。
「什麼?」她問。
他穿的是一條四角內褲和一件嫌太大的T恤。她毫不掩飾地上上下下打量他身上每一處。
「難以清楚。」他說。
「但你為什麼會在這裡?你來很久了嗎?」
他垂下頭,看似是在思考,琢磨這複雜問題的每個細節。
他倆站在屋外草坡的最高處,眺望一艘在白浪中起起伏伏的捕龍蝦船。先前她端了些隔夜湯和麵包給他吃。麵包有些烤過,有些沒烤過。你得把烤麵包機按下去兩次才能把麵包烤得恰到好處。
「你看見些什麼?」她問,向著龍蝦船和愈來愈逼近的烏雲比了比手勢。
「有些樹木。」他說。
「它們隨風搖曳。那些是樺樹,白色的那些。又稱為紙皮樺。」
「白色的那些。」
「對,白色的那些。但除了樹以外呢?」
「除了樹以外呢。」
「看看樹林上方。」她說。
他觀望了一會兒。
「下過很大的雨。」
「還沒下雨。是即將要下雨。」她說。
他穿著風衣和工人褲,看來不喜歡站在戶外。她想方設法打聽他的事。她發現自己受到他的難以捉摸所吸引,也對他那種猶猶豫豫的說話和舉手投足方式發生了興趣。另外,他對於自己可能會被抓去警察局看似毫不擔心。她猜想,他的這種不擔心不是因為無所謂,而是因為缺乏想得更遠的能力,以致無法得知潛入別人家裡而又被發現的嚴重後果。但她不確定他知道潛入別人家裡是犯法行為。
風變得更大了,他們轉身往回走。她打趣地想,他是來自網路空間的,是來自她的電腦螢幕。他是來自芬蘭的科特卡。
她說:「不是下過雨,而是『將要』下雨。」
不管是在室內還是室外,他的行動方式都很彆扭,彷彿空間對他而言是變形扭曲的。她看著他側身走進大門,步伐有一點點拖泥帶水。他也許是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便會飄起來。她忍不住不停地觀察他。
總是「看似」。他看似這樣,他看似那樣。她需要另找一個基準點才能把他定位。
*
他們坐在那間牆壁鑲木板的房間裡。這房間給人一種森嚴的感覺,牆上掛著一些帆船圖畫。電話響了又響。他看著壁爐裡的焦木柴(昨晚燒剩的),而她則看著他。矮書架上的書大都是你會在租賃屋找到的夏天讀物,都是一些恰如其分的讀物:褪色封面上畫著另一個夏天的另一棟租賃屋的那些。不然就是曆書或地圖集。一線陽光停落在書脊較高的書籍頂端。
他的下巴淺得厲害,讓他的臉有一種不完整的感覺。他的頭髮硬邦邦而糾結,這裡那裡凸起著一叢。
她必須全神貫注才能看清他這些外貌特徵。她把他看了又看。他的面貌有什麼不可捉摸之處,似乎每一刻都在變化,每一刻都變得稀薄些。
她低聲說:「對我說話吧。」
他交疊著雙腿,坐姿彆扭,半截褲管被扯起,露出小腿。她因此看見,他在襪口處綁了一圈線繩,以防止襪口滑落。這讓她聯想起某個人。
「對我說話吧。我在說話。」他說。
她認為她懂他的意思。他的聲音裡毫無疑問有種洩氣的味道,暗示著他不管說多少話都無法輕易把事情說清楚。就連他的手勢看來也是費了一番大氣力才比出來。她知道她本應打電話給醫院、療養院和精神治療機構,問問它們是不是有病人失蹤。
雨水疏疏落落拍打著窗戶,輕聲而可數算。但雨勢繼而轉大,變得無所不在,不斷敲擊日光室的頂棚,並且把落水管灌滿。他們繼續坐著,聆聽雨聲。
「你叫什麼名字?」她問。
他望著她,不發一語。
「我來這裡是想要獨處,」她說,「這對我很重要。我願意等。我會給你機會告訴我你是誰。但我不想有別人在我的房子裡,我會給你機會,但不會無了期地等下去。」
她不想表現得像是出言警告,但卻大概不成功。她本來可以打電話給距離最近(一點都不近)的一家收容中心,又或是打電話給鎮上的教堂或小月島上那家缺了尖塔的教堂。如果一切都不管用,她本來還可以祭出最後手段:報警。
「我待在這裡是因為雷伊,他是我丈夫,他死了。我不曉得為什麼要告訴你,因為這明顯是多餘的。但我有需要一個人在這裡住一陣子。只要告訴我你懂不懂我的意思便行。」
他晃動一隻手,像是說她無須再多說。他顯然懂她的意思。但又也許並不懂。
風在怒號,他們坐著聆聽風聲。雨聲鋪天蓋地,他們無法不聆聽。她也可以選擇打電話給房仲,投訴有人闖入她家中。這是另一個她可採取的手段。
雖然早上才過一半,但她卻感覺他倆已經共處了一星期。他們坐著,望著昨晚燒剩的焦木柴。
然後她驚覺眼前這男人讓她聯想到誰。
是他高中的自然科老師。在不確定的光線中,這老師看似有一頭淡色頭髮,但更強烈的日光會顯示他是個禿頭。他講話的速度無比慢吞吞,讓少數有同情心的學生為他感到臉紅,又讓不耐煩的學生(即所有其他學生)公然表示不耐煩。有一次,這老師用隱形膠帶貼住皮鞋上一條裂縫。
既然有那麼多相似之處,她決定用老師的名字來稱呼眼前的不速之客。烏貴先生。她認為此舉可以讓她更容易把他看清楚。
她低聲說:「告訴我些什麼吧。」
他把雙腿分開,兩手各按著一邊膝蓋,樣子像個坐在紅色扶手椅裡的木頭人。然後,他把頭轉向她。
「我知道有多麼的。」他說,「我知道這房子有多麼的。靠在大海孤孤單單。」
他的樣子不能說是高興,但至少是感到滿意:對於自己能夠把最後幾個單字串在一起感到滿意。事實上,她在烏貴先生這句不成句的句子裡聽出深深的弦外之音。一共才四個單字,但它卻能夠道出她的弔詭處境,道出她同時身在「裡面」和「外面」的事實。「孤孤單單」一語既可以是形容她,也可以是形容這房子,而「大海」一詞則既加強了孤獨之感又暗示著強烈的解放,暗示著「大海」可以讓人從被書牆禁錮的自我中逃出來。
她知道這樣細細分析是愚蠢的。事情只是她捏造出來。但他的語焉不詳確實讓她產生一種感覺:一如月亮有許多月相,一個單字也可以有許多方方面面,值得細細玩味。
她說:「我喜歡這房子。對,我想要待在這裡。但它只是租來的。我將會在這裡再待六或七個星期。也許更短。它是我們租來的。租期只剩五、六個星期。也許更短。」
此時她沒有看著他。她看著的是雙手的手背,邊看邊思索,回憶起她與雷伊共處的一些片刻(不,不是片刻而是時光,或說是由片刻匯流成的組合時光),回憶起一些色瞇瞇的睇視和撫觸。她用五指緊扣另一隻手的五指,瞪著被緊握得失去血色的指關節。她在身體裡懷念著他,感受到性的孤單和無底的孤單。
他說:「但妳沒有離開。」
她望著他。
「我將會離開。幾星期後會離開。租約滿了便離開。可能更早。我將會離開。」她說。
「但妳從不離開。」
這種從過去時態向現在時態的轉換似乎意味著他克服了些什麼,克服了一個障礙或約束之類的。他必須延伸自己才能走出這障礙。另外她也從他的聲音裡聽出些什麼。她不確定是什麼,但隱隱覺得不安,便站起來,走到窗前。
她坐在電腦螢幕前觀看。有什麼力量驅策她這樣做,而這力量真實得足以讓她在畫面毫無動靜時繼續堅持。現在是科特卡的凌晨三點,而她等著一輛車子出現——但不是想知道車裡坐了些什麼人。吸引她的只是科特卡這個事實本身。它被裝在一個不為所動的框架裡,在妳看著它的時候是個如其所是的事實。妳邊看著它邊注意螢幕角落那個顯示當地時間的數字鐘。科特卡是另一個世界,但它卻活生生地擺在眼前,讓妳可以看得到它此時、此分、此秒的真實模樣。
她想像有誰也許會一面看著一輛汽車午夜出現在科特卡入城公路的網路畫面,一面手淫。這個思緒讓她...
推薦序
【導讀】 找回感情的重量! /南方朔
著作等身的美國後現代主義大師唐.德里羅(Don DeLillo),每次一出手,全球文學界都必然注意傾聽。他以前著作都卷帙宏大,前幾年出的《陰間冥府》(Underworld)原文即厚達八二七頁。而這次他又出手,卻是部超短的中篇作品。《身體藝術家》(The Body Artist),只有一二四頁,篇幅雖短,受到的注意並沒有減少。
近代文學從一九七○到八○年代起,由於知識理論的改變,而進入了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階段。
文學後現代主義有許多特性,最大的特性之一,乃是由於知識理論改變,人們對事務的辯證正反關係有了更深的理解,並能考掘出隱藏在縫隙間失去的意義。因此,所謂的後現代作品遂著重在大型的反論述上,唐.德里羅就是其中的翹楚。他總是以各種大長篇對既定的事務提出反論,並將它的單一價值推到極限,使它的悖論無所隱藏。正因為他是要對歷史和現實提出大的反論述,所以他對重要課題都必須去做專業學者也未必會有的鑽研。例如他在《白噪音》裡,必須對恐懼問題做出百科全書式哲學和神話人類學研究;在《天秤座》裡,必須對甘迺迪總統遇刺案,去做深入的探討與聯想;在《陰間冥府》裡,必須對當代文明深入反思;在《毛二世》裡,要對權威人格及恐怖主義深入探索。這也是他的每部作品都必須極為龐大的原因。蓋只有如此,始能對歷史和現世的公眾事務做出大型的反論。
而這本新的中篇作品《身體藝術家》,卻和他以前的作品完全不同。這部作品的特色是:
(一)他以前的作品都是談論歷史和現世的集體公共事務,這部作品則是在談論純粹的私人事務。
(二)由於它談的是私人事務,因此整部作品遂相當於是個人的獨白,而沒有公共事務的重量。
(三)由於全書沒有甚麼情節,只是在談兩人記憶中的對話,悼亡的情愫,對話的斷斷續續,隨意的聯想,以及語言的飄飄浮浮,整個對話時語言和細微動作的不確定性,這些細節遂交織成彷彿有如美文般的敘述,美麗的敘述在跳躍,找不到客觀的參考架構。它可以被領會,但不能被覆述,整部作品我反反覆覆的讀了許多次,但也無法說出它究竟是要傳達甚麼確切的訊息,因此,《身體藝術家》這部中篇作品,不能理解為是人們習慣了的小說,只能看成是感情、聯想、語言的飄移故事。它沒有重量,只有飄移。
《身體藝術家》雖然沒有清楚的敘事,但這並不妨礙它那朦朧的人物框架。
雷伊.羅貝爾斯(Rey Robles)是個西班牙裔,在西班牙獨裁統治時,被送至俄國避難,後來輾轉到巴黎,最後落腳紐約,拍攝過得獎的電影,後來風光不再。他一生三娶,第三任妻子是身體藝術家羅蘭.哈特基(Lauren Hartke)。他後來飲彈自殺,得年六十四歲,羅蘭.哈特基則為三十六歲。
在雷伊.羅貝爾斯死後,整個敘述就從他們最後的早餐開始,人的親密生活中那種瑣碎,任意聯想,語言跳躍不定的本質展現無遺。
在第一章敘述之後,經過簡單的過場交代,於是進入了本書的核心,它就是當一個人的配偶死了,他如何去面對那有如精神廢墟的日子?他和她生活過的房屋與空間會留下甚麼樣的記憶碎片?當她在舊屋中輾轉雜思時,出現了一個疑似精神病患的「烏貴先生」(Mr. Tuttle),那是個彷彿已死的他所變成的幽靈,那是個甚至連時態都很混淆的虛擬世界。而她是個身體藝術家,身體藝術是個藉著肢體的主觀象徵動作,去做無聲表達的行為模式,它更加迷離難解。於是,《身體藝術家》整部中篇作品,就彷彿是本文詞優美的獨白和與幽靈的對話,它完全處於一種失重的狀態。它似乎是企圖去問一個可能難解或無解的形而上困惑:我們的人生經過了千山萬水,當他死後,我還是甚麼?我的記憶又是甚麼?
我們閱讀世界,閱讀人生,或者閱讀作品,都希望它有一點重量,明顯的重量才會產生意義,使人們不致於惶惑不安,也跟著處於一種失重的狀態下。《身體藝術家》之所以使人覺得它沒有重量,乃是它的敘述飄浮不平,對所有的私人親密行為都不聚焦,只是語言文詞在閃爍,因而她對他雖有懸念,卻使得懸念沉入進了虛空。但隔著敘述的深化,唐.德里羅最後還是逐漸找回了它失去的重量。她驚覺到自己的心不在焉,有了這樣的提問:
「為什麼不沉下去呢?讓死亡把妳拉倒,讓死亡支配一切吧。
為什麼不讓妳摯愛親人之死把妳帶進淒慘的崩解呢?妳總是不懂得怎樣去愛妳的摯愛親人,直至眼睜睜看著他們戛然消失。然後妳明白了他們的痛苦離妳其實只有咫尺之遙,明白了妳是多麼吝於付出自我,難得有心靈不設防的時候,總是計較著施與受的平衡。」
我自己認為,這幾句話可能就是唐.德里羅在想的要點。本書從追憶最後的早餐起,就顯示出兩人對話的飄浮,那是感情上心不在焉的躲躲閃閃。感情的心不在焉,它本身就造成了一個充滿了詭異氣氛的交流世界,當他們計較,就會在瑣碎的事務上飄來飄去,感情的無重量因而形成,語言縫隙間的懸念遂被稀釋,有情也變成了無情。只有透過不斷的思索和質疑,她才離得開那個形而上的虛無境界,重新知道自己是誰!
唐.德里羅是個喜歡追根究柢的哲學式作家。他以前對各種歷史及現實課題都會問到根本,這次他則是透過悼亡,對主觀的私人感情也作了追究,並解開了感情世界心不在焉所造成的死結問題。這個死結被打開,人們就可以打開窗戶,讓風可以吹進來。或許這就是《身體藝術家》最後的重量!
【導讀】 找回感情的重量! /南方朔
著作等身的美國後現代主義大師唐.德里羅(Don DeLillo),每次一出手,全球文學界都必然注意傾聽。他以前著作都卷帙宏大,前幾年出的《陰間冥府》(Underworld)原文即厚達八二七頁。而這次他又出手,卻是部超短的中篇作品。《身體藝術家》(The Body Artist),只有一二四頁,篇幅雖短,受到的注意並沒有減少。
近代文學從一九七○到八○年代起,由於知識理論的改變,而進入了所謂的後現代主義階段。
文學後現代主義有許多特性,最大的特性之一,乃是由於知識理論改變,人們對事務的辯證正反...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4收藏
14收藏

 31二手徵求有驚喜
3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