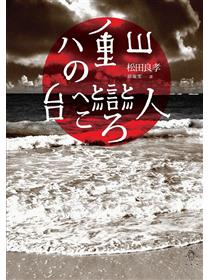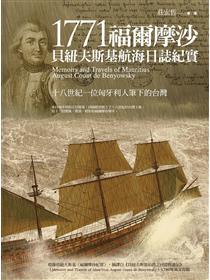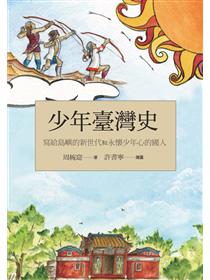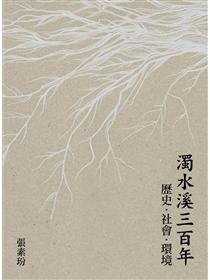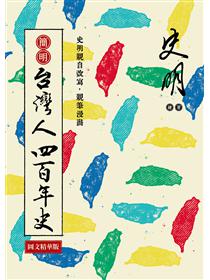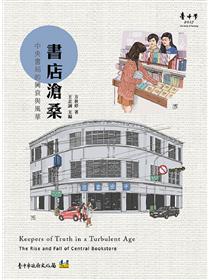「……在我們喧騰熱鬧的島嶼,沒有比花蓮更邊緣的邊緣地帶,此地充斥實驗、矛盾、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理解與融合,最後散發著一股臺灣罕見的「混血」氣質。」
歷史進入大航海時代,歐洲人來到臺灣東部的花蓮,他們看到了什麼?貝林的地圖將花蓮裂成三座小島,像三隻孱弱的小雞緊貼著臺灣。葡萄牙水手在立霧溪河口發現閃閃的砂金,興奮地稱呼這條河為黃金河。英國生物地理家古里馬看到絕美的清水斷崖時大為震驚,不相信世上竟有這樣的海崖。花蓮這塊美麗的海岸大地,在被西部的漢人稱為「後山」之前,究竟發生過哪些事?一部嶄新的東部書寫,一個兼容歷史與文學想像的大敘述,深入臺灣肌理,直觸島嶼靈魂深處。
全書以大航海時代法國皇家製圖師貝林一張謬誤的臺灣地圖為開端,穿梭時空,敘述屬於這塊土地的想像與故事。作者用小說的筆法呈現出花蓮不同以往的全新面貌,先以歷史的廣博凝視,復以文學的深度理解,既看到了東部歷史的幽微,也更深刻地認識了臺灣。
人的想像有多大,歷史就有多深邃。在書中,當代小提琴家米多莉沿著時間的莫比烏斯帶,跟日治時期的記者毛利之俊相遇於布農族奔馳游獵的東部山區。船師文助迷航漂流到東海岸,在秀姑巒溪的奚卜蘭過了幾年如夢似幻的日子。太魯閣族獵人翻越未曾攀登的奇萊主峰,在某個清晨遇見射自東方的耀眼陽光,嗅到空氣中的鹹鮮,第一次看到了東部,也看到了一片美麗的蔚藍大海。漢人吳阿再從湖南來到臺灣,以鎮海後軍士兵的身份,穿著繡有「兵」字的大袖短衣,敗陣逃亡到一棵樹下沉沉睡去,渡過了進入日本時代的第一個夜晚………。寫不完的歷史和說不完的故事在我們四周浮沉,王威智寫出了一個比花蓮更花蓮的花蓮。
作者簡介:
王威智,1970年生。
台大中文系畢業,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碩士。
喜歡棒球和籃球,和小朋友比起來可說打得不錯。
讀很多地圖(有等高線的那種),幻想走在每天一定看見的臺灣脊梁之上。
在不很清楚登山是怎麼回事又無比恐懼高山症的情況下,
一連服了兩天丹木斯,順利在積雪頗深的嚴冬爬上故鄉曾以其名為名的奇萊主北兩峰。
愛高山甚於中級山,由此可知登山之道鑽研得還不夠深入。
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
著有《我的不肖老父》(東村,2012)。
章節試閱
Très peu connue
消失多年的哆囉滿人說:
一開始是洄瀾
因為漳州人看見縈迴巨浪
而瀾與蓮於河洛語為諧音
花俗音如洄
後來泉州人把花讀正
但洄瀾跟花或蓮花有什麼牽連呢?
似乎是另一種漳泉械鬥
走避他鄉的哆囉滿人說:
沙奇萊亞被西班牙人當成地名
現在他們自稱撒奇萊雅
岐萊、奇萊、澳奇萊
都是沙奇萊亞的漢音譯文
只是荷蘭語聽來聱牙走了調
阿美族說太魯閣族像崇爻
聽來像卦名
但阿美族的意思其實是比易經更容易的
猴子
飽受驚嚇的哆囉滿人說:
我們一直住在西班牙人說的Turuboan
或者荷蘭人說的Tarraboan
但太魯閣族已翻越奇萊
順著立霧溪逼近
關於黃金我們僅僅留下傳說
然後奔向蘭陽
投靠哆囉美遠
那個名字與我族相近的北方大社
尋找花蓮的名字於文獻之海
翻閱撒奇萊雅阿美太魯閣閩客荷蘭
還有西班牙
最後發現你的出身其實是
蛋撻式的我的意思是葡式的
金之河
利奧特愛魯
Rio de Ouro
關於黃金可信與不可信的傳說都記錄於誌書,有文為徵的花蓮是從比蛋撻更誘人的黃金開始的。
闖進未知的世界,那是一場葡萄牙風味的冒險,冒著比糖晶過度烤焦更高的風險。
當某個葡萄牙人把terra寫做Terra,他的意思是「地球」。世界並非又平又扁,於是我們想起畢達哥拉斯,他說大地是顆球。
哥倫布相信畢達哥拉斯,他從西班牙一路往西航行,橫渡大西洋,遇見陌生的大陸。哥倫布是鄭和之後最顯赫的航海家,但他聲稱新大陸是馬可.波羅筆下的亞洲大陸,有一次他致信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斷言古巴就是亞洲東岸。
幾年後,佛羅倫斯商人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宣稱四度前往「新大陸」;一五○七年,德國地理學家瓦爾德澤米勒出版《世界地理概論》,以Amerigo之名替歐洲以為的新大陸命名。
葡萄牙人麥哲倫在東南亞參與殖民戰爭時,看見香料群島以東是一片大海,和哥倫布一樣,麥哲倫是地圓說的虔誠信徒,但他認為這片尚未命名的大海的東方盡頭才是美洲。一五一九年八月,在西班牙國王資助下,麥哲倫率領船隊從安達魯西亞出發,十四個月後在南美洲南端發現後來以其為名的麥哲倫海峽,船隊沿著彎彎曲曲時寬時窄的峽道艱難地前進,二十多天後抵達海峽另一端,進入一片全新的海洋,舉目浩瀚,彷彿永遠看不見陸地,遇不到島嶼。
眼前的汪洋何等遼闊,麥哲倫對此一無所知。一路上風平浪靜,沒有駭人的驚濤駭浪,他愛上了這片如受上帝祝福的無名大水。
「何不讓陌生的海洋跟大西洋、印度洋一樣呢?」剎那間,有個念頭閃現了:「給它名字吧!」那時,麥哲倫或許恰好站在船首,迎著風,望向海面,湛藍深邃,如鏡太平。他想了想,於是太平洋在人類歷史上誕生了:
Mare Pacificum !
一五二一年春天,船隊泊在一座無人島,一夥人登島休息取水,忽然發現土著搖著小船,漸漸逼近。麥哲倫的奴僕恩里克用馬來語朝他們喊話,沒想到土人竟然聽得懂。麥哲倫恍然大悟,十二年前他把出生於蘇門答臘的恩里克帶到歐洲,如今他毫無預期地把恩里克帶回舊地。
這裡是亞洲,畢達哥拉斯是對的,大地是球,而他即將完成人類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向歐洲和基督教宣告世界是一顆球,一顆滿覆大水的巨球,這同時意味著象徵財富與爭端的香料群島不遠了。
但是,麥哲倫最終僅以靈魂與精神完成壯舉,他介入菲律賓小島部落間的戰鬥,石塊、弓箭、標槍和利斧齊飛,讓他魂斷東方。
慘遭折損的船隊繼續西行,在摩鹿加群島以當時歐洲市場難以想像的低價,將丁香、豆蔻、肉桂一一搬上船,直到船艙塞不進才罷手。一五二二年九月初,維多利亞號率先回到三年前啟航的桑盧卡爾港,在艱苦的旅程後,船上幾十個水手倖存十八人,疲勞衰弱讓他們個個不成人形。
當我們行經清水斷崖,黃昏時分坐在七星潭的石灘看浪,從石梯港搭上船出海尋鯨,或者什麼也不做只是望著廣漠的太平洋,也許會想到麥哲倫,想起他的環球航線就橫越離我們的島嶼南方並不很遠的海面。
麥哲倫與亞洲最初的接觸是菲律賓的維薩亞斯群島,而維薩亞斯群島與我們僅僅隔著巴士海峽和呂宋島。如果麥哲倫在令他火冒三丈因而縱火殺人的強盜群島以西,命令舵手轉向右舷二十五度,那麼他將在蘭嶼外海遇見臺灣。
麥哲倫不認識黑潮,對這股強勁的洋流十分陌生,但如果麥哲倫遇見臺灣,他和敏感的水手會發現有隻無形手推著船,即使船帆無風可吃,偌大的船身將不停歇也不打轉,航向總會指向北方。
如果麥哲倫遇見臺灣,他將在黑潮的推送下,沿著東海岸向北巡行,穿越臺東與綠島、蘭嶼間的海面,經過石梯港,看見花蓮溪的洄瀾,讚嘆七星潭完美的弧灣。船隊一過立霧溪口,就會看見清水斷崖,誰能忽視那一片綿延四葡浬的插天絕壁?
一五四四年,葡萄牙商船從麻六甲航向日本,途經臺灣東岸,水手在航海日記上寫下Ilha Formosa。如果麥哲倫是遇見臺灣的歐洲第一人,這位成功橫渡太平洋的探險家會不會早在一五二一年的夏天,太平洋剛剛有了名字,也順便為我們的島嶼取名,並且同樣叫做Formosa?
麥哲倫之後,歐洲更急於探索,船隻伸出熱切的觸角,製圖師更加忙碌,他們在紙上經緯大陸,在銅版上蝕刻島嶼,將一筆一劃填進未知的空白。繁忙的工作關乎世界的形狀,製圖師夜以繼日,在油燈的光暈中編織與燈光同樣朦朧的世界的容貌,以日益凹陷的臉頰和深重的皺紋換取世界的輪廓。
繪圖師來自各地,葡萄牙、荷蘭、比利時、英格蘭、法蘭西……,Luis Jorge de Barbuda、Abraham Ortelius、Jodocus Hondius 父子、John Blaue、Alexis-Hubert Jaillot、J. van Keulen……,他們是畫家、耶穌會教士、出版商……,他們熱愛且擅長繪製地圖。一五五四年,葡萄牙製圖師歐蒙(Lopo Homem)畫了一幅有臺灣島的世界地圖,臺灣從此進入歐洲的視野。
杜拉多(Fernão Vaz Dourado)也是葡萄牙籍製圖師,更是同業裡的佼佼者。他在一五六八年完成「東亞地圖」,把臺灣畫成三座獨立島;五年後,杜拉多舊圖新繪,臺灣仍舊「分崩離析」。
姑且將「東亞地圖」裡的「福爾摩沙三島」稱為「北島、中島、南島」,北回歸線明顯地劃過中島下半部,拿現代地圖一對照,不禁令人猜疑中央山脈兩側的幾條大河川就是臺灣一分為三的原因。北島中島之間的海峽大概是立霧溪和大甲溪,而隔開中島南島的可能是秀姑巒溪和濁水溪。
寬闊的河口遠望如汪洋,桅杆之頂的觀測手或許因此錯看了島嶼的形狀。此後,歐洲海圖裡的福爾摩沙島形狀不一,而且經常與琉球混淆,或被當成琉球群島的一分子,直到一六二五年。
十七世紀初葉,荷蘭從巴達維亞城派遣艦隊航向中國,打算突破葡萄牙和西班牙與中國的密切關係,能與中國自由通商。一六二二年,西班牙人到Turuboan採金,就在那一年夏天,荷蘭在澳門向葡萄牙發動攻擊。這場戰事像一場西北雨,很快就落幕了,荷蘭大敗,只好握著敵營的海圖,航向澎湖和陌生的臺灣。
一六二五年春天,荷蘭派遣高級舵手諾得洛斯(Jacob Ijsbrandtsz Noordeloos)率領北港號和新港號兩艘中國戎克船,從臺南出發環繞臺灣一周,二十多天後,北港號順利完成任務。諾得洛斯並未登陸,僅從海上測繪畫成了「北港圖」,這是世界第一張臺灣島圖,雖然島嶼嚴重變形,但確定福爾摩沙島是一座完整獨立的島嶼,過去把福爾摩沙島畫成三座相鄰小島,或者說在福爾摩沙島附近另外畫了兩座大小差不多的島嶼,根本錯得離譜。
諾得洛斯的環島之旅還讓荷蘭得知東臺灣山高谷深,沒有合適的港口,不是建立據點的好地方。不過這並未減低荷蘭對東臺灣的興趣,他們發現原住民的飾物綴有黃金,而原住民尚未和外邦人做起生意,所以他們身上的黃金顯然不是進口貨,而是當地的產物。此外,荷蘭人想必也聽聞了種種關於臺灣東岸的黃金傳說。
十八世紀初年,康熙皇帝諭令耶穌會教士前往全國各地,以科學方法測量中國,繪成中國第一部有經緯線的地圖集,也就是著名的「皇輿全覽圖」。一七一四年春夏之交,馮秉正與雷孝思、德瑪諾三名耶穌會士從金門料羅出發,經澎湖於安平港登陸。
馮秉正一行一抵達臺灣府,受到地方官吏熱烈的歡迎,他們本來有機會把臺灣好好看一遍,但不知基於什麼原因,教士將臺灣島分成東邊和西邊,而且認為只有西半部才屬於中國,他們說東半部荒山野地上的原住民「與美洲的野番大同小異,但沒有易洛魁人那麼粗暴,比印第安人還純潔。他們天性溫柔和平,彼此相親相愛,相互扶持,不追求個人利益,不重視金銀,但報復心太重,不知法律、政府、警察、宗教為何物。」
馮秉正承認那是中國人的說法,而中國人和臺灣的原住民幾無往來,所以他不保證那樣的描述正確與否。他還提到漢人為了黃金一度考慮開發東部,原住民因此遭到殺害,他認為那是「心懷不軌」的後果。
馮秉正等人從頭到尾只關心臺灣西半部,在滿清官員的陪同下負責南臺灣的測繪工作,雷、德兩位負責北臺灣。他們描繪的臺灣西岸輪廓比以前更詳細,儘管河流、地名有些不一樣,卻是全新踏勘的成果。東海岸就令人搖頭了,由於山脈另一邊並非王土,「皇輿」不必「全覽」,所以不必花力氣走一趟。耶穌會士憑著想像和不見得可靠的傳聞創造了臺灣的東海岸。
後來馮秉正寫了一封長信回歐洲,描述在臺的見聞。諸如此類來自東方的第一手資料立刻成為描繪東亞地圖時最新最重要的依據,而這應該令製圖師感到十分苦惱,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描繪這座遠東美麗之島的東部海岸。
杜赫德神父(Jean Baptiste Du Halde)沒來過亞洲,但他是十八世紀歐洲著名的漢學家。一七三五年,他出版巨著《中華帝國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轟動歐洲,被譽為「法國漢學三大奠基作之一」。《中華帝國全志》有一幅「福建省圖」,畫面右下方——也就是福建省東南方——有一座不小的島嶼,圖中地名如Fong-chan-hien(鳳山縣)、Nganpinching(安平鎮)、Ta-kia-chi(大甲溪)……,一看就知道是臺灣,可是為什麼整座島看起來像一支過度彎曲的鵝毛筆?
「福建省圖」的製圖師把最後一筆落在高聳的中央山脈,也許他曾盯著空白的臺灣東部,搔頭抓腦想著下一筆。在反覆的推敲琢磨後,他決定不讓島嶼的東半部出現在地圖裡,於是「福建省圖」裡的臺灣島沒有東半部。臺灣島畸形的元兇很可能是博學的耶穌會士,他們讓十八世紀歐洲眼中的中華帝國一度不包括花蓮。
法國第一位海軍海圖工程師貝林(Jacques Nicolas Bellin)是水文地理學家,也是皇家製圖師與皇家學會會員。他畫過好幾幅「福爾摩沙島與中國沿海局部圖」(L'ISLE FORMOSE ET PARTIES DES COSTES DE LA CHINE),另外他在一七六三年還畫了一幅「中國海岸之福爾摩沙島圖」(CARTE DE L'ISLE FORMOSE Aux Costes de la Chine)。
貝林當然參考了耶穌會士和法國航海測量師的測繪成果,他發現福爾摩沙島西岸資料豐富,東岸卻蒼白貧乏。最後他決定不打迷糊仗,乾脆張開想像的翅膀,在美麗的遠東島嶼上空盡情翱翔。
貝林異想天開——也可能得自義大利製圖師柯羅內里(Vincenzo Mario Coronelli)一六九六年「中國東部圖」(Parte Orientale della China)的啟發——將立霧溪、花蓮溪和秀姑巒溪當成分割花東縱谷與奇萊平原的條狀內海。
在這一系列地圖裡,花蓮彷彿經歷了驚天大地震,劫後餘生,裂成三座南北相接的小島,像三隻孱弱的小雞,又像三個挨了揍的無賴,緊緊貼著福爾摩沙島。
「三座島至少是新鮮的布局吧。」貝林可能一邊畫一邊這麼想,他的美麗島是十八世紀西海岸與十七世紀東海岸的奇異組合,這意味著在他的時代歐洲對臺灣東岸的認識仍然有限,不比一百年前的荷蘭人更高明。或許他考量的是:
福爾摩沙是一座完整的島嶼,中央有高大的山脈,人們對島嶼內部一無所知(L'interieur de cette Isle n'est pas connue.);山脈以東應該有平地,接著才是沒入太平洋的海岸線。我的地圖不能跟「福建省圖」一樣,一刀削去東半部,不過我缺乏足夠的資料,只好委屈東海岸停留在荷蘭時代。我將繼續採用荷蘭時期的地名,也就是一百年前荷蘭人探金時留下的紀錄,譬如黃金河R. Goude。
貝林在「三島」右方下了註記。一七三○年,他以幾乎比地名還細小的法文寫著:Toute cette coste est très peu connue.。那時我們的海岸是如此神秘,神秘到讓一直在發現世界的歐洲也對之幾乎一無所知,和島嶼中央的深山地帶差不多。在一七六○年版的地圖裡,貝林在法文註解旁另外添上一行意思相同的荷蘭文:Deeze gantse kust is weinig bekend.。
身為法蘭西最具聲望的製圖師之一,貝林會不會因無法明確地描出一座遠東島嶼的海岸線,以至於心虛到不得不拉著荷蘭人作陪,吞吞吐吐地說:此處海岸鮮為人知?
貝林先生,容我致最高的敬意。您必定不知道,花蓮像個年輕的村姑,內向少話,其實沒那麼渴望被理解。不必擔心,不必掛意,更不要感到歉疚,儘管您對我們的海岸所知甚少。
對了,您那三顆小島其實很有意思,像隱喻,更像預言。
Très peu connue
消失多年的哆囉滿人說:
一開始是洄瀾
因為漳州人看見縈迴巨浪
而瀾與蓮於河洛語為諧音
花俗音如洄
後來泉州人把花讀正
但洄瀾跟花或蓮花有什麼牽連呢?
似乎是另一種漳泉械鬥
走避他鄉的哆囉滿人說:
沙奇萊亞被西班牙人當成地名
現在他們自稱撒奇萊雅
岐萊、奇萊、澳奇萊
都是沙奇萊亞的漢音譯文
只是荷蘭語聽來聱牙走了調
阿美族說太魯閣族像崇爻
聽來像卦名
但阿美族的意思其實是比易經更容易的
猴子
飽受驚嚇的哆囉滿人說:
我們一直住在西班牙人說的Turuboan
或者荷蘭人說的Tarraboan
但...
作者序
沉默交易
整整二十前我從師長口中得知《東臺灣展望》,那時我跟在他們後頭幫忙編綴一套地方文史叢書,書中部分圖片就引自《東臺灣展望》。那些非專業翻拍、略顯模糊的照片不但是珍貴的影像,對我而言更是被凍結的時間,勾起我對花蓮「過去」的想像。
幾年後我才有機會一睹傳說中的《東臺灣展望》,個頭壯碩,巨大的開本和繁多的書頁使其份量重若大山,外觀深絳,書名燙金,硬皮精裝,作者毛利之俊的用心昭然可見,1930年代大阪的印刷與裝幀技藝也極為可觀,但時間令書況不佳,讓它看起來像一個魁梧的糟老頭,裱布破損,裝訂崩散,書頁脆化泛黃。
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東臺灣展望》必須受到妥善的收藏,同時心頭有個疑問像打不掉的寄生蟲那樣糾纏不休:毛利先生受到何種動力的驅使而獨力編寫這樣一本他所謂的「紀念冊」?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毛利先生早就給了答案:紀念冊。《東臺灣展望》無疑是一本向時間致敬之書。
我開始凝視毛利先生的「展望」,在史籍裡翻找線索,把想像當成筋肉,一片一片貼上歷史的骸骨,如同人類學者在實驗室就出土的殘缺頭骨重建M6的頭顱顏面。歷史本來就是「他人的故事」,地圖和史書在某方面可說是一模一樣的智識產物,它們都是經過詮釋的成品,被寫出來被畫出來的目的往往是指導或誤導。《製圖師的預言》不是一本地方誌,即便寬鬆以待也難以視之為「誌」,儘管確實奠基於某些確定的地理、史實與出土材料,但也僅只於此,說穿了只是一趟「自以為是」的「重建」之旅。
在旅程中我走過部落、河岸、蜿蜒的山徑,聽見鎮海軍吳阿再竄逃的喘息夾雜著穿梭於蓁莽雜林間身體四肢與枝葉摩擦的窸窣聲,看見形容枯槁的蝦夷地船師文助和他的水手目睹順吉丸被阿美族人焚毀時滿臉的驚訝與無奈,甚至一度飄浮在空中俯望花蓮溪口海階上蹦蹦跳跳的M家族。當然,我最常聽見的是毛利先生的腳步聲,但從未與他見上一面,我們似乎各自佔據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的一側,並且不停走動,有時來到同一處,但時間只允許我透過文字「看見」毛利先生,「看見」他讓攝影師以鏡頭凍結的人物和風景。
莫比烏斯帶是一個奇異的連續曲面,看起來像環,擁有內外兩面,其實只有一個面。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輕易地製作莫比烏斯帶,只要將一條矩形紙帶扭轉180度再黏合起來,就是一條莫比烏斯帶。假設某人沿著莫比烏斯帶走,那麼他將在中途回到——或者說「經過」——起點,只不過是在另一側;繼續走,最後會走完整條莫比烏斯帶。莫比烏斯帶讓人以為從這一面走到另一面,其實始終是在同一平面。如果有兩個人沿著莫比烏斯帶反向而行,則他們將在某一點相遇,但那不是一般意義的相遇,他們可以聽見彼此,卻無法面對面,他們只是在一個連續曲面的相異兩點以奇異的方式相遇罷了。莫比烏斯帶沒有邊界,宇宙之所以無垠,會不會宇宙根本只是一條宇宙超級無敵大的莫比烏斯帶?
時間也像莫比烏斯帶,自我複製無限循環,特別當我自以為看見麥哲倫站在船頭迎著風為陌生海洋命名的那一刻,聽見太魯閣族的先人第一次看見東方的日出瞇著眼謙卑而順從地驚呼之時,或者自以為是地認為吉田初三郎一定帶著徒弟在蘇澳搭上東海自動車株式會社的嶄新巴士一路顛簸來到花蓮,不然他如何決定讓斷崖做為「大太魯閣交通鳥瞰圖」的前景?
這也是一次看見「混血力量」的旅程。在我們喧騰熱鬧的島嶼,沒有比花蓮更邊緣的邊緣地帶,此地充斥實驗、矛盾、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理解與融合,最後散發著一股臺灣罕見的「混血」氣質。這股氣質引發一種可有可無的調調,讓此地其實頗具活力的生活看起來慵懶散漫,它的源頭是匆匆航經立霧溪口的葡萄牙水手,肩負重任眼射精光的荷蘭探金隊小隊長,在颱風一來必定淹沒的海階平台上討日子的史前人類M家族,認為向陽那一側才是前山的太魯閣族先人(和我的漢族先人比起來,他們的見解多麼奇異啊!),在清領轄下而實為無政府之地的奚卜蘭地方酣暢度日的阿美族,拒飲阿美族小米酒卻樂意教授編席之術的日本船師文助,還有佩刀持槍在深山監控布農族的日警,我甚至咬了一口他們種在托馬斯的蘋果,才知道他們不但難逃螞蝗和冰雪的啃嚙,也得面對又酸又澀的鄉愁,儘管將砲管瞄準頑強的「蕃人」,但原來他們和「蕃人」一樣,有血有肉。
當然還有從事「沉默交易」的哆囉滿人。他們或許是臺灣最早的採金人,明白黃金是珍稀之物,卻不清楚買賣之道,於是有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易物之術。假設有個哆囉滿人,他在岩石上鋪了樹葉,在樹葉上放了黃金,那是一個期待交易的訊息。如果恰巧有人帶了兩張鹿皮經過並認為拿兩張鹿皮換一小塊黃金是合理的交易,那麼他會留下鹿皮,取走黃金;過了幾天,哆囉滿人回頭查看,他看見並取走鹿皮。
如此迂迴、緩慢、樸素而安靜的交易需要誠實、正直、尊重與謙卑。基於尊重,我迂迴地與消逝的時間談生意,當然,想像和誠實隔了一段距離,但我的確盡可能謙卑地以文字填補遺骨與遺骨間的孔縫,藉以認識這一片南北狹長東西狹窄的罕為人知的山海地。
沉默交易
整整二十前我從師長口中得知《東臺灣展望》,那時我跟在他們後頭幫忙編綴一套地方文史叢書,書中部分圖片就引自《東臺灣展望》。那些非專業翻拍、略顯模糊的照片不但是珍貴的影像,對我而言更是被凍結的時間,勾起我對花蓮「過去」的想像。
幾年後我才有機會一睹傳說中的《東臺灣展望》,個頭壯碩,巨大的開本和繁多的書頁使其份量重若大山,外觀深絳,書名燙金,硬皮精裝,作者毛利之俊的用心昭然可見,1930年代大阪的印刷與裝幀技藝也極為可觀,但時間令書況不佳,讓它看起來像一個魁梧的糟老頭,裱布破損,裝訂崩散,書頁脆...
目錄
序
1. Très peu connue (鮮為人知)
2. 製圖師的預言
3. Rio de Ouro (金之河)
4. Klbiyun (聖山)
5. M6
6. 申酉方向迷航
7. チョプラン (在河口)
8. 吳阿再溝
9. 大タロコ (大太魯閣)
10. みどり (綠)
註解/附錄圖說
序
1. Très peu connue (鮮為人知)
2. 製圖師的預言
3. Rio de Ouro (金之河)
4. Klbiyun (聖山)
5. M6
6. 申酉方向迷航
7. チョプラン (在河口)
8. 吳阿再溝
9. 大タロコ (大太魯閣)
10. みどり (綠)
註解/附錄圖說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6收藏
36收藏

 28二手徵求有驚喜
28二手徵求有驚喜



 36收藏
36收藏

 28二手徵求有驚喜
2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