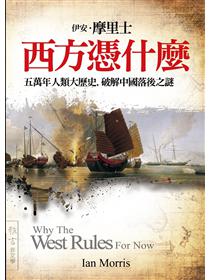大明王朝末年最窘迫傾危時刻
鄭森,潮漳總兵鄭芝龍之子,大儒錢謙益之徒
面對家國覆滅的凶險,周旋於父兄師友的算計之間
做出死生一線的抉擇……
鄭森,幼名福松(暱稱ふくちぁん),1624年出生於日本九州平戶島,六歲以前跟著母親田川氏於日本生活,七歲被父親接回中國。
父親鄭芝龍是海上鉅商、邊鎮大將,卻也曾是打家劫舍的海盜頭子。鄭森飽讀聖賢書,一心躋身為士大夫、協助朝廷「驅逐韃虜」,但自己卻擁有一半「倭人」血統……
崇禎十六年(1643),鄭森二十歲。
面對日漸逼近的清軍威脅,朝廷調遣廣東潮漳署總兵鄭芝龍率水軍前往遼東協助海防,但鄭芝龍抗令不出。鄭森基於忠義之心勸諫父親,鄭芝龍表示出兵遼東對大局無益。在父子一夕交心談話中,鄭芝龍提到他的夢想是能夠不必依賴荷蘭人的中轉,建立中國人自己的海上貿易體系,使百姓安樂、國富民強。
駐守武昌的明朝總兵左良玉藉口糧餉不足,意欲率領大軍東下南京「自行籌餉」,一時江南震動。此舉對鄭芝龍的海外貿易貨源造成巨大威脅,遂派鄭森前往南京活動退兵。鄭森因緣際會拜大儒錢謙益為師,並認識黃宗羲、侯方域等復社文友。侯方域的父親侯恂對左良玉有恩,鄭森與其交心,促成侯方域寫信勸左退兵。經過一番冒險周折,鄭森終於將書信送到左良玉手中,並且成功說服對方。
鄭森無意間認識閹黨人物阮大鋮,但基於公理及對復社的認同而拒絕與其來往。然而父親、老師錢謙益和阮大鋮結盟,商議共謀安定江南的政治布置,鄭芝龍並要鄭森為大局著想與其妥協。但阮為報私仇企圖陷害侯方域等人,鄭森在最後一刻決定報訊救友,因而違抗了父親。
本書特色
*全景呈現鄭家水師艦隊威武懾人的陣法砲列
*靈活勾勒晚明海外貿易與河運經濟的生意命脈
*生動刻畫商賈生計與士大夫思維的矛盾衝突
*巧妙鋪陳官場心計與冷風熱血的黨爭禍端
*細筆雕琢明代文人冶遊世界的風雅與色藝
*感性描繪鄭芝龍與鄭森父子之間的交心與破裂
作者簡介:
朱和之
本名朱致賢,台北人,一九七五年生。拿傳播文憑而偏好於文史。好音樂,不求甚解。著有《滄海月明──找尋台灣歷史幽光》(入圍2011台北國際書展大獎)、《指揮大師亨利‧梅哲》;編著有《杜撰的城堡──附中野史》;為《音樂時代》、《音樂年代》、《新朝藝術》、《MUZIK》雜誌主筆。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工頭堅(歷史旅遊愛好者)
何健(冶堂主人)
邱坤良(北藝大戲劇系教授)
侯季然(電影導演)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尉天驄(政大中文系名譽教授)
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楊澤(詩人)
同場站台,豪情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一支深愛不忍的筆,穿透層層累積的歷史迷霧,把鄭成功還原成一個奔波在海上的徬徨青年,有一雙深邃的眼睛與一顆渴愛的心,只想找到自己的家。三百七十年來,鄭成功從未如此真實過。——侯季然
名人推薦:工頭堅(歷史旅遊愛好者)
何健(冶堂主人)
邱坤良(北藝大戲劇系教授)
侯季然(電影導演)
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尉天驄(政大中文系名譽教授)
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
楊澤(詩人)
同場站台,豪情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一支深愛不忍的筆,穿透層層累積的歷史迷霧,把鄭成功還原成一個奔波在海上的徬徨青年,有一雙深邃的眼睛與一顆渴愛的心,只想找到自己的家。三百七十年來,鄭成功從未如此真實過。——侯季然
章節試閱
張肯堂入了大堂,居中坐下,神色嚴峻,已非適才溫煦的老好人模樣。此番到安海來前,與一干幕僚智囊計議,當時頗有勸他不要親自前來的,怕萬一張肯堂調不動鄭芝龍,有失巡撫威信。但流寇在中原和西北各省奔竄,清兵又入關大肆劫掠,南北音信斷絕,國勢十分危急,因此張肯堂以巡閱為名,慨然動身前來。
他盤算著,福建、廣東兩省撥款給鄭芝龍募兵、造艦,若鄭芝龍有侵吞公款的跡象,便奏明朝廷查辦。若兵、船如實備辦,便責成鄭芝龍即刻出兵。
眾人依次在兩邊站定,鄭芝龍見張肯堂沒有讓眾人坐下的意思,故意打個哈哈,對李嗣京和林文燦道:「兩位大人別客氣,像是罰站似地,請入座吧。」
「撫台大人未賜坐,下官怎敢擅坐?」李嗣京道。
「咱們是議事,又不是審案。您是巡按御史,代天巡守,乃是欽差,怎可無座。」鄭芝龍一邊說著,自個兒就坐了下來。他話裡說的是李嗣京,其實也在自況,蓋巡撫和總兵都是無品級的欽差,最初都是有特殊的事務時才奉敕到地方公幹或征伐,事畢還朝。明末時巡撫與總兵實際上已改為常設,巡撫節制地方文武官員也早就成為行之有年的通例,但因朝廷不敢改動「祖制」,在體制上仍屬欽差而非地方官,就形式言並無統屬關係。鄭芝龍故意這麼說,從大道理上還不容易駁他得倒。
李嗣京看看張肯堂,張肯堂點點頭道:「各位大人都請坐吧。」於是眾人紛紛坐下。
「張大人公務繁忙,遠道而來,著實辛苦。」鄭芝龍道。
「有些事總要親眼看看,才能得實情。」張肯堂道:「何況本撫幾次請總兵大人前來福州,大人都推說有事,想見一面竟是千難萬難。」
「大人言重。」鄭芝龍一派輕鬆地道:「確實是軍務繁忙,走不開身。大人別瞧這兒太平年月似地,其實紅夷倭寇、山賊海盜,剿也剿不完。還得一面督造戰船、操練士卒,這些都是本鎮必須親力為之,責無旁貸之事。」
「如此說來,總鎮大人乃是勤勞王事,宵旰焦勞啊?」李嗣京語帶譏諷地道。
「李大人美言了,這不過是分所應為。」鄭芝龍像是受了稱讚似地坦然受之。
「總兵大人,」張肯堂不願在口舌上耗事,切入正題道:「上年朝廷命你速挑堪用水兵三千,星夜揚帆,飛赴關外覺華島一帶,如今大半年過去了,總兵大人為何還不出兵?」
「大人明知故問了,本鎮前已奏明朝廷。東南海防需人,兵卒未便多調,必須重新選練。遊寨戰船若取現成,萬里驅馳怕不夠堅固,必須從新再造。舊有銃器久經磨耗,火口過寬射擊不準,也須新製。而督造之責,職不容辭,是以始終走不開身。」
張肯堂想,若鄭芝龍仍以船械未備推託,就以玩忽職守責之。於是問道:「如今已備否?」
「盡皆齊備!」鄭芝龍爽快地回答。「本鎮督造大號福船二十隻、中號趕繒船二十隻,都已造就。廣東掌印都司新造大斑鳩銃四百門、彈二萬顆,中斑鳩銃二百四十門、彈一萬二千顆,鳥銃九百門,日前皆已撥到,本鎮點收無誤。此外水兵三千,本鎮日夜操練,已成一支勁旅。我本就有意請張大人前來校閱,張大人這次來得可巧呢!」
張肯堂聽鄭芝龍說得俐落,心想倒要看他一看,別給蒙混了。於是道:「如此甚好,正要瞻仰貴鎮軍容,請問何時可以校閱?」
「都已經準備好了,」鄭芝龍兩手往膝蓋上一拍,從椅子上彈起來,「這就去看,請各位大人移步吧!」
鄭芝龍說走就走,張肯堂等三人倒有些反應不及,見鄭芝龍一個勁兒往外走去,只好離座跟上。
眾人出得署衙,從側邊走出不遠就是碼頭,平日此處商船、民船、軍艦往來停靠十分熱鬧,這時卻只見兩艘嶄新的福船停靠在空盪的碼頭邊。
李嗣京疑惑地道:「總鎮大人,貴鎮的四十隻船呢?」
「碼頭窄,怎停得下四十隻戰船?都已在海上待命了。」鄭芝龍道:「各位大人請登船吧!」
「不能就在岸上看嗎?」李嗣京道。
「要看船操,當然得在海上。」馮聲海道:「在碼頭裡也瞧不出船隻造得好壞,有些船外表光鮮,卻禁不得風浪,一出海就要散架的。」
李嗣京苦笑道:「這個,我是北方人,怕坐不慣海船。附近可有山丘岬崖,可以居高臨下觀看?」
「那可難辦了,附近是有高處,但離海甚遠,甚麼也看不清。」馮聲海道:「好在今日風平浪靜,坐船出海應該是不礙的。」
「今日原想好好操演一番,大人們若坐不慣海船,唉,那也只好作罷論了。」鄭芝龍故意裝出一副十分可惜的樣子。
「哼,出海就出海,鄭帥不怕咱們看,咱們還怕看?」林文燦說著,大踏步從斜搭在碼頭邊的長跳板走上船去。張肯堂想,莫非鄭芝龍故意要他們知難而退?傳聞此人富可敵國,乃是海外通商而來,卻不知是否也由貪贓所得,這船隊非看不可。於是手一比,道:「請!」跟著走上船去。李嗣京見此光景,自然不能獨後,只好硬著頭皮跟上。鄭芝龍見鄭森混在人群裡觀望,招手要他一塊上船。
福船分為四層,底層填塞土石壓艙,第二層是兵士寢息之所,第三層左右各開六個方型的小窗,官廳設於中間,前後則是解纜下椗和炊爨之處。第四層如露台,開有梯穴通往下層,矢石火砲都由此而發。船後又有高聳的尾樓和將台。
眾人踩著跳板登船,鄭芝龍隨即命施天福指揮解纜揚帆,道:「外頭風大,各位大人且在官廳稍坐,待到海上再請到上層看操。」領著眾人下梯進到官廳。這官廳錦幃繡帳地布置得十分華麗,用的桌椅也是紫檀木,關上窗就像一般平地的房舍似地。林文燦不由嘖嘖讚道:「鄭帥打仗好舒服,真叫人大開眼界,回頭我也請撫台大人調我去做水師。」鄭芝龍聞言笑笑不答。
船離碼頭甚是平穩,若不往窗外看還不覺船在移動。鄭芝龍淨說些笑話,從人流水價送上酒餚,仿如富商乘船遊玩。張肯堂等三人起先都說出營看操不宜飲宴,後來禁不住鄭芝龍等人則頻頻相勸,說稍飲可擋風寒,才勉強喝了一點。
不多時,船身搖晃漸強,李嗣京道:「這酒勁道好沉。」走到窗邊一看,只見海面湧動、浪花飛濺,霎時一陣暈眩,忙扶著板壁回座。還沒坐定,忽聽得遠近一片霹靂之聲轟然爆響,心頭一驚,胸口煩惡之感大盛。
「船隊放砲相迎,到地方了。請各位大人移步吧。」鄭芝龍說著,起身領眾人出了官廳,循梯上到頂層。這梯子既窄且陡,在搖晃的艙腹中顯得格外幽暗狹小。出得頂層甲板卻是豁然開朗,四望天寬海闊,長風勁直凜冽。近處海面上,四十艘簇新的戰船井然陣列,旗幟拍動,兵卒衣甲鮮明挺立船頭,煞是壯觀。
鄭森觀望四周,船隊停泊在圍頭灣正中心,與北方南安、石井,東北方的圍頭以及南邊的金門差不多等距。
鄭芝龍又領眾人走到尾樓將台上,手一擺道:「張大人,這便是此番新造的二十隻福船和二十隻趕繒船,一共四十號戰船。」
施天福向鄭芝龍和張肯堂一個抱拳道:「請大人看操!」
張肯堂點點頭道:「請吧。」
施天福轉身高喊:「結寨!」尾樓上頓時三聲砲響、戰鼓急擂,艙板隨之震動,立在桅斗上的旗手也打起旗語。四十艘戰船立即升帆駛動,向著鄭芝龍等人的旗艦迎上來,將之圍在中間。
船隻排成四列,首尾相接如同四道平行的木牆,形成一座水寨。
施天福又高喊:「變陣!」尾樓鼓響數通,船隊轉動,須臾排成一個魚形:二十艘大福船圍著中軍旗艦排成菱形船陣,算是魚身,左右和陣尾後掠的四列趕繒船是魚鰭和魚尾。
施天福再喊:「啟航!」砲響帆升,中軍向前駛進,船隊同時並發,陣形絲毫不亂。
林文燦見船隊進退有法,不由得讚道:「陸兵擺陣,也難整齊。海船操持不易,而能有此法度,鄭帥帶兵真是有一套!」
鄭芝龍微微笑道:「海上風向不定、波濤變幻,難拘一定之勢,操演陣法不過令船隊熟習進退之道,臨敵之際,還得從權應變。」他對張肯堂道:「撫台大人,海戰之道無他,不過大船勝小船、多船勝寡船,大銃勝小銃、多銃勝寡銃而已。又兩軍相峙,上風順潮者利,下風逆潮者不利。」
「喔?願聞其詳。」張肯堂道。
「福船舷高船堅,遇著小船,當頭駛過去就能將之犁沉。且大船上的火砲和弓箭居高臨下,擊小船就如捏雞蛋似地。此所謂大船勝小船;又海上交鋒,火器最先。蓋火器及遠,海上又無從掩蔽。若敵我船隻一般大小,則銃大且多者,自然得利。而不論是衝犁還是發砲,都須順風順潮,才顯得出威力。反之,下風逆潮則船速遲、煙火倒吹,是授敵以大勢。」
張肯堂向舷邊走了兩步,張望陣中較小的趕繒船,彷彿想像著從福船上往下攻擊的光景,一面點頭道:「信然也。」
林文燦問道:「聽說紅夷的夾板船比福船還要巨大,可是真的?」
「是的,夾板船舟長可達十八丈,橫廣五、六丈,豎桅杆五支,設夾板五層,舷側鑿小窗置銅銃數十門。其大銃長二丈餘,銃門如四尺車輪之轂。可謂樓高船堅,遠非我中華船舶可比。」馮聲海答道。
「長十八丈?」林文燦咋舌道:「那豈不是比福船大了一半有餘?」
「一點不錯。」
「若此,敵船大我船小,豈非無法可制?然將軍曾在浯嶼大破紅夷,是以何策?」張肯堂問。
「紅夷夾板船固然難制,畢竟萬里遠來,其數不多、其援不濟。」鄭芝龍道:「要跟它比大,自然比不過,此時便得以多取勝了。以十圍一,順流火攻,或者群擁而上登船肉搏,以己之長攻其所短,可奏全功。」
張、林二人恍然,連連點頭。張肯堂忽指著海上問:「那是甚麼?」鄭森順著他所指看去,見船陣前方有六艘船下了椗停在海面上,仔細一看似乎不是戰船,而是略顯破敗的舊船,船舷邊立著許多人形木牌。
鄭芝龍笑著說道:「大人,這是幾艘靶船,用來操演火器的!」說罷下頷朝著施天福一揚,施天福立時高喊:「列砲陣!」船尾鼓響、桅斗旗舞,魚形船隊向左右展開,成為一個倒寫「人」字般的逆雁行之勢,由中軍正對著那六艘靶船,兩翼斜伸包抄。施天福又一個指令,船隊轉以右舷對靶船,同時艙板下腳步聲響,六十一名黑人銃手從底艙循梯而上,在右舷邊排成三排,熟練地裝藥、填彈、上火繩,然後第一排銃手舉銃瞄準,等待命令。
張肯堂等見了這隊黑人銃手,還在驚奇之際,施天福已大聲喊道:「開火!」銃兵頭領多默手中長刀一揮,二十管鳥銃同時轟然噴出火光,硝煙大作,靶船上的人形木靶片片碎散。第一列銃手隨即退到後排,第二列銃手上前舉銃,立時又是一陣銃響。等第三列銃手也如法射擊完,第一列銃手已然裝填完了,隨時可以再發。
張肯堂等人還不及讚嘆,施天福手一揮,銃兵隨即拆下火繩轉身退開。另一隊兵卒扛著十門大銃上前,俐落地裝藥、填彈。鄭芝龍道:「撫台大人,這便是新造的大斑鳩銃了。」眾人看這大斑鳩銃,與鳥銃十分相似,只是更為巨大。鄭芝龍道:「大斑鳩銃威力強大,但十分笨重,無法單憑雙手施為,須用一根木棒立在地上撐住銃身。」銃兵一如所言,裝填好火藥鉛彈後把銃身架在一根直豎的木棒上,接著得令發火,威勢又勝鳥銃一籌。
鄭森站在眾人後面,正覺煙硝嗆人,忽見李嗣京有些異樣,曲下身子手扶短欄,於是上前問道:「李大人您還好嗎?」李嗣京捂著胸口勉強說道:「還⋯⋯還好,就是有點暈。」鄭森見他嘴唇發白,眼光渙散,知他醉船得凶,忙問:「大人要不要進艙去休息一下?」李嗣京搖搖手,卻說不出話來。鄭森抬頭一看,張肯堂和林文燦臉色也不好,都在強自撐持。
這時大斑鳩銃手已經退下,砲手們推著八門佛郎機砲,簇擁著正中一門碩大無朋的巨砲,在舷邊砲位上就定。
「請眾位大人看我潮漳水師無堅不摧的砲陣,」鄭芝龍道:「這佛郎機砲,鉛彈可及百餘丈之遠。自嘉靖時傳入中國,已歷百年,雖海盜小賊間亦有之,但要如我軍數量之多、演練之精,放眼神州那是絕無僅有。」他又指著正中間的那門大砲道:「當中這門巨砲,乃是我重金向濠鏡澳的佛郎機人所購,重千餘斤,能發二十四斤之彈,及遠四、五里。在佛郎機國也是難得之物。本鎮名之為『龍槓』,請大人校閱!」
鄭芝龍言罷,施天福隨即高喊:「開砲!」頓時舷邊八門佛郎機砲碰隆齊響,跟著左右四十艘戰船紛紛開砲不歇,有如天降雷神,霹靂爆發。眾人舉手捂住耳朵,卻絲毫不減震撼。鄭森直感胸臆翻騰、五內顛倒,腳下艙板震顫欲裂,叫人幾乎站立不住。定神向靶船看去時,只見六艘船上木屑噴飛,不多時便已千瘡百孔、處處洞穿。一艘船上的主桅忽然中彈,嘩啦一下折倒,杆頭倒栽進水裡去,濺起極高的水花。
鄭森雖也熟練鳥銃,但一直有意遠離兵事,像這樣上百門火砲齊發的陣仗也是初見,不覺血脈賁張,對父親也更增敬意。鄭森數著,火砲不過放了三輪,感覺卻是地老天荒一般。
好容易才覺得砲聲漸歇,剛喘過一口氣來,冷不防一聲轟然巨響,如焦雷怒劈直中座艦,正是龍槓砲發。對面一艘靶船應聲從船身中段栗喇斷碎,糜爛一團。鄭森嚇了一大跳,心想虧得靶船上沒有人,否則真不知會是多麼悽慘的光景。
龍槓發後,眾砲俱寂,海上一瞬間又恢復了安靜。鄭森卻猶覺耳中嗡鳴、心跳狂急。海風到處,圍著船隊的濃密硝煙團團飛走,而鄭森鼻中依然聞到刺鼻的硝磺氣味,中人欲嘔。
施天福老神在在,看鄭芝龍向他一點頭,遂高喊:「操演完畢!」號砲響過,四十艘船上的水兵們齊聲呼喝。施天福轉身抱拳道:「大人!砲操完畢!」
張肯堂等三人不能發一語,只有擺手點頭示意。李嗣京忽然趴在欄杆上嘔吐起來,他起先還顧念著官儀掙扎忍耐,卻終於撐持不住一嘔再嘔。鄭森忙俯身幫李嗣京拍背,按壓他掌心勞宮穴幫著順氣。鄭森看看另一邊,張肯堂臉色蒼白,邊扶著欄杆邊撫胸喘氣。林文燦也好不到哪裡去,雖勉強扠腰而立,卻掩不住腳下虛軟。
「唉呀,三位大人醉船了。快扶大人們進船艙裡去休息。」馮聲海趕緊招呼。
「李大人能移步嗎?」鄭森問。李嗣京神情委頓,依然說不出話來,只能淺淺地搖頭。鄭森看看陡峭的梯級,對鄭芝龍道:「爹,大人們很不舒服,怕不好下梯。」
「那就快取凳子來。」鄭芝龍道:「還有醒船湯!」
很快有小兵取來三張凳子,張肯堂卻堅持不肯坐下,只道:「我⋯⋯一會兒進艙去再休息⋯⋯」胃中猛然一股酸水湧到嘴邊,咬緊牙關不肯嘔出,硬是吞了回去。
鄭芝龍看在眼裡,道:「撫台大人,我軍操演已畢,請寬坐吧。海上風浪大,咱們待慣了的不覺有甚麼,頭一回上船都是這樣的,還是坐著舒坦些。」馮聲海則斥責小兵道:「慢手慢腳的幹甚麼吃的,快把水和盆子取來讓李大人淨淨口,伺候大人們吃醒船湯。」
張肯堂向施天福答個禮,算是校閱已畢,這才願意坐下。林文燦見己方三人大為失態,勉強開口破破氣氛道:「看來幹水兵也不是挺舒服啊。不過平日裡便這般操演,不嫌太費火藥了?」
施天福答道:「海上交鋒火砲最先,平日吝於操練,上陣時船讓敵人打沉了,火藥還不是都得白白泡進海水裡去。」
眾人一陣忙亂,三人總算緩過來些。鄭芝龍抱歉道:「大人們委屈了,還是進艙去避避風吧,咱們這就回頭。」一邊交代施天福慢慢返航。
張肯堂等人進了中艙官廳,猶難言語,或以手撐頭,或抱著胸腹,只盼望趕緊回到陸地上。
鄭芝龍等人見此光景,也不多打擾,自往另一個艙間喝酒談話去,留下鄭森陪伴三人以備有事時進來。鄭森走到隔壁,見無人影,登梯走上頂層,不由詫然,原本一望千里的朗朗海天,此刻卻成了白茫茫一片,幾丈之外即已影綽難辨,整艘船像是被塞在一大團棉花裡,與方才仿如兩個世界。
「果然起霧了。」施天福道。
馮聲海見鄭森上來,清咳一聲,刻意大聲道:「不知怎麼回事,忽然起得好大霧。」
「方才還是一碧萬頃,怎麼就霧重如此?」鄭森不解地問。
「海上風波瞬息萬變,森兒今日可親眼見識了吧。」鄭芝龍道:「冬盡春初,陽氣乍生,此間海面常有大霧,並非出奇之事。但似今日濃霧來得如此之速,卻也少見。」接著又向施天福道:「這霧實在太重,別撞了船了。」
張肯堂入了大堂,居中坐下,神色嚴峻,已非適才溫煦的老好人模樣。此番到安海來前,與一干幕僚智囊計議,當時頗有勸他不要親自前來的,怕萬一張肯堂調不動鄭芝龍,有失巡撫威信。但流寇在中原和西北各省奔竄,清兵又入關大肆劫掠,南北音信斷絕,國勢十分危急,因此張肯堂以巡閱為名,慨然動身前來。
他盤算著,福建、廣東兩省撥款給鄭芝龍募兵、造艦,若鄭芝龍有侵吞公款的跡象,便奏明朝廷查辦。若兵、船如實備辦,便責成鄭芝龍即刻出兵。
眾人依次在兩邊站定,鄭芝龍見張肯堂沒有讓眾人坐下的意思,故意打個哈哈,對李嗣京和林文燦...
作者序
序
二○○四年,我到日本九州平戶島上的千里濱海灘,去看一塊石頭。這塊石頭黑黝黝地,略作錐狀,無甚奇特之處。將近四百年前,一位姓田川的少婦,在一個細雨紛飛的日子獨自來此,忽然陣痛分娩,生下了一名男嬰。少婦為孩子命名福松,取其諧音等待幸福之意。
這孩子日後有個響噹噹的名號:國姓爺。
國姓爺誰不認識?從小,我們就聽說過他的各種傳說。他在台灣初嚐了一種好吃的魚,直問「啥麼魚?」從此這魚就被稱為「虱目魚」;他率軍到北台灣,遭遇劍潭魚精和鶯歌妖石,都一傢伙就給鎮殺了……我們的身邊,充滿了跟他有關的名號:國姓埔、延平路、成功大學。
曾經,他是矢志反攻大陸的民族英雄典範。等到標舉復國的年代過去,又聽說,大陸在鼓浪嶼立了他的像,讚揚他收復台灣。有人說他的功業是將台灣收入版圖,也有人說他在台灣建國立都,連日本人都說他是日本血裔海外雄飛的代表。在每個不同的時代,哪怕立場極端對立的不同官府,都要拿他來拉攏台灣民心。
這麼一來,不可避免地使他過於神格化,失去了作為人的面貌,且看清朝的漢臣沈葆楨連「創格完人」這樣到頂的話都搬出來了。可是他實際上脾氣壞得很,動不動就誅殺犯過的部將。他的部隊在海上無敵,卻非常不會打陸仗。他決定攻打台灣這件事,後世大加推崇,但當時人們認為他到海外便是放棄復國,是一面倒地反對的。
我站在平戶千里濱的「兒誕石」旁邊,回到他生命的原點上,忽然強烈地感受到他出身於海外的事實。我不由得奇怪,在反清復明這場「驅逐韃虜」的戰爭中,他一個倭人之子,怎麼能夠在整班漢人文武間建立領導統御的正當性?他的父親鄭芝龍是一代海上梟雄,他為什麼卻走上科舉的仕宦之路?
聚集在他身上的各種複雜衝突霎時鮮明起來:日本血統與中華衣冠、儒家道德與商業務實、追隨父親還是移孝作忠、海洋戰略對抗大陸思維……他實是個無比生動又富戲劇性的人物啊。而他所面對的命題,更是台灣人世世代代糾扯不清的困惑。
之後,我只要有機會就去走訪與他有關的歷史現場。我前往他少年以後的家鄉泉州安海、觀兵弈棋的金門山巔、立營整軍的廈門海港,當然還有台南安平──他最後悲慟於復國不成,抓破臉面,無顏見先帝於地下的辭世之處,我也一次又一次去了。
他寫的詩、題的字,所有關於他的歷史文獻記載,我讀了又讀。
我試著去理解他,理解他的冷風熱血、青年疑惑,以及比國破家亡更為沉重的,整個內在世界的天崩地解。他追尋儒道,而儒道不存。他欽仰父親的經世之能,而時代的浪潮將父親的生命和事業徹底捲走。他日夜渴念著分離十餘年的母子親情,卻只得短暫重逢便又天人永隔。
青年成為孤軍統帥,成為王,成為神,終於失去本來面目。
而在將他從神明還原成青年的追尋中,他與他的時代樣貌逐漸清晰起來。於是我寫下這個故事──一個名為鄭森的青年在無比綺麗,卻又詭譎無常的晚明世界裡衝闖碰撞。越是熱血澎湃越是激起無窮質問,越是腳步堅定越是走向悲壯的結局。
這是一次對他的人格樣貌之揣摩,也是一次對歷史的重新探索。
序
二○○四年,我到日本九州平戶島上的千里濱海灘,去看一塊石頭。這塊石頭黑黝黝地,略作錐狀,無甚奇特之處。將近四百年前,一位姓田川的少婦,在一個細雨紛飛的日子獨自來此,忽然陣痛分娩,生下了一名男嬰。少婦為孩子命名福松,取其諧音等待幸福之意。
這孩子日後有個響噹噹的名號:國姓爺。
國姓爺誰不認識?從小,我們就聽說過他的各種傳說。他在台灣初嚐了一種好吃的魚,直問「啥麼魚?」從此這魚就被稱為「虱目魚」;他率軍到北台灣,遭遇劍潭魚精和鶯歌妖石,都一傢伙就給鎮殺了……我們的身邊,充滿了跟他有關的名號:國...
目錄
第壹回 聞警
第貳回 抗令
第參回 請纓
第肆回 拜師
第伍回 訪社
第陸回 遊院
第柒回 勸友
第捌回 遇險
第玖回 諫兵
第拾回 離合
第壹回 聞警
第貳回 抗令
第參回 請纓
第肆回 拜師
第伍回 訪社
第陸回 遊院
第柒回 勸友
第捌回 遇險
第玖回 諫兵
第拾回 離合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7收藏
7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




 7收藏
7收藏

 8二手徵求有驚喜
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