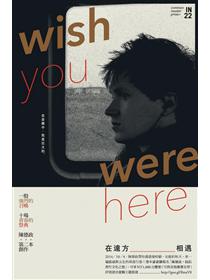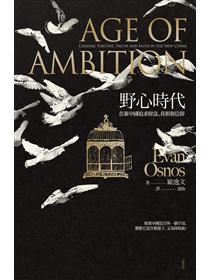我們以為自己是一個完整的人,殊不知剝離是邁向死亡必經之途。
身體的各個部位隨著年歲、意外,如同花瓣紛紛凋零。我們的肉體、器官終究難逃時間、空間的侵蝕而灰飛煙滅。郭漢辰藉由自己罹病、切除器官的經驗以及長久以來的鄉土觀察,創作出根植台灣文化瑰麗奇幻的短篇小說集。藉由各個器官剝離的想像,勾勒生命渺小的不安與惶恐。
「剝離人」的世界裡,我們活得卑微。只能輕聲探問:下一個離家出走的器官,會是什麼?
疲倦的〈舌〉
江知野猜想,可能是長時間的操勞,無法休息,才會逼迫舌頭採取罷工的激烈手段。
事到如今,江知野也只能這樣胡亂猜測。
當他的嘴裡傳出一陣劇烈的疼痛時,他趕緊跑進服務處洗手間,對著洗手檯上方那面泛起霧氣的鏡子,用力吐露舌頭,照了又照,彷彿自己的舌頭是個大明星,要用探照燈,將它照個仔細,讓它榮耀上臺,卻也要讓它光芒萬丈下臺。
鏡子裡,江知野發現自己的舌頭,竟然少了半截!
溫暖〈臂彎〉
她一直在他臂彎裡靜靜溫存,從未想過要從這個美夢裡甦醒。
她只覺得有些液體從他的臂灣裡絲絲滲出。
一直流入她想像中的港灣。
她拿起衛生紙,仔仔細細擦拭他的手臂與身體原本相連接的部位…
她低頭發現紅色液水是從這裡滲流而出,彷若一條蜿蜒的小河,一直垂流到他不長不粗的中指處,一滴一滴的液汁,像是流星般滴落了下來。
從她朝思慕想,那靈活而有勁的手指處,滴滴答答,如春雨般滴落下來。
真假〈雙腳〉
他一直認為他的一生及身體是完完整整的,毫無瑕疵。
直到醫師告訴他,右腳下半肢開始潰爛了,非得離開他的身體不可,他才知道身體發生了統一或者獨立的問題。
在醫院動完截肢手術之後的幾天,醫師遞給他一支碳纖材料製作的義肢,叫他和新朋友好好建立感情。
每當睡覺時要先脫掉義肢,但是睡到一半時,想上廁所,他還以為自己是完好無缺,根本忘了自己要穿上義肢,就惡狠狠地從床上站立了起來,結果右腳下半部沒有支撐,整個人像個紙娃娃摔倒在地板上,看到義肢剛好就在旁邊睜大著眼,笑得合不攏嘴,猛烈嘲笑自己的健忘。
下一個出走的,是誰?
書籍重點
手、腳、眼睛、舌頭,甚至靈魂
我們一路走來,一路剝離……
歡迎來到「剝離人」的世界。
遺落逃竄的器官在此宣告獨立,各表其志。
以器官、魂魄與身體的剝離、隔閡,書寫二十一世紀臺灣社會各階層的混亂百態。小說家郭漢辰企圖藉著這一系列短篇小說,探究生死之界、幽冥之隔,呈現現代人生命的詭奇與命運的幻變。我們就如同「剝離人」,空有完整肉體,隨時會有東西向外剝落,零散在外界,透露我們走到盡頭的心思與困窘的生命情境。
作者簡介:
郭漢辰
1965年生,屏東人,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碩士,目前專職文字創作。作品豐富多樣,跨及小說、散文、現代詩以及報導文學等各個領域。小說作品被臺灣文壇耆老葉石濤評選為首獎,知名小說家平路評論其創作「文字新穎靈動,人物面貌栩栩如生」。曾獲國內多項重要文學獎,以及國藝會、高雄市寫作計畫等,著有《封城之日》、《記憶之都》、《誰在綠洲唱歌》以及《剝離人》等小說集。
章節試閱
行走
天空下起細雨,陰沉灰重的雲,掠走整個眼前的視野。
他一個人走路,在K1號道路上走著。
道路右方海浪拍打岸邊,有時浪潮大些,鹹鹹的海水會噴打到道路上,一輛輛快速急駛而過的車子,在道路左方,如鬼魅魎影往前奔去。
他不知走了多久?
三十分鐘?
還是一個小時?
他沒有帶手錶的習慣,一直覺得人生,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手錶懸掛在腕上,像把一大串的歲月,沉甸甸地銬在手上。
他不喜歡這樣的沉重,這樣的負荷。
他如今只習慣看手機上的螢幕,從簡易的阿拉伯數字裡,了解現在是幾點幾分,像他這種人,不但不戴手錶,也不戴已婚男子一定要套上的結婚戒指,老婆為此叨絮幾句,老婆若有所思望著他光禿的手指頭,看得他心裡拂過一陣涼意。
他全身沒有一項身外物,除了衣服,只有放在褲子後方的COWA皮夾,以及口袋裡一支銀色光澤的三星手機。
他剛從車子爬行出來時,放在方向盤旁置物架上的手機,隨著汽車大力衝撞,往右方拋擲,它一頭撞破車窗的玻璃,跌落在車子右前方一公尺處,跌得支離破碎。
他走到大哥大身邊,發現它腦殼破裂,體內的微小片板,摔在道路上滾動著,手機失去生命跡象,往常會在螢光幕發亮的小光點,也消失無蹤。
他究竟走了多久?
雨一絲絲下著,下穿過他的身體,淋濕他的衣服。
雨勢不大,他往前方的路望去,在這條漫漫通往天際的道路上,從早上到現在,有薄霧輕盈浮動,雨絲輕巧越過飄起的霧。
他身上沒有手機,不能探看時間的挪動,無法報案說自己發生車禍,或是撥給老婆,說他在何處撞車,請老婆盡釋前嫌來載他。
前一天晚上為管教小孩的事,兩人又吵得互擲怒火,小孩還在旁邊嚇哭,吐出滿地汙黃的穢物。
早上他開車出來時,老婆無言看著他的車子遠去,他忽然記起有人說過,有些家庭成員性格不一樣,家就是把各種各樣動物,關鎖在一起的囚籠。
如果真是這樣,那老婆一定是暴烈的獅子,他是溫馴年老的老虎,年輕時偶而對獅子的攻襲還能回擊幾下,如今他只能病懨懨地低頭沉思,無法像往日那般風雲呼嘯。
他持續走著。
他到底在何處?
在K1線三一一公里嗎?還是二五一公里處?
他距離有人煙的地方,到底還有多遠?
他嘗試揮揮雙手,想呼叫路上穿梭來去的車子停下來,看有沒有人好心載他一程。否則用一雙腳,要走到什麼時候,才會到達有城鎮的地方呢?
沒有人願意停下車載他,所有的車子急急開過,像一道飛奔眼前的閃電。
或許這社會詐騙案太多,像最近每隔幾天,上午八點或是下午兩點,都會接到一個有大陸口音女子的電話,彷彿她很準時上班似的,有時在電話中告知他有法院的信函,放在郵局沒有人去拿,請他趕緊按1轉接。
有時那女子又化身成了某某國際銀行的好心總機小姐,說他的信用卡被盜刷,請他立即按9與服務人員連絡。
每次他都很有耐心聽完那女子所有的說話,再平心靜氣又輕巧地把話筒掛起來,讓那女子查覺不出,他早已知這是詐騙電話。
或許是這個緣由,沒有人停下車子將他載走。
人人都懷疑接觸的對方,可能是個詐騙者。車上如果有人看到他在路旁揮手,都會想這人或許是要來欺騙別人、陷害別人,大家對他人起疑心,沒有人可以被信任,只好留他一個人,在天涯海角的道路走著。
K1號道路很熟,他真的很熟。每天都要開這條路上班,沿著一面倚靠山壁,一邊可面向大海呼喊的道路,這樣開一個小時的車程,就可到達大城市某一棟大樓的第十二層樓上班。
每次上班感覺落差都很大,開車時,盡是在山海無邊無際的擁抱裡奔馳著。
只要車子一進入市區,卻被人類窄小世界的喧囂,團團包圍,這中間完全沒有緩衝區。在到達辦公室的一路上,幾乎看不見其他小城鎮,只有幾棟小房子零星地孤立著,像是要對著山海吶喊些什麼。
大部分道路的景緻,都是山與海、海與山的錯置堆疊。
他就走在這樣荒涼的路上。身上沒有手機,可以發出電波,上天下地連繫全世界。他也失去了可以駕駛的車子,與風互相追馳奔逃。
他只能走在山與海中間的道路上。
他無止盡走著。
多久沒有這樣,只用兩隻腳走路,就可走到天之涯,海之角?
他往好處想,也可逛逛這條看似熟悉,卻又陌生的道路。
他只要往右方一伸手,就可握住海浪的鹹度及溫度,往左邊看去則是無盡的峭拔壁,無法逃避的堅硬如鐵。
他應該和很多人一樣,國小三年級學會腳踏車,國中二年級會騎機車,大一那個暑假學會開汽車後,每段歲月都用不同種類的替代品,替換自己雙腳,奔走長遠的路,走路對他來說,變成很陌生的事。
他記得只有當兵走過那麼漫長的道路,第一次行軍時,班長叫他們放假要去買絲襪,因為要走很遠很遠的路,腳皮會被磨破磨出汙血來,那疼痛可是入骨入肉,最好的方法,要先穿一雙絲襪,再套上一般男生穿的襪子,然後再穿上軍用大皮靴。
他利用休假的時間,去買了女生絲襪,百貨公司專櫃小姐還很貼心地說,既然是行軍要穿的,不用買太貴,一般便宜的就可以了。
他沒想到,行軍那天,太陽整天生龍活虎地在天空陪伴著他們,一點也不懶惰,甚至從營區陪到隔一個山頭的海邊,烈日燒灼背部,都要成了香氣洋溢的烤肉。
到了傍晚,才有一點點烏雲,把那自以為是的太陽遮了起來。他不但流了滿身汗,單是雙腳那邊流的汗水,可能比夏季西北雨的雨量還要豐沛。
到晚上休息時,他把絲襪脫了起來,難聞的汗臭味,燻得整班的人都無法睡覺,隔天行軍時,他把絲襪丟到垃圾筒中,他一輩子不敢再碰那原本就屬於女性的物品。
那次行軍走了三天三夜,走過黑夜與白天,走到全身只剩下雙腳還在走,因為腳板早已磨破、滲血,腳還知道痛,身魂不知走往何處了,像此時的他一樣,走到天涯又海角。
現在呢?
他好像走了很久,應該沒有行軍那次那麼遙遠,行軍時無論走多遠,道路都綿延無盡,走到一處有人煙的地方,又是一條漫長的路延伸下去,自從那次後,才知道原來島國雖小,卻有著千萬條通往千萬個方向的路,永無止盡開闔,讓人們走著。
這次,也是走很遠很遠了,雙腳沒有嚴重的疼痛感,可能是其他部分早就有傷口。
剛剛從車子裡出來時,他發現有流動的液體,從額頭淌流下來,現在才有空,用手一摸。
「哇!」他驚呼是鮮血呢!食指中指沾滿黏答答乾掉的血塊。
好在數量沒有太多,如果像是潺潺溪水流下額頭,那肯定會嚇死自己。手腳關節處的衣服、褲子,都在車子撞擊時,摩擦出了破洞,想必這兩處肌膚,多少也有鮮血滲流,糊糊的血水,成了窩藏在衣褲內不願曝光的祕密。
疼痛在他手腳處,閃閃爍爍。
想到流血,剛走過一大段上坡路段的他,氣息有點喘不過來。
他卻想起二十年前,與第一個女友在她出租處的二、三事,在一個聞到彼此體味的夜裡,她嘴裡喃喃說有些痛啊,那個絲細的聲音,到現在還在他耳邊飄起。女友沒有拒絕他的進入,他後來看到床單有血水的滴痕,那是他第一次看到有血,從女人身體流出。
還有一個在他眼前流血,是他的母親。
母親患有肝硬化後,身體的五臟六腑,再也不言聽計從服膺母親的話了。食道是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母親的器官,汙黑色的血,從曲張的食道靜脈瘤裡爆發,往食道上方洶湧,最後從母親嘴內一口口吐出。
他用衣服、用毛巾、用母親床邊的棉被,都無法來得及擦拭從母親體內大量
奔流出來的血液。
另一個在鏡子之前,獨自流血的是他自己。
他老是無法刮乾淨自己的鬍子,他怪罪所買的電動刮鬍刀太便宜,刀鋒不夠犀利,無法很密實地刮完下巴所有的鬍渣子,不只一次成為上司、同事拿來做為訕笑他的題材。
他聽說手動刮鬍刀能斬草除根,有天他下定決心購買了它,他想雙手親自料理那些刮不盡的鬍渣子,以免春風吹又生。
手動刮鬍刀的確有它的殺傷力,右手推輾過去,鬍渣都躺平斷根,不過,不知他是否用法錯誤,還是哪裡出了差錯,就算他抹了刮鬍膏,還是無法阻止刮鬍刀刮傷自己下巴,有時傷口出現在上嘴唇,有時被刮破的傷口留在下嘴唇,被刀鋒切開了小洞,鮮血汨汨流出,雖然出血量不是很大,總有兩三個小傷口擱在那裡,像被小針刺了一下,傷口痠痠痛痛。
在浴室的鏡子之前,他看到自己在流血,從下巴的好幾處小洞,冒出微微的小湧泉,湧出他自己的鮮血。
他必須想想這些事,才能繼續走下去。
回家的路還很長,開車走這條路就要四十分鐘了,走路一定更久。
他到底要走多久,才能走回到家?
他也想過,直接在路上攔一部計程車,讓計程車直直穿越這條他的上班公路,快速地送他回家,他可以馬上躺在軟綿綿的床上休憩。他發現皮夾遺留在車上,身上沒有錢,只好打消這個念頭,在這個資本主義時代,沒錢萬萬不能,口袋裡只有幾個一元、五元的硬幣,可以供他撥打公共電話,但一路走來,沒幾棟房子和他打招呼,更不用說公共電話筒,會突然出現在自己眼前。
他真的走得有些累了,停下來看看大海。
鹹鹹的海風,從木麻黃林裡徐徐向他吹來,吹得他額頭上的傷口有些發疼。
他就這樣坐在路邊,一動也不動休憩著。
說不定老婆及上班的公司,會向警方報案,可能沒有多久,警車就會沿著這條道路停停看看,那紅色的警示燈,會一直鳴叫著,直到找到他為止。
警察會發現一個四十歲快要沒有工作的中年男子,呆坐在路旁突出的路欄上,警察會不會問這名男子:「喂,你為何從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對著大海沉思呢? 」
他是一個很實際的男人,浪漫五分鐘就夠了,文藝細胞不用太多。他曾幻想過自己是作家,曾經在那年夏天,寫過一篇男子一直在走路的故事,沒有人要刊登,他也不想再投稿,就差有人當面和他說破,當面宣布他不是作家,叫他不要再寫這些廢物了,直接丟擲給垃圾筒閱讀比較迅捷。
但他的雙腳還是要走著,他還是只想順著這條路走回家,其餘事情都是白費
力氣。
他一個人還在K1號道路上,前進著。
有些灰濁的海在右邊,中央山脈最後支脈形成的小山丘,孤零零站立在左邊方向,獨自觀望著大海,彷若都是他熟悉的老友,他們卻都沒有走下來看他,只讓他一人孤單地走在山與海的交會。
多久沒有這樣,只用兩隻腳走著?
他忖問著正在走路的自己。
這漫長長的道路,第一個有人煙匯聚的地方,開始在他有些矇矓的眼前隱隱約約浮現。
大約有兩三棟平房,灰色的建築,還有一個搭乘客運的亭子,在海風吹拂之下,抖顫顫地矗立前方,隨著他腳步愈來愈近,房子開始放大,從迷你的小屋,變成了真實生活裡的房子。
一個阿嬤坐在雜貨鋪前的藤椅上,在他眼前,一口口吐出鮮紅檳榔汁液,彷彿他從來不曾存在似地。
他繞過望天望海的阿嬤,自己站立在販售各種飲料的大冰箱前,他多想喝個礦泉水、蘋果西打、紅茶,只要是喝點有水分的東西都可以。他的血糖比一般人還高,很容易就口渴,走路走了一個多小時,到現在一滴水都沒得喝,自己像一個迷路在廣闊沙漠的旅人,許久許久沒水可喝,只要嘴唇沾一點點水,都可以獲得解決。
可惜自己連一百元都沒有,口袋裡摸來摸去,他只剩四個五元硬幣,七個一元硬幣,加一加身上的錢,他最多只能喝一瓶飲料,那就喝礦泉水好了,他心裡做著決定。
「老闆,一瓶礦泉水。」他探頭對著雜貨鋪裡面喊著。
就在他掏找零錢的那一瞬間,那個阿嬤一眨眼不見蹤影,雜貨鋪空空盪盪,連一個鬼影子都沒有,不要說是人,那個阿嬤呢?怎麼忽然不見了,他是真的遇到鬼,還只是運氣不佳?剛碰到的人,從空氣裡憑空消失。
「有人在嗎?」他連喊了數聲,雜貨鋪裡無人回應。
他走進雜貨鋪,各種物品堆堆疊疊,有些箱子堆得比他還高,店面後方還有一個房間,床鋪凌亂,棉被攤開,可見有人剛躺過,電風扇還獨自發出喧鬧的機械聲,不停左右轉動,桌子放著幾顆剝開來的檳榔,等著主人往口腔裡塞,住在此處的這個人,應該剛剛才離開,他彷若可感受到那人的溫度、身體的味道,迎面吹來。
他走回店面,考慮還要不要走下去?還是先喝一口水?
他打開冰箱,拿出一瓶烏龍茶,右手用力拉開瓶罐上的環扣,趕緊往自己嘴裡,灌進一口又一口的金黃色液體,他實在渴死了,彷若在沙漠行走了數十天,不曾喝入一口水,行走長途的路,把他體內的水分全都抽乾了,讓他渴得如一片乾旱的田,急須狂飆的大雨,來個天降甘霖的快感。
他喝完飲料,精神又來了,彷若裝滿汽油的車子,可跑個百里千里。再出發前,他先到這聚落附近的房子看看,還是一個人影都不見,人們好像都被匿藏了起來,他無法看見他們,碰觸不到他們,自己只好行走回自己的方框世界裡,這樣也好,一個人行動也自由些,他又走回了雜貨鋪,看見店門口,擺著一具公共電話,他掏找出硬幣投了進去,撥打著老婆的電話。
他撥打家裡電話,只聽見聲嘶力竭的鈴聲,在話筒裡一生一世響個沒完,他只得再撥打老婆的手機,耳裡響起了流行歌曲的聲音,什麼愛你一萬年、愛你一千年。
他心裡想著,只要愛得滿一百年就很厲害了,超過百年人早成了飛灰,哪裡還會愛?他發現家裡電話、老婆手機都沒人接,或許老婆送完小孩,已出去上班了。
他愛老婆嗎?生活幸福嗎?
這個問題難以回答,不知多久沒有和老婆交合,性交是夫妻唯一可以討論及共同投入的事嗎?
那幸福這檔事呢?好像早已化成雲煙。
他想起大學時讀過一個哲學家改寫的希臘神話,說一個叛逆的天神,被天庭處罰要把大石頭推上山,卻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每天大石頭快要接近山頂時,又嘩啦嘩啦地滾下山。
結婚後,更多瑣碎的日常生活,滾成了一塊青苔滿滿的大石,他光推著這顆大石上山,就氣喘吁吁,上氣接不到下氣。哪有時間管和老婆的床笫之事?
他到現在都覺得這個比喻很貼近。
每天一張開眼睛,生活的大石就滾到身旁來,向他說聲︰「哈囉,請你把我推上山。」
在這一整天的過程,大石頭化身成生活的各種面貌,你得接孩子上下學,看到老闆變天般的臉色,你得低聲下氣,好好看管住那隻要躍出胸膛外咬死老闆的野性老虎。佛祖保佑,千萬別讓牠衝跑出來。
到了傍晚,你以為工作完成了,把石頭推到峰頂置放了,安心地去接小孩回家。不料,那塊大石卻在電光火石間,二話不說從山頂飛滾下來,一點警告都沒有,大力輾壓過自己,自己成了一塊扁扁無法恢復正常的肉塊,他真是一個澈澈底底的窩囊廢,他這樣覺得。
行走
天空下起細雨,陰沉灰重的雲,掠走整個眼前的視野。
他一個人走路,在K1號道路上走著。
道路右方海浪拍打岸邊,有時浪潮大些,鹹鹹的海水會噴打到道路上,一輛輛快速急駛而過的車子,在道路左方,如鬼魅魎影往前奔去。
他不知走了多久?
三十分鐘?
還是一個小時?
他沒有帶手錶的習慣,一直覺得人生,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手錶懸掛在腕上,像把一大串的歲月,沉甸甸地銬在手上。
他不喜歡這樣的沉重,這樣的負荷。
他如今只習慣看手機上的螢幕,從簡易的阿拉伯數字裡,了解現在是幾...
作者序
【序】 完整與破碎之間
我在離家不遠的路上,撿拾到自己遊走的靈魂、一隻孤單的胳臂、一截滴著血的小腿,還有半條正在逃命的斷舌……
我有些驚訝,眼睛張瞪得老大,右手大力揪擰臉頰,我想試看看,這究竟是不是一場夢?
我最後會不會從夢裡,因痛得尖叫而甦醒過來?
人生路上一路走來,像上述那樣的畫面,一場場如真似幻的夢境,天天迎面襲來。它既讓人們擁有真實的苦痛,又讓自己像在夢境裡,如常行走且生活,卻在有一天,讓我們措手不及,開始逐一失去。
我母親在世時,因為肝硬化而膽囊發炎,昏倒住院,醫師展開緊急手術,將她嚴重發炎的膽囊切除。十多年後,丈母娘胃癌末期,醫師同樣摘除她三分之二的胃。
我們這群家人在手術室外痴等苦等,等到卻是醫師拿出一只冷冷的金屬盆,躺在那上面的是血淋淋被剛切除的臟器。醫師還叫我們心底不要害怕,用手指去碰觸那沒生命氣息的器官,「你有沒有摸到那些硬如石頭的部分?那就是癌細胞,它們在體內築起堅硬的城堡,抵擋好細胞的反攻。」
我萬分詑異地看著醫師年輕白皙的臉孔,看樣子他不會超過四十歲,一生極為平順,家庭生活美滿,未曾遭受工作挫折,也沒有與親人有過揮灑淚水的生離死別。
醫師比誰更懂得癌細胞的意義及結構。但是他不會了解,它們不是異形,它們不是增生細胞,它們是我們摰親血肉的一部分,它會與人們一同壯烈赴死。到時家人的心,會被刀切千片萬片,痛不欲生。
不只是家人,而是每個人都得忍受生命末日來臨的那一剎那。那時人體內天崩地裂,洪水火山泛濫爆發。身上一個又一個部位,紛紛掉落,如同命運裡的流星雨,如霧亦如電地,奔灑在這塊大地上。
這正是此部小說的創作核心。生命裡有太多的欲望或想像,讓許多的「個體」,紛紛從主體裡陸續「剝離」,那些失去的東西,多得讓我們無法拾回。
我們的靈魂與肉體澈底分離……
我們的手臂與身體道聲莎喲娜拉,從此不相見……
我們的雙眼從眼眶裡躍跳而出,一跳跳到街頭,外宿不歸。
我們的雙腳及舌勇敢切斷與主人的關係,走出專屬自己的生命大道。
我們一路走來,卻一路失去,那麼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這就是人生及文學最玄妙的地方。既然身上的所有,都註定被命運「剝離」,最後人們更只會剩下一堆風吹來就會灰飛煙滅的灰粉。我們還是能使用文字和想像,將失去的生命,逐一彌補回來。
遠古時期,女媧用五色石修補被神明撞壞的天地,我們何嘗不能用愛與記憶,將散落在地上的四肢和肉塊,一一撿拾,重新造人,讓我們和摰愛的家人,在有限的時空含淚相聚。
或許真的有一天,我會在離家不遠的路上,撿拾到自己所有走失的手腳眼睛舌頭等,都安好地躺放在我即將經過的路上。
我一定會用盡方法試看看,這究竟是不是一場夢?
這真的不是夢,雙手先蹦跳到我眼前,將癱軟在地上無法站立的我,輕輕地扶了起來。雙腳接著自動來到我的膝下,與我的大腿切割處完美接合。眼睛也浪子回頭了,重新住進凹陷的眼眶。始終想獨立的舌頭,還是得回到口腔,才能安心立命。
只不過,人生終究是夢一場,在我的身體重新合體後,我到頭來還是只能再賴活個一二十年。
到了那時候,不,應該就是這幾年,我還是會摧枯拉朽癱成一地的肉泥。
到時請別忘了叫我一聲:
「剝離人。」
【序】 完整與破碎之間
我在離家不遠的路上,撿拾到自己遊走的靈魂、一隻孤單的胳臂、一截滴著血的小腿,還有半條正在逃命的斷舌……
我有些驚訝,眼睛張瞪得老大,右手大力揪擰臉頰,我想試看看,這究竟是不是一場夢?
我最後會不會從夢裡,因痛得尖叫而甦醒過來?
人生路上一路走來,像上述那樣的畫面,一場場如真似幻的夢境,天天迎面襲來。它既讓人們擁有真實的苦痛,又讓自己像在夢境裡,如常行走且生活,卻在有一天,讓我們措手不及,開始逐一失去。
我母親在世時,因為肝硬化而膽囊發炎,昏倒住院,醫...
目錄
髮絲
舌
臂彎
瞳
雙腳
剝離人
胎音
巢
洞
後記 食夢獸的孤獨書寫
髮絲
舌
臂彎
瞳
雙腳
剝離人
胎音
巢
洞
後記 食夢獸的孤獨書寫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5收藏
5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




 5收藏
5收藏

 1二手徵求有驚喜
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