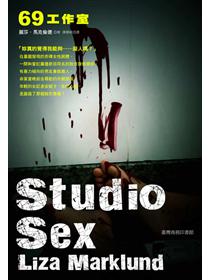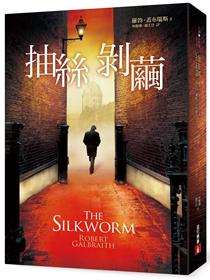她以為逃離就能躲避傷痛,沒想到卻一步步走向無可挽回的悲劇
★讓《別相信任何人》作者SJ‧華森徹夜未眠讀通霄!
★已授權四種語言版本。
★以主角艾莉克絲的倒敘與某位學生的日記雙線並行,交織出一部構思聰明、布局精巧,令人越陷越深的心理懸疑作品。
★隨著故事逐漸清晰,讀者將會發現處處呼應著希臘悲劇的元素:當艾莉克絲一邊進行自我療傷,一邊帶領學生踏入古典文學的殿堂,卻也逐步啟動了一齣難以歸咎、引人喟嘆的悲劇!
她不明白,事情怎麼會演變成這樣。在那之前,她是劇場界倍受矚目的新星,正要與此生最愛的人展開人生的新頁。一切美好,在某個尋常的下午,完全變了調。
她倉皇逃離倫敦,孑然一身來到愛丁堡,在一所特殊學校任教,這裡專門輔導被其他學校開除的學生。她帶領學生閱讀古希臘悲劇,從逃不過弒父娶母神諭的伊底帕斯王,代夫受死又被拯救的阿柯絲提斯,到阿加曼儂王兩代的冤冤相報,劇中殘酷的命運,血腥的復仇,終極難解的命題彷彿打開少年少女們的心,給了他們討論情緒與自身處境的契機。
她原以為已放下傷痛,但她眼神中的哀傷,竟引發學生們的關切與好奇,有人開始跟蹤她,挖掘當初迫使她離開倫敦的殘酷真相。當她發現,奪取他人幸福之人,竟能幸福地邁向未來,她決定要有所行動。而這計畫,只有她的日記知道……
作者簡介:
娜塔莉‧海恩斯(Natalie Haynes)
古典學者與作家。評論家,點評範圍涵蓋書籍、影視與藝術,也擔任BBC第四電台的Front Row與Saturday Review節目的評論者。她為電視與廣播寫作及講述過的主題極為廣泛,包括希臘悲劇與電視肥皂劇的關連、吸血鬼與殭屍各自的優點等。也在《獨立報》撰寫每週專欄。非文學著作The Ancient Guide to Modern Life於二○一○年由Profile出版,大獲好評。她曾擔任二○一二年柑橘獎評審,目前是曼布克獎的現任評審團之一。她也曾是單口相聲喜劇演員,後來發現自己喜愛悲劇甚於喜劇,故而退休。
譯者簡介:
方淑惠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從事翻譯十餘年,譯有《你出生那天,就是我的父親節》、《濟貧院的陰影》、《大藍海洋》、《美少女祕密成長日記》等近三十部作品。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我徹夜未眠,將《琥珀的憤怒》一口氣看完。這個故事引人入勝、扣人心弦,讓人一頁接著一頁停不下來,字裡行間洋溢著仁慈與溫情。
──SJ‧華森(S. J. Watson,《別相信任何人》作者)
海恩斯的第一部作品不僅是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的驚悚小說,更以優美的筆觸描繪出哀痛及重拾生活秩序的過程。此外,她也透過本書讚頌古典文學及教學,如實呈現充滿挑戰性的課堂所具有的緊張與趣味節奏。我很喜歡。
──瑪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阿基里斯之歌》作者)
情節緊湊,時而哀戚、風趣,時而極其悲傷,海恩斯的故事就像一條河流,讓讀者順流而下,來到瀑布,彷彿被催眠了一樣。
──喬斯‧溫登(Joss Whedon,《魔法奇兵》創作人、《玩具總動員》編劇)
海恩斯擅長描寫人物之間的互動,對話充滿活力,筆下的角色彼此對話時極有魅力……或許這本書適合改編成劇本!
──《衛報》
這部小說模仿五幕劇的形式,如希臘悲劇作家歐里庇德斯著重在情緒與女性角色,還有熟悉的主題:命運、復仇、暴力、愛,還有背叛與挫折。
──《獨立報》
名人推薦:我徹夜未眠,將《琥珀的憤怒》一口氣看完。這個故事引人入勝、扣人心弦,讓人一頁接著一頁停不下來,字裡行間洋溢著仁慈與溫情。
──SJ‧華森(S. J. Watson,《別相信任何人》作者)
海恩斯的第一部作品不僅是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的驚悚小說,更以優美的筆觸描繪出哀痛及重拾生活秩序的過程。此外,她也透過本書讚頌古典文學及教學,如實呈現充滿挑戰性的課堂所具有的緊張與趣味節奏。我很喜歡。
──瑪德琳‧米勒(Madeline Miller,《阿基里斯之歌》作者)
情節緊湊,時而哀戚、風趣,時而極其悲傷,海恩斯的故事就像一...
章節試閱
1
他們首先問我的第一件事,是我如何認識她的。當然,他們早已知道了,這絕不是他們提問的目的,絕對不是。
我記得路克受訓時曾告訴我,如果你已經知道答案,就只會問一個問題。律師不喜歡意外,更別提會留下紀錄的意外。他們之所以提問,不是因為想知道日期、時間、地址等所有的細節,我相信他們會先做好功課,他們早就與羅伯特、也就是我的前老闆談過,知道我何時抵達愛丁堡,從哪一日開始上班。他們可能還掌握了我的行事曆,甚至可以說出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幾時幾分。
他們之所以提問,不是想知道我說了什麼,而是想知道我怎麼說。我的視線會飄向右邊還是左邊?我是在回憶或是在編造謊言?他們會依據其他證人的證詞衡量我的說法,評估我是否能信賴、抑或是在撒謊。
所以他們提問時,我不會翻白眼,也不會抱怨他們浪費我的時間。我不會告訴他們,要我回想整件事幾乎讓我難以忍受,每當有人問起,我都必須再次重新經歷一切,幾乎讓我無法承受。我不會問他們知不知道一肩扛下所有責任是什麼感覺,我不會爭論這點,這麼做一點幫助都沒有。
我會淡淡地吸一口氣、直視前方,將真相告訴他們。我不能緊張,不能滔滔不絕地說前往愛丁堡原本不在我的計畫之內。我不會要求他們記得我遭遇了什麼事,究竟為何要逃離倫敦,為何要來蘇格蘭。我不會提醒他們,我對於會發生什麼事毫無頭緒,也無法預期事情會演變得如此糟糕。此外,就算我能預料,當時的我也不在乎,那時我什麼都不在乎。
我只會盡可能簡單回答:我是在二○一一年一月六日,於朗凱勒街五十八號的地下室和他們見面的。而我沒料到他們當中有人會做出如此駭人聽聞之事。
當然,或許並非全然如此。即便以收容所的標準而言,這群人也相當難纏。羅伯特早已警告過我他們不好應付,因此我原本就不抱過多期望。
我在開學前一天到朗凱勒街的學生收容所與羅伯特見面。整棟樓除了我們以外空無一人,但我得拿表格、檔案與註冊名單。這些文件上大多貼滿了便利貼,註明孩子們的姓名與健康狀況。乍看之下,至少有一半的孩子都對某些東西過敏,包括堅果、花粉、空氣污染、麩質、霉菌孢子等。
我將羅伯特剛交給我的檔案翻閱了前幾頁後表示:「他們好像不是很健康。」他的辦公室是一間挑高的大房間,但優雅的空間比例被一道隔間牆一分為二;其中一半是他祕書的辦公室,裡頭擺滿了檔案櫃,櫃子前放著她整齊的辦公桌。她的電腦擺在書桌一角,對角則有三個網籃層層相疊,上頭分別標示著「入學」、「離校」、「未決」,所有籃子都空空如也。籃子旁有張照片,照片裡兩個黑髮小朋友站在滂沱大雨的湖前咧嘴而笑。相框顯然是手工自製──以鮮豔但歪七扭八的紫色黏土捏成──想必是相片裡其中一個孩子的作品。
羅伯特的辦公室與辛西亞辦公室截然不同,就像陰陽兩極。所有平坦的地方都放滿了塞得鼓鼓的檔案,包括地面。檔案夾上堆著隨意撕下的紙片,紙上寫著姓名或名字縮寫。辛西亞辦公室裡唯一的光源,是天花板上那顆發出淡綠光的長壽燈泡,而羅伯特的辦公室裡則有兩扇上下拉開式的大窗戶,從窗戶向外望,可以看見朗凱勒街的街景。向左遠眺,薩里斯貝里崖映入眼簾,黑色的峭壁怒視著愛丁堡,提醒你在這裡千萬別胡鬧。兩扇窗戶都掛著彷彿劇場裡看得到的厚重窗簾,暗紅色的褶層上積了薄薄一層灰,褶層後是狹窄曲折的窗簾軌道。有人曾經用吸塵器清理過窗簾軌道,但似乎還沒清完便中途放棄了。
「上頭寫的一個字也不要信,」羅伯特氣喘噓噓地說,不停在辦公桌、茶几與廢棄壁爐上的壁爐架之間來回尋找資料,努力確認他沒無遺漏任何寫著「艾莉克絲」、「A.M.」或類似名字的文件。「我是說,還是要信啦,」他改口說:「不要朝他們丟花生或叫有氣喘病的孩子去爬樓梯來測試那些記錄的真假。不過妳放心,艾莉克絲,這些孩子不會被區區一個過敏打倒。當然,這些細節都是醫生與社工在評估他們的特殊教育需求及問題時提出來的,所以我們必須完整保存各項記錄,就算是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細節也不能遺漏。」他低頭看了手中的檔案一眼,「不過我懷疑,妳班上的珍妮‧史崔會因為對荔枝過敏而遇到什麼大災難。畢竟你還得大費周章在這座城市裡找到荔枝才行。真讓人懷疑他們到底是怎麼發現她有過敏的。等到這些孩子熟悉妳之後,大多數都很好相處。有些孩子可能比較不喜歡戲劇或戲劇心理治療。妳也知道,有些孩子很有自信,有些則是比較害羞。」
「這裡收了多少孩子?」我看著散亂的文件問他。這間收容所是由四層樓的連棟大樓改建而成,黃磚已經被塵土染黑,這棟樓裡不可能有空間容納這許多表格所代表的兒童數量。
「這裡一直維持約三十名孩子,不過很顯然的,他們來來去去。我猜想在開學第二週之後,會有新學生轉進這裡。但同時,我們也會失去一些孩子。」
「失去?」
「朗凱勒街是慈善機構。那些其他地方不願意收留的孩子都會來到這裡。多虧有資助人幫忙,我們才能收容一些不被體制接納的孩子。他們大多都至少被退學一次以上,不過我們也會收留一些尚未被退學的孩子。」他開始在桌上的一堆文件裡翻找東西。「他們的家長或監護人向我們提出申請,如果我們認為幫得上忙,而且是真正的幫忙,就會努力騰出空間收容他們。當初能獲贈這棟樓以及資金,就是因為我們奉行的入院圭臬受到肯定:我們不收僅是在學業方面有困難的孩子,因為他們還有其他許多選擇。我知道這些選擇並非都很理想,但確實存在。」他終於找到想找的東西:一枝破爛的百樂原子筆,他用這枝筆在左手拿著的檔案上潦草地寫字,同時一邊說話。「我們收容那些無法適應其他地方的孩子,無論理由為何:他們可能曾被霸凌,或霸凌過別人,或是在團體中格格不入,或有其他原因。我們收容的是能真正被我們感化的孩子。但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讓這些孩子重新回到主流學校。所以,老實說,當孩子一進來這裡,我們就要努力讓他們盡快離開。有時候,這方法還真的奏效,」他解釋,「但不一定每次都順利。不過有些孩子在其他學校的適應情況比在這裡更好,因此我們也會失去一些孩子。妳知道,就算是安全網也有漏洞。」
我點點頭,揣摩羅伯特究竟是什麼意思。他總是這樣:老是以為別人跟得上他的思考邏輯,但其實別人根本辦不到;至少我就是。
「不過通常每學期不會超過一、兩個人,」他補充說:「除非那個學期的情況特別糟。」他的視線從半月形眼鏡的上方看向我現在努力依序整理的文件。「這一班,」他伸手過來用原子筆的另一頭戳了戳其中一頁文件說:「對妳來說或許是最難纏的。」
「為什麼?」那張紙上頭只列了五個名字,是四年級生組成的小班級。我在腦中算了一下:十五歲大的孩子。他又遞給我三個檔案夾,我依照看似合理順序排安插這些檔案。如果我能搞定文件,或許也能掌控一個班級。現在每一班都有一系列的檔案,這些孩子根據入院年數分別組成班級,一共有五班。我看著一長串陌生的姓名,納悶要多久才能將這些名字與孩子們的臉對上。羅伯特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想這應該是最後一個,艾莉克絲,」他說。「我不想騙妳,他們真的是一群小混蛋。不過別擔心,妳遲早能抓住他們的心。我不會把每個孩子的所有文件都交給妳:這樣只會增加妳的壓力,讓妳覺得必須看完所有的資料。妳需要的資料都在妳手裡了,如果對哪個學生有疑問,再來要他們的完整檔案吧:辛西亞會把妳能看的檔案交給妳。不過這些孩子不應該因為過去的記錄被當成犯人看待,所以等真的有必要知道更多資訊時再來要檔案。」
我想問他沒交給我的那些檔案裡可能包含哪種資訊,但他已經話鋒一轉,講起別的事情來了。他就是我媽所說的蝴蝶型跳躍思考:總是提起某個話題,然後別人還來不及跟上,他又跳去另一個話題了。這種情況原本會讓人覺得火大,但他總是熱情十足,讓人想跟上他的思考速度,而非氣他丟下自己逕自講起別的事情。他總是這樣,早在我還是個學生,他在喬治廣場的大學裡教戲劇時就是如此,如今我坐在他那張粗花呢布面椅子毫無裝飾的扶手上,當年上課的教室就在離這裡不到兩公里遠的地方。他是學生夢寐以求的那種老師:熱情、激動、風趣,圓胖的身材給人一種親切和藹的感覺,但只有在學生準時交出列印整齊、附有完整參考資料的作業時才是如此。雖然如今他的紅髮已褪為灰白的赤棕色,臉上也多了好幾條皺紋,但看起來依舊有年輕時當演員的架勢。即使現在收容所尚未正式開學,他仍穿著三件式西裝配上格子花紋背心,就像是婚禮上獻唱的男中音,只是合唱團的其他成員暫時失蹤了而已。這還只是他平時的休閒穿著。我低頭看著自己的牛仔褲,上頭沾滿了從我手中文件落下的白色小紙屑,像是骯髒的五彩小碎紙。
2.
我聽從羅伯特的建議,在下一次替那些四年級生上課前去了一趟布萊克威爾書店。我又買了幾本書,包括索福克勒斯 的劇本選集《海鷗》,同時努力回想自己十五歲時喜歡看什麼書。我父親是家裡的戲迷:每次有新戲上演或老劇重演他都會買票。他的書架被滿滿的亮面劇場節目表和劇本壓彎。我現在已經想不起來當初是如何選擇想看的戲劇:也許是看劇名吧。那都已經是十一年前的事了,總之,我在他們這個年紀時和他們截然不同──從來不惹老師生氣,更別說被學校開除了。但我們一定至少有一個共通點。我掃視著書架,努力猜哪一部劇本能吸引他們。
我剛搬來愛丁堡時最不喜歡這裡的一點,就是一般筆直的道路老是在改名字,彷彿是有一長串不在場證明的罪犯一樣。北橋改名為南橋,南橋改名為尼可森街,尼可森街變成克勒克街。我老是記不清楚轉車的地點,所以就連對主要公車路線也是模糊而不確定。現在我來到克勒克街,但看到空店面增加,就連二手慈善商店也減少,心情因而變得低落。我向左轉來到朗凱勒街,走向這條路的盡頭,抬起頭看到亞瑟王座山陰沉地矗立在前方,雲層環繞著山峰。這座火山早已成為死火山,但陰沉的樣貌始終未變。收容所是這條路盡頭的最後一棟建築物,旁邊是一家小報攤,想必主要的營收來源是向收容所的學生賣薯片和香菸。
我看到五位四年級學生都到齊,既鬆了一口氣也覺得訝異。
「哈囉,又見面了。」
他們咕噥著坐到老位子上。
「根據安妮卡的建議,我帶了一些劇本來給你們,」我說。瑞奇重重嘆了口氣,他今天在嬌小的身軀外罩了一件寬鬆的綠色橄欖球衣,衣服隨著他吐氣平貼在他胸口。他穿著這件球衣瑟縮在位子上,顯然覺得冷,起滿疙瘩的手肘又粗又紅。
「抱歉,瑞奇。我知道你比較喜歡上美術課,可是我們一定要上戲劇課。班上多數同學都比較想上戲劇課,這也是我來這裡教書的目的。」他回頭看著同班同學,想找出在他背後陷害他的人。
「如果你想畫圖或畫油畫,儘管去做。我們上課的時候會討論戲劇,可是我希望你下課之後也能做一些功課。」
喬諾揚起眉毛,我知道這個希望成真的機率很渺茫。我繼續對瑞奇說話。
「你可以把畫圖當成回家作業交給我。其實這樣還挺不賴的。」
「挺不賴的……」雖然我似乎安撫了瑞奇,但喬諾卻開始偷偷學我說話。我發現這是和這些孩子打交道最困難的部分。為了安撫其中一個孩子,我勢必會引起另一個孩子的敵意,即使他們表面上都是朋友。我其他班級的學生也是如此,不過他們通常都比這一班的學生好應付。總是會有人覺得不公平。
瑞奇在位子上乖乖坐好,開始在他的練習簿背面隨手亂畫。
「我們一起選一部劇本來讀。你們喜歡哪一部?莎士比亞?莫里哀 ?契訶夫 ?」我一本接一本將這些書拿起來給全班看。
「妳說的那些都只是字而已,」瑞奇說。「老實說,連字都不是,只是雜音而已。有什麼差別?」
「那些劇本很難嗎?」喬諾問。「我們應該選最簡單的一本。」
「為什麼?」
「因為那最簡單啊,」他說完搖搖頭,彷彿我是個笨蛋。我敢說他也是用這種態度對他的父母,我一定比他的父母年輕至少十歲,但他這種態度讓我覺得自己很老。我試著替自己解釋。
「困難的劇本有什麼不好?你們很聰明。大家都跟我說你們五個人很聰明。為什麼困難就一定不好?」
他面無表情地盯著我,我也盯著他。我開始明白這就是愛丁堡的孩子溝通的方式。我原先以為朗凱勒街的孩子都會說黑話,像倫敦的孩子一樣──不分階級或貧富,用的都是完全特殊的方言,完全只是因為他們想用大人聽不懂的語言對話。但在這裡,青少年的用語中規中矩多了,感覺彷彿回到了過去。不知道老師不在教室時,他們是否也是這樣說話,還是因為有人盯著才影響了他們說話的方式。無論是哪一種情況,他們似乎只有兩種設定:成人的說話方式,或是盯著對方和咕噥。
「這只是常識,」他嘆口氣說。「困難代表無聊。」
「哪時開始有這種說法的?你選電玩的時候也是選最簡單的嗎?」
「當然不是啊。那樣我一天就玩完了。妳知道那些電動要四十英鎊耶。」瑞奇聽到這句話開始竊笑。後來我才從教基本技能的老師那裡得知,這兩個男生都因為順手牽羊而被禁止進入聖詹姆斯中心,也就是新城區的破爛購物中心。
「好,那我們就用這種態度來看這些劇本吧。假設困難並不代表無聊,而是表示你必須多花一點心思,這樣你會比較喜歡。」
「電玩和功課又不一樣,」他說。「這很明顯吧。」
「幫個忙,假裝兩者是一樣的嘛,好不好?只要一陣子就好。」
我心想這堂課是不是即將有人要率先走出教室了。但喬諾仍坐在位子上,梅兒出於同情,替我打破了尷尬的沉默。我心想她是否可以感覺到沉默的好壞差別,還是她只是想說話就說話而已。
「不要莎士比亞,」她搖搖頭說。「我在以前的學校讀過羅密歐與茱麗葉。那個帥哥中間就死了。」
「帥哥是指莫古修(Mercutio)?」我想確認。
「對啊。莎士比亞殺了他,只是為了讓羅密歐看起來比較沒那麼像廢柴。」
「他是黑人嗎?」卡莉問。「他很帥耶。」
「黑人?」我問。
「在電影裡啊。就是李奧納多‧狄卡皮歐演的那一部?」
「噢,對。莫古修是黑人。」他們終於對某件事感興趣了,即使是電影改編版也無妨。
「我也不想看莎士比亞,」瑞奇說。
「好,那就不要莎士比亞。」他們當然不想看莎士比亞。要他們在學校看完馬克白,恐怕會讓他們無聊到哭。「那現代的劇作家怎麼樣?」
「像是誰?」
「我們可以選《耶路撒冷》(Jerusalem),」我拿起為他們買的最新劇本。「裡頭有很多髒話喔,你們可能會喜歡。」
「劇情是什麼?」喬諾問。
「是在講一個住在拖車裡的人。議會想把他趕走。」喬諾被紅色的封面以及一個男人抽大麻菸的照片吸引,伸手過來從我手裡接過那本書。
「看起來不賴,」他說完把書翻過來看封底簡介。「等等,」他說。「上面寫說:『敘述現代英格蘭鄉村生活的黑色喜劇』。」他用粗短的手指戳著那幾個字。
「對啊,」我回答,沒發覺陷阱正在我腳邊張開。
「還有,『一部大膽又讓人捧腹大笑的英格蘭戲劇。』」
「這部戲的評價很高,」我贊同地說。「你要選這部嗎?」
「我為什麼要看一部講英格蘭的劇本?」他輕蔑地說。「和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噢,天哪,」安妮卡重重拍了桌子一下說:「你可以再更可悲一點嗎?」
他滿臉通紅地說:「是呀,妳當然無所謂,因為妳又不是該死的蘇格蘭人。所以妳根本不懂,對吧?」
「天哪,你可以不要再擺出一副被害者的樣子嗎,」她尖聲說。「這種『我們勇敢的蘇格蘭人真可憐』的心態。」對一個母語是瑞典文的女孩而言,她用愛丁堡口音嘲諷人的功力好得讓人不安。「實在是很,」她焦急地尋找那個字眼:「無聊。」
她伸手要去拿背包。瑞奇愈來愈激動地塗鴉,打算用畫圖來逃避這場衝突。
「不要這樣小題大作嘛,」我說,他們兩個人一起怒氣沖沖地轉頭看我,我壓下想舉手投降的衝動。我依稀記得在以前的學校看過代課老師哭,知道自己正在朝那條路前進。「又不是生死攸關的事情,只是一齣戲而已。我原本以為你們會喜歡,但就算不喜歡也沒關係,反正我們還有很多劇本可以選啊。梅兒、卡莉──妳們變得好沉默。有沒有什麼想法?」我又遞了兩本書給他們。梅兒向前傾要接過其中一本。我發現她的袖子實在太長,即使伸長了手,仍然有半個手掌藏在毛衣淺藍色的袖口裡。
「這本,」卡莉一面說一面看著新版《恨世者》(The Misanthrope)的書皮。
「不要,」梅兒說:「我受不了她。」她用大拇指比著最近在這部戲的倫敦重演中擔綱演出的電影明星。
「好吧,」我的耐性已經磨光了。「妳手上的是哪一本?」
「索福克勒斯的《希臘悲劇三部曲》(The Theban Plays),」她回答。
「那我們要來看其中一部嗎?」我急忙說道。「故事不是發生在英格蘭,也沒有帥哥在中間死掉,綺拉‧奈特莉(Keira Knightley)從來沒演過,而且我想有好幾幕可以讓瑞奇畫畫。怎麼樣?」
瑞奇聽到我叫他的名字嚇了一跳,但知道自己沒惹禍之後,又繼續用交叉線條畫他的圖。其他人則是一臉漠然。
「劇情在講什麼?」卡莉默默地問。
「那我們來看《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吧,是這本書的第一部戲,講一個男人命中注定要犯下大錯,但他努力要逃避自己的命運。」
「他的命運是什麼?」她問。
「他注定要殺了自己的父親,娶他的母親。」
「太噁了吧,」瑞奇說完開始大笑。教室裡的緊張氣氛稍微輕鬆了一點,我覺得自己的肩膀也放鬆了一吋。
「古希臘人對這種事情的看法比我們更反感,」我說,試著回憶大學第一年的情景,當時我們讀遍了這些希臘悲劇:羅伯特一定是利用這種方法來淘汰那些他認為對這門課不夠認真的學生。我寫了一堆報告講述對希臘悲劇的感想及其歷史背景,默默感謝我的父親曾經在我唸書時拖著我去看了其中幾部戲,那些記憶全都儲存在我腦中的某個地方。
安妮卡盯著窗外的白牆,喬諾仍粗重地喘息,不過臉色已經恢復正常。
「我不認為他們會比我更覺得這種事噁心,」瑞奇說。
「是真的。在他們的世界裡,亂倫真的是一大禁忌。很多我們認為是禁忌的事他們都不在乎,所以他們認為是禁忌的事,嚴重性是我們認為的兩倍以上。」
「什麼是禁忌?」他問,手裡依舊握著鉛筆,但已經不再拿著筆亂畫。
「就是大家禁止做的事,像是亂倫、戀童癖之類的事情。」現在瑞奇合理地咯咯笑了起來,就連喬諾也露出淺笑。
「希臘人完全不介意戀童癖,」我說,希望這是正確的方向。「但和媽媽發生性關係的確是非常嚴重的事。」
「簡直他媽的怪透了,」喬諾說。
「如果是你媽的話就還不錯,」瑞奇說。喬諾轉頭看著他。「抱歉,老兄,我不是故意的。」
「我們不要過度聯想了,好嗎?」我發現這門課就算往全新的方向發展,還是可能會出錯。
「抱歉,老師,」他又拿起鉛筆。
「所以我們就決定來讀伊底帕斯囉。我會在今天放學之前準備好五份劇本,你們可以在回家前到我的桌上拿。」
1
他們首先問我的第一件事,是我如何認識她的。當然,他們早已知道了,這絕不是他們提問的目的,絕對不是。
我記得路克受訓時曾告訴我,如果你已經知道答案,就只會問一個問題。律師不喜歡意外,更別提會留下紀錄的意外。他們之所以提問,不是因為想知道日期、時間、地址等所有的細節,我相信他們會先做好功課,他們早就與羅伯特、也就是我的前老闆談過,知道我何時抵達愛丁堡,從哪一日開始上班。他們可能還掌握了我的行事曆,甚至可以說出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幾時幾分。
他們之所以提問,不是想知道我說了什麼,而是想知道我怎麼說。我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