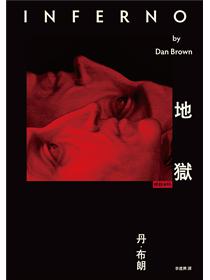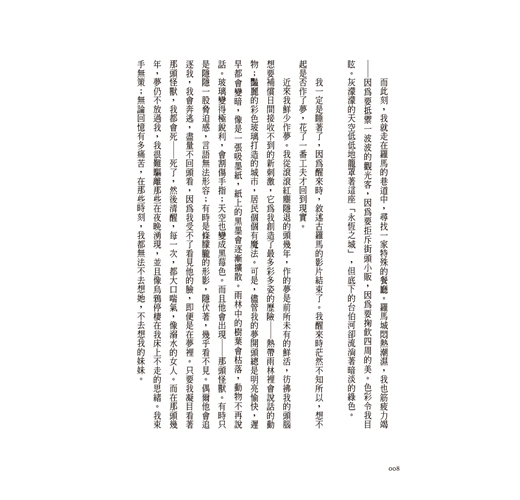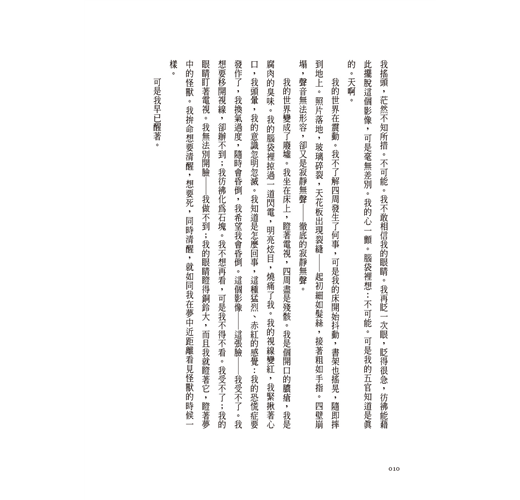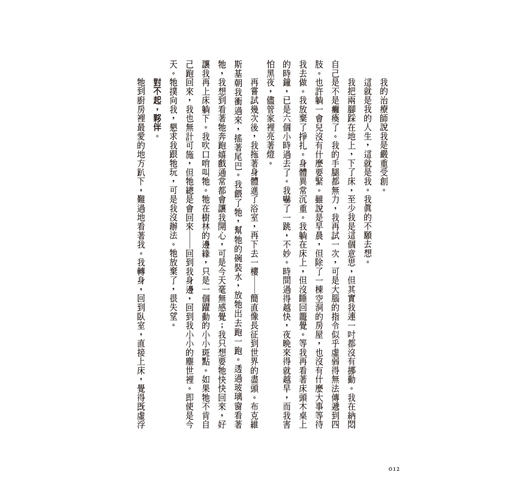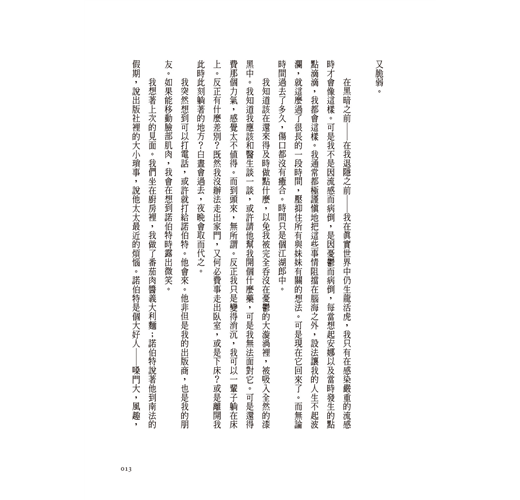《控制》的德國版回應!
●罪咎與恐懼交織,真實與夢魘迷亂,亞馬遜★★★★好評推薦!
●售出二十一個國家版權,美國三星影業即將改拍成電影!
小說也可以客製化?!
暢銷作家孤注一擲的索命挑戰.......
我的世界只有白晝,永遠維持同樣的溫度,因為這棟別墅就是我的世界。
我已經十一年沒踏出去一步了。
我叫琳達.康拉德茲,一年寫一本暢銷小說的神祕作家。
事實上,我早已不是我。自從看到妹妹躺在血泊中,自從看到那雙怪獸般的眼睛對著我,轉身離去.......
難以置信,那雙眼睛十幾年後竟又盯著我!在電視螢幕上的他,是個記者;只有我知道,他就是凶手!
我是大家都想採訪的知名作家,而他是個記者──復仇,看來很簡單。
我坐在電腦前飛快地打字,這將是琳達.康拉德茲的第一本犯罪小說。或者,應該說是獻給凶手的誘餌.......
作者簡介:
梅蘭妮.拉貝Melanie Raabe
一九八一年出生於原東德的小村莊。大學主修傳播科學及比較文學,在科隆市一家雜誌社完成實習訓練後,她又成為演員、部落客、採訪記者、舞台劇與電視劇編劇。熱愛舞台、旅遊、烹飪、高空彈跳、紋身、獨立搖滾和貓的梅蘭妮有自己的訪談部落格,先前所寫劇本與短篇小說並贏得多個獎項。
《陷阱》是她的長篇小說處女作,一出手即登上國際最熱門的外國小說之一!目前售出二十一個國家的版權,美國三星影業即將改拍成電影,梅蘭妮絕對是一顆值得期待的文壇新星。
譯者簡介:
趙丕慧
一九六四年生,輔仁大學英國文學碩士。譯有《臨時空缺》、《少年Pi的奇幻漂流》、《易經》、《雷峯塔》、《穿條紋衣的男孩》、《不能說的名字》等書。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推理評論人 冬陽.《青田街一號》導演 李中.《百日告別》導演 林書宇 齊聲盛讚
媒體推薦:
*你絕對抗拒不了。──《Elle》雜誌
*這本書什麼都有:複雜的人物,侷限住行動的強烈地方感,迂迴迷人的情節。──《環球郵報》
*吉莉安.弗琳和珀拉.霍金斯的書迷一定會喜歡這本節奏明快、峰迴路轉的小說。──美國《書單》雜誌
*極具巧思,令人費解的驚悚小說。──《女人與家》雜誌
*寫得真好.......情節充滿了出人意表的轉折.......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混雜,讓《陷阱》製造出的大漩渦就跟它的魅力一樣大。──德國《世界日報》
*愛、張力、深度,以及一縷史蒂芬.金的風格──全都在這本精采的小說裡。──德國《布莉姬》女性雜誌
*寫得漂亮又精采的心理驚悚小說.......就國際的標準來看,也是一本精心打造的處女作,趣味盎然。──西德廣播公司
*梅蘭妮.拉貝的小說對大衛.芬奇執導的犯罪故事《控制》提出了德國人的回答。──德國《阿萊格拉》女性雜誌
*一本引人入勝的心理驚悚小說。──德國《圖片報》
*我一翻開書就入迷了.......拉貝讓你從頭至尾不停質問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同時步步營造出緊張的氣氛。──Debbie Howells,《The Bones of You》作者
*愛看驚悚小說的人絕不能錯過。──《Essentials》月刊
*精采的處女作!──3Sat Kulturzeit/Krimibuchtipps
*一本令人驚豔的懸疑小說。──《Für Sie》雙週
名人推薦:推理評論人 冬陽.《青田街一號》導演 李中.《百日告別》導演 林書宇 齊聲盛讚媒體推薦:*你絕對抗拒不了。──《Elle》雜誌
*這本書什麼都有:複雜的人物,侷限住行動的強烈地方感,迂迴迷人的情節。──《環球郵報》
*吉莉安.弗琳和珀拉.霍金斯的書迷一定會喜歡這本節奏明快、峰迴路轉的小說。──美國《書單》雜誌
*極具巧思,令人費解的驚悚小說。──《女人與家》雜誌
*寫得真好.......情節充滿了出人意表的轉折.......可能就是因為這樣的混雜,讓《陷阱》製造出的大漩渦就跟它的魅力一樣大。──德國《世界日...
章節試閱
一
我不是塵世中人,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好像只有一個塵世似的。
我就站在從未使用過的空洞、寬闊的餐廳裡,從大窗戶向外望。餐廳在一樓,可以將屋後的草原盡收眼底,還有樹林的邊緣,有時能看見鹿或狐狸。
現在是秋天,我佇立眺望,感覺像在照鏡子。色彩由淡轉濃,層層敷設;秋風吹得樹木搖曳,吹彎了一些枝椏,也吹斷了幾根樹枝。今天是很美、很濃豔的一天。大自然似乎也覺察到有什麼事即將落幕,因此凝聚起全身之力,要做最後一次的激湧。不久之後,我窗外的景致就會了無生氣。日光會變為濕濕的灰色,然後是易脆的白。來看我的人——我的幫手、我的出版商、我的經紀人(也是僅有的一個)——會抱怨濕氣太重,溫度太低。抱怨他們必須用麻木的手指刮擋風玻璃之後才能出發,抱怨他們─早晨離家時天色仍暗,晚上回家時仍得摸黑。這些事都與我無關。在我的塵世裡,無論冬夏,都是攝式二十三點二度。在我的塵世裡,只有永晝,沒有黑夜。在這裡,無雨,無雪,無凍僵的手指。在我的塵世裡,唯有一個季節,而我至今仍無以名之。
這棟別墅就是我的塵世。有著敞開式火爐的客廳是我的亞洲,圖書室是我的歐洲,廚房是我的非洲。北美洲在我的書房,我的臥室是南美洲,澳洲及大洋洲在外面的露台上,雖僅數步之遙,卻遙不可及。
我有十一年沒有走出屋外了。
你可以在所有的報章上讀到原因,儘管某些過於誇大。我病了,沒錯。我沒法離開屋子,正確。可是我並不是被迫生活在一片魆黑之中,我也沒有睡在氧氣帳裡。我的生活差強人意,事事井然有序。時間是一道潮流,強大卻溫和,讓我能逐波而浮。只有布克維斯基偶爾會引入混亂,牠到草原上嬉鬧後,爪子會帶進泥土,毛皮會帶進雨水。我極愛以手去撫摸牠蓬鬆的粗毛,去感覺濕氣附著我的皮膚。我極愛布克維斯基在地磚及鑲花木地板上留下戶外的粗獷痕跡。在我的塵世裡,沒有泥巴,沒有樹木,沒有草原,沒有兔子,沒有陽光。啁啾鳥鳴來自錄音帶,陽光來自地下室的日光治療室。我的塵世並不遼闊,卻安全。至少,我是這麼想的。
二
地動山搖發生在週二,事前並沒有微震——至少沒有能驚動我的徵兆。地動山搖時我在義大利。我經常旅行。我發現造訪那些我熟悉的國家最是輕鬆自在,況且從前我常去義大利,我不時會舊地重遊。義大利是個美麗又危險的國家,因為它讓我想起我的妹妹。安娜,還沒去過義大利就深深愛上它;安娜,買了義大利語錄音帶,天天聽,時時聽,把錄音帶都聽壞了。安娜,辛辛苦苦存錢買了台偉士牌機車,在我們的家鄉小鎮上馳騁,彷彿在羅馬的窄巷中狂飆。義大利讓我想起妹妹以及昔日舊事,在黑暗來襲之前。我一直想把安娜從腦海中驅逐,可是她黏得牢牢的,像舊時的黏蠅紙。其他黑暗的想法也會落在這張紙上,無法阻止。所以管他的,就去義大利。整整一週,我躲進樓上從未使用過的三間客房,命名為義大利。我放上義大利音樂,看義大利電影,沉溺在描述義大利文化風情的紀錄片中,翻閱大本精裝書,叫外賣送來義大利的珍饈美食,還有葡萄酒。喔,葡萄酒,幾乎讓我的義大利名副其實。
而此刻,我就走在羅馬的巷道中,尋找一家特殊的餐廳。羅馬城悶熱潮濕,我也筋疲力竭──因為要抵禦一波波的觀光客,因為要拒斥街頭小販,因為要掬飲四周的美。色彩令我目眩。灰濛濛的天空低低地籠罩著這座「永恆之城」,但底下的台伯河卻流淌著暗淡的綠色。
我一定是睡著了,因為醒來時,敘述古羅馬的影片結束了。我醒來時茫然不知所以,想不起是否作了夢,花了一番工夫才回到現實。
近來我鮮少作夢。我從滾滾紅塵隱退的頭幾年,作的夢是前所未有的鮮活,彷彿我的頭腦想要補償日間接收不到的新刺激,它為我創造了最多彩多姿的歷險——熱帶雨林裡會說話的動物;豔麗的彩色玻璃打造的城市,居民個個有魔法。可是,儘管我的夢一開頭總是明亮愉快,遲早都會變暗,像是一張吸墨紙,紙上的黑墨會逐漸擴散。雨林中的樹葉會枯落,動物不再說話。玻璃變得極銳利,會割傷手指;天空也變成黑莓色。而且他會出現——那頭怪獸。有時只是隱隱一股脅迫感,言語無法形容;有時是條朦朧的形影,隱伏著,幾乎看─不見。偶爾他會追逐我,我會奔逃,盡量不回頭看,因為我受不了看見他的臉,即便是在夢裡。只要我凝目看著那頭怪獸,我都會死——死了,然後清醒,每一次,都大口喘氣,像溺水的女人。而在那頭幾年,夢仍不放過我,我很難驅離那些在夜晚湧現,並且像烏鴉停棲在我床上不走的思緒。我束手無策;無論回憶有多痛苦,在那些時刻,我都無法不去想她,不去想我的妹妹。
今夜無夢,也無怪獸,可是我仍不自在。我的腦袋裡縈繞著一句話,卻模糊不清。還有人聲。我眨眨眼,眼皮膠著。我注意到我的右臂睡死了,我按摩右臂,想讓它恢復生氣。電視仍開著,聲音就是從那兒來的——聲音不知怎地鑽入了我的夢,喚醒了我。
是男人的聲音,一板一眼,不卑不亢,這些播映我極喜愛的紀錄片的新聞頻道都是這類的聲音。我把身體抬起來,摸索著遙控器,卻找不到。我的床很大,我的床是海洋,一堆枕頭和鴨絨被,波浪似的大本精裝書,以及一整支的遙控器艦隊:電視的,電視接收機的,光碟播放機的,兩部格式不同、客製藍光播放機的,音響的,舊影帶錄影機的。我挫折地吐息,電視的聲音說著我不想知道的中東諸事——此時不想聽,今天不想聽。我在度假,我在義大利,我一直很期待這次的旅行!
來不及了。電視上的人聲仍播報著真實世界的事實——許許多多的戰爭、災禍、暴行,我本希望耳根能清靜幾天的——都爭先恐後地往我的腦袋裡─鑽,幾秒之內就逐走了我的明朗心情。義大利氛圍消失了,旅行夭折了。明天早晨我會回到我真正的臥室,把義大利徹底清除。我揉揉眼,光亮的螢幕害我的眼睛痠澀。主播報導完了中東,正在報導國內新聞。我認命地看著他,疲累的眼睛水汪汪的。男主播的滔滔不絕結束了,換上了柏林的現場報導。一名記者在說什麼總理最近的一次出訪,他後面的德國國會大廈高聳入雲,宏偉莊嚴。
我的眼睛調整焦距,心中一驚,眼睛一眨,不敢相信。可是我看見他了!就在我的面前!
我搖頭,茫然不知所措。不可能。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我再眨一次眼,眨得很急,彷彿能藉此擺脫這個影像,可是毫無差別。我的心一顫。腦袋裡想:不可能。可是我的五官知道是真的。天啊。
我的世界在震動。我不了解四周發生了何事,可是我的床開始抖動,書架也搖晃,隨即摔到地上。照片落地,玻璃碎裂,天花板出現裂縫——起初細如髮絲,接著粗如手指。四壁崩塌,聲音無法形容,卻又是寂靜無聲——徹底的寂靜無聲。
我的世界變成了廢墟。我坐在床上,瞪著電視,四周盡是殘骸。我是個開口的膿瘡,我是腐肉的臭味。我的腦袋裡掠過一道閃電,明亮炫目,燒痛了我。我的視線變紅,我緊揪著心口,我頭暈,我的意識忽明忽滅。我知道是怎麼回事,這種猛烈、赤紅的感覺:我的恐慌症要發作了,我換氣過度,隨時會昏倒,我希望我會昏倒。這個影像——這張臉——我受不了。我想要移開視線,卻辦不到;我彷彿化為石塊。我不想再看,可是我不得不看。我受不了;我的眼睛盯著電視。我無法別開臉——我做不到;我的眼睛瞪得銅鈴大,而且我就瞪著它,瞪著夢中的怪獸。我拚命想要清醒,想要死,同時清醒,就如同我在夢中近距離看見怪獸的時候一樣。
可是我早已醒著。
三
隔天早晨,我從瓦礫堆下爬出來,把自己一塊一塊拼接回去。我叫琳達.康拉德茲,是個作家。每年我都規定自己要寫一本小說。小說很暢銷,我的生活富裕,也就是說,我有很多錢。我三十八歲,我生了病。媒體臆測我罹患了神祕的疾病,不良於行。我有十年多沒邁出家門。我有家庭。應該說是我的父母仍健在,我有很長一段時間沒見過他們了。他們不來看我,我沒法去看他們。我們也不常通電話。
有一件事是我不願去想的,可卻也是我沒法不去想的。事關我的妹妹。事情發生在多年之前。我愛我的妹妹,她叫安娜。我妹妹死了。她比我小三歲。我妹妹十二年前死的。妹妹不是就那麼死了,妹妹是被謀殺的。十二年前我妹妹被殺害了,而我發現了她。我看著凶手逃走,看見了凶手的臉。凶手是個男人。凶手把臉轉過來對著我,然後就逃走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逃,我不知道他為什麼不攻擊我,我只知道妹妹死了,而我活著。
我的治療師說我是嚴重受創。
這就是我的人生,這就是我。我真的不願去想。
我把兩腳踩在地上,下了床,至少我是這個意思,但其實我連一吋都沒有挪動。我在納悶自己是不是癱瘓了。我的手腿都無力,我再試一次,可是大腦的指令似乎虛弱得無法傳遞到四肢。也許躺一會兒沒有什麼要緊。雖說是早晨,但除了一棟空洞的房屋,也沒有什麼大事等待我去做。我放棄了掙扎。身體異常沉重。我躺在床上,但沒睡回籠覺。等我再看著床頭木桌上的時鐘,已是六個小時過去了。我嚇了一跳,不妙。時間過得越快,夜晚來得就越早,而我害怕黑夜,儘管家裡亮著燈。
再嘗試幾次後,我拖著身體進了浴室,再下去一樓——簡直像長征到世界的盡頭。布克維斯基朝我衝過來,搖著尾巴。我餵了牠,幫牠的碗裝水,放牠出去跑一跑。透過玻璃窗看著牠,我想到看著牠奔跑嬉戲通常都會讓我開心,可是今天毫無感覺;我只想要牠快快回來,好讓我再上床躺下。我吹口哨叫牠。牠在樹林的邊緣,只是一個躍動的小小斑點。如果牠不肯自己跑回來,我也無計可施,但牠總是會回來——回到我身邊,回到我小小的塵世裡。即使是今天。牠撲向我,懇求我跟牠玩,可是我沒辦法。牠放棄了,很失望。
對不起,夥伴。
牠到廚房裡最愛的地方趴下,難過地看著我。我轉身,回到臥室,直接上床,覺得既虛浮又脆弱。
在黑暗之前——在我退隱之前——我在真實世界中仍生龍活虎,我只有在感染嚴重的流感時才會像這樣。可是我不是因流感而病倒,是因憂鬱而病倒,每當想起安娜以及當時發生的點點滴滴,我都會這樣。我通常都極謹慎地把這些事情阻擋在腦海之外,設法讓我的人生不起波瀾,就這麼過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壓抑住所有與妹妹有關的想法。可是現在它回來了。而無論時間過去了多久,傷口都沒有癒合。時間只是個江湖郎中。
我知道該在還來得及時做點什麼,以免我被完全吞沒在憂鬱的大漩渦裡,被吸入全然的漆黑中。我知道我應該和醫生談一談,或許請他幫我開個什麼藥,可是我無法面對它。可是還得費那個力氣,感覺太不值得。而到頭來,無所謂。反正我只是變得消沉,我可以一輩子躺在床上。反正有什麼差別?既然我沒辦法走出家門,又何必費事走出臥室,或是下床?或是離開我此時此刻躺著的地方?白晝會過去,夜晚會取而代之。
我突然想到可以打電話,或許就打給諾伯特。他會來。他非但是我的出版商,也是我的朋友。如果能移動臉部肌肉,我會在想到諾伯特時露出微笑。
我想著上次的見面。我們坐在廚房裡,我做了番茄肉醬義大利麵;諾伯特說著他到南法的假期,說出版社裡的大小瑣事,說他太太最近的煩惱。諾伯特是個大好人——嗓門大,風趣,滿肚子的故事。他有全世界最悅耳的笑聲;精確一點來說,是他和我這兩個世界裡最悅耳的笑聲。
諾伯特稱我是他的嗜極生物。他第一次這麼叫我,我還得上網查資料,查到後驚訝不已,他說得還真對。嗜極生物是一種有機體,適應了極端的生活環境,能夠在對生存有害的棲地存活下來,例如高溫或冰凍、黑暗、輻射的環境,強酸中,或是徹底的孤絕中——這必定是諾伯特的原意。嗜極生物,我喜歡這個詞,我也喜歡他這麼叫我,聽來像是這一切都是我自己自願的,彷彿我自己喜歡這種特立獨行的生活,彷彿我有選擇。
此時此刻,我唯一的選擇是向右或向左側躺,是平躺或趴睡。幾小時過去了。我費了極大的力氣不去東想西想。不知何時,我下了床,走向四壁長長的書架,拿了幾本書,拋到床上,再播放我最愛的比莉.哈樂黛唱片,再溜回鴨絨被下。我聽著音樂,翻著書頁,閱讀到眼睛痠澀,渾身也因音樂的洗禮而軟綿綿的,像洗過了熱水澡。我不想再看書了,我想看電影,可是我不敢打開電視。我就是不敢。
我聽見了腳步聲,嚇了一跳。比莉的歌聲不再。我必定是在某個時刻以我的遙控器關掉了她哀傷的聲音。誰來了?現在可是半夜三更。狗為什麼不叫?我想把自己弄下床,抓個東西來自衛,或是躲起來,或是做點什麼,可是我只是躺在床上,呼吸淺促,瞪大雙眼。有人敲門,我沒吭聲。
「哈囉!」有人大喊。我不認得的聲音。
又一次。「哈囉!有人在家嗎?」
門開了。我悶哼了一聲——這是我無力的尖叫。是莎樂特,我的幫手。我當然認得她的聲
音,是我的恐懼扭曲了她的聲音,變得陌生。莎樂特每週會來兩次,幫我購物、寄信,照料一切該照料的事。是我付錢與紅塵的聯繫。
這時她立在門口,猶豫不決。「妳還好嗎?」
我的思緒重新歸位。既然莎樂特來了,那就不可能是夜晚。我一定是在床上躺了相當長的時間了。
「對不起,貿然闖進來,可是我按了電鈴,妳沒回應,我不放心,就自己進來了。」
電鈴?我記得有一聲鈴聲鑽進了我的夢裡。這麼多年了,我又作夢了!
「我覺得有點不舒服。」我說。「我睡得很熟,沒聽見電鈴響,對不起。」我很慚愧,連坐起來都沒辦法。莎樂特似乎很擔心,雖然她不是個容易大驚小怪的人。這
也是我會雇用她的原因。莎樂特比我年輕,可能年近三十。她身兼一堆工作——在幾家咖啡館當服務生,在鎮上的電影院賣票,諸如此類的。而每週她會來我這裡兩次。我喜歡莎樂特,喜歡她染成藍黑色的短髮,喜歡她結實的體格,喜歡她俗豔的刺青,喜歡她粗俗的幽默,喜歡她說她的小兒子,她都叫他「不要臉的小魔鬼」。
既然莎樂特看起來很緊張,那我一定是一副鬼樣。
「妳需要什麼嗎?要我跑趟藥局還是哪裡嗎?」
「不用了,謝謝,家裡什麼都有。」我說。
我的聲音怪怪的,像機器人。我自己聽得出來,可是我無力改善。
「今天沒有事讓妳做,莎樂特。我應該早點通知妳的,對不起。」
「沒關係。採買的東西都在冰箱裡了。要不要在我走之前帶狗出去?」
天啊,狗狗。我究竟是在床上躺了多久?
「那就麻煩妳了。」我說。「順便也餵牠一下好嗎?」
「沒問題。」
我把鴨絨被拉上來蓋住了鼻子,表示對話結束。
莎樂特在門口又徘徊了一會兒,應該是不放心丟下我一個人,然後她做了決定,轉身走了。我聽見她在廚房餵布克維斯基。我通常很喜歡屋子裡有聲響,但今天只覺空落落的。我讓枕頭和鴨絨被和黑暗包圍住我,可是我睡不著。
四
我躺在黑暗中,想著我的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記得在妹妹下葬的那天,我哭不出來──當下沒辦法。我的頭腦和身體只充滿了一個想法。為什麼?所有的空間只容納得下一個問題:為什麼死的會是她?
我總覺得我父母也在問我相同的問題 我的父母,其他弔喪的人,安娜的朋友、同事,幾乎是每一個人──因為,畢竟我也在,我必─定看見了什麼。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死的會是安娜?
我記得弔喪的人哭泣,拋擲鮮花在棺木上,互相依偎,擦淚擤鼻。一切對我都好不真實,整個都是扭曲的──聲響,顏色,甚至是情感。牧師的聲音拖沓得奇怪。人人都是慢動作。玫瑰和百合──都是單一顏色。
喔,對了,花!想到花讓我瞬間落回現實。我在床上坐了起來。我忘了叫莎樂特澆暖房裡的花,而她現在已經走了。莎樂特知道我有多愛我的花,她知道我通常都會親力親為,所以她不太可能會澆花。沒有別的法子了,只能我自己去。
我下了床,一面呻吟。赤腳踩著涼涼的地板,我硬逼著自己一腳前一腳後,沿著走廊走向樓梯,下去一樓,穿過大客廳與餐廳。我打開暖房,進入了叢林。
我的屋子裡盡是空落落的地方和死氣沉沉的物件──布克維斯基是例外。但是在暖房這裡,綠意盎然,由生命所統領。棕櫚、蕨類、西番蓮、天堂鳥、火鶴花,以及最重要的蘭花。我愛極了異國花卉。
我把暖房視作我個人的小溫室,蒸騰的熱氣幾乎立刻就讓我的額頭出汗,而我當作睡衣的寬鬆長T恤也黏著我的身體。我愛這片翠綠的叢林。我不要秩序井然,我要的是混亂,是生命。我要細枝樹葉拂過我,恍如置身森林中。我要聞到花香,我要在花香中醺然如醉。我要吸收所有的色彩。
我環顧四周。我知道看見我的植物應該能給我喜悅,但今天卻毫無感覺。我的暖房光線明亮,外頭卻是黑夜。冷漠的星斗透過玻璃屋頂眨呀眨。我像換上了自動導航系統,執行著平時能給予我無限滿足的工作。我澆花,以手指觸摸土壤,感覺是否乾燥鬆塌、需要澆水,或是會沾黏在手指上。
我穿枝拂葉,走到暖房後頭,這裡有我的私藏蘭園。恣放的蘭花擠在架上,或是吊掛在天花板上。我的最愛在這裡──我的最愛,也是我的問題兒童。那是一株小蘭花,與妍麗茂盛的其他姐妹株相比,它貌不驚人,幾乎可說是醜陋,僅有兩、三片暗淡的深綠色葉片和乾乾的、灰色的根,算不上有莖梗,沒有花朵,很長一段時間不開花了。只有這一棵不是我特地為暖房採購的,它是我在許久許久以前從我的往昔、從真正的塵世帶來的。我知道它不會開花,但我就是捨不得丟棄。我給它一點水,接著我轉而注意一株特別美麗的白色蘭花。我用手滑過葉片,感覺天鵝絨似的花瓣。花苞摸起來強韌,綻放著生命,無須多久就會有鮮花怒放。我想著剪下幾枝含苞的莖梗,拿回屋中插瓶,那會多美;但這念頭一浮現,我就又想到了安娜。即使是在暖房裡,我也無法把她從腦海中驅逐。
小時候,安娜不像我一樣,也不像其他的孩子一樣愛摘花。她覺得把美麗的花朵拔下來很殘忍。如今回想起來,我的唇邊忍不住露出微笑。安娜的怪癖。我相當清楚地看見妹妹站在我的眼前──金髮,矢車菊藍眼眸,小巧的鼻子,大大的嘴巴,淡色眉毛,只要一生氣眉心就會出現深紋,左頰上的痣正好點出一個三角形。角度對的話,夏日的陽光會照出她臉上的細細的金毛。我能清楚地看見她,也能聽見她的聲音,銀鈴般清脆,還有她放肆、男孩般的大笑,與她陰柔的天性是那麼鮮明的對比。我看見她在我的眼前,哈哈大笑,我的肚子像是挨了一拳。
我回想起和治療師的第一堂諮商,就在安娜死後不久。警方毫無頭緒,以我的口述組合出的嫌犯圖像也毫無用處。就連我自己都覺得不像是我看見的凶手。可是,無論多麼努力,我就是只能做到這樣。我記得我跟治療師說我必須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說這種懸而不決對我是種折磨。我記得她跟我說這樣子很正常,對親屬而言,最壞的地方就是─不知道。她推薦了一個自助團體給我。自助團體──簡直是笑話。我記得我說只要能找出原因來,我願意付出一切代價。這是我欠妹妹的,我至少得為她做這件事。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妳對這個問題太過執念了,康拉德茲小姐。這樣不好,妳得放下,妳還有自己的人生。」
我努力擺脫安娜的影像以及與她有關的一切想法。我不要去想她,因為我知道會陷入死胡同。當年,我幾乎發瘋,知道安娜死了,知道凶手仍逍遙法外。
一籌莫展是最可怕的部分。最好是壓根就不去想,讓自己分心,忘掉安娜。
我現在也盡量這麼做,可是這一次卻行不通。為什麼?
接著新聞主播的臉孔在我的心裡掠過,我的腦袋像打開了什麼開關,忽然明白幾個小時以來我都處於震驚之中。
我終於弄清楚了。電視上的那個人,害我如此消沉的那個人,是真的。
不是惡夢,是現實。
我看到了殺害我妹妹的凶手。雖然十二年過去了,我卻記得每一個小細節,其中的意義讓我不想明白都不行。
我手上的澆水器掉了,鏘一聲落在地上,水潑灑在我的光腳上。我一轉身,離開了暖房,一路絆到腳趾,但我不理會腳上的傷,匆匆前進。
我迅速地穿過一樓,往樓上跑,在走廊上疾行,進了臥室,喘不過氣來。我的筆電在床上,隱隱透著威嚇。我遲疑了一下,隨即坐在床上,把筆電拉過來,手指顫抖。我害怕打開電腦,好像有人可能會透過螢幕監視我。
我打開了 Google,輸入了我看見那個人的新聞頻道。我很緊張,老敲錯鍵,第三次才敲對。我叫出了網頁,進入「記者」欄。我就快認為整件事純粹是出於我的想像了──就快認為那個人並不存在,是我夢見的。
但是,我找到了他,只不過按了幾下滑鼠。那頭怪獸。我本能地伸出左手擋住他的照片。我無法直視他──還不行。牆壁又開始搖晃,我的心跳狂飆。我專注地呼吸,閉著眼睛。平靜淡定,就是這樣。我再度睜開眼睛,讀他的姓名,他的簡介。我發現他得過獎,已成家,功成名就,人生美滿。我心裡有根弦繃斷了,我感覺到了多年來不曾有過的感覺,滾燙熾熱。我緩緩拿開了遮著螢幕的手。
我看著他。
我直視那個殺害我妹妹的男人的臉孔。
憤怒堵住了我的喉頭,我只能想到一件事:我一定會逮住你。
我砰地合上筆電,推開,站了起來。
我的心思電轉,心跳如雷。
最不可置信的一點是,他就近在咫尺!隨便哪個正常人都能輕易查出他的下落,但我困在
自己的房子裡。而警方──警方當年就是不相信我。不是真的信。
如果我想跟他說話──如果我想跟他對質,想叫他自清──那麼我得讓他自己過來。我要如何誘惑他來這裡呢?
我的心中又掠過了與治療師的談話。
「可是為什麼?為什麼死的偏偏是安娜?」
「妳或許永遠也找不到答案,妳必須接受這種可能,琳達。」
「我沒辦法接受,永遠也沒辦法。」
「妳遲早會懂的。」
永遠不會。
我思索再三,情緒激盪。他是記者,而我是知名作家,出了名的隱士,多年來各大雜誌和電視台爭相要訪問我,尤其是新書上市期間。
我記得我的治療師說:「妳只是在折磨自己,琳達。」
「我沒辦法不去想。」
「如果妳需要理由,就編一個,或是寫本書。把它從心裡沖刷掉,然後妳一定得放下,過妳自己的人生。」
我的寒毛根根倒豎。沒錯,就是這樣!
我的全身都起了雞皮疙瘩。
答案明擺在眼前。
我會寫一本新書。以過去發生的事為基底,寫一本犯罪小說。設下誘餌來釣凶手,同時也是為我自己準備良藥。
我的身體擺脫了沉重之感。我離開臥室,四肢又乖乖聽話了。我進入浴室,沖了個澡,擦乾身體,換上衣服,走進書房,打開電腦,開始寫作。
一
我不是塵世中人,至少他們是這麼說的。好像只有一個塵世似的。
我就站在從未使用過的空洞、寬闊的餐廳裡,從大窗戶向外望。餐廳在一樓,可以將屋後的草原盡收眼底,還有樹林的邊緣,有時能看見鹿或狐狸。
現在是秋天,我佇立眺望,感覺像在照鏡子。色彩由淡轉濃,層層敷設;秋風吹得樹木搖曳,吹彎了一些枝椏,也吹斷了幾根樹枝。今天是很美、很濃豔的一天。大自然似乎也覺察到有什麼事即將落幕,因此凝聚起全身之力,要做最後一次的激湧。不久之後,我窗外的景致就會了無生氣。日光會變為濕濕的灰色,然後是易脆的白。來看我的人—...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