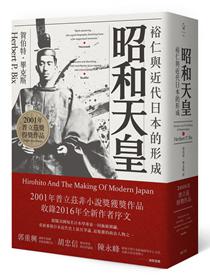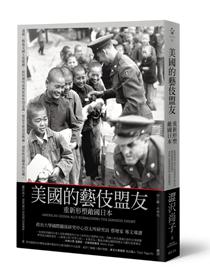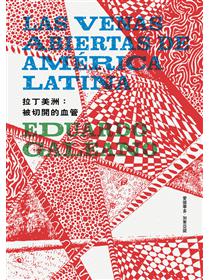打破中國狹隘視角,首次引進日本內部視點
東京審判――史上首次戰爭罪犯審判的全景和真相★★本書榮獲三得利學藝獎(思想.歷史部門)★★
★★東京審判研究第一人――「日暮吉延」權威之作★★
★★知名歷史學家保坂正康盛讚:「東京審判過後六十年,『歷史』所殷殷期盼的書終於出現。」★★.東京審判究竟是「文明的制裁」還是「勝者的報復」?
.同盟國在如何起訴、又如何處置均有歧見,內部有哪些政治盤算?
.為什麼不起訴天皇?二十八名甲級戰犯如何定罪、又為何釋放?
.東京審判和紐倫堡審判有何不同之處?為什麼不實施第二次東京審判?
.靖國神社合祀為何風波不斷?東京審判究竟給日本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
◎華文世界首次引進日本內部論點的東京審判
全面、翔實、冷靜、實證。從東京審判的結構如何確立、同盟國如何起訴、為何不起訴天皇、日本如何因應,到如何撰寫判決、為何未實施第二次東京審判、如何釋放戰犯――尤其是甲級戰犯,以及審判對日本的意義究竟是什麼,一一呈現日本這個戰敗國家被審判的全景。
◎這是一場「文明的審判」,還是「勝者的審判」?
在戰後的日本,較之於被審判的當時,屈辱感反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加強,對於審判的意見也激烈分化。而伴隨著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感情和道義等糾纏的議題,這兩者已經化為難以和解的「價值對立」。本書的作者又是如何看待審判呢?
◎打破中文世界對東京審判的刻板印象
在中文世界裡,對東京審判似已蓋棺論定,幾乎聽不到異議的聲音或討論的空間,也缺少對東京審判基於「事實」的冷靜且實證的研究,從而一般讀者形成一種刻板和偏見印象,自居正義,把審判、甲級戰犯、懲罰軍國主義者符號化和簡化。也很少深入思考審判究竟為日本帶來了什麼樣的「結果」:民主化和安全保障。
作者簡介:
日暮吉延
1962年生於東京。1993年立教大學研究所博士課程屆滿退學。2000年獲得學習院大學博士學位(政治學)。專攻日本政治外交史、國際關係論。2012年起任帝京大學法學部教授,歷任鹿兒島大學教養部助教授、法文學部助教授、教授等職。
著有:《東京審判的國際關係》(木鐸社,2002年)獲吉田茂獎,《東京審判》(講談社現代新書,2008年)獲三得利學藝獎。另合著有《正確解讀東京審判》(文春新書,2008年)等。
譯者簡介:
黃耀進
曾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員,目前為日本一橋大學大學院言語社會研究科博士候選人,內容力有限公司內容製作總監。譯有《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亂世的犧牲者:重探川島芳子的悲劇一生》、合譯有《滿洲國的實相與幻象》、《「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台灣人的日語》、《半路上》等書。
熊紹惟
國立台北大學財經法律系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目前為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譯有山本英史著〈光棍律的成立及其背景――清初秩序形成的過程〉,收錄於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法律史譯評2014年卷》。
章節試閱
東京審判法官團的分裂
◎帕爾表明辭意◎
印度法官帕爾最初堂堂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時,正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團駁回辯方所提管轄權迴避動議之際。實際上除了印度與菲律賓之外的九位法官,已經達成文書合意,如果判決中出現少數意見,將不對外公開,但晚來的帕爾卻拒絕加入此項合意。當下,法官團立刻陷入苦惱,擔心少數意見可能被公諸於世。
如同英國法官派翠克(William D. Patrick)感嘆「帕爾從被任命之初,便採取了與眾不同的鮮明立場」一般,帕爾抵達日本之際,便對「反和平罪」採取否定立場。
不過,帕爾卻未料想到審判時期竟會如此之久。原本預估東京審判很快就會結束,因此才答應前往日本擔任法官的帕爾,當他察覺審判將曠日廢時後,即於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對首席法官威廉.韋伯表明辭意,希望辭去自己擔任的法官一職。
當初明言(東京審判任務)只有半年期間。……基於此一認知,……在高等法院長期休假結束前……本人推遲了所有的重要案件。之後因得知本軍事法庭工作,終究無法在半年內結束……本人為了履行對加爾各答委託人與法庭之責任,必須返回印度。(美國務院文書)
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四條b規定,只要「出席法官過半數」之下,便可執行法庭的意思決定。但開庭至今不過才過五個多月,便有法官退出,場面恐怕不太好看。麥克阿瑟反對帕爾辭職,並以之前印度在法官指派上已經造成過一次騷動為由,說服帕爾留任。
如此一來不得不滯留至東京審判結束的帕爾,除了上法庭與進圖書館之外,就是蟄居在帝國飯店的房中,分析大量審判記錄與文獻,持續撰寫他的判決意見書,前述那份冗長的判決意見書便是在這種狀態下書寫而成。
帕爾的另一個特色,就是缺席公審的次數異常地多。他為了探望臥病在床的夫人,多次長期回國,公審的四百六十六日當中,帕爾缺席日數實際上達到一百零九天(第二名是韋伯的五十三天)。
◎首席法官韋伯才是對立的核心◎
但是,法官團不安的因素,並非只有帕爾。尤有比帕爾更甚者,那就是批判「反和平罪」帶有事後法性格,在法官團中帶來緊張與造成內部分歧的首席法官――韋伯。
甫開庭後的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三日,辯護方提出管轄權迴避動議,主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反和平罪」與「危害人類罪」並無管轄權。為此法官團針對「反和平罪」問題陷入了一陣苦思(但沒有證據顯示他們同樣在意「危害人類罪」)。
法官團磋商後,英國法官派翠克主張《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確實具備正當性,他的意見獲得不少支持,但反對意見也相當強勢。歷經長時間的「爭論」,最終法官團僅對法庭具有管轄權一事達成合意。
接下來在五月十七日的公審上,韋伯駁回了辯方此項動議,並宣布「理由將於未來宣告」。辯方批評沒有出示理由即駁回動議,未免太過牽強,但法官團內部的見解仍處於分裂對立的狀態,因此根本不可能發布駁回的「理由」。
因為美國已經指定了首席檢察官,所以麥克阿瑟選擇了在戰爭時期曾協助對日戰爭犯罪調查的澳大利亞法官韋伯擔任首席法官(紐倫堡審判時,首席法官由法官之間互相推選)。但韋伯卻恩將仇報,在法官團的協調中,他讓管轄權相關問題的共識――亦即侵略戰爭的犯罪性問題,從大英國協內部便開始分崩離析。
事情起於韋伯的議論。
他從一九四六年六月起到八月提出一個議題,主張法官團應針對「紐倫堡原則(Nuremberg doctrines)」――把侵略戰爭當成國際法上的犯罪,也就是「反和平罪」的命題——進行慎重的考量。亦即,把交戰時期的戰爭本身違法化,再把此事認定為國際法上的犯罪,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應只對《降伏文書》簽署時間點上所存在的戰爭犯罪進行管轄。若沒有條約依據即宣告被告有罪,法庭將成為「司法殺人者」,並會招來全世界的非難。如果本次審判的憲章與當前的國際法有所扞格,那麼法官的「義務」便是無視遭憲章變更的部分。
韋伯的企圖,與其說是「批判審判」,不如說是想要「表現法庭的嚴正」,而他初期的國際法論,又與「帕爾判決」非常相似。
許多法官,特別是大英國協的法官們,認為韋伯不過是「同儕中首席」,卻採取了如此專制的作法,紛紛表達了不滿。而且韋伯是個沒耐性又神經質的人物,他也儘量避免與同僚法官們有私人交流。這種情感上的尖銳摩擦,在在煽動著法官團。
◎團結的派翠克集團◎
英國的派翠克法官任職於高等法院(蘇格蘭的最高刑事法院),屬於典型「具威嚴的法官」,是一位給人崇高尊嚴感的人物。派翠克法官認為,如何合理運用本次憲章的「戰爭犯罪化與個人責任」本質,才是法官們的責任。他相信討厭此一想法的人,都不應該成為東京審判的法官。
派翠克和紐西蘭法官諾斯克羅夫特、加拿大法官愛德華.麥克杜加聯手,共同對抗韋伯。法官團內部的對立,便沿著「韋伯集團對抗派翠克集團」這條軸線展開。
派翠克集團的三人,著重於國際軍事審判中的普遍性與案例價值,主張簽署《降伏文書》的時間點上,侵略戰爭已然是國際法上的犯罪,而扮演事實認定角色的法官,並沒有重新檢討憲章的權限。這也成為之後多數判決的立場。
如果法官團都一致同意這條路線的話,那麼對於東京審判是「最初就已經決定好結論」(德富蘇峰《德富蘇峰.終戰後日記》Ⅲ)的看法,可以說就是正確的。但是,僅從判決相關事宜來看,所謂「已經先有結論」的論調,恐怕只是街談巷議間的事後諸葛說法。從事實上來看,法官團內部從開庭起,便針對如何規範「戰爭的犯罪性」而出現尖銳對立,隨著對立的演進,其實也隱藏了會出現完全不同的判決、以及法庭甚將瓦解的可能性。
在英國系統的法庭中,有由首席法官撰寫作為判決基礎的「前導性判決」慣例。因此,韋伯一邊看準了紐倫堡的判決結果,一邊於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分發了意見書給其他各國法官。意見書中冗長地引用了亞里斯多德、聖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湯瑪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胡果.格老秀斯(Hugo de Groot)等人的言說,以自然法說明侵略戰爭的違法性,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憲章之法與自然法一致,因此具有正當性。所謂的「自然法」,舉例來說,指的是「不侵犯他人之物」等人類理性中存在的普遍令式,是與成文法、習慣法等因人為而成立的「實證法」相對立的概念。
然而,韋伯此一意見書,卻遭大英國協的三位法官加上蘇聯法官大加撻伐,甚至連內斂的中國法官梅汝璈也提出批評。諾斯克羅夫特甚至私底下嚴厲批評說那是「學生寫的程度很差的國際法論文」,簡而言之,就是無法使用的判決案。韋伯受到屈辱,滿腔激憤,但卻沒有其他法官願意支持他。
即便如此,韋伯仍繼續撰寫意見書。因為韋伯的意見書始終不如己意,派翠克集團在不悅之下,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告知韋伯,他們將自行起草判決理由書。經此刺激,韋伯更加激憤,一九四七年一月二十日再度提出意見書,雖然更改了在《巴黎非戰公約》下侵略戰爭遭犯罪化的理論,但仍堅持自然法的法理。
@小小標:各國法官團的多樣立場
一九四七年初左右,其他的法官們又做如何考量?以下將整理諸位法官的立場。
中國的梅汝璈法官雖然無法確認此時所採取的立場,但從前後的態度來看,他對「紐倫堡原則」是採取肯定的態度。
蘇聯的伊凡.柴揚諾夫少將大致同意派翠克集團的見解,同時也認為除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之外,也應該併用其他國際法原則為佳。
最年輕的荷蘭法官伯特.羅林(Bert V. A. Röling)於一九四七年一月論及,因無前例可尋,因此認為「不應將侵略戰爭視為國際法上的犯罪」。而且,他認為通常會激起人們報復慾望的正是另一方所採取的殘虐行為,因此處罰此一部分便屬充分。羅林本身是刑法學專家,依他本人的說法,他被任命時「關於國際法的問題一竅不通」(伯特.羅林等著《東京審判與超越」》),因此他抵達日本後,對「紐倫堡原則」大概是採取批判的態度。
法國法官亨利.伯納德(Henri Bernard)則從憲章之法的正當性乃由人性「良心」引導而出的自然法論展開自己的意見。這論點與韋伯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下述的三名法官因到任較遲,因此開庭時尚不在場。
印度法官帕爾從到任之後,不僅對東京審判的「規範」採取否定的態度,同盟國內部也對他保持警戒。在這個時期他也發布約二百六十頁、迴避「反和平罪」的法律意見書。帕爾貫徹不顧他人眼光、「特立獨行」的風格,在法官團中算是游離分子。派翠克對於印度政府為何要指派帕爾,而英國政府又為何要支持任命印度法官一事,始終不斷抱怨。
不過,此處不可誤解,法官團中的對立主軸其實並不在帕爾身上,而是在「韋伯對派翠克集團」上。日本人似乎都過度重視帕爾的存在,事實上帕爾在法官團內部不過是個「邊緣」的角色,最終連派翠克也放棄了始終固執己見的帕爾。
菲律賓法官德爾芬.哈那尼拉(Delfin Jaranilla)在開庭後大約一個月的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三日才初次加入審判。有關他的部分,似乎沒有人知道他的想法,但考量到他是「巴丹死亡行軍」的當事人,在對此事仍記憶猶新的前提下,可以推估他大概是站在贊成有罪判決的一方。
最年長的美國法官密朗.克萊墨爾(Myron C. Cramer)少將,因約翰.希金斯(John P. Higgins,麻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質疑東京審判的合法性而於開庭之初辭職,克萊墨爾因而於一九四六年七月接任美方法官一職。克萊墨爾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後即投身法律工作,從軍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改進入美國陸軍軍法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擔任軍法署署長,是一位對史汀生戰爭犯罪化路線進行嚴厲批判的人物。他就任法官時,已經接受了「紐倫堡原則」,但他因遲於到任加上個人的消極性,使美國在法官團內部的存在感明顯縮小許多。
如此這般,諸位法官的意見完全未能統一,因此法官團只能於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決定,關於管轄權的判決理由,將等到「最終判決」時才發表。
@小小標:瀕臨瓦解的法官團
在歐洲方面,紐倫堡審判採取由代表英國的傑弗里.勞倫斯(Geoffrey Lawrence)首席法官起草判決文,接著尋求他國法官意見的方法。雖說如此,實際上並無法完全由單一個人撰寫,因此判決書針對特定部分分配給各法官執筆。紐倫堡審判的法官團因為培養出相當的團結心,在判決書撰寫的運作上相當圓滑順暢。即便是個人意見書,也只有蘇聯法官認為應該更加重判刑而提出反對意見,僅此而已。
但東京審判的情況卻截然不同。根據派翠克寫給倫敦的報告書,提道:「隨著時間的經過,卻遲遲不見首席法官能與法官團針對單一判決意見整理出一套合意,其他的法官們對首席法官的所作所為都抱持著批判的態度。」
要處理一個新的法律,動用了十一位來自不同法律體系的法官,確實是太多了。一九四七年二月左右,法官們擅自處理個別業務,想要基於「紐倫堡原則」而做出統一的判決,幾乎成了不可能的任務。這個情況究竟有多嚴重,可以透過站在同盟國立場並為之代辯的橫田喜三郎(東京大學教授,後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見解反推,便可窺知一二。「這兩次的國際判決……,若在法律理論上能完全一致,即可獲得國際法上極具價值的決定性先例,藉此可以得到確立國際法規則的效果。」(〈東京判決之解剖〉)換言之,如果紐倫堡與東京審判不相一致,則判決在法律上、道義上的正當性將全面崩解。
接著從三月到四月,紐西蘭法官諾斯克羅夫特與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加已經不耐事態發展,皆向本國提出辭意。紐西蘭政府以辭任將導致大英國協破壞東京審判的理由,加以慰留諾斯克羅夫特。由此可知,審判團的危機――或者可以說是東京審判的危機,竟已發展到這種地步。
一九四七年三月底,派翠克向倫敦報告東京的現狀。四月,諾斯克羅夫特認為帕爾與羅林大概會提出反對意見,因此與英國的加德納中將談及,如果因此浪費了紐倫堡審判的成果,不如終止東京審判更為妥適。加德納的情報一傳回倫敦,英國首相艾德禮立刻要求外交大臣貝文妥善處置此事。
◎與麥克阿瑟的衝突◎
從英國政府的角度看來,東京的事態已經到了「毀滅性」的地步。
如果終止審判,東京審判將會變成一場鬧劇,「歐洲的威信」將瓦解粉碎,並將受到全世界的嘲笑;接著同盟國也將不得不接受、承認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正當性。
在經濟的苦境中,加上「帝國」瀕臨危機的狀態,英國至少想要維持住自身的「威信」,因此開始找尋有無防止東京審判失敗的方法。
英國的相關人士於五月十四日,在上議院的大法官室進行協商,並達成了兩項合意。亦即:
一、由麥克阿瑟打開僵局。
二、派遣盟國戰爭犯罪委員會(UNWCC)委員長萊特(澳大利亞代表)前往東京,說服法官們不再批評《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英國駐日代表處處長愛爾佛瑞.加斯科因收到這個命令,於同年五月十四日前往與麥克阿瑟會談。不過麥克阿瑟對「美國那些巧詐律師們」採取策略導致審判長期化感到憤怒,至於法官團的內部紛爭,則覺得很遺憾並不能給予韋伯絕對性的權力,對話至此便告一段落。而且麥克阿瑟將軍認為,法官團應該會判決珍珠港事件相關負責人有罪,並樂觀認為不必然要根據紐倫堡原則。
對麥克阿瑟而言,「紐倫堡原則」怎麼樣都無妨,可以說從基本上就與英國此番來訪所提的問題意識相去甚遠。
◎多數派的七位法官◎
一九四八年二月到三月,法官團內部整合出了「多數派」,成立了以下七位法官的集團。
派翠克(英國)
麥克杜加(加拿大)
諾斯克羅夫特(紐西蘭)
克萊墨爾(美國)
柴揚諾夫(蘇聯)
梅汝璈(中國)
哈那尼拉(菲律賓)
剩下的一方,這四位在決策過程中遭到排除而成為「少數派」:
韋伯(澳大利亞)
羅林(荷蘭)
伯納德(法國)
帕爾(印度)
所謂的「多數派」,皆為贊成「紐倫堡原則」的法官集團,認為侵略戰爭已然屬於國際法上的犯罪行為。派翠克大約由一九四七年春天,即開始拉攏克萊墨爾、柴揚諾夫、梅汝璈、哈那尼拉、伯納德(最終拉攏失敗),暗地進行集結多數派的作業;派翠克也與韋伯、羅林、帕爾接觸過,但從最初就對這三位不抱太大希望。
換言之,形成「多數派」該歸功於英國法官派翠克的運作。英國原本只為了「確保帝國威信」與「處罰殘虐行為」而參加了東京審判,結果卻意料之外地,不得不扮演起重要角色,挑起從撰寫起訴書到判決作成等之重責。
接著,組織起「多數派起草委員會」(委員長為美國法官克萊墨爾),開始作成法律部分的判決。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七日的會議中,決定了管轄權的判定理由。派翠克與麥克杜加不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加入獨自的新見解,而借用了紐倫堡判決中的「憲章之法具有決定性,本法庭受其拘束」的概念。
順帶說明,清瀨一郎寫道:「判決起草委員會成立後……法官並不出席,無論調查證人或法庭作業,皆使用不知名人士擔任委員來執行,而所謂的判決書,不過是參考起訴書與其他二、三種文件寫就的文章罷了。」(《秘錄東京審判》)這大概是法官們請秘書蒐集資料撰寫草稿的情況,被誇大之後傳入清瀨耳中,才出現這段文字。不過,實際上這並不符合事實。
◎判決的「紐倫堡化」◎
一九四八年四月審結後,七月三十一日發布了禁止公務員爭議行為的「政令二○一號」,引發了激烈的反對運動。八月下旬,眾所矚目的「帝銀事件」(強盜殺人事件)嫌疑犯落網,負責乙丙級戰犯的橫濱審判宣告九州大學活體解剖事件的判決(死刑五名、終身監禁四名)。接著昭電冤獄事件越演越烈,終於導致蘆田均內閣下台,第二次吉田茂內閣於十月十五日成立。各家報社接連追蹤這些事件,連負責不知何時才會出現判決的東京審判記者們,也被調派支援報導其他社會事件。
被告之一的武藤章寫道:「在監獄中待了三年,對人生已經抱持相當的覺悟,只想告訴對方,怎麼樣都好,趕緊說清楚;對於判決結果,既不抱希望,也不帶有期待。」(《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錄》)被告們對於漫長等待的心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當他們終於被告知公審宣判的日期時,已經是開庭前的十一月二日了。
根據韋伯的說法,多數判決的朗讀從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四日一直進行到十二日,共進行了七天。少數意見雖然會發表,但並不在法庭上宣讀。
東京審判的「判決」,採取多數審判的方法。《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二十六條記有「法庭判決為最終判決,且不再允許再審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雖然沒有相同的再審禁止規定,不過這不過是將麥克阿瑟的量刑變更權以「再審查」字樣來表現而已――紐倫堡審判中,同盟國管理理事會擁有量刑變更權,可確認量刑――並非意味其他司法機關有權「再審」。開庭前檢方也已經考量到被沒有「再審查」的訴願權。除去制度面問題,東鄉茂德表示:「東京審判的判決……是不可能變更的。若能更改,則美國政府、駐日盟軍總司令(SCAP)等將陷入fiasco(混亂狀態)。」(東鄉茂彥《祖父東鄉茂德的生涯》)
簡要來說,就是東京審判的多數判決是不具上訴審資格的最終確定判決。
接著來看一下多數判決的認定。首先,關於造成法官團分裂的管轄權法律問題,法庭表示,對於紐倫堡判決的立場持「無條件贊成」之意,認定法庭憲章「對本法庭法具有決定性,本法庭受其拘束。」換言之,此特別法庭的管轄權依據,僅根據法庭憲章;反過來說,關於憲章規定之「反和平罪」,法庭依此做出判決,便是理所當然。在《巴黎非戰公約》中已經將侵略戰爭視為「國際法上之不法」,只要「計畫、遂行(侵略戰爭)者……即為犯罪」。罪刑法定主義不過是「一般性的正義原則」,對於自覺有違法性的侵略者,不加以處罰才是「不當」。如此這般,強調國際軍事法庭之法,並未脫離國際法,並以此作為駁回辯護方管轄權迴避動議的理由。
至此,東京審判的判決,終於達成「紐倫堡化」了。
◎判決的「歷史」觀◎
在事實認定上,以二次大戰以前的日本「歷史」而言,皆採「反軸心國主義」的策略來描寫。多數判決中寫道:「由起訴事實來看,我們必須直接調查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五年,共十七年間的日本歷史。……我們的調查……也延伸至更過往的日本歷史研究。……起訴事實涵蓋的時期,也是日本在內政與外交上採取強力活動的期間。」
接下來判決書中詳述的事實認定,具備了以下三種特質。
第一種特質:多數判決書認定,自一九二八年以降橫跨十八年的期間,日本存有一種「全面性的共謀」。日本以掌控東亞、西太平洋、南太平洋、印度洋――至少沒寫成掌控全世界――為目的之「共謀」產生於田中義一內閣的一九二七年至二九年、「軍人一派」與提倡控制亞洲、西伯利亞東部、南洋諸島的大川周明合作的時期,之後便一直存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為止。
成為九一八事變導火石的柳條湖事件,被認定是「由隸屬於參謀本部的軍官、關東軍的軍官、櫻會的會員及其他人員,經過事前綿密計畫」後施行的,而作為陸軍中央的負責人建川美次少將,以及作為滿洲「關鍵人物」的板垣征四郎大佐皆遭指名。陸軍大臣南次郎「承認關東軍的行動」,板垣與土肥原賢二大佐則遭認定擁立遜帝溥儀。柳條湖發生前後的經過都有詳細的說明,但石原莞爾卻未登場。
接著在一九三六年,廣田弘毅內閣時決定的「基準國策」,實際上原本只併列了作為對外政策目標的陸軍北進論與海軍南進論,但在判決上卻誇大認定為「日本進行戰爭準備的整體基礎」,成為日本根本的侵略計畫。
之後這些共謀者們,逐次打垮日本的穩健派勢力,到了第一次近衛文麿內閣成立時,已然達成「支配日本」的狀態,為了達成他們自身的目的,「逐一遂行」必要的對外侵略。這樣的判決最後提出的結論是:為了遂行侵略戰爭的共謀,已經構成了最高程度的犯罪。
簡要而言,判決的「歷史」觀便是,罔顧從田中義一內閣至鈴木貫太郎為止歷經了十七任政權轉換,日本一直表現出「侵略政策的一貫性」。在此判決的歷史觀中,陸軍被當成了主角,但當武藤章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得知,連重光葵也認同不管發生任何事件,錯誤全部都在軍方時,感嘆地在日記中寫下:「連日本的外交代表也這是這種狀態,無怪乎外國會如此誤解日本。」(《軍務局長武藤章回想錄》)
布蘭農律師的結辯主張:「證據反而明白顯示……缺乏指導力……並不存在具有共通計畫與目的之中央集權團體。」(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日)如布蘭農所述,東京審判只明白顯示出日本政治不具中央集權性,呈現分權特徵,以及政治菁英之間充滿對立。東鄉茂德也對不通曉國際政治與日本政治狀況的法官們,「籠統」又「不負責」的定下判決,感到憤怒不已。(東鄉茂彥《祖父東鄉茂德的生涯》)
然而,法庭判決的使命,並不在掌握日本政治外交史的幅度,也不在於根據事實進行實證分析,而在於展示日本「錯誤的歷史」,並在此基礎上評判被告究竟是有罪還是無罪。
追根究底,美國導入「共謀」要件,是因為靠此構成要件便能將被告一網打盡,因此這不過是一種陰謀史觀的說明工具罷了。所謂基於事實認定的「共謀」,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根本不是值得生氣加以反駁的貨色。
正常而言,法官的工作應該是針對檢察官與辯護律師兩造的主張,進行綜合性的判斷。在這部分,多數判決派的法官所持立場卻與檢察官極為相近。雖然如此,前文已經闡明法官團內部的對立結構,各法官的想法相當多樣,而且有時立場相互對立,如果沒有派翠克的拉攏多數動員――日本的最高法院也有這種拉攏動員――法庭是有可能會陷入無法提出統一判決的狀況。
法庭與檢方各自獨立作業,是下面將說明的第二種特徵。
◎如果與「國際政治結果」切割◎
第二種特質:就是為了以均等方式處理長期的「共謀」過程,導致了美國相當重視的太平洋戰爭階段於判決中所占比重下降。特別是以珍珠港為目標的「殺人」訴因在過程中也遭削除。
判決文中淡淡整理了「走向珍珠港之道」,甚至提及東鄉外務大臣「確實有發電報」給日本駐美大使,該「訓令」電報命令駐美大使於攻擊開始前三十分鐘必須親手交付最後通牒,此敘述等於否定了檢方「無事前通知逕行攻擊」的舉證。「如果一切運作順利,為了警告珍珠港的軍隊,應該能給華盛頓方面大約二十分鐘的反應時間。雖然如此,日方確實也深切期望能達到偷襲效果,完全不給對方任何餘裕對應此次預料之外的事故」。這部分判決與其說是「單方面的論罪」,不如說是對美國相當冷淡。由基南對「珍珠港的相關事宜幾乎全遭漠視」而大為震怒來看,可以得知判決並不符合美國與麥克阿瑟的期待。
第三種特質:對於蘇聯的部分,日本對蘇政策遭法庭微妙地認定為「具積極攻擊性與侵略性」。判決中說明,《日蘇中立條約》(《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簽署後,松岡外務大臣迅速提及若德蘇爆發戰爭,日本將攻擊蘇聯,因此指責日本政府採取「不誠實政策」。但在張鼓峰事件上,「日軍的攻擊」係由陸軍參謀本部與板垣陸軍大臣「蓄意計畫」,故認定為「明顯之侵略行為」,判決文認為諾門罕事件也「應認定是由日本方面施行之侵略戰爭」(引用判決文上的強調旁點皆為作者所加)。
基本上,因顧忌於屬於多數派的蘇聯法官,因此判決向檢方告發的內容靠攏,即便難以直言斷定日方行為即屬「侵略」,仍採取了類似的微妙表達方式。
第四種特質:認定殘虐行為的起訴理由54及55為「經證實之犯罪」。且於「通例的戰爭犯罪」上列舉眾多實例,而在東京疏忽自己防止義務的指導者(包含文官),則判定負有不作為責任。「結論只能有一個,亦即――殘虐行為若非是日本政府、諸位官吏及軍隊指揮者的秘密命令,便是故意容許其發生。」
另一方面,關於「危害人類罪」,既無事實認定亦無起訴理由認定。羅林的日後回想提及,東京審判中「危害人類罪」的重要性不高,鴉片政策等控訴舉證也不夠充分。法官團比檢方更不重視此一犯罪類型。
我們經常聽到「歷史是由勝利者寫的」。無論古今東西,所謂的政府,就是否定前朝的政治體制,將其描述為一個「黑暗的時代」,藉此開啟自身的正當性。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外國),也寫下了否定日本舊體制的「歷史」。
然而,此種論罪式的「歷史」,往往會刺激失敗者一方的憤怒與屈辱感,加之描述的內容總有不合理之處,不可能永續流存。「歷史」的決定與確定,本身即為一種政治行為,從同盟國一方來看,使用此種論述實際上是相當危險的政策。
另外,從日本這方面來看又如何?確實,東京審判給日本人一個面對自己過去的機會。但我們也必須確認,在這個基礎上判決的「歷史」,不過只是國際政治的運作結果,與科學性的「歷史」具有本質上的差異。即便如此,我們也不至於全盤否定,認為「東京審判毫無意義」,畢竟,如果能將「國際政治的結果」切割出去,我們應該可以更冷靜地理解東京審判的判決。
(本文節錄自第五章「如何撰寫判決?」)
東京審判法官團的分裂
◎帕爾表明辭意◎
印度法官帕爾最初堂堂出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時,正值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法官團駁回辯方所提管轄權迴避動議之際。實際上除了印度與菲律賓之外的九位法官,已經達成文書合意,如果判決中出現少數意見,將不對外公開,但晚來的帕爾卻拒絕加入此項合意。當下,法官團立刻陷入苦惱,擔心少數意見可能被公諸於世。
如同英國法官派翠克(William D. Patrick)感嘆「帕爾從被任命之初,便採取了與眾不同的鮮明立場」一般,帕爾抵達日本之際,便對「反和平罪」採取否定立場。
不過,帕爾卻未...
目錄
第一章 如何看待東京審判
1/靖國神社的合祀問題
2/甲級與乙丙級之間
3/「文明的審判」論與「勝者的審判」論
第二章 東京審判的結構是如何誕生的呢?
1/以「凡爾賽的失敗」為鑑
2/美國的主導?同盟國的協調?
3/不起訴天皇與各國的疑惑
第三章 同盟國所起訴者為何?
1/同盟國檢察局的發動
2/被告與起訴事由的確定
3/檢察官方論理
第四章 日本如何因應呢?
1/合作與抵抗
2/辯護方的論據
3/「國家辯護」與「個人辯護」
第五章 如何撰寫判決
1/法官團的分裂
2/法官團的重整以及做出判決
3/如何解讀帕爾判決
第六章 為何未實施第二次東京審判
1/國際審判與後續審判
2/麥克阿瑟的執念
3/審判終結後的轉變
第七章 如何開始釋放戰犯
1/何時、如何辦理
2/《舊金山和約》中的戰犯條款
3/日本恢復獨立後的「重大國內問題」
第八章 為何甲級戰犯獲得釋放
1/展開赦免建議
2/「釋放急進論」的抬頭
3/在東京審判之後
後記
簡稱一覽表
參考文獻
相關年表
第一章 如何看待東京審判
1/靖國神社的合祀問題
2/甲級與乙丙級之間
3/「文明的審判」論與「勝者的審判」論
第二章 東京審判的結構是如何誕生的呢?
1/以「凡爾賽的失敗」為鑑
2/美國的主導?同盟國的協調?
3/不起訴天皇與各國的疑惑
第三章 同盟國所起訴者為何?
1/同盟國檢察局的發動
2/被告與起訴事由的確定
3/檢察官方論理
第四章 日本如何因應呢?
1/合作與抵抗
2/辯護方的論據
3/「國家辯護」與「個人辯護」
第五章 如何撰寫判決
1/法官團的分裂
2/法官團的重整以及做出判決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28收藏
28收藏

 70二手徵求有驚喜
70二手徵求有驚喜



 28收藏
28收藏

 70二手徵求有驚喜
70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