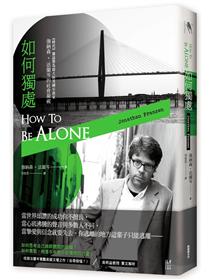這是一封寫給母親的道歉信,也是寫給母親的致謝函。小說家的細膩心思用文字一層一層追索與尋找內在對於母親的和解答案,
另一方面親自碰撞台灣對老者的照顧與看護,
反映當下社會對於長照的普遍匱乏,生如何生,
死如何死,尊嚴與愛嬌,在創作者的心中拔河拉扯……當告別來臨前,我一直讓母親知道,照顧妳,是此生榮耀……
生命有最後一場局賽尚未結束,這場加碼延長賽是我向神求,
祈求神給我時間,讓我有時間侍奉我的老小孩……
「生命如果沒有悲傷的平衡,那麼幸福這個詞也就失去意義。」__榮格
作家鍾文音與母親啟動一場漫長的告別。
新書中她寫年少時早逝的父親,寫年輕母親的命運鎖鏈,寫綑綁自己一輩子所逃不開的母愛情結……
年輕時如果可以遠走飛離,她一刻也不願多留。流蕩海外,人子遊蹤,少有一刻不捨。歷驗人世,大千世界太曼妙,但有一天人子老了,而母后更老,倒下的母親,讓她開口說,對不起,我愛妳。
這是一封寫給母親的道歉信,也是寫給母親的致謝函。
她來到母親居住的屋,沒有母親的房子她想像母親最後倒下時是何等光景?
她打開抽屜,獨居的親情緊緊收藏她早已經忘記的物件。
她搓洗從醫院帶回母親的衣物,眼淚決堤開啟告別的漫漫長夜。
她走過母親走過的路,前往母親登過的山,她的書桌就在病房,書寫與疼痛,病愛一體,女兒與母親,世上最長的分手距離。
一年半的時間,她往返於病院、母親所在的場所,在奔赴病塌喘息之間,在流了淚水又擦乾之間,在欣喜歡樂與憂傷沉默之間……隱隱感覺命運殘酷的雙眼銳利,面臨摯愛不知何時將至的死亡,深陷現實囹圄的寫作者如何拾起書寫的筆墨,在苦痛裡開出花朵?
小說家的細膩心思用文字一層一層追索與尋找內在對於母親的和解答案,另一方面親自碰撞台灣對老者的照顧與看護,反映當下社會對於長照的普遍匱乏,生如何生,死如何死,尊嚴與愛嬌,在創作者的心中拔河拉扯……
作者簡介:
鍾文音
淡江大傳系畢,曾赴紐約習畫。專職寫作,以小說和散文為主,兼擅攝影,並以繪畫修身。一個人周遊列國多年,曾參與台灣東華、愛荷華、柏林、聖塔菲、香港等大學之國際作家駐村計畫,講授創作等課程。
曾獲中時、聯合報、吳三連等國內重要文學獎。二OO六以《豔歌行》獲(開卷)中文創作十大好書。已出版《一天兩個人》、《少女老樣子》等多部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與長篇小說等,質量兼具,筆耕不輟。小說《在河左岸》改編成三十集電視劇,深受好評。
二O一一年出版百萬字鉅作:台灣島嶼三部曲《豔歌行》、《短歌行》、《傷歌行》,並已出版簡體版、日文版與英文版。
最新散文集《憂傷向誰傾訴》、《最後的情人》。
章節試閱
p.160-165
和母親一起流浪
父親走後,我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原地。
我離開母親,開始我人生流浪的長征,知識與愛情,只是一種掩護,泰半都是不知所以的隨際遇四處飄蕩,在讀書留學與幾場感情中虛度光陰。我長途流浪之後,有幾回返家時嚇到妳,尤其是地中海與北非郵輪的那回,母親開門時,嚇壞了,因為妳看到一個黑人,我曬得跟木炭差不多,曬傷的紅色褪去後轉成了黑色素,脫皮的肌膚與發舊的牛仔褲,看起來都像個浪女。丐幫之類的什麼波希米亞都是妳討厭的形象。
在我無數的旅途裡,其實在旅館隻身一人時,我常無端想起妳,帶著內疚似的想念,揪著心,像一場又一場童年的移動,那時的妳帶著小包包,裡面裝著企圖要賣出去的走私洋菸洋酒,妳勤勞地畫著移動的版圖,每天晚上入睡前想著明天要去哪一區賣,哪一區比較有店家,妳就像一個跑單幫的個體戶,熟悉每一條街誰有錢,知道哪一家店是老闆作主還是老闆娘作主,是喜歡飲酒還是喜歡抽菸的,妳都會留意著店家主人的癖好。
我在一間又一間的旅店移動時,白日張望著世界,到了夜晚盯著天花板發著愣時,母親的形象就跑進來了。那時我會很想打一通電話給妳,聽聽妳那年輕時因為在市場叫賣而早已粗啞的嗓子,即使只是喂一聲,因為那一聲代表妳還好好的。但我常常想著想著仍沒有打電話,有時候電話會響起,妳打來了。但妳彷彿也和我的心思一樣,只想聽我喂一聲,確定我在旅途裡安然無恙,然後就急匆匆地說國際電話太貴了,不聊了。徒留我在遙遠的彼端悵然。那種悵然是既想靠近又想遠離,既愛又畏,知道相處超過兩天就要翻臉的一種緊繃關係,因而遲疑著靠近的步履。
母親不曾和我流浪,最靠近的一次旅行計畫是說好要去琉球玩,但還沒成行,妳就突然癱倒,琉球成了未履行的失約之地。
而我開始和妳一起流浪。
這像是一場又一場的旅行輓歌,新流浪者之歌,在苦痛國度流轉。
母親,我本是一個人上路的旅者,現在妳的生命陌路,有我陪妳。
如果拍公路電影,我會這麼拍:女兒載著母親,車窗外不斷消退的是從以前到入夜之後的所有回憶之地,直到生命的盡頭,直到苦痛的邊境。
我的流浪生活圈開始以二十八天為一個週期,並被迫短暫就此生根。剪髮吃飯洗衣慢跑散步……流浪的地方沒有咖啡香與抵達的想像歡愉,只有酒精刺鼻與尿屎藥味撲鼻,以及無盡的孤獨和午夜的夢囈呻吟。
隨母親流浪在各家醫院,我才明白我們的健保制度是一家醫院健保給付僅提供住院二十八天,之後如醫生允許那可以有兩週自費的彈性,如二十八天的時間到了,而要轉去的另一家醫院病床卻尚未有著落時,那麼就有一種等著被拋棄之感。每當快要二十八天屆滿前,醫生或護理師總是跑來關切著,詢問下一家醫院有無著落等等,生怕我們要賴著不走。就像旅店中午前得要check out一樣,時間一到電話急催,多待一個小時就要加錢似的急急如律令。我總是擔心著我們要被丟到醫院外圍了,恍如是旅途流浪時,入夜卻仍尋不到旅館時的惶惶然。
常常護理長最後總會跑來關切母親動向,何時要離院啊,不能再住了喔,最慢這週五一定要辦離院手續喔,每個句子都加了個尾音,好讓我們聽了舒服些。那語氣像是捨不得母親離開似的,而往往當時下一個醫院病房還沒有著落。
在每回護理站的最後通牒裡,總是緊張兮兮地想怎麼辦,去排隊的醫院住房部還沒通知,但母親又要被踢出去了。然後我展開「社交」,透過臉書訊息傳給朋友,詢問是否有可能提供協助,但通常都是幫不上忙的,連知名醫生朋友最多也只是傳一個護理朋友的電話給我。平常說認識某某醫院名醫的朋友,也沒打通關節。
那時我們是醫院流浪的新手,這江湖還很不熟悉。
原來要轉院的前兩週就得去排隊,且要掛多間醫院,以避免排不到。當時正好流感發生,很多人住院,醫院病房全滿,連自費都一房難求。去振興醫院掛診時,排了一整個上午,見到醫生時只說了一句:滿了,無法收。我拿著母親的病歷走人,心裡想簡直被當成購物或者旅館訂房似的,一句滿了就結束。
這讓我想到我的流浪,有時下一站沒有預訂好旅館,就開始想是否要去住車站或者開始找朋友幫忙介紹他們的朋友是否可以臨時借住。
母親倒下的時間,剛好卡到舊曆年,醫院也是不斷來提醒告知:過年不收病患,所有的病人都要返家,之後再回到醫院。過年不准生病嗎?後來才知道真要住也可以,但得自費。說來說去都是錢的問題,然和看護聊才知道這已經是不錯的待遇了,因為有的醫院連自費也不行,因為護理人員休假,他們也無法看顧留在醫院的病人。自費對家屬是很大的負擔,但若母親回家,我們當時完全無法照料,連把她抬上沒有電梯的公寓都是問題。過年病房廊道靜悄悄的,猶如在星際漂浮的太空船,護理站更像是零星一兩個太空人守著空蕩蕩的太空站之感。母親的病房外是一座運動場,平日跑步運動的人不見了,幾個小孩放著沖天炮,偶爾閃過窗邊的鞭炮聲卻十分孤寂。過年了,我說。拉開蘋果綠簾子,母親撇頭望了窗外一眼,旋即闔上目光,瞳孔一瞬間有點濡濕。這是我見過最寂寥的病房時光,連看護都要請假拜拜與吃年夜飯。病人是回家的回家,送短期安養院的送安養院,剩下沒有其他選項的病人,我聽見廊道的盡頭有一家人在互道新年快樂,我剝了顆柑橘,果皮的氣味瞬間掩過鼻息,我面無表情地一瓣接著一瓣,吃著吃著忽然很想掉淚。
世間旅路如斯萬劫歷生,就這麼一瞬灰飛煙滅。
我握著母親的手,給妳冬日的溫暖,然後遞給妳一個紅包,就像童年一樣,只是收受的手換了,紋路變了。
舊曆年眨眼要過了,開市的鞭炮聲響從夜裡就爆響,而掛了兩三家醫院的電話卻仍無消無息,打去住院中心也都是沒有病床,只能等候通知,新聞報導著冬末的致命流感擠爆了病床,一床難求。
床,流浪一日的終點,在奔勞中覓得一床可歇憩,供旅人洗塵,躺下,床收容了旅人的身心或者愛慾。床,人身一生的終點,撤去的肉身等待下一具移進,不可見的無形動線,躺著時間的身體。
二十八天的時間到了,自費的時間也逼近了。終於電話響了,且一響就是好幾間,忽然病床不擠了,流感病人好了,母親的流浪旅程又取得了通行的護照。
就這樣,二十八的週期持續著,開始半年的循環。每個流浪的環節逐漸熟悉,運送的救護車已經開始見到熟悉面孔的司機,常採買物品的商家店員還會打電話來說有折扣,水果店告知柑橘快要到尾聲,看護開始要我留意輪椅和電動床的價位,並暗示她介紹的小楊很可靠﹝其實是他給的佣金很可靠﹞。
彷彿旅行時入住過的旅店不時傳來有折扣的簡訊,或者航空公司寄來的優惠特價套餐伊媚兒,或者不時跳出折價券將要過期的訊息……我的流浪充滿著藍天大海高山綠樹的誘人風光,或者飄滿咖啡美人的異旅氣息。而關於和母親的流浪,跳出來的字眼多是輪椅折價、氣墊床特惠、包大人買三送一、亞培買三箱送六瓶……毫無喜悅的折價,反而一直被提醒某種難言的疼痛。
護理站像旅館櫃台,夜晚總有失眠家屬殷切著急詢問各式各樣狀況,就像在流浪的旅館裡,旅人睡眼惺忪地說著水龍頭壞了、馬桶阻塞、電話不通、隔壁太吵等等。我也曾站在護理站多次,和護理站的人近乎客訴地說著隔壁床是疥瘡病患應該隔離,因為疥瘡感染很快,母親臥床不能自理,很容易就會感染了。或者我詢問著肺結核病患睡在母親隔壁床是否適宜的問題,那時只見護理站的人很冷淡地說這是非開放性肺結核啦,不用擔心。這肺結核名詞還是頗干擾心情,只見母親的看護臉色垮垮的,聽了這解釋仍一臉不高興。或者問著母親不斷拉肚子是否該改營養品,或者隔壁的不斷咆哮導致的失眠……我旅行邊界與邊界,很少駐足櫃台,而母親流浪醫院期間,我駐足櫃台的次數超過我二十年旅行的總和。
我可能也得了焦慮症了。
流浪的旅程終有離與返,母親的衣物隨著冬日延展到初夏,季節清楚地幫我們標誌這段流浪的時間維度。
每回轉院,我們都得陪同母親再次受苦一次,因為她總是再度失望,以為可以回家,結果卻又回到了醫院。
漫長的旅程終結束時,才想到和母親一起流浪了冬春夏三季節,回想又歷歷在目又飄忽已遠的記憶,就像一個旅人在旅行時無法回憶,必須旅程畫上終點,回憶才進來,從午夜的高燒囈語轉成日常的人生。
苦痛邊境的大街小巷
那時我的流浪生活圈環繞在奇異的兩端,痛苦的病房與甜美庶民生活。比如在關渡醫院旁剪髮,在新北市聯合醫院對面的星巴克寫作,在陽明醫院旁的天母一帶的百貨公司美食街吃飯。在竹圍馬偕醫院的大街小巷,猶如一座繁華小城。醫院旁的咖啡館,客人的對話多環繞在身體話題,或者家屬約保險公司的人在咖啡館談保險,疾病的語言不斷傳入耳內的是中風心臟病腎衰竭肝硬化紅斑性狼瘡帕金森氏症腸躁症胃潰瘍免疫系統失調內分泌失調糖尿病甲狀腺……嗅覺聞著咖啡香,視覺望著幽微的燈光,聽覺卻充滿身體的腐朽感,這是環繞醫院的獨有話語。
流浪的醫院雖不同,但周遭景觀卻多有雷同之處,只是規模大小的差異。必然有的杏一藥店、屈臣氏、速食店、便當店、雜物百貨行、眼鏡店、藥妝店、皮鞋店、理髮店、麵包店、服飾店、牙醫診所、小吃店、素食餐廳、有機店、健康鞋功夫鞋、醫療器材行、按摩足浴店、內衣睡衣小店、修灰指甲、水果賣場、超商、菜場……臨時集結的攤販擺貨人也特別多,高檔與低檔貨物形成兩端,就像病房單人自費房到擠著三、四個人的健保房的差異,不過攤販都是賣廉價物,好像病人不需要用到高檔的,似乎認為病人在醫院時間不會在意美醜似的,或者認為離開醫院就想把這種沾惹著病房氣味的物品丟棄了。其中又以在榮總醫院一帶最像庶民生活,有時只是幫母親出來買個小醫療物品,但卻深陷整條街的物件召喚。手裡拎著很多塑膠袋回到母親身邊。塑膠袋裡頭經常裝的有蔥油餅、新疆餅、東北饅頭與炸物,許多北方麵食與零食,大概都是我可以用吃來治偶發憂鬱的東西,我偏愛北方麵食,因此榮總外圍的攤販很能滿足。偶爾會買的有鞋子、竹炭內衣褲、一百元衣物或一百元手錶﹝給看護臨時用﹞……整條街店家與小販和人來人往的人群在騎樓裡彼此錯身。每隔兩三家就出現一家醫療用品店,維康、杏一、健康一生、躍獅……因規模不同而有不同服務,一般人的生病所需都可以找到,但像母親這樣重度傷殘所需的物件就得到大型醫療連鎖店訂購。每一家都加入會員,會員價價差吸引人,塑膠卡片一下子暴增好幾張,但多麼希望這些卡片全消失,再也用不著。
經常會遇到臨時叫喊著一件兩百九甚至一百元的擺攤人,但我並不想給母親穿廉價衣服,我想妳應該成為醫院的女王。但每回看到的是大陸看護讓母親穿一百元的廉價衣服,母親穿得像是女工般的在復健中心運動手腳,難怪那麼愛美的妳總提不起勁。
p.219-221
我與母親的摩斯密碼
我和母親合演一齣人間默劇,不是卓別林式的喜劇。
這空間有三個失語者。
一個是身體的失語者,一個是異鄉的失語者,一個是精神的失語者。
異鄉的失語者是阿蒂,剛抵達島嶼的印尼看護,只會叫我小姐小姐,還有阿嬤阿嬤。精神的失語者是我,一個寫作者的失語,文學的失語,作家成了午夜的喃喃自語者,在當代不斷說話卻是少有人懂的失語者。
若沒有言語,能否什麼都明白?沒有文字,如何表達思想?明白生滅將在無情風雨的夜裡告別,在光暈裡共舞,在隱含的憂傷中,一切化成碎片。
起初我也跟著進入沉默的銀河,忽忽只剩下淚水,難以言說。逐漸地母癱之事才對外說出來。幾場已經答應的講座,更是很難穩住心的動盪。
身體的失語者是母親,我和她的摩斯密碼是抓我的長髮一下代表﹝是﹞或﹝要﹞,兩下代表﹝不是﹞或﹝不要﹞。於今才發現留長髮有好處,方便她抓,讓她表示她要或不要。我告訴她,抓一下要,抓兩下不要。
母親只能不斷用好的左手撫摸我。左手成了唯一的表達工具,她成了永遠的左派。失語後,她的手顯得很重要。左手是她的表達工具,生氣捏我,或者招手,或者比畫。
她常把我的手握得很緊。然而大部分時候我去醫院看見她時,她的手都被套上乒乓球拍的護套而動彈不得。
不認識字真麻煩,曾經母親這樣對我說。現在更麻煩,因為失語之後,連書寫都無法補救。
因母親受傷的是左腦和語言區,又傷及聲帶,導致右邊癱瘓。舌頭往內縮,捲進去變短,無法說話。之前在加護病房還聽過幾次,後來就逐漸失去最後一點聲音。母親開口的第一句話是我的名字。
我最後一次聽母親說話的聲音是一月二日,新年過後的第二天。
那是很奇異的感覺,新年才和朋友互道平安,不久就接到母親昏迷的電話。而前一通是母親打來問我喝她煮的中藥湯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我想起母親說我嬰孩時安安靜靜,不哭不鬧,乖得像是個啞孩子。她說當時在鄉下差點把我養到餓死,所以說不說話也沒緊張過。我開口的第一句話是什麼?她也忘了,說應該也是媽媽爸爸吧。我在醫院裡,總想著母親如果重新開口說話,她會說的第一句是什麼?哥開玩笑說可能問家裡瓦斯關了沒?
總是漂流。但記得母親說過人吃一口氣,無論如何也要死在自己的信念上。什麼樣的信念足以讓人生讓人死?
我找個地方坐下來,看著流逝的人世風景,想弄懂母親的信念。
我們大多在眾人的注視裡長大,衰蕪、荒朽,最後真正可以成為自己的部分是那麼地微少。
當夜裡無盡的哀傷流淌在身體的所有血液時,點上一盞燭火,身體映在屋內白牆,像是一束白光下,待放映的膠卷,投射著靈魂的優雅狀態。
我是唯一的觀者,獨自看著過去,一部顧影自憐的影片,一部孤芳自賞的影片。但誰想孤芳自賞呢?連上帝自己也不想如此這樣孤單,有人說祂造人、造景就是祂也不想孤單的。生比死艱辛,但這艱辛卻又是為了修得「好死」。當我寫作時,我動用了最大部分的靈性,在那裡看見人的處境與卑微和透徹。
女兒這個寫作者的萬言,不如母親的一默。
p.160-165
和母親一起流浪
父親走後,我把母親一個人留在原地。
我離開母親,開始我人生流浪的長征,知識與愛情,只是一種掩護,泰半都是不知所以的隨際遇四處飄蕩,在讀書留學與幾場感情中虛度光陰。我長途流浪之後,有幾回返家時嚇到妳,尤其是地中海與北非郵輪的那回,母親開門時,嚇壞了,因為妳看到一個黑人,我曬得跟木炭差不多,曬傷的紅色褪去後轉成了黑色素,脫皮的肌膚與發舊的牛仔褲,看起來都像個浪女。丐幫之類的什麼波希米亞都是妳討厭的形象。
在我無數的旅途裡,其實在旅館隻身一人時,我常無端想起妳,帶著內疚似的...
推薦序
【編按】
在初夏午後,台北正處於滂沱雷陣雨的季節,因為新書我們與作者做了一次小小的訪談,在訪問過程中默默感受作者泫然欲泣的的憂傷,鍾文音說,我們每個人不必然會成為母親,但我們每個人必然都是一個孩子……照顧老小孩的歷程無比艱辛,新書中她寫,當告別來臨前,我一直讓母親知道,照顧妳,是此生榮耀……文學家的書寫是公共財,是夜深人靜足堪安慰我們的微光。
◎母親是我最後的情人
問:二○一五年《最後的情人》出版後,就沒有新作,這兩年間發生了什麼?
鍾文音﹝以下簡稱鍾﹞:二○一五年對我來說是極端的一年。出版《最後的情人》後,我前往愛荷華寫作駐村計劃,也回到年輕時讀書的現場─紐約。可是出發前總有一種隱隱的,暴雨將至,呼之欲出的惶然……有一種放不下的感覺,過去常常一出門就不知天高皇帝遠,想飛多遠就飛多遠。但這一次我的心裡覺得必須把握跟媽媽在島嶼的時光。
如果旅行時你的心裝了太多東西,你根本飛不起來,你的心都在墜地的狀態,我以前沒辦法體會旅行會想念家人,但這是我第一次有這種感覺。第一次把家人裝進去的感覺,以前心裡都是世界。
二○一四年三十七歲正值壯年的至親堂妹過世,接著跟我住了十年的姊姊在我駐村期間傳來過世的訊息。從愛荷華回來後,二○一六年一月母親倒下……這兩年的生命大概是這樣,一段愛荷華的野遊,一段被母親釘在島嶼的時光。從《最後的情人》到現在,我只剩下母親這個情人。
◎和母親同穿一雙鞋,同刺痛,同哀衿
問:在妳的作品中,「母親」是永遠的場景,也是重覆出現的場域,妳年輕時逃離母親,中年開始擁抱母親,讀到新書最後,我們可以說這是妳與母親的和解之書嗎?
鍾:母親對我的影響很大,好像她成就了妳,可是妳的任性又把她的愛毀掉。「母親」是很複雜的。每個人在家庭中都會有雙型塑自己背後的手,對我來說,型塑我的那雙手就是母親。我以前的書寫,母親是一個畏懼的原型,像第一本《女島紀行》,還有《在河左岸》,但現在比較不同了,現在我跟母親好像穿同一雙鞋,走她走的路,那鞋子裡面佈滿砂石,每走一步就戳痛著心。
說和解倒也不是,其實我沒有怨過母親。我是個很心軟的人,只是我覺得以前一直逃離她很不
對,因為她的疾病多少也都是心病,鍾愛的女兒老是野遊他方……
《憂傷向誰傾訴》裡寫到我的一個英國好朋友的故事,丈夫外遇,小孩一歲跟三歲,經濟上無法教養,本來想留給社會局,自己打算自殺……可是她媽媽生了病,回到台灣探望,她在醫院居然認不得媽媽……本來以為至少晚年會有些可堪記憶的樣子,才發現疾病會摧毀一個人的樣貌……突然間她被打醒了,後悔自己把生命浪費在一個根本已經轉身的丈夫身上?這件事影響我非常大。
母親中風倒下後,其實有兩次醫師都把我叫去「準備」,關於捨得和捨不得,關於生和死的學分。母親驟然倒下撼動了我。我看見我的不捨,她對我的執著,我們彼此生命裡未竟的功課。命運有其自身的隱喻,母親已經遺忘了她自己,連生病都還是只看著我,她一直在教我些事情,讓我了解她的愛。
◎文學無用,文學還不如一顆止痛藥?
問:無論是家人、朋友、伴侶,每個人終究會面臨與親愛之人告別的時刻,每個人告別的時間長短不同,告別的方式也不一樣。對於告別與不捨,妳認為自己找到平衡了嗎?
鍾:也許有學習到平衡,但說學習仍然抽象。每個人的苦多大過於文學所承載的所。我一度質疑文學的救贖,因為文學其實處理不了真正身體的苦痛,且感情深度往往也超越了文字,比如時在醫院聽到哀嚎聲,會覺得文學還不如一顆止痛藥。可是當午夜夢迴,文學還是救了你,因為那種孤獨,只有文學家可以融化你,比如我看羅蘭.巴特《哀悼日記》等等。但白天我常想搞文學幹嘛?想朗讀,媽媽又聽不懂,文學在醫院非常遙遠。以前講到錢我都覺得俗得要死,每次媽媽說妳要存錢啊,我都不理她。以前覺得是俗物,現在一點都不俗了。我覺得自己覺悟得很慢,當然不是說有錢就好,但至少不要讓母親操心,且不要求別人的幫忙。《捨不得不見妳》可以說也是對母親的道歉書,也是對母親的致謝函。
我想每個人都會經歷一些過程,人的情緒不是永恆性的定在那裡。上一刻我可能痛哭流涕,然後又一切平靜,於是趕快寫一點,但下一刻我又潰堤了。很多人以為書寫就可得到治療,其實根本沒有。因為文學抽象性的語言並無法抵達正在慌亂者的心,捕捉不到真實的苦痛。但我又想,文學不是哲學,它不提供答案。文學是一面小小的裂鏡,是作者種種的觀照,因認真書寫而折射了同樣有此苦痛的人,雖然文學照得不是很清楚,但有時被折射到時,也能有所慰藉或者洗滌。
我這樣寫或許也沒有療癒我自己,但通過這個過程,顯影了無法逆返的一段陪伴母親的時光。有時我走在繁華城市,常常一縷意識會乍然跑到陪母親在醫院流浪的場景,瞬間城市成了荒原,繁華中的荒原……走在台北,洪流大眾與你錯身而過……瞬間我自己的心有如契訶夫的小說,所有陌生人的辛酸都是作者的哀愁,此刻我突然就非常能夠體會了。
每個人的感情經驗,或需要的生命樣態都不同,我覺得我可能終生都在學習捨得和捨不得,這本書就像是一個提點,記錄陪母親打這場仗的歷程。這是我的一種感情揭露,一個時光指標。我知道我寫這些,有人會說妳為何不放下,妳要捨得啊,但我心裡想:廢話,捨得哪那麼容易,記憶的告別太難啊……
【編按】
在初夏午後,台北正處於滂沱雷陣雨的季節,因為新書我們與作者做了一次小小的訪談,在訪問過程中默默感受作者泫然欲泣的的憂傷,鍾文音說,我們每個人不必然會成為母親,但我們每個人必然都是一個孩子……照顧老小孩的歷程無比艱辛,新書中她寫,當告別來臨前,我一直讓母親知道,照顧妳,是此生榮耀……文學家的書寫是公共財,是夜深人靜足堪安慰我們的微光。
◎母親是我最後的情人
問:二○一五年《最後的情人》出版後,就沒有新作,這兩年間發生了什麼?
鍾文音﹝以下簡稱鍾﹞:二○一五年對我來說是極端的一年。出版...
作者序
【序幕】
母親的守夜人—啟動一場漫長的告別
三月驚蟄,母親分娩女兒的春日,野貓奔走,雷雨交加,晝夜潮濕,如體內住了座海,魚不斷洄游命運的迴圈。雨漫過河,漫過家門,穿行母親的夢境,然後女嬰漂浮,來到了恥骨下方,即將和她面世。
人世第一個見面的臉孔,是滿頭大汗的母親,剛剛結束撕裂疼痛的臉孔。
她說,這個女嬰差點要了我的命。
她說,這個女嬰命很硬。
女兒讓母親哭泣,但母親也曾讓女兒哭傷了每個夜與夜。
母親是女兒生命的第一尾魚,掙扎、擱淺、焦懼……母親的女兒,安靜啞寂,一刀刀都是疼痛的書寫,伴隨對整個人世的哀歡。
比如前一刻流淚,下一刻欣喜。
母親長年是天未亮起床,而我是天未亮前入睡。我們像兩輛列車交錯而過,她的清晨銜接我的夜夢,我的月亮隨著她的太陽下沉。如此就過了大半輩子。
直到母親突然倒下。
她最怕的事情發生了,突如其來的毫無防備。這是一個多麼奇異的詞彙:中風,極其殘酷的詩意之詞,奪取人自由意志與能力的詞。
風神雨師,捲起風浪颳起颶風,風吹得人面目全非,只能倒下臣服的風,如此狂烈,將母親的一生吹得落花流水,摧枯拉朽折枝斷葉。
唯根猶在。
無常,第一個功課。
她還要教我很多功課,所以不走了。在加護病房,我體會到這一點。能和死神拔河,撐過危險的生命,定然有其後續的意義。而我是母親最主要的懸念,我開始學習錯過的人生功課:生死大事無常迅速。
從沒想過可以再次回到十八歲前,和母親生活在同一個屋簷下的時光。
年輕時恐懼的時光,是恐懼母親的嚴厲語言與突如其來的暴怒。
現在和母親同住的恐懼依然,卻是害怕母親的靜默。
角色互換,不再是遊戲。
自此,明亮的母親屬於黑夜,黑暗的我屬於太陽。
自此,話多的母親泰半靜默,話少的我負責解碼。
被疾病禁錮的舌頭不再言說成話,我的名字是母親最後喃喃的舌音,她曾把每個人都叫成我的名,母親才是我的鋼粉。
我浪費大半生的時間在他人身上,而﹁時間﹂是最難換算成等值的虛幻東西,那些離去者遺忘了感情的付出不是能用數字換算的。只有和母親生活的時間才點滴入心,沒有虛妄,沒有算計,沒有是非。我時刻都在觀察她的狀況,但我自己也清楚知道,任何和時間在拔河的感情,都是具有十足的分量。
這回飛蛾不撲火了,飛蛾成了標本。
我回到以往只是我一個人所屬的洞穴,現在的洞穴人,包括把我帶到世界上的這個人。洞穴蝸居不再有溫暖的羊水,母親轉成釘在我骨上的肉,骨肉沾黏,稍一撕扯就痛徹心扉。
我們在命運交織的房間,呼喊愛。母親臥床,臥成一隻貓。母親失語,失成一只蠶。
母親是老小孩,女兒是小孩老。母親變女兒,輪迴就在眼前,不用等下一世。
愛,不必然天荒地老,但失去卻刻骨銘心。
妳躺在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我奔忙在太陽下的色身領地。
為妳,我流浪了很多以前我不會流浪的地方,學了很多不曾學過的東西,買了從未買過的用品,走進不曾走進的商家。那些醫療器材店琳瑯滿目,從沒想過服務一座色身的帝國需要如此繁複的工序世界。方便圈住被照顧者移位用的帶子,有著奇異的名稱:好神帶。好神好神,好神是否入滅?否則怎能讓人間如此苦痛?有意思的是人在幸福時又會遺忘神,在苦痛時才想要召喚神。
沿著醫院外的商街走著,就像走在生死輪迴之路。幫寶適的隔壁往往是包大人,健身運動器材前坐落的是無言的成排輪椅,亞培安素旁是嬰兒奶粉……兩個顧客彼此挑選,透現不同的喜憂神情。
器材行經常懸掛著廣告標語:「兼顧照顧者與被照顧者,感到幸福的新輔具」,但經常買了新輔具而沒用,原因是被照顧者不願意用,或者是照顧者覺得不實用。閒置的輔具,就像廢棄的玩具。
從玩具到輔具,一個小孩變成報廢的老人。
生活是如此真切,務實﹝要勤儉持家﹞又務虛﹝心須放空才不會陷溺傷懷﹞,如此就過了一年半載了,母親多了一個紀念日,她失能失語的那一天,必須銘刻那一天,提醒時間難以捕捉,提醒無常之迅速。
日日進出收容病體的空間,流浪在此領地是如此地苦痛。十多年前我在一本長篇小說寫過一段感情:太陽照不到的地方,我屬於你。母親躺下的地方也不屬於太陽了。
我成了母親的守夜人。
眼睛盯著起伏的胸膛,觀察那微小的呼氣通道,這使我常常一夜起身多回,躡手躡腳潛進母親的夢境,甚至偷偷在她的耳際說著話。或者我會唸著神佛的聖號,期盼母親將懸念的人替換成菩薩。
我是和月亮共進退的文字夜行者,輕易就成了母親的守夜人。
即使清晨無法早起,也都會先起來一下,讓早起的母親看一眼,讓她知道我在,這樣她會有安全感。她最怕不知身在何處,每回見到親人,總是緊握著手。但再如何地守著,也無法時時刻刻守著。因而母親泰半如懸浮物般的度過她晚年的日與夜,她和一個異鄉陌生人同處一室,繭居靜默如虛空。但虛空尚有雷電交加的轟然大響、尚有群鳥高歌拜訪,母親卻只有濃稠呼吸聲閃過她的平原。她從大山變成平原,從1變成一,從一躺成低於海平面。
我遊蕩無數的旅途,轉換無數比景片要快的風景,但在這生命轉運站的時光渡口、感情分離的碼頭上,不管多久終會鳴起的拔錨聲響,我將陪母親走這條陌路。她抱怨我過往的天涯海角不曾帶她上路﹝她不知道她一點都不是個好旅者,因為她牽掛又牽掛,心室因而不斷肥大,阻塞通道。疾病的隱喻,莫過於此﹞。現在她明白原來我是一個好旅者,好的結伴者,好的同行者,好的擺渡人。女兒值得母親信賴,值得她把最後的一哩路交給我,這讓我在繭居時光的淚水中,有了奇異的小小安慰,因而我開始流淌墨水,將其滲透至生命記事簿,徜徉在病愛與思索的心海。這樣的人生,這樣的晚景,或許有些啟示錄。
母親是抵達的一切
以前母親常掛在嘴巴說的話是有一天我早晚會被妳氣死。
沒想到,母親晚年卻是最常被我從死神手中救起。
長途跋涉,只為救妳。
自此我不再逃逸。
但我也看著自己的心越發地執著起來,甚至在照顧母親之後,變得神經質。夜晚起床好幾次去看母親是否有呼吸,常下意識翻棉被檢查母親尿床是否有濕疹,離開家裡就心神不寧地一直看手機,早晨第一通電話響起通常都會滾下床去接電話﹝應該算是被嚇醒的﹞,母親一有風吹草動就覺得自己沒有照顧好的自責疚愧……
執著的心是怎麼被滋養而壯大的?捨不得是如何噬咬著心?替眼睛乾涸的母親流淚,替無法吃東西的母親吃飯,替無法看電影的母親看電影,替無法行走的母親前進她無法再履及之地。
我願以我的雙眼,繼續幫滯留人世的母親討得一點生活的歡愉,但討好她已經很難很難,近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母親無法享有人世間任何一丁點快樂了,禁語禁足,囚在一方天地。在那段嘗試讓母親復健的醫院流浪時光,目睹醫院裡有丈夫殺病妻的人倫悲劇,目睹久病厭世而自裁的倖存者發生在病體空間的四周,目睹看護與被看護者的諸多八點檔劇情,目睹母親的苦痛……作為人子,我們該如何替無法做抉擇的親人按下選擇鍵?無效醫療文章與長照資源的訊息日日在手機裡轉載,不斷地跳出視框。但看別人清楚,到了自己是家屬時,決定就萬分困難。因為感情的連結深淺非旁人可以理解。我也曾經歷在母親加護病房時希望她不受折磨能夠快速好走,但隨著她的意識清醒,隨著相處的時間日增,心願轉換成希望她滯留人世的時間再長一點。時間也會滋長了執著,這提醒了我:「捨不得」只是一個階段,之後仍要練習「當捨則捨」。
從母親角度再到女兒角度,心情不斷來回切換,最終是母親決定了自己的命運,她還沒有要走,她還有許多功課要讓我學習。
雖知悉生老病死隨時虎視眈眈著,但人總有逃避之心,因此其實我從來沒有正視過身體病老之景,母親的示現,是我今生最大的一門功課,生死學、看護學、心理學、穴脈學、用藥學、溝通學……我學得好多好多,這些都遠遠比我的文學還要廣大而深遠。聯副請我寫:今天不談文學,擱淺許久﹝然我擱淺的又豈只是書寫呢,我的心擱淺撞礁﹞,雖可以談的東西很多,但有心情寫下的卻極少。因為這段時光的學習,是用母親的重病所換來的眼淚學分。
書寫無須援引「想像」,當「現實」層層疊疊都來不及挪用時,想像力再也飛翔不起來。
在縫隙時間的碎光裡喘息
這是我一個人看電影最多的時期了。什麼電影都看,甚至有過在電影院裡竟只有我一個人看電影的紀錄。如果一週兩三場,一年就可以看上百場。但我卻不記得我看了哪些片子,彷彿我是童年的母親,她帶我進電影院常常是一進入黑洞就開始打盹,她只是進去休息。而我也是進去休息,腦子放空。
這種逃逸就像是在被封存的洞穴中,突然見到時光的裂縫,僅僅是一絲裂縫就足以餵養氧氣。
以往的天涯海角,轉變成滯留在黑箱裡,從背後投來的一束光,或者吃咬爆米花的微碎聲響,都讓我想走上銀幕,化為影中人,成為怎麼樣都殺不死的人。
電影院賣票櫃台問,幾張票?
一張票。
中間位置嗎?
最後一排,最邊邊即可﹝沒說出口的是最爛的位置就行了﹞。
除了大學時代曾經好幾年狂看電影與勤跑金馬獎國際影展之外,就數這一年是我最密集看電影的時光,且近乎什麼電影都看﹝除了驚悚鬼片之外,生活已夠驚嚇了﹞。我一個人在電影院裡看著銀幕的人生,眼睛在銀幕上,心卻在母親身上。看著電影的人生,心裡滲著苦水。躲進其他人的人生,並沒有辦法換取自己的人生。回到家裡,只要一推開門,聽見一口痰咳不出,看到一滴淚流不開,耳聞喉間努力的擦撞音彈上來……母親病房的空氣就足以讓我的心霎時縮緊,淚水奪眶奔流。
如陷雨中泥淖,如處迷霧森林的行走者,如日落前在山巔眺望灰濛人間的孤單者,這大概是這一兩年我身影所能描繪的形象。
當摯愛陷落漫長的黑洞苦痛時,作為一個生命的同盟者,一個旁觀的介入者,一個介入的抽離者,除了陪伴、除了祈願、除了拜懺……所幸我是個書寫者,點燃一絲微火在母親的床岸前。
以文字挖開囚住母親的疾病領地,這是這段繭居時光的淚水與墨水。
血緣的繼承者,傷心的守夜人,靜默的失語者……前世滲透今世,過去疊印現在,啟動一場漫長的告別。
不管漫長有多久,當告別來臨前,我一直讓母親知道—我愛妳。
我捨不得不見妳。
直到不得不分離。
世上最長的分手距離—女兒和母親。
【序幕】
母親的守夜人—啟動一場漫長的告別
三月驚蟄,母親分娩女兒的春日,野貓奔走,雷雨交加,晝夜潮濕,如體內住了座海,魚不斷洄游命運的迴圈。雨漫過河,漫過家門,穿行母親的夢境,然後女嬰漂浮,來到了恥骨下方,即將和她面世。
人世第一個見面的臉孔,是滿頭大汗的母親,剛剛結束撕裂疼痛的臉孔。
她說,這個女嬰差點要了我的命。
她說,這個女嬰命很硬。
女兒讓母親哭泣,但母親也曾讓女兒哭傷了每個夜與夜。
母親是女兒生命的第一尾魚,掙扎、擱淺、焦懼……母親的女兒,安靜啞寂,一刀刀都是疼痛的書寫,伴隨對整個人...
目錄
序幕
006母親的守夜人
──啟動一場漫長的告別
1繼承者
019父女同種
056平原的母親
069姊姊
2回憶之地
085尋找母親的存在身影
089草山的缺席者
103囍門咖啡座
3捨不得不見妳
119不要太愛一個人
160和母親一起流浪
4母親的看護
185看護人生
195當一個作家變看護
204等待異鄉人
5失語者
219我與母親的摩斯密碼
222刀劍與玫瑰的語言
229放心,媽媽做鬼也會保護妳
240神的暗號
6母親的感官世界
245再看我一眼
249耳朵裡的小宇宙
252秋老虎的虎牙
256偽象鼻財神
258長在腹腔的嘴巴
7重返十八歲時光
275幫母親洗衣服
281穿母親買的衣服
8有母親的家
295母親不在的房子
306病愛一體的新書房
9只要能救妳
327神農氏與花女巫
332母親妳得跟上來
10一個業餘看護的備忘錄
序幕
006母親的守夜人
──啟動一場漫長的告別
1繼承者
019父女同種
056平原的母親
069姊姊
2回憶之地
085尋找母親的存在身影
089草山的缺席者
103囍門咖啡座
3捨不得不見妳
119不要太愛一個人
160和母親一起流浪
4母親的看護
185看護人生
195當一個作家變看護
204等待異鄉人
5失語者
219我與母親的摩斯密碼
222刀劍與玫瑰的語言
229放心,媽媽做鬼也會保護妳
240神的暗號
6母親的感官世界
245再看我一眼
249耳朵裡的小宇宙
252秋老虎的虎牙
256偽象鼻財神
258長在腹腔的嘴巴
7重返十八歲時光...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9收藏
19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19收藏
19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