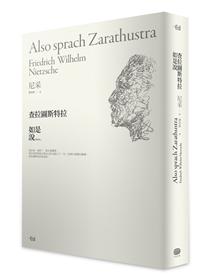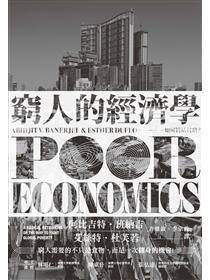為了壓倒個體的危險侵略性,文明總是企圖削弱個體,使他手無寸鐵,並如同攻城後留下駐防部隊一樣,建立起內在權威來監督個體的行為。
縱觀歷史,有些書能改變世界,這些著作扭轉了我們對自身和他人的看法,甚至引發爭論、產生異見,挑起戰爭,催化革命。這些著作發人深省,激發憤懣,鼓動情緒,提供慰藉。它們使我們的生命變得豐盛,卻同時帶來破壞。
“偉大思想家系列”叢書精挑細選了偉大思想家、先驅、激進分子和夢想家的經典著作,當中的思想曾經撼動世界,也塑造了讀者的人生。
佛洛伊德劃時代的觀點,顛覆了我們對自身的認識,構成了現代精神分析的基礎。在《文明與缺憾》中,他闡述了人類與生俱來具有“死亡本能”這個理論,指出人類文明扭曲了這種本能的侵略性,並將可怕的罪惡感強加於人類身上。
作者簡介:
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奧地利精神科、神經科醫生、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1856年5月6日出生,1881年獲維也納大學醫學博士學位。後執業行醫,擔任臨床神經專科醫生,終生從事精神病臨床治療工作。在探尋精神病病源方面,佛洛伊德拋棄當時主流的生理病因說,逐步走向心理病因說,創立了精神分析學說(Psychoanalysis),認為精神病起源於心理內部動機的衝突。他在探討問題時,往往引述文學、歷史、醫學、哲學、宗教等材料,揭示人們心靈的底層。主要著作有《夢的解釋》、《性學三論》、《心理分析導論》、《文明與缺撼》等。
章節試閱
文明與缺憾
1
人通常會追逐權力、成功與財富,羨慕別人所擁有的這一切,卻對生命中真正有價值的事物不予重視,並且依據錯誤的標準作出判斷──人們很容易發出這樣的感慨。然而,作出如此籠統的概括,很容易忽略人類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豐富多彩。有一些人受到同時代人的尊崇,然而其偉大品質和功績卻往往與很多人的理想和目標不相符合。人們或許認為這些偉人畢竟只為少數人所欣賞,而大多數人對他們毫無興趣。然而,由於人們思想和行為方式的差異,個人慾望和追求的不同,事情恐怕不會如此簡單。
有這樣一位傑出人士,與我有通信往來,並在信中稱我為好友。我曾給他寫過一封簡短的信,稱宗教乃是幻想。他回信說,對我的見解表示完全贊成,但他很遺憾我未能理解人們對宗教虔誠的真正根源。這種根源在於一種特別的感覺,他自己就從未擺脫過這種感覺,也在很多人身上得到驗證,因此他認為這種感覺亦應該為千萬人所共有,他稱之為“永生”,一種無邊無際的“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他繼續說,這種感覺純粹是主觀的,不是一種信條,不能確保人們永存,但卻是宗教力量的源泉,為各個教派和宗教體系所利用,被引到特定的渠道,自然被這些教派和宗教體系吸收和利用。單憑這種海洋般無邊無盡的感覺,人們即可稱自己是信奉宗教的,即使他們拒絕相信任何信條、任何幻想。
我那可敬的朋友1曾經以詩的形式讚揚了幻想的魔力。他的觀點給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惑。我自身絲毫不能感到這種“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要知道讓科學理性地對待感覺是很不容易的。人們可能會試圖描述感覺的生理表現,但這是行不通的,而且恐怕這種“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是無助於描述的。我們能做的只是研究那些與感覺最為接近的概念性的東西。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我那朋友指的“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是一種慰藉,就像一位古怪卻又才思新穎的作家給予選擇結束自己生命的主角的一種安慰:“我們不會脫離這個世界的。”這是一種與身外世界緊密相聯的歸屬感。對於我來說這屬於一種理性的領悟,當然也不乏情感的色彩,儘管在其他類似的思維活動中也不乏情感色彩。憑藉我自己的經驗,我實在無法讓自己信服這種“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但我無法否認在他人身上這種感覺實實在在地存在着。然而,唯一的問題是,這種感覺是否得到了準確的解釋,或者說是否應該理所當然地看作是宗教的源泉。
對於這一問題,我也沒有決定性的、建設性的解決建議。但僅僅憑一種直接的感覺,來告知人們與外部世界存在的聯繫,並用來解釋人們需要宗教的原因,這樣的想法從一開始聽上去就很奇怪,並且與我們的心理結構不相吻合。因此,我們需要找出一種心理分析的方法,對於這種感覺的遺傳起源作出合理的解釋。以下的思路即論證了這一點。我們通常不會產生比對自我更確定的感覺。人們大多會覺得這種自我是獨立的整體,並與一切其他的東西對立。其實不然,心理分析學的研究首先告訴我們這是錯誤的,事實上自我向內在延伸,延伸至一種我們稱之為本我的無意識心理實體,且界限模糊不清;自我就好像是本我的外表。對於自我與本我的關係,心理分析仍有很多方面可向我們揭示。然而至少表面來看,自我的輪廓似乎可以被清晰分明地勾勒出來。
只有一種狀態──誠然是一種不尋常的狀態,但不應被貶為病態的狀態──自我不再輪廓分明。在情愛的巔峰狀態,自我與對象的界限會變得模糊。儘管與認識相悖,戀愛中的人們總會宣稱“我”和“你”是一體的,並且隨時表現得像一體的。這種自我與外界的界限能夠暫時地被生理功能打斷,自然也會被疾病打斷。病理學的研究讓我們認識到,在很多情況下自我與外部世界的界限會變得模糊不清,或者說根本是被錯誤地劃分了。在有些病例中,人身體的某些部分,甚至是精神生活的某些部分,如觀念、思想、感覺,似乎變得很陌生,從自我中分離開來。在另一些情況中,他把那些明顯產生於自我並應該得到自我認識的事情歸於外部世界。因此,即使是自身的感覺也會產生混亂,而且自身的界限並不是恆定的。
通過進一步的思考,我們便可知道,成年人對於自己的感覺不可能與剛出生時相同,它必然經過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可以理解的是,這樣的過程並不能被實際演示出來,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構。對於一個新生兒來說,外部世界就是其感覺的由來;一開始,他並未將自我與外部世界分離開來。但在外部各種刺激的作用下,他逐漸學會了將自我與外界區分開來。他會發現,有些刺激源任何時候都可以向其傳遞感覺,後來他認識到這些刺激源屬於自己的器官;而另外一些──包括他最渴望的東西,如母親的乳房,會暫時挪開,只有通過哭喊才會重回眼前,以上這些區別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是以這種方式,自我首次碰到了“客體”,即某種外在的事物,只有通過特定的行為,才能促使它出現。將自我從各種感覺中分離出來,進而認識到“外部世界”;更進一步的誘因來自頻繁的、各種各樣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或者說幸福缺失),這種痛苦的感覺,只有在快樂原則發揮絕對作用時,才能得以避免和消除。
於是這樣一種趨勢就會產生,即將自我和任何可能產生這樣不愉快體驗的事物區分開,並將這種不愉快的體驗趕走,以便建立與一個陌生、險惡的外部世界相抗衡的純粹追求快樂的自我。這種以快樂為導向的原始自我必然會受到經驗的修正。畢竟,有些給予我們快樂、我們不願放棄的事物並不屬於自我,而屬於客體;而另外一些我們想要消除的折磨和痛苦,卻證明是來自內部,與自我密不可分。
於是,我們掌握了一種方法,通過有目的性地控制我們的感覺活動和合適的肌體運動,來區分甚麼是來自內部的(即屬於自我的),甚麼是來自外部的(即來自外界的)。這就向建立現實世界原則邁出了第一步,對未來發展起着支配作用。這種內部和外部的區分具有現實意義,使人們免於不愉快的經歷對自己造成的威脅。事實上,自我在驅除源於內部的某些不愉快感覺時,如果採取與驅除來源於外部不愉快事物同樣的手段,往往會成為重大心理疾病的起始點。
自我正是通過這種方法使其從外部世界中分離開來。更確切地說,自我在一開始是包括一切的,只是後來從自身中分離出了一個外部的世界。於是,我們現在的自我感覺,只是更為廣泛、包羅萬象的一種感覺的濃縮物,與自我和周邊世界更為密切的聯繫相一致。如果我們可以作如下假設,即自我的這種原始的感覺某種程度上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中存續下來,那麼它會像一個搭檔,與範圍狹窄、嚴格界定的成熟的自我感覺共存。與之相對應的內容就是那些與宇宙一體和無邊無際的概念,即我的朋友常用來闡釋“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的概念。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假定:最初存在的事物仍然會存續下去,與後來從中演化而來的事物共同存在呢?
毋庸置疑!這種情況無論發生在精神領域還是其他領域,都不足為奇。以動物世界為例,人們通常認為動物是由低級向高級進化的。然而,如今所有低級形式的生命依然存在。有些大型爬行動物,如大型蜥蜴,已經滅絕或進化成哺乳動物,但大型爬行動物真正的代表──鱷魚卻依然存在。這樣的類比或許有點牽強,況且很多存活下來的低級物種也並非現存的高級物種的祖先,中間的環節大多已經消失了,我們只能通過重新構建才可以得知,這就削弱了這個類比的可比性。然而,在精神領域,原始的感覺與從中演化出來的感覺是共存的。這樣的現象非常普遍,不必舉例去證明。這往往是發展中的分叉導致,即一部分(從數量上講)態度或者本能衝動保持不變,而另一部分卻得到進一步發展。
由此,又提起一個精神領域裏更為普遍的記憶和保留的問題,這一問題幾乎尚未研究過,卻充滿研究魅力、意義重大,我們不妨探討一下,儘管理由尚不夠充分。我們曾經認為,我們經常遺忘是因為記憶痕跡的破壞,即記憶痕跡的消亡,但在糾正了這一錯誤觀點之後,我們發現事實恰恰相反。即在精神生活中,一樣東西一旦形成就永遠都不會消失,一切皆以某種形式得到保存,條件合適時,皆可找回。例如,只要(因催眠或精神疾患)回到從前,即可找回當時的記憶。這樣的假設意味着甚麼,讓我們試着用另一領域的類比來揭示。以“永恆的城市”的發展為例,歷史學家告訴我們最早期的羅馬是一個四方城,是帕拉蒂尼山上用柵欄圍起來的居住點。
之後是七山城階段,是由各個分散的山丘上的居住點組成的聯盟。接着,是塞維安牆圍起來的城市。再之後,經過羅馬共和國的不斷變遷,以及經歷過帝國時代的早期,就成了奧瑞里安皇帝用城牆圍起來的城市。我們不再向前追溯城市所經歷的種種變遷了,只是不由自主地會想,如果一個擁有豐富歷史學與地形學知識的旅行者去羅馬旅遊時,他能發現羅馬早期各個階段的多少遺跡呢?他會發現除了一些缺口,奧瑞里安的城牆並沒有多大的變化。
他可以不時地看到挖掘出土顯露出來的一段段塞維安城牆上的痕跡。憑藉足夠的考古學知識(至少要比當今考古學家具有更豐富的知識)他能看出整個塞維安城牆的整體佈局,透過現代羅馬城的規劃他能看到羅馬四方城的輪廓。至於古城中曾經的建築物,他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找到的,因為它們已經不存在了,頂多能找到一些殘片而已。關於羅馬共和國的豐富知識至多能使他指出羅馬古城中的廟宇在當時究竟位於何方,公共建築究竟曾經建於何處。現在這些地方早已被廢墟掩蓋──但並非是原來建築的廢墟,而是在這些建築被焚燒、破壞後又建起來的建築的廢墟。無須贅言,古羅馬的這些遺跡,已成為碎片,散落在文藝復興後近代興建的大都市的混亂之中。誠然,舊址依然存在,只是掩埋在現代建築之下。像羅馬這樣的歷史古城,過去就是這樣延續下來的。
現在讓我們作這樣一個奇妙的假想,即假定羅馬並非是一個人們居住的地方,而是一個與羅馬一樣有着漫長而豐富多彩歷史的精神實體。在這個精神實體中,一旦形成的東西就不會消失,並且先前的發展時期與現今是共存的。對羅馬而言,就相當於一直到被哥特人圍攻時,塞弗尤斯宮殿與凱撒大帝皇宮依然矗立在帕拉蒂尼山上;聖安吉羅堡的城垛上仍然裝飾着美麗的塑像。不僅如此,朱庇特神廟會屹立在卡法萊里—克萊門蒂諾宮之上,而沒有必要將後者移除,而且,這座神廟不僅具有當時的形態,即羅馬帝國時期所見到的形態,還保留着更早期的姿態,依然保留着伊特魯里亞人的元素,其簷口依然用陶瓦裝飾。在如今的圓形大劇場,我們仍然可以欣賞已經消失的尼祿時代金色的房屋。在萬神殿廣場上,我們不僅可以找到今天由哈德良傳給我們的萬神殿,同時,還能找到拉格瑞帕人所建的最初的大廈;在同一塊土地上,矗立着密涅瓦聖瑪麗亞教堂以及該教堂的前身,即古老的神廟。觀察者也許只需要改變他的視線或位置就可以看到其中一個或另一個。
顯然,再進一步展開這樣的想像毫無意義:結果會無法想像,甚至荒誕可笑。我們要在空間上表現歷史順序,唯一的辦法就是將空間鋪開並列,因為同一空間不能存放兩個不同的事物。這樣的嘗試似乎是一項沒有意義的遊戲。唯一的正當理由是:它向我們表明,通過形象的描述,我們距離掌握精神生活的特性還有多遠。
但是有一個異議我們必須回應。人們或許會問,為甚麼要把一個城市的過去與我們精神的過去相提並論呢?即便是對於我們的精神而言,一切過去皆被保存下來,這個假定也得滿足一個前提,即我們的大腦必須是完整的,其組織結構沒有受到創傷或炎症的損害。這些疾病的原因可以比作是破壞性的因素。然而對於一個城市而言,這些破壞性因素是司空見慣的,即便這個城市不像羅馬那樣動盪不安,即便像倫敦那樣幾乎沒有遭到外敵的蹂躪。一個城市的和平發展少不了拆除和更新一些建築,基於此,任何城市都無法與精神有機體相比。
我們欣然接受這樣的異議,放棄鮮明對比的做法,轉而與更為相關的事物相比較,如動物肌體和人類肌體。但這裏我們也會發現同樣的問題。肌體成長的早期階段根本沒有被保存下來,只是為後期階段提供材料,並被吸收到後期階段。成年人的身體中是找不到胚胎的,兒童的胸腺在青春期之後會被結締組織取代,胸腺的形式不復存在。在成年人的骨骼之中,固然可以找到兒童時代骨骼的大致輪廓,但骨骼在不斷加長、增厚並最終定型,在這一生長過程中,兒童的骨骼形態消失了。事實上,早期階段與最終的形態並存,也許只有在精神領域中才可能發生,我們根本無法拿其他事物與精神相提並論,並試圖闡釋精神這一現象。
也許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扯得太遠了。或許我們應該滿足於這樣的結論,即過去在精神生活中可能會得到保存,沒有必要被摧毀。情況可能是這樣的:即使是在精神領域之中,過去、陳舊的東西也會變得模糊或者被吸收,不管是在事物的正常發展情況之下或者是在其他例外情況下。更有甚者,我們不能利用任何方法使它們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又或許只有在特定的有利條件下我們才可能做到。對於這一點,我們無法得知。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堅信在精神世界中,對過去的保存記憶是一條定律,而非令人驚訝的例外。
因此,如果我們準備承認許多人都有那一種“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並欲將其追溯到自我感覺的早期階段,那麼一個新的問題就又出現了:是甚麼東西使得這種感覺被認作是宗教需要的源泉呢?
我並不覺得這種說法是令人信服的。畢竟一種感覺只有是某種強烈需要的表現時,才能成為力量的源泉。我認為,宗教的需要無疑是從嬰兒的無助,和由此引起的對父親的渴望中衍生出來的,尤其因為這種感覺不僅僅存在於童年時代,而且由於恐懼命運的至上權力,它被永久地保存了下來。我實在無法找出對於兒童來說比父親的保護更加強烈的需求。因此,那種可能力圖恢復無限自戀的“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在宗教需要中就不可能發揮主要作用。人們信奉宗教的緣由,可以清晰地追溯到孩子的無助的感覺中。可能這其後還隱藏着甚麼,但目前我們還不得而知。
我可以想像這種“如海洋般浩淼”的感覺隨後與宗教發生了聯繫。與這種浩渺感覺相連的觀念認識是,“自我與宇宙融為一體”,這成為把宗教當作慰藉的初步嘗試,即以另一種方式否認自我感覺到的源於外界的危險。我不得不再次承認研究這些無形的概念非常困難。我的另一個朋友懷着對知識的極大渴求,做了一個極其不尋常的實驗,變得似乎無所不知。他向我保證說,人們在練習瑜伽的過程中,背對外界,將注意力集中到肌體的功能之上,運用特殊的呼吸方式,可以獲得全新的、宇宙般的感覺。他把這樣的感覺解釋成向精神生活被長久掩蓋的原始形態的回歸。他由此可以說看到了神秘主義智慧的重要生理基礎;也找到了這與諸如恍惚、入迷這類難解的精神狀態的關係。但我還是忍不住用席勒民謠中潛水者的話來說:
……讓他欣悅吧,那在玫瑰色的光芒中呼吸的人。
----------------------------------------
1 羅曼‧羅蘭。
文明與缺憾
1
人通常會追逐權力、成功與財富,羨慕別人所擁有的這一切,卻對生命中真正有價值的事物不予重視,並且依據錯誤的標準作出判斷──人們很容易發出這樣的感慨。然而,作出如此籠統的概括,很容易忽略人類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豐富多彩。有一些人受到同時代人的尊崇,然而其偉大品質和功績卻往往與很多人的理想和目標不相符合。人們或許認為這些偉人畢竟只為少數人所欣賞,而大多數人對他們毫無興趣。然而,由於人們思想和行為方式的差異,個人慾望和追求的不同,事情恐怕不會如此簡單。
有這樣一位傑出人士,與我有通信往來...
作者序
偉大思想系列”中文版序
企鵝“偉大思想系列”2004年開始出版。美國出版的叢書規模略小,德國的同類叢書規模更小一些。叢書銷量已遠遠超過200萬冊,在全球很多人中間,尤其是學生當中,普及了哲學和政治學。中文版“偉大思想系列”的推出,邁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歡欣鼓舞。
推出這套叢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再次與一些偉大的非小說類經典著作面對面地交流。太長時間以來,確定版本依據這樣一個假設──讀者在教室裏學習這些著作,因此需要導讀、詳盡的註釋、參考書目等。此類版本無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夠重建托馬斯‧潘恩《常識》或約翰‧羅斯金《藝術與人生》初版時的環境,重新營造更具親和力的氛圍,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當時,讀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理性思考外沒有其他參照。
這樣做有一定的缺點:每個作者的話難免有難解或不可解之處,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識會缺失。例如,讀者對亨利‧梭羅創作時的情況毫無頭緒,也不了解該書的接受情況及影響。不過,這樣做的優點也很明顯。最突出的優點是,作者的初衷又一次變得重要起來──托馬斯‧潘恩的憤怒、查爾斯‧達爾文的靈光、塞內加的隱逸。這些作家在那麼多國家影響了那麼多人的生活,其影響不可估量,有的長達幾個世紀,讀他們書的樂趣罕有匹敵。沒有亞當‧斯密或阿圖爾‧叔本華,難以想像我們今天的世界。這些小書的創作年代已很久遠,但其中的話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智力生活、社會規劃和宗教信仰。
“偉大思想系列”一直求新求變。地區不同,收錄的作家也不同。在中國或美國,一些作家更受歡迎。英國“偉大思想系列”收錄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則默默無聞。稱其為“偉大思想”,我們亦慎之又慎。思想之偉大,在於其影響之深遠,而不意味着這些思想是“好”的,實際上一些書可列入“壞”思想之列。叢書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叢書其他作家的很大影響,例如,馬塞爾‧普魯斯特承認受約翰‧羅斯金影響很大,米歇爾‧德‧蒙田也承認深受塞內加影響,但其他作家彼此憎恨,如果發現他們被收入同一叢書,一定會氣憤難平。不過,讀者可自行決定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們衷心希望,您能在閱讀這些傑作中得到樂趣。
“偉大思想系列”出版人
西蒙‧溫德爾
偉大思想系列”中文版序
企鵝“偉大思想系列”2004年開始出版。美國出版的叢書規模略小,德國的同類叢書規模更小一些。叢書銷量已遠遠超過200萬冊,在全球很多人中間,尤其是學生當中,普及了哲學和政治學。中文版“偉大思想系列”的推出,邁出了新的一步,令人歡欣鼓舞。
推出這套叢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再次與一些偉大的非小說類經典著作面對面地交流。太長時間以來,確定版本依據這樣一個假設──讀者在教室裏學習這些著作,因此需要導讀、詳盡的註釋、參考書目等。此類版本無疑非常有用,但我想,如果能夠重建托馬斯‧潘恩《常識》或約...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收藏
3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