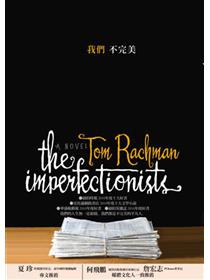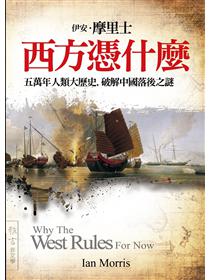真正的愛,是明白愛你有多困難,還選擇愛你。
真正的長大,是知道生活的真相,依然熱愛生活。
張悅然,中國八○後最富才情且最受歡迎女作家
曾入圍法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
在名聲鼎沸的時刻沉潛,花十年琢磨一部作品
二十七萬字鉅著《繭》,深刻鑽寫當代青年的心靈困境
以為一九九○才剛過,一轉眼已快三十年
上一輩的傷害無可挽回,下一代的寬諒之路如何展開?
三千里路的遠,遠不過成長的曲折
梁文道、余華、閻連科 慎重推薦
★《亞洲週刊》年度小說
張悅然以《繭》榮獲2016第十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2016誠品書店閱讀職人大賞(大陸)「年度最期待作家」、《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中國青年領袖」
「就像李佳棲這個名字所喻指的那樣,她如同一隻鳥,一直在尋找適合她棲息之地。但她所需要的不是一個歇腳的地方,而是一個精神上的家園。這樣的選擇註定無法被大多數人理解。但是,這種試圖和父輩建立連接的努力,是可貴的。歷史是由無數個體的歷史組成的。我們每個人都承擔著個體歷史的收集和記錄的工作。」——張悅然
五十年前,那個下雨的夜晚,廢棄的醫院大樓水塔內究竟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一根鐵釘就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榮耀的背後隱藏著什麼樣的悲劇?
一個是受人敬仰的院士、名醫,一個是意識全無的植物人,他們彼此之間有著什麼牽連,當年鑄下的重罪以為無人知曉,卻如毒液漫進了三個家族及其子孫,造成無可轉圜的遺疚。
李佳棲和程恭,兩個八○年代出生的年輕人,活困於不再年輕的父祖輩的愛與折磨裡。故事以兩人視角交錯展開,李佳棲交付自己全部的熱情,去靠近,去體會父親,但它卻無法兌換成任何實質性的愛。把愛放在虛無的對象身上,不會有分離和背叛,但也不會得到慰藉和溫暖。即便如此,她寧可圍在亡靈的篝火旁取暖,也不願意回到熱鬧的現實中來。程恭,他想打破祕密的禁忌,卻呵護着祕密,他想遠離家庭的束縛,卻一直守在原地。他有理由恨,但沒有恨。他漸漸認為:一些人的生命可能天生比另外一些人尊貴,他們掌握著擺布那些卑微生命的權力。他甚至開始碾壓他認為比他更卑微的生命……
作者簡介:
張悅然,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著有短篇小說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愛》,長篇小說《櫻桃之遠》、《水仙已乘鯉魚去》、《誓鳥》等作品。
作品被翻譯成英、日、韓、德、西班牙、義大利等多國文字。
曾獲得「華語傳媒文學獎」最具潛力新人獎、年度小說家、人民文學獎優秀散文獎、新加坡大專文學獎、春天文學獎,《人民文學》評選「未來大家Top20」,《誓鳥》入選2006年中國小說排行榜,《十愛》入圍愛爾蘭「法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
2008年創辦了文學主題書《鯉》系列,擔任其主編。2012年起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章節試閱
孩子,我所能給你的祝願不過是些許不幸而已。
—— 薩克萊《玫瑰與指環》
第一章
李佳棲
回到南院已經兩個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裡都沒有去。哦,還去過一次藥店,因為總是失眠。
我一直待在這幢大房子裡,守著這個將死的人。直到今天早晨,他陷入了昏迷,怎麼也叫不醒。天陰著,房間裡的氣壓很低。我站在床邊,感覺死亡的陰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盤旋。這一天終於要來了。我離開了房間。
我從旅行箱裡拿出厚毛衣外套。這裡的暖氣總是不夠熱,也可能是房子太大的緣故。我一直試著和那種從牆皮裡滲出來的寒冷相處,終於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我走到洗手間,沒有開燈。細細的燈棍散發出青寒色的光,會讓人覺得更冷。我站在水池邊洗臉,想著明天以後的事。明天,等他死了,我要把這房子裡所有燈都換掉。洗手池的下水管漏了,熱水汩汩地逸出來,在黑暗中靜靜地流過我的腳面,像血一樣溫暖。我站在那裡,捨不得把水龍頭關掉。
我走下樓,到廚房裡煎了兩只蛋,把切片麵包放進烤麵包機。我坐在桌前,慢慢地吃完早餐,然後從儲物間搬出梯子,把所有房間的窗簾都摘下。再回到一樓客廳的時候,發現它完全變了一個樣子。
我站在門邊,瞇起眼睛看著光禿禿的大窗戶。陽光照亮了角落裡的每一顆灰塵,吹拂著房間裡的祕密。
中午過後,我回到這個房間來看他。他的身體壓在厚厚的鵝毛被底下,好像縮小了一點。天仍舊陰著,死亡繼續盤旋,遲遲不肯降下來。我感覺胸口窒悶,太陽穴突突在跳,穿起大衣,從這幢房子裡逃了出去。
我在醫科大學的校園裡漫無目的地走。閒置的小學、圖書館背後的回廊、操場上荒涼的看台,這些都沒有讓我想起你。直到來到南院的西區。從前那片舊樓都拆了,現在是幾幢新蓋的高層公寓,樓洞前安裝著錚亮的防盜門。我走到最西邊,繞過它們,驚訝地發現你家那幢樓還在,被高樓圍堵起來,孤零零地縮在牆邊。
這麼多年過去了,我不相信你仍舊住在裡面。可我還是走進去,按響了一○二室的門鈴。裡面的人應聲說,進來。我遲疑了一下,拉開門。房間裡很昏暗,爐子上似乎在煮什麼東西,洇散著很重的水氣。有個男人坐在沙發上,閉著眼睛,好像睡著了。隔著陰鷙的光線、濕漉漉的水氣以及十幾年的時光,我認得出那是你。程恭,我輕輕叫了一聲。你慢慢睜開眼睛,好像一直在等我,等得乏了,就睡了過去。有那麼一刻,我幾乎懷疑是不是早就約好和你見面,只不過是自己失去了記憶。可事實上你並沒有認出我,在我說了我是誰以後,也表現得很冷漠。我吃力地和你寒暄著,提到從前的朋友,問起廢棄的小學,很快把最表層的話都說完,就陷入了沉默。我想不出繼續留下的理由,只好起身告辭。
你把我送到門口。我說再見,你說保重,我轉過身去,門在我的背後關上了。走廊裡很靜,能聽到防盜門鐵櫺上灰塵震落的聲音。我站在那裡,不敢邁出樓洞。生怕一旦匯入外面的天光,我們就會再度失散。冷風湧進來,防盜門吱呀呀地響了幾聲,像是有個人在暗處歎氣。一些含混的念頭在心裡,如同奄奄的火種,經風一吹,又活了過來。我好像有點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到這裡來,鼓起勇氣又按響了門鈴。我約你晚上到小白樓來一趟。沒等你反應過來,我就轉身走了。
我沿著湖邊的小路慢慢往回走。再回到這間屋子的時候,內心變得很平靜,從抽屜裡拿出那張一直沒看的光碟,放進影碟機。然後泡了茶,搬來兩把椅子,坐下來等你。窗外的天光漸漸乏暗,床上的人喃喃自語了一小陣,好像在作一個很深的夢。他呼吸得非常賣力,整個屋子裡都是從他的爛肺裡呼出的醬紫色空氣。光線暗下去,忽然又亮起來一點。迴光返照的天色,好像要有什麼異象出現。大風把窗戶吹開了,我走過去關上,才發現外面下雪了。我忽然覺得你不會來了。可是我仍在等。
我隱約知道,一切必將這樣發生。天完全黑了,雪下得越來越大。我走到窗邊,眺望著遠處的路。
已經沒有路了,只有一片茫茫的白色。我一直盯著它,看得眼睛幾乎盲了。終於,一個黑點在眼底出現,像顆破土萌發的種子,衝開了那片白色,在視線裡擴大。是你朝這邊走來。
你什麼也沒有問,就跟著我走上樓梯,來到這間屋子。你好像早就有預感,看到他躺在床上,並沒有表現出驚訝。你向前走了幾步,以一種總結性的目光端詳著他的臉,好像在丈量他的一生。那是太複雜的運算,你有點迷失了,只是怔怔地盯著他,直到我搬來椅子,讓你坐下。
是的,你看到了,他就要死了,我的爺爺。我知道我應該給醫院打一個電話。他們會立即派車把他接走,連夜召集專家會診,竭盡全力搶救。生命或許可以多維持幾天,但也不會太久。然後他們開始準備葬禮—李冀生院士的隆重葬禮。追悼會那天,我將作為唯一到場的家屬和大家一起為他送行。
人們眼含熱淚念誦他的生平,慢慢挪著腳步瞻仰他的遺容,一些不認識的人走上來和我講話,對我說我爺爺是怎樣一個人,偉大、睿智、令人尊敬……省長或市長也會趕來,親切地握住我的手,對我說節哀順變。攝像機鏡頭像一條忠誠的狗,跟著他搖過來,在我的臉上採集欣慰的表情。一切都會有人打點好,我什麼都不用做,除了準備好充足的眼淚。
我應該也能哭出來吧,不是因為他,而是為了那些和他一起離開的東西。可是我無法讓自己按下醫院的電話號碼。一旦撥通電話,他的死將會變成一樁公共事件,和我再也沒有關係了。他的身邊圍滿了護士、醫生、他的學生和同事、來探望的領導,還有媒體……人們烏烏泱泱擠進他生命最後一點時間裡,展現出這場即將到來的死亡應有的規模。死亡的規模就是他生命的重量。一艘巨輪的沉沒。
我不應該阻止一個偉大的人隆重地死,我知道,可是眼下我卻攥著這一點時間,怎麼也不想交出來。
過去那麼多年裡,我沒問他要過任何東西,他的關心、他的寵愛、他的榮譽……他的一切我都不想要。
現在我只想要他的死,把他的死據為己有。我等待著那一刻降臨,等待著一個不存在的聲音向我宣布,
一切都結束了。
下午見面的時候,我能感覺到有些東西橫亙在我們之間,那個祕密,也許你早就知道了吧。它可能已經在漫長的時光裡消融,滲入生命的肌理。但是不管以何種形態,我相信它仍舊存在著,並且你也像我一樣,無法對它視而不見。就讓我們談一談好嗎,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把關於這個祕密的一切,都留在今晚。
外面的雪下得真大。大片的雪花從天空中紛紛落下,彷彿是上帝在傾倒世人寫給祂的信。撕得粉碎。
----------
程恭
我不能在這裡待太久。等會兒雪小一些,就要去火車站了。今晚我要出一趟遠門,其實下午就應該走了,你來找我的時候,我正在等一個送水的人,要是他早點來,我們恐怕就不會遇到。
下午我收拾好行李,去廚房倒杯水,發現飲水機空了,就給水站打了電話。過了半個小時,送水的男孩還是沒來。本來不打算等了,但是上次沒現金,借了他的錢,總覺得還是要還上。出門之前,能了結的事應該都了結一下。外面陰著天,我覺得越發口渴,從櫃子裡翻出一只很破的鐵壺,煮上了水。蒼藍的火焰在壺底吱吱燃燒,鐵壺發出細瑣的聲響,我坐在沙發上,竟然睡著了,還作了夢。夢裡我、大斌和子峰,我們還是一群少年的模樣,在夜晚的巷子裡奔跑,大家都喝了一些酒,似乎很快樂的樣子,臉上的青春痘紅得發光。就這樣一直跑啊跑,跑到了大街上。大街上霓虹燈閃爍,有很多和我們一樣的年輕人,他們拎著啤酒罐,朝不遠處的廣場走去。我們跳上了路邊的一輛吉普車,紅色的,引擎隆隆地發動起來,大家歡呼著,吹起了口哨,把身體從車窗裡探出去。在一派節日狂歡的氣氛裡,汽車疾速朝前方駛去。
迷濛中我聽到了敲門聲,猜想應該是送水的男孩,就向著門口喊了聲「進來」。門沒有鎖,那個男孩自己會推開門,扛著水桶進來。我仍舊閉著眼睛,回想著先前的夢。它像是一個電影的結尾,遠去的汽車,縮小的房屋和街道,漸漸聽不見了的歡呼和笑聲。大幕落下,一片漆黑。好像所有的東西都被帶走了,我靜靜地待在黑裡,像一只空碗。隔了一會兒,我才感覺到湧進來的冷風,知道門被打開了。卻沒有腳步聲,屋子裡一片寂靜。
我睜開眼睛。你站在門口。我不知道你已經站了多久,沒準連我在夢裡大笑都看到了。還有醒來的悲傷,最虛弱時刻的樣子。程恭,你低聲喊出我的名字,聲音非常沙啞,似乎已經很久沒有開口講過話。快要下雪了,天陰得厲害,屋子裡黑漆漆的。爐子上的水沸了,咕嚕嚕地翻滾著。我仔細地看了你一會兒,確信自己並不認識你。可是在昏暗的光線裡,我忽然覺得這個站在對面的陌生人,似乎與我的生命有很深的聯結。那種感覺讓人背後一陣發涼。我努力回想著,記憶的卡片在頭腦中嘩啦嘩啦地翻動。然後你說,你是李佳棲。
你嘴巴裡呼出的白色哈氣,被風撩起的鬈曲頭髮,大衣下襬底下微微顫動的膝蓋,這些讓我相信眼前的你是真實的存在,並非是先前那個夢的延續。十八年沒見了,認不出來也不奇怪。你沒有化妝,蒼白的臉有一點浮腫,不過總算沒有辜負大家的期望,長成了一個美人。只是那張桃心小臉烏戚戚的,一副在大都市待久了的神情。你問我,你的樣子是不是和我想像的不一樣。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坦白說,我從未想像過你長大之後的樣子。對我而言,和你有關的一切都已經裝進檔案袋,封上了火漆。
說出來或許會有些傷人吧,不過,我真的沒有期待與你再見面。
我走到廚房關掉爐子。水已經蒸發了半壺,整個房間彌漫在白霧裡。你侷促地坐下來,看著我倒茶。
「你還跟奶奶和姑姑一起住嗎?」你問。
我告訴你,奶奶已經去世了,現在我和姑姑一起生活。
「她一直沒成家?」你問。
「嗯。」
我們的談話進行得很艱難。每次陷入沉默,我都覺得心臟受到壓迫,只想快點結束這次見面。你似乎有所察覺,但還在努力尋找話題。茶冷下去,屋子裡的白霧已經散盡,你終於起身告辭。我剛關上門,感覺鬆了一口氣,門鈴又響了。你站在門口,請我晚些到小白樓來。我還沒有來得及推辭,你已經走出了樓洞。
我並不打算赴約。不管是因為什麼,我想我們都沒有再見面的必要了。我坐在沙發上一支一支地抽菸,天色越來越暗,門突然篤篤地敲響了。送水的男孩扛著水桶站在門口,說是給西郊的一戶人家送水去了。他戴著一頂髒兮兮的灰色毛線帽子,神情恍惚。
「我迷路了。」他說。
我把送水的男孩送走,繫上外套的扣子,拖著旅行箱出了家門。外面已經黑了,天空開始飄雪。
走出南院,我站在街邊等了很久,也不見有計程車經過。好不容易來了一輛,司機擺手說要收工了。
天冷得厲害,我不停地跺著腳,把熱氣呼到手心上。身後是一個小飯館,門呼啦一下打開了。老闆娘從裡面走出來,她到隔壁的小賣部替客人買菸,看到了我就熱情地打招呼。去年夏天有一陣子我常來她這裡喝酒。
「要出遠門啊?」她問。我點點頭。
「著急嗎?雪小一點再走吧,這會兒很難打車。」她說。我跟隨她走進小飯館。最裡面的位子上坐著一個中年男人,拿過老闆娘買回來的香菸,剝掉塑膠紙,點著了一根。我在靠窗的桌子前面坐下,要了一份滷味拼盤。老闆娘是潮州人,跟著老公來到這裡,後來老公跟著別人的女人跑了,她卻留了下來。
「有新進的老撾啤酒,要不要試一下?」她問我。我說好啊,雖然並不想喝。我知道酒會讓意志變得軟弱。
我一邊喝酒,一邊吃著滷豆干。啤酒很淡,有夏天的味道。老闆娘和中年男人一直熱絡地聊著天,從媽祖像到釀豆腐的作法。
「這裡的水不好,豆腐不好吃。」老闆娘感慨道。
過了一會兒,中年男人付了帳走了。店裡只剩下我一個客人,變得很寂靜。
「你朋友的哮喘好些了嗎?」老闆娘忽然問。「前陣子有個客人到店裡來,說起家裡有個祖傳的治哮喘的偏方,我就讓他寫下來了。」她翻騰著收銀台底下的抽屜,「咦,放在哪裡了?」
「沒事,別找了。」我說。
「在這兒呢!」她說,「我就記得收起來了。」
「謝謝。」我接過藥方,塞進口袋裡。
她回到座位上,點了一支菸。
「好大的雪啊。」她喃喃地說。
我轉過頭去看著窗外。黑沉的夜幕中雪花紛飛。地上已經是白茫茫的一片。馬路沿上留下的腳印被新雪覆蓋,只剩下淺淺的窩。
「要不是因為這裡會下雪,我早就回南方了。」老闆娘說,「你喜歡雪嗎?」
「喜歡。」我說。
我們都沒再說話,只是靜靜地看著外面的雪。我盯著路燈下的那道光渠,大片的雪花在當中劇烈地翻卷、墜落,如同在苦海裡掙扎。
我想起很多年前的那個下午,也下著這樣大的雪,我離開學校去你爺爺家見你。你要走了,你媽媽領著你到學校辦了轉學的手續。在辦公室門口,你遇到大斌,跟他說你要見我,讓我晚些去你爺爺家找你。
我知道以後也許很難再見面了,這恐怕是最後的機會將那些事情告訴你。可是我卻越走越慢,最終在我們從前常去的康康小賣部門口停住了。然後,我掉頭回家去了。據說那天你等了很久,快吃晚飯的時候才被你媽媽帶走。讓你空等一場,我一直感到很抱歉。我也說不清為什麼這樣做。可能因為沒有什麼是我能夠主宰的,所以我想自己來決定如何結束這場友誼。從那個時刻起,我把和你有關的一切封存進了檔案袋。
大斌有你的新地址,你生日前的一天,他伏在桌上給你寫生日卡,但我拒絕把自己的名字添在他的後面。後來他還為你沒有回信,也沒有在他生日的時候寄來卡片而難過。沒有人知道你的消息。你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得乾乾淨淨,一如我希望的那樣。我猜你在用這樣的方式告訴我,你贊同我的決定,既然再也不能回到過去,保持聯繫也就毫無意義。我們曾那麼親密,以為友誼堅不可摧,可事實上它非常脆弱。因為它從一開始就是錯的,如同長在道路中央的樹,遲早會被砍掉。
我喝光了三瓶啤酒,扣上外套的紐扣,站起身來。
「要走了嗎?」老闆娘問。我掏出錢來給她。
「你往前再走一段,前面的大路口沒準會有車。」她手腳麻利地把找回來的錢塞到我手裡,「路上多保重。」呼啦一聲,她拉開半扇門,冷風夾雜著碎雪湧進來。
我一隻腳跨出了門檻,又停住了。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裡,酒精灼燒著我的臉。
「能先把箱子放在你這裡一會兒嗎?」我聽到自己說,「我想起還有一件事沒有辦。」
「好啊,反正下那麼大的雪,我也回不了住處了,你多晚來取都行。」她笑著說,「難怪整晚心事重重,快去吧。」
我謝過她,邁出門跨入風雪中。
剛才走在來見你的路上,又經過康康小賣部。它已經改成東東速食店。旁邊存放自行車的大車棚拆掉了,從前那個陡峭的斜坡被墊平了,你爺爺的家也從西區搬到了小白樓。可是大雪覆蓋了這所有的變化,讓我恍惚覺得還是十一歲的那個夜晚,你要走了,我趕來見你。這一次經過康康小賣部的時候我沒有停下。我終於把那個晚上沒有走完的一段路走完了。
孩子,我所能給你的祝願不過是些許不幸而已。
—— 薩克萊《玫瑰與指環》
第一章
李佳棲
回到南院已經兩個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裡都沒有去。哦,還去過一次藥店,因為總是失眠。
我一直待在這幢大房子裡,守著這個將死的人。直到今天早晨,他陷入了昏迷,怎麼也叫不醒。天陰著,房間裡的氣壓很低。我站在床邊,感覺死亡的陰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盤旋。這一天終於要來了。我離開了房間。
我從旅行箱裡拿出厚毛衣外套。這裡的暖氣總是不夠熱,也可能是房子太大的緣故。我一直試著和那種從牆皮裡滲出來的寒冷相處,終於到...
作者序
後 記
一九七七年男孩告別了他工作的糧食局車隊,走進大學的校門。報到那天,教會他開車的師傅堅持要送他,戴上白手套,穿上工作服,開了車隊最新的一輛解放牌卡車。路上師傅不說話,一支接一支地抽菸,快到學校的時候才忍不住問,你那個中文系具體是學什麼的?男孩說,不知道,我想學寫小說。師傅說,寫那玩意兒有什麼用?男孩說,我就是想寫。師傅歎了一口氣,放著那麼好的工作不幹了,我怕你遲早是要後悔的。
第二年秋天,男孩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把它寄給了上海的一個文學雜誌。小說的題目叫〈釘子〉,源自一件少年時代目睹的真事。在他居住的醫院家屬院裡,隔壁樓洞的一個醫生在批鬥中,被人往腦袋裡摁了一枚釘子。那人漸漸失去言語和行動的能力,變成了植物人,後來一直躺在醫院裡。在那個動盪的年月,身邊發生過不少殘忍的事,可是不知道為什麼,這一件好像在他的頭腦中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個月後,男孩收到了雜誌社的錄用通知。他很高興,把這件事告訴了他的女朋友,他們還慶祝了一下。又過了一個月,他收到編輯的信,說上面覺得那篇小說的調子太灰,恐怕還是沒法用。一場空歡喜。男孩把稿子丟進抽屜,再也沒看過。後來,他又寫了幾篇小說,調子都很灰,寄出去就沒有了消息。畢業之後,他留在了學校教書,和那個女朋友結了婚。教工宿舍是一幢擁擠的筒子樓,過道裡堆滿了書和白菜,傍晚的時候,大家在走廊裡做飯,整幢樓裡都是蔥蒜的氣味。孩子出生以後,他的寫字檯被搬走,換成了一張嬰兒床。從那之後,他再也沒有寫過小說。把日常生活對人的消磨當作停止寫作的原因,在任何情況下都很合理。只不過偶爾一些時候,他的頭腦中會冷不丁冒出他師傅的話:寫那玩意兒有什麼用?小說雖然沒有寫下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讀大學的決定顯得越來越英明,他心裡不免有點慶幸。世界上的事大抵如此,走著走著就忘了初衷,偏離了原來的道路,可是四下望望,好像也不算太糟,就繼續往前走了。
至於那篇小說,沒多久就在一次搬家中丟失,男孩漸漸也忘記了當時寫過什麼。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基本等同於沒有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直到很多年後,他說起寫過這篇小說,連帶著回憶起釘子的事。那個沉入記憶谷底的故事,早已褪色、風乾,變得非常瘦小。他自己說著也覺得沒意思,幾句話就把它講完了。又過了一些年,有一天吃晚飯的時候,他的女兒漫不經心地向他宣布,我打算把釘子的事寫成一個小說。他花了點時間才記起釘子的事指的是什麼,隨即笑了笑,那有什麼可寫的?女兒沒理會,只是向他詢問更多的細節。他勉強回憶起幾處,其他都想不起來了。女兒顯得有些失望,沒有再談起這件事。後來他才知道,女兒自己跑到那座醫院去作調查,蒐集了一些關於植物人的資料。但此後就沒動靜了。她向來有點捉摸不定,今天這樣明天那樣,他早就習慣了。這個女兒,從世俗意義上說不算特別叛逆,但也絕對談不上乖巧。總之,肯定不是他理想中的那種女兒。就這樣又過去很多年。他退了休,有些時間會住在北京的女兒家裡。有一天,他發現女兒家有一摞白皮的書。那是她剛寫完的小說,在正式出版之前影印了一點,打算送給周圍的朋友讀。女兒填寫了寄書的單子,委託給他,然後就出門了。他把那些書一一塞進袋子,交給送快遞的人。有一本書,因為缺少收件人的手機號碼,滯留下來。他把它擱在了茶几上。吃完晚飯,他在電腦上下了一會兒圍棋,對方水準很糟糕,眼看快輸了,於是就臨陣脫逃。他有點不甘心地在螢幕前等了一會兒,才合上筆記本。客廳裡很安靜,外面有一點春天末尾的風聲。他倒了杯茶,重新回到沙發上,發了一會兒呆,目光落在那本白皮書上。他朝前坐了坐,拿起那本書,翻開第一頁——
回到南院已經兩個星期,除了附近的超市,我哪裡都沒有去。哦,還去過一次藥店,因為總是失眠。我一直待在這幢大房子裡,守著這個將死的人。直到今天早晨,他陷入了昏迷,怎麼也叫不醒。天陰著,房間裡的氣壓很低。我站在床邊,感覺死亡的陰影像一群黑色翅膀的蝙蝠在屋子上空盤旋。這一天終於要來了。我離開了房間。
我從旅行箱裡拿出厚毛衣外套。這裡的暖氣總是不夠熱,也可能是房子太大的緣故。我一直試著和那種從牆皮裡滲出來的寒冷相處,終於到了無法忍受的地步。我走到洗手間,沒有開燈。細細的燈棍散發出青寒色的光,會讓人覺得更冷。我站在水池邊洗臉,想著明天以後的事。明天,等他死了,我要把這房子裡所有燈都換掉。洗手池的下水管漏了,熱水汩汩地逸出來,在黑暗中靜靜地流過我的腳面,像血一樣溫暖。我站在那裡,捨不得把水龍頭關掉。
我寫下這行字的時候,大約是二○一一年初。這個當時還沒有名字的小說,在那之前已經換過好幾個開頭。有的開頭女主人公坐在高牆上,有的開頭女主人公坐在火車上。最離奇的一個開頭,竟然出現了一隻紅尾巴的狐狸。現在我已經想不起,為什麼需要那麼一隻狐狸了,但在當時好像覺得牠不出場,故事就沒法說下去。應該是個類似先知的角色,可惜總是幫倒忙。我記得狐狸當時還警告女主人公,你最好接受我的存在,我既然出現了,就不可能再消失了。結果沒過幾個星期,這隻挺威風的狐狸,就從word文檔裡徹底被刪除了。沒有了狐狸以後,主人公變得有些萎靡不振,好像在茫茫大海中失去了航標,就那麼漫無目的地漂著。我試了幾次,也沒找到方向,就撇下她不管,去寫別的東西了。那時候,我和她的交情沒那麼深,見不到也不至於太牽掛。
春節前,我回到了濟南的父母家。他們剛搬了家,又住到了我小時候生活的大學家屬院。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去過。從前住的舊樓已經拆了,原來的地方蓋起了高層公寓。乍然一看變化很大。但是除夕那天下午,我一個人在院子裡遊逛,很快發現到處都是從前的痕跡。樹木,平房,垃圾站。門口賣報的男人還在那裡,幫她爸爸守著水果攤的女孩,也仍舊坐在原來的地方,只是已經是個中年女人,眼睛變得渾濁了。看到這些,我並沒有覺得親切,反倒感到一絲恐怖。我離開之後,那些人還在原來的地方繼續生活著,事情本來不就是這樣嗎,可是看到他們的那一刻,好像發現了什麼巨大的祕密似的,自己嚇了一跳。隨即有些不安,仿佛是我拋棄了他們,把他們留在了原地。我停在那裡,看著由那些熟悉的人和景物組成的圖景,似乎在等待著什麼。等著下一秒,另一個我走進畫面。那個我和這個我具體有什麼不同,好像也說不太清楚,但總之那是另一個我,一個從未離開的我,在這裡長大,衰老,有快樂也有煩惱。也就是說,我們所離開的童年,不是一個閉合的、完結的時空,而是一個一直默默運轉著的平行的世界。那天下午,我在大院門口站了很久,當然並沒有等到另一個我現身。不過小說中一直面目模糊的另外一位主人公,倒是一點點在頭腦中顯影。他大概更像女主人公的“另一個我”,留在童年的平行世界裡。
接近零點的時候,一簇一簇的煙火躥上天空,照亮了黑漆漆的窗戶。我坐在那張書桌前,寫下了現在的小說開頭。稍後我發現,它不僅決定了小說的敘述視角,也確立了小說的結構。在此之前,我一直想不好該怎麼去講那個早就交到我手裡的故事。我作了一些調查和採訪,用各種方式接近那個故事,但總有一些隔膜的感覺。這個夜晚,我回到小時候生活的地方,驚訝地發現原來通往故事的路徑,就在我的童年裡。
釘子的故事發生在我爸爸的童年,我的童年裡卻有它的入口,這或許說明我和爸爸的童年,本來就是連接著的吧。那件事在他的童年烙下深刻的印記,也必將以某種方式在我的童年中顯露出痕跡。那些歷史,並不是在我們覺察它們、認出它們的一刻,才來到我們的生命裡的。它們一直都在我們的周圍。
那年春節,我一直沉浸在某種童年的氣氛裡,卻沒怎麼跟我爸爸說過話。我們本來就是一對交流很少的父女,到了那個時候,更是變得少得可憐。我在努力避免和他講話,似乎只有隔絕和他的聯繫,才能把他的故事完全變成我自己的。可是隨著時間推移,等到小說寫了一半,我發現我爸爸已經進入了這個小說。我好像沒法把他和他的故事剝離開,他們是長在一起的。他進入這個小說的方式,並不是化作了某個具體的人物,而是確定了一種基調。失望,拒絕,不再相信什麼。那是我爸爸身上的一種東西,長久以來,或許就是它,一直離間著我們之間的感情。特別是對於童年裡那個對世界充滿無限熱情的我來說,一定會覺得有些難以接受吧。但是直到現在,我才意識到那種性情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它和時代、歷史之間存在著許多關連。幾乎是在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就在表達一種對愛的需索,也意識到在愛這件事上,自己是有困難的,不懂得去愛,或者是失去了一部分愛的能力。在隨後的寫作中,我不知不覺地寫到爸爸,似乎開始意識到很多關於愛的問題都和父輩相關。然而直到寫這個小說的時候,我才真切地明白根源或許是他們所經歷的事,是那些改變他們、塑造他們的歷史。
我出生的時候,那個植物人還活著。就躺在同一座醫院的同一幢住院樓裡。秋天的午後,他是否聽到隔壁病房傳來的嬰兒的哭聲,是否能夠知道,很多年以後,這個女孩將重新回到醫院,收集和他有關的點滴,把他的故事寫出來呢?他也許根本沒有興趣知道。對於一個已經身在世界之外的人來說,他的故事以何種形態存在,是消散在空氣裡,還是被書寫和記錄下來,又有什麼分別呢?這個故事對我爸爸來說,也不再重要。我的書寫並不會照亮他的記憶,喚起少年時的那種內心的震動。他也許會在百無聊賴的時候拿起這本小說翻幾下,但是幾乎不可能把它讀完。這當然也是因為我寫得不夠有趣,不過更重要的是,他不再相信虛構的魔法了吧。
並沒有什麼人需要這個故事。它只是對我很重要。七年前我帶著這個小說上路,對於它具體是什麼樣子,完全沒有想法,隨著一步步向前走,一點點撩開迷霧,它的輪廓開始清晰,血肉慢慢浮現。多少時日的晨昏相伴,它陪著我走過了青春的最後一些時間。說完全不在乎最終的結果,那是假的,可是我確實想說,這個探尋和發現的過程遠比結果更重要。因為說到底,文學的意義是使我們抵達更深的生命層次,獲得一種從未有過的體驗。
我的腦海中,總是無端地浮現出那個植物人臉上的微笑。就是在那個秋天的午後,聽到隔壁嬰兒啼哭的時候,他臉上慢慢露出的一絲微笑。我沒見過他,卻見到了那個微笑。於是我相信,在寫下這個故事的時候,我一定是在被什麼看不見的人祝福著的吧。
後 記
一九七七年男孩告別了他工作的糧食局車隊,走進大學的校門。報到那天,教會他開車的師傅堅持要送他,戴上白手套,穿上工作服,開了車隊最新的一輛解放牌卡車。路上師傅不說話,一支接一支地抽菸,快到學校的時候才忍不住問,你那個中文系具體是學什麼的?男孩說,不知道,我想學寫小說。師傅說,寫那玩意兒有什麼用?男孩說,我就是想寫。師傅歎了一口氣,放著那麼好的工作不幹了,我怕你遲早是要後悔的。
第二年秋天,男孩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小說,把它寄給了上海的一個文學雜誌。小說的題目叫〈釘子〉,源自一件少年時代目睹的真事...
目錄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後記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後記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11收藏
11收藏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1收藏
11收藏

 18二手徵求有驚喜
18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