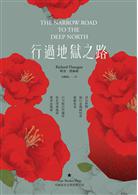★ELLE雜誌風格人物大獎最佳新銳作家
★《獨立報》英國年輕作家20強
★柑橘獎入圍作家
★2010年亞馬遜百大編輯選書
「我們應該有一些故事,它們不會告訴我們怎麼生活,也不會告訴我們怎樣把生活變成故事,它們只會防止我們將自己虛構化。」
祕密。
有人讀了、實踐了《祕密》之後,或中了樂透,或功成名就。
宇宙會回應你的訂單嗎?
梅格專門幫科普書寫書評,同時她也是個為出版社捉刀寫偵探小說的影子作家,但她真正想做的是寫一本真正的文學小說。
可是她卡住了。她正面臨寫作生涯的重大瓶頸,她的銀行存款就要見底、她的感情生活一攤死水,都快沒什麼剩下的東西了。
然而因為一篇陰錯陽差的科普書書評,報社編輯提議,讓她試著向宇宙下訂單、親身體驗心靈勵志書的建議,並寫成一個專欄。
這太荒謬了。梅格相信花精、相信順勢療法、相信安慰劑效應,但她一點也不想要一個答應她所有請求的宇宙(也不希望宇宙真會回應她)——但話說回來,這將拯救她乾渴的銀行存款,於是她答應這麼做了。
她向宇宙下訂單。
如果世上一切都依循「等價交換」的原則,當宇宙應允了你什麼,你又得付出什麼代價呢?
作者簡介:
史嘉蕾•湯瑪斯Scarlett Thomas
出生於倫敦。迄今為止她已出版了八本小說,作品被譯為二十多種語言。2001年入選為《獨立報》(The Independent)英國年輕作家20強。2002年獲「埃蒂安雜誌風格獎」(Elle Style Awards)最佳新作家。
史嘉蕾為多家刊物撰寫文章和短篇小說,其中包括《自然》雜誌(Nature)、《衛報》(The Guardian)、《星期日獨立報》(Independent on Sunday),《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蘇格蘭星期天》(Scotland on Sunday)等。
小說作品有:《光彩年華》(Bright Young Things)、《外出》(Going Out)、《流行公司》(PopCo)、《Y先生的結局》(The End of Mr. Y)。
自2004年至今皆在肯特大學教授英國文學與創意寫作,之前在達特茅斯學院、東南埃塞克斯大學和東倫敦大學授課。業餘時間在攻讀民族植物學碩士學位(MSc in Ethnobotany)。
譯者簡介:
金玲
上海出生長大,香港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士,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研究碩士。現旅居美國,靠業餘翻譯、寫作維持與母語的聯繫。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充滿趣味,尤其是湯瑪斯的寫作能力讓人印象深刻……充滿活力與生命力。——《黃金羅盤》作者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我們悲慘的宇宙》出乎我的意料,讓我顫慄。它讓人如此上癮、無法自拔,只能在湯瑪斯的咒語裡愈沉愈深。她是個天才。——《X世代》作者Douglas Coupland
將一本書形容為「善良」是不是很奇怪?在折騰人的網路時代,這個詞已經愈來愈少見。所以讀到《我們悲慘的宇宙》這樣一本充滿憐憫與溫暖的書時,我才如此訝異,如此欣喜。書中的觀點,我也許不贊成,但我非常願意花時間去跟那些人物爭論。他們就像你身邊的朋友:氣人、善良,又真實。——《衛報》
名人推薦:充滿趣味,尤其是湯瑪斯的寫作能力讓人印象深刻……充滿活力與生命力。——《黃金羅盤》作者菲力普.普曼(Philip Pullman)
《我們悲慘的宇宙》出乎我的意料,讓我顫慄。它讓人如此上癮、無法自拔,只能在湯瑪斯的咒語裡愈沉愈深。她是個天才。——《X世代》作者Douglas Coupland
將一本書形容為「善良」是不是很奇怪?在折騰人的網路時代,這個詞已經愈來愈少見。所以讀到《我們悲慘的宇宙》這樣一本充滿憐憫與溫暖的書時,我才如此訝異,如此欣喜。書中的觀點,我也許不贊成,但我非常願意花時間去跟那些人物爭論。他們...
章節試閱
我的朋友莉比發來簡訊的時候我正在讀一本關於如何活過世界末日的書。她說:「你能在十五分鐘內趕到河堤嗎?出大事了!」這是二月初的一個寒冷周日,我幾乎一整天都縮在床上。我在達特茅斯住的小屋潮濕破舊。奧斯卡,我投稿報紙的文學編輯,寄來了凱爾西•紐曼的《永生的科學》,要我寫書評。隨書寄來的還有一張紙條,寫著奉承的話。那些日子我非常缺錢,所以什麼活兒都接。情況其實也沒那麼糟:在科學書評界我已經逐漸樹立起了一定的名聲,因此奧斯卡總是把最好的書給我。我的男友克里斯多夫在世界遺產遺址做無償志工,所以我必須獨力負擔全部的房租。我從不放過任何工作機會。雖然,對於凱爾西•紐曼這本書,和他挨過時間的末點這個概念,我還不知道能說點什麼。
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已經倖存於各種時間的末點之外:截稿日期,銀行的透支額度和銀行經理的最後通牒。我趕稿子賺錢,但不一定拿去還款。那個冬天,我只到佩恩頓一個收費高昂、拒絕提問的地方兌現支票,然後到郵局用現金交水電費。但你能要求什麼?我根本不是知名大作家,儘管我仍未放棄這個計畫。每當有白色信封從銀行寄來,克里斯多夫就會把它擱在我二樓書桌上的那遝信件上。但我一封也沒有打開過。電話餘額不多,我沒回莉比簡訊;不過我還是放下了書,從床上站起來,換上運動鞋。因為種種複雜的原因,我曾發誓絕不在周日晚上離開達特茅斯。但我無法拒絕莉比。
灰濛濛的下午像隻受了驚的土鼈蟲般被夜晚吞沒。還有五十頁《永生的科學》要讀,截稿日期就是明天。如果我想讓文章在周日見報,就必須馬上看完書並及時寄出書評。不然就得拖到下周,而我也將一個月沒有收入。克里斯多夫正在樓下的沙發上鋸再生木塊,打算做個工具箱。我們沒有花園,他只能在院子裡工作,院子由混凝土建成,狹小封閉,圍牆很高。青蛙及其他各種小動物時常如從天而降般神奇地出現在院子裡。走進客廳,我發現到處都是木屑,但我沒出聲。我的吉他倚在壁爐旁。克里斯多夫每拉動一次鋸子,振動就在房間裡穿梭,吉他的E弦也一併振動起來,發出細微的聲響,低沉憂傷而又綿綿不絕。克里斯多夫鋸得很認真:他的弟弟喬許昨天過來吃了午飯,顯然他還沒能平復過來。喬許覺得談論母親的去世有撫慰作用,而克里斯多夫並不苟同。喬許為父親正和一個二十五歲的服務生約會而感到高興,可克里斯多夫覺得那非常噁心。可能當時該由我來結束那場談話,但我正在發愁:那本要評論的書我一眼都沒看,甚至都不知道是怎樣的一本書;桌上的麵包快吃完了,而那是我們僅剩的一些。況且,我真的不知道該如何結束那樣的談話。
有時,我會在下樓的時候想著要說點兒什麼,然後想像克里斯多夫的反應,通常我最終會沉默不語,但這次我開口了:「你猜怎麼了?」克里斯多夫仍發瘋似的鋸著木頭,彷彿那是喬許的頭,也可能是米莉的頭,接著他說:「親愛的,你知道我最討厭你這樣說話。」我道了歉,他讓我幫他拿住一塊木塊,我說得出門遛狗了。
「她太久沒出門了,」我說,「天都快黑了。」
貝絲正在玄關上的一塊牛皮墊上滾來滾去。
「我以為你今天下午遛過她了」,克里斯多夫說。
我套上防風衣,戴上紅色羊毛圍巾,一言不發就出門了;我聽見克里斯多夫一盒釘子掉在地上,但我沒回頭,雖然我知道應該要。
╱
如何活過世界末日?答案很簡單。當宇宙衰老脆弱到終將崩潰時,人類就可以隨意處置它。人類將有上億年的時間來學習,不會有女舍監來阻止他們,沒有自由主義大報,也沒有憂傷的聖歌。到時候,只需要把那些衰老的星球一個一個用輪椅推到宇宙的一邊;當你處理這個星球時,下一個正在另一個星系裡悲傷地尿濕褲子。一切都在等待著最後一擊:所有事物都轉變為別的形狀,宇宙開始它美妙的崩潰,它喘著大氣流著汗,直到每一個生命都被拋出去,直到所有物質被擠壓成一點並最終消失殆盡。在毀滅前的最後時刻,宇宙發出微弱的喘息和高潮的呻吟,所有的黏液、膿水、腐臭的汁液都將轉變為純粹的能量。在那一瞬間,那能量可以為所欲為。我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費心嘗試向克里斯多夫解釋這一切。有一次,他拒絕接受空間的多維性,把我給急哭了。另一次,我畫了一張示意圖來證明畢達哥拉斯定理,他卻連看都不想看,我們大吵了一架。在克里斯多夫看來,我評論的書都「太費腦子了,寶貝。」真不知道他會怎麼看我手上這本,它能把你的腦子完全搞亂。
凱爾西•紐曼認為,宇宙是一部電腦,到了某一個瞬間,它的密度會變得非常高,也將因此擁有強大的能量,可以計算出一切。那為什麼不乾脆編一個程式來類比出一個新宇宙,一個永恆的、讓所有人從此幸福快樂的宇宙?這個瞬間被稱為歐米伽點,它的力量能容納萬物,因此它很像上帝。但它又不同於上帝,因為它靠一種稱為能源的處理能量運作。在宇宙即將崩潰的時候,沒人要去作一首關於宇宙毀滅的詩,或去做最後一次愛,也不會四處亂逛、飄飄欲仙或無精打采,一邊靜靜等著被毀滅,一邊想像彼岸那不可言喻的美景。所有人都將各就各位,為了一個終極目標:存活。只須通過物理知識和自己的雙手,人類將構建出歐米伽點。歐米伽點擁有無窮的能量,它可以、基於千萬種理由也一定會,讓所有人復活——對,甚至包括你,已經死了上億年的你——這能量澤被蒼生,它會創造出完美的天堂。在宇宙結束的時候,什麼都可能發生,除了一件事。
你將不會死去,永遠不會。
奧斯卡一般不會寄這樣的書給我。我們做大眾科學,雖然會挑古怪一點兒的,但我們的底線是新世紀類。這本書屬於新世紀類嗎?很難說。介紹上說紐曼是紐約一位備受尊敬的精神分析學家,他當過總統顧問,雖沒說明是哪一任總統。受知名物理學家法蘭克•提普勒(Frank Tipler)的啟發,紐曼著手寫下這本書。歐米伽點的說法是法蘭克•提普勒最先提出的,他做了所有必要的計算,證明一旦那種能量被啟動,你、我——所有曾經活著的人們,所有可能存在卻沒能活過的人們——都能在時間的末點復活。死亡將只是一段小憩,從死亡到在永生中醒來,你不會意識到時間的流逝。
那幹麼還要為世事煩惱?幹麼要成為知名小說家?幹麼要交帳單、剃腿毛、吃充足的蔬菜?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唯一明智的選擇便是現在就一槍斃了自己。可然後呢?我熱愛這個宇宙,尤其是那些我基本能理解的各種美妙的點滴,如相對論、萬有引力、上夸克和下夸克、進化論、波動函數;但我還沒有對它迷戀到想要活過它的自然末日、和所有人一起被連到一台「宇宙生命維持機」上,在某種昏迷中寸步難行。我曾被告知——最近又再次被提醒——我將一無所有。我要那樣的一個天堂做什麼?永生就像是嫁給你自己,而且永遠不能離婚。
╱
我們走下三十一級石階,來到街上。經過轉角處雷格的商店後,我和貝絲穿過市集廣場。整個廣場如同荒原般毫無生氣,只有一隻海鷗不停啄著地上的薯片袋,發出「嗒、嗒、嗒」的聲響,像一挺孤獨的機關槍。經過米勒熟食店附近的巴特走廊時,貝絲緊挨著牆壁走,一到皇家大道花園,她就停下來撒尿。一切似乎都關閉了,破碎了,死去了,冬眠了。室外舞臺空空如也,噴泉乾涸。棕櫚樹在風中簌簌抖動。空氣中彌漫著鹹味和一股類似海藻的氣味。愈是靠近河邊,這氣味就愈強烈。四下無人。天色漸漸變暗,對岸金斯韋爾的天空慢慢形成了一種糊狀的顏色,混合著綠、棕和紫色,就像蘋果皮。風從海上吹來,水面上的小船隨風晃動,如同被施了魔法,發出幽靈般的聲響。
我拉上防風衣的帽子,貝絲四處嗅著。她喜歡先一一問候北岸河堤的所有長椅,然後繞著遊艇停泊處走一圈,最後經過加冕公園回家。她在冬天總是走得很慢,而且精神不濟。在家的時候我常發現她蜷成一團躲在床單裡,像是隨時準備要冬眠。不過出門的時候她還是會沿著以往的路線散步。每天穿過加冕公園時,我們都會停下來看看那個神祕的建築工地。去年秋天,莉比從她編織小組裡的老瑪麗那兒聽說,這裡將興建一個小型石頭迷宮。迷宮會建在一塊高高的草坪上,在那兒可以將河景盡收眼底,草坪也將經過精心設計。可直到現在,這兒都還只是個洞。這個項目由地方議會撥款,因為有研究表示,建造這種迷宮可以幫助大家平靜身心。達特茅斯是一個安靜的港口城市,人們來這裡退休、等死、寫小說,或安靜地開一間小店。這裡唯一需要平靜的人,是皇家海軍學院的學生,而他們永遠不會來走這個迷宮。我最擔心的是建築工人會砍掉我最愛的那棵樹,因此我幾乎每天都會過來檢查,看它是不是還在那裡。風呼嘯著吹過公園,建築工地上的臨時塑膠圍欄在風中拍打,我匆匆看了一眼我的樹,催促貝絲趕快離開工地,又走回了河堤。這個二月寒冷、嚴酷,令人厭惡,我只想快點回家躺在床上,雖然家裡並不比室外暖和多少,而且屋內潮濕的空氣會讓我喘個不停。貝絲顯然也想早點回家。我想像著她和我一起窩在被窩裡,進入冬眠。
周圍仍然一個人也沒有。也許過去的幾個月來,我一直在為一些不可能發生的事情而苦惱。也許他再也不會來了。也許他從沒來過。
海爾渡輪從河的上游朝達特茅斯駛來,發動機不停發出突突的聲響。渡輪上只有一輛車,車燈在黑暗中閃爍,可能是莉比的車。河面上有東西在叮叮作響。我站在那裡等莉比,同時掃視河面上的船隻;我不是在找他。聽著那「叮叮」聲,我不禁猜想它為何顯得如此鬼魅。我摸進防風衣內裡的口袋。我知道那裡有什麼:一張小紙片,上面寫著一個我已經能背出來的電郵位址,還有一個附吸管的棕色藥瓶。瓶裡剩下最後一點花精。這花精是朋友薇幾個星期前調給我的。前些日子,我、薇還有她的男友法蘭克一起去了他們在蘇格蘭的度假小屋,我們在那裡過耶誕節,當時克里斯多夫去了布萊頓。但後來事情弄僵了,薇不再跟我說話。所以事實上,我現在前所未有地孤單。但其實也還好,我有房子住,有男朋友,還有貝絲,這些已經足夠。我還有這瓶花精,它很管用。瓶子的標籤上,薇的字跡還依稀可辨:龍膽花,冬青,角樹,甜栗,野燕麥,野玫瑰。我滴了幾滴在舌尖,感覺到瞬間的溫暖。
幾分鐘後渡輪靠岸了。搖板放下的時候發出砰的一聲巨響,船門打開,唯一的那輛汽車開出來,駛向河堤。果然是莉比。我揮了揮手。兩年前,莉比和她的丈夫鮑勃關掉了逐漸走下坡的漫畫書店,開始經營米勒熟食店。他們賣各種東西,包括未經巴氏消毒的乳酪、鵝脂、檸檬塔、自製沙拉、浮木雕塑品,以及他們自己或是朋友織的披肩或毯子。我也會做些果醬、橘皮果凍拿去他們店裡賣,在寫作之餘賺點兒外快。我經常在冬天的早晨去他們店裡拿我最愛的午餐飯盒:一盒醃製的大蒜,一些魚醬,半個法式長棍。莉比開得很慢,車窗大開,頭髮在風中亂飛。一看見我,她就停下車。莉比穿著牛仔褲和緊身T恤,裹著一條紅色的手織披肩,寒冷的二月似乎完全拿她沒辦法,而她也像是從來沒戴過厚眼鏡,或穿過印有恐怖片主角頭像的肥大上衣的樣子。
「梅格,該死。感謝老天。克里斯多夫不在這兒,對吧?」
「當然不在。」我說,「沒別人。怎麼了?你沒事吧?你不冷嗎?」
「不冷。我腎上腺素分泌過多了。我徹底完蛋了。我可不可以說我在你這兒?」
「什麼時候?」
「今天。一整天。還有昨天晚上。鮑勃昨天提早回來了。你能相信嗎?蓋特維克的機場跑道太滑,他的航班改降在埃克塞特!」
「你跟他說過話了?」
「還沒,但是他傳了簡訊。本來他會在飛機降落蓋特維克的時候傳簡訊給我,那樣我就來得及回家換衣服、收拾屋子,讓他看不出來我沒留在家裡。所以聽到簡訊鈴聲的時候,我認定是鮑勃從蓋特維克傳來的——時間差不多——可當時我跟馬克在床上,所以沒立刻看簡訊。你想,從下飛機到離開機場要半個小時、機場到維多利亞要半個小時、維多利亞到帕丁頓要二十分鐘、帕丁頓再到托特尼斯去取汽車要三個小時,拿到車開回家還要二十分鐘。所以我一點都不慌。不過當我看手機的時候,我發現他又傳了條簡訊說『半個小時後見』,接著又是一條問我在哪裡、是否都沒事——我差點兒心臟病發了。」
莉比跟馬克有婚外情。馬克是個生活混亂的傢伙。他住在一個叫徹斯頓的村子裡,在托貝的那條河邊。馬克曾經一貧如洗,後來從祖父那兒繼承了一棟海灘棚屋。他住在這海灘棚屋裡,吃魚、在船塢和碼頭打各種零工。他正在存錢,準備開一間自己的船舶設計公司,但莉比說他還早呢。週一至週五莉比通常和鮑勃在熟食店工作,剩下的時間,鮑勃玩電吉他或者算帳,而她,就學習編織愈來愈複雜的圖案,或用深紅色墨水寫情書給馬克。她捏造了一個讀書會,告訴鮑勃她每週五晚上都要去徹斯頓圖書館參加小組活動。週三的編織小組上她也會見到馬克,不過在那兒更麻煩,因為鮑勃隨時會帶著店裡賣剩下的蛋糕突然出現,或是小組裡的某個老婆婆可能會看到馬克撫摸莉比的膝蓋。這個週末不太一樣,因為鮑勃去德國看他的姑婆和叔公。她從週五開始就和馬克待在一塊兒。
「所以你昨晚來我這兒,然後……?」
我皺眉頭。我們都知道莉比絕不可能在我家待上一整晚。有時她會從熟食店帶瓶紅酒來我家,不過最近她來得很少。我們通常會坐在餐桌邊聊天,而克里斯多夫則獨自坐在幾英尺外的沙發上生悶氣。他會用盜版的「天空系統」(Sky system)看美國新聞或講獨裁者的紀錄片,嘴裡嘟噥著世界何其腐敗、有錢人何其貪得無厭。他是故意的,因為莉比有錢,他不平衡。通常我會約莉比在酒吧見面,儘管克里斯多夫總是抱怨我把他一個人丟家裡。貝絲之前一直在地上嗅來嗅去,現在她趴在車門上,對著車窗嗚咽。她想上車。她喜歡鑽進車裡。莉比拍了拍她的頭,但沒有看她。
「不……我得弄丟鑰匙才行。」她開始思索可能性。「我們,呃,我和你昨晚一起出去玩,我丟了鑰匙,所以必須待在你家。我喝醉了,我沒有找鮑勃,因為他在德國,我打算今天出門找鑰匙,所以他傳訊給我的時候我正在找鑰匙,可是我把手機留在你家裡,所以……」
「但你現在就在開你的車。房門鑰匙是分開的嗎?我還以為所有鑰匙都在同一個鑰匙圈上。」
莉比看著地面。「也許我找到鑰匙了……他媽的。噢,老天!噢,梅格,我該怎麼辦?我為什麼要開車去你家呀?走路只要五分鐘。我沒辦法把這一切拼湊起來。」她皺眉。「拜託,你才是作家,你知道怎麼安排情節。」
我似笑非笑道:「對啦。你會讀書。我確定你也知道如何安排情節。」
「對,但你以此維生。而且還教這個。」
「對,可是……」
「這裡的配方奶是什麼?」
配方奶,就是用來代替母乳餵給嬰兒的那種東西。她說得沒錯,這是我的專長。一九九七年我贏得一個短篇小說獎,之後就有人帶著合約來找我出版首部小說,我得寫一篇具有開創性的嚴肅文學小說:這種小說通常會贏得更多獎項,然後在書店櫥窗裡展示。但實際上過去十一年來我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寫類型小說,因為這樣更容易賺錢;我需要錢付房租、付帳單、買吃的。我事先得到了一千英鎊的預付款,本該用這筆錢來還清債務,我卻買了一台筆記型電腦、一枝鋼筆,還有一些筆記本。正當我準備為這部小說寫綱要時,奧布圖書的克勞蒂亞打來說,如果我能在六個禮拜內寫出一本青少年驚悚小說,就可以賺到兩千英鎊。這本小說的官方作者是澤布•羅斯,他一年要出版四本書。其實世上並無此人,所以當時克勞蒂亞在招募新的槍手作家。我連想都不用想就可以作出決定:賺到兩倍的錢,然後開始寫真正的小說。可當我自己的小說才寫了幾章,第二本澤布•羅斯又來了,緊接著又是一本。幾年後我開始擴大範圍,用自己的名字寫了四本科幻小說,全部屬於一個系列,故事設定在一個叫紐托邦的地方。我一直打算完成自己那本「真正的」小說,但這看似永遠不會發生,哪怕到時間的末點。如果凱爾西•紐曼是對的,歐米伽點會在世界末日的時候令所有活過和沒活過的人復活,那澤布•羅斯定將是其中一員,這樣他就可以自己寫他的書了。而我,想必還是有房租要付。
我歎了口氣:「問題是,當你為自己的書設計劇情,你可以回頭去修改那些奇怪的地方,從而讓一切都合情合理。你可以刪除幾段或是幾頁的文字,甚至刪掉整篇稿子。但我不能讓時光倒流、讓你坐公車去馬克家——這也許是最好的辦法。」
「為什那樣就行得通?」
我聳聳肩。「天曉得。這樣的話你就可以像你說的那樣,走到我家,忘了鑰匙和電話。」
「但為什麼我會帶著個週末旅行袋?」
「是啊。我哪知。」
「肯定有辦法的。讓我們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怎麼樣講一個好故事?一言以蔽之。」
我看看錶。克里斯多夫一定在疑惑我在哪裡。
「鮑勃不是在等你嗎?」我說。
「我得把這件事搞定,不然就再也沒有鮑勃這個人了。」
「好。我們就長話短說。把故事建立在起因和結果上。只有三幕。」
「三幕?」
「開頭,中間,結尾。問題、高潮、解決方案。你要把它們串起來。讓某人搭上他不該上的船,把船弄沉,最後拯救他們——我只是舉例,不是要你這麼做。你必須先有個問題,再讓情況變糟,最後解決它。除非你是要寫悲劇。」
「萬一這真是悲劇怎麼辦?」
「莉比……」
「好啦。我和你一起出門,我搞丟了鑰匙。那很糟。更糟的是,我在找鑰匙的過程被輪暴了,而現在我失去了記憶,綁匪則帶走了你,因為你是證人、只有貝絲知道你在哪裡,她試圖告訴克里斯多夫,但是……」
「太複雜啦。簡單一點。你只需要解釋車子的問題。故事應該是我們一起出去玩,你丟了鑰匙,這讓你很煩惱。然後可能因為你丟了鑰匙又丟了車,所以你更加苦惱。也許有人偷走了你的鑰匙和車。誰知道呢?你只知道你丟了鑰匙。這裡唯一的技術問題就是你的車還在。」
等等等、點點點。我好像變成了一台設計來吐出這些鬼東西的「情節自動產生器」。為奧布圖書的新槍手作家「調配」類似的建議時,我總是告訴他們應該對自己的寫作有信心,不能只是遵循既定的規則。但是,當他們在原創的荒野裡迷路時,我就會引導他們回到配方奶的康莊大道上。
「那我和鮑勃怎樣才能從此幸福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呢?」
我想了一會兒。
「顯然你得把車推進河裡。」我笑道。
莉比呆坐了大約十秒鐘,兩隻手因為緊緊抓住方向盤而愈來愈蒼白。然後她下車,看了看四周。北岸河堤看上去仍如同荒野一般。沒有想要偷船的孩子,沒有遊客,沒有其他遛狗的人。沒有人在找我。莉比發出一聲嗚咽,有點兒像貝絲之前那樣。
「你說得沒錯,」她說,「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
「莉比,」我說,「我是在開玩笑。」
她回車上,原地開了一個踉蹌的三點轉向,把車頭朝向河面,開上了堤壩。有一瞬間,她看著像是要把車開進河裡。我站在那兒,不知道她是不是只是在胡鬧,也不知道是該笑還是該阻止她。她下了車,走到車子後面。莉比很嬌小,可當她的二頭肌繃緊起來我意識到她的手臂非常強壯。車動了,她肯定沒有拉上手煞車。她推車,車前輪越過了堤岸邊緣。
「莉比。」我又叫了她一聲。
「我一定是瘋了。我在幹什麼?」她說。
「沒事,」我說,「過來,不要這樣。你很難把事情解釋清楚。」
接著她就把車推進了河裡,然後把鑰匙扔出去。
「我會說是那些小鬼幹的。」她的聲音蓋過了水花和車下沉發出的聲響。「他們偷了我的鑰匙。儘管這聽起來也不太可信,但沒人會相信我絕望到把自己的車推進河裡,對吧?有什麼事會讓我做出這麼蠢的事呢!媽的。謝謝你,梅格。這真是個好主意。我明天再打給你——如果我還活著的話。」
她看錶,沿著河堤走向檸檬小屋,紅色披肩一面旗似的在風中飄蕩。我想起一個禪宗的故事,關於風和旗。是風在動,還是旗在動?兩個和尚就這個問題爭論不休,後來出現了一位智者,他說:「既非風動,亦非幡動,乃爾心動。」我慢慢往回走,貝絲又嗅了一遍長椅,就好像剛才什麼事都沒發生過。莉比沒有回頭,我看見她變得愈來愈小,走到街角後消失在貝亞達斯灣的方向。當然,科學家會告訴你,她並沒有愈變愈小,只是走遠罷了。
我的朋友莉比發來簡訊的時候我正在讀一本關於如何活過世界末日的書。她說:「你能在十五分鐘內趕到河堤嗎?出大事了!」這是二月初的一個寒冷周日,我幾乎一整天都縮在床上。我在達特茅斯住的小屋潮濕破舊。奧斯卡,我投稿報紙的文學編輯,寄來了凱爾西•紐曼的《永生的科學》,要我寫書評。隨書寄來的還有一張紙條,寫著奉承的話。那些日子我非常缺錢,所以什麼活兒都接。情況其實也沒那麼糟:在科學書評界我已經逐漸樹立起了一定的名聲,因此奧斯卡總是把最好的書給我。我的男友克里斯多夫在世界遺產遺址做無償志工,所以我必須獨力負擔...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