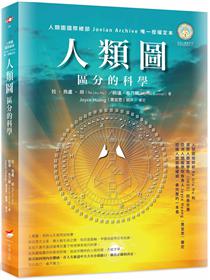七月與安生
七月第一次遇見安生的時候,是十三歲的時候。新生報到會上,一大堆排著隊的陌生同學。是炎熱的秋日午後,明亮的陽光照得人眼睛發花。突然一個女孩轉過臉來對七月說,我們去操場轉轉吧。女孩的微笑很快樂。七月莫名其妙地就跟著她跑了。
很久以後,七月對家明說,她和安生之間,她是一次被選擇的結果。只是她心甘情願。
雖然對這種心甘情願,她並不能做出更多的解釋。
我的名字叫七月。當安生問她的時候,七月對她說,那是她出生的月分。那一年的夏天非常炎熱。對母親來說,酷暑和難產是一次劫難。可是她給七月取了一個平淡的名字。
就像世間的很多事物。人們並無方法從它寂靜的表像上猜測到暗湧。比如一個人和另一個人的相遇,或者他們的離別。
而安生,她說,她僅僅只證實到自己的生命。她攤開七月的手心,用她的指尖塗下簡單的筆畫,臉上帶著自嘲的微笑。那是她們初次相見的景象。秋日午後的陽光在安生的手背上跳躍,像一群活潑的小鳥振動著翅膀飛遠。
那時候她還沒有告訴七月,她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她的母親因為愛一個男人,為他生下孩子,卻註定一生要為他守口如瓶。七月也沒有告訴安生,安生的名字在那一刻已在她的手心裡留下無痕的烙印。
因為安生,夏天成為一個充滿幻覺和迷惘的季節。
十三歲到十六歲。那是七月和安生如影相隨的三年。有時候七月是安生的影子。有時候安生是七月的影子。一起做作業。跑到商店去看內衣。週末的時候安生去七月家裡吃飯,留宿。走在路上都要手拉著手。
七月第一次到安生的家裡去玩的時候,感覺到安生很寂寞。安生獨自住一大套公寓。她的母親常年在國外,僱了一個保母和安生一起生活。安生的房間布置得像公主的宮殿,有滿滿衣櫥的漂亮衣服。可是因為沒有人,顯得很寒冷。七月坐了一會兒就感到身上發抖。安生把空調和所有的燈都打開了。她說,她一個人的時候常常就這樣。然後她帶七月去看她母親養的一缸熱帶魚。安生丟飼料下去的時候,美麗的小魚就像一條條斑斕的綢緞在抖動。
安生說,這裡的水是溫暖的。可是有些魚,牠們會成群地穿越寒冷的海洋,遷徙到遼闊的遠方。因為那裡有牠們的家。安生那時候的臉上有一種很陰鬱的神情。
在學校裡,安生是個讓老師頭痛的孩子。言辭尖銳,桀驁不馴,常常因為和老師搶白而被逐出教室。少年的安生獨自坐在教室外的空地上,陽光灑在她倔強的臉上。七月偷偷地從書包裡抽出小說和話梅,扔給窗外的安生。然後她知道安生會跑到她的窩去看書。
那是她們在開學的那個下午跑到操場上找到的大樹。很老的樟樹,樹葉會散發出刺鼻的清香。安生踢掉鞋子,用幾分鐘時間就能爬到樹杈的最高處。她像一隻鳥一樣躲在樹葉裡。晃動著兩條赤裸的小腿,眺望操場裡空蕩蕩的草地和遠方。七月問她能看到什麼。她說,有綠色的小河,有開滿金黃雛菊的田野,還有石頭橋。一條很長很長的鐵軌,不知道通向哪裡。
然後她伸手給她,高聲地叫著,七月,來啊。七月仰著頭,絞扭著自己的手指,又興奮又恐懼。可是她始終沒有跟安生學會爬樹。
終於有一天,她們決定去看看那條鐵路。她們走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暮色迷離,還沒有兜到那片田野裡面。半路突然下起大雨。兩個女孩躲進了路邊的破茅草屋裡。七月說,我們還是回家吧。安生說,我肯定再走一會兒就到了。我曾發誓一定要到這段每天都能看到的鐵路上走走。
於是大雨中,兩個女孩撐著一把傘向前方飛跑。裙子和鞋子都溼透了。終於看到了長長的鐵軌。在暮色和雨霧中蔓延到蒼茫的遠方。而田野裡的雛菊早已經凋謝。
安生的頭髮和臉上都是雨水。她說,七月,總有一天,我會擺脫掉所有的束縛,去更遠的地方。七月低下頭有些難過。她說,那我呢。安生說,妳和我一起走。她似乎早替七月做好打算。
國中畢業,十六歲。七月考入市裡最好的重點中學。安生上了職業高中,學習廣告設計。
七月成為學校裡出眾的女孩。成績好,脾氣也一貫的溫良,而且非常美麗。她參加了學校的文學社。雖然作文常常在比賽中獲獎,但是她知道真正寫得好的人是安生。她們曾借來大套大套的外國小說閱讀,最喜歡的作家是海明威。只是安生向來不屑參加這些活動。而且她的作文總是被老師評論為不健康的頹廢。
沒有安生陪伴的活動,七月顯得有些落寞。文學社的第一次會議,七月到得很早。開會的教室裡都是陽光和桂花香,有個男孩在黑板上寫字。七月推開門說,請問……然後男孩轉過臉來,他說,七月,進來開會。他的笑容很溫和。
蘇家明是七月十六歲以前包括以後看到過的,最英俊的男人。
七月開完會忍不住對安生說,妳喜歡什麼樣的男人。安生說,我不會喜歡男人。有人說,除非妳非常愛這個男人,否則男人都是難以忍受的。她一邊說一邊拿出菸來抽。安生已開始去打工。她對學習早就喪失了樂趣。
她去麥當勞打工,去酒吧做服務生找老外聊天,去美院學習油畫。她迫不及待地想擺脫掉寂寞的生活,只想不斷地經歷生命中新鮮的事物和體驗。為了和一幫美院學生一起去山區寫生,她逃了學校一個月的課。學校因此要把安生開除。
安生的母親第一次出現。擺平安生惹下的禍,還專門和七月見了面。她穿縫著精緻寬邊的緞子旗袍,戴著小顆鑽石耳針,說話的聲音很嬌柔。她說,七月,妳們兩個要好好在一起。我馬上要回英國,妳要管住她。七月說,安生會很希望妳陪著她,為什麼妳不留下來。她微笑著輕輕嘆了口氣,很多事情並不像妳們小孩想得那麼自由。
七月不明白。她只覺得安生寂寞,安生每次到她家裡來都不肯走。一起吃飯,一起睡覺。她喜歡屋子裡有溫暖的燈光和人的聲音。七月家裡有她父母弟弟一共四個人,安生對每個人都會撒嬌。
七月看著安生的母親。覺得她很像安生的房間,空曠而華麗。而寒冷深入骨髓。
那天夜晚,七月在家裡,和父母弟弟一起吃飯,感到特別溫情。她想,她擁有的東西實在比安生多。她不知道可以分給安生一些什麼。晚上下起雨來,七月修改校刊上的文章,又模糊地想起陽光和桂花香中那張微笑的臉。家明很喜歡她,週末約了她去看電影。也許安生能愛上一個人也會好一些。
深夜的時候,七月聽到敲門聲。她打開門,看到渾身淋得溼透的安生,抱著雙臂靠在門框上。她走了。安生面無表情地對七月說。搭的是晚上的飛機。
七月給安生煮了熱牛奶,又給她放熱水,拿乾淨衣服。安生躺下後,一言不發地閉上眼睛。七月關掉燈,在安生旁邊慢慢躺下來,突然安生就緊緊地抱住了她。她把頭埋在七月的懷裡,發出像動物一樣受傷而沉悶的嗚咽,溫暖黏溼的眼淚順著七月的脖子往下淌。七月反抱住她。好了,安生乖。一切都會好的。我們會長大的,長大了就沒事了。
七月說著說著,在黑暗中也哭了。
七月和家明去看電影。看完走出劇院以後,想起來安生曾對她說,她在附近的Blue酒吧做夜班。家明,我們去看看安生。七月曾對他提起過自己最好的朋友。家明說,好。他在夜風中輕輕把七月的手放在自己的大衣口袋裡。兩個人都是安靜溫和的人。所以即使在重點中學裡,老師也沒有什麼意見。因為都是成績品性優良的學生。
遠遠看到Blue舊舊的雕花木門。一推開,震耳欲聾的音樂和嗆人的菸草味道就撲面兜過來。狹小的舞池擠滿跳舞的人群。還有人打牌或聊天。七月牽著家明的手擠到圓形的吧檯邊,問一個在調酒的長頭髮男人,請問安生在嗎。男人抬起臉冷冷地看了七月一眼,然後高聲地叫,Vivian,有人找。然後一個女孩就從人群裡鑽了出來。
陰暗的光線下,七月差點認不出來這就是安生。一頭濃密漆黑的頭髮紮成一束束的小辮子,髮梢綴著彩色的玻璃珠。銀白的眼影,紫色的睫毛膏,還有酒紅的脣膏。穿著一件黑色鏤空的蕾絲上衣,緊繃著她美好的胸脯。安生先看到家明,愣了一下。然後對七月笑著說,我們來喝酒吧。
加冰塊的海尼根,家明喝掉了一瓶。然後他問安生,覺得蹺課一個月去寫生快樂嗎。
安生說,我們在茫茫野地中生火煮咖啡。在冰涼的溪水中洗澡。晚上躺在睡袋裡看滿天星斗。那一刻,我問自己,活著是為了什麼。看著漫天繁星的時候,我會以為生命也許就是如此而已。回來後畫了油畫星夜。畫布上有深深的藍,和掉著眼淚的星斗。有人問我一百塊錢賣不賣。我說賣。為什麼不賣。它到了一個看得懂的人的手裡,就是有了價值。
安生說完看著家明。她說,家明,你的眼睛很明亮。家明笑了。
把七月送到家門口以後,家明說,安生是個不漂亮的女孩,但是她像一棵散發詭異濃郁芳香的植物,會開出讓人恐懼的迷離花朵。
七月生日的時候,家明想帶七月去郊外爬山。七月說,每次生日安生都要和我在一起的。家明說,我們當然可以和安生在一起。
安生很快樂地和七月家明一起,騎著破單車來到郊外。爬到山頂的時候發現上面有個小寺廟。陽光很明亮。那天安生穿著洗得褪色的牛仔褲和白襯衫,又回復她一貫的清純樣子。家明和七月都穿著白色的T恤。安生提議大家把鞋子脫下來,光著腳坐在山路臺階上讓相機自拍,來張合影。大家就歡歡喜喜地拍了照片,然後走進寺廟裡面。
這裡有些陰森森的。七月說。她感覺這座頹敗幽深的小廟裡,有一種神祕的氣息。她說她累了,不想再爬到上面去看佛像。我來保管包包和相機吧,你們快點看完快點下來。
家明和安生爬上高高的臺階,走進陰暗幽涼的殿堂裡面。安生坐在蒲團上,看著佛說,祂們知道一切嗎。家明說,也許。他仰起頭,感覺到在空蕩蕩的屋簷間穿梭過去的風和陽光。然後他聽到安生輕輕地說,那祂們知道我喜歡你嗎。
七月看到家明和安生慢慢地走了下來。她聞著風中的花香,感覺到這是自己最幸福的一刻。她心愛的男人和最好的朋友,都在她的身邊。很多年以後,七月才知道這是她最快樂的時間。只是一切都無法在最美好的時刻凝固。
家明,廟裡在賣玉石鐲子。七月說,我剛才一個人過去看了,很漂亮的。安生說,好啊,讓家明送一個。只剩下兩個了。一個是淡青中嵌深綠的,另一個是潔白中含著絲縷的褐黃。家明說,七月妳喜歡哪一個。七月說,也要給安生買的。安生喜歡哪一個。
安生看看,很快地點了一下那個白色的,說,我要這個。
她把白鐲子戴到手腕上,高興地放在陽光下照。真的很好看啊,七月。七月也快樂地看著孩子一樣的安生。我還想起來,古人說環珮叮噹,是不是兩個鐲子放在一起,會發出好聽的聲音。走了一半山路,安生又突發奇想。來,七月,把妳的綠鐲子拿過來,讓我戴在一起試試看。安生興高采烈地把七月取下來的綠鐲子往手腕上套。就是一剎那的事情。兩個鐲子剛碰到一起,白鐲子就碎成兩半,掉了下來。山路上灑滿白色的碎玉末子。
安生愣在了那裡。只有她手上屬於七月的綠鐲子還在輕輕搖晃著。家明臉色蒼白。
七月,我要走了。安生對七月說,我要去海南打工,然後去北京學習油畫。
秋天的時候,安生決定輟學離開這個她生活了十七年的城市。她說,我和阿Pan同去。
阿Pan想關掉Blue,是那個長頭髮的男人?七月問。是。他會調酒,會吹薩克斯風,會飆車,會畫畫。我很喜歡他。安生低下頭輕輕地微笑。
一個男人,妳要很愛很愛他,妳才能忍受他。那妳能忍受他嗎。
我不知道。安生拿出一支菸。她的菸開始抽得厲害。有時候畫一張油畫,整個晚上會留下十多個菸頭。可是安生,妳媽媽請求過我要管住妳。七月抱住她。
關她屁事。安生粗魯地咒駡了一句。她的存在與否和我沒有關係。安生神情冷漠地抽了一口菸。我恨她。我最恨的人,就是她和我從來沒有顯形過的父親。
七月難過地低下頭。她想起小時候她們冒著雨跑到鐵路軌道上的情景。她說,安生,那我呢。妳會考上大學,會有好工作。當然還有家明。她笑著說,告訴我,妳會嫁給他嗎。七月?
嗯。如果他不想改變。七月有些害羞,畢竟時間還有很長。
不長,不會太長。安生抬起頭看著窗外。我從來不知道永遠到底有多遠,也許一切都是很短暫的。
安生走的那天,乘的是晚上的火車。她想省錢,而且也過慣了辛苦日子。阿Pan已經先到海南。安生獨自走。安生只背了一個簡單的行李包,還是穿著舊舊的牛仔褲,裹了一件羽絨外套。七月一開始有點麻木,只是愣愣看著安生檢查行李,驗票,上車把東西放妥。
她把洗出來的合影給安生。那張照片拍得很好。陽光燦爛,三張年輕的笑臉,充滿愛情。
家明真英俊。安生對七月微笑,一邊把照片放進外套胸兜裡。七月就在這時看到她脖子上露出來的一條紅絲線。這是什麼。她拉出來看。是塊小玉牌墜子。玉牌很舊了,一角還有點殘缺,整片皎白已經蒙上暈黃。安生說,我在城隍廟小攤上買的,給自己避避邪氣。她很快把墜子放進衣服裡面。
七月,妳要好好的,知道嗎。我會寫信來。
汽笛鳴響了,火車開始緩緩移動駛出月臺。安生從窗戶探出頭來向七月揮手。七月心裡一陣尖銳的疼痛,突然明白過來安生要離開她走了。一起上學,吃飯,睡覺的安生,她不會再看到了。
安生,安生。七月跟著火車跑,安生妳不要走。空蕩蕩的月臺上,七月哭著蹲下身來。
該回家了,七月。匆匆趕來的家明抱住了七月。是的,家明。該回家了。七月緊緊拉住家明溫暖的手。家明把她冰涼的手放在自己的口袋裡,然後把她的臉埋入懷裡。他的眼睛裡有淚光。
家明,不管如何,我們一直在一起不要分開,好不好。七月低聲地問他。家明沉默了一下,然後輕輕地點了一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