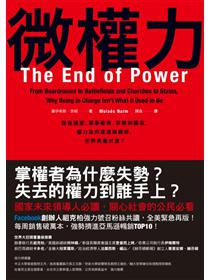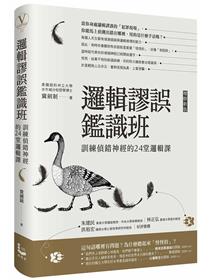★ 英國歷史寫作傳奇/戰史書寫第一健筆/百萬暢銷名家作品臺灣首發
★ 以戰爭著述入圍法國文壇最崇隆之【梅迪奇文學獎】
★ 經典影集《諾曼第大空降》101 空降師血淚戰役場景/細膩還原
★ 全書收錄詳盡軍事圖例/19 張精密描繪的戰場地圖/48 張第一手戰事、人物珍稀照片
★ 二戰迎向終點的關鍵一役/徹底完結希特勒稱霸幻夢
1944 年 12 月。嚴冬。險峻的阿登山區。幽暗密林。
納粹裝甲傾巢而出,絕命一搏!
上百萬飽受凍瘡與飢寒所迫的大兵,正在雪地上用鮮血踏出文明的生路。【內容簡介】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希特勒在比利時阿登山區發動了「最後一場豪賭」。這位納粹軍頭堅信他的裝甲鐵蹄可一路直衝安特衛普,分裂盟軍,並迫使盟軍從德國本土撤出,重新奪回西線主導權。德軍毫無保留,精銳盡出,動員一切人力、武器,欲在雪封千里的幽暗深林徹底粉碎盟軍。英、美兵將浴血挺立,縱然火彈穿身、凍瘡蝕肉,也堅抗不退,最終聯手保住戰線。天命有時,狂人終要俯首認敗。這就是持續一個多月、參與人數超過百萬、二戰結束前西線戰場最大規模的悲壯輓歌「突出部之役」。經此一役,希特勒再無後備兵力可供運用,德軍從此無以阻擋盟軍挺進。幾個月後,納粹軍敗亡,二戰結束。
本書由獲獎無數的英國軍事寫作傳奇安東尼•畢佛爵士執筆,精采重述這場絕命之戰。筆法猶似電影分鏡,靈活編織大量獨家文件、對話、日記、報導片段,從戰場前線小兵的悲情家書,到高階將官暗懷鬼胎的內心劇碼,第一手還原戰事中每一位角色的心理狀態與當下實感。隨著這位文字導演節奏分明的換幕跟拍,我們已然身處冰雪連天的戰場:七十五年前,一處歐陸的山區。雪地坦克履帶深痕。戰壕腳正在足下發爛。黑暗中,一輛虎式戰車的砲塔轉了過來……
『希特勒出其不意又殘忍無情的阿登攻勢,將東線戰場的慘烈帶到了西線。然而,正如日本一九三七年入侵中國、納粹一九四一年入侵蘇聯,全面戰爭的震撼,並未如他們預期的引來舉世驚慌與崩潰。相反地,它激起廣大群眾負隅頑抗、即便受到包圍也要作戰到底的決心。當德國大軍呼嘯著進攻,孤軍奮戰的連隊在極度不利的情況下堅守關鍵村落。他們的犧牲為盟軍爭取增援部隊抵達的時間;這是他們為打破希特勒的美夢所做的重大貢獻。也許,德國領導人在阿登攻勢犯下的最大錯誤,就是低估了他們長期以來故作輕蔑的部隊與士兵。』── 安東尼•畢佛
【各界最高讚譽】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軍事散文。
── 西班牙《國家報》(El País)
當代最優異的軍事歷史學家之一。本書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除了散文的生動性與作者對戰鬥事件的清晰闡述,更有賴他細膩描摹、引用的技巧,還原了戰場的實況與氣味。作者巧妙地將龐大的策略與戰鬥敘述編織在一起,神乎其技。
──《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屢獲殊榮的軍事歷史學家畢佛深入探討了突出部之役。這是一系列珍貴、令人難忘的人物側描,全書細節驚人,視野廣博,揭露許多引人入勝的軼聞──極可能是關於這場經典戰役在未來多年內都難以超越的決定之書。對二戰史感興趣的人,絕對必讀。
──《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要寫下戰爭的歷史,首先得有能力說故事。沒有人比畢佛說得更好。本書堪稱他迄今最好的著作。
──《MHQ 雜誌》(MHQ Magazine)
作者簡介:
安東尼.畢佛Antony Beevor
英國著名史學家,被譽為「當今世上最優秀的軍事歷史學家之一」。曾任英國作家協會主席、肯特大學客座教授。撰寫多部二戰軍事戰史著作,並已售出七百萬本以上、翻譯為三十多種語言發行全球。每回作品出版皆為盛事,且立即登上暢銷書榜,是英國歷史寫作的金字招牌。
畢佛曾在皇家第十一輕騎兵隊服役,之後投身於歷史非虛構寫作。作品主要關注二戰與戰後世界,榮獲史學界及文壇多個重量級獎項。代表作品有《史達林格勒》(Stalingrad)、《柏林陷落》(Berlin : The Downfall 1945)、《諾曼第登陸之戰》(D-Day : The Battle for Normandy)、《第二次世界大戰》(The Second World War)等。本書《解密突出部之役》曾於 2015 年獲得法國地位崇高的「梅迪奇文學獎」論說文類(Prix Médicis essai)提名。
有鑑於他在歷史、文學領域的傑出貢獻,法國政府授予他「藝術與文學騎士勳章」;2014 年更獲頒美國普利茲克文學獎「軍事寫作終身成就獎」(Pritzker Literature Award for Lifetime Achievement in Military Writing)。2017 年,畢佛晉升為英國爵士勳位。
譯者簡介:
黃佳瑜
臺灣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企管碩士。曾任聯合利華行銷企劃、美商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管理顧問。現為自由譯者,譯作有:《Jack》、《但求無傷》、《敦克爾克大撤退》、《發光體》、《孤獨的反義詞》、《財團治國的年代》、《精神病院裡的歷史學家》、《向 50 位頂尖管理大師學領導》、《成為這樣的我:蜜雪兒‧歐巴馬》(合譯)等。
章節試閱
1. 勝利熱潮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晨,艾森豪將軍從沙特爾(Chartres)啟程,準備看看剛解放的巴黎。「今天是星期天,」盟軍最高司令告訴隨行的布萊德雷將軍(Omar Bradley),「所有人都會賴床,我們此行可以不驚動任何人。」然而,當兩位將軍在這趟所謂的「非正式參訪」朝法國首都風馳電掣行進時,他們的行動很難不引人注目。最高司令的草綠色凱迪拉克由兩輛裝甲車護送,另有一名准將坐鎮吉普車負責前導。
當他們抵達奧爾良門,第三十八騎兵偵察中隊已在傑羅少將(Lenoard Gerow)的指揮下呈檢閱隊形恭候大駕,形成了更盛大的護送隊伍。傑羅少將是艾森豪的老朋友;進攻巴黎期間,法軍第二裝甲師的勒克萊爾將軍(Philippe Leclerc)三番兩次違抗他的命令,此刻,他依然為此怒氣衝天。傑羅以巴黎的軍事首長自居,前一天,他下令禁止勒克萊爾及其部隊參與戴高樂將軍從凱旋門到聖母院的遊行。相反地,他囑咐他「堅守當前任務,肅清殘留在巴黎及其近郊的敵人」。收復首都的過程中,勒克萊爾始終對傑羅的命令置若罔聞,但是那天早晨,他確實派遣了部分軍隊前往城市北郊,掃蕩聖德尼(Saint-Denis)一帶的德軍陣地。
巴黎街道冷冷清清,因為還能動的車輛幾乎被撤退的德軍掠奪殆盡。由於電力供應微弱,就連地鐵也不太可靠。事實上,這座有「光城」之名的城市已淪落到要用黑市蠟燭照明的地步。美麗的建築雖然幸運逃過一劫,卻顯得黯淡而陳舊。希特勒要讓巴黎化為「一片廢墟」的命令並未被貫徹執行。街頭民眾憑著喜悅的新鮮後勁,一見到美國大兵或美軍車輛仍會響起一陣歡呼,不過,要不了多久,巴黎市民就會開始咕噥著說,「比德國佬還糟。」
儘管艾森豪表示這趟巴黎之行「可以不驚動任何人」,但他們此行有一個明確的目的。他們打算會見戴高樂將軍──羅斯福總統拒絕承認的法國臨時政府領導人。羅斯福堅決表示,在法國的美國軍事力量不會協助戴高樂將軍取得政權,然而個性務實的艾森豪已準備好忽略總統的明確指令。最高司令需要在前線後方建立穩固的力量,既然戴高樂是提供穩定力量的不二人選,他願意支持他。
戴高樂和艾森豪都不希望見到解放時期的危險混亂局面一發不可收拾,尤其值此流言四起、風聲鶴唳、陰謀論和告發賣國賊的惡言惡語此起彼落的年代。在鄰近巴黎市政廳的一次行動中,作家沙林傑(時任第四步兵師反情報上士)與同袍聯手逮捕了一名嫌犯,卻只能任由群眾拖走嫌犯,眼睜睜看著他們將他毆打致死。戴高樂前一天從凱旋門到聖母院的勝利遊行,最後在教堂槍聲大作中告終。這起事件讓戴高樂確信他必須解除地下反抗軍(the Resistance)的武裝,將其成員整編成正規的法國部隊。當天下午,SHAEF──盟軍遠征軍最高司令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Expeditionary Force)──接到一萬五千套制服的請求。很不巧,小號制服的數量不夠,因為一般法國男性的個頭明顯比美國同輩矮小。
戴高樂在聖多米尼克街的陸軍部(ministry of war)會晤兩位美國將軍。悲慘的一九四○年夏天,他短暫的部長生涯就是從這裡展開的。如今他回到此地,特意表達延續的意味。要抹除維琪政權的恥辱,他的解決辦法簡潔有力:「共和國從未停止存在。」戴高樂希望艾森豪讓勒克萊爾師留守巴黎以維護法律與秩序,但既然勒克萊爾的幾支部隊已經開拔,他提議美軍不妨透過「展現壯盛軍容」來懾服老百姓,向他們保證德軍不會回頭進犯。何不讓一兩個師在出征前線的途中,順道遊行穿越巴黎?眼看戴高樂竟然要求美軍幫忙「鞏固他的地位」,艾森豪不免有些啼笑皆非,於是轉而徵詢布萊德雷的想法。布萊德雷表示他可以在一兩天內完成調度,毫無問題。於是艾森豪邀請戴高樂在布萊德雷將軍陪同下接受軍隊致敬,他本人則迴避出席。
在返回沙特爾途中,艾森豪邀請蒙哥馬利將軍(Sir Bernard Montgomery)陪同戴高樂與布萊德雷參加遊行,但蒙哥馬利拒絕前往巴黎。這麼一個微小卻相關的細節,並不妨礙英國某些報紙指控美方企圖獨占所有榮耀。「艦隊街」(Fleet Street)難以克制衝動,每每把SHAEF的決策視為藐視蒙哥馬利──也就是怠慢英國──的舉動,嚴重傷害了同盟國之間的關係。這反映出英國民眾普遍不滿自己的國家遭到排擠,退居二線地位。現在是美國人當家了,他們將搶盡勝利的功勞。英國媒體的偏見,讓艾森豪的英籍副手──空軍上將亞瑟.泰德爵士(Sir Arthur Tedder)──憂心忡忡:「根據我在SHAEF聽到的一切,我忍不住擔心,這段期間埋下了盟國之間嚴重分裂的種子。」
隔天晚上,第二十八步兵師奉指揮官諾曼.科塔少將(Norman D. Cota)之命,冒著滂沱大雨從凡爾賽朝巴黎前進。在奧瑪哈海灘展現過人勇氣與領導能力的「荷蘭人」科塔,不到兩星期前才因為前任指揮官遭德國狙擊手槍殺身亡而剛剛走馬上任。六、七月間,在灌木叢生的諾曼第鄉間作戰,是一場進度緩慢而死傷慘重的戰事,但是八月初,喬治.巴頓將軍(George S. Patton)的第三軍團帶頭突圍,使得進攻塞納河與巴黎期間,盟軍部隊的樂觀情緒高漲。
布洛涅森林(Bois de Boulogne)裡搭起了淋浴設備,供科塔的弟兄在遊行前把自己梳洗乾淨。翌日上午,也就是八月二十九日,部隊從福熙大街(Avenue Foch)和凱旋門之間出發,踏上風景如畫的香榭麗舍大道。步兵們頭戴鋼盔,扛起上了刺刀的步槍,以完整的戰鬥序列展開遊行。浩大的草綠色隊伍橫跨整條馬路,一列接著一列,每列二十四人。每名士兵的肩上都別著師隊徽章──代表賓州的紅色「拱心石」標誌;這個肩章以其形狀被德軍取了「血色鏟斗」的綽號。
法國民眾大感驚奇,一方面因為美軍制服顯得輕鬆隨意,另一方面則因為美軍看似擁有無限量的機械裝備。「一支機械大軍,」日記作家尚.加爾蒂耶─布瓦西埃(Jean Galtier-Boissière)如此評論。那天早上在香榭麗舍大道,法國民眾簡直無法相信一個步兵師竟擁有如此眾多的車輛:數不盡的吉普車,部分車輛後頭架著點五○機關槍;偵察車;以履帶牽引車拖曳的一五五毫米「長腳湯姆」(Long Tom)榴彈砲;工程車;勤務單位的小型軍車與十噸大卡車;M4謝爾曼坦克和坦克殲擊車。德國國防軍自一九四○年以來在法國似乎戰無不勝,然而美軍的展示,卻讓德軍的馬車運輸看起來古怪而過時。
閱兵台設在協和廣場,那是陸軍工兵以倒扣的登陸艇搭建而成的,上頭用一條長長的三色布幔遮蓋,並且插著不計其數的星條旗在微風中飄揚。由五十六人組成的樂隊在最前方帶頭遊行,吹奏著師隊進行曲〈卡其比爾〉(Khaki Bill)。觀賞閱兵表演的法國民眾恐怕料想不到,但全體官兵心知肚明,第二十八師即將朝城市北緣的德軍陣地出發。「那是史上最不尋常的進攻命令,」布萊德雷後來對他的侍從官說,「我想,沒幾個人知道這群弟兄要從遊行隊伍直接走上戰場。」
在英吉利海峽沿岸,加拿大第一軍團必須奪下大港口勒阿弗爾(Le Havre),英國第二軍團則朝東北方的加萊海峽省(Pas de Calais)推進,目標是德軍的幾處V型飛彈發射場。儘管坦克駕駛兵已疲憊不堪,而且八月三十到三十一日間的夜裡下了一場狂風暴雨,英軍近衛裝甲師(Guards Armoured Division)仍在法國反抗軍協助下攻占亞眠(Amiens),並跨越索姆河(Somme)的幾道橋梁。隔天早晨,德軍第五裝甲軍團司令海因里希.埃伯巴赫將軍(Heinrich Eberbach)被殺了個猝不及防;英軍得以在據守加萊海峽省的德軍第五裝甲軍團及第十五軍團的殘部之間切出一道缺口。由加拿大皇家軍團(Royal Regiment of Canada)、皇家漢密爾頓輕步兵團(Royal Hamilton Light Infantry)以及埃塞克斯蘇格蘭步兵團(Essex Scottish)領頭的加拿大軍隊,則朝他們兩年前在突襲戰中傷亡慘重的第厄普(Dieppe)前進。
盟軍陣營裡,勝利的歡喜氣氛前所未有地高漲。那年夏天,刺殺希特勒的七月炸彈陰謀(July bomb plot)讓人不由得相信德軍內部已開始分崩離析,正如一九一八年的情況。然而實際上,刺殺行動的失敗卻讓納粹勢力毫無節制地擴張。SHAEF的G-2情報部門歡欣鼓舞地表示:「八月的會戰已了結對手,西面的敵軍遭受了致命打擊。」在倫敦,戰爭內閣相信一切將在耶誕節以前結束,為了計劃之便,他們把結束戰事的日期訂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只有邱吉爾仍然提防著德國人奮戰到底的決心。華府也抱持類似的假設,因此逐漸將注意力轉向戰情依然膠著的太平洋對日戰爭;美國戰時生產局(War Production Board)開始取消包括砲彈在內的軍需品合約。
許多德國人也認為大勢已去。駐烏特勒支(Utrecht)的弗立茲.福爾里德中校(Fritz Fullriede)在日記中寫道:「西線完蛋了,敵軍已進入比利時、瀕臨德國邊境;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洛伐克和芬蘭紛紛求和,有如一九一八年舊事重演。」在柏林火車站,抗議群眾膽敢高舉這樣的標語:「我們企求和平,不計一切代價。」在東線戰場,紅軍的巴格拉基昂行動(Operation Bagration)粉碎了德國的中央集團軍(Army Group Centre),大軍推進五百公里,直抵華沙外圍和維斯瓦河(River Vistula)。三個月之內,德國國防軍在東線折損了五十八萬九千四百二十五人,在西線則損失了十五萬六千七百二十六名兵力。
紅軍挺進維斯瓦河,鼓舞了勇氣十足卻註定失敗的波蘭救國軍(Armia Krajowa)起義。史達林並不希望波蘭獨立,因此無情地旁觀德軍鎮壓波蘭的起義行動。東普魯士以及希特勒位於拉斯滕堡(Rastenburg)附近的總部「狼穴」(Wolfsschanze)也面臨了威脅,除此之外,德國在巴爾幹地區同樣兵敗如山倒。就在巴黎解放兩天前,羅馬尼亞在蘇聯軍隊大舉壓境之際叛離了軸心國。八月三十日,紅軍進入布加勒斯特,占領普羅耶什蒂(Ploesti)一帶的重要油田。通往匈牙利平原及多瑙河的道路暢行無阻,一路延伸進入奧地利及德國本土。
八月中,喬治.巴頓將軍的第三軍團從諾曼第殺向塞納河,在此同時,龍騎兵行動(Operation Dragoon)成功在地中海沿岸的坎城(Cannes)和土倫(Toulon)之間登陸。德軍面臨後路被切斷的威脅,不得不大舉橫越法國進行撤退。心知自己一旦落入反抗軍之手即難逃厄運的維琪民兵(Vichy Milice)成員,也紛紛穿越敵境到德國尋求安全,有些人甚至跋涉上千公里。臨時湊成的「行軍隊伍」──由德國陸海空三軍及大西洋沿岸的非作戰人員所組成──奉命往東撤逃,沿路設法躲避法國反抗軍。德國國防軍開始在第戎(Dijon)附近的突出部加強兵力,設法護送將近二十五萬名德軍。另有五萬一千名士兵困在大西洋沿岸及地中海地區。儘管毫無希望奪回幾座重大港口,但這些大港仍被元首指定為「要塞」據點。一名德國將軍把這樣的否認現實比喻成天主教神父在耶穌受難節對盤子上的豬肉灑聖水,然後說:「你是一條魚。」
七月二十日的炸彈行刺事件落幕後,希特勒的偏執達到了新頂點。在東普魯士狼穴,他原本就對德國總參謀部嗤之以鼻,嘲笑他們不過是「一群知識分子」,如今更變本加厲。「現在我知道為什麼我這幾年對俄羅斯的偉大計劃一再失敗,」他說,「全都因為背叛!如果不是那些叛徒,我們老早就贏了。」希特勒痛恨七月陰謀的參與者,不僅因為他們企圖謀反,也因為他們傷害了德國的團結形象,並且對第三帝國的盟友與中立國家產生了負面影響。
希特勒在八月三十一日的戰情會議上宣稱:「同盟國內部關係總有緊繃到決裂的一天,在歷史上,國與國之間的聯盟必定會在某些瞬間崩潰瓦解。」不久後,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很快在柏林一場部長會議沿襲元首的思維路線。「隨著同盟國眼看即將勝利,其內部的政治衝突肯定逐日攀升,總有一天,敵營必將出現無法修補的裂痕。」
德國空軍參謀長維爾納.克萊普中將(Werner Kreipe)在八月最後一天的日記中說道:「傍晚傳來西線潰守的消息。」在「命令、指示、電話聯繫」之下,慌亂的行動持續徹夜。隔天早晨,國防軍最高統帥部(OKW)首長威廉.凱特爾陸軍元帥(Wilhelm Keitel)要求空軍將另外五萬名士兵調到地面部隊。九月二日,克萊普寫道:「西線顯然註定瓦解,約德爾(Jodl;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作戰廳長)出乎意料地鎮定。芬蘭人跟我們劃清界線。」在那天的會議中,希特勒開始出言侮辱芬蘭領袖曼納海姆元帥(Marshal Mannerheim)。他也因為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竟然懶得在此關鍵時刻現身而大發雷霆,甚至建議解散德國的空軍中隊、將飛行組員轉調到高射砲部隊。
紅軍如今瀕臨東普魯士邊境,希特勒擔心自己會遭蘇聯傘兵部隊逮捕。狼穴成了一座堡壘。「此刻,一座巨大裝置已搭建完成,」他的祕書特勞德爾.榮格(Traudl Junge)寫道,「到處是路障與新的崗哨,還有地雷、纏繞的棘刺鐵絲網和瞭望塔。」
希特勒希望找到值得信任的軍官來指揮他的護衛部隊。奧圖.瑞馬上校(Otto Remer)曾率領柏林大德意志衛戍營(Grossdeutschland guard battalion)擊潰七月二十日行刺事件的黨羽,所以當希特勒聽說瑞馬請求重回戰場,便命令他組建一支旅級部隊,負責防衛狼穴。瑞馬的部隊最初是以柏林營以及擁有八組砲台的戈林高砲團為基礎,隨後一天天擴大勢力。元首護衛旅(Führer Begleit Brigade)在九月成軍,準備好為狼穴抵禦「二到三個空降師的空降作戰行動」。瑞馬口中這個「不尋常的聯合隊伍」被賦予絕對優先權,可以優先取得武器、裝備,以及主要來自大德意志師的「資深前線作戰人員」。
狼穴氣氛極度低迷。接連幾天,希特勒成天賴在床上,無精打采地躺著,而他的祕書則「打出一疊又一疊的傷亡報告」,東線和西線戰事雙雙失利。在此同時,戈林留在東普魯士,他之前強占了霍亨索倫家族的羅明登(Rominten)狩獵莊園,此刻正躲在這裡生悶氣。他的空軍在諾曼第遭受挫敗後,他知道在元首面前,自己已被競爭對手將了一軍,尤其是日後成了他的剋星、心機很深的馬丁.鮑曼(Martin Bormann)。他的另一個對手,黨衛軍全國領袖(Reichsführer-SS)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則在預備軍總部策畫的炸彈陰謀失敗之後接掌了後備軍的指揮權。而似乎完全掌控了大後方的戈培爾,則被任命為帝國全權代表(Reich Plenipotentiary),負責發動「全面戰爭」(Total War Effort)。但鮑曼和各地省長仍能破壞戈培爾的計劃,以便掌控自己的地盤。
儘管絕大多數德國百姓對刺殺希特勒的行動深感震驚,但隨著蘇聯大軍進逼東普魯士邊界,全國人民的士氣迅速瓦解。女人尤其希望結束戰爭,正如黨衛軍祕密警察彙報的,許多人已對元首失去信心。觀察力敏銳的人發現,只要元首還活著,就不可能有結束戰爭的一天。
儘管(或許也正因為)夏天的奏捷,盟軍高層將領之間的明爭暗鬥開始浮出檯面。艾森豪──正如一位觀察家所言,是一名「軍事政治家而非軍閥頭子」──試圖維持和諧,但讓布萊德雷氣憤而巴頓輕蔑的是,他似乎一心一意討好蒙哥馬利和英國。始於八月十九日的那場爭論,點燃了盟軍內部從一九四四年下半直至新的一年間的緊張衝突。
蒙哥馬利要求把將近全數的盟軍兵力納入他的指揮,由他率領大軍穿越比利時與荷蘭,進入德國的魯爾(Ruhr)工業區。提議被拒之後,他希望他自己的第二十一集團軍在考特尼.霍奇斯將軍(Courtney Hodges)的第一軍團支援下,仍然循這條路線進攻。盟軍將能因此奪下轟炸倫敦的V型飛彈發射場,並占領對日後軍需供應至關緊要的安特衛普(Antwerp)深水港。布萊德雷及其麾下的兩位陸軍司令──巴頓和霍奇斯──同意占領安特衛普的必要性,但他們希望往東取道薩爾(Saar);那是進入德國的最短路徑。幾位美軍將領認為己方在眼鏡蛇行動(Operation Cobra)的成功,以及巴頓的第三軍團帶領盟軍一口氣攻到塞納河的戰功,應該讓他們享有優先配給權。然而,艾森豪深知單一的強勢進攻──不論由北方的英軍或中路的美軍率領──都會引發更甚於軍事風險的政治危機。假如自己國家的軍隊由於補給問題而暫停行動,另一個國家的軍隊卻能繼續挺進,不論美國或英國媒體都會爆發憤慨的指責聲浪。
九月一日,延宕多時的布萊德雷調任案終於公布。嚴格來說,他原本是蒙哥馬利的下屬,此刻將接任美國第十二集團軍司令。消息一出,英國媒體再度一片譁然。艦隊街把這項改組視為對蒙哥馬利的打壓,因為如今艾森豪坐鎮法國,蒙哥馬利不再是地面部隊的最高指揮官。倫敦早就預見問題,為了平息事態,蒙哥馬利被晉升為陸軍元帥(此舉理論上讓他的位階壓過只有四星的艾森豪)。巴頓當天早上聆聽廣播,聽到「艾克說蒙弟是當今最偉大的軍人,晉升元帥當之無愧」時,心裡很不舒服。廣播完全沒提到其他人的成就。翌日在布萊德雷的總部開完會之後,曾率軍橫掃法國的巴頓說:「對於我們的功勞,艾克沒有向我們任何一人表達謝意或祝賀。」兩天後,他的第三軍團抵達默茲河(River Meuse)河畔。
無論如何,美國第一軍團偕同英國第二軍團以迅雷之勢深入比利時,事後證明是整場戰爭最快速的一次行動。倘若不是沿途在每一個比利時鄉鎮受到當地居民狂熱歡迎而耽擱了時間,行動還可以更迅速。第三十軍軍長布萊恩.何洛克斯中將(Brian Horrocks)評論:「在香檳、鮮花、民眾和趴在無線電通訊車車頂的女孩簇擁之下,實在很難繼續作戰。」美軍也發現他們在比利時受到的歡迎與熱情,遠勝過在法國得到的待遇。九月三日,英軍近衛裝甲師進入比利時,受到空前的熱烈歡迎,街頭巷尾一片歡騰,熱鬧滾滾。
隔天,「好手」羅伯茲少將(‘Pip’ Roberts)的第十一裝甲師以一次非凡的突襲行動攻進安特衛普。透過比利時反抗軍(Belgian Resistance)協助,他們搶在德軍摧毀設備之前占領了港口。第一五九步兵旅攻擊德軍設在公園的總部,到了晚上八點,德軍駐防指揮官宣布投降,他的六千名弟兄被押解到動物園,關進一座空的獸欄;裡頭的動物早被饑民搶著吃光了。「俘虜坐在乾草上,」瑪莎.蓋爾霍恩(Martha Gellhorn)描述,「透過柵欄向外凝望。」安特衛普的淪陷震驚了元首總部。「你們才剛剛勉強過了索姆河,」砲兵中將華特.瓦利蒙特(Walter Warlimont)隔年對盟軍審訊人員承認,「然後突然之間,你們的一兩個裝甲師殺到了安特衛普門口。我們沒料到你們能這樣長驅直入,毫無防備。消息傳來的時候,我們大感震驚。」
美國第一軍團也迅速行動,設法攔截撤離的德軍。第二裝甲師偵察營遠遠走在其他部隊前頭,摸清了敵軍的撤退路線。剛剛入夜之後,他們便在村莊或城鎮完成輕型坦克的埋伏。「我們等到敵軍車隊進入最有效的射程才開火。輕型坦克負責把擊毀的車輛拖到城裡的建築物之間藏好,免得被後來的車隊發現。行動持續了一整夜。」一名美軍坦克指揮官估計,八月十八日到九月五日之間,他的戰車行進了五百六十三英里,「幾乎完全沒停下來維修保養。」
布萊德雷的部隊在法國與比利時邊界使用鉗形戰術,大軍於芒斯(Mons)附近會合,取得了更甚於英軍的勝利。德軍三個裝甲師的機動部隊在美國第一步兵師完成合圍之前設法逃了出來。第三及第六空降獵兵師(Fallschirmjäger-Division)的傘兵憤憤不平,武裝黨衛軍再度只求自保,完全不顧其他人死活。美軍困住了來自諾曼第的六個師的殘餘部隊,總計超過兩萬五千人。這些人若不投降,就只能等死。第九步兵師的砲兵彙報情況:「我們的一五五毫米砲直接對準敵軍縱隊開火,造成慘重傷亡,最後擄獲六千一百名戰俘,包括三位將軍。」
比利時反抗軍在芒斯包圍戰的攻擊行動,揭開了德軍一連串報復的序幕。六十個平民喪生,許多房屋付之一炬。在最後的清剿階段,來自比利時民族運動(Mouvement National Belge)、獨立陣線(Front de l’Indépendance)及白衣部隊(Armée Blanche)的地下軍事力量跟美軍密切合作。德國軍事指揮部又氣又怕,擔心德軍穿越比利時、朝西牆(Westwall;也就是盟軍口中的「齊格菲防線」〔Siegfried Line〕)撤離的路上,會遭遇大規模起義。比利時年輕人群起攻擊,引發了嚴重後果;不僅當下如此,當十二月的阿登戰役帶回渴望報復的德國軍隊,情況更是不堪設想。
九月一日,在阿登北部地區羅什福爾(Rochefort)附近的熱梅勒(Jemelle),莫里斯.狄凡尼(Maurice Delvenne)心滿意足地看著德軍撤離比利時。「德軍撤退的腳步似乎逐漸加快,而且越來越漫無章法,」他在日記中寫道,「工兵、步兵、海軍、空軍和砲兵擠在同一輛卡車上,所有人顯然剛從戰區回來。他們又髒又憔悴,最關心的莫過於離家鄉還有幾公里遠,而無可厚非的,我們誇大距離捉弄他們,暗自開心。」
兩天後,黨衛軍部隊通過了熱梅勒,有些人頭上纏著繃帶。「他們表情嚴峻,對人投以仇恨的目光。」他們對所經之地極盡破壞:焚毀建築物、扯斷電話線、驅趕掠奪來的羊群和牛群。住在阿登東部德語區的農民,被命令帶著家人和牲口搬到齊格菲防線後方,遷入第三帝國境內。光是盟軍的轟炸消息便足以讓他們裹足不前,更何況絕大多數人壓根不想離開自己的農地,於是他們帶著牲口躲入樹林,直到德軍消失蹤影。
九月五日,年輕反抗軍的事蹟惹怒了撤退的德軍,引發德軍焚毀N4公路從馬爾什昂法梅訥(Marche-en-Famenne)到巴斯通(Bastogne)路段旁的三十五棟民宅,就在邦德村(Bande)附近。等到德軍在耶誕節前夕因為阿登突襲行動而折返時,更慘的情況還在後頭。反抗軍攻擊行動激起的報復,讓一般老百姓人心惶惶。九月六日,德軍為了兩天前的攻擊在比松維爾(Buissonville)展開報復,縱火燒掉當地及鄰村的二十二間房屋。
在德軍的撤退路線上,沿途各個村落和城鎮的居民紛紛插上比利時、英國和美國國旗來歡迎他們的解放者。有時候,當另一支潰逃的德軍小隊在大街上現身,他們得手忙腳亂藏好這些旗幟。據德軍駐守荷蘭烏特勒支的福爾里德中校描述:「一群可悲的荷蘭國家社會主義人士(Dutch National Socialist)撤往德國,逃離憤怒的荷蘭人民。其中有許多婦女及兒童。」這群荷蘭納粹黨徒在比利時邊境的埃赫特爾(Hechtel)遭遇戰鬥,最後游過運河才逃出包圍,但是「有損英軍名聲的是──投降的受傷官兵絕大多數遭比利時人槍殺(英軍顯然袖手旁觀)」。歷經四年的占領期,荷蘭人和比利時人都對德國充滿怨恨。
德軍在比利時與荷蘭的陣線似乎完全潰堤。後方的混亂局面中隱含著恐慌,使得德國第八十九軍在作戰日誌中寫道:「一個愧對德國軍隊、讓德軍蒙羞的畫面。」憲兵懲戒大隊(Feldjäger Streifengruppen)抓捕脫隊的散兵,帶回集運中心,然後由軍官押送到前線,通常每批六十人。在列日(Liège)附近,大約一千名士兵在軍官的槍口下走上前線。有逃兵嫌疑的人必須接受軍法審判,一旦定罪,將被判處死刑或送往緩刑營(事實上更像懲戒營)。俯首認罪或換上平民服裝的逃兵,則會被當場處決。
每一名憲兵都配戴印有「OKW憲兵」的紅色臂章,並持有特殊證件,上頭的綠色對角線上寫著:「如有不從,有權使用武器。」德國憲兵被強力洗腦;教官每星期給他們上一次課,教導他們:「世界局勢、德國的堅不可摧、元首絕不會犯錯,以及有助於智取敵人的地下工廠。」
瓦爾特.莫德爾元帥(Walter Model)呼籲西線部隊堅守崗位、為元首爭取時間,但他「對西線戰士的籲請」並未受到重視。軍方採取了最激烈的手段。凱特爾元帥在九月二日下令,「凡裝病或偷懶的懦夫,包括軍官在內」,一律立刻處決。莫德爾警告,如果要阻擋敵軍攻進德國北部,他最少需要十個步兵師和五個裝甲師。然而德國並沒有如此大規模的可用之兵。
在北部,拜加拿大軍隊延遲追擊之賜,德軍在海峽沿岸的撤退行動顯得有秩序多了。古斯塔夫.燦根步兵中將(Gustav von Zangen)率領第十五軍團,井然有序地從加萊海峽省撤到比利時北部。當盟軍情報單位表示,「目前已知即將抵達荷蘭的唯一增援兵力,是取道荷蘭各島逃離比利時的第十五軍團殘部;他們軍心潰散,漫無組織」,情報顯然嚴重錯誤。
盟軍突然奪下安特衛普,或許曾給予德軍高層強力的打擊,但接下來幾天,由於英軍遲遲無法攻克須耳德河(Scheldt)出海口北岸,燦根將軍得以設立了防線,包括須耳德河口南岸一道稱為「布萊茲肯斯口袋」(Breskens pocket)的二十公里寬的防禦工事、北岸的南貝弗蘭(South Beveland)半島,以及瓦爾赫倫島(Walcheren)。他的部隊很快召集八萬兩千名士兵,部署五百三十座砲台,阻擋英國皇家海軍渡過水雷和地雷密布的出海口。
盟軍海軍總司令貝特倫.拉姆齊上將(Bertram Ramsay)曾提醒SHAEF和蒙哥馬利,德軍有可能輕而易舉封鎖須耳德河出海口。第一海務大臣──海軍上將安德魯.康寧漢爵士(Andrew Cunningham)也曾警告,除非打通通道,否則安特衛普「對我們的用處,跟廷巴克圖(Timbuctoo)沒什麼兩樣」。陸軍指揮官何洛克斯將軍後來自承失敗的責任。「拿破崙無疑能洞悉問題,」他寫道,「但何洛克斯恐怕無能為力。」然而,那不是何洛克斯的錯,也不是第十一裝甲師指揮官羅伯茲將軍的錯。問題出在對河口興趣缺缺、以為加拿大軍隊可以稍後清除障礙的蒙哥馬利。
那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導致盟軍日後遭受嚴重打擊。但在那個歡欣鼓舞的時期,曾經參與一次世界大戰的將領深信一九四四年九月是一九一八年九月的翻版。「報紙上刊登盟軍六天內挺進兩百一十英里的消息,指出荷蘭、盧森堡、薩爾布魯根(Saarbrücken)、布魯塞爾和安特衛普都已落入同盟國手中,」戰爭歷史學家佛瑞斯特.波格(Forrest Pogue)寫道,「各個陣線傳來的戰情預估,幾乎全都樂觀得昏了頭。」高階將領將目光鎖定萊茵河,心裡想著盟軍可以一舉過河。艾森豪無疑沉醉於如此幻想,而蒙哥馬利基於自己的原因,也越來越執迷於這個美夢。
1. 勝利熱潮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晨,艾森豪將軍從沙特爾(Chartres)啟程,準備看看剛解放的巴黎。「今天是星期天,」盟軍最高司令告訴隨行的布萊德雷將軍(Omar Bradley),「所有人都會賴床,我們此行可以不驚動任何人。」然而,當兩位將軍在這趟所謂的「非正式參訪」朝法國首都風馳電掣行進時,他們的行動很難不引人注目。最高司令的草綠色凱迪拉克由兩輛裝甲車護送,另有一名准將坐鎮吉普車負責前導。
當他們抵達奧爾良門,第三十八騎兵偵察中隊已在傑羅少將(Lenoard Gerow)的指揮下呈檢閱隊形恭候大駕,形成了更盛大的護...
目錄
軍事標誌圖例
詞彙表
1. 勝利熱潮
2. 安特衛普與德國邊境
3. 亞琛戰役
4. 戰爭進入冬天
5. 許特根森林
6. 德軍準備出擊
7. 情報失靈
8.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9.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天
10.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
11. 斯科爾茲尼與海特
12.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二
13.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14.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15.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16.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17.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天
18. 耶誕節
19.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20. 盟軍準備反攻
21. 雙重奇襲
22. 反攻
23. 剷平突出部
24. 結語
註釋
參考書目
致謝
照片出處
軍事標誌圖例
詞彙表
1. 勝利熱潮
2. 安特衛普與德國邊境
3. 亞琛戰役
4. 戰爭進入冬天
5. 許特根森林
6. 德軍準備出擊
7. 情報失靈
8. 十二月十六日星期六
9. 十二月十七日星期天
10. 十二月十八日星期一
11. 斯科爾茲尼與海特
12. 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二
13.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三
14. 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
15. 十二月二十二日星期五
16. 十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
17. 十二月二十四日星期天
18. 耶誕節
19. 十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20. 盟軍準備反攻
21. 雙重奇襲
22. 反攻
23. 剷平突出部
24. 結語
註釋
參考書...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5收藏
5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5收藏
5收藏

 22二手徵求有驚喜
2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