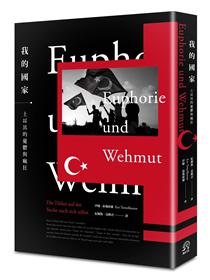張愛玲:《海上花》是最好的寫實的作品。
我常常替它不平,總覺得它應當是世界名著。
海派傳人筆下的海派傳奇,影響張愛玲創作最深的作品!
導演大師侯孝賢改編拍成電影,榮獲金馬獎評審團大獎!
張愛玲
百歲誕辰
紀念版
樸齋心裏熱得像熾炭一般,
卻關礙著小村,不敢動手,只目不轉睛的呆看;
見她雪白的面孔,漆黑的眉毛,亮晶晶的眼睛,血滴滴的嘴唇,
越看越愛,越愛越看。
清末的上海,是金錢與情欲交織的魔都,在租界一隅的娼館「長三書寓」裡上演的諸般情節,看似光怪陸離,其實都是浮世眾生相的隱喻。男人們留戀這裡的萬種風情,女人們沉溺那處的虛情假意,彼此各懷鬼胎,緣起緣滅,終究沉淪。張愛玲以精準的文字完美還原清代才子韓子雲的吳語章回小說《海上花列傳》,更針對原作中的晚清服飾和風俗文化做了詳盡的詮釋。本書不僅是張愛玲對於近代文學史的重大貢獻,更是一代經典傑作的浴火重生。
作者簡介:
張愛玲
本名張煐,一九二○年生於上海。二十歲時便以一系列小說令文壇為之驚豔。她的作品主要以上海、南京和香港為故事場景,在荒涼的氛圍中鋪張男女的感情糾葛以及時代的繁華和傾頹。
有人說張愛玲是當代的曹雪芹,文學評論權威夏志清教授更將她的作品與魯迅、茅盾等大師等量齊觀,而日後許多作家都不諱言受到「張派」文風的深刻影響。
張愛玲晚年獨居美國洛杉磯,深居簡出的生活更增添她的神秘色彩,但研究張愛玲的風潮從未止息,並不斷有知名導演取材其作品,李安改拍〈色,戒〉,更是轟動各界的代表佳作。
一九九五年九月張愛玲逝於洛杉磯公寓,享年七十四歲。她的友人依照她的遺願,在她生日那天將她的骨灰撒在太平洋,結束了她傳奇的一生。
章節試閱
第一回
趙樸齋 鹹瓜街訪舅
洪善卿 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說部書係花也憐儂所著,名曰海上花列傳。只因海上自通商以來,南部煙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傾覆流離於狎邪者,不知凡幾。雖有父兄,禁之不可;雖有師友,諫之不從。此豈其冥頑不靈哉?獨不得一過來人為之現身說法耳。方其目挑心許,百樣綢繆,當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經描摹出來,便覺令人欲嘔,其有不爽然若失,廢然自返者乎?花也憐儂具菩提心,運廣長舌,寫照傳神,屬辭此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卻絕無半個淫褻穢污字樣,蓋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云。茍閱者按跡尋踪,心通其意,見當前之媚於西子,即可知背後之潑於夜叉;見今日之密於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於蛇蝎:也算得是欲覺晨鐘,發人深省者矣。此海上花列傳之所以作也。
看官,你道這花也憐儂究是何等樣人?原來古槐安國之北有黑甜鄉,其主者曰趾離氏,嘗仕為天祿大夫,晉封醴泉郡公,乃流寓於眾香國之溫柔鄉,而自號花也憐儂云。所以花也憐儂,實是黑甜鄉主人,日日在夢中過活,自己偏不信是夢,只當真的作起書來;及至捏造了這一部夢中之書,然後喚醒了那一場書中之夢。看官啊,你不要只在那裏做夢,且看看這書,倒也不錯。
這書即從花也憐儂一夢而起;也不知花也憐儂如何到了夢中,只覺得自己身子飄飄蕩蕩,把握不定,好似雲催霧趕的滾了去,舉首一望,已不在本原之地了,前後左右,尋不出一條道路,竟是一大片浩淼蒼茫無邊無際的花海。
看官須知道,「花海」二字非是杜撰的,只因這海本來沒有什麼水,只有無數花朵,連枝帶葉,漂在海面上,又平勻,又綿軟,渾如繡茵錦罽一般,竟把海水都蓋住了。
花也憐儂只見花,不見水,喜得手舞足蹈起來,並不去理會這海的闊若干頃,深若干尋,還當在平地上似的,躑躅留連,不忍舍去。不料那花雖然枝葉扶疎,卻都是沒有根蒂的,花底下即是海水,被海水沖激起來,那花也只得隨波逐流,聽其所止。若不是遇著了蝶浪蜂狂,鶯欺燕妒,就為那蚱蜢蜣螂蝦蟆螻蟻之屬,一味的披猖折辱,狼藉蹂躪。惟夭如桃,穠如李,富貴如牡丹,猶能砥柱中流,為群芳吐氣;至於菊之秀逸,梅之孤高,蘭之空山自芳,蓮之出水不染,哪裏禁得起一些委屈,早已沉淪汩沒於其間!
花也憐儂見此光景,輒有所感,又不禁愴然悲之。這一喜一悲也不打緊,只反害了自己,更覺得心慌意亂,目眩神搖;又被罡風一吹,身子越發亂撞亂磕的,登時闖空了一腳,便從那花縫裏陷溺下去,竟跌在花海中了。
花也憐儂大叫一聲,待要掙扎,早已一落千丈,直墜至地,卻正墜在一處,睜眼看時,乃是上海地面,華洋交界的陸家石橋。
花也憐儂揉揉眼睛,立定了腳跟,方記今日是二月十二日;大清早起,從家裏出門,走了錯路,混入花海裏面,翻了一個筋斗,幸虧這一跌倒跌醒了;回想適纔多少情事,歷歷在目,自覺好笑道:「竟做了一場大夢!」嘆息怪詫了一回。
看官,你道這花也憐儂究竟醒了不曾?請各位猜一猜這啞謎兒如何?但在花也憐儂自己以為是醒的了,想要回家裏去,不知從那一頭走,模模糊糊,踅下橋來。剛至橋堍,突然有一個後生,穿 著月白竹布箭衣,金醬甯綢馬褂,從橋下直衝上來。花也憐儂讓避不及,對面一撞,那後生撲塌地跌了一交,跌得滿身淋漓的泥漿水。那後生一骨碌爬起來拉住花也憐儂亂嚷亂罵,花也憐儂向他分說,也不聽見。當時有青布號衣中國巡捕過來查問。後生道:「我叫趙樸齋,要到鹹瓜街去。哪曉得這冒失鬼跑來撞我跌一交!你看我馬褂上爛泥!要他賠的!」
花也憐儂正要回言,只見巡捕道:「你自己也不小心嚜。放他去罷。」趙樸齋還咕噥了兩句,沒奈何,放開手,眼睜睜地看著花也憐儂揚長自去。看的人擠滿了路口,有說的,有笑得。趙樸齋抖抖衣襟,發急道:「教我怎樣去見我舅舅呃?」巡捕也笑起來道:「你到茶館裏拿手巾來揩揩b。1」
一句提醒了趙樸齋,即在橋堍近水台茶館佔著個靠街的座兒,脫下馬褂,等到堂倌舀面水來,樸齋絞把手巾,細細的擦那馬褂,擦得沒一些痕跡,方才穿上,呷一口茶,會賬起身,逕至鹹瓜街中巿,尋見永昌參店招牌,踱進石庫門,高聲問洪善卿先生。有小夥計答應,邀進客堂,問明姓字,忙去通報。
不多時,洪善卿匆匆出來。趙樸齋雖也久別,見他削骨臉,爆眼睛,卻還認得,趨步上前,口稱「舅舅」,行下禮去。洪善卿還禮不迭,請起上坐,隨問:「令堂可好?有沒一塊來?寓在哪裏?」樸齋道:「小寓寶善街 悅來客棧。媽沒來,說給舅舅請安。」
說著,小夥計送上煙茶二事。洪善卿問及來意。樸齋道:「也沒什麼事,要想找點生意做做。」善卿道:「近來上海灘上倒也沒什麼生意好做b。」樸齋道:「因為媽說,人嚜一年大一年了,在家裏幹什麼?還是出來做做生意罷。」善卿道:「話也不錯。你今年十幾歲?」樸齋說:「十七。」善卿道:「你還有個令妹,也好幾年不見了,比你小幾歲?有沒定親?」樸齋說:「沒有;今年也十五歲了。」善卿道:「家裏還有什麼人?」樸齋道:「不過三個人,用個娘姨。」善卿道:「人少,開消到底也有限。」樸齋道:「比起從前省得多了。」
說話時,只聽得天然几上自鳴鐘連敲了十二下,善卿即留樸齋便飯,叫小夥計來說了。
須臾,搬上四盤兩碗,還有一壺酒,甥舅兩人,對坐同飲,絮語些近年景況,閒談些鄉下情形。善卿又道:「你一個人住在客棧裏,沒有照應嚜?」樸齋道:「有個米行裏朋友,叫張小村,也到上海來找生意,一塊住著。」善卿道:「那也罷了。」喫過了飯,揩面漱口。善卿將水煙筒授與樸齋道:「你坐一會,等我幹掉點小事,跟你一塊北頭2去。」樸齋唯唯聽命。善卿仍匆匆的進去了。
樸齋獨自坐著,把水煙吸了個不耐煩,直敲過兩點鐘,方見善卿出來,又叫小夥計來叮囑了幾句,然後一同出去到寶善街 悅來客棧。房中先有一人躺著吸煙。善卿略一招呼,便問:「閣下想是小村先生?」小村說道:「正是。老伯可是善卿先生?」善卿道:「豈敢,豈敢。」小村道:「沒過來奉候,抱歉之至。」
謙遜一回,對面坐定。趙樸齋取一支水煙筒送上善卿。善卿道:「舍甥初次到上海,全仗大力照應照應。」小村道:「小姪也不懂什麼事,一塊出來嚜,自然大家照應點。」又談了些客套,善卿把水煙筒送過來,小村一手接著,一手讓去床上吸鴉片煙。善卿說:「不會喫。」仍各坐下。
樸齋坐在一邊,聽他們說話,慢慢的說到堂子倌人。樸齋正要開口問問,恰好小村送過水煙筒,樸齋趁勢向小村耳邊說了幾句。小村先哈哈一笑,然後向善卿道:「樸兄說要到堂子裏見識見識,好不好?」善卿道:「到哪去b?」小村道:「還是棋盤街上去走走罷。」善卿道:「我記得西棋盤街 聚秀堂裏有個倌人,叫陸秀寶,倒還不錯。」樸齋插嘴道:「那這就去囉。」小村只是笑。善卿不覺也笑了。
樸齋催小村收拾起煙盤,又等他換了一副簇新行頭,頭戴瓜棱小帽,腳登京式鑲鞋,身穿銀灰杭紡棉袍,外罩寶藍甯綢馬褂,再把脫下的衣裳,一件件都摺疊起來,方纔與善卿相讓同行。
樸齋正自性急,拽上房門,隨手鎖了,跟著善卿 小村出了客棧。轉兩個彎,已到西棋盤街,望見一盞八角玻璃燈,從鐵管撐起在大門首,上寫「聚秀堂」三個朱字。善卿引小村 樸齋進去。外場認得善卿,忙喊:「楊家媽,莊大少爺朋友來。」只聽得樓上答應一聲,便登登登一路腳聲到樓門口迎接。
三人上樓,那娘姨楊家媽見了道:「噢,洪大少爺,房裏請坐。」一個十三四歲的大姐3,早打起簾子等候。不料房間裏先有一人橫躺在榻床上,摟著個倌人,正戲笑哩;見洪善卿進房,方丟下倌人,起身招呼,向張小村 趙樸齋也拱一拱手,隨問尊姓。洪善卿代答了,又轉身向張小村道:「這位是莊荔甫先生。」小村說聲「久仰」。
那倌人掩在莊荔甫背後,等坐定了,纔上前來敬瓜子。大姐也拿水煙筒來裝水煙。莊荔甫向洪善卿道:「正要來找你,有好些東西,你看看,可有什麼人作成。」即去身邊摸出個摺子,授與洪善卿。善卿打開看時,上面開列的,或是珍寶,或是古董,或是書畫,或是衣服,底下角明價值號碼。善卿皺眉道:「這種東西,消場倒難b。聽見說杭州 黎篆鴻在這裏,可要去問他一聲看?」莊荔甫道:「黎篆鴻那兒,我教陳小雲拿了去了,沒有回信。」善卿道:「東西在哪裏?」荔甫道:「就在宏壽書坊裏樓上。可要去看看?」善卿道:「我是外行,看什麼b。」
趙樸齋聽這等說話,好不耐煩,自別轉頭,細細的打量那倌人:一張雪白的圓面孔,五官端正,七竅玲瓏;最可愛的是一點朱唇,時時含笑,一雙俏眼,處處生情;見她家常只戴得一支銀絲蝴蝶,穿一件東方亮竹布衫,罩一件元色縐心緞鑲馬甲,下束膏荷縐心月白緞鑲三道繡織花邊的袴子。
樸齋看得出神,早被那倌人覺著,笑了一笑,慢慢走到靠壁大洋鏡前,左右端詳,掠掠鬢腳。樸齋忘其所以,眼光也跟了過去。忽聽洪善卿叫道:「秀林小姐,我替你秀寶妹子做個媒人好不好?」樸齋方知那倌人是陸秀林,不是陸秀寶。只見陸秀林回頭答道:「照應我妹子,有什麼不好!」即高聲叫楊家媽。正值楊家媽來絞手巾,沖茶碗。陸秀林便叫她喊秀寶上來加茶碗。楊家媽問:「哪一位呀?」洪善卿伸手指著樸齋,說是「趙大少爺。」楊家媽眱了兩眼道:「可是這位趙大少爺?我去喊秀寶來。」接了手巾,忙登登登跑了去。
不多時,一路咭咭咯咯小腳聲音,知道是陸秀寶來了,趙樸齋眼望著簾子,見陸秀寶一進房間,先取瓜子碟子,從莊大少爺 洪大少爺4挨順敬去;敬到張小村 趙樸齋兩位,問了尊姓,卻向樸齋微微一笑。樸齋看陸秀寶也是個小圓面孔,同陸秀林一模一樣,但比秀林年紀輕些,身材短些,若不是同在一處,竟認不清楚。
陸秀寶放下碟子,挨著趙樸齋肩膀坐下。樸齋倒有些不好意思的,左不是,右不是,坐又坐不定,走又走不開。幸虧楊家媽又跑來說:「趙大少爺,房間裏去。」陸秀寶道:「一塊請過去囉。」大家聽說,都立起來相讓。莊荔甫道:「我來引導。」正要先走,被陸秀林一把拉住袖口,說道:「你不要去b。讓他們去好了。」
洪善卿回頭一笑,隨同張小村 趙樸齋跟著楊家媽走過陸秀寶房間裏,就在陸秀林房間的間壁,一切鋪設裝潢不相上下,也有著衣鏡,也有自鳴鐘,也有泥金箋對,也有彩畫絹燈,大家隨意散坐。楊家媽又亂著加茶碗,又叫大姐裝水煙。接著外場5送進乾濕6來。陸秀寶一手托了,又敬一遍,仍來和趙樸齋並坐。
楊家媽在一旁問洪善卿道:「趙大少爺公館在哪呀?」善卿道:「他跟張大少爺一塊在悅來客棧。」楊家媽轉問張小村道:「張大少爺可有相好啊?」小村微笑搖頭。楊家媽道:「張大少爺沒有相好嚜,也攀一個囉。」小村道:「是不是你教我攀相好?我就攀你嚜囉。好不好?」說得大家鬨然一笑。楊家媽笑了,又道:「攀了相好嚜,跟趙大少爺一塊走走,不是熱鬧點?」小村冷笑不答,自去榻床躺下吸煙。楊家媽向趙樸齋道:「趙大少爺,你來做個媒人罷。」樸齋正和陸秀寶鬼混,裝做不聽見,秀寶奪過手說道:「教你做媒人,怎麼不作聲哪?」樸齋仍不語。秀寶催道:「你說說b。」樸齋沒法,看看張小村面色要說。小村只管吸煙,不理他。
正在為難,恰好莊荔甫掀簾進房,趙樸齋借勢起身讓坐。楊家媽見沒意思,方同大姐出去了。
莊荔甫對著洪善卿坐下,講論些生意場中情事。張小村仍躺下吸煙。陸秀寶兩隻手按住趙樸齋的手,不許動,只和樸齋說閒話,一回說要看戲,一回說要喫酒。樸齋嘻著嘴笑。秀寶索性擱起腳來,滾在懷裏。樸齋騰出一手,伸進秀寶袖子裏去。秀寶掩緊胸脯,發急道:「不要b!」
張小村正吸完兩口煙,笑道:「你放著『水餃子』不喫,倒要喫『饅頭』!」樸齋不懂,問小村道:「你說什麼?」秀寶忙放下腳,拉樸齋道:「你不要去聽他!他在拿你開心哦!」復眱著張小村,把嘴披下來道:「你相好嚜不攀,說倒會說得很呢!」一句說得張小村沒趣起來,訕訕的起身去看鐘。
洪善卿覺小村意思要走,也立起來道:「我們一塊喫晚飯去。」趙樸齋聽說,慌忙摸塊洋錢丟在乾濕碟子裏。陸秀寶見了道:「再坐會b。」一面喊秀林:「姐姐,要走了。」陸秀林也跑過這邊來,低聲和莊荔甫說了些什麼,纔同陸秀寶送至樓門口,都說:「等會一塊來。」四人答應下樓。
1‧原文作「c」。作者在「例言」中云「c」音「眼」,當是吳語「眼」字,額顏切,近代口音變化為「b」,亦即本世紀二○、三○年間吳語小說中的「d」字,含有不耐煩催促之意,兼用作加強的問號或驚嘆號,可能帶氣憤或無可奈何的口吻,為吳語最常用的語助詞之一,里巷中母親喚孩子,一片「來b!」「去b!」聲。普通白話沒有可代用的字眼,只好保存原音。
2‧上海租界和閘北叫北頭,城內及南巿──華界──叫南頭。
3‧未婚女傭。
4‧二等妓院客人不分老少一律稱大少爺。
5‧妓院男僕。
6‧桂圓等乾菓與菓脯。
第一回
趙樸齋 鹹瓜街訪舅
洪善卿 聚秀堂做媒
按此一大說部書係花也憐儂所著,名曰海上花列傳。只因海上自通商以來,南部煙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傾覆流離於狎邪者,不知凡幾。雖有父兄,禁之不可;雖有師友,諫之不從。此豈其冥頑不靈哉?獨不得一過來人為之現身說法耳。方其目挑心許,百樣綢繆,當局者津津乎若有味焉;一經描摹出來,便覺令人欲嘔,其有不爽然若失,廢然自返者乎?花也憐儂具菩提心,運廣長舌,寫照傳神,屬辭此事,點綴渲染,躍躍如生,卻絕無半個淫褻穢污字樣,蓋總不離警覺提撕之旨云。茍閱者按跡尋踪,心...
作者序
譯者識
張愛玲
半世紀前,胡適先生為《海上花》作序,稱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滄海桑田,當時盛行的寫妓院的吳語小說早已跟著較廣義的「社會小說」過時了,絕跡前也並沒有第二部傑作出現。「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不如說是方言文學的第一部傑作,既然粵語閩南語文學還是生氣蓬勃,閩南語的尤其前途廣闊,因為外省人養成欣賞力的更多。
自《九尾龜》以來,吳語小說其實都是夾蘇白,或是妓女說蘇白,嫖客說官話,一般人比較容易懂。全部吳語對白,《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後的一個,沒人敢再蹈覆轍──如果知道有這本書的話。《海上花》在十九世紀末出版;民初倒已經湮滅了。一九二○年蔣瑞藻著《小說考證》,引《譚瀛室筆記》,說《海上花列傳》作者「花也憐儂」是松江韓子雲。一九二二年清華書局翻印《海上花》,許菫父序中說︰「或曰松江韓太癡所著也。」三年後胡適另托朋友在松江同鄉中打聽,發現孫玉聲(海上漱石生)曾經認識韓子雲,但是也不知道他的底細,輾轉代問小時報專欄作家「松江顛公」(大概是雷瑨,字君曜),答覆是《小時報》上一篇長文關於韓邦慶(字子雲),這才有了些可靠的傳記資料。胡適算出生卒年。一八九四年《海上花》出單行本,同年作者逝世,才三十九歲。
一九二六年亞東書局出版的標點本《海上花》有胡適、劉半農序。現在僅存的亞東本,海外幾家大學圖書館收藏的都算是稀有的珍本了。清華書局出的想必絕版得更早,曇花一現。迄今很少人知道。我等於做打撈工作,把書中吳語翻譯出來,像譯外文一樣,難免有些地方失去語氣的神韻,但是希望至少替大眾保存了這本書。
胡適指出此書當初滯銷不是完全因為用吳語。但是到了二○、三○年間,看小說的態度不同了,而經胡適發掘出來,與劉半農合力推薦的結果,怎麼還是一部失落的傑作?關於這一點,我的感想很多,等這國語本連載完了再談了,也免得提起內容,洩漏情節,破壞了故事的懸疑。
第三十八回前附記︰
亞東本劉半農序指出此書缺點在後半部大段平舖直敘寫名園名士──內中高亞白文武雙全,還精通醫道,簡直有點像《野叟曝言》的文素臣──借此把作者「自己以為得意」的一些詩詞與文言小說插入書中。我覺得尤其是幾個「四書酒令」是卡住現代讀者的一個瓶頸──過去讀書人《四書》全都滾瓜爛熟,這種文字遊戲的趣味不幸是有時間性的,而又不像《紅樓夢》裏的酒令表達個性,有的還預言各人命運。
所以《海上花》連載到中途,還是不得不照原先的譯書計劃,為了尊重原著放棄了的︰刪掉四回,用最低限度的改寫補綴起來,成為較緊湊的「六十回海上花」。回目沒動,除了第四十、四十一回兩回併一回,原來的回目是︰
縱翫賞七夕鵲填橋 善俳諧一言雕貫箭
衝繡閣惡語牽三劃1 佐瑤觴陳言別四聲
代擬為︰
渡銀河七夕續歡娛 衝繡閣一旦斷情誼
第五十、五十一回也是兩回併一回,回目本來是︰
軟廝纏有意捉訛頭2 惡打岔無端嘗毒手
胸中塊「穢史」寄牢騷3 眼下釘小蠻4爭寵眷
改為︰
軟裏硬太歲找碴 眼中釘小蠻爭寵
書中典故幸而有宋淇夫婦幫忙。本來還要多,多數在刪掉的四回內。好像他們還不夠忙,還要白忙!實在真對不起人。但是資料我都保留著,萬一這六十回本能成為普及本,甚至於引起研究的興趣,會再出完整的六十四回本,就還可以加註。
1‧即「三劃王」。
2‧流氓尋釁,捉出一個由頭,好訛人。
3‧書中高亞白與尹癡鴛打賭,要他根據一本春宮古畫冊寫篇故事,以包下最豪華的粵菜館請客作交換條件。尹癡鴛大概因為考場失意,也就借此發洩胸中塊壘。
4‧白居易詩︰「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寫擅歌舞的家妓。
譯者識
張愛玲
半世紀前,胡適先生為《海上花》作序,稱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滄海桑田,當時盛行的寫妓院的吳語小說早已跟著較廣義的「社會小說」過時了,絕跡前也並沒有第二部傑作出現。「吳語文學的第一部傑作」,不如說是方言文學的第一部傑作,既然粵語閩南語文學還是生氣蓬勃,閩南語的尤其前途廣闊,因為外省人養成欣賞力的更多。
自《九尾龜》以來,吳語小說其實都是夾蘇白,或是妓女說蘇白,嫖客說官話,一般人比較容易懂。全部吳語對白,《海上花》是...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7收藏
7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7收藏
7收藏

 11二手徵求有驚喜
11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