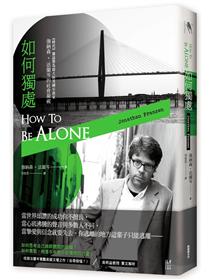令人嫉妒又擔憂的青春記事,
如鯨魚優游姿態潛入地底,
那些在地表上的謊言、傷害、真實、溫柔與陽光,
終將在呼吸吐納間浮出,繼續奔跑前行……
李欣倫/作家
言叔夏/作家
凌性傑/作家
蔣亞妮/作家
──好評推薦
她每年都買一本記事本,裡頭慘澹如忘了換水的水族箱,
日子可能突像快速滑落的坡道,可能像轉軸卡住的卡帶,
啃食著體內的生活感。
一場喪禮,是親情攻防角力,生命終段理應涼涼卻如此灼燒。
機械式吞下大量考試、公開排名、懲罰,再佐以「氣」的姿態吐出消化。
和友人在記憶海灘擱淺;或和聚集在交友網站、湖邊、地下道的各種邊緣人交換滿是窟窿的祕密。種種,似苦裡帶甜的咖啡。
作者以旋轉魔術方塊般之筆觸,重組同色塊卻分置不同區塊的文字;從自身路徑走入他人路徑,讓生活裡的槍、日子的燙,成為一道又一道擴散的漩渦。在畸形博物館、像谷底的U型小巷、漆黑街道,編織文字,收束情感,拼出無聲對抗,拼出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如何物換星移。
‧好評推薦
無論寫父親母親家族私史,還是寫校園、情感、關於日子與書寫的思索,光伴隨著影,影又佐著魍魎,三重意象,交織成敘事中不可承受之輕。我跟隨著閔淳,從白晝的人際往來,獨自走入夜晚,夜間散步、騎車與寫作。忽忽我想起閔淳碩士論文寫張愛玲。蒼涼張望中,雷電般的敘事裡,光與影與魍魎輪番幻化,相偕舞來。──李欣倫
這本書裡的文字如同沙漠中的夜雨,靜謐地流成一條沒有尾巴的河。河裡的陷落與淤積,自成作者心中一座遙遠的城池,是從許多此刻以外的他方折射而來的海市與蜃樓。即使沒有終點,它仍在沙中以它自身的流淌,做了一個關於沙漠的夢。──言叔夏
對許多散文創作者來說,最想寫、也最難寫的是家人,家庭的重量往往決定成長過程使否順遂。許閔淳深入挖掘記憶深處的礦場,正視迷離潮濕的過往,不虛張聲勢、不過於耽溺,展現了過人的敘述才華。這部散文集裡,許閔淳把貼身穿戴的感情記憶拿出來示人,這真需要莫大的勇氣。我尤其喜歡〈螢火蟲的光〉、〈所謂日子〉、〈一盞燈的明滅〉這些篇章的語氣,以及對細節的處理。因為有了無可替代的細節,散文才能顯現只屬於自己的獨特面目。──凌性傑
閔淳曾和我說過,她是一個喉輪空白的人,話少言疏。我一貫緊張地回以寥落字詞,卻有事物在閱讀她寫的字時,洶湧結成。世間如細沙,時間被糊化,日子黏膩冰冷,原來宇宙所有的繁華在她迷幻雙眼,不過冷涼爬蟲,走過深宵。當時,我就知道她的心結成了一個奇怪蟲蛹,有小小事物藏在裡頭,玲瓏小巧地以寫代說,字成象再成蛹繭,質地是絲線、皮層與浮沫,裡頭的夢與愛全是彩色的。如果你輕輕敲擊字蛹,會聽到不同的波長赫茲跳躍回應,像蜂鳥拍動翅膀、大海潮湧嘆息、巷道日落剝離,就是這本散文集發出的聲音。這些聲音,你聽不見,卻看得清。──蔣亞妮
‧封面設計的話
看完「地底下的鯨魚」作者的文字後,對於「鯨魚」有著不一樣的想法,我們生活在這個社會,面對各種不如預期的壓力,就像鯨魚生活在充滿氣壓的大海中,只不過我們比較像在地底下生活,只想低調且緩慢著度過每一天。而我們也有著如同「鯨魚遷徙」的本能,一直向著遠方尋找適合自己的生存方法,鯨魚的「換氣動作」,猶如我們在生活上的壓力宣洩,宣洩結束後,又會回到安靜的地底下漫遊著。因此在設計以呈現地底感覺為主,放上代表「壓力宣洩」的鯨魚換氣姿態,書衣挑選手感美術紙張增加觸覺感受,希望藉由實際觸摸書籍的方式,讓大家可以感受到生活的分量。(Akira Lai)
作者簡介:
許閔淳
1991年生,相信夢裡有真實,真實裡有夢。曾獲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學獎、打狗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東海文學獎、西子灣文學獎、中區寫作獎項、蕭毅虹文學獎學金等。
章節試閱
所謂日子
日子忽然被推入斜坡,如一顆小小的果核,在不斷的滾動中,先是黏上了塵埃,幾根被染得烏黑的羽毛纏上來,然後是暗沉的砂礫,接著是大量的損壞收音機般的嘈雜聲,交錯不停、慌亂的光和影。
我的日子,本是一顆小小果核,漫著美麗而天然紋路的日子,就這麼被一個斜坡包覆再包覆,最後它什麼也不是了,有時候我看見這團怪物停下來,我仔細的撫摸它、用不再靈敏的鼻子嗅嗅它、最後把它裝入我的眼中。「這裡已經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再捲進來囉!」我用很輕的聲調對我的日子說,它沒有說話,只是安靜的蜷縮起來,躲在我眼裡最柔軟的地方。
它用一雙清澈的、嬰孩般無辜的雙眼看著我,好像我是一個罪人。
我看著這團怪物,輕柔地擁抱著它,漸漸的習慣了它滾下坡道的規律,有時候,好像什麼都平穩了,我和這個滾動的規律似乎合而為一了,但當回頭看見這攤東西,發現我擁抱的根本什麼也不是,而這團怪物,是我一手將它推入斜坡的。
我內心的懷疑如烏雲般密布起來,這是我想要的日子嗎?日子被質疑得很無辜。我看著眼前以各樣形式的文字堆疊起來的一塚一塚的山丘,一股深深的無力感地震般搖晃著,但這些山丘沒有被震碎,沒有被夷平,依然神氣地站立著,像那些臉上不斷冒出的固執痘痘,我已經很久沒有長痘痘了,望著額頭上的痘痘,它們不速之客般地入侵我的額頭,H說:「就跟你說你還青春。」他躺在沙發上,不以為然。H常常盯著我,用一種感慨的聲音說:「唉年輕真好!」事實上他也沒有多老,但卻一直認為自己老了,他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我已經老得推不動日子了。」
這句話讓我想到宮崎駿的電影,女主角在得罪荒野女巫後,隔天起床在鏡中被自己衰老的容貌驚嚇,她離開了家,在一棟奇怪的城堡中展開一段光怪的日子。有一幕她坐在湖邊,體態臃腫神情衰老,卻安詳的說道:「怎麼會如此寧靜呢?好像內心真的得到了拯救。」這句話放出了大量的光芒,我明白到,女主角真正的日子是現在才開始的。我和H說:「或許變老也不是什麼壞事吧?」H只是搖搖頭。
努力、努力、努力,日子被推下斜坡後我不斷對自己說,要努力,努力往上爬,成為一個優秀的人,所謂的優秀是什麼?早睡早起、每日記帳、記事本爬滿待辦事項、規律運動,我每年都買一本記事本,每年裡頭都慘澹得如忘了換水的水族箱,幾枝枯萎的水草飄著,刮一下表面還有厚厚的黃垢,但卻有幾隻孔雀魚仍擺動著尾鰭展現牠們出淤泥而不染的豔麗人生,至少還是有生氣的。但當日子開始被推到一個快速滑落的坡道時,這一年的記事本開始忙碌了起來,每日換水、扔擲飼料、清理汙垢,好像水族箱本來就該如此潔淨,好像擁有一個水族箱本該如此忙碌,我如一顆陀螺般打轉地照顧這個水族箱,但當我停下來一看,魚卻都死了,牠們死了許多時日,亮麗的鰭早已成為死屍的灰白,我打了個寒顫,並且因為這樣從此不敢吃小魚乾,「這不公平!」我抗議。「那你為什麼要把水族箱搞成這樣?孔雀魚本來就無法活在太乾淨的水裡。」H慢慢地說著。我愣住了,過了很久我緩慢地吐出:「因為人們只欣賞潔淨的水族箱。」H沉默,他沒有再說話,但我知道他想說什麼:「為了一個欣賞?」
或許是吧。當日子被調換成白晝比黑夜多時,我的心就開始變得庸陋,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問題,有時候我甚至懷疑自己上輩子是夜行性動物,但這個世界對夜行性動物並不友善,久了身體便要全盤崩毀,有時候我很生氣,這是種根深的歧視吧!白天的陽光將所有事物曬出一種機械的氣息,一種科技文明的壯勢、一種強光照射的霸道,白天的我昏沉地上課、說話,直到地平線吃掉最後一口陽光,才忽然覺得自己終於醒了過來。但為了下坡的日子,我必須堅強起來當個健康的人,必須當一朵向日葵,吸滿陽光,我強迫自己早睡,每天都感到空洞,好像一天還沒開始便結束了,我緊盯著時間細細的腳,當它一走到那個數子,便必須躺著,死亡般地躺著,更慘的是,從這時開始,什麼都與數字扯上關聯,像一大串甩也甩不掉的鑰匙,手機冒出了一個記帳APP,每天睡前我都痛苦地回憶著整天吃了什麼,買了什麼,再輸入一個又一個的數字,我看著餘額,惱怒了起來,你們到底憑什麼來窺探我的人生呢?H看著我與數字奮鬥,揶揄地說:「你會成為富婆,我則是越來越窮。」我無奈地看著自己被數字攻占的生活,想起《小王子》裡的精明的企業家,他每天都忙著算數,小王子說:「你們大人就是那麼愛數字!」我恍然大悟,意識到原來自己成為大人。
我的日子成為一團奇怪的龐然大物,它披散著灰塵與毛髮,像一顆瘋子的頭顱,我一手遮住眼睛,一手撫摸它,那乾燥的感覺就如同百年未喝水的植物。
面對日子的無力感一直到H出現後才真正地描出清楚的輪廓,這或許是因為我和H是多麼的相似卻又相異,我在那片亮白的世界遇見H,他用那張略微蒼老的臉龐為我朦朧的世界構築了一棟清晰的房子,在其中我可以聽見他猶如透明玻璃般清朗的語調,那種語調撫平了我內心因為面對世界的荒謬而起的無數困惑毛球。我們各自成為一個水潭,中間卻又有小橋般的水流使我們得以聽得懂對方,我流得過去,他也流得過來。如果說這世界上真的有誰聽得懂我那麼我想只有H。
我想那或許會是我這一生,至少到目前為止,說最多話的時刻,更精確的說法是,我說出最多「我想說的話」的時刻,H那邊的水潭像永遠不會滿溢似的,容納著我所有透明的想法,後來我發覺我們對日子的感受幾乎相同,苦悶與無助,像是軀體只是一個暫時彌留的空殼,而靈魂的渴望自由卻因這個殼子倍受毀壞。H出現以前,我一直試圖掩藏這種想法,我該如何向人訴說日子之於我的空洞,我內心的真實風景:荒涼與殘破。我聽同儕們說話,並且與他們說同樣的話,說完總感到內心更加破碎,因為沒有一句是我內心真正的想法,就如同他們眼中的我並非真實的我,但什麼又是真實?沒有真實,最大的真實就是虛偽。
把自己包在一個完好的殼子,買衣服與鞋子,花錢整理頭髮,像在布置一間空無一物的房子。有時候我不懂日子明明是穩健的,它似乎看似飽滿,何以我的內在總是空的?陽光明明將我們曬出健康的影子,何以內在如此荒涼?荒涼到要抓緊所有來抵抗這種荒敗感,我們再無法擁有什麼,能擁有的不過是手中的一瞬。
H出現以後,所有的所有都變得具體了。
那個冬季,H每天騎著白色的老摩托車,那老舊的白漆上有幾抹黑色的油漬,像抓住白色冬天,一雙又一雙細弱的黑色枯枝,像飛不動的雁子。我和H穿著黑色外套也像飛不動的雁子,我們下了摩托車,爬上堤防,堤防後有一條河,有時我們看著河說話,有時我們靜默,我喝咖啡,他抽菸,他總會很體貼的先觀察風向,不讓我聞到菸味,我看著H那張略顯蒼老的側臉,他吐出白煙,菸頭橘紅的發亮,像一隻璀璨的眼睛,此時H的眼神特別光亮,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到廟裡拿著香的自己,與母親一同拜佛,母親的念念有詞總是特別冗長,我說完了,便呆呆地看著香,看著那點橘紅不斷地流出筆直的白煙,我無聊地晃動著香,灰色的香灰崩落下來,煙的飄動跟著擺浮,像我手中拿的是筆,那些煙如字,對母親而言這些煙是心裡的話,她把所有的意念都集中在這炷香,煙裡有母親的信念。
我忽然碰了H的菸,白色的煙抖動了一下,「幹麼?」「沒事,只是覺得這畫面很熟悉。」或許菸是H的香,煙裡有他的信念,「你抽菸的時候都想什麼?」「沒想什麼呀。」他頓了一下,「其實,我不喜歡抽菸,但是,該怎麼說呢?抽菸能夠讓我看清楚日子與生活的輪廓吧。」「聽起來像是種媒介。」「Maybe。」我可以了解H的意思,就像黑咖啡之於我像是種面對日子的象徵,久了便戒不掉了。
在那個冬季的清晨,我們每日來到河邊,說一些零星的小事,或奢侈的沉默,河緩緩的流動著,時間快速走過。這是我對於白天最好的回憶,為了與H見面,在清晨將自己拔起,街道還空涼,人煙稀疏,我從沒想過早晨能夠如此清美,陽光薄得像紗,如同後來我在夏日憶起這段回憶的不實,一切都恍若夢境。
如果人生有上坡與下坡之分,和H在一起的那個冬季便是不可取代的上坡,坡上有光。
有時我會懷疑與H在一起的這道坡還是不是在世間?我們用彼此能理解的語言講一些彼此能懂或不能懂的話,無論能不能懂,重要的是可以理解,與H越靠近,越覺得自己遠離了現世的光景,我們的談話如輪子般滾動,我們在一台隱形的列車上,慢慢地被載往另一個虛無的所在,那裡有極白的光,光裡有不存在的獨角獸,我看見牠頭上美麗的角瑩瑩地流爍著一種安靜的銀色,那裡沒有任何人了,沒有任何房子車子與噪音,一切靜謐得彷彿不存在。然而這確實是不實的,但每當我與H越是靠近時,這樣的感受便越是清晰,好像我若再擁有一個勇敢的腳步,便能夠騎上獨角獸,永永遠遠的離開。
但我仍舊無法如H那樣灑脫,好像世間用怎樣的法則轉動都與他無關。後來,H消失了。我的日子一併坍塌下來,當然這所謂的坍塌是對比出來的。H走了,生活被抽出另一端的支柱,便那樣斜了下去。
我知道H會消失,在認識H的一個月後,便時常看見和我一起坐在河邊的H忽而變得透明,有時候他的身軀淡到比他吐出的煙還要稀薄,我看著他透明的身子,沒有說出半句話,我不知道H知不知道自己會消失,消失後又到哪去了?
我獨自面對著那塊在沼澤中的日子,好像隨時會被那濁綠色的液體完全消化,我繼續和數字搏鬥,然而沒有一天贏過,我很想知道H在哪裡,他戰勝了我們一起為之所困的數字了嗎?在現實裡我假裝沒有H這個人,沒有對任何人提起H,或許因為自己也開始懷疑起那段霧白的記憶中,H真的出現過嗎?我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我說日子依舊暴力,但在你離去後一切都平靜了,平靜不代表安穩,而是更寂靜的絕望。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著,再一封一封的撕碎,碎片化為那些銀亮的、無法抵達的星子。
我根本沒有H的地址。
有時候我會想H或許死了,他到了那個極白極亮的世界,他觸摸到獨角獸那琉璃般美麗的角,而我卻再怎麼樣都記不起當時的感受,我的日子嘩的一聲秋葉般枯黃的散開來,踩過去有清脆的碎裂聲,雖然一切看似都好了,都平靜了。
列車滑開黃昏的濃稠,成為一抹黑色的痕跡,裡頭坐著一個用枯葉堆起的人,笛聲響起,如遠山傳來的鳥鳴,輪子快速滾動,甩出陣陣風聲,它將開往暮色最深的地方。時間走到一點,我爬上床,蓋上一片勻整的深黑。
地底下的鯨魚
總是閃爍著不同敘事的可能,時而光亮如火、時而平靜淡漠。有時思緒被一種悲傷占據,彷彿它們原來就安靜地貼伏在內心湖底的石子,透過某種撥弄,便一發不可收拾地藉著波紋喧鬧整個湖面。
於夜晚的操場一圈又一圈地跑著時,這種感受總是特別濃烈,也許因為整個人都隨著耳機裡的音樂滑動到現實之外,也許因為操場的燈光帶著一抹老沉的暈黃,這種暈黃讓人感覺悠遠。跑著的瞬間,那移動的身體便不像只是在跑,而是升騰於地表的飛翔感。
能夠飛翔的時候能看見什麼呢?此時終於不再黏於僵硬的地表,我們移動著,好像自身之於世界是一只永遠不會停止的陀螺,移動或轉動都是必備的本能。能飛的時候,一些模糊的片段也跟著長出翅膀,在記憶中鼓動。那聲音讓我想到一些人,走過生命風景的人、正在生活路上的人,他們說過的話、寫過的字,甚至連身形或觸感都漸漸具體起來。
總有幾個極少數的人在此時會出現,甚至連拉扯一些回憶的線頭都不必要,就那般自然出現了。
操場中央或外圍總是攢蹙著一股熱騰的氣息,簡直就像甫蒸好的一籠燒賣,充滿繽紛色澤。那傾洩而出如布幔的白煙,以及富有彈性的口感,都使人感到青春。此時,總無以復加的想起你,但也只是一種淡然的無以復加了吧。
關於你,有太多無從清楚解釋的形容詞,總抗拒著書寫你,並非在這種書寫中帶著什麼危險的可能,而是有另外更複雜的原因。但你總是出現在我閃爍的敘事裡,無論如何置換形式,你仍會像一個謎底出現。曾努力的探求那樣的色調究竟參雜什麼元素,或究竟是什麼使一切產生這種色調,可是沒有答案,因為這種色調根本是不存在的嘛,只是一種幻覺罷了,因為太擅長用過於浪漫的濾鏡去看待重要的人事物。
你可能會對此表現出不以為然,但又做出和我同等的事情來。
並列的照明燈隊伍一般,聽見風的口號而熄滅,操場陷入沼澤的黑暗。年輕的人們逐漸散去了,整個操場寬闊得令人感覺自己像荒原中的馬。所有的灑水器於此時一併開啟,中間的草坪出現一幅美妙畫面,若干潔白的圓弧水柱舞動,像是草皮底下游動著一隻隻的鯨魚,牠們快樂的優游換氣。這樣的幻想總在我腦中樂此不疲的上演。緩慢地跑著,風很快地拂過,把空氣削的冰涼。然後想起你,跑,想起你,跑。
冷的日子就快來了,帶著透明的心思降臨。當我操控著意識有距離的思念你時,並非一件好事。那些距離足以塞滿太多想像,而想像是不適用於我們之間的。
冬日之於我們是最清晰的一段了,我們縮在各自的大衣裡,伸手觸碰同一杯熱咖啡,當一起在風中看著熱氣不停從杯緣飄散,彼此究竟懷著怎樣的心事呢?在那個光亮的歲月末,我遇見了你,像是跌入一個萬花筒般的愛麗絲洞穴,身軀縮小又放大,在光怪的世界中看見屬於自己的一條小路,旁邊的樹上掛有一隻粉紫迷幻的笑貓,和劇情不同的是,後來這條路上僅有我獨自一人。
草地下的鯨魚仍不停噴出水柱,中間的球場以水柱為圓心,畫出一汪又一汪的水,遠方BRT的站牌仍兀自發出黃紅藍的燈光,這些色彩映在水窪裡,成為一種如古教堂的彩色玻璃透出的光。眼睛的閃光又使一切更像是撕下宣紙般,綻放絨絨的毛邊。天空無雲,星子彷彿被擦拭,水晶般地發出不可思議的光亮。
我總愛提一些「日子」、「生活」的字眼,張懸有首歌,歌詞的最末是這麼寫的:「我們像所有人一樣謙卑,忙碌與分別。走出家裡,走在日復一日的大街。」歌詞唱的正是我心中畏懼的,那種日復一日的循環。有時覺得自己的人生不知出了什麼亂子,總是在安定/開花、狂亂/朽壞之間反覆輪轉,彷彿不這樣子就無法確認自己處於此世。有次我說我害怕這樣的安穩,而你笑著說,放心,你的混亂由我來確保。
我將那句肯定句視為謊言,因為你隨時都會到更遠的地方,或隨時都有在風中散逸的可能,之於彼此來說都是相同的。那遠行的人,可能就是自己,背起一個不回頭的念頭,便一下就抵達了。那或許是為什麼神話總強調不要回頭,因為那是神話的緣故。
回頭究竟會看見什麼呢?那條你悄悄在我掌中凹折的紋路,一切就那樣子有了岔路與轉彎。
撿起斷裂的步伐,將奔跑的樣子拼好,時針指在十一。人煙稀疏的操場頓時空曠起來,像是世界的縮影,奔跑的姿態就如我們在生活裡努力求生的模樣。我一圈又一圈的跑著,喘了便停下來用走的,走累了便開始跑。當我經過同一棵榕樹或昏黃的路燈時,忽然領悟到「日復一日的大街」這句歌詞,那種日復一日感並非因為刻意忽視時光分秒織就的嶄新部分,而是因為「那條路」已經融為心底的一部分,就算身在異國,也改變不了這樣的基調與本質。
你仍是缺席了,無論是伏在內核那不動的路,或是外在變幻的視野。灑水器安靜下來,周身霎時空曠靜謐。你在地底製造出幻夢般的水花,贈予地表上的我,因為我們都明白,誰都不可能到對方的真實世界,我下不去,你上不來。
直到全然安靜了我才明白,地表下的不是鯨魚,而是游向遠方的你。
所謂日子
日子忽然被推入斜坡,如一顆小小的果核,在不斷的滾動中,先是黏上了塵埃,幾根被染得烏黑的羽毛纏上來,然後是暗沉的砂礫,接著是大量的損壞收音機般的嘈雜聲,交錯不停、慌亂的光和影。
我的日子,本是一顆小小果核,漫著美麗而天然紋路的日子,就這麼被一個斜坡包覆再包覆,最後它什麼也不是了,有時候我看見這團怪物停下來,我仔細的撫摸它、用不再靈敏的鼻子嗅嗅它、最後把它裝入我的眼中。「這裡已經沒有其他東西可以再捲進來囉!」我用很輕的聲調對我的日子說,它沒有說話,只是安靜的蜷縮起來,躲在我眼裡最柔軟的地方。...
推薦序
推薦序
光與影與魍魎──讀《地底下的鯨魚》
李欣倫
最早認識閔淳,是在幾位東海、靜宜喜愛文學的師生共組的讀書會上,由於初識,她給我靦腆而安靜的感覺,眼神裡有靈動的光。進一步讀到閔淳的作品則是在東海文學獎散文決審會議上,當時我最支持並堅持的就是〈螢火蟲的光〉,一篇寫女女情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句子是寫KTV中,投映在女孩子身上閃動、旋轉的五彩燈光,「黑暗中,將我們分割成各種零散的色塊」,接著閔淳寫「像一場殘忍的祭典」。
不知為何,當時讀到「殘忍的祭典」這幾個字,有種正面迎擊的強烈感受,我驚訝的不是兩個女孩兒不被認可的擁抱,或是被龐大體制、秩序隻手遮蔽下的殘喘青春,而是那旋轉流蕩的KTV五彩燈影,應隱喻狂放或暴走的青春,所有的感官如同無限暢飲的可樂啤酒,應盡情流淌甚至浪費,但在女孩敘事者的眼中,卻藏不住鋒利的鋸齒,割裂寂寞又徨然的青春,等待屠宰,殘忍祭典。那篇以螢光終結的散文,讓我始終記得的卻是這間彷彿流亡最終站的KTV。
這是我初識的閔淳,也是後來始終被我記憶收妥的閔淳文字:安靜沉穩敘事中,平淡家常的小日子裡,隱匿著一間五彩霓虹旋映、情感被分割再分割的暗房。這次讀《地底下的鯨魚》,暗房幻變成不同形式,像是〈地下人〉中「豢養著一批殘弱不堪的老人」的火車站地下道,還有懷抱著殘疾秘密的B的房間,黯黑記憶築構出的內心地下道,收納秘密和腐敗往昔的場所,被閔淳慎重的折疊起來,暗藏在敘事樓閣中,待你的目光經過,像機關般乍然彈出(像不像伏在錦羅綢緞中冷光森然的匕首),於是,就只能身陷其中。
〈地下人〉的最末,在光的反射下,窗外大雨迴照出室內激烈的黑色雨影,如同將青春分割成色塊的廉價五彩燈飾,書中光耀處處,我也跟著閔淳駐足看光:河面上廣告招牌的光之倒影,遠處飛馳的車燈,黑暗的房間摸索孤獨,思量我與世界的距離:「而透進我世界的光也只有那痕細瘦的分量」(〈阿冷〉)。閔淳對光的捕捉似乎一向到位(敘事場景的燈控師?)無論上場的是寂寞或恐懼、慾望還是希望,閔淳說要有光,就有光,這樣的光,如同觀音千百億化身,現身於字裡行間,也是我喜歡重複品讀處,例如〈地底下的鯨魚〉寫到BRT站牌黃紅藍的色彩,燦燦顏彩融入水光,她將之形容成古老教堂彩色玻璃透出的光,繼而又疊以星光,閔淳極富耐心並掌握條理的為一重又一重的視覺疊影命名,又十分用心於意象經營,蟲、繭、照片、水、地下道等所有等待命名的物件,都有它該好好待著的多寶閣小抽屜。想來是微物之神:將某個意象的核心精準萃取、延伸並乾淨的收束,文中開演的層次與秩序井然,展現了寫作者的美德。
有光就有影,影中還有魍魎,所有的天堂在寫作者的目光中,悉可折射成地獄無間,罔罔威脅,同樣的,可怖輪迴經過敘事濾鏡,也可造就絕美山水無數,無論寫父親母親家族私史,還是寫校園、情感、關於日子與書寫的思索,光伴隨著影,影又佐著魍魎,三重意象,交織成敘事中不可承受之輕。我跟隨著閔淳,從白晝的人際往來,獨自走入夜晚,夜間散步、騎車與寫作。忽忽我想起閔淳碩士論文寫張愛玲。蒼涼張望中,雷電般的敘事裡,光與影與魍魎輪番幻化,相偕舞來。
自序
平地木
桌前的小黃燈下,紙張散著,上面漂浮著自己寫下的文字。一口氣潛入裡頭,彷彿又回到那空曠的時日。無盡的寂寞燃燒,似在森林裡獨行、在雨中戲劇性的對話……。這些潮濕的文字又一次回到面前,數度震驚著自己。我修剪字句、更換用詞,試圖使這些蔓生的文字草叢不那麼張狂,然而很快地發現,無論再如何試圖遮掩,都掩不去那些曾經清晰的情感,掩不去這些皆是一部分的真實。
想起童年的時光,著迷於金庸,在家中附近小小的市立圖書館一套一套的讀著。那撩亂的情節、人物關係、絢麗的武打招式在多年後已逐漸忘卻,然而卻一直記得那披著黑色罩衫的行走姿態,荒山裡多崎的小路,突如其來的石洞,簷上的飛行,走不出的變幻八卦陣。
曾經因為金庸,暗自在心底許下一個成為俠女的願望,卻終於長成了一個幾乎是俠女性格反面的心思曲折女子。那些童年寫下的亮晃晃的志願,都一個一個歧出散開了,成為別種模樣。現今想起,金庸之於我,也許從來都不算是一部武俠小說,在我心中留下的從來都是別的事物。
後來再長大一點的我,仍在那圖書館裡借閱各種書籍、讀教科書,然而現下想起來,那個我在書櫃上取下紫微斗數書的下午,很有可能是後來寫下文字的某重要驅動力之一。
那個下午我在窗邊寬綽、因舖上透明桌墊而微微反光如湖面的大桌上,一邊翻閱紫微書,一邊在空白的紙上畫下十二格子,依據書上的指示,一步驟一步驟地幫自己將上頭所有的星宿排列而上,漸漸地主星、吉星、煞星、飛星,全都在那空白的紙上出現了。印象中是一個陰涼的午後,所在的三樓罕無人跡,我終於完成命盤,揣著那張紙,小心翼翼的夾入課本,像是忽然擁有了一個極重要的秘密。
後來,我經常在讀教科書疲憊之際便跑到三樓閱讀其他書籍,悄悄攤開那張紙,在書櫃上取下那本紫微書,試圖從中解出那些星宿組合的密語。(當然,很快地網路就遍布生活,我發覺只要在隨意一個命理網站上輸入生辰,整張命盤便能夠自動排好,根本毋須如此勞費手工,便感覺當時的自己傻蠢又純粹。)
那些午後我究竟想要知道些什麼?
記憶中一直有那麼樣一個片段,時序依然是童年,一個男孩忽然就倒在地上,翻出眼白,全身抽搐著,雖然後來我明白到那是一種病理症狀。但那模樣依然在我心裡遺留下了些神祕的軌跡。當時我想:他怎麼了?原本的他呢?倒在地上的為什麼是他?不是我?
為什麼我不是他,他不是我?
我是誰呢?這樣子一個大哉問的問題存在心中。看著那些在十二宮格上的星宿組合,試圖從中探求答解,為什麼我會遇到那些事情?為什麼?為什麼?我想那並非為了預知什麼,而是想更加看清那些纏繞在自己身上的事物。
後來,我並沒有一頭鑽入命理世界,終究是在表層游移,我知道命盤終究不代表一切。讓我真正理出自己的,也許更多是在文字裡的時候。我始終是相信文字的人,然而當在文字中直面自身,許多痕跡、圖像如沙一般浮現出來,它們是我嗎?也許是我也非我,但其中有真實。
這本散文以某篇年少寫下的文章「地底下的鯨魚」來命名,寫下它的時日距今已十分遙遠,裡頭的心情與人在當時非常重要,然而隨著時日漸漸被擦拭。現下我更願意將這個名字視為對自我的探求,用鯨魚悠遊的姿態潛入地底,去看那些根、巢穴、腐壞,堅韌或柔軟。
地表上的事仍全都在行進,無論是謊言、傷害、病毒,還是真實、溫柔與陽光;在地底游過的鯨魚,將會浮出,以更清晰的姿態穩住、行走、奔跑。
謝謝促成這本書的所有人,謝謝那僅有投影機散發出微光教室,許多人的字、聲音、臉龐在白色布幕上流動,全都瀑布河流般地侵蝕、洗刷著我。謝謝所有空曠如草原的時日、每條夜裡通往清晨,浮晃著光亮的路。
推薦序
光與影與魍魎──讀《地底下的鯨魚》
李欣倫
最早認識閔淳,是在幾位東海、靜宜喜愛文學的師生共組的讀書會上,由於初識,她給我靦腆而安靜的感覺,眼神裡有靈動的光。進一步讀到閔淳的作品則是在東海文學獎散文決審會議上,當時我最支持並堅持的就是〈螢火蟲的光〉,一篇寫女女情感的作品,印象最深的句子是寫KTV中,投映在女孩子身上閃動、旋轉的五彩燈光,「黑暗中,將我們分割成各種零散的色塊」,接著閔淳寫「像一場殘忍的祭典」。
不知為何,當時讀到「殘忍的祭典」這幾個字,有種正面迎擊的強烈感受,我驚訝的不是兩個女孩兒...
目錄
推薦序
光與影與魍魎/李欣倫
推薦語/言叔夏、凌性傑、蔣亞妮
自序
平地木
輯一 掘土拼圖
蟲之拼圖
僵病
雙繭
涼涼
天線
輯二 浮漚
螢火蟲的光
路徑
地下人
殼
所謂日子
阿冷
U
地底下的鯨魚
一盞燈的明滅
輯三 海面日出
湖水色時間
花開怎麼沒聲音
黑色的歌
咖啡事
車窗和雨滴
茶與字
推薦序
光與影與魍魎/李欣倫
推薦語/言叔夏、凌性傑、蔣亞妮
自序
平地木
輯一 掘土拼圖
蟲之拼圖
僵病
雙繭
涼涼
天線
輯二 浮漚
螢火蟲的光
路徑
地下人
殼
所謂日子
阿冷
U
地底下的鯨魚
一盞燈的明滅
輯三 海面日出
湖水色時間
花開怎麼沒聲音
黑色的歌
咖啡事
車窗和雨滴
茶與字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3收藏
3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




 3收藏
3收藏

 4二手徵求有驚喜
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