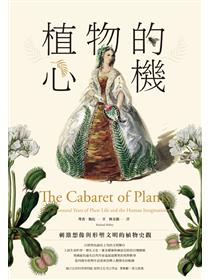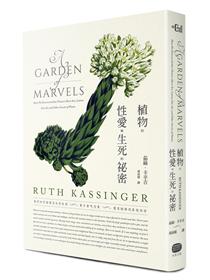屬於台灣靈魂的《湖濱散記》
「我是山林自然書籤,鑲嵌、斜插在草葉、花瓣之間,
但待朋友們信手展閱,我們究竟處的無窮性靈,
從銀河星辰,普唱到地心……」這是一本融合植物知識、山林智慧與自然哲思的美麗之書
讓我們為台灣的一花一草一木、大山大海,著迷沉醉、震撼不已
心心念念與這塊土地真實深刻的連結
將它最珍貴的寶藏,世代存續於人類生存的地球上
2020年初,生態學家陳玉峯教授自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退休後,除了幾句「人之常情」外,沒有依戀離情,他回歸山林,目光朝向山後方無邊無際的宇宙。
本書即為他「和社會解除契約關係」後,筆耕山林的自然書寫作品。
一篇篇美麗的情書,傳遞著與土地生界的浪漫邂逅,愛意堅定而無盡。他「走筆如林」,捕捉自然的躍動幻變,化為充滿靈性的語言。
「山林本來就是人們意識起源的母體子宮,足以孕育太虛幻境的所有程式與非程式;天神將數不清的稜鏡,藏在萬萬端無窮的萬象,隨時隨地讓人應現心境。」
「這些狀似反覆的地文記事有什麼意義?青蛙記得、蚯蚓知道,還有我的生命的一段呼與吸,牢牢地烙印在這片地土,形成草根的滋養。不需等待,時程一到,自然會有一片花海歌唱。」
四十年來,陳玉峯教授從台灣環境生態的鬥士,到一位諄諄教育者,對於土地山林孤獨的哀戚,以及至死戰鬥方休的樂觀,時時充塞胸臆。在書中,鬥士與仁者的真實感受將不再孤鳴;展閱之間,每一口靈魂的深呼吸,都會喚醒你我內心最理性的感動。
【熱情推薦】
對大自然的款款深情,看完掩卷還會隔空透暖,餘波盪漾……
知名編劇、導演 王小棣
作者簡介:
陳玉峯
生態學家,台灣民間自然保育、文化改造的代表性人物。
畢業於台灣大學植物系,台灣大學理學碩士,東海大學理學博士。先後任教於台大、逢甲、東海、靜宜大學,曾任靜宜大學副校長、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台灣生態學會理事長。現為「山林書院」負責人、台灣生態研究中心負責人。
專業研究台灣山林植物生態與分類,積約四十年台灣山林研究、調查經驗,從事生態保育運動與教育、社運、政治運動、自然寫作、生態攝影、社教演講等。
1991年創設「台灣生態研究中心」。2002年創設全國第一所生態學系暨研究所,並捐獻、募款三千萬元,興建生態館。2003年10月成立台灣生態學會。
同年,榮獲第二屆總統文化獎──鳳蝶獎。
2007年辭職,勘旅全球、搶救熱帶雨林,並學習、探索台灣宗教哲學。2012年開創「山林書院」。2014年8月起,任教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於2020年1月底退休。
四十年來筆耕不輟,系列研究報告之外,著有《台灣植被誌》二十册,教育、生態解說、自然散文、宗教哲學及社運等專書近百册。每年演講數十場,持續為台灣文化注入新活力。
章節試閱
菁芳草的黏功
一直擱著、一直擱著,不知不敢或不想明說或碰觸,菁芳草的美感真的吹彈可破,所以我下不了筆。
今天,我再度走向沒有菜的菜圃,被滿滿的菁芳草所盤佔。
我是忍了好長的一段時日,終於狠下心來清除菜圃上的菁芳草,因為我種植的一批白菜、青梗菜,全數被菁芳草所消滅,而它又是那麼楚楚可憐樣,小小的圓卵形對生葉,不只討喜,當水分無虞時,他噴掃眼底的綠,勾魂攝魄;夢幻般的綠,沁入骨髓,以致於我都儘量不置足跡。
可是當我狠狠地清除時,柔弱的草軀頓成繩索般地頑強,它們死纏著地母,彷彿我拉扯的是土地的臍帶。我拔到手軟與心虛。
除非我翻土,挑除掉潛伏土中的植枝,否則不出一個月,它們一樣綠得美豔。我不是不知道一般種菜的方式,我只是不想吃脆弱多病的蔬菜,否則市場上買。既然自己要種,就種有骨氣的菜,但市場上販賣的菜籽,就是如此不爭氣。
種了兩輪之後,我放棄。所以我現在的菜圃,就只單純欣賞著菁芳草。
一九七七到一九八三年間,我在台北地區觀察、調查次生演替時,界定了菁芳草的生態區位。我是觀測一個廢棄的魚池,隨著淤積,先是青萍的浮水植物在水面,而後李氏禾由岸邊逐漸入侵,大約一年時程,李氏禾完全覆蓋而積水消失。然後,菁芳草加入戰局,冷飯藤也湊上一腳。第四年,山黃麻幼齡族群盤佔,嗜濕的菁芳草、冷飯藤漸式微,山黃麻及水同木的次生林發展過程中,菁芳草即消失。
菁芳草屬於低矮型多年生草本,分布中心是偏潮濕的壤土地,對陽光的需求量偏高,但半遮蔭處尚可存活,它的無性繁殖力很強,因而靠藉族群的彼此支援,半遮蔭處的植物體分享了破空陽光直照部分的資源,一樣可以繁盛,但一旦次生林形成,它們得不到充分的光源而消失。
我的菜圃是因為不時的人為干擾,阻礙了樹木的入侵,且三不五時有朋友幫忙除草,反而促成菁芳草的長存。如果放任自然營力,我估計菁芳草在三年內,就被大花咸豐草等吞噬。
菁芳草的傳播,最主要靠藉著它的「黏功」,它的整個花序枝、萼片上,長滿老花眼看不清楚的綿毛,分泌著黏液,一旦人畜走過,不只褲管、皮膚或鞋襪,就連塑膠、木板都上黏,它們的花果序簡直就是萬用強力膠,水柱也難沖洗掉它們。
有句歌詞:「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如果指的是菁芳草,很適合改一個字:碧「黏」天,它必然是多情種。
假寐甜心
現代人重視養生,卻往往遺漏鄉土植物超療效的無形力道,那是從子宮時代起算的療程!
§鄉土
鄉土,意味著你來到這個世界上,那個時空交叉點上,周遭一切動態環境給予你的祝福,而且,你的誕生也開始或正式地影響著環境場域。不是你有經驗、記憶的累積而已,庭前屋後的花草、樹木一樣經驗、記憶著你。它們真的認識你!
可是,當人們不斷學習知識、經驗、累積自我,就不斷地遺忘或拋棄他在童騃時代,最真實的,聯結環境的各種情愫、慰藉,或只是某些奇特的安全、安定感,事實上,人從母體出,一生都在地球時空的超級子宮之中,尋求對永恆及未知的安定或錨定感。
於是,在遺忘的渺遠空窗期中,鄉土曾經陪伴你,還惦記著你的植物或地景,在你全然不經意的偶遇瞬間,不時遞出一絲絲慰藉,而大家都不知道,或未曾察覺那股子宮來的加持,常常只在文明、文字符號中,例如詩詞、小說、精神上的某類聯結時,找到原始況味的替代品,像台灣鄉間尋常作物的香蕉,就與文字中的芭蕉雜交且替代,而充其量說是移情作用;古人的睹物傷情或藉物賦、比、興,卻可取代你始源的母體記憶。
然而,當你心緒沉澱,恰好在意識流竄的缺口上,又與鄉土植物近距離接觸,就有可能發生抽象臍帶的通聯,而植物就是有著跨時空導航的神奇能力,讓人翱翔在思維之上,啟動潛意識底層的網頁,進入思考不能及的天地,鄉土始源的座標原點處,就會引發心靈自我的按摩,進行系列內分泌等的調整,而不止於外在負離子的唯物解釋。
§蕉葉
香蕉「樹」是由層層螺旋套疊的葉鞘組合而成的假莖,撐起巨大的單葉,真正的莖在地中。它是超大型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也是假樹。
不管植物學正確的知識怎麼說,香蕉就是小人國中,放大的草本,天生屬於童話世界的幻象國度,幾乎沒有台灣人不認得它,而它的美,有點不大實際,偌大的長扇葉如此柔軟多汁,生來好似偏好惹風來撕裂。
我的山居處附近到處是蕉園與檳榔,即令不是蕉農,前庭、後院、路邊,也會種上幾株附風沾雅。而我每次觀見蕉樹,就有著飄渺漫遠的鄉情,我老是想截留幾幅捉摸不定的美,卻老是按不下快門,一種很貼切的近鄉情怯。
這天下午,傾斜四十度左右的陽光,有偏光、有逆光,總成強烈又淡淡的招攬,就在種瓜坑溪畔,我隨意截圖。
三片蕉葉左側是平展後的老葉,平行脈局部黃化;中偏右是已開展的新葉;右側是正在旋展中的初葉。
初生蕉葉捲旋成桶柱,有如捲紙筒,先端遭霜凍傷,有如燃香燼,然後旋轉開張,攤展成平面,平行脈運輸光能所合成的多醣,聯結來自地土的水分與礦物質,進行生命的天責。中肋也此過程中,由直立而下傾。老葉黃枯後,下垂而宿存。
寫實的生、住、滅。
平展的新蕉葉翠綠欲滴、生機旺盛,富滿青春的美感與朝氣,凝視著它,來自地母后土的生命力,可以經由目觸,啟動你的原力中樞,是謂養眼,實則起心正念。
重雨敲擊或強風撕裂,則大葉片會沿著平行脈開裂,分散風阻或風險。老葉則先黃化,葉綠體進行裂解、養分回收,供養花果,並存貯於地下莖芽。
枯黃轉褐焦的蕉葉大致回收了基本養分,徒留乾褐的粗纖維片,宿存一段時程,實踐天責之後,自成收斂之美。
我在這片斜逆光的蕉園停留三分鐘,理想中我該看它三年。三分鐘看樣相;三年觀生命。只因眾生紛紛,有時候三分鐘足以聯結三年或一世。
斜光
一直對斜照的陽光印象深刻。
只有晨昏或特定時段的斜射光,可以點燃林床的一席金黃,我是指路徑穿越處的森林下,也才可揭露局部地被沉睡的夢境,為它們披灑華麗的金粉,好為諸多幽靜修行的林下草本、灌木的容顏感光截圖。它們絕不會貪圖熾熱短暫的激情,但我確定它們的光合作用能量激增。我也確定斜光確保溪谷、林緣保留一席棲地,好讓被林海吞噬的次生物種宿存它們的種源基因庫,一俟森林發生變故,再度復出,擔任補地的首席修護工。
不只是我看斜光烘托出來的色層、色溫連續變化,也可以讓我品味有別於一般生態相關的奧秘。記得年輕時代的我,老師的研究室有了什麼新的儀器,我總是很想要拿到野外測試去,有次,自己買了一部打折廉價的光度計,帶去南仁山的原始森林內,爬樹、架梯,測量林冠下幾百個點的光度,測量時邊測邊嘲笑自己的愚蠢,每分秒光線都在林內複雜位移,加上樹葉、光斑連動,要產生相對精確的相對光度,我必須「同時」測量多少數據啊?後來,只好依理想化的模式,繪製森林分層結構與光梯度,而且,只能在中午測量。斜射光則又是另一回事。我想著年輕時的天真,忖度著年邁之後如何以意識觀我心的山林光影?
目前,我只以手機,隨順捕捉側光的寫影、唱詩、聽靜。
斜光側照,樹葉的逆光照最富飽滿的韻味。
我山居前,溪溝對岸的一片薩爾瓦多銀合歡,只有在斜射光入照時,整個林相才渾厚立體地活了出來。
有次,我在一處大約三十度的山坡上,陽光大致平行於山坡斜射進來,林下的江某小樹,偌大掌狀複葉的七至九片小葉,彷同被點亮的綠花傘,溫柔養眼的綠光,聚焦了世界。宇宙就在那個位置上,成就了意識的黑洞。
如果說佛洛斯特的〈林間小佇〉或〈未竟之路〉是我壯年或之前的況味;眼前的江某,就是當下「我」的意識。「我」不是「我」的我,是萬物、萬象在我內靈外魄的我;我是不必脫殼的蟬,直接入定。
所以我也恰好觀自己的風動及葉動。
幾乎每種葉片,甚至每一片葉片或小葉葉片,都有自己獨特的風中舞步,也都會演奏自己的調性,發出唯一的音或聲。我大概是世間最貪心的人,我想聽盡每片葉子的「古典音樂」。
江某隨著林隙或道路吹送進來的風力大小,會有特定的小葉片起舞或起乩。如果風力或氣流超過一定程度,則全面「翻盤」。
過往生理生態的研究,多集中在葉片氣孔的蒸散作用等面向,可是我認為太簡化了,龐多葉片的動態或與氣流的動態力學,必然包括各枝條生長的調整,也隨著樹齡作修飾,事涉從根部到枝梢的水文、光合作用、呼吸作用、重力平衡等等,乃至葉片與葉片、葉片與枝條、葉片與全方位環境因子無窮的互動與交涉。
有時候我以為植物生理的生態研究,太過於人學化,就是欠缺植物本身角度的探索,包括從根系到枝葉的整體體會。
植物不只有「感覺」,還有「意識」,並非化學激素的唯物思維所能究竟。森林內,我不時觀見「植物奧義書」,不是一冊冊,而是一片片葉子的交響曲。
我了知斜射光淋上谷地岩隙或林緣五節芒的時段,曲曲長長的葉片,演奏的是宏亮的進行曲。
新情也綿綿
§茄苳的身教
說起茄苳,必定是我某一世的情人吧?可是,它是雌雄異株,我說的「情」人,只是強調因緣綿長,我認定的「情」字,偏向「心中長青」,永遠生機旺盛、鬥志高昂而情義相挺。
小時候我就讀故鄉北港的南陽國小。記憶中,我們小朋友常會撿拾掉在地上,有一種長長的葉柄,然後彼此將葉柄交叉成X形,用力一扯,看看誰手中的柄斷掉了?沒斷掉的勝方,繼續以該葉柄跟人比賽,直到斷掉。
我們努力地去找尋最堅韌的葉柄。我們都知道,剛掉下來新鮮的落葉柄,飽滿、圓潤、多汁,卻是最脆弱,一扯即斷;我們都會找那種較乾癟,卻堅韌厚實的。我們樂此不疲,就是要找到一根堅忍不拔的葉柄,即令贏了多回,我們也知道,很快地,再怎麼堅強的「王」,也會斷掉。沒有人知道,贏了有什麼好處,只是瞬間的歡呼。
不確定是否茄苳公給予小孩子無言的「身教」,也不曉得這樣是不是自然的教化?我們都知道「眼見不一定為真」,經驗也常槓龜,所有形象都很容易滑動。我們究竟在找什麼究竟?秋天故鄉常是滿滿的陰天,我們的答案就寫在茫茫的天上。
§茄苳老樹的戀情
二○○九年八八災變的幾個月前,有天,我在台21公路(註:即今之台29公路)的楠梓仙溪支流調查植被。
就在公路旁的溪溝側,有株老茄苳樹,其周圍算是演替較完整的次生林,所以我設置樣區進行調查。
正當我以皮尺圍抱老茄苳量胸圍時,我看見公路上有位老阿嬤,跨騎著一部「小綿羊」(機車)從旁經過。她一直盯著我看,看得我為她捏把冷汗:
「歐巴桑!小心看路喔!不要掉到溪溝啊!」她沒理會,甚至還回頭看我。
她前行約百公尺,停車,且調頭騎到我跟前,開始跟我談這株老茄苳。
她說了老半天,我搞不懂她在說什麼。我是在工作,甚至厭煩她的磨蹭。
後來,我終於弄清楚怎麼一回事。
茄苳嗜濕。茄苳成林或大樹下,常有地下水或湧泉,而我在調查的這株巨木,幹基旁有出冒的泉水。這正是台灣早期移民拓殖的地名,常出現「茄苳腳」、「上茄苳」、「下茄苳」等等小聚落名稱的原因,因為定居其地的先決條件之一,即覓得穩定的水源,而茄苳往往是地下水的指標,先民懂得下挖一探。
水源指標樹在台灣最有名的,大概首推茄苳。在中國,殆如水柳。所以左宗棠帶兵打新疆,先差人種柳樹,柳樹長得好的地方,很可能有地下水源,畢竟行軍沒水是個大問題。
回阿婆的故事。
原來,阿婆是附近窮人家的孩子,七、八歲即負責一家人洗衣服的工作。她每天一早,提著衣籃來到這株茄苳樹下搗衣洗淨。她洗了十幾年,直到結婚。
我終於明白她為什麼騎車盯著我看,更在車行百公尺之後,回頭跟我話茄苳。
讀者不妨想像,從小女生,經懷春少女,乃至婚配,一生最是浪漫情懷的灰姑娘,數不清的心緒,化作清濁漣漪了無痕跡,她自言自語,若有對象,唯獨這株茄苳傾聽、陪伴!
這樣的人樹情,很可能終其一生無人知曉或分享。而就在這天,她看見我「擁抱著」她的春天,拚老命也得過來一遣悲懷啊!我把她的故事編在人地情感項下講述,那是我演講土地倫理的一環節。
有時候我也會想起我在南橫東段,新武呂溪畔調查到生平唯一調查過的茄苳純林時,何其雀躍、滿心歡喜。偏偏撕肝裂肺的不幸發生了!南橫工程單位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剷除了我記憶中唯一的天然純林,架設了水泥鋼筋駁崁,那群茄苳老少的慘叫聲浪,迄今傳達到太平洋上,永遠哭泣的海濤,而恆無人知曉。
「不是我的錯!」
§植物說話
人魔病毒橫行全球以來,許多城市、區域執行隔離,各地的幽默創意也傾巢相傳,從卡通可愛的,到古板神明的諷刺,琳瑯滿目,而我一樣寫著與植物的對話,所以朋友傳來一則:
「精神科醫師協會通知:
親愛的公民,如果被隔離,您開始和花樹聊天,這很正常,無需來電。只有在那花樹開始回答您的情況下,才有必要尋求專業協助。
您疲憊的精神科醫生。」
朋友還加了一句:「你適合參考。」
我看了,打算要說給植物朋友聽,看看它們會告訴我什麼?不同的專業也理應對話。
沿著68山路,在高架橋下看見幾株台灣肖楠、台灣楓香及相思樹的植樹及人工草皮後,陽坡馬拉巴栗的次生族群逐漸增多。道路右側下方,外來種荖葉攀纏在兩株檳榔樹上,間夾一株南台指標的次生樹種蟲屎,似乎代表台灣西南平原物種,東進內山的最前哨,或說氣候暖化以來,西南半壁帶有半沙漠氣候的物種,近年來才北進東升,來到了68山路。
我想不出任何理由人們會種植蟲屎。
我們依序經過綠竹園、雜林等,我記錄著茄苳、龍眼、九芎、龍柏、台灣櫸木、第二片酒瓶蘭園、月橘、馬拉巴栗次生林、榔榆、檳榔、野莧、台灣肖楠(或者中國翠柏)、相思樹⋯⋯香蕉園。
就在一大片香蕉園下段,乾旱立地中,出現密密麻麻的小花寬葉馬偕花。
§千錯萬錯不是我的錯!
小花寬葉馬偕花是一、二十年來的外來入侵種,以不到二十年的時程,遍布全國中、低海拔地區,而它的屬名的中文俗名叫做「十萬錯屬」(Asystasia),拉丁文的原意帶有「不按牌理出牌」、「不一致」的意味,原本的命名者是基於它的花部型態給人困惑,所以取下這樣的學名,譯成中文時,加重了強調,於是就出現了「十萬錯屬」,所以這一屬的所有植物,當然都可以冠以「十萬錯」之小名。
我在拍它照時,它就跟我說:
「不是我愛強佔你們的土地,我也不想欺凌其他的物種,是因為你們不斷下重肥、施灑化學藥劑,導致土壤劣化、酸化,迫令太多原本的物種生病、體弱,而我們族群初來貴地,一開始過著大富大貴的生活,承蒙台灣人百般呵護。哪知道你們喜新厭舊,短短好日子之後,我們就被掃地出門,流落街頭垃圾堆旁。許多我們的同胞埋冤異域,幸虧少數先人吃苦耐勞、耐旱抗毒,而且大量生殖,賦予我們接上台灣的地氣,趁著這樣的氛圍,我們才可能在你們糟蹋過後的荒地,取得綠卡……」
我說:「那我之前說你們是異形,你們讓台灣生界異化,是我誣賴了你們?」
小花十萬錯:「沒錯!你先考量一下時間順序與因果邏輯。是你們到國外百般遴選,派出大花轎把我們的先人迎娶入門,然後遺棄我們時,你們大概認定我們準死無疑,或說你們本來就不在乎我們的死活。而長年來,你們一直強取豪奪你們的土地,用盡種種殘酷的手段,壓榨、虐殺土地的生靈,導致土地垂死,清空原生植物基因庫,而我們的先人歷經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拉拔我們這些適應惡地的族群存活下來,替你們在不毛惡地,撐起護土的責任分擔。是你們先造成土地的異化,而後有我們的迴饋,以德報怨……」
在此敦請假精神醫學協會出面評鑑,是台灣人有問題,還是入侵植物犯了精神異常?
台灣人數十年來視本土物種為「雜木、雜草」,去之而後快,每年成千上萬引進外來物種,且一波換過一波。種了樹又每年數度強加截肢斷根,或是偷偷謀殺;每年編列預算,表面上清除外來入侵物種,實質上增加演化壓力,逼迫外來種縮短生幅、調整生活型,加速世代突變,培訓外來戰鬥的能力,於是最近十五年來,外來種的馴化與入侵速率暴增,實在是導因於「台灣人十萬錯」啊!
不只山坡地小花十萬錯的猖獗,68山路的路面間隙,一樣見有它們的足跡,更且體型甚至可縮小至六、七公分以下即行開花結實。
小花十萬錯的抗告辭,小花蔓澤蘭說過十萬次、大花咸豐草說過十萬次、馬拉巴栗正要說,而銀合歡早已懶得說話了。
樹的感覺
§台灣低海拔落葉林的精義
西元二十二至三十七年間,漢光武帝在建立東漢帝國期間,戰功最了不起的,後世為其立傳的,所謂雲台二十八將。其中一位功勞最大的叫馮異,他為人謙虛,生性不喜歡爭功諉過,每當打勝仗之後,大家在爭論誰的功勞最大的場合,他便悄悄地走去大樹下,坐靠在樹幹看天邊。這樣的情況多了,大家就叫他為「大樹將軍」。
馮異打戰時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大小傷口不斷。有天,他死了,他經常去樹下的那棵大樹,所有的樹葉一夕之間掉光,於是史家為他留下了八個字:「將軍一去,大樹飄零!」
我在大一時,中通老師語帶感情地說了這個故事。
我們這一代人,年輕時被灌輸了很多中國式的瀟灑浪漫,加上我唸了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海明威、卡繆……等等,他們描述西伯利亞大草原,我腦海便升起廣漠草原地景或白雪皚皚;他們敘述黑死病屠城,我腦海中浮現彷如武肺在全球最淒慘的畫面,因而「將軍一去,大樹飄零」頓時把樹木的性靈或意識呈現出哀傷美麗的畫面,永遠烙印。
我那時候不瞭解溫帶落葉樹種,在強烈寒流的洗禮之下,是可能「一夕」落光樹葉的,也不會去考據,馮異是否在冬季逝世的,只是陶醉在悲劇的美感之中。
這是人的移情作用,文學的感染效應,不是樹木的情感。
樹有「情感」嗎?人家說:故鄉的樹木記得你,這是一種不是真、假值的真或假,而一半是人的意識投射。(「台灣低海拔的落葉林解說輯」)
§天文、地文、生文與人文
大學四年,我從植物採鑑、社會調查、歷來研究報告文獻的收集與研讀,漸漸釐清自己的志趣,然而,真實影響我的,是無法說明或明說的,就像佛教界唯識等,把人的意識劃分為八或九識,眼、耳、鼻、舌、身、意(志)或思維的第六識、第七識(或潛意識),到第八的阿賴耶識,或意識到能意識的那個主體(純意識)本身,然而,是因為我們現在溝通的工具及思維、心念、知識、經驗等等,是在第六識的範圍,而第七、八識(靈魂、純意識本身)是無法使用第六識去明確說明及理解的,為了可溝通,所以才權宜地劃分為八識,事實上根本無分,所有人為劃分的什麼識,其實都是一體、本一的。
我第一次調查玉山之後,接著首度調查中央山脈秀姑巒山區時,從中央金礦到白洋金礦途中,處在台灣二葉松疏林及滿山遍野的紅毛杜鵑盛花之間,我腦海中萬花的視覺連結到聽覺記憶庫,浮現出熱門搖滾;山徑一轉鐵杉幽林、深澗,又轉為古典如歌的行板,我了悟五識是迅速轉換、互為聯動的。
不只感官識覺交互快速聯動一體,經驗知識記憶海、思維、意識通通瞬息流轉,只因我們要轉換為語言、文字時,必須聚焦,以致於習慣性地將意識現象,狹限在特定的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受覺或思考等。
我們在起心動念、思考時,雖然聚焦在特定的範圍或對象,事實上也是全意識聯動、整體在運作。但是,我們在思考中不僅不會注意到極其錯綜複雜的心識漂流,反而排斥那些內在的「騷動」,甚至斥之為反理性之類的。所以,專注深思是種美妙的單純,也放棄了無限的可能,除非思想沒被自我綁架。
「自我」不是「我」,只是「我」在生長、生活中,經驗、學習而來的知識或資訊、記憶的總和,隨時都在改變。「自我」放下時,那個「我」才會出現,那個「我」才能感覺樹木的感覺、感覺可以感覺的我。
然而,由學習而來的抽象經驗資訊,有時卻是刺激、啟發原「我」的媒介,即使在理性的範圍很難掌握。
在我搜集任何關於台灣植物或生態的文獻過程中,有天我影印了松田英二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發表的一篇短文〈追思相馬先生〉,悼念在採集回來後,以三十六歲英年逝世的相馬禎三郎。
我先前已經轉述了二、三次,我還是要再敘述一次。松田英二寫道:
「……自然的研究當然是一項高潔的志業,我以為世界上沒什麼(比它)更重要的事了。然而,當我目睹『死亡』這個大事實的時候,我似乎被引領著,要去尋求自然研究之上的某種東西啊!
我想五感(官)的研究之外,更需要第六感的探究。西洋有:Be right with God and all will be right的諺語;所謂自然的研究,不是多數人所認為的,樹木與花草的研究;不是石頭與土壤的研究;也不是蟒蛇與蚱蜢的研究,而是透過這些,去敬拜背後的造物主或對神的虔敬。
有人問我採集植物的目的,我以為是這樣的:
進入山林的目的只有一個,
想要看聖父的奇異的事業!(註:原文以日本短歌文體寫的。)
我的目的在此。
說採集、研究,只不過是為了觀察更深奧的,廟堂宮殿之上的『某種東西』的程序而已!
(不是給別人看的,而是為了將來的回憶而書寫。)」
松田英二(Matsuda Eizi;1894-1978年)是長崎人,二十來歲來到台灣,曾任職於總督府殖產局植物調查課、高雄州屏東尋常高等小學校教諭;寫下這篇悼文時,他才二十三歲!
一九二二年,他二十八歲時舉家移民墨西哥開農場,同時研究動植物;一九五一年,他五十七歲時任職墨西哥國立自主大學教授(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一九六○年,東京大學授予名譽博士。
一九五六年,一種墨西哥特產種的仙人掌,以他的姓氏命名為種小名;菊科有一個新成立的屬,以他的姓命名「松田菊屬」(Matudina);還有,有兩種青蛙也是以他為名……
他在台灣的時間不長,松田女貞、松田冬青、松田莢迷以他為名,寒莓(Rubus pseudo-buergeri)的模式標本,是他在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於拉拉山所採集,如今存放在台大原植物系標本館中。
雖然我尚未去搜尋他晚年的作品,但我很想看看他一輩子戮力自然的調查研究之後,回頭看他這篇悼念文時,「聖父奇異的事業」究竟開啟了他心靈何等的向度、深度與靈悟?
我約在二十四歲時,看到松田前輩二十三歲的感受很是激動。我在高中時代極為醉心於哲學的理想與浪漫。然而,我在台大植物系、所,耳濡目染的價值系統中,愈是所謂的典範、表率或是被承認是「大牌教授」的,似乎愈是唯物科學主義者,加上自己本來在高中時代即被中國霸道唯心唯我主義「嚇」到,才會轉向自然科學的,況且台灣人裸真禪的性格,教我識破「中國來台虛假」的一面,所以我從大四開始,自行以台灣自然為師,跑去台灣最複雜的原始森林區,恆春半島南仁山,從山頂殺到溪谷,一草一木測量出平面分布圖,並測度繁雜的各項徵值(parameters)。
那個年代,我每次到野外調查,就是跟真理之神把臂而行,真理之神就是我的拜把兄弟。我的情懷,如同松田氏在說的:「高尚的志業」,而且,是唯物論客觀實物的驗證。
就這樣,從一九七七年到二○○七年,三十年期間,調查、消化台灣歷來幾盡所有植群的報告,一九九四年正式開撰,一九九五年出版第一冊《台灣自然史・台灣植被誌(第一卷):總論及植被帶概論》,二○○七年為止,共計寫成十五冊(註:兩冊未出版),二○○七至二○一九年再增補「生態綠化」及綠島等四冊,總共十九大冊。然而,除了第一冊被《聯合報》選為一九九五年「十大好書」之一以外,四十四個年頭,我最主要的十九冊自然史系列似乎像是從人間蒸發了,一般認識我的,反而是其他七十餘本為環境運動打仗的、教育的、宗教的、自然文學或其他雜文當中,少數的幾本。(「山林生涯路幻燈輯」)
§樹的感覺
我始終將自己立志在一個學習上帝志業的研究者,我投入種種弱勢運動、環境運動、生態教育的流程中,台灣生界是我的後花園、靈糧堂,自然的啟發,隨時隨地逢機逬發,而心智、性靈是沒有年齡的,生、死也不是端點,一個接著一個山林生靈的史詩、故事,都不是給人答案,而是新生的重新出發,我的老話:再老的樹幹,長出的還是嫩枝新葉鮮花,永遠天真,如天之真!
從幼小接受台灣禪宗隱性文化的薰習,到日本、德國科學文化的自我教育,乃至直接投入台灣最真實的,二百五十萬年大化天演道場的教化,我在山林中的驚喜無窮,也不斷地分享給有緣的人。因為我從感官識覺,經思想意志,到主體意識的示現渾然一體(註:我從沒有結合什麼人文與科學、理性與感性、左腦與右腦,或所謂二元論的分別識,我沒有結合,我只是沒有分割而已!)。現今大家好像分不清、搞不懂「主體」跟「自我」是徹底的兩回事。
主體,簡單地說,就是靈魂、能意識到所有意識的純意識本身;「自我」是意識或主體示現、呈現、作用下的,隨時都在變化的經驗、記憶、知識、資訊海。再說一次,放掉「自我」的綁架,讓主體同萬物、萬象對話、聯結。
一九九○年代,我帶人到阿里山進行山林解說,在經過一株空心的台灣紅檜時,我會請大家一一進入樹洞靜坐一下下;又,抱抱這株大樹,體會能夠聽到什麼?
當你願意抱著大樹時,你已經放掉了一大部分的自我障礙。你的皮膚接觸粗糙、冰冷的樹皮時,你可以想像你是樹上的一隻花豹,你可以任意馳騁心念,但只放鬆,然而,你也可以不思不想、不起心動念,進入單純專注。
這時,你的聽覺變得相對敏銳,你可以聽聞鳥叫蟲鳴、遠近諸多聲浪;如果你的心再靜注些,你會聽見微風吹拂枝葉聲,我曾經在不等風力、風向中,諦聽不同樹種的葉樂,最容易區辨者,針闊葉之別,事實上,每株樹各有其音階、調性,多樣非凡;如果你把耳朵壓貼在樹幹上,特定的壓力及角度,如同你枕肱側睡的偶然,或你捂壓耳孔,你立馬聽見自己的心跳、血液流經大大小小血管中的汪洋澎湃,而真正滿聽的,是數不清微血管的合奏;如果你冥想著你擁抱的樹,漸漸止息心念,彷彿入定的時分,你的血管同樹的維管束汁液的流動,彷彿對話彼此的心音而無彼此。
事實上你並不是只在聽取樹木的音聲,你的心肺正在快速繁忙地,同樹的皮孔、氣孔交換氣體元素;你的觸覺、嗅覺、視覺、心念的節拍、每一毛孔,都處於跟環境場域的氛圍交流,你在影響著場域,共同的氛圍也在感染著你。
放下自然、自然放下,你不見得抱樹,你是隨順徜徉在無心無念時,數不清的綠精靈翱翔於自在天,你可以睡著,你可以淨空,不知所終之間,你「知道了」樹同你共同的「感覺」,無法「說」,說無法。
我所領略的,每株樹各有其不同場域的質感,種種味道超越想像。不必搜索你的經驗記憶海,而是接納全然新奇的新經驗。我不可能告訴你是什麼感覺,是你要去告訴你的樹。
我每次上阿里山,頻常會去看看一株老朋友長尾栲。我從它是小樹,看到它撐開了一座樹塔。有時我拍攝他的長尾尖,有時看看它的葉金背。我沒有任何一絲絲想要幹什麼、說什麼。你有如此的朋友嗎?
有次,我前往新竹鳥嘴山,我在一片台灣紅檜及闊葉樹的混生林中,恰好陽光斜射、雲霧瀰漫,一條條光霧柱的水精靈游走,我坐定,環顧一周。這株紅檜樹齡當一千五百年、那株五百歲、另株苗木正茁壯、有株枯立木正分解……密密麻麻的大小樹木,各自且聯結成連動的大場域,美得讓靈魂戰慄。我估算目力所及的大小樹木,它們的樹齡總和超過一萬年,而萬年來這個場域從來沉默,那等美感和力道,只有沉默能解。
我在南一段狂風暴雨的噴射氣流中,體悟自己數十年穿梭數百萬年的大化天演,我明白了自己之所說。我了然台灣的脊稜為何呈現劇烈的鋸齒分布;我感悟山羊、黑熊在此天地家園的「心情」;我知道為何槍林彈雨火海中,生命鬥士唯一的心志就是往前衝,全然沒有生死……
有一回在新仙山頂冷杉林緣大雷雨的暗夜,每當一道閃電霹靂祭起,銀光撲射而來,每株冷杉筆直森列的黑影瞬間羅列,顯影在腦海心靈深處,美到神經錯亂、視覺永駐。
隔天我們冒著暴風雨,搶登東台首嶽新康山頂做調查。我永遠記得雙手抓傘,讓我在筆記本記錄樣區的助理拉・乎以,他割傷手指的鮮血,一滴滴,滴落在我的調查簿上。
調查結束下山,是夜整理樣區資料,我才明白新康山神為何三度阻止我登頂調查,事涉「東台首嶽」的令譽因我登頂而降格,它不是高山!它在演化史上已然脫離高山生態帶。
我從年輕進入到晚年,大大小小山頂的體悟 ,從鼻頭角山岬巔、南岬大尖石山山尖、北大武懸崖絕嶺、各大高山頂天書的展讀,樹木的感覺,如是況味。
我曾經在南仁山頂獨自一人放聲大哭,我歷經野牛陣的包圍、蛇族的威嚇、虎頭蜂的盤旋示警、數不清螞蝗的吸血……,首度登頂玉山,山神的考驗,乃至將近半個世紀兆億山林精靈的賜福,我知道我無能分享屬靈的境界,但我了悟,場域隨著我感染十方。
今年以來,我開始依著自身的體會感受,撰寫個別物種的介紹,且集中在台灣當今的景觀樹種,我的重點迥異於歷來的植物介紹,強調每物種的「質性」,也就是人與樹之間意識流動的映射,當然只限於個人一生跟植物之間的情誼與體悟。長年間,植物投射的場域、況味,乃至它們對人們身、心、靈的影響,大家都忽略最大部分的能量場,通常只看上它們的生殖器官,褻瀆了植物崇高、尊嚴、更龐大的能效。
事實上宇宙萬物皆存有不等程度的「意識」,目前為止,「意識」的開發以人類最為強烈,但人性仍然十分野蠻。意識的覺醒,便是各種宗教的終極目標,也是生靈的究竟。我久參自然禪。感恩樹木賜予我的法喜!
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
菁芳草的黏功
一直擱著、一直擱著,不知不敢或不想明說或碰觸,菁芳草的美感真的吹彈可破,所以我下不了筆。
今天,我再度走向沒有菜的菜圃,被滿滿的菁芳草所盤佔。
我是忍了好長的一段時日,終於狠下心來清除菜圃上的菁芳草,因為我種植的一批白菜、青梗菜,全數被菁芳草所消滅,而它又是那麼楚楚可憐樣,小小的圓卵形對生葉,不只討喜,當水分無虞時,他噴掃眼底的綠,勾魂攝魄;夢幻般的綠,沁入骨髓,以致於我都儘量不置足跡。
可是當我狠狠地清除時,柔弱的草軀頓成繩索般地頑強,它們死纏著地母,彷彿我拉扯的是土地...
推薦序
一生植物情
知名編劇、導演 王小棣
陳玉峯老師人如其名,總是仰之彌高。
他有時像巨大板塊衝撞隆起的地殼,激進昂揚;像切割大地奔流的岩漿,狂野率性;有時像亂世中聳拔峻嶺上一間孤廟裡的高僧,淡定坦然自在。
陳老師說這本書是寫他「一生與植物間的情誼和體悟」,我靜心拜讀,時而傻笑,時而嘆息,這書裡對人世不再苦口婆心、不再辛辣勸諫,只有深厚靈修,簡約行止。在字裡行間分享他走向更高之處的旅程。
他那種對大自然的款款深情,冬日看完掩卷還會隔空透暖,餘波盪漾……
一生植物情
知名編劇、導演 王小棣
陳玉峯老師人如其名,總是仰之彌高。
他有時像巨大板塊衝撞隆起的地殼,激進昂揚;像切割大地奔流的岩漿,狂野率性;有時像亂世中聳拔峻嶺上一間孤廟裡的高僧,淡定坦然自在。
陳老師說這本書是寫他「一生與植物間的情誼和體悟」,我靜心拜讀,時而傻笑,時而嘆息,這書裡對人世不再苦口婆心、不再辛辣勸諫,只有深厚靈修,簡約行止。在字裡行間分享他走向更高之處的旅程。
他那種對大自然的款款深情,冬日看完掩卷還會隔空透暖,餘波盪漾……
目錄
〈專文推薦〉一生植物情 王小棣
〈代序〉《山林書籤》注
第一部 木屋
山居注略
將山居
半工
一株台灣五葉松
家園
日落時和諧永無止境
思維掉落的胎毛
廢墟徹夜未眠
第二部 特寫
山棕
白袍子
菁芳草的黏功
節制的青剛櫟
酒瓶蘭
繞指柔(一)
繞指柔(二)
白雪姬
假寐甜心
菁仔叢
出水蓮葉
蓮花落
蓮說
第三部 隨筆
藍鵲
肥阿猴與草捕鳥
自然的魔術風箱
大珠小珠落自如
生命線
去花
佛從毛孔放光
春紅
斜光
春傷
圖無案
桐花祭
春暮
噤聲蛙夜
一個鳳梨的故事
長園金蛛的迷思
醉果
第四部 話語
溪流
早春與食物
東山飄雨西山晴
神助
見鬼
自證悟
新情也綿綿
真心話大冒險
大自然的話語
乾溪物語
半天一塊碗,雨來沃未滿
「不是我的錯!」
世界盡頭之外
水沖腳
樹的感覺
後註
〈專文推薦〉一生植物情 王小棣
〈代序〉《山林書籤》注
第一部 木屋
山居注略
將山居
半工
一株台灣五葉松
家園
日落時和諧永無止境
思維掉落的胎毛
廢墟徹夜未眠
第二部 特寫
山棕
白袍子
菁芳草的黏功
節制的青剛櫟
酒瓶蘭
繞指柔(一)
繞指柔(二)
白雪姬
假寐甜心
菁仔叢
出水蓮葉
蓮花落
蓮說
第三部 隨筆
藍鵲
肥阿猴與草捕鳥
自然的魔術風箱
大珠小珠落自如
生命線
去花
佛從毛孔放光
春紅
斜光
春傷
圖無案
桐花祭
春暮
噤聲蛙夜
一個鳳梨的故事
長園金蛛的迷思
...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會員均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換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辦理退換貨時,請保持商品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本身、贈品、贈票、附件、內外包裝、保證書、隨貨文件等)一併寄回。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
 4收藏
4收藏

 14二手徵求有驚喜
14二手徵求有驚喜



 4收藏
4收藏

 14二手徵求有驚喜
14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