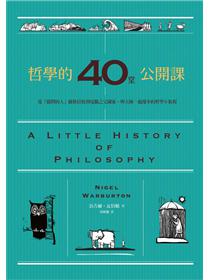如果卜洛克的馬修史卡德讓我們理解紐約的邊緣,
臥斧則是以碎夢系列讓我們理解臺北的道德墮落。趁著颱風天讀完了小說,看到劇情中有太陽花、非法移工、新二代、仲介、外配,感覺滿有趣,應該是目前臺灣的小說中少數可以把這麼多社會議題和多元族群置入的一本小說。──廖雲章
我正在聽莫里森的〈抵達夢土通知我〉。這城對阿嘉莎而言,是她心目中的夢土嗎?現在阿嘉莎去世了,該通知誰呢?
三月某一天晚上,抗議進入第N天,民眾已試圖占領我城的行政機關……然而就在緊鄰的暗巷,在交通事故中失去記憶的主角,遇到了被虐打並割掉雙耳的東南亞移工阿嘉莎,但死的不只有她一個……我城依然持續墮落。
《抵達夢土通知我》是延續《碎夢大道》卻可以單獨閱讀的作品,這個系列中作者臥斧塑造失憶的主角,以一起起親歷事件解剖臺灣社會近年來經常出現的問題。以這個主角為系列的作品,目前處理過街友死亡、都更地區無故起火等議題,夢土則是以移工連續死亡案件為主要梗概。
雙線進行的故事中,有超現實的能力、推理的情節、殘酷的謀殺,以及偏執的愛情,亦會看到移工工作、生活與娛樂的空間如何與城市交疊,並以占領運動為大背景,描繪城市既有在夜店醉生夢死的族群,也有為政治自主而激動的人們。所謂世界,就是眾人夢土的總和。
《抵達夢土通知我》的人物設定
●失去自身記憶、目前為夜店老闆工作的主角,在夜半的街頭救了一個衣衫不整、遭人凌虐的外籍女子,卻被刑警認定為行凶的嫌犯。
●被稱為藝術家、自認是個工匠、來歷不明的男子,透過擁有駭客技術的同志酒保,請主角找尋自己在這城失聯的小妹。
●喜歡古典樂、一心想要成為偉大設計師的學生,在生活中接連碰上不順心的遭遇後,擬出一個報復世界的計畫。
為何要讀夢土
一、從小說瞭解移工
移工在我們社會是如何的存在?即便已經不少試圖去描繪移工處境的研究與報導,但這些文字仍舊無法取代文學能達到的目的,也就是瞭解移工做為一個人,她的情感與夢想,是能更立體地浮現書中移工的形象。
二、從小說瞭解社會
我們每天穿梭生活的城市,其實我們經常並不瞭解這些地方發生過什麼事,文學的作用正在於把事件與人物崁進具體的時空中,並因此形成具體的印象。透過推理案件的疏離感,更能某種程度讓讀者站在旁觀者的位置,重新檢視生活的社會空間。
作者簡介:
臥斧。唸醫學工程但是在出版相關行業打滾。想做的事情很多。能睡覺的時間很少。工作時數很長。錢包很薄。覺得書店唱片行電影院很可怕。隻身犯險的次數很頻繁。出版:《給S的音樂情書》(小知堂)、《塞滿鑰匙的空房間》(寶瓶)、《雨狗空間》(寶瓶)、《溫啤酒與冷女人》(如何)、《馬戲團離鎮》(寶瓶)、《舌行家族》(九歌)、《沒人知道我走了》(天下文化)、《碎夢大道》(讀癮)、《硬漢有時軟軟的》(逗點)。喜歡說故事。討厭自我介紹。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冬陽(馬可孛羅出版副總編輯)
吳叡人(推理讀者/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張國立(作家)
廖雲章(曾協助創辦四方報,現為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譚光磊(光磊國際版權公司創辦人)
廖雲章/曾創辦四方報,現為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移民工的身影往往隱沒在主流論述中,臥斧的《抵達夢土通知我》卻讓移工與所謂新二代以如此激烈的角色出現,令人驚豔的是,作者巧妙揉雜了當代社會運動與移工處境,寫出了這部反映時代的作品,雖是虛構,卻如此真實。
張國立/作家
五具屍體,三名凶嫌。在這塊期待成為夢土的島嶼上,浮現出陰暗的一面。
臥斧抽絲剝繭,尋找真正的凶手,他宣誓的是即使非法正義,也必須維持夢土的純真性。
寫得波折,讀得痛快。
名人推薦:冬陽(馬可孛羅出版副總編輯)
吳叡人(推理讀者/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
張國立(作家)
廖雲章(曾協助創辦四方報,現為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譚光磊(光磊國際版權公司創辦人)
廖雲章/曾創辦四方報,現為獨立評論@天下主編
移民工的身影往往隱沒在主流論述中,臥斧的《抵達夢土通知我》卻讓移工與所謂新二代以如此激烈的角色出現,令人驚豔的是,作者巧妙揉雜了當代社會運動與移工處境,寫出了這部反映時代的作品,雖是虛構,卻如此真實。
張國立/作家
五具屍體,三名凶嫌。在這塊期待成為夢土的島嶼上,浮...
章節試閱
【零】在夜的燥熱當中
在夜的燥熱當中,不知何故,我覺得像個沒娘的孩子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by Ray Charles
1.
摟住她的剎那,我的大腦倏地塞滿互相推擠的疑問,讓不出思考的空間。
她的個子不高,隔著圍住她上半身的大浴巾,我可以感覺到她豐腴肉感的軀體持續顫抖。現在是三月下旬,這城夜半的空氣仍然有點寒意,但在浴巾裡頭,她只穿了貼身內衣褲,我的視線由上而下,可以從浴巾沒遮住的範圍看見深深的乳溝。
可惜我現在完全沒有欣賞女體曲線的興致。
她的顴骨有明顯的瘀青,嘴角破裂,眼眶外圍烏黑腫脹,裸露的手臂上交疊著又紅又紫的色斑,胸前覆著大片血汙。順著血汙淌流的路徑回溯,可以發現源頭來自她的頭部兩側──本來應該長著耳朵的部位,只剩下兩個血洞。
血洞邊緣的皮肉不大平整,可能是外耳先被用力拉扯,再遭到不夠鋒利的刀剪之類器械割除;傷口看起來仍然新鮮,不過從側臉到前胸的血汙都已經乾涸,可以推斷這雖然不是幾分鐘前剛發生的、不過絕對是這幾個小時內才遇上的經歷。
也就是說,我剛才在路邊走來走去、偶爾坐下聆聽短講時,她可能就在幾個街區外被人凌虐。
約莫一週之前,一項極具爭議的法案在立法機構被民意代表以不合程序的手段強制通過。這起事件引發幾個公民團體不滿,集結在立法大樓外抗議,其中有不少成員是關心時局的學生;部分學生趁下班後的立法大樓警備較鬆,潛進議場靜坐,接著其他學生突破警方的封鎖線,占據立法大樓的主要議場。那天晚上,到立法大樓增援的警力數度嘗試攻堅,但學生們用議會裡的座椅阻擋出入口,成功抵擋警方的行動;警方驅離未果,也沒有撤離,開始與學生對峙。
幾個鐘頭內,接到消息的各種公民團體已經在立法大樓外集結,聲援學生的抗爭行動,也有民眾因為擔心衝突升高、學生受傷,於是自動在立法大樓周邊靜坐守望。
接下來的幾天,立法大樓外圍的學生和民眾數量有增無減,各方捐贈的物資、醫療小組、律師團隊也陸續出現,一方面提供必要的援助,一方面也直接表態,支持抗議行動。占領議場的學生代表發出聲明,希望與政府領導人針對法案進行對話,但領導人只在媒體上發言譴責,完全沒有認真面對,情況持續乾耗。
我從新聞裡得知的狀況大致如此。
先前我在網路上看過很多國外的抗議報導,總以為現在的立法大樓附近應該會有氣氛緊繃的警民對峙、警員舉著盾牌揮著短棍、抗議者隨時從地上撿起破磚角或水泥塊奮力丟擲之類的場面。
但等到自己在現場待了一會兒,才發現氣氛與原先想像的不同。
立法大樓外圍靜坐的公民團體正在舉辦短講,邀請各界學者簡單說明法案的問題及行動的宗旨,包括藝人、樂團在內的公眾人物也前來打氣,還有單純關心學生及法案的一般民眾上臺分享自己的觀察和經驗;靜坐抗議的現場,儼然是個難能可貴的街頭公民教室。
我混在人群裡,感覺很奇妙。
除了學生和公民團體之外,看得出來現場還有不少自動自發前來參與的一般民眾,在他們上臺講述自己為什麼到這裡來的短講中,會發現有些人一下班就趕過來的,有些人特地請假、從外地搭車來參加的。
我的工作時間不怎麼固定,完全看老闆什麼時候交辦了多急迫或多複雜的差事,所以理論上有許多空餘時間可以運用;但和這些充滿熱血的行動派不同,我雖然持續關注抗議行動相關新聞,卻一直沒打算來現場聲援。
追根究柢,我不確定這個行動能產生什麼作用。
況且,真到了現場,還發現整個行動比想像中平和太多。
議場不可能一直占著,政府目前的應對方式看起來就是持續拖延,時日一久,這場運動的能量大約就會耗盡。
但我的同事猩猩不這麼想。
猩猩身材高壯,鼓脹的肌肉似乎隨時會繃開勉力勾著釦眼的襯衫鈕釦,他和我一樣為夜店老闆工作,負責的是代客泊車、管控入場秩序,以及處理隨時可能發生的各類麻煩──簡而言之,猩猩是夜店的圍事,每個晚上都有固定的上班時間。
去年獨力撫養猩猩長大的祖母過世,原因與猩猩老家的果園農地被徵收有關,自此之後,猩猩就開始注意各種公民團體的活動,他認為祖母在世時他沒能幫什麼忙,至少可以替其他被公權力壓迫的人盡點力。
是故,從公民團體占領議場那晚開始,猩猩每天都到立法大樓外頭報到。
「現場人數愈多,條子愈不敢用太過激烈的手段強制驅離;」猩猩告訴我,「議長不就公開說不會派警力對付學生了嗎?證明我們在那裡守著,是有作用的。」
我認為議長的公開喊話原因沒那麼單純。眾所皆知,目前的執政黨中存在許多明爭暗鬥,議長與執政黨黨魁不合根本是公開的祕密,所以,議長的舉動說不定只是鬥爭手段之一。不過猩猩十分認真,我也認為沒必要潑他冷水,身為朋友,我能做的就是幫他站在夜店門口代班。
但遇上週末,猩猩就很難請假。
週六週日夜店一向很忙,尤其是午夜前後,狀況常常很多,有時猩猩和另一名圍事金毛忙不過來,還會找我去幫忙──幾個小時前我在夜店附近吃晚飯時接到猩猩的電話,本來也以為他要找我去店裡支援。
「你能不能到抗議現場去一下?」猩猩在電話裡問,「我現在走不開。」
猩猩告訴我,不久之前,一群抗議人士衝進行政大樓。行政大樓與立法大樓只隔幾條街道,目前立法大樓外的靜坐和短講仍在繼續,但有人通知猩猩,希望盡量找人到場。
「我擔心會出事;」猩猩道,「幫我個忙,去現場看看。」
雖然到了現場,但我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只能到處晃來晃去。圍牆上、人行道上、天橋的樓梯欄杆上,甚至帶刺的蛇籠拒馬上,都貼著許多諷刺執政當局的漫畫及標語,走在其中,似乎正在參觀大型的公共藝術展覽。一個短講剛結束,主持人提及行政大樓附近警力明顯增加,鎮暴水車也已經出動,呼籲大家不要使用暴力、注意自身安全。
我離開靜坐隊伍,走到行政大樓附近張望,行政大樓裡頭傳出用大聲公演講的聲音,配備盾牌和棍棒的警察數量的確變多了,但看起來還算穩定,雙方沒什麼火藥味。過了一會兒,一部分原來在立法大樓外圍的群眾也移到行政大樓附近繼續靜坐──大家的想法可能和猩猩類似:人數愈多,警方愈不可能硬來。
時間接近凌晨一點,現場看起來仍然平和,我判斷不大可能發生衝突,猩猩大約是多慮了。我用手機發訊息告訴猩猩說現場沒什麼問題,想了想,決定走一段路到健身房,做完例行運動,再回住處睡覺。
繞過兩個街區,我拿下口罩,拐進一條巷子,然後遇上她。
2.
附近街道的路燈昏暗。我先注意到從不遠處走來的她腳步不穩,再發現她居然沒穿鞋子,接著驚覺:她披著一條浴巾、光裸著腿,半夜如此在外獨行,一定遇上了什麼事。
我趕前兩步,她看見我,踉踉蹌蹌地跑了起來;我加快腳步,她撞進我懷裡,喘著氣快速說出幾句話,接著昏了過去。
那幾句話的發音不怎麼標準,夾雜一些帶著口音的英語,加上她的淺棕膚色與五官樣貌,我猜她來自東南亞國家,可能是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菲律賓;她是個嫁到這城的外籍新娘?還是個來這城工作的外籍幫傭?她剛才那幾句簡短的話,反覆講的是「救命」、「恐怖」,以及「我被攻擊了」。她是不是和夫家或雇主起了什麼爭執?她做了什麼事,才會被人虐打、割下耳朵?或者這和夫家或雇主無關,而是她倒楣遇上了壞蛋?
我擡起頭,路上看不見血跡,無法判定她是從哪一棟樓房裡逃出來的;這一帶的建物全是舊公寓,彼此之間挨得很近,巷弄靜謐,我沒看見有人追她,也看不清對她施虐的人是否躲在暗處。我皺起眉,忽然察覺懷裡的她顫抖幅度變大,開始抽搐。她的傷勢比我看見的情況更嚴重,我看不見的部位,一定也遭受了暴力攻擊。
危險。我把顱腔裡不停出現的疑問掃開,掏出手機撥一一九,快快地說明有個傷患急需救助,講了大略地址。
「我們馬上派車過去;」接聽的男子聲音保持平穩,「不過你所在的位置附近有抗議行動,救護車可能得花點時間才到。」
「多久?」
「大概二十到三十分鐘。」
半個小時?她的狀況可是分秒必爭。「最近的醫院?」我問。
電話那頭講了醫院地址,我估算一下,如果撐一下,我應該可以在十分鐘內趕到。
事不宜遲,我把她攔腰抱起,撒腿就跑。
附近道路晚上人車不多,我沒理會沿途的六個紅綠燈,抱著她直接衝進醫院急診室。
值班的護士明顯被我嚇了一跳──我大半夜裡戴著墨鏡,張口喘氣,講不出話,看起來就是個危險人物;不過我臂彎裡的傷者立刻吸引護士專業的注意力,護士拿起電話,兩名醫護人員馬上推著病床出現,將她送進急診病房。
我沒看錶,不確定自己跑了多久,但應該已經超過原來估計的時間;因為雖然我為了節省時間違反交通規則地大闖紅燈,但她比我想像得重多了。手臂上的負擔一鬆,我彎下腰呼呼喘息,幾乎無力擡起。我一面試著緩下心臟幾乎撞開胸骨的劇烈跳動,一面思索:自己是否應該要增加在跑步機上運動的時間和重量訓練的強度?
這思緒其實可笑,因為我不可能常常遇上這種突發狀況;不過身體的運動暫停、腦袋的轉動開始,抱著她狂奔時切進腦子裡的雜亂影像,便重新聚焦。
3.
兩年多之前,我遇上一場火車出軌意外。
火車中段的兩節車廂猛烈扭曲,力量大到數名乘客被拋出車外,我也是其中之一。我飛得最遠、臉朝下著地、滾了幾圈之後鼻子和額頭蹭著沙礫滑下邊坡,很不合群地離開事故現場,沒被趕來的急救隊伍發現。要不是老闆當時正好駕車經過下方公路、停下來查看,我可能就會在草叢裡躺到停止呼吸。
我的口袋裡沒有任何身分證件,清醒之後想不起自己是誰,除了老闆,住院期間沒有別人來探望過我。老闆替我墊了醫療費用,要我出院後到夜店工作、分期償還,還在夜店地下室騰出一方空間當我的住所;對我而言,老闆不但救了我的命,還提供了延續這條命的重要助力。
出院後我常覺得身體不聽使喚,於是開始持續運動;飛出車窗、滾下邊坡後留在身體上的傷害大多已經痊癒,只留下臉部上方橫七豎八的疤痕,以及在翻滾時不知頸部撞上什麼而受損的喉嚨──這兩個問題都不難應付。只要出門,不管白天黑夜,我都會戴上運動型墨鏡遮住傷疤;至於說起話來粗嘎可怕的情況,只要我少開口就不會嚇到人。
幸好我本來就不喜歡說話。
那場意外後最古怪的一件事,是我發現自己有閱讀他者記憶的能力。
我不確定這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還是意外後才出現的異能。只要我用手指接觸他者,就可以拉出由他者記憶凝成的晶亮絲線。最初我發覺只要能將糾結的絲線理順,被我拉出絲線的他者就能做場好夢,所以將這些絲線命名為「夢線」;但過了一陣子,我發現只要集中精神,我就能經由夢線讀到他者的記憶。
經過實驗,我歸納出這個能力的限制:首先,我必須接觸到他者的肌膚,如果隔著衣物,無論材質或厚薄,這個能力都無法啟動;再者,他者必須處於失去意識的狀態,如果他者是清醒的,這個能力就沒有作用。
最後,也最諷刺的,是我沒法子用這個方法讀自己的記憶。
或許這是因為第二個限制──我不可能在自己失去意識的同時集中精神閱讀記憶。
也或許這個能力就是如此。
除了我之外,沒有別人看得到夢線,這件事聽起來匪夷所思,所以我沒有告訴任何人。夜店的同事並不知道我是個沒有過去的人,唯一知道這件事的老闆,也不知道我有這種異能。
方才抱著她狂奔,我沒有餘裕、也沒有打算閱讀她的記憶──記憶畢竟私密,我給自己定了規矩,如非必要,不會主動去做這件事;但在到達醫院之前,她的記憶卻片片段段地撞進我的腦海。可能因為她受虐的記憶滿載激動的驚恐情緒,所以強制啟動了我的能力;可能因為她在我奔跑的途中時昏時醒,所以我讀到的記憶也就斷斷續續。
如果從剛才讀到的幾個片段推測,她的記憶不大連貫的原因還有一個可能:在被虐打之前,不管是自願還是被迫,她都使用過某種迷幻藥物。
閱讀記憶的過程像闖進電影已經播到一半的劇院,但除了看到沒頭沒腦的影像之外,我還會聽到、聞到、感覺到他者經歷該段記憶時,五感所接收到的一切訊息,以及像電臺雜訊似的思考加注。
她的記憶,是段意識不清時看到的恐怖電影預告。
4.
她身處一個不大的房間,光線微暗但是溫暖,沒看到窗戶,一面牆上掛著幾個鑲著玻璃的木框,從厚度看來不像是繪畫作品,而像是小小的標本箱;玻璃的反光和她模糊的視線,讓她依稀看見標本箱裡展示著的東西,似乎是展翅的蝴蝶。她躺在地板上,整片地板都鋪著地毯,躺在上頭的感覺蠻舒服的,只是她認不出這是哪裡,又意識到自己的手腳都被綑綁,心情完全輕鬆不起來。
越過房間與蝴蝶標本相對的,是幾個挨著另一面牆壁擺放的唱片櫃,唱片數量很多,除了CD,也有黑膠,看得見的牆面上沒有壁紙,貼滿厚厚的灰色吸音棉;她遲鈍地轉動脖子,我看見一個單人用的懶骨頭沙發。整組播放器材架在對面的牆邊,包括一個大尺寸、幾乎占滿小小牆面的薄型螢幕,以及安置在角落的巨大名牌音箱。
這是一間精緻講究的小視聽室。
音箱裡傳來的旋律有點哀傷,也有點緊張,時響時靜的鋼琴伴奏急急地持續,一個乾淨的男聲用聲樂唱腔吟唱,我聽不懂歌詞,只覺得聽起來像是德文。
這是我綜合幾段紊亂紛雜影像得出來的印象。她的感官有時清醒有時昏沉,眼中看見的顏色有時正常有時怪異,空氣的味道聞起來很普通,倒是那段不斷重覆的歌劇還算清楚。
唱片櫃一側的牆面有個銀色的弧狀圓柱,我花了點時間才看清那是個喇叭鎖門把。門把轉動,灰色的隔音棉整齊地切出一條線,一個人走進房間。
那人身高中等,身形看得出是名男子,不胖不瘦,沒什麼特色,穿著每家便利商店都會販售的抛棄式廉價雨衣
怪異的是,那人戴著一個馬頭面具。
面具不是只蓋住臉部的簡單款式,而是包裹住整個頭部的頭套,棕色的馬頭頂端和後頸還加了鬃毛。馬嘴半開,兩眼圓睜,本來應該滑稽好笑的表情,在這樣的場景裡顯出一種詭異的驚恐。
馬頭人抱著一捲透明的塑膠布,用鼻音哼著歌;雖然隔著頭罩,但仍聽得出馬頭人哼的就是音箱裡播放的旋律。馬頭人放下塑膠布,掏出膠帶和剪刀,她和我同時緊張起來。不過馬頭人沒看她,自顧自地拉開塑膠布,剪下大大的一塊。
她情緒稍鬆,又昏睡過去。
下一段記憶開始,她感覺到自己被推著滾了幾圈;還沒弄清楚發生什麼事,她又被滾回原處,身體與地毯之間,多了塑膠布的觸感。她睜開眼睛,看見馬頭人背對著她,正在把覆滿房間地面的塑膠布沿著牆腳貼牢。她眨眨眼,發現整個房間都已經貼滿塑膠布,唱片櫃、標本盒、播放器材和音箱全都被塑膠布蓋住。
馬頭人完成工作,拍拍手,站起身子,轉頭俯身,湊近她的臉。
她看見面具上方圓凸的假眼似乎正無神地瞪著天花板,馬頭黝黑的鼻孔正對自己;她張開嘴,無法控制地發出尖叫。
馬頭人似乎一點兒也不意外。她幾乎聽得見頭罩裡頭發出一聲短笑。
那是一種大權在握、成竹在胸的輕蔑笑聲。
她深吸一口氣,還沒發出下一輪尖叫,馬頭人的拳頭已經揮下。
5.
我得到的記憶資訊只有這些。
沒有房子的外觀、也看不見馬頭人的真正長相,不知道她當時身處哪棟建築、也不知道馬頭人的身分。雖然我讀到的記憶或許能夠為找出這個戴頭套的施虐者提供助力,但資訊太少,用處不大。
而且,我要怎麼告訴警方這些訊息?
警察先生,您好,我在離開抗議現場的時候救了這位小姐。雖然她陷入昏迷,但我恰好有可以在人家失去意識時閱讀人家記憶的超能力,所以從她的記憶裡得知,她應該是在一間小視聽室裡被一個戴馬頭頭套的男人虐打的,這男人可能很喜歡一闕聲樂樂曲,因為他施虐前邊聽邊哼,只是我不知道那闕聲樂的曲名,也不知道唱的是什麼。
別鬧了。警察根本不會理我。
其實警察也不需要我多事。等她醒來,就能提供相關資料;不管她是自願服藥還是被人下藥、是與人發生爭執還是被人綁架,這都是警察該去處理的問題。
再怎麼說,查辦這宗施暴案件都比在立法大樓或行政大樓與學生和公民團體對峙來得理所應為。
我直起腰桿,走到急診櫃檯另一邊的飲水機喝水。醫院的丟棄式紙杯容量很小,我連著喝了三杯,看看手錶,已經快兩點了。我一面倒第四杯,一面考慮:負重跑了這一段之後,還要去健身房做重量訓練嗎?
刺耳的警笛聲忽然由遠而近衝來。
我轉過頭,看見門外出現兩部救護車,醫護人員正十萬火急地將傷患搬下車、送進急診室。
經過我眼前的傷患,個個頭破血流,似乎受的都是外傷;大多數年紀不大,有幾個上臂或頭部綁著在靜坐抗議會場常見的黃底黑字標語布條。立法大樓或行政大樓那裡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抬頭望向架在天花板下方的電視螢幕,小小的螢幕裡正在進行直播;字幕告訴我,警力已經進駐我剛離開不久的抗議現場,開始強制驅離,但無聲的影像只看見靜坐群眾,沒看到驅離畫面。
只是強制驅離,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傷患?
一週前靜坐抗議活動開始後,就有熱心的網友每天到現場進行直播,直播的畫面通常比媒體的直播車更快速,也更多元。我想起這事,掏出手機,快快找到其中一個直播頻道。
我皺起眉頭。
不是因為直播畫面晃動得太厲害。而是因為直播內容看起來太震撼。
幾個鐘頭前我還想著:這城的抗議行動真是和平,與國外街頭抗爭的照片完全不同;但現在手機裡出現的景象,比那些照片更誇張。
警察將手臂勾在一起的靜坐民眾一一扯開,抬離道路──這種情況很正常,一般而言,警方會把抗議人士抬到較遠的地方,如果警力充足,警方還會把抗議人士用車載走,讓抗議人士沒法子馬上回到現場──讓我覺得震撼的,是警察將靜坐民眾或拖或抬地拉扯一段距離之後,把他們扔在地上。
接著,警方舉起棍棒盾牌,開始痛毆。
【零】在夜的燥熱當中
在夜的燥熱當中,不知何故,我覺得像個沒娘的孩子
──〈In the Heat of The Night〉by Ray Charles
1.
摟住她的剎那,我的大腦倏地塞滿互相推擠的疑問,讓不出思考的空間。
她的個子不高,隔著圍住她上半身的大浴巾,我可以感覺到她豐腴肉感的軀體持續顫抖。現在是三月下旬,這城夜半的空氣仍然有點寒意,但在浴巾裡頭,她只穿了貼身內衣褲,我的視線由上而下,可以從浴巾沒遮住的範圍看見深深的乳溝。
可惜我現在完全沒有欣賞女體曲線的興致。
她的顴骨有明顯的瘀青,嘴角破裂,眼眶外圍烏黑腫脹,裸...
目錄
【零】在夜的燥熱當中
【一】一夢之逝
【二】失蹤女孩
【三】在這城聖人難以生存
【四】嗎啡姊妹
【五】當聖者踏步前行
【六】另一個日子,另一名死者
【七】魔王
【八】壞損的心何去何從
【九】拷貝貓
【十】抵達夢土通知我
後記 或許某日,我們終會抵達夢土
【零】在夜的燥熱當中
【一】一夢之逝
【二】失蹤女孩
【三】在這城聖人難以生存
【四】嗎啡姊妹
【五】當聖者踏步前行
【六】另一個日子,另一名死者
【七】魔王
【八】壞損的心何去何從
【九】拷貝貓
【十】抵達夢土通知我
後記 或許某日,我們終會抵達夢土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