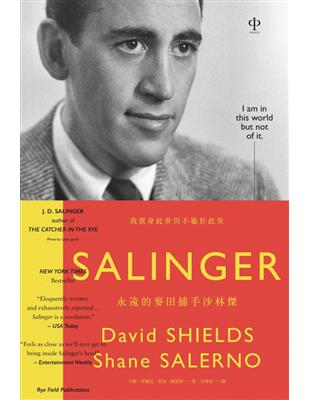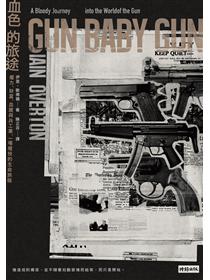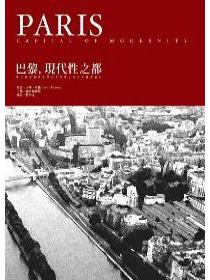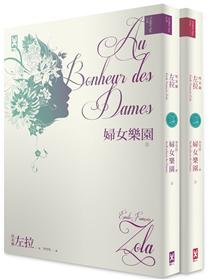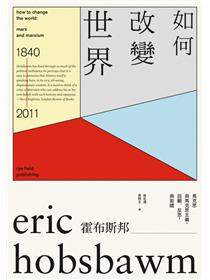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沙林傑以十年的光陰撰寫《麥田捕手》(The Cather in the Rye),隨後終身悔恨不已。
在發表《麥田捕手》之前,沙林傑是二戰退伍軍人,深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之苦,戰後不斷尋覓療癒心傷的良方。自描繪「預科高中男生」的小說《麥田捕手》爆紅後,一則神話隨之而生:沙氏猶如主人翁霍爾頓,生性太敏感,碰觸不得;心地太善良,不適合俗世。神話的自己與現實的自己相互牴觸,為了折衷兩者,沙林傑用餘生屢屢嘗試,屢屢失敗。
《麥田捕手》銷售量突破六千五百萬冊,每年更以至少五十萬本的數字累積中,是跨世代經典,也是屹立不搖的美國青少年圖騰。沙林傑畢生著作不多,僅發表四部頁數偏低的小說,但這些作品對當今文壇的文化影響力與滲透力少有人能出其右。由於沙氏封口不語,半世紀以來,文評與書迷僅能從其文拼湊其人之相貌。沙林傑走出個人的生涯路,執迷保護個人隱私,不遺餘力捍衛他拒不曝光的大批私房著作,再再為其傳奇色彩構築密不透風的城牆。
沙林傑生性極其複雜,而且嚴重自相矛盾。多數人認為,沙氏終老之前深居簡出長達五十五年,其實不然;他的足跡廣泛,用情對象眾多,不乏維繫一生的友誼,大量接觸通俗文化,也常做出他藉小說批判的許多言行。他非但不是隱士,反而常與外界對話,以強化外界對他隱居的觀感。他追求的是隱私,隱士生活導致他惜字如金,世人卻將他與惜字如金的態度畫上等號,如同將他和《麥田捕手》一書視為密不可分一樣。在這種迷思的籠罩下,生活與創作必定難上加難,各界對此現象多有著墨,這也是不爭的事實;至於沙氏在這方面順水推舟的心意多寡,且讓本書帶讀者認識。
坊間書寫沙林傑的著作可略分為三大類,一是學術界的論述,二是必然高度主觀的個人回憶錄,第三種是傳記,若非過度尊崇沙氏,就是對他怨怒滿溢,這類傳記礙於採訪關鍵當事人不易,退而求其次,援引公認是事實的資料,失之於以訛傳訛。普林斯頓大學與德州大學奧斯丁收藏有沙林傑的文書與未付梓手稿,數量相對少,好比一口淺井,先前的傳記多數從中反覆汲取,訛誤資訊也因而再三流傳。本書節錄的沙林傑書信遠自一九四○年,近至二○○八年,對象包含摯友、數十年間交往的女伴、二戰袍澤、心靈導師等等,絕大多數的信件至今從未曝光。
本書的著眼點有三:探究沙林傑不再出書的內情、為何自我封閉、近四十五年來有何創作。九年多來,我們足跡遍及五大洲,訪問超過兩百人,其中許多人之前一直拒絕接受正式訪談。全數受訪者的訪問皆無預設條件。我們的目的是針對傳主沙林傑提供多重觀點,呈現受訪者的第一人稱敘述,這些人包括他長年保持聯繫的反情報隊弟兄,以及他的情人、朋友、照顧者、同學、編輯、發行人、《紐約客》同事、仰慕者、批判者。另有多位名人也暢談沙林傑對他們人生、事業還有社會文化的影響。
本書刊載一百餘幀相片、節錄日記、隨筆、信件、回憶錄、法庭紀錄、證詞,以及近年解密的軍方資料,希望藉由這些前所未見的資料澄清諸多事實,揭露重大隱情。沙氏後半生遁世離群五十五年,傳記作者不得其門而入,本書對這段時期尤其關照。
儘管如此,撰寫本書期間,我們遭遇到兩大障礙:一是幾位關鍵人士早走了一步,二是部分家屬起初表示配合,沙林傑家族最終成員並未接受正式訪談。儘管未能直接採訪親屬,我們仍設法蒐集他們的言論,有些是公開發言,有些是我們取得的私信與從未付梓的文件,經我們抽絲剝繭後,這些人的原音散現於本書各處。除此之外,許多不願接受訪談的人士轉介了關鍵資訊,並且提供他們終身保密的相片、信件、日記;最重要的受訪者當中有六位是在沙氏去世後才願意接受訪問。
本書也呈現十二段「與沙林傑對話」,跨時逾半世紀,對話的一方是文字記者、攝影、尋道者、書迷、家庭成員,另一方則是天天過著反情報士生活的沙林傑。透過這些對話,讀者能步步親近這位堅決拒人於千里外逾半世紀的作家。
*
沙林傑的人生有兩大分水嶺:第二次世界大戰與吠檀多的研修。二戰搗毀了他的身心,卻也造就一名大文豪。宗教提供他生而為人所需的慰藉,卻也斲喪他的才情。
本書的主人翁是從戎不投筆的軍人,在二戰死裡逃生,卻從未全心擁抱生存的喜悅;他是曼哈頓豪宅出身的混血猶太人,戰爭近尾聲時才覺醒身為猶太人的意義。本書探討他如何藉文筆重塑身心俱殘的自我,成為二十世紀文壇巨擘,隨後又透過宗教信仰自毀文采。
沙氏生來具有一種難以啟齒的缺陷,在心靈上形成畢生揮之不去的陰影。他大學中輟,是個善變的才子,直如費茲傑羅筆下自以為是的時尚少爺,堅決要成為大作家。尤金.歐尼爾(Eugene O’Neill)可說是美國最偉大的劇作家,家有絕色千金烏娜,曾與沙林傑交往。沙氏曾在《週六晚郵報》(Saturday Evening Post)與其他以銅版紙印刷的「俗誌」發表短篇小說數則。戰後,沙林傑全面封殺這些作品,拒絕讓這幾短篇再版。戰爭扼殺了戰前的那位作家。
沙林傑在第十二步兵團擔任上士,於一九四四至四五年間,在歐洲戰區親臨五場浴血戰。身為反情報士,他負責訊問戰俘,出入盟軍與德軍之間的無人地帶從事諜報戰,針對百姓、傷兵、叛徒、黑市商賈進行情蒐,曾親眼看見戰火蹂躪的焦土。戰爭末期,他與一群軍人進入考夫囹四號監獄(Kaufering IV),亦即達郝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的附屬單位。沙林傑見證考夫囹的慘狀後,旋即躺進紐倫堡平民醫院,淪為二戰最後一場慘劇所殘害的心理傷兵。
大戰方酣時,以及戰後住院期間,置身屍首製造機裡的沙林傑帶著私人護身符:一部小說的頭六章,主角名叫霍爾頓.考菲爾德,是《麥田捕手》一書的雛形。《麥田捕手》重新界定了戰後的美國社會,從戰爭的角度閱讀此書,最能理解故事的內涵。世人一廂情願相信,文壇能堅守英勇崇高的理想,但走出戰場的沙林傑不以為然。沙林傑不像諾曼.梅勒、詹姆斯.鍾斯(James Jones)、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並沒有發表戰爭小說,而是將戰爭創傷嵌入一則表面上看似成年洗禮的故事。《九個故事》(Nine Stories)亦然,內涵仍是戰後創傷:第一則故事就有人尋短,中間自殺差點成功,最後的故事再度以絕路收尾。
身受重創(為害者不僅是戰爭)的他變得麻木不仁,渴望看見、感受到萬物的和諧一貫性未果,只好選擇自絕於所有人的痛苦之外,只正視個人的心傷,而這份心傷先是沉痛難以負荷,後來全面盤踞他的心靈。再婚之後,他逐步拉開與家人之間的距離,蝸居於獨棟碉堡中,一躲數星期不見人影,並叮囑髮妻克萊兒(Claire)、兒子馬修(Matthew)和女兒瑪格麗特(Margaret):「除非房子失火,否則不准打擾我。」他藉小說謳歌叛逆的特質,膽大的瑪格麗特也具備幾分叛逆,他卻對女兒疏遠得令人心寒。他藉文字塑造出葛拉斯兄弟姊妹法蘭妮、卓依、希謨爾,儘管(或正因為)這些人頻頻鬧自殺,竟然比有血有肉的家屬更令他萬分傾心。
沙林傑猶如落水人,死命賴著救生筏,與塵世漸行漸遠,戀棧愈來愈抽象的範疇,遁入吠檀多哲學,尋求宗教的撫慰:人非肉身,人非心智,棄絕富貴名望。「超脫吧,朋友,唯有出離超脫(detachment)」,他在〈卓依〉一文寫道。「無慾。『斷絕所有遐念。』」他的作品依循這種玄實概念的主軸,每發表一本書,就更加深以散布教義為個人職志的信念。
沙林傑的藏書庫將在本書末章開啟,讀者可一窺足以界定沙氏本性與寫作生涯的點滴,但找不到可以詮釋其人性情的「天機」。找得到的是一連串環環相扣的事件,從生理到情史,乃至於戰爭、名望、宗教,一一由我們揭露、追蹤、連結。
沙林傑開創了一片私人天地,裡面的萬物皆由他宰制,讓他得以從二戰的苦難淬鍊出精純不朽的藝術。其後,當所有的苦痛蓄積成沉痾令心思細膩的他難以承受,因而失去對一切的掌控,他於是徹底投效吠檀多,踏入長年與幽靈周旋的後半生。他對普天萬眾再也無言可傾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