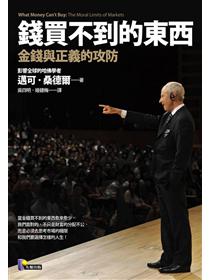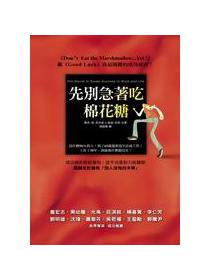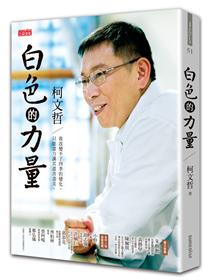〈幸福的滋味〉
屏東盛產洋蔥,品種很多,有的甘甜爽脆,有的辛辣夠勁。小時候家裡似乎從不缺洋蔥,南部的親戚來台北看爸爸,總是會帶著一些土產的洋蔥當伴手禮。
爸爸很喜歡吃來自家鄉的洋蔥炒蛋,我們家的小孩對洋蔥雖不排斥,但也沒有特別喜歡。家裡至今流傳著一個笑話:爸爸以前除了資助屏東的美和青少年棒球隊外,每次棒球隊的人來台北找爸爸幫忙,爸爸都會招待他們。有一次,一位棒球隊的小球員來台北,爸爸很熱情地招呼小朋友,問他想吃什麼時,這位小朋友說:「什麼都可以!但拜託不要給我洋蔥炒蛋!」
每次在家裡講到這件事時,我們家人還是會笑成一團。
我們家一向是媽媽燒飯。有一天,媽媽不在家,只有我和爸爸兩人在家。到了用餐時間,才發現媽媽也沒有安排,我和爸爸兩人只有面面相覷。這時,我肚子不爭氣地「咕嚕」叫了一聲,爸爸嘆了一口氣,站起來,鑽進了廚房。
過了沒多久,爸爸端出了一盤香氣四溢的洋蔥炒蛋。我們倆找出剩飯,配著洋蔥炒蛋,兩個人低頭扒飯都沒有說話,安靜地吃完那一餐。
這是爸爸唯一為我做過的一道菜。記憶中,那道洋蔥炒蛋的味道很香、很好吃。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洋蔥和蛋的香味,更記得安安靜靜和爸爸在屋子裡的氣氛。
可能因為受日本式教育,爸爸平常很嚴肅;但或許因為我是老么,又是女孩子,爸爸對我比較溫柔,從來沒有處罰過我。他還會自己動手做玩具給小孩,那是一般人沒有的「手工玩具」。像現在流行的可以載人的玩具小汽車,當時爸爸就做給我們玩了。小孩子可以坐在上面,用腳一踩,車子就會動。而且,他還把小汽車的後面做成消防車的樣子,裡面可以再站兩個小孩,我們就在裡面享受小小的快感。
從小我們就知道,爸爸不讓我們養尊處優。陽明山的冬天又濕又冷,有時候早上的氣溫才五、六度,他就會把我從床上挖起來,叫我洗車,每每洗完,我的手已經凍得失去知覺。
儘管嚴格,爸爸卻帶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和安全感。我在冬天早上要開車去學校時,車子常常無法發動。爸爸就會起個大早,拿了吹風機,對著起動馬達和線路吹,然後再幫我把汽車發動。我永遠記得他蹲在地上拿吹風機的模樣。
我的父母都很堅持,即使負擔得起,也不送我們去私立的貴族明星學校。爸爸認為,念公立的中小學,可以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家庭背景的人,對這個社會會多一份真實的感覺。
上大學時,從陽明山到台大,路程遙遠,搭公車來回,一天得花上三小時。爸爸替我買了車,但並非外界所流傳的進口好車,只是一輛國產車,作為上學的交通工具。但他規定:不是上學,不能開車。理由很簡單:車子只是給妳上學用的。他堅持小孩子不能開太好的車,但偶爾也會因為寵愛小孩而做出調整。我從英國回來,在政大教書,他給了我一輛很舊的車,開了一陣子後,有一天,他突然開了一輛進口車回家,看到我,就把鑰匙拿給我說:「這輛車是妳的!」其他什麼也沒說。有些感情是不太需要說出來的,我跟爸爸都很清楚這一點。
11 嘿!妳這個笨女人
〈我是1.5個博士!〉
雖然我的博士論文寫得快,但老師大都很忙,要讓他們把整本論文好好看完、審查完,可要花不少時間。我把論文交上去後,過了半年,才得到論文口試的機會。
口試那天,姊姊特地從台灣飛來陪我。雖然我很緊張,但口試過程很順利,沒有花太長時間,我坐在外面等委員會的決定;本來覺得口試順利,問題不大,但等了兩個多小時後,卻依然不見動靜,我開始緊張起來,坐也坐不住了,在那裡開始胡思亂想:「為什麼讓我等這麼久,難道他們不打算讓我過嗎?」「是不是要當掉我?」
正在緊張的時候,忽然見到我的指導老師探出頭來,對我招手:「蜜斯蔡,妳進來一下。」我快步走過去,看到老師臉上的笑容,我的心還放不下來。走進房間,老師先向我道歉,解釋說委員會花了很多時間討論、辯論,「我們討論了很久,但不是討論要不要給妳博士學位,而是無法決定該給妳一個博士學位,還是兩個?」
討論到最後,論文委員會決定授予我一個半的博士學位:一個法學博士學位,上面並加註了我「對於國際貿易有很強的學術背景」,相當於半個國際貿易學的博士學位。
〈一語罵醒夢中人〉
聽到這麼好的消息,我實在太高興了。當我去拜訪學校另一位教授時,我忍不住告訴他,我剛才通過了審查,拿到博士學位。他馬上就恭喜我,並說:「那麼,妳也是一位博士了。」
在重視知識分子的英國,博士的頭銜雖非萬能,但表示了肯定。那一句「妳也是一位博士了」載著我,讓我全身輕飄飄的。
我真的很高興,無法靜下來,就走出校門,上街閒逛。過馬路時,因為沒注意來車,差點被一輛敞篷跑車撞個正著。車子快速擦過我,我也嚇出一身冷汗。這時,敞篷車的駕駛探頭出來,是一名龐克打扮的年輕女子,她指著我的鼻頭,大罵:「妳這個笨女人!」(You stupid woman!)然後揚長而去。
被這意外一打擾,我忽然掉回現實,原來學術和生活還是有落差的。我開始想:「已經是博士了,接下來要做什麼?」
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我有一種瘋狂的想法:很想把博士論文燒掉,然後從此不再看法律的書,因為我已經受夠了。我四處去旅行,還想到新加坡大學去教書,不知過了多久,爸爸終於在世界的某個角落找到我,他打電話叫我回台灣。
17 一婦當關
〈媽祖大? 還是蔡主委大?〉
在推動小三通的過程中,有一個引起熱烈討論的是「宗教直航」。台中縣大甲鎮瀾宮經過連續二個「筊杯」獲得媽祖「聖諭」,決定搶在小三通前,於二○○○年七月十六日從台中港起駕前往大陸,前往湄州謁祖、進香。
問題來了,在小三通前可不可以讓神明先通?這個議題涉及宗教、政治、兩岸,而且預估進香團的人數在三千人以上,迅速成為熱門話題。
陸委會對宗教直航抱持積極正面的態度。雖然「離島建設條例」已賦予離島小三通法源,但宗教直航涉及台灣本島與中國的直接往來,因此應納在大三通架構下考量。在缺乏法源依據下,而且在小三通還沒有完全規畫好之前,不可能大規模實施宗教通航。
當此事在立法院提出後,引發了朝野立委「人神交戰」的議論。多位民進黨立委要求我堅守決策立場,不應讓宗教團體假借擲筊、神諭等藉口來要脅政府。我也表示不會在壓力下同意無法源依據的宗教直航。
但接著在野黨立委質詢我,這是否表示蔡英文對信徒們的擲筊不高興?「還是擲筊有兩個媽祖,另一個是蔡英文,擲完媽祖的筊之後,還要擲她(蔡英文)的筊?」
另一位委員在質詢時更突然爆出這麼一句:「究竟是媽祖大?還是蔡主委大?」
這時不管說誰大,接下來一定逃不了立委的砲轟,當下我忽然想起英文中有一句:「You cannot compare apples with oranges.」(蘋果不能拿來和橘子比。)於是回答他:「哎呀!橘子和香蕉是不能比的。」
只是一緊張,把蘋果換成了香蕉。此話一出,引起哄堂大笑,立委大概一時想不出如何連結神明、政務官和水果,只好草草結束。
21 女性副閣揆
我在接受陸委會主委的工作時,並未事先告知家人,他們是從報上得知我的新職務。
當了一年立委後,受命組織新內閣的行政院院長蘇貞昌徵召我去當他的副手——行政院副院長。消息靈通的媒體,再度在我決定前就公布了我的新去向。爸爸從報上看到消息,打電話來問我情況。
我可以察覺他對我的新工作有複雜的情緒,一方面感到高興,他和我都沒想到我會走到副閣揆這一步,但他又擔心我工作負荷過重,壓力太大;而未說出口的是對小女兒的憐惜。
最後,爸爸交代我:「以後不要再讓我從報上得到妳的新工作消息。」我答應了。
我自己也沒想到,這真是最後一次的機會,因為以後再也沒有「以後」了。
〈爸爸,再見〉
生與死,好像有一種神秘的連結。
為了完成總統和院長交付的籌辦經續會重責大任,我全心全力投入。然而在經續會緊鑼密鼓籌備之際,爸爸去世了。
爸爸的逝去並非意外,之前已有徵兆,全賴哥哥、嫂嫂的呵護照顧得以延展,本以為早有心理準備,但心中的哀傷卻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但因為此時經續會正值最緊張的時刻,我身為主要推手實在無法放手不管。
我沒有請假,也沒有讓太多人知道,依舊將全部精神和時間放到經續會的籌辦與進行上,即使是碰到週休假日,我也常花時間和各部會、外商及工商團體進行溝通,排除歧見,取得共識。
只是每當下班後,我會回到陽明山老家,坐在客廳,和停靈在客廳的爸爸說話,我在心裡告訴爸爸我今天做了什麼⋯⋯達成了什麼⋯⋯碰到了什麼困難等等,就像以前我偶爾會和他聊天一樣。我非常清楚爸爸不會怪我,但不知為什麼,我的心裡仍然有一種內疚的感覺。
一直到經續會記者會結束後,我才請了一週喪假,幫忙處理喪事。媒體知道了這件事後,形容我是「意志堅強」「公私分明」「過人的意志力」,甚至是「強忍哀傷」,但在我眼裡,這些詞都是同一個意思:「內疚」。
十個月後,蘇內閣總辭。當天,我去了爸爸的墓園,和他說說話。
行政院後來送來一枚勳章,我連開都沒開就退了回去。再送回來,我再退。我對外解釋:「我沒有接受勳章的習慣。」其實我真正心想的是:收了,只是提醒我的內疚。
25 再起的契機—小額募款的奇蹟
〈小英便當〉
有一次,我們來到屏東進行小額募款。募款餐會的方式是以「小英便當」餐會的形式進行。
「小英便當」是年輕黨工想出來的可愛募款妙招,包括上面印有我圖像的帆布便當袋、一個可重複使用的便當盒及一雙筷子。便當裡都是在地的食材,例如在台南縣舉辦的某次募款餐會,菜單共有九道菜,使用的食材全是台南縣各鄉鎮的特產,包括後壁冠軍米、學甲鰻魚、下營鵝肉、白河蓮子飯、關廟鳳梨排骨、善化鴨蛋、將軍胡蘿蔔、花椰菜及安平蝦卷,還搭配龍崎的竹炭筷和當地水果。
我們的募款餐券是一張一萬元,但餐會吃的不是什麼酒席或流水席,而是便當。算起來,一個便當一萬元,真的很貴。
那一天,有一桌坐了十人,算算這就是十萬元的捐款了。負責這一桌的人告訴我:「主席,其實這十個人代表了一百個人。」我不解,為什麼他們代表一百個人?原來,一萬元對他們每一個人都是不小的負擔,所以,經過討論,他們決定一人出一千元,十個人湊了一萬元,然後再派一個代表來吃這個小英便當。
這些「代表」多是來自鄉村的農人。他們面目黝黑,有的人臉上有深刻的皺紋,但神情很靦腆。可以當代表,來吃「小英便當」,讓他們看起來既驕傲又害羞。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穿著乾淨且燙得平平整整的襯衫,安靜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像其他人一樣搶著擠過來,和我握手、照相,他們只是對著我笑,笑得很純樸。
後來他們告訴我,有人還是從恆春半島趕來參加這場餐會。我一下子覺得更溫暖了。原來是來自家鄉的人。
面對這些人,看著他們眼神中安靜而激烈的期待,握著他們粗糙生著老繭的手,並且知道就是這雙手拿出錢來捐款後,我想,任何接受這筆捐款的人,大概一輩子都不敢辜負這些對你有期待的人。
我帶了一杯水過去,以水代酒,向他們表示感謝,也向他們背後的其他九十個人致意。那一天的募款餐會裡,忘了我舉杯敬了多少次「酒」。
回到家裡,只覺得滿肚子都是酒水,滿肚子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