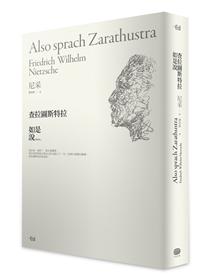子女犯罪,是子女自己的責任,還是父母的責任?
環境被污染,是誰該負責?是企業?是國家?還是你我?
面對無法控制的核災,面對尚未出生的孩子們,身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又該負起什麼責任?
這些倫理(道德)問題,是21世紀人類最深層的精神問題,也是數千年來人類生存問題的核心之一。日本當代思想家柄谷行人縱剖近代歷史,橫跨基督教、佛教、與西洋哲學,尋找倫理問題的答案。最後,他以康德的思想為軸,試圖為21世紀的人類,尋找個人心靈的依歸,以及世界和平之可能。
作者提出,我們必須把「認識原因」和「追究責任」分開進行,否則永遠無法從歷史學到教訓。其次,他相信人類即使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依然有「決定自己行為的自由」,也因此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否則就無法釐清善惡,人類的文明也無法往前躍進。
作者所謂的倫理,指的是「自由」這個義務。倫理要求我們的,就是必須「作個自由的主體」,並且「不只把他人視為手段,同時也要將他人當作目的來對待」。我們除了要認真對待現在活著的他人,也要對尚未出生的人類負責。這是身為人類的義務,也是合乎「倫理」的生存之道。
從2010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可以預見資本主義即將走到盡頭。但即使資本主義社會崩解,人類仍要繼續活下去。作者提出馬克斯的「可能實現的共產主義」以對抗資本主義,為人類的未來社會擘畫新藍圖。
作者簡介:
柄谷行人(Karatani Kojin, 1941~)
日本當代思想家、文藝評論家。1960年代參加反安保運動。1969年以討論夏目漱石的〈意識與自然〉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賞。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運動衰退後,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來站在亞洲邊陲的位置,持續探討「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之理念,2000年曾組織 NAM(New Associationist Movement)。重要著作有《倫理21》、《柄谷行人談政治》、《近代日本文學之起源》《超越的批判--康德與馬克思》、《邁向世界共和國》、《世界史的構造》等等。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 盧郁佳(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
◎ 龔卓軍(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長)
聯合推薦
名人推薦:◎ 盧郁佳(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
◎ 龔卓軍(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所長)
聯合推薦
章節試閱
第一章
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關於責任的問題,一開始我打算從身邊取例,討論在神戶發生的中學生(少年A)事件。並不是因為這個事件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病理——這一類的意見我們已經聽了很多,而且相關的書籍也出版了不少,關於這一點我打算之後再回頭討論。我想談論的,並不是這個事件所展現的個人與社會最近發生的、種種新的病態;相反地,我想透過這個事件,來觀察日本社會長久以來,一直不變的某些樣貌。這與其說是事件本身,不如說是該事件所引起的反應,也就是每當年少者犯罪的時候,社會上必定會出現的言論。
這些言論具體來說,就是追究「家長的責任」。舉例來說,該少年的雙親遭到大眾媒體的攻擊,一再地要求他們道歉,而事實上他們也道歉了。這裡面攻擊最為苛刻猛烈的新聞媒體,他們平常對於要求日本為二次大戰的侵略行動道歉的亞洲諸國抱著輕蔑的態度,對於回應這些道歉的要求之日本政治家更是大加撻伐。到底,這些平常對「責任」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們,自己又不是受害者,為什麼會如此熱烈地追究家長的責任?究竟對這些人來說,「責任」是什麼?在談到戰爭責任之前,我想先從這個問題思考起。
最初我開始思考「家長的責任」,是在一九七二年,連合赤軍事件發生的時候。當時,赤軍成員的家長們在「世間」——只能這麼稱呼的不特定的社會壓力——的責難之下,不得不辭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殺。不用說,這是因為來自周遭的人,以及大眾媒體的攻擊。我對連合赤軍本身抱持極端否定的態度,完全不能認同。但是,卻無法不關心這個事件。一九七五年我出版的第二本書《「意義」這種病》(河出書房新社)中,關於馬克白的論述,雖然完全沒有直接談到連合赤軍,但其實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的刺激而寫作的。雖然我認為連合赤軍的行為極度地愚蠢卑劣,但是一九六○年代萌芽的新左翼運動竟然以這樣的結局收場,自己很難置身於外。
就在那篇關於馬克白的文章完稿的時候,連合赤軍領導人夫婦之一的森恆夫自殺身亡。這個情形,與《馬克白》的情節如出一轍。在聽到了馬克白夫人自殺的消息之後,馬克白說了以下的一段話:
馬克白:這樣啊。一定會走上死亡這條路的。我一直認為,遲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明天,明天的明天,再一個明天,時間日復一日悠悠地過去,終將走到它的盡頭。所有的昨日,照亮了傻子們走向佈滿塵埃的死亡之路。熄滅吧,熄滅吧,短暫的燈火!人生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可悲的演員,在舞台上比手畫腳,登場既畢,便再也無形無蹤。人生只不過是白痴講述的故事,再怎麼大聲喧嚷,還是沒有任何意義。
連合赤軍事件中,與《馬克白》相反地,「丈夫」自殺了;但我並不覺得驚訝。就像馬克白說的,「遲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森恆夫在遺書裡寫著,長久以來與體制戰鬥、抗爭,沒想到自己做出了同樣的東西來。自殺,是他自己承擔責任的作法。因此,我並不覺得驚訝。
但是,連合赤軍風波中的另一起自殺事件,則使我感到非常驚訝。不,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憤怒。那就是其中一名赤軍成員的父親自縊身亡。在這之前,雖然也知道赤軍成員的家長們受到各方的非難,甚至有人因而辭去工作,但沒想到竟然到了尋死的地步。赤軍的那些傢伙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當然要負起責任,但是家長們並沒有任何責任。我對於把人逼到自殺絕境的「世間」感到生氣,對於那位自殺的父親也感到生氣。我認為這種時候,絕對不應該自殺。
另外一件令我氣忿難耐的,是殺害多名女童的M君事件。當時也有不少人,發表了各式各樣的評論。某些像是御宅族評論家的人,企圖從M這樣個別的事件推論到世代的共通性,在我看來不但奇怪,而且盡是些牽強附會的言論。其實對我造成最大衝擊的,是這個事件之後,M的雙親幾乎完全從社會上消失了蹤影。兩個人離了婚,各自改了姓名,從此行蹤不明。後來聽說,M君的父親似乎死去了。另外,M君有一位姊姊,也在婚期將近的時候,被迫解除婚約,失去了消息,她的行蹤我們當然不應該追查。最令我沮喪的是,從連合赤軍事件以來經過將近二十年,仍然發生這種犯罪者的家人受到責難、牽連的情況。M君的事件能不能代表一個世代,能不能象徵現在日本的情況,這很難說;但我可以說,發生在M君家人身上的遭遇,毫無疑問是日本社會的象徵。如果要談論這二十年來日本社會的變遷,就這一點看來,只能說一點改變也沒有。
有些行為,即使在法律上是無罪的,卻仍然有道德上的責任。如果說法律由國家來執行,那麼追究道德責任的則是共同體。在這個意義上,道德可以說是維繫共同體存續的規範。不管社會開化的程度,不管在哪個國家,都是如此。但是,和別的國家比較起來就不難明白,日本的情況相當特別。因為前述的幾個事件,我變得對這種事情很敏感,經常找機會觀察。
美國經常發生一些可怕的少年犯罪,發生這些事情時,社會上是如何看待、要求家長的?我經常在美國的電視上看到,犯人的家長對著鏡頭宣稱,相信自己的孩子是無罪的。一九九六年的秋天我到紐約去的時候,剛好聽到收音機播報,在甘迺迪機場有一名神學院的學生,因為持有包含手槍在內的各種槍械被逮捕。第二天我注意看報紙,這個新聞只佔很小的版面,旁邊有兩則來自親友的評論。犯人的友人說:「很意外,看不出來他會做這種事。」另一則犯人母親的評論,讓我有些驚訝:「這是陷阱,我的孩子被美國警察設計陷害了。」我雖然覺得她的辯解不可能成立,但並沒有聽到任何譴責她的聲音。因為美國人認為,作母親的為自己的孩子辯護,是理所當然的事。
在那之前的一九九五年,日本的沖繩縣發生美軍士兵性侵少女的事件。基於政治考量,美國總統迅速作出反應,正式公開道歉。審判當時其中一名黑人士兵的母親來到日本,宣稱「這個審判是個陷阱,我的兒子是無罪的,在日本警察的拷問下被迫承認捏造的罪行。」某個週刊的專欄發表評論:「這個母親毫不講理,完全不知反省。」但是,對美國人來說,孩子犯下這種錯而母親卻堅稱他無罪,沒有人會譴責她沒有責任感。因為兒子犯了重罪,家長為他辯護,是完全正當的,沒有什麼奇怪,也不是沒有責任感。像日本一樣,社會大眾異口同聲,一致譴責家長的情形,在美國是不會發生的。
一開始,我以為因為美國是個人主義的社會,所以會有這樣的差異;如果是韓國和中國,情形應該和日本一樣。但是幾年前我參加由《批評空間》(太田出版)這本雜誌舉辦的座談會,遇到安宇植教授(他是居住在日本的韓國人),偶而談起這件事。安教授肯定地說,在韓國絕對不會發生這種事;韓國的父母一定會維護自己的小孩,也沒有人會因此責怪父母,更不會有父母為此自殺。
神戶的中學生事件之後,我到韓國參加會議,大家偶然談起在日韓國人的作家柳美里女士,大家問我關於她的事,於是我談起了神戶事件。柳美里對於神戶的中學生事件曾發表強硬的談話,要求「A君」的家長應該下跪道歉。事實上,「A君」的雙親真的下跪道歉,長達九十分鐘。但即使這樣,還是覺得他們反省得不夠。那麼,要怎樣才能表示他們的悔意呢?只好去死。簡單地說,實際上是叫他們去死。但是我認為,不但沒有必要去死,也沒有必要在電視機前下跪。
就我所知,在韓國,沒有叫別人家長下跪的文化。我的一位韓國友人,四十來歲的評論家、大學教授,據他所說,從小到大都是正襟危坐地和父親說話,而且一次也沒有頂過嘴。這位友人自己有了子女以後,不願意再當那種形象的爸爸。我想近年來韓國的社會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吧。柳美里大概從小和威權的父親抗爭著長大,但是日本的父親一般來說不是那樣的,對於這一點,她有著錯誤的認知。柳美里因此對「父親」這個形象產生攻擊性,雖然可以理解,但很不幸地被最沒有資格談論「責任」的日本新聞媒體利用了。比起早一些的連合赤軍、或是「M君」的事件,「A君」的事件更明顯暴露出日本社會的特性。在前兩次的風波中,至少還沒有人要犯人的家長下跪,也沒有人說要看犯人家長的臉長什麼樣子。
「世間」這個實體不明的東西所具有的力量
為什麼子女的所作所為家長必須負責?對誰負責?說起來,就是對所謂的「世間」。犯了罪的子女接受與其罪行相當的懲處,其家長也因此受苦、受罰。受害者家長無法抑制的憤怒我們可以理解,但憑什麼「世間」——實際上就是新聞媒體——要來為他們的憤怒代言呢?如果遭到非難攻擊的犯人家長因此自殺喪命,「世間」會負起責任嗎?所謂的「世間」,是模糊曖昧的東西,並沒有清楚明確的主體。因此那些想要追究家長責任的人,並不說是自己的主張,而推說是「世間」的意見。
經常有人說,歐美的基督教道德是個人主義的基礎。但是,從別的角度來看,在儒教影響下的中國和韓國,他們的道德觀也可能形成另一種個人主義。像這樣的東西,日本沒有。代替道德的,是所謂「世間」這個實體不明的東西。本居宣長曾說,「道德」是中國傳來的觀念,遠古的日本原來是沒有的,也沒有那種需要。某種意義來說,本居宣長的說法是正確的。道德這個東西對日本人來說,總是有拘束、不舒服的感覺。有人主張二次大戰後,日本受到美國的影響,因而道德觀崩壞,那不是真的。但日本沒有道德規範這件事,並不意味著日本人不受共同體的規範和制約,是完全自由的;日本人透過「世間」這樣的東西而受到規範和制約,而且「世間」的規範和制約非常強烈,一直都存在。
比方說,有人認為家父長制在現今的日本仍然頑強地存在。並且,這個家父長制並不是自古就有的東西,而是明治時代之後,隨著近代國家與資本主義一起形成的。與歐美或韓國的家父長制比起來,的確日本的家長對於子女有諸多管束,但其實家長的自由受到子女很大的限制。日本的家父長制就存在於這種相互制約之中。其原因在於日本的社會中,不論子女們惹出什麼事,家長都會被要求負責。乍看之下家長握有很大的權力,充滿威嚴,事實上他們非常害怕自己的子女出事,經常成為子女的犧牲品;因為害怕,才更要限制子女的自由。
我們必須對這種文化上的差異保持敏銳的知覺,否則會搞錯抗爭的對象。柳美里曾自稱不願以「在日韓國人」為寫作的主題,這當然沒問題,但光是這樣並不能保證她的作品具有普遍性。在她的作品中出現的父親的形象,和真實的、日本的父親是不相符的。某位芥川賞的評審委員曾以「現實中不會有這種父親」為由,對柳美里投了否定票。後來有人對他說明,這位作家是住在日本的外國人,他才釋懷。但隨即該位評審又說,「如果是這樣,那就應該寫出這件事」。基本上我也有同感。
不只是柳美里,一般人對於「私小說」有些誤解。舉例來說,很多人以為私小說都是用第一人稱寫成的;但事實上用第三人稱寫作的私小說數量也不少,而且也不一定都是自傳性質,常加入大量虛構的成份。因此,光從外形無法判斷一部作品是不是私小說。如果要嚴密定義的話,私小說指的是,閱讀時必須依賴作品之外的脈絡(譯註:比如作者的個人背景)才能產生意義的小說。一般通稱私小說的作品中,有一些就算完全不知道作者的事,也不妨礙我們的理解;反過來說,不管怎麼樣的小說,我們都可以用私小說的方式來閱讀。所以我才說,是不是私小說,光從外表看不出來。就算柳美里的小說中沒有韓國人出現,但是如果我們必須了解她「在日韓國人」的背景才能讀懂她的作品,那就是「私小說」。否則,就算小說中有「在日韓國人」登場,也不會使她的作品變成私小說。
由於對這一點缺乏知識,柳美里的作品反而能夠呈現一些新鮮的面相,但是那無法構成真正動人的力量。柳美里曾因為在小說中以某位韓國女性為本,描述當事人的私事而遭到毀損名譽的控訴,並且被判有罪。面對法院的判決,她表示這對日本的私小說傳統是一種傷害。可是,就算私小說有它的傳統,也不值得肯定。這不是文學傳統的問題,而是「言論自由」的問題。就像《不敬文學論序說》(一九九九年,太田出版)的作者渡部直巳所說,如果我們同意這樣的判決,那今後以天皇為模型的小說,就不能寫了。
自從神戶事件以來,關於當今未成年者的處境,有著各式各樣言論。確實,現在的小孩們處境相當惡劣,原因也很複雜。比如升學考試,雖然從以前就有,但現在競爭的壓力比以前大很多。那是因為在後產業資本主義社會,必須透過教育來提高「勞動力的價值」,不管在世界上哪一個地方都一樣。那麼為什麼日本的狀況特別糟呢?韓國的升學競爭也很激烈,但總覺得有些不同。在韓國,家長叫小孩唸書,小孩就唸。但是日本的家長卻不這樣直接命令小孩。大部份的日本家長都會說:「我並不想說這種話。其實我希望他們可以自由地、從容地成長。」但是,如果真的讓小孩自由,又怕他們日後遭人歧視,覺得自己對小孩的將來有責任。重視小孩的事,結果綑綁住他們,也壓得自己喘不過氣。
從前太宰治曾說過「比起小孩,父母更重要」。這聽起來有家父長制的意味,但事實上日本的社會並非如此。舉例來說,為人父母者,特別是女性,如果自己有什麼想做的事,經常會被身邊的人以小孩為由勸阻。就這樣,父母被限制了自由;而這樣的父母,更容易限制小孩的自由。比方,日本的母親很少對小孩說:「不准這樣做!」而比較常用軟性的語調說:「拜託你,請不要這樣做。」這種時候,小孩子雖然沒有被直接命令,卻以另一種方式受到束縛。這樣的情況下,首先更是非強調父母的重要性不可;一再強調的結果,又變成過度重視小孩。就這樣循環著。太宰治這個作家,是個犧牲了家族、整日耽於遊蕩的傢伙,而且竟然還說出自己是「為了『義』而遊玩」這種不合情理的話來。我個人討厭太宰治,比起來還比較喜歡說過「就算有父母在,小孩還是會長大」的坂口安吾。不過太宰治的話語裡,不可否認地有些洞見。想要與日本的家族制度抗爭,光是由小孩與家長抗爭是不夠的。一定要父母與孩子協力,共同和社會上強大的壓制力抗爭才行。「比起小孩,父母更重要」這句話倒過來思考,指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稍後我將會再度提及,円地文子的《沒有餐桌的家》(一九七九年,新潮社出版)就是以此為主題。我認為像圓地文子這樣的作家們,其抗爭的對象,與其說是家父長制,不如說是之前提過的「世間」。「世間」不只對家庭,對公司等等一切社會組織都產生重大影響。但是,像「世間」這種實體不明的東西,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力量?我們在日本社會中遭遇的,並不是像儒教或基督教那樣明確的道德法則,而是主體、原則都曖昧不明的「世間」的道德。順帶一提,韓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基督教徒;他們信仰的基督教在某些地方和儒教有共通點,因此在社會上有很深的根基。另一方面,和「世間」抗爭的困難,在於它善變而沒有明確的實體。我們如果執著於它,「世間」很快地忘記我們;我們如果忽視它,則「世間」就如附骨之蛆,黏著我們不放。日本的週刊常製作〈那個人現在如何如何——〉的特集,所謂「世間」就是這樣的東西。
像這樣的「世間」是從哪裡產生的?根據我的考察,「世間」來自德川時代所形成的,一種畸形的「群落共同體」。這個「群落共同體」歷經明治時代,甚至經過二次大戰、農地解放之後,仍然存在,沒有解體。一般的論述,稱呼戰前的社會經濟體制為「封建遺制」,指的是由地主支配佃農的制度。這個說法用來描述歐洲、中國、或者韓國或許是貼切的,在這些地區,地主是由封建領主或官吏擔任,因此封建遺制及階級對立也很銳利明顯。但是在日本,從德川時代形成的「群落共同體」原封不動地流傳下來,不只佃農,連地主階級也受到「群落共同體」的約束與限制。如果要談日本的「封建遺制」,應該要討論這個「群落共同體」才對。
乍看之下,「群落共同體」好像是緊密、親和的團體,其實不然。以前有一位留學法國的人類學家,用Kida Minoru的筆名寫作了一本叫《癲狂部落周遊紀行》(一九四八年,吾妻書房出版)的書。這本書因為標題帶有歧視的意味,有一段時期遭到排斥,但其實很值得一讀。內容簡單地說,是以初訪地球之外星人的眼光,來觀察隨處可見的、典型的日本農村。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關於農民人際關係的描寫。想像中農民與農民之間,理所當然存在著友情,但其實沒有。友情存在的先決條件,是每個人要有「自我」。但農村裡的人,沒有「自我」。共同體的核心就是所謂的「世間」,而大家對這個「世間」感到恐懼。所以,大家因為害怕被「世間」孤立,而勉力和睦相處,但關係非常表面。基本上是自我主義者,但卻沒有「自我」。
這令我想起最近的現象。有人指出當今的年輕人是「隨和型自閉」。舉例來說,當今年輕人可以在一起愉快地飲宴嘻鬧,彼此間卻不願意建立較深層的關係。精神分析醫師小此木啟吾稱之為「精神分裂症(Schizoid )人類」。 乍看之下,這是一個後現代社會特有的、新的現象,但其實有它歷史的根源。這個現象在美國,以及其它先進國家都有日益普遍的趨勢,可是為什麼在日本顯得特別嚴重呢?我認為那是「群落共同體」殘留的影響。先前說過的、傳統農村的村民,雖然彼此間過從甚密,卻沒有類似「友情」那種深厚的關係。他們對於天下國家大事,既不關心,也無意參與。只要統治者徵收的年貢不要太過分,只要還能守得住自己的土地,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和他們無關。他們唯一的作為,就是出於恐懼,小心地不要偏離「世間」的行事標準。
円地文子的《沒有餐桌的家》中所描述的兩場鬥爭
在受「世間」支配的社會中,不論是談到與家父長制的鬥爭,或是與國家權力的鬥爭,都沒辦法單純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在這裡,我想提出一部與連合赤軍事件有關的重要文學作品,円地文子的小說《沒有餐桌的家》。這部小說寫作於連合赤軍事件發生之後幾年,在報紙上連載。小說的主題,是某位兒子涉及類似連合赤軍的事件遭到逮捕,其父親的遭遇與反應。小說中的這位父親身兼某公司的幹部與技術人員,即使遭到世間的非難,卻堅持不辭職。故事的這一部分當然是虛構的;正如前述,作為小說模型的、現實中的連合赤軍成員的父親們,有一位辭去了工作,另一位甚至自殺身亡。所以,這部作品雖然是以實際的案例為本,卻發展出完全不同、在日本這個國家絕不可能發生的結果。作者透過這樣與現實相反的情節,進行了一項「思想實驗」。小說裡,有這樣一段文字:
不論這些父母們如何嘗試著辯解,擺在眼前的事實是無可否認的。面對世間排山倒海而來的攻訐,他們形容狼狽,不斷退縮,最後對於兒子非法的惡行,只能一逕地道歉謝罪。
不管任何時候,對於殘酷暴虐的行為,輿論只能毫不容情地發揮自衛的本能。只有在事過境遷之後,才能對當時的情況作出冷靜的判斷。這個事件發生的時候也是一樣;如果事件的規模僅止於包圍八岳山莊的游擊戰,或許世人的關心會偏向單純的好奇,事件也會以一個無害的騷動結束。但是這些犯人們被逼到走投無路時,彼此間懷疑猜忌、施行私刑,那種駭人聽聞的殘忍,在世人的心中燃起了怒火。憤怒的對象不斷擴大,不知不覺中,把犯人的家人都涵括進來,「罪誅九族」的倫理觀就像獲得羽翼的巨鳥振翅高飛,支配了世人的觀感。這種現象,可以說是日本人的本能吧。
但是,小說中唯獨這名父親不願謝罪,也不肯辭職。他或許是這樣想的吧:孩子參加赤軍一事,自己絲毫不能贊成,而且事情演變成如此,說不定自己是原因之一。但是面對世間,關於兒子的所作所為,自己沒有任何負責的理由。如果子女只是父母的附屬品,沒有獨立的人格,那麼或許父母是有責任的。但事實並非如此。假使自己順從輿論的壓力辭去工作,就等於默認兒子不是一個自由的個體。兒子自己做的事,讓他自己負起責任……。
可是,身在日本,要採取像這名父親的態度,需要了不起的勇氣和決斷力。這就是我所說的,小說中的另一場鬥爭。顯然對於作者円地文子來說,這場鬥爭比連合赤軍的鬥爭更為重要。換句話說,這部作品裡有兩場鬥爭;其一是對抗國家權力的鬥爭,小說中的兒子一直到最後都堅持立場,加入了流亡阿拉伯的日本赤軍。另一方面,父親的鬥爭則是與「世間」對抗,而且和兒子的遭遇一樣慘烈。兒子的鬥爭演變成同志間互相的大屠殺,父親的鬥爭最後則導致女兒的婚約破裂,妻子死亡,家庭瓦解崩潰。因此,小說中登場的另一人物(次男)這樣描述自己的父親:「哥哥的事件發生的時候,爸爸的表情,一直保持異常的冷靜……比起哥哥和他的同伴們的所作所為,爸爸的反應更讓我感到心寒。」
這位父親,被世間,甚至被自己的妻子、女兒,批評為沒有責任感、冷酷,但是我認為他是位極度堅守「倫理」的人。這位父親雖然不贊同、不支持兒子的行為,卻一直到最後都堅持認同自己的兒子是一個可以為自己負責的、自由的主體。如果身為父母者屈服於世間的壓力,以辭職的方式表示負責,無異損害了子女的主體性。他本人並沒有反抗世間道德標準的意思,只是為了尊重兒子的「自由」,不得不抵抗來自世間的非難。
討論到這裡,我們面對了兩種不同的道德性、倫理性;稍後我們還會談到,齊克果稱之為倫理A與倫理B。第一種,是世間(共同體)加諸我們身上的、善惡的基準。另一種想法,則認為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找到道德性。康德的思想,屬於後者。我希望讀者們能夠注意,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任意地使用、不加以區別,但是道德性、責任、自由這些字眼,其實有雙重、而且相反的意義。在進一步討論我們的主題之前,首先必須整理、釐清這種用語和概念上的混亂。
第一章
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關於責任的問題,一開始我打算從身邊取例,討論在神戶發生的中學生(少年A)事件。並不是因為這個事件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病理——這一類的意見我們已經聽了很多,而且相關的書籍也出版了不少,關於這一點我打算之後再回頭討論。我想談論的,並不是這個事件所展現的個人與社會最近發生的、種種新的病態;相反地,我想透過這個事件,來觀察日本社會長久以來,一直不變的某些樣貌。這與其說是事件本身,不如說是該事件所引起的反應,也就是每當年少者犯罪的時候,社會上必定會出現的言論。
這些...
目錄
目錄
推薦序 無知是一種邪降
譯者序 真正的原創力
前言
〔第一章〕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世間」這個實體不明的東西所具有的力量
円地文子的《沒有餐桌的家》中所描述的兩場鬥爭
〔第二章〕認識人類的攻擊性
精神分析不能直接應用在育兒與教育上
不論用多麼和平的方式養育,在多麼和平的環境下成長,人類的「攻擊性」也不會完全消失
〔第三章〕自由絕對不會從「自然」中產生
認識「決定人類行為的結構」
「作一個自由的主體」之義務與自由
〔第四章〕將自然的、社會的因果性置入括號之中
從「自由」的觀點來看道德性
如何負起「徹底認識原因」之責任
〔第五章〕從世界公民的角度思考,才是真正「公眾的」
康德對於「私領域」與「公領域」的顛覆性看法
與抱持不同「共通感覺」的他者取得共識
〔第六章〕 只有用倫理的角度來看,宗教才值得肯定
世界宗教否定自由意志
五十步與百步,其差異之絕對性
〔第七章〕幸福主義(功利主義)裡沒有「自由」
憑藉幸福主義不能解決環境問題
「敬畏死者」這句話的意義
〔第八章〕責任的四種區別與其根本的形而上本質
實現康德理念之國際法
關於戰爭責任議題「哲學家」的欺瞞
〔第九章〕日本天皇對於戰爭應負的刑事責任
為什麼東京大審判沒有追究天皇的戰爭責任
天皇制度的結構和天皇的戰爭責任
〔第十章〕「非轉向」共產黨員之「政治責任」
丸山真男的共產黨批判
以現實的認知問題,來思考大戰時的轉向與非轉向
〔第十一章〕「已死的他者」和我們的關係
「歷史的重新認識」不可避免
〔第十二章〕我們對「尚未出生的他者」應負的倫理義務
以「可能實現的共產主義」對抗資本與國家
後記
目錄
推薦序 無知是一種邪降
譯者序 真正的原創力
前言
〔第一章〕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世間」這個實體不明的東西所具有的力量
円地文子的《沒有餐桌的家》中所描述的兩場鬥爭
〔第二章〕認識人類的攻擊性
精神分析不能直接應用在育兒與教育上
不論用多麼和平的方式養育,在多麼和平的環境下成長,人類的「攻擊性」也不會完全消失
〔第三章〕自由絕對不會從「自然」中產生
認識「決定人類行為的結構」
「作一個自由的主體」之義務與自由
〔第四章〕將自然的、社會的因果性置入括號之中
從「自由...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42收藏
42收藏

 39二手徵求有驚喜
39二手徵求有驚喜




 42收藏
42收藏

 39二手徵求有驚喜
39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