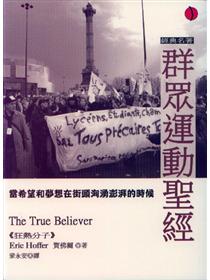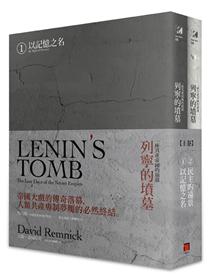這一次,泥塑世間實相的散文家,
轉身成為推理事物的極限運動員。
事物在此一實然世界的確實停止之處,我稱之為盡頭
在這裡,一次一次的,最終,總的來說,揭示的是人的種種真實處境
剖析流浪幾世的靈魂:溫泉鄉的屍體路仁娜、特洛伊十年後的海倫、回憶四十年前柏林童年的本雅明……解讀現世的集體意識:不那麼擔憂電視的錢永祥、每天都在查禁書的唐諾、那位從紐約找上門來的NBA迷……。
十七個獨一無二的人物,穿越時空式的撞擊與迸發,透視著書寫與閱讀,那一截多出來的世界。一波波在我們察覺不到的微型或廣漠宇宙中的文字量子,鑲嵌刻痕在那個意義的能量點,繼續流動到下一個讀書人或寫者身上。一種不斷前行、不斷展開、不停生長的,唯有前進到某個新位置才可顯現的有跡可循的盡頭。
作者簡介:
唐諾
一九五八年生,台灣宜蘭人,台大歷史系畢業,現從事自由寫作。不是專業球評,早期卻以NBA籃球文章廣為人知。不是專業推理小說評論者,著有「唐諾」風的推理小說導讀。不是專業文字學者,著有《文字的故事》一書,同年囊括國內三大好書獎。
唯一「專業」的頭銜是作家、兼資深讀者,著有《世間的名字》、《讀者時代》、《閱讀的故事》、《唐諾推理小說導讀選Ⅰ、Ⅱ》、《在咖啡館遇見14個作家》。
章節試閱
說明
盡頭,這次這個書名倒是我自己取的,沒有麻煩任何人,惟實際的內容絕沒有此一書名顯示的這麼「巨大」,當然更不會像看起來這麼悲傷這麼抒情。
不是所謂的全書主題,這只是這兩年半書寫時間裡自始至終徘徊腦中不去的有用概念,我以為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不管當下想的寫的是什麼,如同一種根本的意識,一種時時處處的自我提醒,因此,我特別記下它來。寫上一本《世間的名字》當時,我一直想著的是「極限」,太陽會燒完自己,小說會哪天寫完它的全部,各種自然的、以及人的事物各自能做的和做不到的邊界究竟何在,包括其空間的(何處)和時間的(何時)邊界,凡此種種─但《世間的名字》末尾,我開始自省到自己的不自量力部分,事物極限的思索,其實應該由更專業的人來想來說才是,其中的潛力潛質、其中隱藏的諸多猶有可能,最終只有在日復一日專注如只此一途的實踐中才(被迫)有所發現,或者說有所發明。我自己稱此為希望,一處一處具體的、確確實實的希望。
另一面,極限的思索可能也是個太「奢侈」的思索,其實我們通常等不到它到來,也就無須憂慮它。也因此,這樣的思索結果遠比想像的要乾淨透明,不僅不可懼不威嚇,甚至還太過美好;相對於我們現實人生,你不是感覺被無情截斷,而是居然還延長延伸出去,不是少掉了,而是多出來─很快的,我們便會發現,這樣的思索只一兩個大步就越過了眼前的實然世界,進入到本來有可能發生但實際上尚未發生、不會發生的這「一截」多出來的世界之中。更多時候,再觸到我們的並不是它的終歸有限,而是它果然「美好得不像是真的」,賈西亞‧馬奎茲聽到「你屬於我所熱愛的那個世界」這句話當場熱淚盈眶,我相信,那一刻因此被叫喚出來、讓人以為置身其中的,就是這一截多出來的世界。
極限的思索,讓人曉得自己其實可以更好。
惟極限不會到來,事物總是在用盡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達盡頭,這是因為現實世界同時會有很多事發生,先一步打斷它中止它替換它並遺忘它。比方,民主政治本來還可以再好一些再睿智一些就像小彌爾講的那樣,但實際上有另外更大的力量拉扯下它限制住它;電影做為一種藝術創作形式,至今仍未用盡自身全部可能,但昆德拉指出來它實際上走向另一種發展(成為一種令人變笨的東西),以至於電影做為一種藝術創作形式的這一道歷史已提前殞沒了,凡此。極限的思索讓我們箭一樣射向遠方,但注視它實際上的力竭停止之處,轉而追究它「本來可以發生卻為什麼沒發生」、「已堪堪發生卻退回去復歸不會發生」,則讓我們老老實實落回此時此地來,這比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
事物在此一實然世界的確實停止之處,我稱之為盡頭。在這裡,一次一次的,最終,總的來說,揭示的是人的種種真實處境。
書寫工作,我仍很偶爾會想起年輕,還「無法進入到這個世界」(昆德拉語)的時日,當時,現在想來不知從何而生的空氣中彷彿有個神奇的允諾,好像這是個接近無所不能、或至少足夠自由輕靈到可以一再穿透各種界線、時間界線、空間界線、乃至於人生死界線的太好東西,也許曾經、或本來可以這樣沒錯。多年之後,我漸漸相信並且認定,在原來這也不能那也不能的實然世界之中,書寫仍有這樣一件事可以做而且得做,接近一種責任,那就是─此時此地,書寫者至少得奮力的說出人的當下處境、他自身的處境。世紀交迭,萬事發生,惟這一刻我們站在哪裡,記得什麼,看著什麼,知道些什麼,意識著什麼,猶期盼什麼。仔細看,這其實是書寫時間長河中一代一代的連續工作,所以說像是個不懈的責任。
這本書,我麻煩了我的好友詩人初安民為我寫序,從《文字的故事》以來這已十年以上時間,除了朱天文朱天心,他是始終在場、冷眼看著而且一直以各種必要方式協助我的人,沒有他我大概還是會寫,只是很難想像會是個什麼光景,我於是用這樣讓他麻煩、讓他困擾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感激,並紀念這一段逝去時光,但悲傷的是,十月裡安民的母親以八十五之齡溘然長逝,這當然比這篇序文重大,所以安民的序也只能留到我的下一本書。初安民把他幾十年的生命時間多用在文學編輯工作上,我們都一起來到這個年歲了,時間所剩不多,未盡之志一堆,我仍然希望他回來認真的書寫,像個詩人、像他本來應該的那樣子寫。
溫泉鄉的屍體路仁娜
《賦別曲》很顯然是昆德拉較容易看的一部小說,一個封閉性的單一場景,五天時間,八個
人,一次死亡或說謀殺。事實上,這部小說順時間分五個章節,創世紀般以「第一天」「第二天」……命名,到第五天因死亡而終結,這幾乎已是推理小說的標記─當然,昆德拉這個強烈而且複雜難馴的書寫者名字不真的令我們錯覺(或期待)自己正讀著一本推理小說,但我想,如果書出版時發生了這個那個意外,以至於作者名字被誤植為阿嘉莎‧克麗絲蒂那會怎麼樣呢?
我不相信昆德拉不是有意的,你看,故事設定在昆德拉故國某個健康療養勝地的溫泉小鎮裡,
封閉、遺世獨立,這是典型到令人生氣的謀殺舞台,這種地方在小說裡不死人那才叫奇怪;故事的啟動開關是一次不恰當的懷孕,療養院的年輕護士路仁娜堅信這是兩個月前的一夜情結果,男方是聲名如日中天的喇叭手也是樂團領導人柯利墨,路仁娜拒絕墮胎息事,而柯利墨有著病弱但依然絕美如昔的妻子,他深愛她且自誓要照顧她一輩子,所以被害人(屍體)也第一時間準備好了;接下來,相關人物一一登場如演員上台或說嫌犯指認,每個人都有他臉譜也似的極其安定身分、性格、年紀和他唯一想做成近乎附魔的那件事,有嗅聞出外遇不祥氣味追過來的妻子卡蜜拉,有異想天開一直暗中執行他生育改造世界計畫的產科醫生史克塔,有妒火中燒像個四處移動炸藥的在地年輕情人胡南特,有只是路經此地即將去國不返如昆德拉自己的政治犯良心犯賈庫,有賈庫監護超過十年、身世坎坷、腦子遠比胸部發育成熟的小女孩歐爾佳,此外,療養院還住著一個錢多得要命、該說優雅得很噁心還是優雅得很殘酷的美籍老人富豪巴雷夫(我感覺自己好像又回到擔任推理小說編輯的老日子,正負責寫著某本書的封底誘惑文字)可能的凶手也全數就位了;事實上,凶器一直就在我們眼前晃著,昆德拉不斷特寫它,這是一顆劇毒藥片,泛著淡藍光輝,擁有者是政治犯賈庫,配藥人是醫生史克塔:「我擁有這顆藥已經有十五年以上。我在獄中待了一年之後學到一件事:一個囚犯至少需要有這種把握─那就是,他主宰自己的死亡,能夠選擇死亡的時間和方式。當你有
了這種把握後,你就幾乎能夠忍受一切。你始終確知,你有力量在自己所選擇的時間結束自己的生命。」「在這個國家之中,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有這種需要。除此而外,我認為這是一種原則。我認為,每一個人一旦成年之後,就應該擁有一顆毒藥,並且要舉行隆重的贈與毒藥典禮。這並不是為了引誘人們自殺,相反的,是要讓他們生活得比較平靜,比較安全,讓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有一種把握,即他們是自己生命和死亡的主人。」
這使我想起但丁‧加布里埃爾‧羅塞蒂讀了《咆哮山莊》後寫給朋友信中的精采話語:「事情
發生在地獄,但不知為什麼全都是英國地名。」─當我們活著的地方是監獄,或是地獄,這樣的一顆藥片便成為一把鑰匙,我們隨時可跟自己說夠了開門離去。
用死亡來保護生命,波赫士也有相似的想法,他沒藥片,但他用跟自己約定自殺來替代(「如
果××事沒改善,兩個月後我就自殺。」云云),一種唯心的劇毒藥片,波赫士說做成這個約定總讓他精神振奮,不懼陷入更糟的未來,也再沒有超過忍受極限的未來。現實之中,我認識的人唯一擁有藥片的是一位旅居紐約的前輩作家,他也是半生緊緊攜帶著如同某個有實體有重量的生命信念,更像陪著他水裡來火裡去的守護神,只是他認為我當時還太年輕,拒絕了我的請求,我是沒敢像昆德拉(或只是賈庫)說的主張人人該有一顆,但我確實覺得自己應該擁有。
好,謀殺開始,人們天南地北來到此地;謀殺完成,大家一一握手道別各奔西東,讓時間恢復流動,讓生命重拾它們原先的路徑暨其樣態繼續不回頭前行─
誰殺了路仁娜呢?
8-1=7,這七個人裡,究竟誰殺了路仁娜?總有人得負責當凶手的;還是說,我們不該這麼
快把這個1(路仁娜自己)給減掉,如果你推理小說看得夠多,已成為某種風聲鶴唳型的讀者了,你一定不會那麼快排除路仁娜自己動手的可能,她可能只是自殺,也可能會謀殺了自己,為著某個更惡毒更復仇天使式的企圖。
很神經是吧?的確是但沒辦法,生活裡通常我們不會這樣,只有我們讀著某部小說時、如踩進了某種小說陷阱時才不由自主這樣。依波赫士,是愛倫‧坡創造了推理讀者,亦即創造出這樣接受暗示讀小說的我們。
於是,最典型最神經兮兮的推理小說總包含著這誇大的、遙遙相望的兩端:一端是最終必須有明確的、排除的、單一執行的凶手,惟人數可以是複數無妨;另一端則是,通常會下英雄帖般召集全世界都可能殺此人的嫌犯,從當下利益糾結到沉睡百年的家族恩仇,附帶著諸如此類阿嘉莎式的陰森森喟歎:「是啊,我常奇怪為什麼每個人都會殺人。」但其實更奇怪更虛張聲勢的是(但願只是虛張聲勢而已),為什麼每個人都有這麼多人可能殺他。
近年來,音量頗大的響著一種對此小說單行道結局的質疑聲音,依附在平等、多元、民主、開放云云這一團我們這個時代最無可阻止的思維主流裡因此更顯理直氣壯,其積極實踐形式便是所謂開放性文本的書寫嘗試,大家一起來,多歧路的人生不是只一種可能,小說也就不是只允許一種結局,我們自己提筆就可以改變它。所以,安娜‧卡列尼娜不是非死不可,從她和伏隆斯基發生戀情到她跳向火車之間有足夠長時間,而且還是呈樹枝狀展開而非單行道形狀的時間,也有足夠多的偶然阻止她或供她做出不一樣的抉擇,這也才是完整的人生事實,我們眼前結了婚又忍不住談起戀愛的男女不比比皆是嗎?所以,大白鯨莫比敵克也可以轉過頭來由牠天涯海角獵殺阿哈船長,這樣也許更好玩更溫暖更富節奏變化甚至有機會帶出更複雜的善惡寓意,或者也可以考慮讓這一條如此珍稀的白鯨列入瀕臨絕種動物名單得到保護,失業的阿哈可以改行上岸寫小說如康拉德船長那樣,或應徵上「全世界最好的工作」成為南太平洋某小島的海洋巡邏員,由他負責照顧莫比敵克,一人一鯨,死生契闊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
當然,這兩個例子都很不好,因為《安娜‧卡列尼娜》和《白鯨記》這兩部鉅著太厚了,玩開放性文本的人不會選擇它們,這是有確確實實理由的,甚至這才是關鍵所在。一般而言,他們會選擇短而輕而明確的東西,因此童話和寓言優先考慮,至多到那幾本其實看電影或看電視即可的流行小說;我們隨便走進一家書店或上網看其成果也的確如此,有不化為泡沫和沒成為回收物資的小美人魚和快樂王子,但並沒有不自殺身亡的安娜,有變臉令人戰慄的小紅帽或青鳥,但並沒有學會寬恕的阿哈和莫比敵克。
這難免令人悵然若失甚至奇怪,理論上,敲開封閉硬殼,打斷宿命鐵鍊,讓自由和其他無限可能宛如天起涼風吹灌進來,我們有理由期待、甚至有理由要求,應該獲得另一本乃至於一排更好或至少不遜色的《安娜‧卡列尼娜》或《白鯨記》,但何以我們只得到這些比報紙上四格漫畫稍微有意思一點點的東西而已?雷聲隆隆的解放卻是荒漠一片的成果?如果原因是夠好的書寫者沒參加,那我們仍得回答,何以這麼動人的解放主張不吸引他們,他們不是最要求無限自由而且永遠缺乏好題材的一批人嗎?究竟什麼阻止了他們?
總之,不管問題怎麼問,都是福爾摩斯所說的,「奇怪的不是為什麼深夜傳來狗吠,真正奇怪
的是狗為什麼沒有叫」。
好,誰殺了路仁娜?小說裡我們可以就說是流亡的賈庫,但當然不是典型推理小說式的殺法,
而是用昆德拉自己的方式來,有鬼使神差的味道─第四天,路仁娜把裝鎮靜劑的玻璃藥管忘在酒店桌子上(典型推理小說讀者會第一時間注意到鎮靜劑和毒藥相似的淡藍色,從第一天就開始盯著這管鎮靜劑),被賈庫撿拾起來,「這幾個小時是他在祖國的最後幾個小時,甚至最微小的事情也具有不尋常的意義,並且轉變成寓言的戲劇。他在心中自問:偏偏在這一天,有一個人留給我一個淡藍色藥片的管子,這是什麼意思呢?為什麼留給我這個管子的人是一個很特殊的女人─迫害者的侍女、劊子手的朋友?難道她是想告訴我說:我還需要淡藍色的藥嗎?或者,她是在提醒我毒藥,為的是肯定她無止盡的憎意?或者,她是要讓我知道:我離開這個國家是一種投降的行為,就像吞下背心口袋裡那顆淡藍色的藥?」然後,是接連而來讓人不及反應的意外,先是已知道有這顆毒藥存在的少女歐爾佳進來,正比較兩種藥片色澤和大小微差的賈庫下意識的把真正的毒藥也收入管子內,馬上路仁娜又去而復返,不容分說奪回多了一顆藥的管子揚長而去,並在十八小時之後吞下它。這很冤枉,吞藥當時她已和美國富翁巴雷夫共度一夜,新的生活花朵綻放般豁然打開,眼前一片亮光,她已準備好墮胎重新開始。
這十八小時,賈庫為何不追回這顆可能害命的毒藥?這是典型推理小說說不通的地方,但在人生現實卻是成立的,也總是小說中特別好特別深刻的片段;推理小說並不信任人個別的思維和反應,它相信一般性,這是它的基本限制─賈庫在路仁娜吞藥之前就開車離境,此時他已傾向於相信毒藥是假的,是他老朋友史克塔醫生的一個溫暖的玩笑(「他曾經相信:那小張衛生紙一直包著死神,其實,它只包著史克塔沉默的笑聲。」);他也回頭檢視著自己內心最深處那一絲順勢的殺意,持續想著杜斯妥也夫斯基《罪與罰》中以斧頭砍殺放債老婦的雷斯科尼可夫,思緒順著鄉村的車行清風往上飄,從自身,到國家,再到人類歷史和世界,具體的死亡乃至於禍福逐漸稀釋並隨之蒸發──
《賦別曲》,從戲劇結構來說搭建得非常巧妙,太巧妙了,一種誇大的、難能置信的、但偏偏
一切就如此準確的巧妙,每一人每一物每一個稍縱即逝的時間點和人心念頭都被撿起、被嵌入、被利用並且得到解釋;結局也擺放得文風不動,每個人都得其所哉,滿心安適的離去。但和典型推理小說最顯著的不同在於,這不是凶手的精妙設計步步為營結果,因為這個戲劇性主結構的完成包含了、而且依賴著太多無可預期的、不必然發生的意外和人不確定的心思。對推理小說而言,偶然是流沙是雜質,是建築結構裡不合法的材料,當然,好一點的、膽子大一點的推理小說也會試著馴服一些偶然,讓小說顯現出某種見機而作的機智(還有人沒看過電影傑生‧波恩三部曲嗎?尤其是第三集開頭波恩護衛著英國記者逃避狙殺的經典一段,波恩利用的全是現場隨手抓來的物件和那些一閃即逝的時間差隙縫,這於是成為一次無法重現的逃亡),但這裡仍有某一道天條也似的界線存在,越過這界線,戲劇結構就崩塌了,人也失去了駕馭能力乃至於自主能力,交給了命運的鬼使神差,它會更像是我們現實人生而不是一部小說,也就是波赫士曾經指出的,某本書裡存在著一個這麼難以解釋的角色,原因在於這最可能是照著真人寫的,某些事只在我們人生現實裡才發生。
昆德拉知不知道《賦別曲》是個太巧妙以至於太脆弱的故事?我得說,我自己在小說閱讀時好像一直聽到他不懷好意的笑聲。他曾經比較過托爾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和喬哀斯的《猶力西士》,指出來這兩部小說都正面向著無時無刻源源不絕襲來的偶然碎片,這些某一時刻在人腦際閃過、到下一秒就完全消失的東西,在喬哀斯那裡這只是人心迷航但什麼事也沒發生的尋常一天,而在托爾斯泰筆下卻促成安娜突如其來的自殺悲劇。昆德拉以為,托爾斯泰做到了比較困難的事。
我們也可以就這麼直說,既然你我所有人都早曉得偶然近乎無限的存在,這也就意味著所有傻傻寫小說的人一樣都早知道了不是嗎?但知道偶然存在是一回事,想方設法捕捉它、看清楚它是什麼東西、追蹤它鬼魅般的變化軌跡及其微量影響、並成功在自己的書寫理解它消化它,這又是另一回事。後者是只能一點一點、一次一次精密從事的工作,而且危險,因為小說要收納、消化愈大量愈捉摸不定的偶然(想像它每一個都不一樣大小、都長不同樣子),便得被迫一再改變自己破壞自己,一直到小說被逼到自身存在樣式的臨界點,如安博托‧艾可講的,你永遠無法製成一張跟現實一樣大小、一樣保有全部細節的地圖,因為那直接就是現實世界了,小說也就喪失了自身的邊界泯滅了。所以《猶力西士》的真正成就不在於小說這才首次發現了數量無限大且不斷岔生的偶然存在,而是它極具說服力也虛無的宣告幾世紀以來這道小說之路的到此終結,小說永遠無法一次馴服全部的偶然,同時,不會也不再需要有下一部《猶力西士》。
也就是說,早在《戰爭與和平》書裡托爾斯泰所揭示的歷史微積分,做為小說認識的一種極
限,事隔百年,喬哀斯打造出這個偶然的大博物館,實證的將它們一次展示出來。
回到《賦別曲》來。誰殺了路仁娜?既然路仁娜之死是一連串偶然參與的結果,而偶然又全是可替換的(B偶然取代了A偶然,酒店裡歐爾佳先一步進來撿走了鎮靜劑云云),因此凶手也就不必然非賈庫或路仁娜自己不可了,當然也可以是小男友、富翁這兩個一樣和她有性關係的人或路人甲;甚至,死的也不一定非路仁娜不可,誰說最像死者的人就得真是死者,讓劈腿的柯利墨得到報應不好嗎?或這顆毒藥繞一大圈、浪子返鄉般回頭毒死創造它的醫生史克塔不更好玩嗎?還有,可以從頭到尾根本沒有人死不是嗎?大家誤會一場,在這溫泉勝地愉快渡他幾天假,只有我們這些手心冒汗的讀者知道,死神的鋒利鐮刀曾怎麼堪堪從這些人頭頂上掃過。
多年來,我自知自己是沒能耐寫小說的人,想像力嚴重不足;但如果連我都能在三分鐘內想出一堆其他可能,相信我,那些專業的小說書寫者只會察覺得更快更多。
說明
盡頭,這次這個書名倒是我自己取的,沒有麻煩任何人,惟實際的內容絕沒有此一書名顯示的這麼「巨大」,當然更不會像看起來這麼悲傷這麼抒情。
不是所謂的全書主題,這只是這兩年半書寫時間裡自始至終徘徊腦中不去的有用概念,我以為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不管當下想的寫的是什麼,如同一種根本的意識,一種時時處處的自我提醒,因此,我特別記下它來。寫上一本《世間的名字》當時,我一直想著的是「極限」,太陽會燒完自己,小說會哪天寫完它的全部,各種自然的、以及人的事物各自能做的和做不到的邊界究竟何在,包括其空間的...
目錄
說明
溫泉鄉的屍體路仁娜
回布拉格開同學會的伊蓮娜
特洛伊十年後的海倫
畫百美圖的俠客金蒲孤
抄寫在日本墓園裡的王維
擺攤的寫字先生臥雲居士
不那麼擔憂電視的錢永祥
每天都在查禁書的唐諾
回憶四十年前柏林童年的本雅明
負責發明新病的小說家豐瑋
念自己小說給祖母聽的林俊頴
那位從紐約找上門來的NBA迷
放棄繪畫、改用素描和文字的達文西
叛國的六十二歲間諜卡瑟爾
忘了預言金融大風暴的克魯曼
在湖水上唱歌跳舞的卡欽那
隨西伯利亞寒流入境的藍仙子
說明
溫泉鄉的屍體路仁娜
回布拉格開同學會的伊蓮娜
特洛伊十年後的海倫
畫百美圖的俠客金蒲孤
抄寫在日本墓園裡的王維
擺攤的寫字先生臥雲居士
不那麼擔憂電視的錢永祥
每天都在查禁書的唐諾
回憶四十年前柏林童年的本雅明
負責發明新病的小說家豐瑋
念自己小說給祖母聽的林俊頴
那位從紐約找上門來的NBA迷
放棄繪畫、改用素描和文字的達文西
叛國的六十二歲間諜卡瑟爾
忘了預言金融大風暴的克魯曼
在湖水上唱歌跳舞的卡欽那
隨西伯利亞寒流入境的藍仙子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
 17收藏
17收藏

 42二手徵求有驚喜
42二手徵求有驚喜






 17收藏
17收藏

 42二手徵求有驚喜
42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