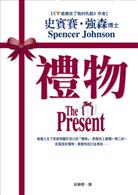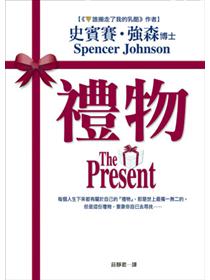二○○一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三月九日,我進行一項任務,了解並協助UNHCR在獅子山和坦尚尼亞的單位照顧難民。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我在往非洲的飛機上,將於巴黎機場臨停兩小時,接著到象牙海岸首都阿必尚。
這是旅程和日記的起點。我不知道為誰而寫--我猜,是為自己,或為任何人,無論你是誰。我並非為讀者而寫,是為所寫的對象而寫。
我真心想幫忙,不相信自己和別人不同。我想,我們都希望得到正義與平等,想要有機會去過有意義的生活。所有人都願意相信,如果身處逆境,別人會伸出援手。
我不曉得這趟行程會完成什麼事情,只知道每天越來越了解這個世界及其他國家,就更明白自己的無知。
我做了許多研究,並且和華盛頓UNHCR的許多人談過。我盡可能地閱讀資料,發現驚人的統計數字以及令我心疼的報導,也讀到許多令人作嘔的內容。我因此作了惡夢--不多,但嚇人。
我不懂為何有些事會被談論,有些則不。
我不懂為何認為自己可以造成任何改變,只知道我想去做。
我不確定是否該動身,仍不確定,但--有些人可能認為是錯的--我想到那些沒有機會的人們。
有些朋友認為這很瘋狂,我居然想離開溫暖又安全的家。他們問:「為什麼不能就在這裡幫忙?為什麼必須親眼目睹?」我不知該如何回答,也不確定自己是否瘋了或傻了。
父親試圖取消我的行程,去電UNHCR美國辦事處。但既然我是成年人,他就阻止不了我。我對他感到憤怒,卻也告訴他,我知道他愛我。身為父親,他試著保護我免受傷害。我們互相擁抱並相視而笑。
母親看著我,彷彿我是她的小女孩。她泛淚光對我微笑,擔心我。擁抱我道別時,她告訴我來自我哥傑米的特有訊息:「告訴安潔,我愛她。如果害怕、難過或憤怒時,記得抬頭看夜空,尋找右邊第二顆星星,追隨它直到天明。」那源自我們最愛的故事之一--《小飛俠彼得潘》。
我想著那些人,我讀過許多關於他們的事情。他們和心愛的家人分離,沒有家,目睹所愛的人死去,自己也瀕死。而且他們毫無選擇。
我不曉得即將前往的地方是什麼樣子,卻期待見到這些人。
我的第一站是在巴黎停留幾小時,然後轉往非洲。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在來自巴黎的飛機上,有位非洲人穿著質感很好的藍色西裝,他熱情微笑地問我是不是記者。我說:「不是,只是一個想認識非洲的美國人。」他說:「很好!」
他似乎是位重要人物,身邊圍繞其他穿西裝的人,都對他以禮相待。他和隨行的人一起下飛機時,兩名軍人一前一後地帶路。當他問候另一位重要團體代表,一旁有攝影機捕捉他的鏡頭。
我將這些情形全部記錄下來是因為,他在飛機上問我,是否要到非洲其他地區。我告訴他:「獅子山。」他說:「我怕那個地方。」
飛機降落象牙海岸後,我見到來自UNHCR,十分親切的霍夫。他說法語和一些英文,我則會說一些法文。但我很快就知道,微笑和肢體語言有時就能代表一切。我們安靜地並排站著,因為我的行李最後一個下飛機。
每個人的行李都被打開檢查。
現場的軍人比百姓還多。
接著,我見到另一名UNHCR的人員。
我們在車裡談論獅子山的內戰。
變成今天這樣子前,他們和美國人沒什麼兩樣。當他們在這個有影響力的廣大陸地上,決定五十二國的未來時,你會了解幫助和支援他們是何等重要。
把非洲人民當成伙伴,幫助他們建設,結果反而是幫了我們自己。
我發現美方濟助甚多,不容忽視,但相對其他國家仍顯較少。我們擁有比他國多的資源,付出卻相對少。
撇開政治面,基於人道立場,我們應該知道何謂當務之急,了解人人生而平等。
我們應該在人們嘗試及組織的初始就伸出援手,而非等到為時已晚。
冷戰期間,非洲分裂。他們在六○年代獲得獨立,但當冷戰結束,非洲人民需要協助以鞏固民主。
它需要協助去支援那些群眾,他們擁護我們共同信仰的自由。
我在獅子山看到一卷錄影帶。
幾年前,他們為民主而走上街頭。我忘了是哪一年,但是在最慘烈的戰事開打前。
假如當時我們能伸出援手,也許就不會像現在這個樣子。
我們不能忘記美國的開國元勳也是流亡人士。
之後,印第安人成為難民。
接待我的那個人談到他在美國的日子。我們都意識到美國民眾接收的消息少之又少,彷彿被過度保護,矇在鼓裡。但他們的優點在於,看見世界各地所發生的慘事時(從CNN的特別報導到偶爾出現的報紙新聞),大多數的美國人會十分樂意幫忙,非常慷慨。
他告訴我,他曾去密蘇里州的堪薩斯城過一次耶誕節,也和我分享其他在美國的經歷。我想,他花時間到美國旅行,目的是「想了解美國一點」。
我們之中卻很少人到過他的出生地--西非馬利。
他想和我分享他的國家,那可能是他如此好客的原因。
我入住在象牙海岸阿必尚的飯店。這間飯店想必風光一時,它比我預期中來得好。待在此處,我有罪惡感,即使只有幾個晚上。我要在阿必尚和UNHCR的人員開會。星期六就要前往獅子山自由城,和難民一起。
我必須承認實在很感謝能有適度的熱水澡和睡眠。我知道今晚要享受這一切,而且心存感激。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我坐在阿必尚UNHCR辦公室的椅子上,度過漫長的早晨。
我得知許多事情,然而,仍有許多不知道的部分。重點是,我明白自己對這些人的體認如此微薄。
我坐在一則標示下方--UNHCR的海報。上面寫著:變成難民不需要多,種族或信仰就已足夠。
他們允許我加入與「尋求政治庇護人士」的面談。
這些「尋求政治庇護人士」到這裡請求居住在國界的機會,而該國家異於他們的原生地。
UNHCR會傾聽對方的遭遇,有時還會確認真實性。他們盡可能地伸出援手,並試著裁定對方是否符合資格,歸類為難民及尋求政治庇護人士。
這些人必須證明自己需要保護和支援,亦即任何可行的保護和支援,而這在許多國家並不多見。
今天來面談的這對年輕夫婦與兩個孩子失聯了。先生三十歲,妻子二十五歲(和我一樣)。
他們看來比實際年齡老得多,身子相當虛弱,眼神充滿悲傷且絕望。他們都說法語和彆腳的英文,十分理智。
他們試圖讓我自在些。
UNHCR人員介紹我是美國人,來非洲嘗試了解並學習,協助將類似他們的遭遇傳回美國。
我很高興可以感受到他們懂得有人正試著幫忙,但聽過他們的故事後,我覺得無助,卻同時充滿決心。
他們都是既堅強又聰明的人。假如適時給予機會,再加上現在造成國內分崩離析的那些資源,他們可以成為非常強大、富裕的國家。
UNHCR這類的團體偶爾也會力不從心,因為現狀仍是進行式,無法改變。不過,了解難民的狀況以及工作人員所有的努力之後,我發現他們真是犧牲奉獻。
我們都該心存感激。
我相信,沒有他們的介入,難民根本沒有希望,大部分的人都會死亡和被遺忘。
反叛軍和獨裁者會掌控一切。
我們必須繼續援助非洲國家,接受難民,給他們一個家。
本國和他國持續會有難民越界,除非能鞏固他們原來的國家。二月二十三日,星期五
隔天,我到另一個辦公室,遇見艾歐莉。她要我坐下,教我更多事。她精力十足、充滿熱情,還露出令人開懷的笑容。
我學到新電腦科技,能協助計算、認證,並發給難民身分證。
聽到有不同的捐贈儀器以及新方法實在令人振奮。
微軟在科索沃危機時捐了一百台身分證機器。然而,需要有更多技術人員會操作。驚人的是,許多事情必須考慮進去,因此,他們正集資進行訓練課程。
在這裡,這些身分證何等重要,不只為了保護難民,提供安全庇護。最重要的效益在於,當難民前來登記時,卡片會賦予獨立身分。
你可以想像一下,無法證明自己是何種感覺--沒有名字、國籍、家庭或年齡的證明。
缺乏身分證的孩童可能被迫從軍或進行危險勞役,也可能被帶離學校或不予就學。每個孩子都有求安全和受教育的權利。
午餐時刻,我到小型市集買當地的手工藝品。
由於固定站得太久,被一些小到看不見的小蟲叮咬,腳踝開始發癢。
某些地方有腐臭味,令人作嘔。
這裡求生的力量令我驚訝。他們不抱怨,甚至不乞討。
與一般人對該國的印象相反,這裡民智開化,人民堅強、自負,令人震驚。他們充滿幹勁完全是為求生存,沒有時間過得隨性或懶散。
記錄這些細節時,我覺得自己彷彿在動物園觀察他們。
我自以為對他們無所不知,了解他們的掙扎。這種想法讓我覺得既愚蠢又自大。
但我純粹只是在象牙海岸觀察人群。這是我在非洲的第一站,也是唯一到過的非洲國家,甚至還沒見到難民營。
路上有好多學生。男孩子穿著米色衣服,短袖襯衫和長褲;女孩子則是白衣藍裙。
市集中出售大量黃金和象牙--甚至還有鑽石。每樣東西都堆在桌子上。地上全是泥巴。
一位UNHCR的女士--黛姆願意帶我四處逛逛。
我碰見她女兒和朋友,全都十四歲,上國際學校,會說多國語言。他們來自世界各地,十分有趣,每個人都是獨特的個體。
他們夢想未來,比美國的青少年來得成熟許多。
他們都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度。有個女孩問我對美國現任總統布希的看法。
他們也看過許多電影。我希望他們看到的好片跟搞笑片一樣多。但在這裡,能令人發笑似乎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