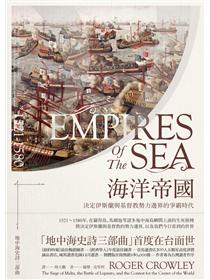推薦序
時值二十年代末,艾力•布萊爾(Eric Blair)辭退駐守緬甸皇 家警察職務,返回英國,五年來他目睹並體驗英屬殖民地之各種怪現狀(詳閱其相關散文The Hanging《絞刑》1931,Shooting An Elephant《射殺一隻大象》1936),身心皆疲,他思索個人生涯去向,決意全力投身寫作。
一九二八年他到了巴黎,持續創作不綴,但他所寫的諸多長短 篇小說未獲青睞,沒人願意出版,據他自稱從此把手稿都銷毀了;這兩年期間,他在饑餓邊緣掙扎求存、充當飯店雜工、苦撐不見天日的勞役,回到倫敦後,因緣際會被迫當了一陣子流浪漢,對英國 的慈善制度著墨甚多,他在兩地低下層社會之所見所聞、眾生相描繪,反成了第一部著作的材料。
布萊爾深知若若用真實姓名發表這部半自傳旅遊散文,一定會嚇壞了雙親,讓家族蒙羞,因此他選擇了了流流浪浪期間最喜愛的化名: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喬治是守護英國的聖徒,歐威爾是自幼熟知的河流。他以這筆名陸續出版了許多著作,包括家喻戶曉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與《1984》。
《巴黎倫敦落拓記》顧名思義分為兩個部份,第一人稱的「作者」敘述在巴黎與倫敦窮困潦 倒的遭遇。巴黎篇一開場,貧民窟街景即生動地呈現眼前——「路 旁是些高聳的房子,斑駁不潔像害了痲瘋病,且怪異地東倒西歪,彷彿在坍塌之際凍結住了。所有的房子皆是旅舍,房客爆滿擠至屋頂,大部份的房客是波蘭、阿拉伯與義大利人。」(見19頁)——想當然爾,旅舍的房客龍蛇雜處,各種怪異超乎想像的人物在作者筆下活靈活現,歐威爾對此有獨特的見解,「貧窮使他們免受常態的 行為模式所束縛,正如金錢使人們免於勞役」。
就旅遊文學的層面而言,《巴黎倫敦落拓記》或可稱得上延續英國文學史的脈絡,遙遙呼應喬叟的中古世紀《坎特伯里故事集》(Canterbury Tales),歐威爾在巴黎收集到的「故事」特多,並以獨立的章節處理,不尋常的房客查理就貢獻了三則,侍者瓦蘭第差點餓 死的喜劇,歐氏與夥伴波力斯碰上俄國詐騙集團等,光怪陸離當中 瞥見人性幽微,加上大大小小的插曲軼聞,造就豐富的敘事肌理,精彩引人。
(文中提及不太願意與俄國「秘密組織」扯上關係,因為巴黎警方已懷疑他是共產黨而盯上他⋯⋯,事實上,歐氏因其政治傾向,確曾 長期遭受英國當局監視,顯然「老大哥在看著你」並不僅限於極權國家。)
然而,誠如作者所云,「貧窮」才是主題,隨後就是與饑餓奮戰的過程了。「挨餓」攸關生死,歐氏花了相當多的篇幅討論細 節,如何一步步戲劇化邁向窮途末路,過程中他強調「維持門面」(不讓他人得知經濟狀況),此點似乎反映了其出身背景,家道中落仕紳階級應對之道。最後他發現所有的偽裝不得不剝除後,坦率面對反而是種解脫。綜觀巴黎篇,當鋪似乎是供窮人紓困的唯一機構,典當衣物極之稀鬆平常,與勢利兼捉摸不定的法國當鋪打交道成了必要之惡。
籠罩全書的陰影就是「挨餓」,歐氏不斷用鮮明的意象形容這狀態:
「你發現一個人只要吃上一星期的人造奶油與麵包,已不能再算是個人,只是個胃加上些附屬的器官」(見35頁),精力低落陷入窮極無聊,唯有食物才能引發動力。
「饑餓使人衰退至一種完全沒脊椎、沒腦袋的狀態,像是罹患感冒後的症狀效應。似乎整個人已變成了隻透明的水母,或是全身的血液都已被抽乾,替換以溫白的水。徹底的倦怠是我對饑餓最深刻的印象;此外,就是得不停地吐痰,痰液是種奇異的白色叢毛 狀,像是布榖鳥的唾液。我不曉得是甚麼原因,但所有挨餓過好幾 天的人都有這現象。」(見53頁)
更讓人驚訝的是,歐氏化身作者描述「親身遭遇」的筆調異常冷靜,毫無自哀自怨的成份,客觀宛若新聞報導,就如同他呈現其 餘房客的故事,精確不加批判,行文走筆常見幽默感。
當時「經濟大蕭條」(1929-1933)已開始影響歐陸,失業者眾 多,歐氏聲稱巴黎有數以千計的人過挨餓的生活。
通常冒險犯難的主角都有位「搭檔」,作者在巴黎的親密夥伴 即是波力斯,熱愛軍事的俄裔前軍官,極之活潑鮮明的角色——兩 人找工作的歷程,反映了不景氣社會之世道艱困、人心險惡,邊挨 餓邊求職的磨難娓娓道來,連烹煮分食都充滿了「內心戲」。
託波力斯之福,兩人終於在大飯店謀得一職,就此進入刷盤子雜工(plongeur)的苦勞世界,透過歐氏繁複而又有條不紊的敘述,讀者宛若身歷其境、在地窖的煉獄廚房內串演「千手觀音」應接不暇⋯⋯;歐氏不僅詳介刷盤子雜工的工作內容與技巧,更由外至內深討其身為人類的存在本質(詳見第二十二章),就勞動力而言,刷盤子雜工從事的是「毫無意義」的勞動,他卻不得不長時間苦幹以維持生計,沒餘裕休閒、另謀出路或作任何改變,歐氏將之類比為「奴隸」,並質疑為何如此奴隸型態會在現代社會沿續?
第二十二章的內容是相當複雜的辯解,在此可以讀出歐氏強烈的社會主義傾向,他懇切認為:「如果雜工稍有思考,他們早就組成工會,罷工要求較佳的待遇。但他們無法思考,因為沒這閒暇;他們的生活模式已迫使他們成為奴隸。」
歐氏甚至將刷盤子雜工比擬作印度的人力車伕或是拖馬車的駑馬,共通點是三者提供的勞役皆是「仿冒的奢華」,毫無必要存在,既然如此為何還會沿續下去?答案是:出自對暴民(mob)的恐懼,讓暴民有事做。誰有這想法?當然是階級對立的富人名流,不 幸的是代表社會良知的知識份子也向富人靠攏,與「非我族類」的窮人劃清界限。歐氏對文人雅士的冷淡頗不以為然,認為他們從未接觸窮人,也沒真正體驗過「貧窮」,才會產生恐懼的臆想——富人與窮人的基本差異在於收入多寡罷了。
與其在歐氏身上貼標簽,倒不如說他確切關懷弱勢,呼應他曾說過的:「我站在被壓迫的那一方」(I stand with the oppressed)。
除了針對刷盤子雜工的「勞動宣言」,歐式也對巴黎飯店餐飲業的內幕著墨甚多,尤其是駭人聽聞的污穢——「污穢在服務區域 的各處化膿滋長——宛若穿透人體內的小腸,污穢像條隱密的脈絡 穿透這家龐巨俗麗的飯店」(見95頁),原來「食安」問題並非始自今日,員工處理食物顧效率顧不了衛生,飯店高價販賣品質低劣的餐飲,全副精力耗費在表面功夫等,簡言之,套用歐氏的話,他們不是提供好的服務,而是「仿冒」好的服務。
隔了八十年後閱讀《巴黎倫敦落拓記》,歐氏記錄當時許多現 象宛若「風土誌」,經過歲月漫長的洗禮,讓人質疑應該不復存在了吧?隨著廚房的設備全面現代化,刷盤子雜工超長的工時應該早已縮減,標榜著好幾顆星星的高級餐廳端出來的美食絕對是「要讓 人吃的」吧?歐氏筆下的搜奇錄絕對是餐飲進化史珍貴的一頁。
倘若是單純旳歷史文獻,審閱不免乏味,閱讀《巴黎倫敦落拓記》的樂趣之一是歐氏的文筆,明明是敘述相當悲慘或不堪的情況,「詼諧」之意卻經常溢出言表,間中描繪景觀,更是線條勾勒 簡潔、蘊含詩意。
譬如黎明匆忙趕去上工,抬頭瞥見「天空像是片龐巨的鈷藍色扁牆,黏貼其上的黑紙是幢幢的屋頂與塔尖」;傍晚放工後回到街道:「迎見街燈的光暈——巴黎街燈散發出奇異的紫光——跨越過河面,艾菲爾鐵塔上從尖頂蜿蜒繞行到底端的空中廣告牌閃爍發光,宛若眾多巨大的火蛇。」
巴黎篇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第十三章,從身為刷盤子雜工被勒令剃掉髭鬚說起,歐氏以其敏銳的觀察力,歸納出飯店員工自有一套階級組織,「每個人的地位就像軍階般劃分得如此精確」,潛規則之運作無所不在。每個階級因職責與薪水多寡而劃分,各有不同的功能、特色、引以為傲之處,相互牽制與鬥爭,但又有志一同 撐過繁忙時段⋯⋯,「飯店能順暢運轉,主要是所有員工都對自己的 工作衷心懷有優越感,儘管這聽起來既愚昧又可笑」(見90頁)。走筆至此,忍不住聯想起歐氏若干年後出版的《動物農莊》(Animal Farm),牲畜遭劃分級別的角色結構,智力高低體能強弱有別,但每種動物都發揮所長、拼死拼活才把強敵驅走。顯然歐氏在巴黎的刷盤子生涯汲取了不少寫作養份,日後應用在創作裡,譬如《動物農莊》裡的「老少校」臨終前向牲畜群發表的演說:
「同志們,我們的生命有甚麼意義呢?坦率面對吧:我們卑苦一生,服無窮的勞役,壽命卻又如此短促。我們生下來,只獲得恰 好不會餓死的口糧,但凡有力氣的皆被迫做苦役,直到流盡最後一 滴血汗方休;一旦變成無用的廢物,即遭殘酷屠宰了⋯⋯。」
將幾個關鍵字眼稍微修改一下,幾乎就是刷盤子雜工的生涯宣言。
此外,侍者在歐氏眼中也是極為特殊的人物,他在巴黎篇也花了不少筆墨描繪其特質——虛榮、勢利眼、心態偏向資方、愛夢想畫大餅等——《動物農莊》裡愛美的白牝馬「茉莉」與主人的寵物烏鴉「摩西」,或多或少分享了上述特質,擬人化的角色綜合。
經歷了兩家餐廳後(另一家預算不足、打工條件更嚴峻、剝削 更明顯),歐氏大概已撐不下去每天十八個小時的苦勞,委託經紀人另覓差事,毅然揮別巴黎返回英倫,略微修改一下,亦可用海明威被引述得熟爛之名言作總結:「如果你年輕時有幸待過巴黎,那 麼巴黎將會跟隨你一輩子,因為巴黎是『一場又一場無盡的勞動苦 役』。」
倫敦篇的時間框架其實只有短短一個月,因僱主出國了,講好的差事無法履職,作者僅剩有限的經費,流落在倫敦青黃不接⋯⋯,即便只在街頭閑晃,歐氏也能以新聞報導的手法,扼要列比雙城印象:
「待過巴黎之後,這裡的一切感覺有些怪異;週遭比較整潔、安靜,也更陰沉。你不禁想念起電車的尖鳴,後街嘈吵頹敗的生態,以及騎兵隊踢踏穿越廣場。民眾穿得較整齊,臉孔也較平和溫馴,缺乏法國人的狠勁與強烈的個人特色,這裡較少看到酗酒現 象,灰塵較少,爭吵較少,無所事事的人卻多很多。三三兩兩的人群站在街角,看起來有些吃不飽,純靠茶與兩片吐司支撐著,倫敦人每隔兩小時就食用的玩意兒。甚至連呼吸的空氣似乎都比不上巴黎的狂熱。這裡是茶甕與勞工介紹所的國度,就像巴黎是小酒館與 血汗工廠的國度。」(見146頁)
待在異國,再不濟還能賣命打工,回到家鄉後遭遇似乎更悲 慘,直接淪為流浪漢,並且還得設法更換上低劣的衣物,以便「躲躲藏藏」融入該階層。作者已點出倫敦與巴黎的社會風貌截然有別,同樣是貧窮與挨餓,倫敦篇揭露的是游民與乞丐的生態。
自夜宿的需求談起,作者從最初的「民宿」到公共宿舍,盤纏用盡再至政府的臨時救濟所——完整地參與了游民的生活圈,深入體驗個中三昧。書中的第三十七章即詳列了各種夜宿的據點,從免錢至收費高低不等,包含公私營、慈善機構等,讀起來有點像「教 戰手冊」,實則包含了不少建言,光顧的是弱勢團體,收費機構竟 然大有利潤,更應該提供對等的服務。倫敦篇大量描寫了公共宿舍與臨時救濟所內的情景,設施簡陋,衛生條件惡劣,龍蛇雜處,擠滿了孤、老、貧病者,夜晚根本難以好眠⋯⋯,種種狀況,不禁讓人聯想起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筆下《孤雛淚》(Oliver Twist)十九世紀低下階層的氛圍,而歐氏更親身感 受到福利政策的諸多弊端,譬如:派發餐⋯取代現金,讓不良商家有 機可趁,進一步剝削了游民的糧食配額;不分冬夏,游民得不斷在 外行走遷徙,因為規定一個月內不得重複投宿同一家救濟所。
參與慈善事業的還有宗教團體,歐氏記錄了數起教會「賜茶」事件(其中一起還涉及游民以多數「欺凌」寡少會眾,頗有鬧劇意 味),聖經有云施比受有福,為何受者毫不領情?此外,還有神職 人員擅闖入寄宿舍作禮拜,遭受全體住宿者漠然以對,視之為不存在,讓前者每回皆霎羽而歸⋯⋯,套句書中帶點嘲諷的評論:「這可奇怪了,一旦你的收入降至某個水準之下,人們理所當然覺得有權利 向你佈道、為你祈禱」。歐氏不但闡明了人性隱藏的弱點——「其實接受慈善的人總是在痛恨行善者」——他也毫不留情批判了基督 教會的行善手法。
鑑於福利政策之荒謬,造成當時社會的怪現象:「太怪異了,有這麼一群人,數以萬計,在全英國上上下下行進,就像為數眾多『流徙的猶太人』」,在第三十六章,歐氏專門探討遊民的本質,或更貼切地說,導正公眾對遊民的偏見、其妖魔化形象——與巴黎 篇第二十二章申論刷盤子雜工有對等意義——並細數「三種特殊的邪惡」,前兩項挨餓以及與女性隔絕或許顯而易見,最後一項「強迫怠惰」卻是一般知識份子難以體會的,對習於勞動或農作的工人而言,終日無所事事、空白漫長的虛耗,有力無處使才特難抵受。 從社經角度綜觀之,無論對國家或個人都是生命與人力無謂的浪費,習以為常的程序,一經歐氏揭露格外顯得愚蠢:「每一天他們(遊民)耗費數不清的步行效能——足以耕犁數千畝田地、鋪數以哩計的路、建數十間房子——卻用在無謂的走路。每一天他們總計可能浪費了十年時間瞪著室內牆壁。他們每人至少耗費國家一週一英鎊,卻無絲毫回報。」(見215頁)
柏迪是作者在倫敦的夥伴,這角色具體而微承載了游民的特徵與習性,歐氏對他的批評毋寧稍嫌嚴厲,但另一位游民波佐,也是 柏迪的友人,卻得到頗高的評價。波佐是河堤區所謂的「人行道畫家」,其實與行乞只有一線之隔,英國的法律又讓這分野更趨模 糊。歐氏在第三十一章,劃分當時含有「行乞」性質的工作與等 級,並揭露其技巧(間中又有些傳奇小插曲),人行道畫家、街頭雜 技員、街頭攝影師、手搖風琴師等牽扯到「技藝」者,皆自認為是「藝術家」,等而下之是賣火柴、鞋帶、薰衣草粒,甚至引亢高歌 為「掩飾」的人員,因為英國法律嚴禁坦然行乞,至少要佯裝有買賣行為。歐氏由此引申「乞丐」的社會地位,他辯稱這行業與其他行業無異,同樣要付出時間勞力,只是行乞收入低、風險高,且受人鄙視。按照其邏輯,無用處甚至傷天害理的工作可多了,乞丐相 對是無害的寄生蟲,即使以道德觀念批判他,他遭受的苦難已夠抵 償了,他被人瞧不起主要是收入太低(嘩,這可是非常「資本主義」的辯證),世人哪管錢是怎麼賺來的⋯⋯,但請別忽略了歐氏申論的嘲諷口吻。
歐氏對文字語言的高度敏感在第三十二章展露無餘,整章聚焦於解讀倫敦的俚語與詛咒、其變遷由來、咒罵與文化的關係等。就如同文中所言,詛咒也隨著時間潮流改變,歐氏列舉了好些咒罵字 眼,因委婉而隱晦不明寫(當時人所皆知吧),超過半世紀再審讀, 已不確定所指為何。無論如何,歐氏深知文字語言蘊含的威力,反映在其後《1984》裡所創的語言運用,或顛倒是非、或箝制思想—— 文字,並不僅僅是詞義所示而已。本章所載口語資料不僅闡明了三十年代的社會背景,本身也成了珍貴的歷史記錄。
回到說故事的層面,隱約有一條線索埋伏全局,前後呼應,那就是「機運」(或曰「造化弄人」),要不是一開始書中主角在巴黎的旅舍遭竊,教英文的課程又戛然而止,讓他幾乎身無分文,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挨窮經歷了——從下水道工作的亨利,「厄運似 乎在一天之間使他變成了半痴呆」,到「時運不濟」的波力斯,在倫敦「多年來顛簸流浪卻毫無領悟」的女游民,再到身殘的人行道 畫家波佐⋯⋯,似乎每位怪異的人物都掙脫不了「命運的枷鎖」。連作者在當鋪典當衣物,獲款高低也得視運氣好壞,引用書中的描述「命運似乎開了一連串不怎麼有趣的玩笑」,然而瀕臨挨餓時刻,卻又常在路上撿到枚硬幣⋯⋯,從巴黎流浪到倫敦,作者深深體會人生運勢之跌宕起伏,並觀盡經濟大蕭條下社會底層的百態,眾生始終擺脫不了大環境因素的牽引。作者自謙其見聞並沒「超越過貧窮邊瀕」,但坦言「如果你身無分文的話,有這麼一個世界等著你」,全書即在描述這個世界,到底能做甚麼改善眾人的遭遇?歐氏行文敘事夾帶議論,感同身受針貶政策的缺失與積弊,他也提出諸多建議與 (可行或不可行的)倡導,所謂知識份子的良知,躍然紙上。
“Down and Out”本有窮途末路、落魄潦倒的涵義,本書譯作「落拓記」,「落拓」意指豪放而不拘小節,取的是「落拓而有大志」,畢竟歐氏只是過客(並沒有一路「落魄」到底,但也有人質疑 這些經歷是他日後罹患肺結核的肇因),他終究回到了作家本業,還 陸續完成了許多重要的著作。
身為譯者,最開心的莫過於能親炙喜愛作家的重要作品,並分享閱讀札記、眉批(美其名曰「導讀」),本書翻譯因種種原因拖宕多年,終於完工得以付梓出版,也是樂事一樁。希望讀者也能體認 本書之深刻涵義,且又不失閱讀之樂趣。
時值二十年代末,艾力•布萊爾(Eric Blair)辭退駐守緬甸皇 家警察職務,返回英國,五年來他目睹並體驗英屬殖民地之各種怪現狀(詳閱其相關散文The Hanging《絞刑》1931,Shooting An Elephant《射殺一隻大象》1936),身心皆疲,他思索個人生涯去向,決意全力投身寫作。
一九二八年他到了巴黎,持續創作不綴,但他所寫的諸多長短 篇小說未獲青睞,沒人願意出版,據他自稱從此把手稿都銷毀了;這兩年期間,他在饑餓邊緣掙扎求存、充當飯店雜工、苦撐不見天日的勞役,回到倫敦後,因緣際會被迫當了一陣子流浪漢,對英國 的慈善制度著墨甚多,他在兩地低下層社會...
 10收藏
10收藏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10收藏
10收藏

 17二手徵求有驚喜
17二手徵求有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