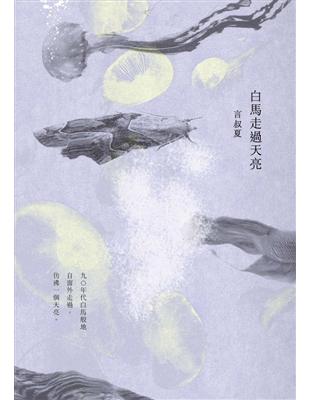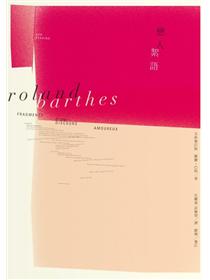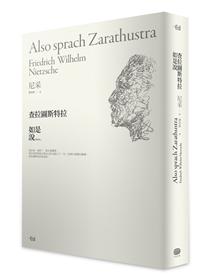★詩意且充滿畫面的文字,充滿想像力且曖昧恍惚的超現實氛圍,組合成獨樹一格的散文。
九0年代白馬般地自窗外走過,彷彿一個天亮。
好繁華的街一整條燈如流水,好勇敢的燈已經撐起一匹黑夜,好遼闊的夜又淹過來整條的街,每一間餐館都人聲鼎沸。我往下行走,譬若夜遊,宛如沿途賣夢。
言叔夏以其純粹,與被時間淘洗卻益發光亮的天真,書寫十數年間自南部小鎮到東部鄉間,再到城市盆地的人事流轉:日常的牙疼、上課,房間裡的衣蛾,以至於家人朋友間的死亡與別離。
彷彿住在水族箱中,以孤獨疏離的基調觀察著世界,僅任由想像力帶出一個接一個的畫面;言叔夏不刻意雕飾詞藻,輕簡幾筆便將事物都變成曖昧恍惚,且些微變形的超現實存在:哭笑不得的小丑,歡樂又憂傷的馬戲團,大象侏儒駱駝馬,穿著白鞋紅裙的小女孩,排成隊伍安靜地穿過空蕩無人的長街……字裡行間盡是詩般的語言與電影的畫面。
縱然面對的是生命的失落與憂鬱,無可迴避的死亡與別離,她卻能以極為世故又極為澄澈的文字,泯滅愛與殘酷、夢想與死亡、溫暖與冰冷的界限。在傾斜瑣碎的世界中,以一枝筆,呵護著一個既晦暗又純真的世界。
作者簡介:
言叔夏
一九八二年一月生。有貓之人。白晝夢遊。夜間散步。
東華大學中文系、政治大學中文所畢業。現為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曾獲花蓮文學獎、台北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
各界推薦
名人推薦:
幻燈之光/郝譽翔
在我教書十多年所遇見的學生之中,言叔夏實在是最優秀的一位。當然,我也不乏看過才華洋溢的青年,但卻沒有人如她一般,即使蜷縮在角落,仍難以掩抑上天賦予她的光輝。她不論寫起散文小說,讀書報告甚至考卷,無不洋溢出早熟的過人文采,令人訝異,讚歎,更不免起了呵護憐惜之心,就怕天才和早熟,有時反倒變成心靈不可承受的重負,壓折了還來不及茁壯的莖與枝。
言叔夏便因此一路戰戰兢兢地走來,以我對她的認識,這本書算是相當遲來的了,但也或許並不算遲,生命如此漫長,時代又如此焦躁紛亂,更需沈澱安靜,耐心以文字織就抵擋俗世洪流的牆垣。於是在這本書中,我讀到了在她看似柔弱的外表之下,一顆堅韌飽滿的心,一種純粹,倔強,或是自持,甚至被時間淘洗卻益發光亮的天真,從方塊鉛字之中汨汨穿透出來。
這也讓我想起了,年輕時代其實是不愛讀散文的,但若是為我所嗜讀著迷的某些散文(我在此不提人名,以免將言叔夏輕易劃歸入哪一流派),則便是與這本《白馬走過天亮》相近似,不刻意雕琢華麗的詞藻,而是運用最儉省之字,只消幾筆,卻能勾勒出奇異的畫面,如:「你的家,長出了河流。」(<用眼睛開花>)「我的地下室沙漠。長長的雨季在地面走過,五月的道路,幾乎是一條傾斜的海了。」(<馬緯度無風帶>)又如:「時光隊伍在白天鳥獸般地散開,在夢裡成群結隊地回來,在睡眠裡圍著螢火齊聲歌唱,然後再甦醒裡裡被全部遣返。」(<尺八癡人>)如此的例子不勝枚舉,彷彿這不再是一本散文集了,而是一本詩集,一部超現實的畫冊,或是楊思凡克梅耶(Jan Svankmajer)的動畫,甚至一頁頁的紙上電影,塔科夫斯基,安哲羅浦洛斯,費里尼。
故讀《白馬走過天亮》,宜把它當成詩般咀嚼,甚而享受視覺的饗宴,任由想像力的時空之軸,被文字不斷拉長,延展,並且容許曖昧恍惚的,夢一般的存在。在言叔夏的筆下,不論是愛與殘酷,夢想與死亡,溫暖與冰冷,皆是泯滅了二分的界限,彼此滲透暈染,讓人腦海裡不由得浮起了許多畫面:哭笑不得的小丑,歡樂又憂傷的馬戲團,大象侏儒駱駝馬,穿著白鞋紅裙的小女孩,排成隊伍安靜地穿過空蕩無人的長街,還有傑克豌豆,沃爾夫精靈,美杜莎,拇指姑娘,鼴鼠太太........。言叔夏一再地召喚純真,以抵抗這個正在傾斜下沈的世界,而在不可逆轉的死亡與腐敗中,卻仍要竭力地張開她那一雙未被污染的,清亮的眼。
這份堅持的姿勢,竟也使我們隨著年紀逐漸堅硬且冰凍的心,一下子,忽然變得柔軟了起來,彷彿被刺痛了似的,泫然落淚。然而淚是溫熱的,哀而不傷,也因此,全書雖然瀰漫著揮之不去的死亡,以及孤獨疏離的基調,但卻不致令人頹喪枯槁。書寫,是告別死亡的最好方法,而這也正是言叔夏一向所關懷的,從論文到創作,皆是念茲在茲不斷回心的主題。在這本散文集中,我卻看到了她對於死亡的詮釋,不是虛無,或是終結,而是以重返孩子的童稚狀態,扳回時鐘的指針,讓一切不可逆轉的,從此有了逆轉的可能,從黑暗中,見到光的萌芽。
而我也以為,這才是言叔夏身上最可貴的素質。這十多年來,她從花蓮到台北,從東部鄉間到城市盆地,從大學到研究所,時間與世俗的塵埃,卻不曾在她的身上駐足,反倒是更加琢磨出一顆有如鑽石般澄淨剔透的心來。而這本散文集就是她心靈的水晶世界,我在讀時,卻又不由自主地聯想起了許多年的某一夜,在北京王府井夜市看拉洋片,眼睛湊在小洞前,看著洞內另一光亮迷離的所在,彩色的剪影一一流轉,有人有動物,有街有樹,悠然而逝,沈靜又天真,若生若死,但就是不在人間,看著看著,我的心中竟忽然湧起了莫名的快樂與悲哀。
土星的環帶/黃錦樹
土星將要離開我的第四宮,四宮的尾巴天蠍座,於是今年的生日,在葬禮中渡過了。整個傍晚我們吹奏號角,圍著圓圈燒火紅蓮花,直到夜暗下來,周圍的景物退得很遠很遠。整個送葬隊伍被霧完全掩蓋。大霧散去,我忽然就只剩下自己一個人,在這個暗黑的平原上了。
有時我感覺自己來到世界,只是個空空的容器。承載世界。有時世界變成了海,就承載了我。好久沒有大哭。雖然我不清楚那是為了什麼。也許是時間。有人告訴我,土星是一個虛的實體,無法抵達,也不能登陸。它的環帶比它本身來得更真實。──Facebook of Camille Liu,12 Jan 2013
去年有位本地學界的朋友又在抱怨台灣本土學人對馬華文學的研究乏善可陳,我隨即轉寄一篇劉淑貞的論文給她看看,附了一句評語:「這論文比她老師寫的好太多了。」這種話或許會為她樹敵吧。但學術之路本也是條江湖路,有敵人也會有朋友,即使刻意廣結善緣的人也會經常中暗箭。最後憑靠的還是自己的實力,況且論文真正能傳世的也不多。
很可慶幸的是,台灣文學研究的領域近年出現了若干有潛力的年輕人,而且同時從事創作。劉淑貞無疑是箇中佼佼者之一。讀她的論文可以看到,在理論的廣泛涉獵之外,還可以清楚感受到有一股對文學的強烈激情。那種激情在她的老師輩的論著那裡幾乎是被徹底壓抑掉的(如果不是從來沒有過的話)。雖然,那也可能是種危險的激情,尤其在台灣學界論文急遽學術化、學究化以利數目字統計的年代。另外一個值得擔心的是,過度膨脹的台灣文學學術產業或許會讓積累畢竟有限的台灣文學不勝負荷。這份負面的冗餘或許會轉嫁給年輕的研究者,限制了他們的可能性。
聽說她也寫作,後來從《現代散文金典》裡讀到她的〈馬緯度無風帶〉、〈憂鬱貝蒂〉。前者是我近年來讀到的少見的散文佳作──因為某種我自己也難以說清楚的原因,大概有幾年忽略了年輕一代的寫作──也許還包括自己的寫作。
寫散文時她或許叫言叔夏,我不知道(也沒那好奇心去探詢)她還有哪些筆名。
爾後在她的部落格裡零零星星的讀到一些文字,羚羊般跳躍的意象,欲語還休的道出自身生命的某些傷害、失落、啟悟,或某種難以言喻的感思。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幾篇寓言或小說),我讀到的她的大部份寫作並沒有逾越現代散文的界限,這種自覺是很值得一談的。
我認為《白馬走過天亮》(九歌,2013)這部散文集是相當標準的現代散文──嚴格意義上的現代散文,是六0年代以來,由余光中、楊牧加以命名、概念化並實踐,從〈鬼雨〉到《年輪》到唐捐《大規模的沈默》,在台灣現當代文學裡斷斷續續的延續著的一種寫作。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台灣文學界對現代散文的自覺創造可以說是對五四抒情散文的侷限的嘗試克服(那一代的現代散文界碑是魯迅的《野草》)。進而言之,那也可能是克服抒情散文的有限性的一種(可能有效)的方式1。
和一般人的認知也許恰好相反,散文(這裡嚴格限定為抒情散文)在現代文學系統裡,可能恰恰是一種最不自由的文類。散文的寫作者很快就會意識到,它其實嚴格的被限定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它不像小說有虛構的自由,也不如現代詩有相似於小說的自由──藉由虛擬的核心、虛擬的情境,次第的展開詞語之花。位置介於小說和詩之間,因著它嚴格的有限性,它之被獨立對待,從文學系統的角度來看是非常勉強的2。大部份寫作者也近乎默契的默默遵守著這限定,少數逾矩者都會付出相當嚴重的代價。如果是文學獎的場合,那甚至是個准準法律問題(「詐欺取財,不當得利」),而不只是個道德問題(欺騙)3。
因此,它其實非常孤單,它被迫直面生命經驗,被逼面對個人經驗的單薄貧瘠。它得到的反饋或許是,它可能是最認真、最真誠面對生命自身的一種文類──它先天的告白特性、凝視自我,甚至反思性。
既然小說式的虛構之路是不被容許的(那是個禁忌),如果不想流於文字的白描,平舖直敘的自我暴露,唯一一個可以選擇的道路就是借鏡於現代詩。那條路徑我曾把它稱為修辭的拓展。但它不限於修辭,而涉及詩的各種技藝,甚至是戲劇化,這在既有的現代詩裡也有許多例證。戲劇化之路可能讓它趨近於小說,但現代散文似乎總是自覺的以主體生命的本真性為其核心。弔詭的是,那往往來自於傷害。罪是另一個可能性,那也有長遠的傳承,譬如西方懺悔錄的傳統。但為什麼歡樂不是?歡樂彷彿是另一個禁忌──在時間之流裡,歡樂容易被它的對立面沖淡、覆蓋、抵消。反之,感傷、悲哀往往有很強的存活力、感染力,可以一直發揮作用──甚至後遺的把未來的某個當下共時化為過去。寫作大概是直面它的最好的方式,也或許是防止它突襲的最好的方式。
雖然是老生常談,傷害往往是啟動書寫的那個按鈕,啟動一種與自我、與遠去的幻影之人的總結式的對話。
言叔夏的書寫似乎毫無選擇的從散文被規定的有限性展開4,以直面自身經驗的有限性、傷害的本真性。於是讀者可以清楚的看到一個年輕的孤獨女子,愛穿黑衣,愛孤癖,獨來獨往,大概慣於從情境中自我抽離為一個觀察者(〈尺八癡人〉、〈白馬走過天亮〉),那也是從小養成的自我保護的能力。她的出生不被祝福,和母親的關係相當緊張(〈閣樓上的瘋女人〉)。從台灣西部的鄉下到遙遠的、暗夜般荒涼的花東去求學。而後北上,有一段時間住在可以看見陌生的腳在窗外頭來來去去的走過的地下室(〈馬緯度無風帶〉),愛亂做夢(〈夢之霾〉)。而她也常常獨自品嘗寂寞,以致幾乎愛上自己蝸居的房間和衣櫥(〈袋蟲〉)。身為那一世代受專業訓練的文藝青年,敘事中偶爾會選擇性的暴露一些讀過的書(太宰治、邱妙津,Susan Sontag,本雅明)和電影,但也許刻意忽略掉的名字更為關鍵。譬如當詞語如此輕快的跳躍:「書名好像是一句法語,唸起來像一隻鼻子,我唸著唸著就覺得自己變成一隻大象。」「那布偶極愛轉彎,那轉彎的弧度極美,那傾斜就是一種正確,那棉花屑,沿路不斷掉落就宛如秘密的雪。」(尺八痴人)那隱藏的名字就出現了。那夏宇似的聯想,瞪羚似的跳躍,是一種文體練習。偏好格言警句,「心是辯術」,「連掌紋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辯術之城〉)「愛這樣遠,痛這麼近」(〈隧道〉)格言警句總是企圖排除時間。Eileen Chang?
雖然像穴居人那樣,那敘述者也需要外出覓食,上課、談戀愛、訪友、看電影、買書,都是些尋常不過的學生生活。但時間一長,感慨就深了。開篇的〈十年〉有相當的概括性:「十年裡我做了什麼?去了一個不喜歡的城市,搬四次家,和三個人分手,換了六份工作。十年裡外婆死了。」生命中關鍵的十年,順利的話可以從大學唸到博士(但文科往往需要更長的時間),取得社會上昇之路的基本資格。但青春的流逝是不可避免的代價,情感的創傷更難以預測。一度親密的情人和朋友,在時間中漸行漸遠後最終都成了大寫的英文字母。彷彿只有那說話的「我」是唯一的真實。敘事中的家庭劇場都是原生的,父母婚姻失敗,以致那原初的愛與依附都殘破不堪;斗轉星移,妹妹懷孕、生子,老輩衰老死去,新來者是全然的未知,生命流轉。葬禮,喪禮如通過儀式,在他人之死中局部的領會生之奧秘。而傷害,又何嘗不是種考驗?
那經驗主體還好不致太過脆弱如邱妙津黃宜君那般,彷彿渾身是風劃出的傷口。言叔夏第一人稱話語的敘述者自有一套詞語的魔術,她有能力爭辯(〈辯術之城〉),即使在她最憂鬱的時候也還保有幾分抽離的灑脫。
〈馬緯度無風帶〉或許是箇中最佳的案例。
一次情傷,背叛,被摧毀的原初的愛(初戀?)。但逼真性的細節一開始即被連串的比喻帶離開,蒙古人的大象,沙塵暴,沙漠,流沙,石頭,馬,駱駝,……大量的問號,猶如漣漪般一圈圈從傷害的核心蕩開。那核心,約莫是被利刃割傷了的純真。反覆出現「黑暗」這樣的意象,也一再把地下室的租處比擬為沙漠。時序推移,從四月到五月,那大概是最難熬的一段時間吧,她用了無風帶的比喻描述那種沈悶。但無風帶其實是個比沙漠有生命力的比喻,它恰恰是一狹長的虛擬的界域。相較於沙漠的乾枯、無盡的絕望,它其實已經蘊含著穿越的希望──代價必須是把那些馬(那些該割捨的)拋進海裡,減輕輜重。渡過之後,就可以感受到迎面而來的風了。
對書寫者來說,縱使不幸也是一種贈予──只要他沒被擊倒,就可以反向的吸收、轉化它。說來弔詭,這像是被信仰者(神)對信仰者的考驗。在一個絕對的意義上,所有的災難都是考驗,即使它帶著絕望的黑暗。因為神意難測,神的時間不同於凡俗時間。譬如猶太教徒召喚的彌賽亞,它到底何時到來?大劫難時何以總不見祂垂憐降世?身處黑暗時代的本雅明(淑貞愛引用的Susan Sontag〈在土星座下〉熱烈頌讚的對象)的答覆晦澀難解,近年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對它做了番細緻入微、但一樣不易理解的詮釋。「某些事物似乎並未發生,但實際上卻發生了。」5一如前陣子的末日預言,世界末日也許真的發生了,但我們並不知道,它被一股我們難以理解的力量抵消了。反之,彌賽亞降臨了,只是你我都不知道,也無法理解。
如果我們把那樣的解說帶到詩學的領域,或者說從詩學的角度去看,可以說,也許詩(辯證意象)即是那可能的神意。不論是對卡夫卡還是本雅明(還有一樣命運多舛的布魯諾‧舒茨),唯一真實的救贖是他們在災難急迫的陰影裡、在危機中寫下的那些神秘難解、彷彿帶著啟示的微光的文字。因著那些詩一般的文字,他們在後人眼裡往往被看成是在世的先知(雖然他們並不知道自己是先知)。那種從劫難廢墟裡奪回的灰燼般的事物,見證了書寫的力量,一種可以把時間喊停,共時化(一如意識批評論證的),甚至變更時間的矢量(「凡不可逆的皆可逆」)。任何有能力的書寫者從自身經驗的災難(甚至個人的悲劇)中,藉由文字向命運爭奪而來的、自身生命本真性的靈光,構成了作為有限性存在的個人的土星的環帶。
我們的被拋狀態無法選擇,但可以選擇與它搏鬥的方式。
謹與淑貞共勉之。
16 Jan 2013,埔里。
1但這一路徑不是沒有流弊,早在余光中的〈逍遙遊〉裡就可以看到修辭的浮濫膨漲。部分後繼者走過頭了,變成反複使用誇大格以致讓語言彈性疲乏。
2黃錦樹〈論嘗試文──現代文學系統裡的現代散文〉《中外文學》32卷7期,2003年12月。
3最近被揭發並引發討論的例子見鍾怡雯,〈神話不再〉《聯合報‧聯合副刊》2012/10/7。
4大概只有兩篇例外,〈用眼睛開花〉、〈Pluto〉。
5阿甘本著,麥永雄譯,〈彌賽亞與主權者:瓦爾特‧本雅明的法律問題〉汪民安主編,《生產》第二輯(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pp268
名人推薦:幻燈之光/郝譽翔
在我教書十多年所遇見的學生之中,言叔夏實在是最優秀的一位。當然,我也不乏看過才華洋溢的青年,但卻沒有人如她一般,即使蜷縮在角落,仍難以掩抑上天賦予她的光輝。她不論寫起散文小說,讀書報告甚至考卷,無不洋溢出早熟的過人文采,令人訝異,讚歎,更不免起了呵護憐惜之心,就怕天才和早熟,有時反倒變成心靈不可承受的重負,壓折了還來不及茁壯的莖與枝。
言叔夏便因此一路戰戰兢兢地走來,以我對她的認識,這本書算是相當遲來的了,但也或許並不算遲,生命如此漫長,時代又如此焦躁紛亂,更需沈澱...
章節試閱
袋蟲
我很喜歡房間。
很喜歡四面牆壁緊緊包圍著的感覺。在房間的中央抱膝蹲坐著的時候,總覺得好像回到了遙遠的地方。
令人懷念的氣息壟罩了上來。像是在孤寂的童年場景般的地方,無論經過了多久,都特地趕來的、某個重要的人,果真翻越重重的日夜,抵達這空無的、只有我獨自一人的洞穴般的房間,而與我相見了。光是為了這份心意,便令人感動得想哭。
雖然,並不知道是什麼人。但是,只要坐在房間裡等待,就知道他一定會來。
或許不是懷念。或許是很久以前失落的某種東西,遠在肉體被生下來前,就已經存在的一種觸感,穿透過潔白得不可思議的光芒,伸過來的一雙手,對我作出神佛般的手勢。不管在房間的任何一個角落,那手臂永遠溫柔地抱住著我。
房間是我非常重要的親人。
夜晚,我在不開燈的房間裡工作著。白天,就放下厚重的窗簾睡眠。
我是作息混亂得像是空中飛人般的二十五歲獨居女性。在井一般的房間裡紊亂地生活著。穿過的衣服、打發時間而隨意從書櫃裡取出的雜誌、坐墊、與積著薄薄灰塵的抱枕,在房間的四處裡散落著。不過,房間沒有發出任何怨言。
不會因為沒有日曬就忍不住抱怨。不會要求增加更多家具。
「本來就該如此的地方,不能勉強。」房間彷彿凌厲地對我說著:
「就算裝出再怎麼可憐的苦瓜臉,房間就是房間,頂多是個箱子。既不會變成夏威夷海灘,也不會變成河流。」簡直像是開光般的告白,房間不用軟弱逃避現實。
壁癌、腐蝕的水管、壞掉的燈、門口銹蝕的綠色信箱。
不管再嚴重的打擊,都將之視作物理性的敗壞。
我想,為什麼房間會有這樣意志般的堅強覺悟呢?彷彿是從有天地以來,就佇立在那裡的窟穴一般,靜謐地、安祥地存在著。有著敦煌石佛般的堅定眼神。
或許,那是因為它具有著人類所沒有的質素吧。
壞毀了也無所謂。被侵蝕了也無所謂。我就是我。而且今後也將繼續以我的形式存在下去。
彷彿聽見房間這麼說。
房間的外面,是一條靜靜流淌的河流。
不過,我卻很少到那條河邊。
在房間的陽台眺望著河水,看著傍晚散步的人們在河堤裡慢慢地走著,我覺得自己好像正在他們的身邊。
不需要特意地到「那邊」去,便覺得已經在「那邊」了,這是房間所教導我的事。
我無法想像不在房間裡的自己。
在夏日耀眼的陽光下行走著,穿著光線下顯得特別鮮艷的綠色T恤,穿越著午後安靜無聲的巷道。五官與輪廓,都因為強烈的曝曬,而變得輕浮了起來。痘疤也好,黑眼圈也罷,即使是再怎麼精緻的臉孔,一旦出現在商店街的櫥窗玻璃裡,被倒映著,無論如何看起來都像是連自己也不認識的別人,而令人愈發感到焦慮了起來。
不過,在房間裡的自己就不會這樣。
房間裡的鏡子所顯現出來的,總是陰涼的、樹蔭般的五官。可以讓人安心地在上面休息。
因此,即使只是到不遠處的便利商店購買食物,我也想快點回家,與房間相見。
萬不得已要出門的時候,我也勢必帶著房間。
那是像是電話亭般的設施,由隱形的玻璃所組成的四方箱子。當我移動的時候,箱子也跟著我一起移動。
如果遇到需要交談的對象,就拿起話筒,隔著透明的玻璃撥打出去,不管在街上、辦公室、學校或者電影院,房間以攜帶式電話亭的方式守護著我。
我想,如果在與朋友或者上司之類的人交談的途中,房間突然現身的話,一定會嚇到大家的吧。
「這是什麼東西呀?你在那裡面做什麼呀?而且,為什麼這個東西會跟著你到處跑呢?」
想必對方要是突然看到了,也會大惑不解吧。
不過,沒有人這樣發問過。
就像童話故事裡只有「聰明的人」才看得到的新衣,房間也是一種「國王的電話亭」吧。
像披著隱形斗篷般的背後靈。不管到了哪裡,總是發出幽靈般的叫喚。我的心無論何時都想與房間緊緊地結合。
簡直像是熱戀,分開的時候懷念得想哭,相見的時候又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每次分離都覺得此生可能不能再相見。
所以,我的房間幾乎沒有任何訪客。
房間喜歡著我,而我也癡狂地喜歡著它,在這漩渦般的戀情裡,容不下第三者。
不過,那個夜晚,卻出現了意外的訪客。
那是一種叫做衣蛾的蟲蛹。袋狀的灰白色外殼。不仔細看的話,還以為是掉了漆的水泥屑。平時總是懸吊在天花板的角落裡,像是水滴般地垂掛著。不過,那一天,在漆黑房間僅有的一盞昏黃光暈裡,一隻衣蛾啪!一聲掉落在我的面前。
「這是什麼?」
正當我好奇地將鼻尖湊近,想看個仔細的時候,桌面上那瓜子殼般的白色袋狀物竟然伸出了頭。我立刻驚嚇地彈跳開來。
不過,衣蛾顯然沒有理會我。
牠只是悠閒地伸長了脖子,打了一個愛睏的呵欠,像是從天而降的仙人一般地,在桌面光圈的平原裡漫步了起來。那個樣子,實在傲慢得令人火大了起來。
「開什麼玩笑,竟把人間當作了自己的天堂嗎?請睜眼瞧瞧看,這裡到底是誰的地盤呀!」
我立刻抽了一張衛生紙,砰!一聲地對著桌上正在散步的衣蛾拍去,衣蛾在皺成一團的衛生紙裡,很快地將頭伸進袋狀的殼蛹裡。牠的身體非常非常小,但是,卻拖帶著很大的殼。
打開電腦,立刻搜尋跟衣蛾有關的資訊。
潮濕的雨季會大量出現,陳舊的老房子裡也為數不少,衣蛾以石頭蛹的群像在房間的四處遷徙著。
也是辛勤的紡織者。蒐集灰塵與毛屑,編織成背上那灰白色的殼。
所以,衣櫥是衣蛾最喜歡的地方。
牠們總是愚公般地搬運著衣物上的毛球與棉屑,地板磁磚上的細小灰塵,排水孔裡短短的一根一根的毛髮,然後,在黑暗的夜裡,將那當作磚瓦水泥般地,一點一點蓋起了自己的房間。
所以,衛生紙裡被捏成一團的灰白色殼蛹,並不能真正殺死衣蛾。
牠總是躲在那灰白的、粉筆色的沒有生命跡象的殼裡,直到敵人遠離,便再次地,將那細長的、懶腰般的頭伸探出來,之後,悠閒地,愉快地繼續行走。
那一定是一張只有在顯微鏡下才能被看得仔細的五官。有很大的眼睛、鼻子、囓人的牙齒。
但是,在肉眼的世界裡,衣蛾所擁有的昆蟲的臉孔,只是原子筆墨水般的黑色小點。當我俯下身張看著從殼裡爬出頭來的衣蛾,衣蛾也正睜大眼睛看著巨人般的我。
一想到這一點,便覺得衣蛾是與我相同具有可以互相對視的眼神的某種存在物,而令人忍不住戰慄了起來。
凡是人以外的東西,只要擁有眼睛,就覺得對方與我似乎能夠用語言溝通。所以,餐桌上的動物,除了魚以外,幾乎都是沒有眼睛的東西。
光是注視著對方的眼睛,無論如何,就不能把牠當作食物般地吞嚥下去,因為,只要稍稍凝視著那彷彿還骨碌地轉動著的眼珠,便覺得有吃食人肉的罪惡之感,雞的臉、豬的臉、牛的臉,不在必要的時刻絕不上桌。
眼睛所傳達出來的心情,說明了一切。
那是超越了國籍、物種以及各種生物間的區別,是不能被歸類為任何一種語言的絕對性存在。在那不需要說話,就能彼此明白的話語裡,只有寬恕一辭可言。
我想,人類之所以能夠恣意地撲殺著衣蛾般的小蟲,正是因為看不見那微不足道的眼睛吧。
所以,徒手打死蚊子就像家常便飯,但是徒手打死蒼蠅卻總是令人忍不住噁心地想吐。那一定是因為蒼蠅的亡靈,以那斗大眼珠的方式,回來指責了人類了吧。
看著衛生紙團裡緩緩張開的衣蛾的殼,我突然有點害怕了起來。
因為,在那無機物所編造的灰白殼裡,所居住的,是和我有著同樣臉孔的生物。
在與我戀人般相戀的房間裡,還有別人存在,這件事讓我很不安。
夜裡,睡覺的時候,衣蛾總是懸吊在天花板上俯瞰著我。
洗完澡後,溼漉漉地走到衣櫥前,邊擦乾頭髮,邊換上衣服,衣蛾也低頭張望著我。
當我惡狠狠地抬頭回瞪著牠,牠總是蠻不在乎地吊掛在原處。
我想,那一定是因為牠隨時都拖帶著那棉絮織成的硬殼的緣故。
衣蛾所在的殼,是個比起自己那微薄的身體,還要來得大上數百倍的殼蛹。以人類來說,就像是一間游泳池般的大小。
不與同伴共用著同一個房間,也絕不背叛自己所在的殼蛹,不管生或者死,都跟房間相與共,衣蛾自律地、堅強地,在自己用灰塵打造出來的巢穴裡生活著。簡直像是肉體與肉體相連的伴侶。
為什麼衣蛾能夠恣意地擁有這樣的人生呢?那種像是宿命似的工作,彷彿一出生,就為了與房間相戀般地來到了世上,終其一生衣蛾都在做著同一件事。直到身體壞毀為止,而終於死在那自己編造出來的殼中。房間也成為了墓穴。
衣蛾的殼中,除了自己以外,什麼也沒有。但是,我的房間裡,卻塞滿各種東西。
旅行回來的紀念品、各時期拍下的大頭照片、分手的戀人所遺留的拖鞋、搬家時從另一個房間攜帶過來的書櫃、床單與家具。
我想,如果我也有一個游泳池般的房間,我所拖帶的東西與回憶,也絕對會塞滿整個游泳池,直到它再也吃不下為止。我不是衣蛾那種家徒四壁的居住者。
不管到了哪裡,不管攜帶著再如何強固的「國王的電話亭」出門,每次回到房間,我一定會將外面的什麼帶了回來。笑語也好,哭泣也罷,別人不經意的一句問候或者心意,傷心的與不傷心的。
彷彿又聽見房間這樣指責著我:
「今天又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帶回來了。你到底有沒有把我當成戀人般認真地看待?」
因此,擁有著絕對戀人身分的衣蛾,帶著自己的房間,像是老年夫婦般相愛地在我的房間裡漫步時,便不免令我惱火了起來。
「簡直像是在跟人類誇耀著自己那潔白的人生了嘛!」我忿忿不平地想著。或許,衣蛾也正在吃吃地嘲笑著我。
這樣的衣蛾,在五月的梅雨季裡,大量地出現在天花板上,並且,流星般地啪啪墜落著。簡直是跳傘部隊。
掉落到地上的衣蛾,像是外星人般降落地球,而且,開始四處流竄著。
明明知道衛生紙無法完全將之撲殺,不過,我仍然在房間的角落到處追逐著牠。衣蛾很輕易地被我捉住,捏成一團,不過,即使是被用衛生紙掐到眼前,與我面面相覷的衣蛾,也完全沒有要妥協的意思。一旦我目露凶光,衣蛾便唰一聲迅速縮回了殼中。
我氣憤得不得了,於是,搖晃著手中的紙團,叫牠投降。
如果是別的動物的話,會跟我正面對決吧。比方說狗,一旦對到了眼睛,就會沒完沒了地跟上來,直到一腳把牠踢開,或者嘶吼回去。受傷也好,被說是腦袋太過單純也罷,狗就是具有那種不達目的絕不善罷甘休的厲害才華。
但是,眼前這片瓜子殼般的袋蟲,卻恬不知恥地縮進了那棉絮做成的房間,連用眼睛向我乞饒的努力也不肯做。這,到底該說是懦弱還是虛無呢?
我不敢把掐捏了衣蛾的衛生紙丟進房間裡的垃圾桶,因為,牠必定會在討伐結束後的黑暗裡,伸頭撥開紙團的皺摺,優雅地,從容地,爬回地面,之後,帶著牠的房間,繼續在黑色的平原裡睡眠旅行。
於是,只要抓到了衣蛾,我就毫不猶豫地往陽台外丟去。樓下加蓋延伸出來的鐵皮屋頂,沒有多久,就遍佈著一團一團白色的衛生紙團,那裡面裝著蒲公英般正在旅行的衣蛾。
不過,即使已經做到了這樣的地步,還是不能安心的。
據說,在一個家庭裡,只要出現一隻蟑螂,就代表這個家庭的暗處埋伏了三千隻其他的蟑螂。衣蛾也是同樣的道理。網路上的人這樣回覆著我的發問:
「如果晴天的話,就把衣櫥裡的衣服全部翻出來洗,用強光曝曬。因為衣蛾很可能已經在那上面產卵,換句話說,在你看不見的地方,都有蠢蠢欲動的孵化中的衣蛾的蛋。」
我完全無法接受房間與我之間還有別人,更不用說是三千位別人。
於是,梅雨季的中間,偶爾出現的少數晴天,我都在歇斯底里地清洗著衣櫃裡的衣服,買吸力很強的吸塵器,拼命洗刷地板。
但是,當雨天再度地來臨時,房間裡的光線轉成陰涼,灰塵薄薄地從陽台的落地窗,被風吹來,在桌面無聲地降落。像是蘑菇一般。頭髮長了,只要漫無目的地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也會在前天剛打掃過後的地板上,看到一根兩根掉落的毛髮。
我想,衣蛾這種東西,該不會天生就是用來指責人類的一切努力,都是沒有用的吧?即使掃除得再怎麼乾淨的地方,灰塵還是會再來的。排水孔的黃垢與銹蝕,無論再怎麼用力刷洗了,經年累月,一樣會出現的。而我,作為一個人類,終其一生,都必須處在和那不潔的污垢敵對的戰爭之中,沒有公休的時間了。那簡直像是,整個人生都在做著自我清理的工作了嘛。
忍不住要沮喪了起來,而頹坐在房間的中間。
房間靜謐地在夜晚裡沉睡著。
熟睡中的房間,有著一張戀人的臉孔。
書櫃、地毯、衣櫥和天花板。鞋櫃裡擺滿我喜歡的鞋子。地墊的方向。電視與電腦那一片漆黑宛如森林的螢幕。
「你到底有沒有心理準備,要跟我這樣單調無聊的箱子,一起生活到死呢?」
彷彿聽見房間這樣問。
「那可不是休息這樣簡單的事而已呀。如果是休息的話,你與我都只是彼此的客人,稍微停留了一下,就勢必要互相告別,到另一個地方去的。不過,你與我之間,不是那樣的關係吧。」房間在夜色裡對我訴說著。「那是更重要、非常重要的另一種關係呀。」
啊。如果可以的話,我也真想成為像衣蛾那樣的人啊。
很想一直與房間相戀,直到變成了白骨為止。一百年以後,被人從牆壁的鋼筋水泥裡挖出來,連身體也一起埋進了這個房間。
生也好,死也好,食物也好,排泄物也無所謂,在同一個房間裡舉行著的,我那自我消化的儀式。
很想被房間緊緊地包裹。書櫃、雜誌、蓋過的棉被、喜歡的鞋子,和重要的回憶,全數捨棄。希望房間能從四面八方把我重要地抱住,溫柔地告訴著我:「這裡已經沒有痛苦的事了噢。」在我與房間之間,只有空空的、像是胸腔般的洞,被風咻咻地經過。發出哭聲般的哀鳴。
不過,如果是那樣真空般的、沒有痛苦的所在,為什麼,我還會聽到那種低泣的哭聲呢?那找不到源頭的悲傷的號哭。像是童年裡一次迷路的孩子,沿著離風很遠的道路,由遠而近,慢慢地回來了。
雨季好像會一直下到世界末日。衣蛾持續侵襲著我。雨滴般不斷掉落在房間的各個角落。似乎帶來了訊息。我想知道那灰白袋狀的殼中究竟訴說了什麼,於是,邊清理著一切,邊愈發焦急了起來。
不過,還是不能知道的。
衣蛾守口如瓶地守護著牠自己的房間。
而我,還是不能成為衣蛾的。
袋蟲
我很喜歡房間。
很喜歡四面牆壁緊緊包圍著的感覺。在房間的中央抱膝蹲坐著的時候,總覺得好像回到了遙遠的地方。
令人懷念的氣息壟罩了上來。像是在孤寂的童年場景般的地方,無論經過了多久,都特地趕來的、某個重要的人,果真翻越重重的日夜,抵達這空無的、只有我獨自一人的洞穴般的房間,而與我相見了。光是為了這份心意,便令人感動得想哭。
雖然,並不知道是什麼人。但是,只要坐在房間裡等待,就知道他一定會來。
或許不是懷念。或許是很久以前失落的某種東西,遠在肉體被生下來前,就已經存在的一種觸感,...
作者序
十年一渡/言叔夏
直到現在,我都還保有多年以來的一種習慣:晚睡。散步。獨自旅行。走一段不遠不近的路回家。有時我會在夜間那種自木柵回到城中的公車中途下車,走一條筆直的羅斯福路,回到那像枝椏般開散在沿途巷道裡的房間。那種筆直有時像是洗衣的塑膠刷子那樣地刷洗著我,將我磨亮,把我擦痛。那種痛裡有一種關於清潔的奇妙感覺。彷彿每一步都是自我核心的鉛錘。銼刀的邊緣,很多年以來,我用這種近乎尖銳的感覺在摩擦著每日天氣的邊界。在這座多雨的城市,傘總是極容易失去的,像你所能失去的任何一件東西。我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年就弄壞了七把傘。它們有的被另一個也失去傘的人理直氣壯地偷走,有的則在一次夏季的午後雷陣雨中被劈得骨架歪斜而最終丟進了路邊的垃圾桶。後來我明白了關於持有,有時比起從未有過來得更加令人不安。所以我喜歡走路,喜歡用雙腳真正從一個捷運站抵達另一個捷運站,踩踏斑馬的背。把道路當作一匹巨大的動物來攀爬。抵達了嗎?真的抵達了嗎?像我老是問自己的話。而道路總是一再地生長,彷彿一種生根植物。在那重複地抵達與推延的路程中,終於感覺自己也成為了一匹老去的海。
我經常想起我出生的那個小鎮。離山很近,而海也在不遠的地方。不管什麼時候回去都有一種琥珀色,像鎮裡那些老人貓一般的瞳孔。那種顏色讓整個小鎮變成了一種沒有時間感的天氣。有時這種天氣會充滿著我的身體,使我飽脹,把我氣球般地灌滿,讓我的肚子裡搖晃著一整座下午的海洋。南方的陰天,雨水的酸味,還有那空島般被遠遠推遲在海平面盡頭的積雲。使我又回到童年時代的某個黃昏,和母親一同凝望過的海。
那或許是我一生中最靠近死亡的時刻。我還記得母親的裙襬是大紅花開,紅豔豔的,在海風裡翻飛亂舞。我玩得累了,一臉一手都是沙子,午後的太陽曬得我昏頭轉向,母親便跟港口旁賣涼水的人買給我一罐十元的舒跑。拉開拉環,拉環的背面寫著小小的字:「再來一罐。」我把它亮晃晃地舉高給母親看,母親便不知怎麼地哭了起來了。
我是要到很多年以後,才真正明白那個被海水所拜訪的下午,究竟意味著什麼樣的意義。黃昏離開,海潮退盡,我們又若無其事地活了下來。彷彿只是一個多出來的下午,被琥珀色的貓眼所窺視。貓眼裡的世界像一個玻璃球,搖了搖就會有細小的雪花掉落,像時間的塵埃。我好像一直在旅行,像一次海難裡倖存下來的一個生還者,孤獨,無依,沒有伴侶,總是隨著洋流的方向漂流。從童年的海港離開,到另一個海。可是其實所有的海都是同一匹海。有時我會在一個極遠極遠的異地海邊,想起那個遙遠的下午,想起關於死亡這樣的事物,不過是從一個夢接連到另一個夢的過道,串接起破碎的時間。通過死亡,我就到了另一個地方。有時我也覺得自己在那個童年的下午已經死過了一回。在生與死的邊界,是母親將我拋擲到那條被棄拋物的最前沿,連同她自己,逼我睜眼凝視海水盡頭那不可見之物,彷彿是一種對於她也對於我的試煉;而在這條拋物線物理容許角度的最極致處,那僅有一步之遙的結界,母親終究是救了我,並正因救了我而終於救起了她自己。
多年以後的許多日子,在一座無海的城市,深陷的盆底,一條過陡的坡道,一間終年暗黑的地下室房間,幾個過不去的夾層縫隙裡,生活的斷面被削減得僅剩下一面牆。壞掉的傘,死去的友人,忘記的名字,像掌心裡不斷從指間佚失的沙。日日重複的日子,一天一天,像壁球的迴力軌道被自我拋擲向自我。有那麼一個瀕臨邊界的時刻裡,我會想起那樣一個有海水的下午,想起自己的存在本身,曾諭示著一種救贖;想起這個世上有一個人曾因我而拋卻了死亡的道路,想起關於獲救這件事,從來都不是一件只有自己的事。還有那個亮晃晃的拉環。彷彿籤詩一樣地對我揭露著關於生界的時間,某種神祕主義式的暗示。再來一罐。再走一段路吧。在轉彎的地方,就會再遇到一片海。而我知道所有的海其實都是同一匹海。它只是十八歲出門遠行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原本的港。
這本書的寫作或許也是那樣的一匹海。書中最早的篇章可以推溯到十一年前的〈失語症練習〉(2002),重新輯錄時,腦海裡便浮現起當時的房間:二十歲的時光,暖橘色地磚,一盞低垂的小黃燈泡,黃澄澄地打在貼有田壯壯《小城之春》海報的牆上,室內就彷彿有了溫暖的爐火可烤。我可以捲著一條毯子就這樣蜷縮著度過一整個小城的冬天。集子裡的許多篇章,隨著不同年歲裡的幾度搬遷,在類似的幾個洞穴房間裡磨磨蹭蹭地寫下。有些心情已經消逝,有些什麼卻積塵般地被堆疊在這本書裡,擁有著屬於那些時光裡它們各自的意志。而我其實是個無比邋遢卻又極端潔癖的矛盾之人,總是時時在心裡擰著一條洗了又洗的抹布,老想著要將心擦得發亮;未料寫了又寫,卻放任了這周身懸游漂浮的塵埃粒子,形成環帶,便也只能將之留作十年以來每個渡口的一種紀念。紀念那些活過的時間。
謝謝黃錦樹、郝譽翔兩位老師為這本書作了如此貴重的序文。也謝謝蔡素芬與陳芳明老師分別在大學和研究所時期給過寫作上的支持。謝謝九歌的陳素芳女士促成了這本書的出版,霧室耐心體貼的傾聽與設計,以及施舜文小姐辛苦地聯繫與編輯各種事宜,包容我任性的焦慮與反覆。謝謝一些重要的朋友,小至養貓做飯清潔地板,乃至宇宙黑洞擴張頻率,謝謝你們沒有邊際的交談。
──2013.3.31,於台北城南
十年一渡/言叔夏
直到現在,我都還保有多年以來的一種習慣:晚睡。散步。獨自旅行。走一段不遠不近的路回家。有時我會在夜間那種自木柵回到城中的公車中途下車,走一條筆直的羅斯福路,回到那像枝椏般開散在沿途巷道裡的房間。那種筆直有時像是洗衣的塑膠刷子那樣地刷洗著我,將我磨亮,把我擦痛。那種痛裡有一種關於清潔的奇妙感覺。彷彿每一步都是自我核心的鉛錘。銼刀的邊緣,很多年以來,我用這種近乎尖銳的感覺在摩擦著每日天氣的邊界。在這座多雨的城市,傘總是極容易失去的,像你所能失去的任何一件東西。我來到這座城市的第一...
目錄
序
幻燈之光 郝譽翔
土星的環帶 黃錦樹
輯一:霧路
黃昏離開。天亮回來
關於那些
夜間旅行的事
只有大霧知道。
十年
袋蟲
牙疼
散步
魚怪之町
閣樓上的瘋女人
月亮一宮人
白菊花之死
白馬走過天亮
輯二:無風帶
「你不打開那只箱子,那為什麼要帶著它過來?」
「就跟你一樣。我不打開你,也從來沒有把你丟棄。」是他說過一個人不可能抵達一個人如同抵達另一座城市。是他說過他終年住過的每一座城都比另一個人來得親密與隱私。是他說的:關於他者。
尺八癡人
禿頭女高音
辯術之城
憂鬱貝蒂
馬緯度無風帶
無理之數
春不老
失語症練習
火宅之城
千高原
輯三:光年
將道路走成一個彎,穿簡單的鞋。
我是如此持重地穿入九月
在身體埋下一顆種子,彷彿懷一個孩子。
到了冬天,牠會不會種出一種年老動物?
Pluto
用眼睛開花
上吊者的小屋
父親
阿斜
夢之霾
截一段路
日暮日暮里
代跋
十年一渡
序
幻燈之光 郝譽翔
土星的環帶 黃錦樹
輯一:霧路
黃昏離開。天亮回來
關於那些
夜間旅行的事
只有大霧知道。
十年
袋蟲
牙疼
散步
魚怪之町
閣樓上的瘋女人
月亮一宮人
白菊花之死
白馬走過天亮
輯二:無風帶
「你不打開那只箱子,那為什麼要帶著它過來?」
「就跟你一樣。我不打開你,也從來沒有把你丟棄。」是他說過一個人不可能抵達一個人如同抵達另一座城市。是他說過他終年住過的每一座城都比另一個人來得親密與隱私。是他說的:關於他者。
尺八癡人
禿頭女高音
辯術之城
憂鬱貝蒂
馬緯度無...
購物須知
關於二手書說明:
商品建檔資料為新書及二手書共用,因是二手商品,實際狀況可能已與建檔資料有差異,購買二手書時,請務必檢視商品書況、備註說明及書況影片,收到商品將以書況影片內呈現為準。若有差異時僅可提供退貨處理,無法換貨或再補寄。
商品版權法律說明:
TAAZE 單純提供網路二手書託售平台予消費者,並不涉入書本作者與原出版商間之任何糾紛;敬請各界鑒察。
退換貨說明:
二手書籍商品享有10天的商品猶豫期(含例假日)。若您欲辦理退貨,請於取得該商品10日內寄回。
二手影音商品(例如CD、DVD等),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二手商品無法提供換貨服務,僅能辦理退貨。如須退貨,請保持該商品及其附件的完整性(包含書籍封底之TAAZE物流條碼)。若退回商品無法回復原狀者,可能影響退換貨權利之行使或須負擔部分費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
退換貨原則、
二手CD、DVD退換貨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