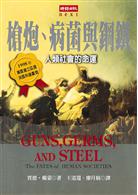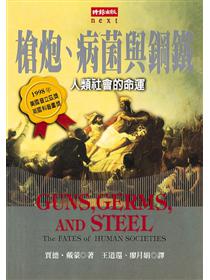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
【編輯室報告】偵探蒸蛋 /執行主編蔡逸君
該先聲明「以下純屬虛構」嗎?卻也未必。虛虛實實的人生與小說,到底哪個務虛哪個著實?猜吧,不然要偵探做什麼。
不管是西洋、東洋推理小說,故事場景經常安排在酒吧內,主角啜飲著威士忌或馬丁尼,開始一段關於「屍體」的敘述、對話……,但台灣不時興這場景,只好改在啤酒攤。安和路上的龜山島或新生南路上的一代佳人都可──千萬別誤會,這二處真的只是喝啤酒的地方,沒有龜沒有山更別提佳人了。喝啤酒就無須顧及氣氛,所以當我們落坐之後,在人聲相當嘈雜的情況下,總編輯神祕兮兮地說,下個月封面我們就做紀蔚然吧!紀蔚然(或稱紀杯、冷伯、紀教授、紀大劇作家、紀老師……)寫新戲啦,太棒了。
「不是劇本,是寫了一部蒸蛋小說,書名就叫私家蒸蛋。」
蒸蛋小說?哇靠,不愧是笑死人不償命的冷伯,連蒸蛋都能寫成小說──但甭管是蒸蛋或皮蛋,任何題材,只要是紀教授出手,萬無一失的啦。
「聽這名字,應該是家庭喜劇之類的吧?」
「是很好笑,但死了不少人。」
連蒸個蛋都能死不少人,而且還把死人場面搞得很好笑,紀伯伯果真吾道一以貫之,連寫小說都不改其志也──至此,我必須做個人懺悔與告解,最近我實在衰暴了,兩耳內破了洞,聽力嚴重受損的情況下,不只馮京馬涼,偵探都蒸蛋了。(紀老師,請原諒我……)啤酒攤後過幾天,我捧著紀大劇作家的偵探小說列印稿上了手術檯。麻醉醫生很善意地說,來,用力深呼吸,這是氧氣。我吸到第三口時發覺不對,這應該是讓人昏迷的醚吧。在我暈過去前的一個念頭是,千萬記得要醒來,小說還沒看完呢。才一會兒(兩小時),我似睡非睡躺在恢復室時作了個夢,紀杯穿著醫師袍來跟我們一堆正待清醒的病人解說:「在全身麻醉下,患者完全失去意識,你不會看到、聽到或感覺到任何事物。全身麻醉同時提供止痛、肌肉放鬆及失憶的效果。」聽著聽著我心想,這不就是在說你自己的小說嗎?紀醫師接著說:「麻醉醫生在手術過程中,會持續使用生理監測儀器觀察你的心跳、心臟節律、血壓、血中的氧氣及二氧化碳濃度……」那一刻,我突然有一種領悟,紀杯表面上是個劇作家或寫小說的,但他其實是個醫生,是診斷我們這個病態台灣社會的醫師。不過,這個領悟在麻醉藥效過後,開始產生後遺症,我看見恢復室裡不少病人像喝醉酒般猛吐──唉,在台灣到底是清醒還是昏迷比較好呢?
接著,我像漂浮在海浪上頭般被推回到病房。巡房的美麗親切可愛的護士小姐對我說:「很少看到全身麻醉後的病人笑得這麼開心耶,你術後不痛嗎?」
痛,當然痛,但我手上捧著紀杯的偵探小說呀。
「耳內手術後,不要用力咳嗽,也不要笑得太誇張喔,……」
知道,我知道……然而一邊痛一邊笑的確讓人感覺很痛快不是嗎?這不也是紀蔚然那種讓人失控的自虐並自樂的風格,《私家偵探》絕對不只是一本偵探小說而已。
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編輯室報告】偵探蒸蛋 /執行主編蔡逸君
該先聲明「以下純屬虛構」嗎?卻也未必。虛虛實實的人生與小說,到底哪個務虛哪個著實?猜吧,不然要偵探做什麼。
不管是西洋、東洋推理小說,故事場景經常安排在酒吧內,主角啜飲著威士忌或馬丁尼,開始一段關於「屍體」的敘述、對話……,但台灣不時興這場景,只好改在啤酒攤。安和路上的龜山島或新生南路上的一代佳人都可──千萬別誤會,這二處真的只是喝啤酒的地方,沒有龜沒有山更別提佳人了。喝啤酒就無須顧及氣氛,所以當我們落坐之後,在人聲相當嘈雜的情況下,...
章節試閱
台灣推理小說的新視野──《私家偵探》 /紀蔚然.文
「乾的地方,靈魂是待不住的。」──拉柏雷,《巨人傳》
攝影/陳建仲
一、辭
我辭去教職,淡出名存實亡的婚姻,變賣新店公寓,遠離混出名號的戲劇圈,和眾位豬哥軟性絕交(別找我喝酒、別找我打牌),帶著小發財便足以打發的細軟家當,穿過幽冥的辛亥隧道,來至這鳥不拉屎以亂葬崗為幕的臥龍街,成為私家偵探。
掛上招牌,印了名片,中文那面燙著楷體「私家偵探 吳誠」,另面印著“Private Eye--Chen Wu”,愈看愈發得意,反覆賞玩。搞了兩盒,沒數日便將告罄,倒不是多人需索或在紅燈下四處濫發給開車族,而是等候生意上門的空檔模仿賭徒把兩疊名片當成撲克洗牌,或以食指中指并夾作暗器練習,不過耗損率最高的是剔牙。
從奇想偶發到越獄般暗中醞釀一直到果敢實踐歷時半年,俟時機成熟才正告親友。反對聲浪一如預期傾巢而來,好似搗了蜂窩,任我掩體揮手力擋,下場仍是滿頭包。活該當災,千夫所指我早習以為常。明月高照,一干猥瑣小人刀劍在握隱身草叢,獨我一襲雪白勁裝疾風兀立曠野,時辰一到萬箭穿心,倒臥血泊中的我手裡沒有兵器,只有一支手電筒。言重了,戲劇出身的我老愛在腦海裡拍電影,胡亂編構淒絕泣血畫面,場景永遠在曠野,故事永遠是關於一名小丑的英雄情結。
這回可是來真的,決心忠於小丑本色。罅隙處處之滄海孤舟,滲入的水向是比掬出的多,人生不過爾爾。叱嗟風雲,抑或退隱於市?寧可選擇後者,不再夾窒其間以致胸懷淤血,亦不再左右巴望落得兩手空空,且大退大進,揮別婆婆媽媽,掙脫世俗枷鎖,切斷江湖連線,一個人過自己的活,何其快哉!
笑傲遺世,我瘋了嗎?
年過七旬的母親最後得知,反應最烈。不准辭職、不准提早退休、不准孟浪行事!當我囁囁吐露一一做了以上,聲嘶力竭換成搥胸頓足──母親灑狗血功夫一流,我的戲劇天分早於娘胎便師承自她──但見她淌淚夾涕揚言要壓我回學校,到校長辦公室請託伊收回成命,甚且跪求亦在所不惜!
未赴了,我說,系主任、院長、校長各個雙手微顫,捧著我遞上的辭呈,宛如天上掉下的禮物,一日內連過三級依極速件處理,執教十數載未嘗見識官僚體系這般神奇效率。他們敷衍慰留卻掩不住感激振奮,只差沒點鞭炮放煙火擊鼓列隊把我歡送出校。以上當然胡扯,我人緣不佳,可還不至惡劣到前腳踏出後邊就有人開香檳的田地。三位長官如何看待本人無預警出走我不得而知,一派瞎掰只為讓老人家死心。
母親頓時啞口,萎荏弓凹的身軀搖搖欲墜,手倚門廓,一會兒盯著她讚歎多年的義大利進口瓷磚,一會兒仰望客廳牆上老爸的畫像,瞬間更形蒼老,正欲發作,我撂下一句仍會按月寄生活費便一溜煙走人。
不孝子我真是,且不單此回,前科累累犯例一堆,所幸她老人家堅毅如山,若無超人意志怎能獨立扶家一手撐起屋頂,安然渡過風浪無數?何能招架不肖兒如我三不五時撒野耍賴竟不吐血倒地?雖已心口不同步、說話些許結巴斷續,母親仍思想澄明,聲音洪亮如沿街放送的廣播,動怒時口頭禪更熟極而流絲毫不斷續結巴。母親口頭禪多不勝數,乃一生育兒實戰的智慧結晶。「死囝仔賊」、「飼兒罔罔」、「氣死有影」、「氣到血冒湧而出」……假以時日我該自費為她出版嘉言錄,以報養育之恩。
走出家門,轉進三民路,「死囝仔賊」依稀可聞,心底一陣溫暖。
適才拎來孝敬老人家的一品香鮮蝦扁食恐怕已被丟棄垃圾桶,接下來我猜母親會打電話給正在上班的小妹,她呢,想也知道會佯裝不知情,好似晴天霹靂:「阿誠,伊起痟了嗎!」
年幼我四歲的小妹從未喚過我「哥」或「阿兄」,不僅因年齡近、孩提時作夥嬉戲感情深,且因我沒大哥樣,基因少了「為兄」的陣頭。自從各自成家,兄妹倆便聚少離多,加之我不興串門聚餐去電問安,近來更為疏分,除了節日拜拜於母親住處不得不外,鮮有見面機會和必要。親情紙薄,倒非有何難以冰釋的嫌隙,橫豎代誌演變至此,毋須欷歔,台灣很多家庭據說都淪落至此。
我以手機「知會」小妹,刻意不用市話聯絡,以免過去的事扯不完。找個不頂安靜但不至喧嘈的街角,挑了深夜時刻,若無其事地丟下炸彈:「辭職了」。彼端傳來久久的沉默,只得耐心等候,給點時間讓她消化突如其來的衝擊。「媽怎麼辦?」語氣極其冰冷。小妹一向坦直,對於我花招頻出早有防禦機制,完全省略「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之類制式反應。哀莫大於心死,這點可能性最大,她早不在乎任何關乎我的狗屁倒灶。
「我還是會按月給她一萬。」
「那不是我的意思。」話語方落,電話便掛了。
家人好辦,自大學便混在一塊的麻友們可沒那麼容易「按奈」。半年前我便點滴吐露退隱口風,他們起先不以為意,只當間歇性牢騷聽聽,爾後發覺事態嚴重便不斷找機會與我喝酒,不斷以勸說為由找喝酒機會。有陣子一干人車輪戰術,啤酒屋油膩矮凳上從未缺席的卻是我。平時聚會我甘居配角,不跟風、不帶頭是我奉行不悖的作風,可這會兒卻難得當上了主角。幾隻嘴混聲合唱一曲勸世老歌,啤酒下肚專屬欲求不滿已婚男人的台灣藍調。
──中年危機嘛忍著點兒掐緊老二晃眼兒就過了。
──創作瓶頸嗎?切忌將寫作和人生混成一談。
──找管馬子貼身肉搏一番,不,找個女學生談戀愛待東窗事發被解聘還不遲。
最扯的應是,倦勤是吧?不想教就隨便教還不簡單。天地良心,我一向隨便教。
事情沒那麼簡單。
總是當他們搭腔搶詞忘情提點──為時僅限於剛坐下咕嚕喝下的兩瓶,一旦酒過三巡臉頰泛豬肝色後便把邀約的主題,我,給忘了──總在他們烈切分享危機處理心得時想到一句老話:友人的災難帶給我們的黑色慰藉往往甚於敵人毀滅的訊息。榮幸之至,個人生涯的巨大丕變竟為與我同等身心俱疲的哥兒們心靈注入一股宛如再造重生的能量,縱然僅僅維持一個菸臭酒臭濃濁如痰的夜晚。
偏執如我原本無意聽勸,管他朋友、親人、同事。自從妻依親到加拿大流連不返,我前一刻萬念俱灰下一秒舒爽暢快,心緒兩極晃蕩如鐘擺,從懮懮慼愀到英氣勃發,從窮途末路到海闊天空,從「蝦米攏去了」到「大幹一場」,直到發條鬆脫,鐘擺凝止於中界。猶如平生第一次學會深呼吸,吸-入-呼-出,徐徐吐納間我找到安靜,以安靜思索下一步。爾後,心底日漸埋下幽微坦蕩根深入魂的退隱之念,先如滴水般涓涓滲泌,繼而一瀉如柱勢不可當,向親友宣告「辭了!」可絕無兜攬可茲轉念的人生哲理的渴望。
但想向他們告別,道一聲珍重。
但望另築一段未知人生,破釜沉舟放手一搏。
骰子擲出,十八啦!BG啊!不上天堂且下地獄。
※
我寄居於白晝和黑夜無甚兩樣的水泥洞穴,雖腳踏實地,卻不見天日。
臥龍街197巷是條死巷,宛如由盲腸內壁延伸而出的一道闌尾。裡面住了五十幾戶人家。地狹人不親,很少看到鄰居之間互動。這條死巷白天時已夠沉寂昏昧,唯一的光源來自一小片上空,到了夜晚因沒街燈更是黑壓壓,若非自住屋窗戶透出的微弱燈光,可真要伸手不見五指了。之所以落腳於此除了租金便宜外,且因為它夠隱密。為了掛牌做生意,我特意選擇自有門戶的一樓。房東為了防賊,用雨棚與鐵柵把前院遮得密不透光。看屋時問房東可否拆掉雨棚,他不假辭色地告訴我,拆掉你就不用租了。
屌斃的招牌掛在一棟中古四樓公寓底層的大門邊石柱上,長方形木板鏤刻質感的「私家偵探」。
小小招牌引來坊間動員不小、不怎麼掩飾的竊竊私語,顯然久廢的「守望相助」因怪咖入侵而再度開張。不時可見午睡方醒的公嬤叔嬸、騎著機車的少年郎、足蹬扣扣作響踏著露趾矮人鞋的美眉、早熟討打的孩童,幾乎所有周遭鄰居排好班表似的輪流徘徊於招牌近處交頭接耳,即便我出入大門,也未曾基於禮貌暫且移開視線。
某日,條子終於找上門來。身為私家偵探,自當料到。
「這是什麼?」管區仔指著木板。
「招牌。」我遞上名片,未及抹去沾在角尖的肉渣。
「有這種職業嗎?」
「沒有,我是台灣唯一,算是台灣首席私家偵探。」
笑話沒引起任何反應。只要一個,誰能找出一個值勤時帶著幽默感的警察,我自願坐牢十天。
「有執照嗎?」
「沒有。我到徵信公會申請,對方說要入會申請書、會員代表身分證影本、公司執照影本,還有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我不想入會,不想開公司,所以沒資格申請。」
「怎麼可以?」
挺著啤酒肚的條子兩隻拇指勾在肚臍下掛著手槍的皮帶上,自以為是小號的約翰韋恩。
「有犯法嗎?」
「這是做啥?」
「救人一命。」
二、跟監
我想救的人其實是自己。
搬來這兒無異走到盡頭,亦無退路。
在一個屋簷下隱居獨住對我而言既新鮮又驚悚,完全違背醫生叮囑。無論多麼厭煩人群,盡量避免獨處,他說。偏偏我反其道而行,決心克服此生最大罩門。不想一直生活於恐懼中,決心在形式上和痼疾硬碰硬。手段看似激烈,心態卻是謙卑的...(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1/94期六月號)
作者簡介:紀蔚然
劇作家,台灣大學戲劇學系教授。輔仁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愛荷華大學英美文學博士。曾發表過的舞台劇本有《愚公移山》、〈死角〉、《難過的一天》、《黑夜白賊》、《夜夜夜麻》、《也無風也無雨》、《一張床四人睡》、《無可奉告》、《烏托邦 Ltd.》、《驚異派對》、《好久不見》、《嬉戲之Who-Ga-Sha-Ga》、《影癡謀殺》、《倒數計時》、《瘋狂年代》等;電影腳本有《絕地反擊》、《自由門神》等;動畫片《紅孩兒:決戰火燄山》。著有戲劇專論《現代戲劇敘事觀:建構與解構》,以及散文集《嬉戲》、《終於直起來》、《誤解莎士比亞》等。
台灣特有種偵探──紀蔚然 /李維菁.文
紀蔚然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劇作家之一,他的《黑夜白賊》、《夜夜夜麻》等代表性劇作彷彿寫出了整個世代的焦慮與整個社會的瘋狂。他的散文犀利嘲諷讓讀者拍案叫絕。三年前,紀蔚然決定暫停,當時的他瀕臨因長年嘲諷憤怒乃至於陷入終極虛無的點上,他停下來,想重新看看這世界,看看路邊的風景,也想好好看看自己。
三年後,五十六歲的紀蔚然交出人生第一部小說,偵探推理小說《私家偵探》。
「就跟這部小說裡頭的主角人物吳誠一樣,我對外推理著這個世界,對內推理著自己內在的厭世。」
他什麼運動都不喜歡,唯獨喜歡走路,暑假開始他每天固定從台北長興街住家出發,每天在六張犁散步,沿著基隆路,走過辛亥路,有時轉到臥龍街去爬福州山,有時則走過富陽街以及小街道,穿越這區域一些小的賺死人財的小小葬儀公司,他會在和平東路口的咖比茶咖啡店坐下歇腳,喝飲料,看看報紙,與店裡的小妹、附近的店家聊聊天打打屁,然後繼續走到台北101大樓作為終點,折返行經和平東路走回家。
在散步的同時,他問自己為什麼不寫這地方的故事呢,就寫在六張犁發生的推理小說。這股衝動突然迸出來。他便開始構思了。
攝影/陳建仲
紀蔚然推理小說主角吳誠是個大學戲劇系教授也是知名劇作家,對學院的迂腐僵化感到厭倦,對劇場的自以為是與浮誇膚淺感到絕望,對情感變質的婚姻感到無奈。有天吳誠突然向學校遞了辭呈,在酒後狂亂的咒罵之後脫離劇場界,戴上他的漁夫帽,拋棄一切,一人走著走著走到臥龍街小屋,掛起招牌,當起私家偵探。
怎麼看,吳誠的身分以及性格中那分嘻笑怒罵核心卻嚴肅憤怒的特質,活脫脫就是紀蔚然的分身。
在小說中吳誠酒後大罵劇場界的合作夥伴,這彷彿是紀蔚然在台灣戲劇界工作了二十年的吶喊與省思。
「二十一世紀之後有了明顯的變化,劇場因消費主義進入戰國時代,大劇場往商業化走再也走不回來了,與此同時,小劇場也同步出現的媚俗,手法與大劇場如出一轍。」他說,「如果劇場作為一種文化批評的藝術形式,我想這種精神百分之九十九已經死了。」
「大家喜歡說台灣多元化,這是狗屁,台灣眾多領域見到的都只有單一化。所謂多元是一只欲蓋彌彰的口號,人的想像力愈來愈薄弱,藝術家的想像力愈來愈稀薄,養分不夠,人,愈來愈笨了。」
「我不能容許我自己變笨。」
「台灣的劇場有兩派主流,一是我稱之為『新感動主義』,浮濫的懷舊,輕言感動,另一種則是大搞刻薄嘲諷。」
「搞藝術的或觀眾都以為刻薄嘲諷就是批判,就是一種對現實的抵制,其實,還是敗了。」因為,一旦創作者開始長期嘲諷現實,基本上就是一路地緊貼現實作反應,被它控制。
「而嘲諷是一種否定,一直不斷地嘲諷,就是一直不斷地否定否定,這樣下去,最終就否定了自我。」
「我能夠想到的解決與出路,還是必須創造出good art,不是那種膚淺的針對表面現狀直接回應的,而是跟現實有關又能加以超越,不要與現實作短線的拉拒。」他說:「戲劇、文學,是尋找意義的形式,背後藏的畢竟還是生存的意義與生命的狀態。」
他說,在劇場界,在台灣社會中,長年以來看到的都成為了便宜的抱怨、便宜的思考、便宜的結論、便宜的評論文章,而大家四處販售著廉價的情感,所謂便宜的,「就大腦的注意力慣性的持續,與真正的思考無關。」
「我不在意我看的是藝術片或商業片,我不在意我看的是藝術劇場還是商業劇場,但我最怕的是半吊子的『假藝術』。」
「我以為我夠疏離,所以可以批判,實在不然,靠太近了,太近了,這樣打太便宜了,打出去也是消耗。」
紀蔚然的散文寫作自成一家,那分犀利嘲諷讓讀者拍案叫絕。有連續四年的時間他在報紙副刊、文學雜誌以及綜合性週刊上寫散文專欄,但他寫了四年決定收手,原因是:「寫雜文使人變笨。」
他說,寫雜文專欄這事情(他堅持不肯說自己寫的是散文,只願說雜文),每週交稿這事情讓他覺得自己的心理狀態處在生產線一般,每週寫,寫完就交稿。「而且我專欄寫到最後已經開始變刻薄了,我的自嘲與刻薄到了無法收拾的程度,這真是自虐也虐人。」
「諷刺也使人變笨,自嘲也只是保護傘,自嘲不能讓你真正面對自己,帶著安全頭盔並不是要面對自己的聰明方式哪!當人處在極端憤世嫉俗的狀態中,我知道我必須停下來好好想想,為什麼充滿了這麼多憎恨。」他說。於是他試著抓回一點理性,整理自己,先暫且不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他寫這部小說,避免陷入殘忍、自虐與耽溺。
正如書中的吳誠,紀蔚然開始了他的旅程,以推理小說方式進行自我追尋的旅程。
「我想做個比較好的人,更公平一點,更善良一點。」
錢德勒寫推理的同時,寫盡了二十世紀上葉洛杉磯這個城市的興起與罪惡,金錢遊戲的刷洗與執法的腐敗。卜洛克的偵探在追查犯罪的同時,展現了紐約的街道與區域漸層,市井小民對於善惡的迷惘與對虛妄的執迷。而在紀蔚然的《私家偵探》中,吳誠寫台灣社會的媒體、大眾集體的膚淺,似是而非曲解宗教的便宜行事。吳誠住在臥龍街,搭公車與小黃辦案,到和平東路的勝立買手電筒,在咖比茶咖啡店研究案情,在信義分局被拘留質問,在臥龍街的巷弄與殺人犯展開追逐,走在六張犁的街道及公園與人交談。讀者不由得以為吳誠及罪犯的食衣住行,還有犯罪與追查,就在大家平常起居熟悉的小店街道中,與大家的日常同步發生。
「六張犁雖在大安區,但有著一種半鄉半城、亦鄉亦城的風貌,這裡沒有星巴克,只有錄影店、鹹酥雞、傳統市場,以及許多老房子,這裡沒有文青,沒有規劃整齊的街道與豪宅,卻又不是那種萬華區或是迪化區的老台北。六張犁這裡散漫、親切,許多外來者,我在大學時期住過這個區域,現在看來,當年的老房子都在,人的行為模式也類似,沒有太大的改變。」
把街道、店名、公園、商店全部寫進去,增加了這部推理小說的真實感。他說,畢竟連續殺人命案不存在每個人的真實生活,加入了這些區域與活動地點,讓這部小說在閱讀上彷彿航船有了錨。
說穿了,紀蔚然的劇本與小說,創作的核心都一樣:台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動筆寫小說後,紀蔚然初始在劇場語彙與小說語彙這兩種不同表現形式之間,花了好些時間進行調整。
他解釋,劇本分為兩種,一種劇本寫的是「事物的發展」,莎士比亞是代表性高手,台灣的劇場也多著墨在此;另一種寫的是「事物的狀態」,代表性的是貝克特的《等待果陀》,而他的劇作也在這個類型中。
「我覺得發展都是表象,狀態才值得探討。」他說,像是一對夫妻從結婚到離婚,這是發展,這是表象,表象一直變。可是關於這對夫婦各自的情感信念、價值觀以及他們關係的結構,這是狀態。
習慣處理「事物的狀態」的紀蔚然,在劇本寫作上最擅長的、大量使用的就是對白,處理對白他辛辣老練,轉折細膩生動。他說,劇場語彙思考的基本上是鏡框式舞台上要總共呈現多少個時空。人物出場,開始對話,由此行經一幕又一幕。劇場重對白,小說則需要一個敘述者。敘述者人稱背景、性格的設定之後,小說敘述的基調才會形成,敘述者的基調總是掌握小說的基調,這點確定之後,布局、情節與懸疑等才後續加入。
「敘述語言決定小說一切,對白語言決定劇場的一切。」
「寫雜文這件事情雖使然變笨,但是卻在寫小說這件事情上幫助了我。」
過去以對白形式的表現語言是他所擅長的,開始寫小說,他就一定必須使用敘述性的語言,「那四年雜文的寫作,彷彿是為了我寫小說在做準備,因為雜文就是敘述性語言,是對我的一個訓練...(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1/94期六月號)
作者簡介:李維菁
台大農經系畢業、台大新聞研究所碩士。長期投入當代藝術觀察與評論寫作,著有《程式不當藝世代18》、《台灣當代美術大系──商品與消費》、《名家文物鑑藏》、《我是這樣想的──蔡國強》,以及小說集《我是許涼涼》。
〈西格瑪是誰?〉追尋Σ的精神與原鄉 /王健文.文
那些穿著斗篷的奇怪的人
正當他像往常一樣,卡在晨間擁擠的車潮中發楞時,忍不住地看到附近好像有很多奇裝異服的人。一群穿著斗篷的人。德思禮先生就是沒辦法忍受奇裝異服——看看那些年輕人的荒唐打扮!他猜想這大概又是某種愚蠢的新流行。——《哈利波特Ⅰ:神祕的魔法石》
二○○三年四月,即將卸任統一企業集團總經理、升任集團總裁的林蒼生,寫了一封短簡,附帶一首剛寫不久的詩,寄給青春好友劉定泮。信中說:「好的詩,常常會掉。例如在Σ sigma時寫的『無人島』,老早就掉了,掉了反而覺得更美,但不知為什麼,總是無法忍受那分失落的感覺,所以決定不再讓現在寫的東西再掉。」
剛剛辭世不久的姜渝生和他的夫人王小娥,也是Σ(西格瑪)。姜渝生在一篇回憶大學剛畢業,與王小娥、劉定泮等,一起創辦文學雜誌《草原》的文章中,曾經引述林蒼生給王小娥信中的一段話:「我有一個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母親,我所有詩性都來自母親的詩細胞;媽成詩一首、一定先給我看,我寫多少,也一定叫媽知道。」
唐諾曾轉述名小說家馮內果說過的一樁耐人尋味的故事。他的一位知名小說家好友,一次趁著酒意當眾演奏鋼琴,忽然嚎啕大哭:「我這輩子一直夢想成為鋼琴家,但這把年紀了,你們說我成了什麼樣了?我只是個小說家。」
我不免好奇,站在事業顛峰的林蒼生,回顧西格瑪與草原年代的青春歲月,會怎麼看待那個被放棄的人生、一個曾經可能也熱切渴望,但未能經歷的另種生命風景?他會不會問自己:「我這輩子一直夢想著成為一個詩人,但是今天,我只是個企業家!」
當然,林蒼生不是一個尋常企業家,年輕時候的詩性始終駐留在他內心深處,等待再一次地召喚。
1965年夏,西格瑪社歡送畢業社友。前排左起:吳良雄、林蒼生、劉中鴻、勞國輝、施仁政、何茂子、劉定泮;後排左起:王小娥、姜渝生、劉紀華、梁肇雄、莊瑪玲、李春英、傅慧成。
一九六七年二月,籌辦《草原》期間,正在服兵役的林蒼生,寫信給還在念成大企管系的谷文瑞,信中有這麼一段話:「聽說自從有了現代文學以後,草原上的那許多鳥的叫聲也都不同起來了。日出的時候他們圍在一起,日落的時候,他們也圍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們談一些什麼,所以,有好幾次我都靜靜地在他們的樹下假寐,現在寫信給你,我心情的沉重就是來自這樹下的體會。」
那一年年底創刊的《草原》,封面上醒目地寫著:「源於傳統,傲視現代」八個字。《草原》是西格瑪的延續,幾個年輕的成大畢業生,帶著天真且純粹的心意,實踐他們對文學、藝術與人生的熱愛。
年輕的谷文瑞是才氣縱橫的早期西格瑪,在《Σ通訊》中熱切地寫著:「我們要看書、要思想、要講演、要辯論、要旅行、要畫圖、要寫詩、要寫情書、要唱中國民謠、要想懶懶的太陽,我們別忘了也要演劇。」
畢業多年後的谷文瑞,曾經是麥當勞重要部門主管,在台灣麥當勞出現經營危機時,臨危受命,擔任台灣麥當勞總經理,短短幾個月內,讓台灣麥當勞回到正軌。正當事業可能再創高峰時,他向麥當勞總公司辭職了。離開絢爛職場的谷文瑞,寫作、畫畫,還成了劇場導演。
一九七○年,極有文采的葉子,在畢業離校的時刻,告別校園,但是她卻遲疑,該不該告別西格瑪?
葉子寫道:「本來想和西格瑪說聲再見的,終於還是沒說。也許,這一輩子是不打算說了。想西格瑪的精神不在『學校』和『年輕』—— 一個西格瑪的走出校園,就仍是一個西格瑪活在社會上,感覺不會變,理想也不會變;生命的style如果已經建立而且確信,還怕以後會再丟掉麼?」
是的,葉子不會忘記,西格瑪們也不會忘記〈那天〉,葉子說:「Σ的吃飯,不快也不慢,恰到好處時,就會一個個踱到草地上躺下,有人挺屍,一隻手撫著肚皮,還會一隻手指著天空問,為什麼今天黃昏的天空這麼美麗呢?」
「其實,天也不很紅,風也不很清,只因為大家圍成了個大圈圈,又會笑,又會叫,就把草都滾綠了。」
那麼,「西格瑪是誰?」或者應該先問:「誰是西格瑪?」
龍應台是不是西格瑪?
六和機械副總退休後任常年顧問的馬毅志說,當年與她互動談論甚多,她來過,是相互吸引有交集的西格瑪之友。多年以後,一群年輕的成大大一學生,因為龍應台演講中西格瑪印象的牽引,重訪西格瑪,揣想一個世代前的風雲際會。
回到成大校園教書的吳鐵肩(老鐵),十年前說她是成大產生的女中豪傑,和西格瑪頗有淵源;十年以後,老鐵說,會來西格瑪的,都是內心有所不安,因為不安,才會想要去追求專業中所沒有的東西,「規矩的人是不會來的,像龍應台就曾經來過。」
寫《野火集》以前的龍應台,在許多人的記憶中是「規矩的」「好學生」,甚至有人覺得《野火集》以後的龍應台還是「規矩」的閨秀書寫,但是,來到西格瑪的龍應台,在在表面的規矩背後,大概心中也潛藏著一個不安的靈魂吧!
當然,西格瑪是沒有形式上的身分憑證的,是不是西格瑪?得看身上是否穿著那襲斗篷。
鄭南榕是西格瑪嗎?
鄭南榕故世多年後,畢業後的西格瑪曹欽榮在整理他的資料中:「看到許多很西格瑪的書寫,只要是西格瑪一眼就能辨識這樣的書寫。」
那是西格瑪的印記嗎?西格瑪沒有社員證,沒有組織章程,社長的產生有時近乎隨興、像是傳奇。那麼,誰是西格瑪?那襲辨識身分的斗篷是什麼?
曹欽榮看到一張卡片,是鄭南榕獄中手記,其中一行寫著:「西格瑪的自由思想」。
是的,後來畢業於台大哲學系的鄭南榕,剛考上成大工程科學系的第一年,是個西格瑪,還當過西格瑪的社長。
谷文瑞回憶,當時與鄭南榕共同閱讀漆木朵的《幻日手記》,感受其中暗藏的反叛心態:「我們同時分析那本書時,看法非常接近;然而我們已經清楚知道兩個人的心情,和將來要走的路子是多麼天差地別了。我的憤世嫉俗使我要逃離,超脫;而他,已經決定要直接進入問題的核心。」
多年後,在鄭南榕成大轉學後,谷文瑞第一次與鄭南榕重逢。鄭南榕因觸犯時禁,在偵騎四出中與當局周旋。「那時看鄭,他說話興致勃勃,拿香菸的手直發著抖。」「就像那夜我們爬在成大煙囪上時,在冷風中,一邊抖著,一邊興奮的展望未來。他的抖,是因為他已經活在他追往理想的路上。」
(更多內容請見《印刻文學生活誌》.2011/94期六月號)
作者簡介:王健文
父母親來自閩北山區,大半生在後山花蓮度過。生於花蓮,讀書在台北,成家在台南。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歷史研究所博士,曾任《歷史月刊》編輯,現任教於成功大學歷史系。著有《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後二十年》,學術論文和非學術文字數十篇。十年前執行主編《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目前正負責編纂成大八十年校史。
台灣推理小說的新視野──《私家偵探》 /紀蔚然.文
「乾的地方,靈魂是待不住的。」──拉柏雷,《巨人傳》
攝影/陳建仲
一、辭
我辭去教職,淡出名存實亡的婚姻,變賣新店公寓,遠離混出名號的戲劇圈,和眾位豬哥軟性絕交(別找我喝酒、別找我打牌),帶著小發財便足以打發的細軟家當,穿過幽冥的辛亥隧道,來至這鳥不拉屎以亂葬崗為幕的臥龍街,成為私家偵探。
掛上招牌,印了名片,中文那面燙著楷體「私家偵探 吳誠」,另面印著“Private Eye--Chen Wu”,愈看愈發得意,反覆賞玩。搞了兩盒,沒數日便將告罄,倒不是多人...
目錄
編輯室報告 偵探蒸蛋 /蔡逸君
縫猿志 合趾猿、長臂猿 /西西
心靈解碼 讓愛飛翔 /林幸惠
封面人物 台灣推理小說的新視野:紀蔚然《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 /紀蔚然
紀蔚然──台灣特有種偵探 /李維菁
穿街踏巷求一探──談紀蔚然的《私家偵探》 /既晴
我的偽自傳,一場驅魔儀式──楊照VS.紀蔚然對談 /劉思坊.記錄整理
張大春專欄:這就是民國
無復相從喪亂中
抗旱鐵牌
一縷孤魂夢不窮
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
郁達夫的詩謎
童偉格專欄:童話故事 神打
劉克襄專欄:F23.5左右 不知前程的台車行──重走吳濁流的119縣道
特別刊載 愴然的回望──聶華苓《三生三世》的回想 /尉天驄
特稿 那一年,出蘆入關 /邱坤良
特輯:奧地利文學標竿與破壞者──伯恩哈德
職業惡人 /李煒
瘋癲者的玩笑──伯恩哈德與他的導演們 /耿一偉
黑暗中一切清明──伯恩哈德劇作中的家和死亡 /紀蔚然
伯恩哈德劇作《麗特、丹妮、佛斯》選讀 /崔延蕙.譯
八九點鐘的月亮 泳池邊的閒閒時光 /張家瑜
漫遊者 Sailing to Formosa /米千因
那些人那些事 西格瑪是誰? /王健文
過日子 食經鼻祖陳夢因 /朱振藩
場邊故事 熱血四要素──無法忘懷的比賽 /鄭浩
CEO生命閱讀
三代‧孤獨國‧明星光芒 ──專訪明星咖啡館經營者簡靜惠
/田運良、林瑩華.採訪 蘇惠昭.文
六月小說 太陽的血是黑的 /胡淑雯
編輯室報告 偵探蒸蛋 /蔡逸君
縫猿志 合趾猿、長臂猿 /西西
心靈解碼 讓愛飛翔 /林幸惠
封面人物 台灣推理小說的新視野:紀蔚然《私家偵探》
私家偵探 /紀蔚然
紀蔚然──台灣特有種偵探 /李維菁
穿街踏巷求一探──談紀蔚然的《私家偵探》 /既晴
我的偽自傳,一場驅魔儀式──楊照VS.紀蔚然對談 /劉思坊.記錄整理
張大春專欄:這就是民國
無復相從喪亂中
抗旱鐵牌
一縷孤魂夢不窮
大澤龍方蟄,中原鹿正肥
郁達夫的詩謎
童偉格專欄:童話故事 神打
劉克襄專欄:F23.5左右 不知前程的台車行──重走吳濁流...
購物須知
退換貨說明:
雜誌商品,恕不提供10天猶豫期退貨。
訂購本商品前請務必詳閱退換貨原則。